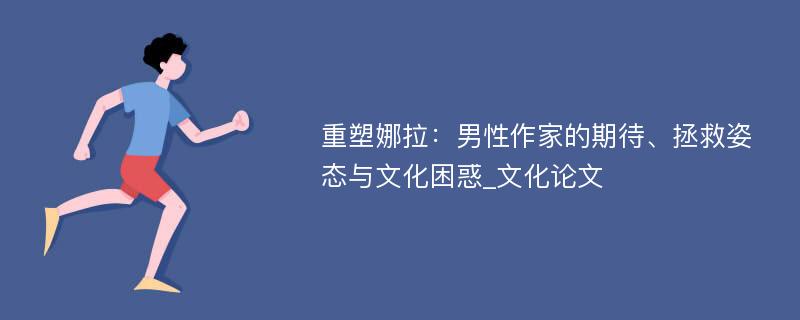
重塑“娜拉”:男性作家的期盼情怀、拯救姿态和文化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姿态论文,困惑论文,男性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较为阔大的文学和文化背景上,从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两个方面,考察八十年代以来男性小说家创造的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群落,探求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时代精神及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指出它在乡土小说史和妇女解放主题表现上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小说家们的男性中心文化心理造成的矛盾困惑及其对把握对象的负面影响,呼唤作家主体对更为博大的现代意识的求致和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超越。
当我们回视八十年代以来男性小说家们营造的女性世界时,一群出走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上月丢下老实憨厚、恪守土地的才才,与聪明能干、任性不羁的门门撑着木伐,从那奔腾不息的河上奔向山外的世界(贾平凹《小月前本》);黑氏在中秋月圆之夜,与心上人来顺逃离了殷实却无爱的家庭(贾平凹《黑氏》);香香扔下以自己的血汗和屈辱垒筑的家园,站在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车站(贾平凹《远山野情》);烟峰离开了因循保守的回回,投入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禾禾的怀抱(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水仙嫂锁上了那扇拒斥男人、关闭自己的大门,留下那把凝聚着无限压抑和酸楚的钳子,走向了外面的世界(李贯通《洞天》);杨梅姐以她对“九十九堆”礼俗的决然抛弃,在那板结的生活中撞开了一道裂缝,将震惊和惶恐留给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古华《“九十九堆”礼俗》);赵巧英几经徘徊,终于从她深爱着的孙旺泉的身边走开,告别封闭落后的老井村,奔向新的天地(郑义《老井》);邹艾以她全部的生命激情和生活智慧,挣扎着,奋斗着,探寻着作为一个女人走出盆地的路,几起几落,矢志不移,留下一串辉煌的失败的足迹(周大新《走出盆地》);麻叶儿在经受了愚昧恶俗和落后婚姻形式对她的情感折磨和肉体摧残之后,终于带着心上人海成留给她的新生儿,走出西府山,去寻找海成,寻找情爱的自由和生活的新天地(朱小平《西府山中》)……
这些女性形象动人心魂的踪影和心灵深处的足音,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感受和意义启迪。同时,她们作为主体的创造物,联系着男性作家们的精神指向和心灵期盼,而这又引领我们将这些女性形象置于更为阔大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情境的背景上加以端详和思索。
女人的出走,作为一个文学母题,早就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故事里——她先是背叛父亲,后是向丈夫复仇。而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中更是屡屡出现,从《十日谈》第二日故事“丈夫与海盗”中的女主人公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再到易卜生的娜拉,以至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都在复现着这一母题,贯穿其间的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和形成的人本精神和民主意识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嫦娥奔月这样美丽凄婉的故事;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下,古代文学中虽有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为生活原型的故事,但多置于引诱和被引诱的模式中加以表现并或隐或显地冠以“淫奔”的道德批判的帽子。直至“五四”新文学开始,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如一面旗帜飘扬于世纪之初的文学天空,女人们的出走才被赋予从西方文化中获取的现代意识而加以表现,于是,鲁迅笔下的子君、茅盾笔下的梅行素、叶紫笔下的春梅、巴金笔下的曾树生等等女性形象,作为“中国的娜拉”,在新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焕发着永久的光彩。无论是欧洲近代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民主意识、人的解放的光照下出现的出走的女人的形象,都体现了作家主体在文化转型、社会变革或某种文化自身矛盾加剧的时候,对新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呼唤与期盼,对女性的人格独立、性爱意识和生命自由本质的关注、体悟和表现。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男性作家笔下的出走的女性形象群落的出现,正是在与上述文学传统的深刻精神联系中产生并显示出自身的特质来。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群女性形象都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乡土社会,她们堪称为“中国乡土的娜拉”,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出走”的姿态和行为几乎专属于知识女性这一事实来说,这群出走的女人的形象体现了创作主体重塑“娜拉”的意图,这一意图又是激发于时代精神的感召。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以空前的迫切和强力,冲击了积淀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之痼弊的乡村社会,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因之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出走的女人的身影里正透露了此种变化的最富于感性的讯息,她们的出走标志着农业村社凝滞坚固的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土壤的大幅度松动乃至崩塌。
“人的行为常常是自我经验与人的社会角色期待之间不断冲突的结果”,①出走的这一行为选择正是女性自我经验对既有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抗争性表现,抑或是说,正是在这种抗争性表现中自我经验明晰起来,展示出来;这既有的社会角色期待实际上联系着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被规定应奉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准则,在这种严格限定的社会关系之外,妇女的“自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五四”以来的中国反封建运动和民主政治革命,虽然动摇了这种对女性的规定,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远远没有消除,而是流淌在乡土文化的血液里。当八十年代作家们从昔日政治权力话语构筑的女性解放的神话中走出,以更为自觉的现代意识和文化意识去看取农村妇女命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五个正值青春的女子在现实生存的极度压抑下走向美丽而神秘的死亡(叶蔚林《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我们看到了蓝花豹在他设的愚昧陷阱中无望的挣扎、身心的畸变与破碎(谭力、昌旭《蓝花豹》),我们看到了彩芳的青春和生命惨烈地吞噬于宗法专制的魔影(朱小平《桑树评记事》)……而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更为全面、深刻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无疑给乡土社会里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它不再是简单地诉诸政治革命、经济翻身或观念更新,而是渗透在文化整体的松动过程引起的生活变动的丰富感性之中。因而作家们通过这些出走的女性形象的创造,表现出对生活变革和文化演进的感应与期待。令我们注目的是,这些女性获得了在传统文化框范中不可设想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感。黑氏“先前以为女人离开了男人,就是没了树的藤,是断了线的筝,如今看来,女人也是人,活得更旺实”;邹艾喊道:“只要男人们分一半,凭啥只给我三分”;香香责问:“我就应该受作贱?受了作贱,又都是我的罪?”古华的《贞女》中桂花姐的抗争也同样在展示着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并且预示着走出爱鹅滩上百年前(应该是几千年来)青玉们的命运阴影。应该看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感的形成,正是这些乡土女性走出原有的生活怪圈和文化囿限的先决条件。
在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中,女人从来就是在与土地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在生育繁衍哺养后代中确定她们的存在。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物,作为财富的代表,其价值与土地一样,她们的生存地位也就在男人对土地的依恋中体现出来。而现在这些女人的出走,则象征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土地的剥离与挣脱;在这里出走的女人显示出与高加林、金狗们这些男性形象同样的意义。巧英离开孙旺泉,小月离开才才,烟峰离开回回,都在昭示着以土地为生存核心的生活方式的解体及其间蕴藏的文化范型的动摇。如果将作家们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创造同五十年代《创业史》中对徐改霞这一形象的创造作一比较,我们即可看到八十年代作家主体意识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吁求和对传统文明的自觉超越;柳青是将出走的徐改霞作为他心目中的新型农民英雄梁生宝的对立面来树立于作品中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评判的目光,使这一形象具有的文化冲撞的意味淹没于落后保守的农业文化意识之中。我们还看到,女人在为家族生养后代中获得自身价值这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价值标准,在出走的女性形象中也被动摇和否定。黑氏、香香、水仙嫂的生命展示中都没有生养这一环节;烟峰从回回那里离开,到禾禾那里有了孩子,这时的生养已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规定,而更多地成为一种新的生活的确证。杨梅姐、邹艾的母亲身份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表现,而没有为之增添价值衡量的砝码。作家们对笔下的女性生养价值的淡化和漠然,突出了她们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价值,同样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规定和设计的女性规范的冲决。
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的品行评价从来就是社会风尚最为敏感的神经,是一社会道德水平的风旗;而女人的出走作为一个文学母题的表现,其强大的震撼力就在于对既有的道德规范的冲破,对更合乎人性的道德规范的呼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家创造的出走的女性形象,也同样体现了道德反叛的勇气。这种道德反叛当然地蕴含在上面我们分析到的这些方面,因为一种道德规范总是联系着文化整体的,道德观念对人的约束从其本质形态和作用方式来说,总是寓于一定的民风习俗和文化承传之中。唯其如此,杨梅姐对“九十九堆”礼俗的绝决背弃,才给当地的人们那样的震动,他们愤怒地喊叫与咒骂,然后“又都不安地沉默着、惶惑着,仿佛他们身上,他们脚下,有什么东西开始移动了,破裂了……”。作家们以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的眼光来观照和表现这些女性的道德勇气,使我们感受到乡土社会在文化碰撞中前进的跫然足音。八十年代初祝兴义创作的《蒹葭苍苍》中的农村姑娘宋芸,已隐约透现出女性在文化冲撞中表现出道德冲撞的意向,但是,创作主体的道德评价模式阻遏了对宋芸行为抉择的深层意蕴的开掘,而代之以一个简单的破镜重圆的结局,文化差异与碰撞在宋芸和长锁之间造成的悲剧性情境被悄悄抹去,宋芸的旧情的破裂和新梦的萌生皆被绳之以道德的标尺而作出近乎漫画式的图解。而创造了出走的女性形象的作家们,放弃了道德评价的模式,将这些女性的行为诉诸文化审视和历史评判,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深层底蕴和人性的深度。邹艾在其走出盆地的几起几落中,许多行为正是在狡黠甚至不乏刻毒的表象下,潜隐着一股挣脱文化规定对女性的无情羁绊的力量,它使女主人公在爱与恨的交织中,手段与目的对立中、无理而合情的悖反中,展现出不屈的进取精神和果敢的挑战意识,女性解放的人性尺度和历史法则正寓含其中,文化困境的批判性表现也因此确立。
对这些出走的女人的道德勇气的表现,更为深入细致地体现在创造主体对女性主人公情欲实现和性爱意识的刻画与描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对女性的情欲和性爱的表现,往往是以扭曲的女性形象来展示的:要么是贞女,要么是荡妇;情欲和性爱在女性的生命常态表现中被迫处于沉默的位置。扭曲的两极女性形象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当代文学中男性作家对女性情欲和性爱的表现,而对乡村女性的刻画则绝少涉及她们的情欲和性爱的生命内容。八十年代出现的这批出走的女性形象却是以生命的常态向我们呈示她们对性爱自由实现的追求的。邵振国的《麦客》中的水香,因为麦客吴顺昌的出现,唤醒了她的情爱,使她意识到自己的青春与爱情的被剥夺,意识到一个女人正当的合乎人性的生活的被剥夺,感到“有一股顽强的力,在她的身上冲撞起来”,但是情欲之火在刚刚燃起的时候便熄灭了,熄灭于那植根于黄土地上道德规范,情感的骚动最终归于一种宁静的忧伤。而在黑氏的生命展示过程中,水香体验到的那股力,终于将她推上了出走的路途。黑氏体悟到的“女人也是人”,不仅意味着贫困的摆脱,经济的独立和尊严的树立,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女人对自己作为人的情感渴求的正视和情爱实现的追求。她和木犊共同创造了摆脱贫困压迫的生活,木犊却没能和她共同创造富于情感内容的生活。在木犊眼里,她只是个妻子,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机器的一个部件;觉醒了的黑氏对此不能忍受,而来顺的多情与体贴触动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欲的琴弦。随之而来的是道德感的压抑的力量和情欲实现的迫切要求之间的激战,小说以细腻而富有诗意的笔触,叙写了黑氏内心压抑的痛苦和悲哀怫郁无可诉求的情怀。这种生命的常态中聚积起的巨大情感力量,驱使黑氏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在这样的道德反叛表现中,黑氏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力得到了最为热烈的肯定。黑氏内在的情感追求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心灵活动的集中表现,它同样体现在香香这一形象中。香香的命运的浓冽的苦涩自有黑氏所不及之处,她身处试图以钱财和权力占有她的队长与以她来赚取钱财的丈夫这样两个男人之间,沦为一种物的存在,她为此痛苦、愤怒以至于麻木,吴三大的到来,以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品性和行为,以他对香香的尊重和呵护乃至神敬,唤醒了她沉睡的灵魂,激发了她生命的活力,热情而无畏地告别过去,奔向一种新的生活。也许贫穷、苦难和挫折在等待着黑氏和香香们,但不管怎样,她们将以真正的人的身份来谱写她们自己的人生历史的新篇章。《洞天》更侧重于女性对自律和自虐的茧缚的冲决。小说中方洞两边的对话描写和水仙嫂的心理、表情、动作的细节,传达了空灵神秘而又美丽忧伤的氛围。其间,石龙的男性的温暖气息融化了水仙嫂心中的坚冰,而他带来的外面世界的一线光亮,也渐渐驱散了她心中徘徊已久的云翳,她心灵深处情感的潮涌与喧腾终于将她推出了阴郁压抑的暗影。麻叶儿对母亲的告别、对西府山的告别,其动力就在于她对与海成之间纯洁自然之爱的追求,对山里女人被作为性欲发泄对象和生养工具的命运的抗争。小说将人物置于不堪忍受的蹂躏与欺侮的情境中,就更加突出了麻叶儿的追求与抗争中蕴含的生命力度。作家们对这些普通乡村女性情感欲望世界的深度感悟和生动表现,揭示了她们走向新生活的内在生命要求,这显示出作家主体以现代性爱观念意识对乡村普通女性心灵空间的观照、拓展和建构。这些女性,正因为她们的普通身份和生命常态,她们的出走才更富于冲击力量,也更能唤起情感的认同;而男性创造主体在对象化过程中对女性的真正的同情、理解和热切期待也从中体现出来,同时,这也表明作家们对妇女解放主题的表现,没有简单地求助于经济形态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更是突破了现代文学中形成的社会政治解放模式,从而为这一主题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审美意蕴。
前面我们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女性的出走这一母题的表现,似乎是作家们给知识女性派定的“专利”,乡土小说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女性,而八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如此集中地出现这样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群落,实在是创作主体从历史变迁、文化演进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变化获得了表现的契机。这一形象群落既是作家对乡村女性在新的社会境遇中自身变化的感应,更是作家们通过这类女性形象的营造表现出的对中国农村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改变旧的生存方式的热情呼唤。这关注和呼唤不仅体现在对出走的女性形象的创造上,而且体现于对欲走而未走,仍在传统文化的框桎与现代文明的向往之间徘徊彷徨,苦苦煎熬的女性形象的创造上,象前面提到的《麦客》中的水香就是这样,还有周大新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里的郜大嫂也是如此:对她们的命运中的痛苦忧伤的表现里,潜隐着作家主体“呼唤出走”的心灵期盼。
对上面所有这些乡村女性来说,同样有一个“走后怎样”的问题等待着她们(也等待着我们),而作家们似乎只是将她们送到出走的关口就不管了,没有给她们以未来的许诺或断言,顶多是将模糊的猜测放在我们的面前。这固然是作家们秉承的现实主义传统使然;我们的社会为走出的乡村女性提供的生存空间远远不及为走出的城市女性提供的生存空间来得阔大,作家们宁愿以热情关注的眼光去看待乡村女性出走的过程,而不愿虚构出她们走出后的美好前景,将它慨然许诺给人们。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我们会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分析一下男性作家们(如张弦、张笑天、刘恒、张一弓等)对“走出的”城市女性形象的创造,当会给我们以启发:这些作家从总体上来说,与创造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的作家们,有着同样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心理结构、同处文化冲突的时代、面临共同的文化转型的情境,因而在对对象的审美把握和表现上有着一定的趋同性。
尹影(张弦《回黄转绿》)、戈一兰(张笑天《公开的“内参”》)、华乃倩(刘恒《白涡》)、麦笛(张一弓《都市里的野美人》)等都是走出了家庭和观念羁绊的女性,她们显然地不同于黑氏、水仙嫂们的幽怨哀婉,显得卓厉风发、洒脱奔放、痛快淋漓。这些形象体现了作家们对城市女性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变化的敏锐感应和捕捉。但是这些形象无一例外地给人以断裂感,而缺乏那种气韵丰沛、鲜活灵动的美学享受。我们看到,尹影自身的心理误区不言而喻,可造成她梦幻破灭的南宇的那番谈话和对她前夫行为的不乏美化的描述,无非是在表明女人应该知道怎样适应男人的需要,做一个好妻子;戈一兰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将现代女性的意识与古代荡妇的品行拼合在一起,纳入作者从社会功利出发的善恶褒贬的框架中;华乃倩的主动与自主,因为被置于性欲实现受阻的逻辑关联中而丧失了女性心灵的丰富品质,于是她的行为在她自身成为对缓和心理焦虑的男性性偶像的寻找,又为周兆路开脱灵魂罪恶感提供了理由;麦笛似乎是无法以既有的文明规范去规定与评说的女性,她的充满自由感和创造性的“野气”,似乎是为现代文明的疲软症开出的一贴良药,但是小说后半部分对她与高梁的性爱关系的表现又落了俗套,她的求爱失败虽然照出了高梁的软弱,却也隐现着男性意识渗透其间的骄傲,且她失败后的表现又使我们对前面她所有的品行性格的展示产生了怀疑。
所有这些“走出的”女性形象的断裂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心理机制携带的道德眼光冲淡了审美眼光、男性中心文化意识阻碍了作家对女性具有丰富感性的生命整体的把握和对女性意识深层的开掘。这样的文化困惑同样表现在作家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创造中,只是在创造了“走出的”城市女性形象的作家们那里,对对象的近距离观照和平视使主体在把握对象的恍惚中突现了自身的困惑,而在创造了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的作家们那里,对对象的远距离观照和俯视,模糊了主体自身的困惑,使它深深地隐匿于形象世界的内层和细部。揭开这些内层和细部,我们将发现这些男性作家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写出出走后的乡村女性形象,与创造了“走出了”城市女性形象的作家们相同的文化困惑是最为内在的制约因素。
男性作家们在叙写乡村女性的出走时,心灵深处还在遥遥地等待着她们的回归。古华在《“九十九堆”礼俗》的结尾处写道:“或许他们之中也有人在想,在盼:杨梅姐还会不会回来到‘九十九堆’这个地方来?或许会回来,或许会有聪明的好汉子,去到山外岭脚她娘家,用在火灰坳上获准开业的‘为民灵药铺’作聘礼,用量米筒一样粗壮、葛藤一样坚韧的双手,把她背回来,抱回来!”这可谓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回归期待的最为直白的表露。《小月前本》的结尾也透露出同样的意向,作者欲以小月的纯然自在的传统文化人格,感应现代文明的召唤,同时沟通和弥合才才与门门之间的矛盾对立。《老井》中出走的巧英,其情感的根须则深深地维系在留守的孙旺泉的身上,这种潜在的情感的牵引,传导着创作主体心灵深处隐秘的消息:试图在古老的儒家文化品格与现代的精神指向之间获得某种平衡,甚至以前者消融后者。这种回归期待的意向在《走出盆地》中的表现或许更为隐蔽一些;与邹艾的三起三落的故事相平行的南阳的三个爱情故事,在其浓郁的地域风情的展示中渗透着强烈的宿命色彩,这固然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感染力,突现了女主人公奋斗不屈的生命力,但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对女主人公超越自身悲剧的否定和对她最终回到盆地的默认。《西府山中》麻叶儿说的“咱走,寻不着你大咱就回”,或许正可看作上述暗示的一个浅显的阐释。
上述这些潜在的回归期待心理内涵,对女人们出走所表现出的冲撞力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缓冲机制。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就会发现,黑氏和香香的出走,并没有明确的描写表明她们是走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引领她们出走的两个男人仍然标示着一个传统的农业文化圈。同时,在这些女性的道德反叛的表现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作家主体对她们的隐忍、善良、无私等品格的道德化表现。这当中当然有传统文化人格遗赠给我们的珍贵的素质,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女性在观念上的自我束缚却没有得到批判性的表现。象黑氏对信贷员之子的行为的一忍再忍中表现出的柔顺气质,作者的叙述渗透着同情却没有拉开一定的距离透视其间的麻木的心灵状态;信贷员一家倒楣后黑氏所表现出的仁慈宽容,亦显得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化;黑氏临行前用心良苦地给饭店更是给木犊找来一个胖姑娘,固然有其善良的因素,可是作者似乎也以此在黑氏的良心(传统人格的承传)与反叛(现代精神的裂变)之间获得某种平衡。《走出盆地》对邹艾为掩饰失贞历史,在新婚床单上划破脚脖子留下血滴的细节描写,也隐寓着作者的传统伦理规范的价值取向,同样的价值取向还体现在周大新的《屠户》中对珠儿的行为描写上,她毅然为死去的战士生下未婚先孕的孩子,其精神动力是为了不致使董家“绝后”。
这种在表现女人的出走时的回归期待心理,正是作家主体置身于文化冲撞造成的文化困境中的矛盾困惑的暴露。他们感应着现代化的进程,以从中获取的现代意识和人的解放的思想来看取乡村妇女生活形态和生命状态的不合理存在,呼唤着她们走向新的生活;而浓厚的乡土情感及浸润其中的传统文化心理又使他们本能地不愿这些女性走得太远。当我们将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置于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世界的整体联系中来看时,这一点就会更加显豁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个女子”、蓝花豹、彩芳以及张石山笔下的甜苣儿、杨争光笔下的甘草等一类女性形象的创造中,作家主体明显地秉持着苦难意识和文化批判意识。而在刘巧珍(路遥《人生》)、小水(贾平凹《浮躁》)、金兰(谭谈《山道弯弯》)等女性形象的创造中则又映现着创造作主体情感回归的意趣,这是因为急剧的文化冲撞造成的精神上的文化休克状态,驱策他们在联系着传统文化母体的女性对象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和救治;与这类女性形象创造的同时,作家们还设置了英英、石华、黄亚萍这类女性形象,在情感态度上与前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面这几类乡村女性形象所呈示出的矛盾状态,为我们理解作家们在表现出走的乡村女性时的回归期待心理,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在作家们的回归期待心理所蕴涵的文化困惑中,还渗透着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它往往体现为一种潜隐的性别优越感,使作家们始终保持一种对女性对象的居高临下的俯视位置。这种俯视的位置在反映妇女的苦难、呼唤妇女的出走的文学表现中体现为主体的拯救姿态。男性作家的这种拯救姿态由来已久。一个无可避讳而又饶有兴味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妇女解放”文学主题的旗帜下,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更多的是男性作家。这一拯救姿态由于社会政治解放模式的形成而得到强化,《白毛女》是其典型范式。但在这一姿态的激进面貌的背后,则是整个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强大引力场。我们知道,女性解放所面临的问题,不外乎她所置身的社会,与她相对的男性和她自身,而中国的妇女解放主题表现中男性作家的拯救姿态恰恰掩饰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阻遏了这一主题的深入开掘。我们看到,男性作家笔下,极少有《伤逝》这样对男性作出深刻反省和批判的作品。即使是茅盾,他所塑造的一系列“新女性”,在对她们的美貌和性魅惑的极力渲染中,在对她们的性的开放态度和放荡姿态的描述中,也透露出男性将女性作为审美愉悦的存在获得心理补偿、缓解心理焦虑的倾向;②巴金笔下的曾树生,虽被赋予叛逆精神和执着追求幸福生活与自我实现的品格,但在与汪文宣的对比中,在与汪母的纠缠中,有时也流露出作者从男性本位和男权意识立场上给予的道德谴责。③八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家们在创造了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丰富了妇女解放主题表现的同时,也不可避地承继了现代文学中男性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急剧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文化困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作家对出走的乡村女的回归期待的深层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决定了她们不可能将他们笔下的出走的乡村女性送得太远,那样的话他们的男权本位所保持的对对象的俯视位置和拯救姿态将显露出动摇和破裂的迹象。实际上这种迹象已在所难免,拯救的姿态已难以为继,男性作家们对“走出的”城市女性形象的创造给人带来的断裂感,就是最好的明证。于是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女权意识在中国女作家那里进一步自觉而冲击文坛,男性作家主体在对女性的表现中,有的走向了对女性生命本真状态的还原性表现,如杨争光、李锐等,有的则从拯救走向逍遥,如苏童、叶兆言等对历史陈迹和空白处的女性生活的表现;这种趋向当然不一定就是文学发展的标志,更不能代表妇女解放主题在男性作家笔下得以展开的方向,但它们无疑显示出摆脱男性作家主体在表现女性时的文化困惑的努力,尽管其中不乏从一种困惑状态步入另一困惑状态的危险。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以来男性作家对出走的乡村女性形象群落的营构,丰富了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和妇女解放主题的表现,同时它所呈现出的创作主体的复杂的心灵状态,构成女性形象世界意蕴阐释的内在依据和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表征之一,而其间所暴露的主体的文化困惑,无疑警醒和呼唤着男性作家对更为博大的现代意识的求致和对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超越。
注释:
①A·马塞勒等著《文化与自我——东西方人的透视》第7页,任鹰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②参见彭晓丰《茅盾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辑
③参见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