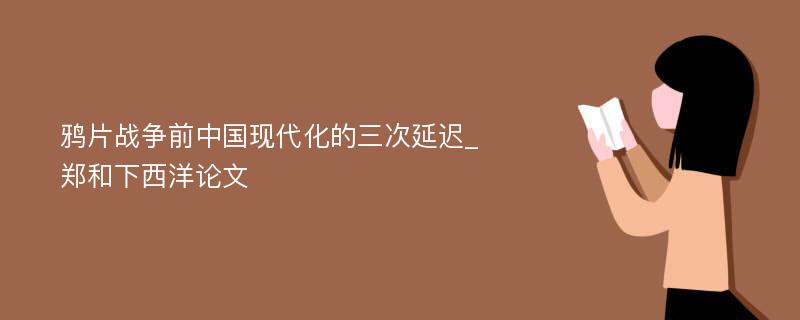
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三次延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历史至少给中国提供了三次走向世界、走向变革的机会,然而,这三次机会无一成为中国社会改造自我的动力。
一
最初的机会出现于15世纪初年,其契机是堪称航海壮举的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省浏河口的刘家港出发,远航“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领的舰队弘舸连舳,巨舰接舻,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人数则多半在2.7万以上。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33),郑和在28年中七下西洋。他每到一地,将“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明太祖实录》卷119)。诸国也“各具方物及兽珍禽等件,……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巩珍《西洋番国志·序》)。由此造成“三十余国,泥首燕都”,“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盛大气象。与此同时,大批华人藉郑和下西洋的推动力移居东南亚各地,形成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描述郑和下西洋产生的双向性影响时说:“明初,遣太监郑和等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意有买田娶妇,留下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达到了最高峰。
历史通过郑和下西洋向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建立在南洋的海上霸权,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在海洋贸易上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分庭抗礼。
然而,中国未能把握这一机遇。仁宗即位之初,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明仁宗实录》卷1)。宣德年间,尽管明宣宗再次派郑和“历忽鲁模斯等十七国而还”(《明史·郑和传》),但自此以后,郑和远航的壮举成为绝响。
当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在海面上消失,大西洋上却扬起了西方人远航的风帆。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州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成为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此三次远航,不仅在时间上迟于郑和下西洋,而且在船只的规模与出航的人数上也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这并不妨碍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完成划时代的业绩:“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3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从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
曾在航海上占有多方面优势的中国人不仅未能完成地理大发现,而且连在南洋的优势也保持未久,后来的西方人却以他们的远航“给我们一个新地球”。后人读史至此,每每不免唏嘘感叹。梁启超以富于情感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国民中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饮冰室文集·祖国航海大家郑和传》)郑和下西洋结局的惨淡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遗憾。
历史活动的直接动力首先是需要或利益。郑和下西洋既无向海外作殖民征服的意图,也不是为了开拓海外贸易,而是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企图通过“宣威海外”以示正朔的一种努力,诚所谓“振纲常以布中外,敷之德以及四方”(费信《星槎胜览·自序》),“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当然,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指出:明成祖“进行这些远航实际上有很多理由:寻宝——郑和的船只叫‘宝船’;显示他的权力和财富;了解帖木儿的和其他西亚蒙古人的计划;扩大朝贡制度;满足他的虚荣心和他对荣誉的渴求;以及使用他的宦官队伍”(年复礼等《剑桥中国明代史》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这些理由仍然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旦帝王的意图改变或兴趣转移,郑和的远航活动自然颓然而逝,无声无息。
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驱动力不同,哥伦布等人之所以百折不挠以向东方,是因为在其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15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旧的货币流通额已不再能容纳西欧商品流通量,“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1页)。于是,一股炽热的“黄金渴望”风靡欧洲,“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0页)。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神秘渲染的东方引起冒险家们的强烈向往。然而,金帐汗国的崩溃、土耳其的扩张、阿拉伯人的垄断,使欧洲与近东的贸易在15世纪末陷入困境。为此,西欧各国汲汲以求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以便直接深入其艳羡已久的远东财富之源。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迭相出现的,它们所表现的,是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而这样一种“生产的利害关系的影响”是远较任何政治意图或帝王欲望更为持久,坚韧的驱动力。
那么,西方航海者为了寻找财富与开辟新航道冒险犯难,中国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为什么除却宣扬国威,招徕远人以及为宫廷搜罗海外珍奇外,对于发展海外贸易与追寻财富一无兴趣?答案必须从大陆—海岸民族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的特征中去追寻。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自春秋战国始,逐渐形成以小农经营为主体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由于农业本身生产最必要的生活产品,较长的农业生产周期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闲暇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其结果造成千万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以此经济结构为基础,中国完全可以在对外封闭的情况下解决自我生存问题。诚然,中国历代也有海外贸易的活动,但这些活动都以输入奢侈品,输出手工制品为主,如汉代的海外输入,“多犀象、玳瑁、珠玑”(《汉书·地理志》)。唐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送郑尚书序》,《昌黎先生全集》卷21)。元代“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马可·波罗行纪》第609页)。而这些奢侈品都与民众的经济生活少有联系。蔽于这种既成的经济表象,唐以前拥护对外贸易的经济思想家如荀卿、桑弘羊、魏征、韩愈等大都从对外贸易可以招致国外珍奇品立论。元、明时代的经济思想家如卢世荣、丘浚、钱薇、许孚远等,虽然主张开放贸易,其目的却是为了打击出口走私,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商品能自足自用,无待于从“外夷”进口,“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经济结构上,明代封建统治者才得以在主持七下西洋的盛大航海活动时,把扩大政治声誉及追求奢侈品的要求放在首要地位,其后又可以毫不犹豫地中止远洋航海,甚至长期厉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
农业型自然经济的根深蒂固也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海洋观。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文化的基本倾向是重陆轻海、先河后海,对于发展海洋事业少有兴趣。周初姜尚受封于营丘滨海处,春秋时齐国依海而立,但姜尚与管仲只不过将海洋视为“通鱼盐”的处所而已,对于发展海运绝无考虑。中国古代的城市虽然发端甚早,但主要建筑于山地、丘陵与平原,海岸型的城市(如泉州等)直到汉唐才出现,而且久未发展充分。唐宋以降,航海业虽然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昔日几近于空白的海洋知识也逐日有所积累,但中国人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郑和下西洋乃至近代以前的海洋事业无以从文化心态上获得大规模展开的动力。
就世界历史格局而言,15世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西方,早期现代化如旭日喷薄欲出。在中国,明政府拥有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在此重要时刻采取从海洋向大陆撤退的退缩政策。其结果是丧失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政治、经济优势,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已开始进入印度洋,中国商人在南洋惨淡经营的贸易基地将在稍后一点的时间内被西方人相继夺去。《剑桥中国明代史》据此指出:“宣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剑桥中国明代史》第334页)中国失去了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西方人东进开辟了通道,西方世界开始向古老的中国进逼过来: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44年踏上澳门;1575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在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夺占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到达东方;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1784年,美国航船“中国皇后”号出现在广州。
对于欧洲人的东来,明代政府虽然深怀戒意,但尚能加以接纳。耶稣会士因而得以携带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其时最受欢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刺交欢,倒履推重,倾一时风流。”(陈仪《性学觕牴·序》)清初虽然针对台湾郑成功厉行海禁,但对传教士大致持欢迎态度,康熙皇帝以一代英主的气魄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后藤末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他自己则召传教士在身边讲授西学。然而,康熙帝与耶稣会士的和洽交往维持未久便因“礼仪之争”而中断,中国从此走向日益严密的文化封锁。
发生于康熙中叶的“礼仪之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转关。康熙帝因罗马教皇干预中国内政而禁教,其“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之语却透露出防范西方人扰乱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隐秘心理。雍正帝在这一问题上说得更为直率,他召见天主教司铎巴多明、冯秉正、费隐,谕之曰:“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坊表信札》:《耶稣会士通信集》第3卷363页)雍正时的清帝国实力强大,但此刻的帝王已开始考虑“千万战舰来我海岸”的可能性,并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有较为清醒的觉察。乾隆一朝中国国力达于高峰,对西方人的防范也更趋向自觉与保守。《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之句(《乾隆御制诗》5集卷26,丁未二《上元灯词》),道出了乾隆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原来的四口通商被改为“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夷商”在广州的活动,也受到清政府严密的管理与监视。
就在中国国门日益封闭之时,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
马戛尔尼来华恰值乾隆83寿辰,使团为此携带了不少体现英国乃至欧洲科学技术水平的礼品,如天象仪、天球仪、反射望远镜、太阳系仪、天文钟、大型战船模型等。然而,使团的更主要使命是为英国谋求在华商务利益,其中包括: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和丝绸的地方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的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其他地区;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从这些要求来看,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具有现代意义,或者说具有资本主义的扩张意义。当年马可·波罗的访问更多是“观光”和“猎奇”,并不意味着两个世界的冲突。马戛尔尼从踏上征程起,就意味着一场冲突的不可避免。
果然,使团一踏上帝国的土地,便碰上强固的壁垒,这一壁垒是由封闭的体制和封闭的心态结构而成。
体制封闭是中国封建统治最核心的部分,维持既定的体制被认为是保障皇帝权力的基本条件。乾隆帝对马戛尔尼的在华活动有多次朱批。在接待规格上,乾隆帝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在拒绝英国派常驻使节时,乾隆敕书说:“此与天朝体制不符,断不可行。”严峻的体制冲突发生在要不要三跪九叩上,当马戛尔尼拒绝这样的礼仪时,乾隆帝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开导对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尔自应遵守天朝法度。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派遣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原文见《中西纪事》卷2《滑夏之渐》)。来自西方的马戛尔尼当然不会懂得,在中国跪拜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礼仪,而是维系与稳定天朝体制的必不可少的“软件”。跪是对权威的认可,接受跪拜是尊者长者的权利。整个中国的生活秩序,就是在跪与受跪中形成。马戛尔尼拒不下跪,无异于亵渎和侵犯了天朝尊严,乾隆帝不能不因此感到恼怒。当然,马戛尔尼即使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并不可能完成他所担负的谋求英国在华商务利益的任务,但他的“无知”或“妄自骄矜”无疑使这一任务的有限实现也失去了希望。
和“天朝体制”密切联系的是“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是一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以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的狭隘文化意识。在这一意识的框架中,中国千古不变地享有施布文教的恩主的尊荣,外邦则只应无条件地处于恭谦臣属的地位。由此而导致使团与天朝官员的对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语境中进行。马戛尔尼作为“特使”来华,清朝官员偏要称为“贡使”“以符体制”。使团给乾隆帝带来了贺寿的礼物,清朝官员却断然纠正道:“不是礼物,是贡礼。”连英王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也被清朝官方的译员按中国人一厢情愿的理解,翻译得面目全非,似乎英王在向乾隆单方面表示效顺和吁请天恩,其中竟译有“向化输诚”、“进献表贡”等语。而乾隆给英王的敕文谕道:“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对于那个不肯向皇上跪拜的贡使马戛尔尼则宣称:“(该贡使)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清朝续文献通考》)
“天朝心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虚骄的文化心态。沉迷于此种心态中的乾隆皇帝及其臣属自然不会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有些许兴趣。使团向清朝官员介绍西方科技产品的优良性能,直隶总督梁肯堂等认为“未免过于夸张”,“是以……接见之时,并不问及贡品之制作”。英人谈及科技产品制造与安装的复杂,乾隆帝斥为“张大其词”。当马戛尔尼向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提出让随身卫队给他表演欧洲火器操练时,福大人漠然答曰:“这种军器操法,量也没有什么稀奇。看也可,不看也可。”(《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卷第27页)
乾隆帝一再强调并全力护卫的“天朝体制”以及弥漫于朝野上下的“天朝心态”集中地表现出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帝国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制》一书中指出,帝国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和维系一元化和中央集权的政体,以及统治者对于该政体的绝对权力”(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制》第10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封闭与停滞便是保持这种体制的不二法门。一旦从封闭走向开放,帝国庞大的身躯就会在变动中风化解体。对于中华帝国生存的机制,远道而来的马戛尔尼有所体悟。他在谈到中国消极抵拒通商政策时说:“彼等以为苛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16页,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远在欧洲的马克思更以一代伟人的精审眼力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页)
叩响中国之门的马戛尔尼一无所得地离开了中国,然而,他并非这次外交活动的真正失败者。马戛尔尼的来华带来了欧洲大陆现代文明的若干信息,他与清朝君臣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则是大英帝国向满清王朝华夷等级秩序提出挑战的最初信号。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乾隆盛世”的辉煌期,拥有雄厚的国力和政治整合力。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属能对马戛尔尼传递过来的信息作出敏锐的应变反应,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在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进取发展的机会。但是马戛尔尼带来的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所有信息却被乾隆帝和朝野士大夫们所忽略,人们仅仅把这位“英吉利贡使”拒绝行跪拜礼的行为理解为远方夷狄不开化的表现。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历史进取的机遇,而一个国际化的竞争时代迫在眉睫地来临。
三
从乾隆朝经嘉庆朝到道光初年,清王朝迅速从繁荣的顶峰跌入财政危机的低谷。财政危机的出现,虽与乾嘉两朝多次用兵有密切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盐、河、漕三大政运转失灵。
治理黄河,对清王朝来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清朝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北京在经济上需要依赖南方的支持,每年源源不绝地从南方各省运输漕粮到北京的运河因此成为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大动脉。然而,由于黄河、淮河、运河交织于苏北一隅,“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故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济运通漕”,以保证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定。
然而,清代治河,除靳辅、陈潢大有成效外,其余治河者皆遭失败,庞大的治河经费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漏卮。魏源概述其每况愈下的情势说:“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即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道光中)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国家全盛财富四千万之出入”,而治河“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魏源集》第365页)。治河之所以靡费巨大,除了黄河因自然因素确实难治、治河中屡有失误之外,加以“食河之餮”乘机贪污中饱,其结果是“万金虚抛”,河患愈亟。
漕运关系京师命脉,其意义也非一般。清代漕务实际上是政府自营的一个庞大的运输系统,为了保证这一系统运转正常,清政府专门设置了漕运总督。总督之下,各省又分设粮道。粮道在运河两岸设立卫所,保护漕粮运输。有漕粮的省份设漕运屯田,以供屯丁运兵。漕粮的大部分运到京城仓库,专供京师驻军食用;少部分运到通州,供皇室百官俸食。如此庞大系统,每年要耗费大量费用,再加漕运以运河为基础,运河沟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河淤则运阻,政府为确保运河畅通,又必须有巨额付出。而由收兑、起解到验收的无数浮收、勒索、舞弊,则使“军船行数千里之运河,剥浅有费,过淮有费,屯官催攒有费,通仓交米有费”(同上书,第426页)。所有这些费用,“丁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同上书,第424页)。“民生日蹙,国计愈贫。”(《清史稿·食货志》)
清代盐务是由政府主控,特许商人承购包销的一个垄断性商业系统。政府从盐业中获取大宗财政收入。道光年间的盐课收入便为国民经济收入总值的14.3%。然而,乾隆朝以来,盐政趋于衰敝。官引滞销,课额积欠,盐商疲惫,私盐猖獗,皆呈现严重局势。虽有江南、湖广大吏多次整饬,盐务仍如垂病之日延一日。
面对河、盐、漕三大政的严重弊端,嘉道朝上下深为忧虑,种种考虑集中于实现占国用之半的盐课完额、增额;稳定京师地区的漕粮供应;同时又避开治河、治运庞大的无效益的资金投入。承担这一改革任务的是道光朝名臣陶澍。
就知名度而言,陶澍当然不及林则徐,就对晚清政治生活的影响而言,陶澍绝不在林则徐之下。遗憾的是,陶澍其人在当代史著中长期湮没无闻。
陶澍改革,首先对河、盐、漕务三大政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性质加以区别。他指出:“河者,天事居其半;盐、漕则皆人事为之。”(黄彭年《陶楼文钞》,《林文忠公政书序》,癸亥刊本)所谓“天事居其半”,指自然因素起一半作用,而克服这一因素有待生产力的提高。所谓“人事为之”,则指盐、漕的弊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而“人事为之”所造成的弊端,也可以通过“人事为之”的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加以救治。
陶澍改革的重心置于“人事为之”的盐务和漕务上。其基本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官方主控作用中,引进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商营取代官营,变已成为生产进程阻力的官方主控作用为动力:在盐政改革上,陶澍于淮北盐区29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票盐”的核心内容是废除世袭专制的“纲商”或曰“窝商”,变盐业官营为商营,实行盐业自由贸易。国家只收税利和场价。与此同时,简化销盐手续,降低票商承销单位额,排除承购和运输过程中的超经济强制。在漕务改革上,陶澍一方面改变运道,“以海代河”,另一方面废除官丁督运制度,“以商代官”,把漕粮运输业务由官方委托给吴淞沿海一带的船运资本家。
漕粮海运与票盐法一旦施行,即在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的作用下,表现出其优越性。漕粮海运的结果是“不损一人一舟”,“每石(漕粮)费仅数十金,视河运省费固倍”,沿海沙船业的发展亦因此获得推动力,据《上海县志》载:“去秋(道光六年,1826)增造(沙船)三百余艘,以备今岁海运之用。”金銮所撰《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也说:漕粮商运使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因此,他们“皆踊跃过望”,对漕粮商运持积极欢迎态度,并将此举视为发展自身事业的契机。淮北盐区实行“票盐法”也大获成效,由于“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魏源集》第439页),食盐成本大为降低。“(旧盐法)每引成本已达十余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盐……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魏源《淮北票盐记》,道光《淮北票盐志略》首卷)。“盐法成本既轻”,盐价也随之跌落。包世臣则报道说:“倡改票盐以来,……洪湖以南食盐居民,率出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闻见。”(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四《上陶宫保书》)由于盐价降低,“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私盐自禁。淮北盐业一时间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清史稿》卷123《食货四》)长期无法解决的盐课拖欠问题亦迎刃而解:“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三纲。澍承积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余,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以前滞欠,且割淮悬引。”(《安化县志·陶澍传》)
因引入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和法则而取得“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巨大效应的陶澍改革,向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提示了改造自然经济总体结构,增强经济实力和民族内聚力的有力手段和原则。深化与扩展陶澍型改革,成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自主走向早期现代化的最后一次机会。令人遗憾的是,陶澍的漕运、盐法改革固然成功,卒因涉及一个庞大社会集团的封建利益而无法往深广两个方向发展:试办海运成功后,陶澍满怀热情请求将江苏苏、淞、太二府一州漕运永归海运,并先后拟定海运章程6条、8条奏呈,道光帝却对陶澍的计划不予批准。道光七年,漕运又恢复了绵延400多年的河漕制度,直到道光二十四年,运河又阻,京仓积粟“动放无存”,道光帝才再次下令“复行海运”。两年后,又决定苏、淞、太二府一州正式改由海运,此时距陶澍初行漕粮海运已有20年。淮北盐区推行票盐法虽大获成效,道光帝也迟迟不支持陶澍向淮南推广,直到道光二十九年,湖广总督陆建瀛方因武昌盐岸失火依魏源之议改淮南票盐。其间已相距19年之久。此时的中国社会因西方的武力侵入与挑战,兴奋点与变革焦点已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标签:郑和下西洋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郑和宝船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论文; 道光论文; 乾隆论文; 陶澍论文; 乔治·马戛尔尼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大航海时代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