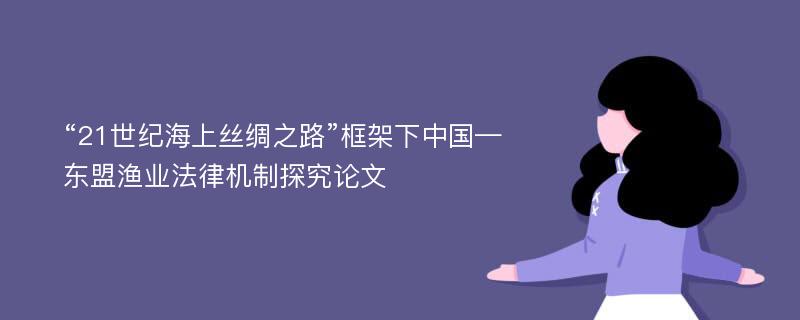
“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探究
陈盼盼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东盟的渔业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分析和梳理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现状,分析了现有框架下的国际公约效力与功能局限,以及区域渔业合作重经贸、轻养管和制度规则缺位等弊端。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对渔业法律机制的需求,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的完善路径:制定中国—东盟渔业合作专门性公约,对渔业资源开发及养管起指导性作用;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渔业合作协议,为渔业资源合作提供可接受的合作途径;稳固中国—东盟渔业合作支持机制,通过多元化渠道夯实合作基础。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渔业合作;法律机制
1“海丝路”下中国—东盟渔业合作意义
渔业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蛋白质来源,由于各国之间巨大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与渔业资源相关的国际博弈愈发激烈。国际上围绕渔业资源开发与管理展开的谈判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渔业领域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当前,渔业问题已处于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的战略高度。我国远洋捕捞地域广阔,因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养管频繁与周边国家产生纠纷,尤其是在南海地区,“六国七方”[1]的局面使深入推进渔业资源合作面临着重大阻碍。面对渔业资源持续不断的恶化,我国适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路”)的倡议,致力于打造一个绿色、合作、共赢的平台,为中国—东盟之间的渔业资源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海丝路”是我国2013年提出来的,出发点主要基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我国提出了该战略构想。2015年我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当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活力和吸引力[2]。
总之,学术论文摘要作为信息来源,是论文学术质量的反映,成为介绍或了解国内外学术成就非常有效的途径。学术论文摘要的翻译应遵循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应按照英文摘要的普遍标准和特征来进行翻译。
《愿景与行动》倡导兼顾了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坚持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建设原则[3]。同时,拓展农林牧渔业、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等。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统计,我国与东盟10国渔业资源丰富,海洋捕捞量位居世界前列[4]。在“海丝路”框架下,我国应积极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建立资源名录和资源库,协助编制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同时,加强渔业领域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也是“海丝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但渔业法律机制作为其中的构成部分并不完善,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已成为合作法律机制构建的重点领域。
调查显示,企业融资贵主要原因是中间环节收费高。综合来看,企业需要支付5%~6%左右的担保费、评估费及过桥费,已接近利率水平,比浙江省平均收费高2~3个百分点。政策性担保机构业务量较少,而商业性担保机构担保费用基本超过2.5%;同时,企业反映,在林权评估领域,超过95%的项目由非专业的评估公司开展,且一般按林权评估价值额的3%~6%收取费用,评估费过高。
2渔业法律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现状
工作流的流转采用了事件驱动机制。事件驱动机制在一个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能够及时通知其他对象,使其根据事件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反映。在这里,一旦活动发出“准备就绪”事件,过程实例对象就立即运行活动的执行程序;程序执行完毕(或手工执行完毕),活动又发出“运行完毕”的事件,过程实例对象在收到此消息后,执行路由程序,找出下一个活动节点,并将其状态有“原始状态”改写为“准备就绪”,重复前面的过程[3]。
双边层面:在双边层面方面,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主要见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简称《中越渔业合作协定》)、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简称《中印尼渔业合作备忘录》)、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农业部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简称《中菲渔业合作备忘录》)。上述双边渔业合作文件在序言中均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促进渔业合作的目标,仅在措辞上有所差异。2003年,越南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渔业及水产养殖协定》,以加强两国在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和渔业管理等方面的合作。2006年,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签署备忘录将渔业合作协议延长至2011年,两国合作项目有开发水产养殖业、海洋渔业捕捞、捕捞后期合作、水产品加工、海水养殖环境保护、打击非法捕捞等。2010年6月,越南与菲律宾签订了渔业合作协定,双方同意开展水产领域的合作,协助渔民在海上捕捞和海上搜救工作。2011年越南先后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水产开发、养殖和水产贸易往来、海产捕捞等达成协议。
目前,在我国与东盟国家参与的区域渔业合作机制中,对渔业信息传播、合作活动开展、渔业相关培训、当下渔业问题与解决措施的提供、渔业相关问题的研究等采取了相应措施,但针对渔业捕捞监管的船旗国责任、渔业资源的评估、渔业纠纷的管理、能力建设和渔业活动的监管领域并未采取明确行动[13]。原有的合作方式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也因为在相关管理层面的空白和缺失而导致渔业合作的可执行性和效率降低。因此,我国与东盟在开展渔业合作时要积极对现有国际渔业管理规则进行消化吸收,纳入双方渔业合作的协定中,促使国际规则区域化,以提升本区域渔业合作的规范标准。另一方面,对现有已达成的有关渔业合作的规范进行细化,强化双方的制度安排和合作的法律框架。如在《框架协议》和自贸区“升级版”的体系内,就渔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关税幅度等进行调整;在东南亚渔业中心区域的渔业资源管理的基础上纳入“中国式”因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行为守则》、《港口国措施协议》、IPOA-IUU、《鱼类种群协定》、《遵守协定》等各国已加入并批准的全球有关渔业管理和共同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国际规则“区域化”,以充实双方的渔业合作规则。
全球层面: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这部“海洋宪法”于1982年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与东盟国家相继签署批准成为《公约》缔约国,并依据《公约》赋予的权利管理海洋事务[5]。《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有有关沿海国权利、义务的第56条,针对渔业资源流动性和跨界活动特点的第63条、第64条,争议海域第74条[6],半闭海制度中的第122条、123条等均规定了沿海国/当事国的合作义务。我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海域渔业合作过程中依据《公约》的有关规则,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加强双方合作。②FAO主导下的国际渔业法律规则。FAO作为全球管理渔业资源的专门组织,为国际渔业的保护和开发做出了突出贡献。形成的公约、规则和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FAO主导下中国—东盟在渔业领域上合作的法律规则主要有1993年的《遵守协定》、1995年的《鱼类种群协定》和《行为守则》、2001年IPOA-IUU、2009年《港口国措施协定》等法律文件。这些文件一方面完善了《公约》中的有关渔业条款,加强了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强化了船旗国、港口国的义务,加强了对捕捞活动的管理,强调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的作用,以促进区域管理合作[7]。③《生物多样性公约》。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增加,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逐渐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重要议题,其中尤其关注到海洋渔业可能导致的对海洋生物资源过度捕捞的问题[8]。《生物多样性公约》呼吁缔约方采取可持续的渔业活动,与FAO等机构和其他国际、区域间组织开展合作,加强对IUU捕捞行为的管理,请各国削减或取消对渔业和渔船的补贴,取缔各种不利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强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④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与贸易的相关规则。基于WTO部长级会议授权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4.6项的要求,WTO就减少和消除渔业补贴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2007年11月,多哈回合渔业补贴规则谈判小组主席分发了一份文本草案,并建议将该文本作为SCM附件八。该文本中包含了禁止性补贴和非禁止性补贴,其中禁止性补贴包含“提供给任何从事IUU捕捞的补贴”。如何完善WTO渔业补贴政策的适用性,我国与东盟国家有着不同的立场,这些不同立场和现有的不同渔业管理框架是缔结渔业补贴贸易相关协定的主要障碍。2018年11月,WTO第11届部长级会议声明文件力求在2019年完成文本谈判。当前WTO渔业补贴谈判主要集中在包括对IUU捕捞活动的认定、触发纪律和过度捕捞、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性和现有的WTO法与其他国际法律框架的新规则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等问题。
目前,规制中国—东盟渔业领域的法律制度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形成专门针对渔业开发和养管的区域协定,但国际社会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均有涉及我国和东盟国家在渔业领域的全球规则、区域规则和双边国家实践。
2.2 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纵观中国—东盟之间的法律制度,尚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渔业领域的条约,使中国—东盟之间的渔业合作法律制度呈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制定系统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在中国—东盟之间成立渔业合作的管理机构,可有效规制合作和渔业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协调能力弱,捕捞标准、渔具渔船、保护措施等方面法律规则的模糊性等问题,同时更有利于及时有效解决双方间的渔业纠纷,增强双方的互信,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从国内出发而言,在我国渔业产业改革和“十三五”计划实施的关键时期,面对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需求,应抓住机遇,完善我国渔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
渔业资源日益恶化,使现有的政策和法律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渔业资源养管和开发的形势需要。中国—东盟渔业领域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有存在以下缺陷:①国际公约效力与功能的局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缺乏针对渔业合作具体的法律制度,仅从宏观层面规定了国家间的合作。不论是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权利与义务,还是争议水域或半闭海水域,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渔业合作均无专门条款可循。尽管FAO主导下的国际渔业法律的部分规则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但条约效力具有相对性,其约束力和制约的范围仅限于批准加入的成员国,不利于合作的稳定与持久。《生物多样性公约》虽然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但由于缺乏对违反行为的有力制裁措施,加之并未完全包含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因此无法保障该公约的有效贯彻落实。WTO争端解决机制一直为各界所称颂,但涉及渔业领域的规则尚处于谈判之中,并未形成确定的法律文本,且局限在贸易领域,难以为中国—东盟渔业领域的合作提供全面保护。国际公约或条约中的涉渔规则多为宏观性和原则性规则,大部分规范都不具有强制性,并且国家既可通过默示行为或缔结条约等明示行为限制国际法规则的行使或设置干预程序,也可通过保留来限定条约的效力范围。虽然该规定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行使,但对中国—东盟在渔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一方未能有效履行约定,对所造成的损失与后果缺少追责的依据,无法充分发挥国际法律制度应有的作用。②区域渔业合作重经贸、轻养管。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东盟间并没有直接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也无统一的渔业合作管理机构。区域渔业组织在成员的覆盖范围上仅涉及到部分东盟成员国,现有可适用于中国—东盟渔业领域的法律机制仅局限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之中。《框架协议》主要集中在渔获物的贸易方面,较少涉及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框架协议》在序言中表述,“期望通过本项具有前瞻性的协议,以构筑双方在21世纪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具体目标在“降低壁垒,加深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同时,确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将在各缔约方之间创造一种伙伴关系,为东亚加强合作和维护经济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机制”。2016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规定了渔产品的关税优惠等方面的情况。从序言中的表述来看,《框架协议》主要旨在深化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两者的经济发展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但在渔业方面的表述中,仅笼统强调加强渔业合作,几乎未曾涉及到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强化具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同时,中国—东盟之间缺乏统一全面的渔业合作法律机制,导致切实有效的规制双方渔业资源开发与养管机制缺失。渔业资源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源,一旦遭到破坏,不但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期,而且对海洋生态链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渔业资源开发及养管依赖于我国与东盟国家实现渔业资源互利互补的客观需求,除对渔业资源进行科学评估、有效管理外,还需要有效沟通与协调的专门机制,避免因无序开发或不当养管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渔业领域的健康和持久合作。建立兼具可行性和有效的渔业合作机制,应当是在“海丝路”框架下渔业合作机制的构建的目标。③具有针对性制度的规则缺位。中国—东盟渔业合作问题不仅深受南海主权声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东盟国家内部渔业产业发展不平衡、渔业资源禀赋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有效推进中国—东盟渔业合作,需要中国—东盟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商讨,以促进渔业领域统一条约的制定。
3完善中国—东盟渔业法律机制的路径
3.1 中国—东盟渔业资源养管专门性条约
为有效推进“海丝路”建设,深化中国—东盟渔业领域合作,可由我国与东盟共同参与制定“海丝路”框架下渔业领域合作专门性条约,吸收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经验,协调我国与东盟国家渔业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结合现行国际法治中有关渔业领域的国际原则、规则与制度,力求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东盟利益诉求的渔业合作条约。
中国—东盟渔业合作条约的定义应对“海丝路”建设起到指导和统领作用,在不违背现行国际法法治规则的情况下,基于双方协商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渔业合作法律制度。条约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①统筹总领——统一管理机构。条约应确立中国—东盟渔业合作的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渔业资源开发与养管规则适用的解释,并负责渔业领域合作相关问题的处理,参与协调双方涉鱼纠纷的协调,统筹相关事宜。②权利义务——内容具体系统。条约应系统规定渔业领域相关的法律原则,包括鱼类种群调查、数据收集、捕捞总量、鱼类资源保育、水产养殖、渔产品贸易等内容在内,为双方提供涉及整个渔业价值链形成普遍的、可接受的法律制度。此外,细化与发展渔业资源保育的规则、标准和方式。③保障机制——信息共建共享。条约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换平台与机制,确立合作机制理念。渔业信息化是应用信息技术对渔业科技、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提升和改造的动态过程,保障中国—东盟国家之间在涉方面信息的共享与通畅,在此基础上确保渔业资源开发和养管措施的有效贯彻落实。④争端解决——在渔业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由于南海海域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如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海洋法法庭等不易直接纳入渔业法律合作规则之中。考虑到南海地区存在的主权与划界争议,我们认为可分类解决相关的渔业争端。首先,涉及水产养殖、产品加工和贸易的争议,可直接纳入《框架协议》中解决;其次,由海洋捕捞引发的争议,可通过由各方代表组成的渔业委员会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三,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争议,由中国—东盟各国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
3.2 完善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渔业协议
区域层面:①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我国与东盟之间有关鱼产品贸易的相关规则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升级版的框架下进行了规制,范围涉及与贸易相关领域的鱼产品合作等。《框架协议》在序言中规定“期望通过具有前瞻性的《框架协议》,以构筑双方在21世纪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具体在“降低壁垒,加深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同时,确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将在各缔约方之间创造一种伙伴关系,并为东亚加强合作和维护经济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机制。从序言中的规定来看,《框架协议》的主要目标是在于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使两者的经济发展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框架协议》早期条款第6条第3款规定了产品范围,其中鱼产品位属之列。第二部分第7条其他经济合作领域方面,第1款规定了农业是5个优先合作的领域[9],第2款规定了在优先合作领域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渔业、知识产权、环境等方面。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渔业管理面临着跨国性和区域性挑战,致使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些区域多边合作的组织,主要有:亚洲—太平洋渔业委员会(APFIC)[10],根据1947年FAO大会第三届会议的建议于1948年11月设立,通过发展、管理捕捞和养殖活动等促进水生生物资源的全面保护。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成立于1967年的政府间组织,宗旨是通过转让新技术、科研和信息共享等活动,合理开发和管理该地区的渔业资源,为人们提供安全可靠的渔产品,减少贫困。该组织成员包括东盟10国和日本[11]。InfoFish成立于1981年,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FAO的试点工程。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逐渐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组织,专门针对亚太地区和吉隆坡其他地区的渔业行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12]。亚洲渔业协会于1984年5月成立于菲律宾罗斯巴诺,宗旨是促进亚洲渔业科学家和技术员相互支持和合作,传播保护和利用水产资源的重要性。印度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联合国发展项目和粮农组织南海渔业合作发展项目以及政府间自治组织—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等的基本功能都涵盖了区域渔业管理的需要。③东盟—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战略伙伴(ASSP)。该伙伴关系正式成立于2007年,1998年东盟与SEAFDEC建立了渔业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了ASEAN-SEAFDEC渔业磋商小组,目的在于协助东盟建立一个“东盟地区渔业管理机制”,推动东盟各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建立共同立场。事实上,东盟已将SEAFDEC作为他们主要的渔业技术咨询单位。2009年,SEAFDEC协助东盟举办了“东盟渔业磋商论坛”,并在部分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并制定了责任国,如打击IUU由印度尼西亚主导,促进捕鱼能力和负责捕鱼行为由马来西亚负责等。此外,ASSP还在一些IUU多发海域开展了次区域合作,如泰国湾和安达曼海。
对于东海天然气而言,通过上式计算得出Δη=10.74%,即:传统燃气锅炉每燃烧1Nm3天然气产生的水蒸气带走的汽化潜热占燃气低热值Qdr的10.74%,这意味着在传统锅炉中,有很大的热损失是由于水蒸气中所含有的汽化潜热造成的[13-15]。同时,该比例可用来表示若将该部分汽化潜热利用,可以使锅炉效率提高的百分比。
3.3 稳固中国—东盟渔业合作支持机制
渔业是东盟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同时,渔业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对东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国家和区域经济以及数百万区域贫困人口的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区域合作的一个重点。我国陆地资源已基本充分利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水域(海洋、江河、湖泊)资源,因此对双方而言,渔业合作是亟待推进的。在政治层面,中国—东盟关系迎来新的“蜜月期”, 2017年发布的《东盟外长会联合公报》描述了中国—东盟关系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时中方提出未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7大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赞同和认可,包括共同制定“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此外,还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框架,明确了下一步推进具体案文磋商的积极态度。
在“海丝路”建设的新态势下,渔业合作可依托现有的资源和途径,在“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支持。“海丝路”建设不是单一机制主导之下的发展设计,而是贯彻开放合作、包容发展的合作原则。因此,在政府先行合作的成果基础上,应充分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组织,以及亚太渔业委员会、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法人实体等的合作,支持建立与多方利益相关的方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组织、民间社团、工商界等广泛参与到渔业合作中。
4结语
当今世界,合作共赢是发展的主旋律,“海丝路”的倡议促使中国—东盟在渔业方面开展合作,追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以稳定、深化中国—东盟渔业合作为目的,建立渔业合作法律机制,设立渔业管理机构,对协调渔业合作过程中我国与东盟以及东盟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吸收借鉴以FAO为主导的国际渔业法律机制、区域性涉鱼规则和双边协调机制,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渔业合作协议,努力促进中国—东盟渔业领域重要法律制度的确立,以保障渔业合作持续、健康、稳定推进,最终实现“海丝路”建设下的中国—东盟渔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全红霞.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法律机制探讨[J].理论月刊,2010,(10)∶161-163.
[2]新华网.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6/c-1124420373.htm.2019.
[3]国务院.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EB/OL].http://www.qstheory.cn/2017-05/12/c_1120962775.htm,2017-05-12.
[4]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R].罗马:2018∶8-10.
[5]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J].中国法学,2012,(6)∶68-77.
[6]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J].法学研究,2003,(3)∶147-160.
[7]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8]银森录,郑苗壮,徐靖,等.《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谈判焦点、影响及我国对策[J].生物多样性,2016,(24)∶855-860.
[9]商务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B/OL].http://fta.mofcom.gov.cn/dongmeng/dongmeng-special.shtml.2002-11-04.
[10]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亚洲及太平洋渔业委员会[EB/OL].http://www.fao.org/asiapacific/apfic/zh/.2019-08-08.
[11]SEAFDEC.About SEAFDEC[EB/OL].http://www.seafdec.org/.2019-08-08.
[12]INFOFISH.About US[EB/OL].http://infofish.org/v3/.2019-08-08.
[13]Jenner C J,Tran Truong Thuy.The South China Sea----A Crucibl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r Conflict-making Sovereignty Claim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Research on China -ASEAN Fisheries Legal Mechanis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
CHEN Pan-pan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the fishe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occupied a pivotal position.By analyzing and combing the status quo of fishery legal mechanism between China and ASEAN,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under the existing framework,the disadvantages of regional fishery cooperation,such as emphasizing economy and trade,neglecting management,the absence of specific institutional rules,etc.,and combine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with fishery legal mechanism needs,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perfecting China-ASEAN fishery legal mechanism under the framework:Formulating a special convention on China-ASEAN fishery cooperation,which would play a guiding role in fishery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perfecting bilateral fishery cooper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to provide acceptable fishery resources cooperation.Means of cooperation,to consolidate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China-ASEAN fisheries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through diversified channels.
Key words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fisheries cooperation;legal mechanism
doi: 10.3969/j.issn.1005-8141.2019.12.012
中图分类号: F307.4;DF9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19)12-1508-05
收稿日期: 2019-05-13;修订日期: 2019-10-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陆海经济一体化增强我国在南海维权手段和能力研究”(编号:18VHQ012)。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简介: 陈盼盼(1991-),女,安徽省亳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海洋法、国际渔业法律制度。
标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文; 渔业合作论文; 法律机制论文;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