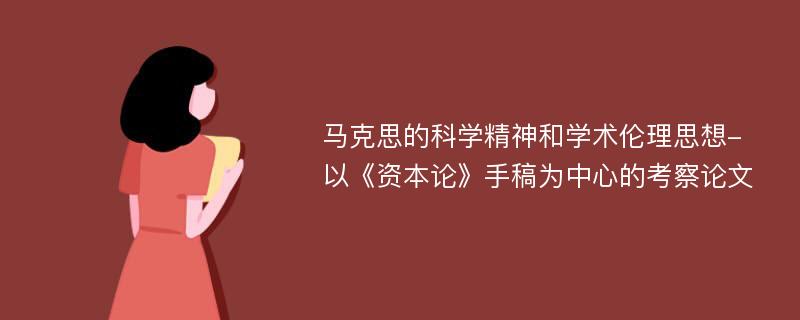
马克思的科学精神和学术伦理思想
——以《资本论》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孙要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蕴含了丰富的学术伦理思想。主要包括:肯定科学研究上的“诚实”和“斯多葛精神”,认为科学研究可以“犯错”而不能“犯罪”,厌恶学术剽窃或生产“拙劣的仿制品”,反对把学术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的行为,反对按照个人好恶偏好任意裁剪科学历史或“在理论上故弄玄虚”。马克思的学术道德观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特殊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坚持科学研究中的大公无私精神,并将学术原创性放在首位,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对科学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学术伦理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和“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阅读了有关经济学的著作1500余种,写了大量笔记与摘录,在批判性思考过程中也有许多评注,并写作、形成了大量手稿。马克思对各种著作的阅读是仔细的,摘录是详细的,评注是严谨的,批判性思考是深刻的。他汲取了所读著作中的不少思想精华,特别是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创造了劳动价值论,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时也发现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牢固基石。除了精心研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马克思对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哪怕是他厌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也作了细心摘录,并做出了自己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有的人他甚至有非常尖锐的评价。在马克思眼中,他所阅读的著作是一个巨大的谱系,包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如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的作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的著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过程中以李嘉图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政治经济学者,以及庸俗经济学者的著作。《资本论》的创作正是在吸收借鉴、批判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就批判方面而言,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批判是为了汲取,并升华为科学的理论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另一些学者的著作,凡是其中有益的论点,马克思也多有借鉴,批判性地加以吸收。而对于一些无产阶级反对派的政治经济学者以及庸俗经济学者的著作,马克思则是以批判的眼光阅读、评价之。马克思对后面这类人的批判是直率的,涵盖的方面非常广泛,既包括阶级立场批判,也包括具体观点批判、历史事实批判、科学研究方法论批判,同时包括学术道德批判。透过《资本论》手稿,我们不难把握马克思的学术道德观,尽管它散见在手稿的各处并不成系统。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资本论》手稿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令人深受启发。然而,学界对《资本论》手稿中蕴含的学术道德观关注却不够。本文拟对手稿中蕴含的学术道德观进行初步发掘,略作梳理和评价,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肯定科学研究上的“诚实”和“斯多葛精神”
在《资本论》手稿中,可以见到马克思对科学研究上的“诚实”和“斯多葛精神”的赞扬。这主要是体现在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著作的摘录中。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和最后完成者,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峰,对后世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所处的时代属于工业革命快速开展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受时代大环境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他希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发展,进而人类社会就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1]127。因此,他认为,生产效率提高、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根本评价标准和理想目的,生产力尺度是判断一切政治经济学说体系的最终尺度。
在李嘉图看来,为了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牺牲地主阶级、无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有社会阶级及其利益都应该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让步,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了工人的人的再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李嘉图1815年在伦敦出版的《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第二版)一书,马克思认真研讨过并作了较详细摘录。该书提出,“如果因考虑到某一个阶级而使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受到阻碍,我将感到非常遗憾。”[1]135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贵族是不劳而获的旧式阶级,是与资本主义尤其工业资本发展相对立的,侵占的是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是社会发展多余的赘疣,土地所有权需要在资本主义方式下重新进行改造。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摧毁旧式土地所有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对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李嘉图将他们看作同机器、牲畜或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而且无产阶级只有作为商品来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促进“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最后形成。对于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摧毁旧式土地所有权、会把无产阶级视为同机器、牲畜等一类商品,马克思认为他这样的思考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卑鄙之处”[1]129。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的彻底分离而导致劳动力必须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基础上的,而在李嘉图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来就有而且一直存在下去的。从这点来说,李嘉图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将无产阶级贬为商品并不属于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实。
中方报道中的“认可”资源的使用频率远高于美方,双方经常以此来表明外部声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从而缩小对话空间。例如:
马克思看到,李嘉图经济理论体系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李嘉图也持有同样的毫无顾忌的“残酷”态度。1822年李嘉图在伦敦出版的《论农业的保护关税》(第四版)一书中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可否认会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损失掉。但是,拥有资本或保持资本是目的呢,还是手段?毫无疑问是手段。我们所需要的是商品的富足〈一般财富〉,如果能证明,牺牲我们的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增加用于使我们享乐和幸福的那些物品的年生产,那我们就不应当为我们的资本的一部分遭受损失而发牢骚。”[1]136从经济学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将科学技术和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过程导致劳动生产率经常性的提高,导致工业资产阶级的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大幅贬值。李嘉图认为,对此我们也应该持欢迎而不是排斥的态度,这是因为资本毕竟是手段、途径,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财富本身就是目的,手段在目的面前没有独立价值。在李嘉图看来,如果说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固定资本贬值一半,这实际上就是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生产力发展面前,他对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是“平等相待”“毫无偏袒”的。根据马克思的见解,与其说李嘉图的学说符合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倒不如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人类社会生产的利益是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如果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发生了矛盾,李嘉图也会像在别的场合对土地贵族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那样残酷地、毫无顾忌地反对工业资产阶级。
马克思本着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从社会中隶属于各个阶级的人只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观点出发来对待李嘉图的理论。李嘉图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生产中心主义”“发展中心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1]128“李嘉图的冷酷无情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 ”[1]127
自然教学资源的分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方面国家干预分配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和援疆计划一样只要有所调控还是可以保证边远山区的小学生们也能享有到一样的先进的教学资源,可以使用到多媒体教学,能够得到体音美的设施配件,可以全面发展。至于优秀师资的调配国家现在既然已经做了学生就近入学的调配,就应该继续尝试保证优秀师资的分配,这样就不会出现学生不就近入学而要花大力气跑远距离趋向名校里的名师。
马克思进而指出:“这是斯多亚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1]129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又称“逻各斯”,“世界理性”“上帝”“命运”,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它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人的美德就应该是“顺应自然”或“顺应理性”。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将生产力发展置于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在内的所有阶级利益之外、之上,这种科学精神、学术精神,就是在科学研究伦理、学术伦理上贯彻了“斯葛多哲学”“斯葛多主义”,就是抱着一种纯粹的使命感去对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用一种“宿命论”“义务论”的态度去追求科学真理、研究学问。这种对科学真理追求的“斯葛多精神”不是一种功利的、偶然的、外在的而是一种存在论的、必然的、内在的精神。如果说这种科学“斯多葛精神”也带有什么功利的话,那也是服务人类社会整体、长远利益而不是特定阶级或短期利益的功利。在李嘉图看来,如果说不是为了生产效率提高或者生产力发展本身而是为了某一个或者几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去发展科学,这本身就不是发展科学而是扭曲科学,这就是“对科学犯罪”[1]129。从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使命本身来说,他是坚决不允许自己这么做的,也是不允许别人这么做的。从另一方面说,李嘉图在阶级利益上的“残酷无情”是他在追求科学真理和坚持科学研究伦理方面“勇敢大义”的体现。但是,马克思也看到,这种科学上的“残酷无情”并没有妨碍他在现实中成为一个生活上的、道德上的“博爱主义者”。“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践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1]129
二、科学研究可以“犯错”而不能“犯罪”
马克思还发现,马尔萨斯亦剽窃过唐森的人口理论。约瑟夫·唐森(1739-1816)是英国牧师、地质学家,是人口论的最早鼓吹者。他在其匿名著作《论济贫法》中最早提出“人口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如果我们把马尔萨斯著名的论人口的著作《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第一版同唐森牧师的著作《论济贫法》(1786年伦敦版)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马尔萨斯的这部短篇著作无论在基本命题还是资料来源方面都是来自唐森,他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创作的思想,他在加工唐森著作时只不过是直接照抄和赤裸转述唐森的著作,但“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1]124马克思认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这本书只应看做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应看做是用亚伯拉罕·圣克拉拉文体对唐森、斯图亚特、华莱士、埃尔伯等人的论断的改写”。[1]13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更是直接说明: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没有一个他独立思考出来的命题”[5]676。
“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发展脱离不了计算机、多媒体等设备。老师的课堂教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粉笔、黑板和课本结合的当面讲授。“互联网+教育”时代使授课方式丰富多彩,例如“MOOC”“网易云课堂”等,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加入名师对重难点知识的分析;课后学生可以回顾教学视频巩固写作知识,把自己不理解的知识点通过留言等方式反馈给老师,课堂上下互为补充,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1830年,麦克库洛赫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二版。马克思认为,在这本书中,麦克库洛赫只是把为斯密《国富论》第四卷中所做的“注释和论述”又重新抄了一遍。如果说在“注释和论述”中,“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在所谓的系统叙述中更容易对付过去”[3]188,那么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矛盾的地方则十分明显。而且,《政治经济学原理》还包括自己发表过的关于论谷物贸易等等的文章,“这些文章他大概已经用20个不同的标题在各种不同的期刊上,甚至往往在不同时间的同一刊物上一字不改地一再发表过。 ”。 [3]188
马克思还注意到,该书还包括从穆勒那里直接抄袭过来但是加上自己极其荒谬解释的东西,其惯用的是矫揉造作的剽窃手法。这点从麦克库洛赫附和穆勒对李嘉图理论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看得出来。李嘉图理论体系存在着两大矛盾——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规律的矛盾,马尔萨斯等人由于不懂得价值、剩余价值向平均利润转化发展的辩证法,而是借助于资本构成不同但利润相同、剩余价值相同但利润下相同这些矛盾直接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批判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穆勒解决李嘉图体系矛盾的办法是将“生产时间”等同于“劳动时间”,将“生产间歇时间”看作“劳动吸收时间”,比如将葡萄酒在酿造过程中的自然发酵过程看作“劳动吸收时间”,从而将“劳动”概念扩大化、虚无化、庸俗化,将使用价值直接等同于交换价值。在解决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上,麦克库洛赫亦步亦趋地附和穆勒的这种解释办法,直接将“资本”看作“劳动”——“积累劳动”,直接将“利润”看作“积累劳动”的“工资”。他这样做,就是与穆勒一样既使“资本”也使“劳动”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直接糟蹋了李嘉图理论学说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劳动价值论,导致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可悲的解体,“他以其惯用的、矫揉造作的剽窃手法,以一般的形式重复了这种胡说,在这种形式下,隐蔽的荒谬思想就暴露出来了,李嘉图体系的以及整个经济思想的最后残余也就被顺利地抛弃了。 ”[3]194
马克思对这位资产阶级化土地贵族的代言人有这样的评价:“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即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1]125拿当时的“谷物法”来说,英国农场主安德森也是维护这个法律的,但是他的立场则是基于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基于已经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的地主贵族利益的考虑。马尔萨斯之所以采用安德森的结论,则是因为他巴结土地贵族。对马尔萨斯来说,只有在安德森的结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限度内,他才保留安德森的实际结论,而对于超出这个限度内的其他结论,他则是予以抛弃。不仅如此,他还为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辩解和为劳动的剥削者进行辩护。在他看来,不是基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异化引起的不平等交换和贫富差距,而是“对罪恶的惩罚”导致了“人间的贫困”,因此必须有一个“悲惨的尘世”来训诫穷人。
马克思通过对马尔萨斯学术史的考察,发现他一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充满着辩护论色彩。他的第一部著作《人口原理》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就是为了反对历史的发展。他的《关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理由》和《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的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过时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纳入对土地贵族、教会和食税者来说才是有利的和合适的范围。
有些一词多译通过增词表示强调,如“最高债权额”一词的译文“maximum allowable amount of creditors’ rights”和“maximum amount of creditors’ rights”,两者仅相差一个“allowable”。两种译文在词义上也不会因为添加了或减少了一个词而有所变化。因此,“allowable”的作用在于强调这个最高债权额的范围,是合同中所约定的、允许的最高债权额。
马克思进而指出,如果说西斯蒙第等人对李嘉图的批判是源于他们不懂得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法,只是没有掌握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辩证法,尚不至于在科学研究或学术道德方面“犯罪”,而只是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犯错”,那么,马尔萨斯在科学研究伦理方面则是“卑鄙的”和“对科学犯罪”。马克思对自己的这样评价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1]129他从科学前提做出的结论是“看人眼色而不是毫无顾忌的”。[1]127“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上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就是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1]129-130详细说来,马尔萨斯“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1]125他反对“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1]128对于被压迫阶级,马尔萨斯则是毫无顾忌、残酷无情,而且毫无隐晦地直接地宣扬这种残酷无情。
马克思主张科学研究公正无私,不能有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而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各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成、发展和没落及其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否则就是对科学犯罪。本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兴起而新生的被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一出生就遭受着苦难,因而值得同情。无产阶级也是将会担负起社会政治解放和整个人类社会解放的阶级,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就是卑鄙的、无道德的。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恩格斯也同样持有。对于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其人口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宣战”[2]484。因此,“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1]130
三、厌恶学术剽窃或生产“拙劣的仿制品”,把学术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的行为
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深恶痛绝的是学术研究中的剽窃,或生产“拙劣的仿制品”,并把学术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马克思在对比、考察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麦克库洛赫两人的著作时,发现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严重道德问题,前者的主要问题是模仿和剽窃他人,后者的主要问题是“一文多发”,把学术变成生意。
对于李嘉图的“生产中心主义”“发展中心主义”,李嘉图主义的一些伤感主义的反对者,如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及其门徒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不是生产本身而是人本身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资本论》手稿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从个体与类的辩证法的角度,对西斯蒙第这种小资产经济学家的经济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西斯蒙第等人实际上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对立起来了,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中心主义或发展中心主义,无非就是强调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是第一位,而人类的生产力又是“人类天性的财富”[1]127。不能将个人福利、个人发展与社会福利、社会发展对立起来,不能因为个人福利而使全人类福利受阻,就像不能因为战争会造成个人死亡而一概反对任何正义战争一样。对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与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人的发展的关系,不能持有形而上学的统一的观点,二者经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的,“种”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作为“类”的人要实现发展,往往会牺牲掉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个性的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但是二者最终会实现和解并取得同步发展。
对于马尔萨斯,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马尔萨斯一直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是一个“惯犯”,一旦他从事独立创作而不能再剽窃别人时,就“表现得如此可怜”[3]36“未必还有什么东西比马尔萨斯关于价值的著作所表现出的那种虚张声势更滑稽可笑的了”[3]53。但是一旦当他“又跨入他作为经济学方面的亚伯拉罕·圣克拉拉曾从事活动的领域时,他又自由自在起来。不过,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违背他那天生的剽窃者的本性。 ”[3]53
马克思通过对马尔萨斯学术著作的梳理考察发现,他先后剽窃过安德森的地租理论、唐森的人口理论、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思想。
马尔萨斯最早剽窃过安德森的级差地租理论。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名农业家、苏格兰农场主,他在经济学上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级差地租理论,马克思称他是“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4]700。他于1775年在爱丁堡出版了三卷本文集《论农业和农村事务》,1797年在伦敦出版了《关于农业、博物学、技艺及其他各种问题的通俗讲座》,这两部著作都是直接为农场主进行实际经营写作的“业务指南”而不是专门的学术理论著作。书中,只有一两篇文章顺便谈到了地租的问题,但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对级差地租理论发现的重要性。对于安德森关于地租问题上的原创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表现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对安德森理论的仿制品很快就出现在1815年,这从仿制品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的研究》。然而,李嘉图并不知道安德森的著作,他在自己著作中把马尔萨斯和威斯特叫做地租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把马尔萨斯的著作同安德森的著作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知道安德森,并且利用安德森的研究成果。
《资本论》手稿体现的一种态度是科学研究可以“犯错”而不能“犯罪”,犯错是着眼其研究方法,犯罪是针对其研究立场。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等人对李嘉图的批判是源于不懂得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与作为“类”的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法,这只是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犯错”,而马尔萨斯在著作中为落后的土地贵族辩护则是“对科学犯罪”[1]129。
马克思也发现马尔萨斯还剽窃过西斯蒙第的思想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反动的东西。西斯蒙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家,他把过去的、古老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起来,并且坚决站在前者一边,并且企图挽救被历史车轮碾碎的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注意到,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出版于1819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拙劣的仿制品1820年就出版了。马尔萨斯也是站在土地贵族的立场上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资本。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只不过是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马尔萨斯化的英译本。“像过去剽窃唐森和安德森一样,他现在又在西斯蒙第那里为自己的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论著找到了理论支点,不过与此同时,他从李嘉图的《原理》一书中学来的一些新理论也派上了用场”[3]53。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学术史的考察,指出马尔萨斯对西斯蒙第的抄袭还不算结束。他提到,“英国基督教神学家、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托马斯·查默斯在其1832年伦敦版的《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一书中又以夸张的、更丑恶得多的形式抄袭马尔萨斯的观点。”[3]57他不仅以更夸张、更丑恶的形式宣扬马尔萨斯的观点,而且在实践上更是表现出为教会、国家开支、富人挥霍进行辩护。
通过对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的学术史考察,马克思发现麦克库洛赫不仅在学术观点方面运用“积累劳动”这种荒谬的、庸俗的、没有概念的观点去化解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矛盾,而且还利用科学成果上的“积累劳动”将科学和学术研究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他尤其擅长通过一稿多投、一文多发赚取好处。他除了抄袭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之外,“自己还不断把他的“积累劳动”以不同的标题一再翻印出售,经常从他以前已经得过报酬的著作中‘大量抄录’”。[3]203
马克思通过学术考察,发现麦克库洛赫在他为斯密《国富论》所做的“注释和论述”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存在着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他指出,1828年,麦克库洛赫出版了斯密《国富论》并在第四卷中做了号称“注释和论述”长篇累牍的东西。但是,这些内容与其说是“注释和论述”,倒不如说是与主题毫无关系的“个人私货”,只是从他自己过去的“零散的著作”中直接抄来的:一部分是他把以前发表过但与主题毫无关系的文章,如关于“长子继承制”的文章这次重新刊印出来;一部分是把“政治经济学史讲义”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一遍,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有许多是从其中抽取出来的”[3]188;再有一部分是把穆勒以及李嘉图的反对者提出的新东西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同化”而吸收进来。
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和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不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代表的则是腐朽的、没落的封建土地贵族和一些不劳而获的社会群体。马尔萨斯作为英国人口学家和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他那个时代庸俗经济学中最保守的人物。对于他的著作,马克思亦充分注意到了。马尔萨斯也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与李嘉图不同而与西斯蒙第相同,但是他与西斯蒙第“相同”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对马尔萨斯来说,还有比生产发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希望的“生产”只有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才可以被接受。也就是说,他只希望为了生产而牺牲某一个或者几个阶级的利益。比如说,他也与李嘉图一样赞同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牲畜甚至陷入饿死和光棍的境地,但是这种“赞同”不会延伸到土地贵族那里,而且是出于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考虑。当生产发展要求减少土地贵族的地租或威胁到教会税收时,或者在贵族同资产阶级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阶层同进步阶层利益对立时,马尔萨斯都是竭尽全力保全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牺牲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在他那里,特殊阶级利益是首位的,为生产力发展所做的牺牲是有限的、局部的。
2017年9月,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程立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1月2日,程立生被检方提起公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英美两国支持的是一个尚未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的欧洲美元市场,而这个基础实际上是指固定汇率。
除马尔萨斯等人外,马克思还发现号称“李嘉图主义者”的麦克库洛赫也存在严重学术道德问题。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在学术研究中没有道德操守,不仅严重“剽窃他人”,还经常“剽窃自己”,经常“换个标题一稿多投”“换个刊物一稿多投”,或者“在同一刊物不同时间发表同一篇文章”。
马克思这里实质上揭露了学术动机与金钱利益的关系。进而,马克思还看出了麦克库洛赫用欺骗手法使自己成名。马克思关注到,1826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逊曾以“莫迪凯·马利昂”为笔名在爱丁堡出版了《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该书对麦克库洛赫在学术方面赚取“积累劳动的工资”的手法专门进行过详细分析,揭示了他“最无耻最恶劣地一再重复这种积累劳动”[3]203。马克思嘲讽道:“这揭示了‘我们这位骗子手是怎样成名的’”。[3]203马克思还摘录了威尔逊的这些批判:“麦克库洛赫不仅把同一些文章当做自己的‘论述’,当做新的著作,轮流卖给《爱丁堡评论》、《苏格兰人报》、《不列颠百科全书》,而且他比如说还在不同年份的《爱丁堡评论》杂志上把同一些文章一字不差地重新发表,只是多少颠倒一下次序,换上新的招牌。在这方面,马利昂是这样评论‘这个最不可相信的修鞋匠’[第31页]、‘这位所有经济学家中最经济的经济学家’[第66页]的,‘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文章不管和天体多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却和星辰相似,就是它们总是定期再现’。(第21页)”[3]203-204马克思反对学术研究中的剽窃,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这种主张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理论创新尤其是引领型、原创型的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学术繁荣的生命力所在。如果学术研究中只是进行思想模仿、观念重复、理论仿制甚至抄袭剽窃,这既伤害了学术发展的生命力,也违背了科学研究发展的道德。
四、反对按照个人好恶偏好任意裁剪科学历史或“在理论上故弄玄虚”
《资本论》手稿体现了一个重要学术原则是,反对按照个人好恶任意裁剪科学历史或“在理论上故弄玄虚”。这主要针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以及马尔萨斯。
人际元功能带有很重的语义负荷(Halliday 1994:190-191)。实现人际功能的语法资源有语气、情态、语调等。在Halliday关于语气的语法研究推动下,早期人际语篇分析主要涉及物品和服务交换以及信息交流的研究,侧重人际交往,聚焦于人际的“际”(Martin 2004)。然而,人际元功能是否只能由语气、情态和语调等语法资源来实现呢?人际功能中“人”的因素如何体现?
马克思在考察政治经济学历史过程中,发现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1817-1894)存在的学术道德问题。罗雪尔主张摒弃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提出更多地要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历史归纳。因此,历史学派的著作,经济问题只占次要位置,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经济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罗雪尔的方法和理论是“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5]110。他的经济学知识十分贫乏,但是他本人十分崇拜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科学之父”修昔底德,因此自称是经济学领域的修昔底德。马克思通过对他在经济学历史评价中不客观、不公正等伦理问题的分析,对这个称号作出了尖锐的嘲讽。
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顶峰和完成者,做出了划时代的科学贡献。然而,罗雪尔在《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中评价李嘉图的科学体系时,却以高傲自大的口吻将李嘉图理论体系不公正地嘲讽为“半个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罗雪尔对待科学和学术是十分“残酷无情”的,我们也可以同样认为罗雪尔的理论体系是“全无真理”[1]135。马克思认为,他在列举学术文献和科学书目方面一点也不“客观”和“公正”:谁不“值得尊敬”,就让谁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比如,他认为,洛贝尔图斯就不属于地租理论家,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在商品价值理论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贝利也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他在整理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时,也不是按照经济学家本人的科学原创性和学科的逻辑结构来进行的,不是抱着虔诚的、自我评判态度,而是按照自“中庸的”“长者的”态度自居于前人之上,以为手中掌握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用看透世事炎凉的高傲态度来“俯视他们”“评判他们”,将他们归于自己的“逻辑体系”之中,按照个人好恶随意剪裁科学历史,硬是将政治经济学历史活生生地变成了一门没有生机活力的“历史编纂学”。他“并且以狡猾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而在这样做时,不是要发现矛盾,而是要寻求完备。这就是扼杀一切体系的精神,到处抹去它们的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在这里,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缓和,这种渊博的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作为稀罕的奇物在它的普通的稀粥里漂荡。(至于它们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超然耸立于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之上,那就不用说了。)因为这类著作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3]361-362马克思这里涉及的个人好恶偏好任意裁剪科学历史问题是重要的。确实,科学评价包括对前人学术贡献、学术创新和学术地位在科学历史长河中的评价估量,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学术史、科学史认知的公正性、客观性,更会影响到原始真实性,也牵涉到未来学术发展创新。因此,学术评价必须真实、客观、公正。
在理论上故弄玄虚,也是马克思不能认可的。作为大思想家,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不仅态度严谨,且善于用朴实的文风表达自己深奥的思想。读马克思的书,可以让人感到,他的论证概念清楚,思路明晰,逻辑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语言表述尽可能作到通俗易懂,从不故弄玄虚。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讨厌一些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表达。故在手稿中,马克思发现马尔萨斯不仅在科学诚信方面存在剽窃问题,其文风也大有问题——“有在理论上故弄玄虚的某种兴趣。”[3]8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在1823年伦敦版的《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一书,就是“它迷醉于诡辩,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么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缺乏理解力。 ”[3]21
With this,the teacher should teach basic knowledge in class,and after class,the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 learning autonom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Teachers should prepare different learning materials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finish the tasks.
由上可见,马克思的学术道德观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特殊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的,他坚守的是在科学、学术研究中的大公无私精神,并将学术原创性放在首位,这体现了马克思对科学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和对自己负责的高尚的道德情操。马克思把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好恶、门户偏见在学术研究中彻底抛弃,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开放胸襟;他推崇朴实无华、逻辑简明的文风,而不欢迎故弄玄虚、自我卖弄而给读者带来麻烦,这充分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学术道德观,立场鲜明,捍卫了学者的尊严,体现了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的神圣使命。马克思的学术道德观内容丰富,加强对它的研究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同时对重塑当代中国学术道德观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当下中国学术泡沫严重泛滥、学术诚信危机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谨慎、严于律己,培养一种崇高的学术道德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26(2019)07-0004-08
[作者简介] 孙要良(1982-),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思想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研究”(项目批准号18BZX05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标签:马克思论文; 《资本论》手稿论文; 学术伦理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