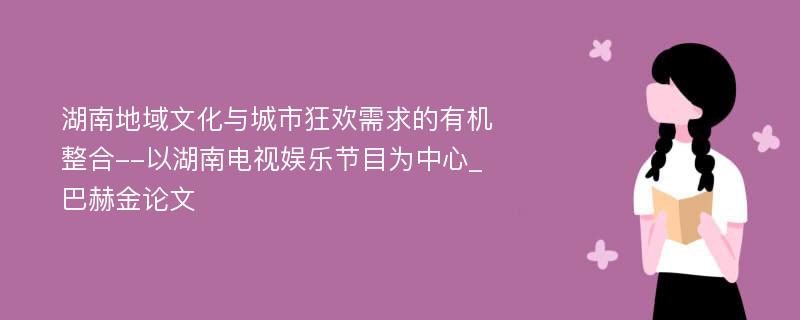
湖南地域文化与都市狂欢诉求的有机融合——以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文化与论文,地域论文,娱乐节目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快乐大本营》、《越策越开心》、《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名声大震》、《舞动奇迹》、《奥运向前冲》、《奥运宝贝向前冲》、《智勇大冲关》为代表栏目的湖南电视娱乐节目已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电视景观。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加以审视的话,这些娱乐节目显现出一定的狂欢化特征:大众参与性、狂欢化广场语言、脱冕与加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巴赫金狂欢理论所表述的现代都市大众文化趋势。这种都市狂欢诉求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氤氲着浓烈神巫祭祀气氛的巫楚文化和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有密切关系。
一、大众参与性
“狂欢”理论源于巴赫金对欧洲历史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集中在中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在他看来,民间广场的狂欢节是“彻底非教会和非宗教的”,“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它的规律,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① 纵观欧洲狂欢节文化,会发现有如下特征:(1)无等级性。即所谓消除等级差异,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参与其间。(2)宣泄性。用各式各样的笑来摆脱现实重负的心理宣泄,无论是纵情欢悦的笑,还是尖刻讥讽的笑,抑或是自我解嘲的笑等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妙。(3)颠覆性。在狂欢节中,人们可以无拘无束颠覆现存的一切,重新构造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无等级性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心理宣泄则是对现实规范的颠覆。(4)大众性。狂欢活动是民间的整体活动,笑文化则更是一种和宫廷文化相对立的通俗文化。② “在这里,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③ 可以说,狂欢的条件是大众的参与和铲除差别。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大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为指归的艺术创作均可被视为具有狂欢特征。《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奥运向前冲》、《奥运宝贝向前冲》、《智勇大冲关》等节目正是以其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呈现出狂欢色彩,但又由于时代科技的发展而具有了崭新的狂欢面貌。
发端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已连续举办了三届,随后而来可谓姊妹篇的《快乐男声》举办了一届。节目涉及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节目收视率之高,参与手机短信投票观众之多以及情绪之狂热,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④ 每一场节目都掀起全民性狂欢。
对于《超级女声》与《快乐男声》而言,大众参与性不仅是指从海选起参与比赛的选手人数众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与粉丝众多,更重要的是,普通大众可以通过短信支持自己喜爱的选手而直接参与到节目中,这样一来,比赛场地、电视和短信这三个有形和无形的载体穿越时空隧道,共同支撑形成了一个狂欢时空。这与狂欢节的狂欢场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在狂欢庆典上,人们是真实地聚集在一起,在全民参与的活动空间里,暂时取消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等级关系,恢复自然的人性状态。《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是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在虚拟的传媒空间实现狂欢,呈现了别样的狂欢形态。虚拟,是指大众的参与并非真正地聚集在一起,而是在各自分散、互相隔离的情形下,通过电视和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在现代传播制造的一个虚实交加的空间中实现狂欢。
如果说《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名声大震》、《舞动奇迹》等节目对选手有一定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才艺的话,大型户外体育趣味节目《奥运向前冲》、《奥运宝贝向前冲》、《智勇大冲关》则可以说是真正的“大众参与”、“全民同乐”,报名者无特殊要求,只要随机抽中则可以成为秀上一把的选手。在这里,体育竞技已经成为其次的重心,参与才是真正目的,选手们不是在比赛,而是一场自我勇气与能量的释放,他们各显其能,身着古装、旗袍、花仙子等各色服装,在冲上赛道之前来一把“才艺秀”。在这里,与其说是竞赛,不如说是个人的特色表演更为合适。观众们最为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放松地欣赏选手们各具特色的出场。竞技在选手与观众的考量指标中淡化,更多成分是一场娱人娱己的表演,这种双向的放松心态造就了浓郁的狂欢气氛。
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与原始的狂欢节场面有别的狂欢形态,这种通过现代传播而形成的大众参与性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人们已经脱离了小农时代的交往方式,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借无形的科技技术而轻易达到广泛的大众参与效果。这显然是一种包含了现代文明发展因子的现代都市的狂欢仪式。
二、脱冕与加冕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最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过往加冕随后脱冕”,这一仪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节的所有庆典上,“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加冕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因此,“它还说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威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⑤ 在巴赫金看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正统的、官方的、教会的、国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等级和一系列道德律令,必须服从于福柯式的权力话语规则;在这个世界里,现有的制度被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不自由的、异己的、非人的。而狂欢节为人们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一世界是彻底非教会非宗教的,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存在领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一律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在这里,人回归到了自我,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可见,在巴赫金那里,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成了狂欢节的真正本性所在。通过皇帝和小丑的位置互换,通过神圣的脱冕方式达到了颠覆原有传统的社会格局和文化面貌的效果。
在湖南的电视娱乐节目中,也可以寻觅到脱冕与加冕的狂欢色彩。但与狂欢节上皇帝和小丑位置互换的程式不同,湖南电视娱乐节目是以这样几种方式来演绎脱冕与加冕的。
1.通过对多重身份的转换完成脱冕与加冕。《快乐大本营》、《名声大震》、《舞动奇迹》等节目,参加的嘉宾均为有一定名气的演艺界人士。但我们看到,嘉宾们在这里均被还原成了普通人,《快乐大本营》中,嘉宾如普通人一般参与游戏,甚至成为被作弄的对象;在《名声大震》和《舞动奇迹》中,半数嘉宾实际上是反串式参赛,即非歌星的演艺人员参加歌唱比赛,非舞星的演艺人员则参加舞蹈比赛,他们分别接受短时期的专业训练,然后进入赛场。从专业角度上看,脱下本行业光环,进入另一个行业赛场的嘉宾们,其技艺与普通人无异。对其技艺的脱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明星角色的脱冕,对既有身份的脱冕。
《越策越开心》中,主持人拥有多重角色,既是主持人,又是节目表演的演员。汪涵、马可与陈英俊、YOYO等人客串表演情景小品,成为节目中的经典瞬间。而且,在情景小品中,男主持人反串女性。这种身份的不断更换、性别的不断转换,正是狂欢节中广场表演的特点。
《奥运向前冲》有这样一批人气骤升、几成网络红人的选手,他们以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黄飞鸿等造型现身,且在赛道上身手敏捷表现不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选手同时具有多重身份:普通人、选手、造型角色,这几重身份在瞬间不断转换,呈现出狂欢节的脱冕与加冕效果。选手以经典造型现身赛道,在比赛的时空里被加冕,比赛结束,随着真实身份的还原进行脱冕。
2.通过话语与情感完成脱冕与加冕。在《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我们看到,现场评委对选手所采用的评判语言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以往大型电视歌手比赛中那种就事论事、不带个人情感倾向的纯粹式评判已难觅踪迹。替而代之的,是一种不隐藏个人情感倾向的、介乎亦师亦友的评判话语。而且,评委之间会因为某个问题而在节目现场争执。选手在角逐中失利离场时,评委也难过动情……评委与选手之间已突破往常的严肃界限,而显现出略带亲昵化的趋向,而狂欢节广场因素就是突出地表现为由取消等级而来的亲昵化。
这种充分情感化的、呈现个人特色的评委风格招来人们热议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仁智之争,个中曲直是非不在本文论述之列。这里要论述的是,这种充分情感化的、呈现个人特色的评委风格,实际以对高高在上的评委角色的解构,完成了评委身份的脱冕,以及评委与选手既定关系的脱冕。
3.通过对微言大义程式的解构完成对“载道”的脱冕。《越策越开心》是一档收视率颇高的脱口秀节目,“策”是长沙方言,相当于北方神侃之意。策,就是天南海北地聊,没有一定主题,其目的就是让观众“开心”——这就是《越策越开心》充分娱乐化和轻松化的旨归。其中尤以情景小品为甚,这些情景小品摆脱了传统小品的思想和主题升华模式,而倾向于一种“无厘头”式的演绎方式,即无主题式的纯搞笑风格。这实际上以对微言大义程式的解构来完成对“载道”的脱冕。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在文艺创作中强调思想高度和主题升华,毋庸置疑,这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看到,当这条规则强调到极限就反而给文艺创作带来一定程度的束缚,成为文艺发展的绊脚石。比如,主题先行和牵强附会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稍嫌严肃和沉重使得文艺的娱乐和放松功能得不到完全实现。但在另一个方面,全然抛弃思想高度和主题升华,这种纯粹的文艺风格自然是轻松了,但如何防止其流于肤浅和低俗,又是人们得提防再三的话题。《越策越开心》正是这样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栏目。
这些脱冕与加冕的具体方式与狂欢节不同,但它们在颠覆这个目的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说狂欢节的脱冕与加冕始于对权威和地位的讥讽,那么,这些娱乐节目中的脱冕与加冕则远离了这种主旨,而是承载了对平凡生活的超越、对日常烦恼的忘却的娱乐功能。
三、狂欢化广场语言
与狂欢化相关的是“广场性”,“广场性”包括诅咒、骂人、耍泼、赌咒、发誓、吆喝、吹牛、欺骗等广场语言,将整个世界进行滑稽化、粗俗化、卑琐化、物质化、肉身化、色情化的广场体裁,随心所欲、不拘形迹的广场式交往,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广场气氛,构成了一种在民间集市和节庆活动中特有的文化征象。狂欢化,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或符号系统。它讽刺摹拟一切高级体裁的语言。这个语言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双重指向性和巨大的象征概括力量。狂欢化的广场语言是一种独特的、具有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的语言。在狂欢式的节庆生活中,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交往的距离缩小,言语交往形式也亲昵化、自由化,言语礼节和言语禁忌淡化,甚至带脏字,说些不体面的话。这些广场语言“都是官方言语的反面,当它们达到足够的数量,就会对整个语境和言语产生颠覆性影响,即言语被转移到了言语规范的对立面,言语摆脱了规则和等级的束缚而变成了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特殊语言。”⑥
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中的语言就具有这类广场色彩,这在《越策越开心》中有集中的体现,节目呈现出很丰富的狂欢特色。
1.民间笑谑语言。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首要原则是重视人类的笑文化。《越策越开心》在此方面与巴赫金不谋而合,它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追求就是“开心”。节目不尊崇传统主持语言的经典,采用大量的湖南村言俗语,更注重语言的休闲性、娱乐性和消遣性,其幽默品格带有浓重的湖南民间诙谐文化特色。在节目中,充满喜剧性的插科打诨和幽默诙谐,寓庄于谐,寓理于趣,常令读者忍俊不禁,兴味无穷。民间笑谑语言已被许多作家所重视,如果戈理就曾打算出版一本《俄语释义词典》,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那种远离乡土和民众精神的一样生活中,固有的俄语本来的意义都被歪曲了,有些被强加了别的意义,有些则全被忘记了。”⑦ 与东北等其他地方一样,湖南也是一块充满民间笑谑文化的土地,这些民间笑谑文化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为地域的相隔和方言的差异而大异其趣。湖南的民间笑谑文化被大量地吸收融入进各类艺术创作中,如乡野风情的湖南花鼓戏,独树一帜的奇志大兵相声表演。《越策越开心》也将这种与方言交织在一起的湖南民间笑谑文化带入节目,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节目在脱口秀节目中别具一格。
在大陆的地方电视台,方言频道及栏目占半壁江山的当数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电视台,这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历史地理及粤语的特殊性有渊源关系,具体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列。我们看到,在这里,粤语已经是官方与民间合一的方言,因此,新闻类、访谈类、娱乐类等频道及栏目中,粤语作为一种方言,除表情达意外,并未承载太多戏谑成分。而在其他省市电视台,基本上是普通话一言堂,而方言多在小品、戏曲等文艺节目中以戏仿搞笑的形态出场,从而达到一种喜剧效果,如东北方言、四川方言、湖南方言等的运用。
《越策越开心》中湖南方言的运用既与广东省市电视台的粤语频道情形有别,也与专门的文艺节目中对方言的运用不一样。节目是普通话与湖南方言无固定规则地交叉运用,在情景小品尤有集中的表现。节目中的湖南方言也不一定是省会长沙方言,而是选取湖南一些更偏更小更具喜剧色彩的地方方言,运用中尤其突出某些来源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但又为大众所熟知颇具搞笑意味的语词,包括地名、俗语、歇后语等,如“马栏山”、方言版“喝杯白酒,交个朋友”……这种运用正是节目与民间笑谑语言的结合,显示了现代传媒与民间笑谑文化的有机融合。
2.“傻瓜”、“小丑”形象。《越策越开心》中的陈英俊,他在情景小品中出演的一般是憨傻可笑的、具湖南特色的市民和村民形象,如同狂欢节中亦庄亦谐的“聪明的傻瓜”、“悲剧的小丑”形象,憨傻而独特的行为和语言与其他人精明的行为和语言形成一种对峙的张力。
骗子、小丑和傻瓜是狂欢节上的主要人物,是狂欢仪式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也是狂欢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他们以独特视角审视现实,以插科打诨的方式说出生活的真相。巴赫金认为,在所有高级的、严肃的、规范的语言里,都积淀了一种高调语言,充斥其间的是虚伪和谎言。作为揭露的力量而同它们抗争的是骗子清醒、风趣而狡黠的头脑,是小丑讽刺模拟式的嘲弄,是傻瓜并无私心的天真和正常的不理解。这类人物无意于遵守现有的生活秩序,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与之对抗,只能采用一种低姿态来与之周旋,最终的任务是戳穿人与人关系中任何成规、任何恶劣的虚伪的常规。⑧
文学作品中的这类人物可谓数不胜数,正如狂欢节上的这类人物进入文学作品后会有或多或少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变形一样,《越策越开心》中的陈英俊所展示的也是这类人物的变体—— 一口地方塑料普通话,浓重的乡村语词穿插其中,角色天真憨傻。当然,我们看到,陈英俊所演绎的“傻瓜”与“小丑”形象并未承载狂欢节上类似角色揭示生活真相、戳穿虚伪常规的既定任务,而只是以其幽默谐趣取得一种狂欢节角色的喜剧艺术效果。
以上这些狂欢化的广场语言,体现出与湖南民间笑谑文化和湖南地方方言的紧密胶着状态,从而彰显出独特的地域艺术风貌。
四、巫楚文化与湖湘文化浸淫下的狂欢特质
上面分析了湖南电视娱乐节目的狂欢特征,虽然这些节目未必受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影响而创作,但是正如著名学者钟敬文所言,“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狂欢活动,中国也概莫能外。当然,“‘狂欢’一词,我国过去在学术上还不曾作为术语来使用”,但是,“中国文化中的狂欢现象,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都是存在的。”诸如民间灶火、迎神赛会中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与世界上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呈现出华夏民族的特殊之处。⑨ 再进一步而言,湖南地方的狂欢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与世界上的狂欢活动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艺术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温床,诚如丹纳所说,“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⑩ 那么,电视娱乐节目之花何以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格外鲜艳?我们认为,娱乐节目的狂欢化特征与巫楚文化和湖湘文化有不解之缘,都市狂欢是实在形态,而湖南地域文化是内存精神。
以下试从巫楚文化和湖湘文化两方面论述湖南地域文化对于湖南电视娱乐节目的影响。
首先,巫楚文化以它的祭祀狂欢特质和宏富的想象力为湖南的电视提供艺术基因。
湖南的艺术深受巫楚文化的影响,电视艺术也莫能外。人类的远古文化与原始宗教和图腾巫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充满神巫性,这与原始时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人们蒙昧的知识水平是对应的。而巫风在楚地尤盛,楚文化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州色彩。这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异宝篇》说:“楚人信鬼。”《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等等。信巫重鬼、好为淫祀,这使楚文化在内质是成为一种“巫鬼文化”、“祭祀文化”。信鬼奉神崇巫的习俗,极大地影响了楚地后人的精神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巫祭祀呈现日益民间娱乐化的趋向。唐代元稹《赛神》诗云:“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荻,赛妖无贫富。杀牛贯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闹里闾隘,凶酗日夜频。”(11) 这首诗中所描绘的是巫事活动中楚地人们不问亲疏、不论贫富、夜以继日、高歌狂舞的场面。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云:“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祠,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这些古籍都生动记载了远古以来的楚民对于巫事活动的热情,和击鼓喝酒、载歌载舞的情形。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明的发展,这些神巫祭祀活动日益淡化了信巫重鬼的原初目的,活动的重心从内容转向形式,而更多表现出民间娱乐的成分。如据湘西《永绥厅志》载,苗族祭鬼活动有“七十余堂之多”。苗族的巫——苗老司,颇有楚巫的古风,他们在祭祀或其他庆典活动中所唱的一首长达一万四五千行的古歌《加》(音译),名法上长短错综,喜用“兮”音放在句中或句尾,类似楚辞;他们还要唱傩愿戏,跳傩愿舞,既娱鬼神又兼娱凡人,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12) 兼娱鬼神与凡人——这便是神巫祭祀日益民间娱乐化的生动描绘。
虽然源头各异,但从形式上看,这些神巫祭祀活动活动与西方狂欢节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其一,二者都需要通过民众集聚的仪式化来达到目的。在目的上,狂欢节自然是为了纯然的狂欢,而神巫祭祀活动在后来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民间娱乐倾向。其二,二者都是以特定方式让参与者进入另一个虚幻世界。狂欢节为人们在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彻底非教会非宗教的,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存在领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神巫祭祀活动则让参与者进入一种迷幻的人、神、鬼共存的世界。其三,二者都通过脱冕与加冕来完成仪式。狂欢节是通过皇帝和小丑的位置互换,通过神圣的脱冕方式达到了颠覆原有传统的社会格局和文化面貌的效果。而神巫祭祀活动则通过巫师—神鬼—凡人的多重角色转换,来达到神鬼人对话与沟通。神巫祭祀日益民间娱乐化是神巫祭祀活动与民间狂欢的特殊结合形式,是远古而来的神巫祭祀活动在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盛行巫风、神奇诡谲的楚地文化也孕育出了独特风貌的楚地艺术。就文学而言,楚文化孕育出了一代代“狂欢文学”作家,屈原的《九歌》即是将主祭的巫师所唱的迎神、娱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而成,不乏神巫化狂欢色彩……而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以沈从文、韩少功、残雪等为突出代表。当然,这些狂欢文学又带有明显地域特色和个人特征,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以节庆、婚嫁和丰收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嬉闹杂耍的狂欢场面,和以生死和肉体为核心的狂欢化意象,以及鲜明的狂欢式话语系统,呈现出一种乡土“类狂欢”形态。(13) 以《马桥词典》、《爸爸爸》为代表的韩少功小说世界则以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进行脱冕、疯言疯语对正常话语进行脱冕,而形成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狂欢效果。以《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为代表的残雪小说世界,则是以人物的呓语、独特的意象完成对现实世界的颠覆,以一种精神迷狂式的狂欢形态来完成作者对于人性和现实的理性拷问。
文章所论的湖南电视娱乐节目就是沿袭巫楚文化狂欢遗风的一种特殊的都市狂欢形态。这对于在巫楚文化的母体文化中生长发展的湖南电视而言,受巫楚文化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们看到,这种都市狂欢形态已经全然远离了巫楚文化中神巫祭祀的特殊内涵,但其中的民间娱乐精神却显现出家学渊源般的内在关联。这也绝非是古老的楚地民间娱乐文化在现代时空的重演,而是楚地民间娱乐文化与现代传媒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具有其特殊的现代形式和现代意味。而深受楚地这种民间娱乐文化浸染的湖湘人们也为湖南的电视娱乐节目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受众基础,这也是全国省市电视台中,湖南的娱乐节目能够引领风骚,并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湖湘文化给湖南电视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推力。
湖湘地区属于楚文化的覆盖区之一,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在潇湘大地上生发、丰富和演变的湖湘文化,成为楚文化重要一支。湖湘文化既保留了楚文化驰骋想象的浪漫基因,又在特定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中融入了积极、理想的独特品格。神奇诡异的楚文化与经世济民的现代湖湘文化也呈现出渐行渐远的不同风格,在相对封闭和荒蛮之地诞生的楚文化,更多体现原始率真的一面;而逐渐成为庙堂文化代表之一的现代湖湘文化,则更多体现其治国安邦的一面。
湖南电视“成功的秘密,就藏在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中:心忧天下,敢为天下。”(14) 这种自我总结是有相当道理的。“湖湘学派具有注重经世实用的传统。湖湘学者坚持认为,儒学与佛学、道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佛、道所追求的‘道’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脱离了人民的实际需求,而儒家的‘道’则是和日用伦常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要求学者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同时还要具有管理国家的知识才能。”(15) 尤其近代,湖湘大地人才辈出,湘军统领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从湖南走向世界,成为较早沐浴欧风西雨,倡风气之先的一代人物。毛泽东等人则开创了中国的新天地……在小康社会、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转型时期,社会对大众化、世俗化文化迫切需要,以变革求新、立于时代潮头著称的湖湘人,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对文化的需求,创办出一系列有影响的娱乐节目,湖南电视娱乐节目应运而生。
当然,在如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交通和信息的畅通发达,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会单纯只受某一种文化的影响。但通过分析,湖南电视的娱乐节目与湖南地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踪可寻的。
巫楚文化与湖湘文化浸淫下生长发展的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以其生机和活力丰富了中国电视文化的多元构成。但其中也不乏重复化和低俗化的苗头,如何真正在电视娱乐节目的精神内质上进一步提升,防止低俗化和庸常化,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后续课题。
注释:
① 巴赫金:《巴赫金文集·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④ 赖大仁:《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文化解读》,《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⑤ 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⑥ 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⑦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等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⑧ 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62页。
⑨ 钟敬文:《文学狂欢化与狂欢》,《光明日报》1999年1月28日。
⑩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11) 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12) 转引自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13) 陈力君:《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狂欢化倾向》,《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4) 魏文彬:《湖湘文化与电视湘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
(15) 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标签:巴赫金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快乐大本营论文; 智勇大冲关论文; 越策越开心论文; 超级女声论文; 快乐男声论文; 狂欢节论文; 语言特色论文; 娱乐活动论文; 娱乐节目论文; 舞动奇迹论文; 名声大震论文; 楚文化论文; 湖湘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