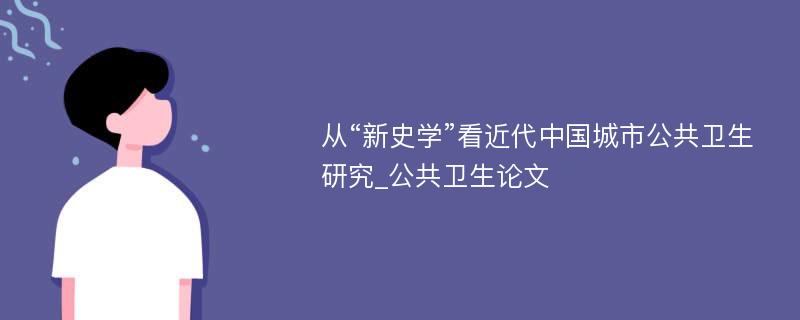
“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学论文,公共卫生论文,视野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2-0173-14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学科互涉的学术研究趋势下,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间的交叉渗透逐渐增强,传统史学积极向“新史学”进军,历史学与医学、公共卫生学的对话便是在此背景下发生。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就是始于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台湾梁其姿女士相关论文的问世①及此后台湾史学界“人群生命史”、“另类医疗史”②概念的提出,台湾、大陆史学界也相继以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变迁为透视点,采取有别于技术史的研究路径,加入疾病医疗史、公共卫生史的研究队伍。2003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疫情——非典爆发,史学面临因应自身革新要求,研究历史资鉴未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双重使命,自此,中外史学界更加聚焦近代中国疾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③,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
由于“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公共卫生作为世界性问题,主要是城市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⑤;相对应的是,近代农村公共卫生建设非常滞后,“农村既无良好医疗之设备,民众又无卫生常识之可言,偶遇疾病流行,死亡载道,无法制止,往往委之天命。”⑥因此,现有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对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既如此,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总体面貌。何况,公共卫生关涉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生活、市政管理、生态环境,它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的考察无疑也能从一个侧面透射目前近代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的综合水平。就笔者有限的涉猎来看,现有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 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在前近代时期,无论中外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大同小异,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⑦。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来,欧洲率先开始了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在来华西医传教士的卫生宣传、租界的示范和刺激、有识之士的呼吁、疫病频发的促使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也相继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艰难历程。何小莲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⑧这就意味着,晚清以来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如上海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⑨之情形,到了民国时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系统探讨近代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变迁。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散见于相关城市史著作,如《近代天津城市史》⑩、《近代武汉城市史》(11)、《近代重庆城市史》(12)、《上海通史》(晚清、民国卷)(13)、《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14)和《北京通史》(清代卷下、民国卷)(15)等,都对相关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作了概略性的勾勒,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史明正先生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16)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别具一格地选择污水排放系统的修整和现代供水系统的构建这两个视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缓慢且无实质性飞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政治学探讨”、经济学乃至技术层面的分析。这种从城市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把城市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融通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些专门论述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变迁的论著和博硕士论文,其考察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武汉、北京、广州、重庆、厦门等大城市。
何小莲在《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17)一文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中国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作了扫描性的述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
Kerrie Macpherson(程恺礼)、罗苏文、朱德明、李达嘉、中岛知惠子、彭善民诸人分别构建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研究体系。Kerrie Macpherson在《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18)一书中以大量西文资料为依据,探讨了上海开埠后50年中,公共租界在工部局的领导下基本建成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大体历程,充分肯定了英国医疗专家们在租界公共卫生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该著被彭善民誉为“是研究上海公共卫生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为华界及1893年后上海的公共卫生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19)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20)(十一、构筑公共卫生的防线)中选择“粪秽股与公厕”、“菜场的设立”、“牛痘疫苗”、“鼠疫查访风波”四个横剖面,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架构,高度赞扬了工部局卫生处作为“最早起步构筑公共卫生防线的前驱”(21)对上海公共卫生建设所起的作用,同时,罗苏文也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医学指导下的租界公共卫生制度对华界的影响。朱德明在《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22)一文中则从卫生行政机构、医院、中西药制销业、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五个方面对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的发展作了概述,认为租界卫生事业为近代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李达嘉在《公共卫生与城市变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个观察》(23)中,“试图从生活即文化的角度切入,以清末上海的公共卫生为题材,从饮水、街道清洁、疾疫的防治和医疗等方面,观察西方文化在上海社会传布的过程。”(24)如果说上述论著主要侧重于对近代上海租界公共卫生史的探讨,并且Kerrie Macpherson等还在很大程度上持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基本是租界示范和西方文明单向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岛知惠子和彭善民则着力于阐释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挫折,并且以中西内外交融互动的价值理性呈现了更为真实复杂的近代上海图像。中岛知惠子在《上海的卫生、医药与民族(1900-1945)》(25)中分别考察了作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物质基础之一的医药行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计划下上海市卫生机构的设置及防疫活动,上海市卫生局二三十年代策动的卫生运动和沦陷时期日本军方和日伪政府在上海霍乱防治上采取的带有人身侵犯性质的强制性措施。该著特别指出上海卫生局策动的卫生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动员民众、启发民众觉醒的政治运动。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26)中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系统考察了近代上海(包括租界和华界)公共卫生事业发生、发展、困顿和重整的历程,并对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判,认为它“既是都市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27)
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发展史研究的卓越成果有美国学者Ruth Rogaski(罗芙芸)的博士论文《从保卫生命到保卫国家: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出现(1859-1953)》(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859-1953)以及据此修纂而成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一著(28)。罗芙芸以“卫生”概念内涵的近代嬗变为切入点,通过水的供应、垃圾粪秽的处理、传染病的预防、卫生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卫生运动的开展等历史图像的串联,描述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近百年历史跨度中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揭示了公共卫生制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想和目标是如何被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移入天津城市空间,并为天津市政府和社会所接受和适应的历程,并从城市政治分裂的角度阐析了外国租界的存在既刺激了天津公共卫生建设又阻碍了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历史事实。
台湾政治大学周瑞坤的硕士论文《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s)》(29)探讨了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前30年代广州城市卫生管理机构通过改良和扩充原有卫生设施,加强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和卫生统计,逐步行使卫生管理职能、贯彻各项卫生措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历程,肯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建设上的积极努力,并指出公共卫生建设也是形塑现代广州市民和现代广州城市政权的过程,揭示了它对广州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该文还指出由于经费的有限及政治的不稳定,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只是治标的改善。这篇硕士论文是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为此后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汉口是中国内地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幅度比较大的地方”(30),因此,对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发展史进行研究也极具学术和现实意义,《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31)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作者周启明首先简介了1861-1926年武汉公共卫生的概况,重点考察了1927-1937期间武汉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肯定了这一时期武汉公共卫生建设的成就,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分析。这篇论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近代武汉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唯一之作,发轫之功应当高度肯定,但此文内容稍显单薄,对10年间武汉公共卫生发展的探讨不够深入。
此外,《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以卫生检疫、粪污处理及自来水事业为中心》(32)、《从基督教福音到公共卫生——近代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概况研究》(33)、《近代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34),也分别采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式按时序对近代厦门、重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了或深或浅的探讨,宁波大学的孙善根还对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述评(35)。这些无疑都为目前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系统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 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程度根本取决于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专题研究遂成为现有研究的又一重要取向,它又包括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及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学校卫生管理、妇幼卫生管理等的专门考察。
首先,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探讨。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36),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1854-1910)》(37),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38)是整体考察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管理的代表性成果。三篇文章从内在架构来说几乎一致,都是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环境卫生管理、疫病管理三个角度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作相对系统的探讨。龚小雪的《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虽以整个清代为考察背景,但从篇幅上来看,重心仍在晚清,而且在“清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一章里还立足于上海租界的个案考察,因此,在内容上,三文也多有相通之处,都对晚清以来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嬗变、相关环境卫生管理和疫病管理条例、法规的颁布及措施的实行,进行了阐述,肯定了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对推动中国近代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对其殖民色彩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有些疑问的是,能否将公共卫生管理的概念沿用至近代之前?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一文显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国已经存在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公共卫生管理了,她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清代传统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里提到了“太医院”和“宫廷药房”,“太医院”和“宫廷药房”能否称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值得商榷,这正如彭善民所言,“传统城市社会的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并不具有公共性”(39)。既然不具有公共性,其职能又并非为了谋求公众的健康,那么近代之前传统医疗机构进行“公共卫生管理”一说就很难成立。除对上海的考察之外,杜丽红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30时代的北平城市管理》(40)中专设一章,从建立卫生稽查员制度、街道清扫管理、垃圾清除管理、粪便收集与处置管理、饮水卫生管理、餐饮卫生管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公共卫生普及八个方面对30年代北平公共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杨韵菲在其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初探》(41)中,从医政管理、环境卫生的整治、传染病的防治、卫生保健、战时紧急医疗救护的管理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工作及其实施效果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
其次,对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这是目前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的领域,其研究主要围绕近代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四个城市展开。
在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42)、《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43)、《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44)和《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45)四篇文章。《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基本构成,包括环境卫生管理的机关部门、具体内容、相关制度及措施等,并对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作了分析,指出“环境卫生管理理念和相关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6)。《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则从环境卫生管理的实际操作出发,如加强对垃圾、蚊虫和阴沟的处理,拆毁破陋的危房和草棚,督查一些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等,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作了简要介绍。《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和《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两文则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个微观角度——公厕运营方式、粪秽商办或市办入手,阐幽发微,深刻揭示了近代上海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的变迁过程及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等时代因素的制约作用和近代中国都市文明漫长而曲折的演进规律。这两篇文章无论从研究的视角还是从反映的思想内涵来看,都堪称近年来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的佳作。
在近代北京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杜丽红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初探——对北平环境卫生管理的实证研究》(47)、《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48)和Xu Yamin的《维护街头文明:与民国时期北京街头乱扔垃圾者、“粪霸”和随地大小便者之间的斗争》(Policing Civility on the Streets:Encounters with Litterbugs,‘Night Soil Lords’,and Street Corner Urinators in Republican Beijing(49))以及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50)是代表性成果。这几篇文章都从粪秽垃圾的管理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北平市政府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上的积极作为。而且,杜丽红和辛圭焕都立足于30年代北平城市粪秽管理的改革,再现了改革背后政府与一部分社会群体(粪商、粪夫)由利益冲突到彼此调适,由试图粪秽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复杂历程。杜丽红还从兼顾多数粪业从业者的利益、权衡自身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的角度,诠释了30年代北平市政府粪秽管理改革方案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必然性和切实性,阐发了一切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启示。辛圭焕则以为30年代北平“政府主导的粪业官办遭受挫折,而为粪商主导的官督商办形式所取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粪业改革方案都是由市政府主导的”(51),强调了粪业管理改革中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
在近代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上,赵文青的《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52)和潘淑华的《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53)是代表性成果。赵文青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几个方面,如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厘定、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拨以及具体的治理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对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潘淑华以广州城市粪秽管理为视点,阐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粪秽管理由商办到市办以及厕所规划由改良旧厕到建造新厕(水厕和女厕)的变迁。文章还指出“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在物质层次上,广州政府并未能够完成其改良厕所的大部分计划……政权介入粪溺管理后,厕所与以往一样的脏,一样的臭。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对厕所及如厕文化的新准则,以及改变了人们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构想。”(54)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20年的厕所和粪秽管理改革并未带来广州城市环境卫生实质上的改变,但却形塑了广州市民新的公共卫生观念和文化、生活追求。此文和上述杜丽红的《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辛圭焕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彭善民的《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等文章一样,是一种从“秽处”着手、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研究思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目前近代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上海、北京、广州之外,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研究也有所开展。朱颖慧在《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55)一文中,从道路清洁和垃圾运除入手,对近代天津清道组织的沿革、经费来源、清道计划等进行了梳理,呈现了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些细节。文章还指出包括天津在内的近代许多城市以清道为环境卫生管理重心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尚处于萌芽状态,人们的卫生意识和习惯依然稚弱。要想真正实现卫生的近代化,最重要的途径或许是树立人们正确的卫生认知,‘内化’人们的卫生习惯。”(56)这一认识为学界如何给予民国公共卫生事业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再次,对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的专门探讨。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朱德明的《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57)、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58)、褚晓琦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59)、Lillian M.Li and Alison J.Dray-Novey的《清季北京的食品卫生:政府、市场和警察》(60)(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State,Market,and Police)。Lillian M.Li and Alison J.Dray-Novey侧重于考察行政权力和卫生警察在清季北京食品卫生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朱德明和褚晓琦分别从食品检疫和菜场规范的角度对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微观研究,陆文雪则依据大量的工部局档案和卫生处年报,着眼于工部局建立、发展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过程,以及日常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对1898-1943年期间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以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为重要分支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诚然,如彭善民所言,陆文雪“在研究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上,尚可进一步展开,此外租界食品卫生管理对华界的影响亦可详加探讨”(61),但无论如何,《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代表了已有近代城市食品卫生管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同时,在近代城市学校卫生管理研究上,朱德明的《30年代上海部分学校卫生状况考述》对30年代上海租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概略性的探讨,认为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卫生股和学校医药事务股所规定的规章制度“已初具现代学校的医疗卫生管理模式”(62)。秦韶华则对30年代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进行了研究,在《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63)一文第二章中,作者从学校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立和嬗变、学校卫生管理和执行人员的专业化配置、各项管理措施的施行和改革这几个方面,对1929-1937上海华界学校卫生管理由偏重卫生到凸显教育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客观评价了上海华界学校卫生所取得的成效。
在近代城市妇幼卫生管理研究上,杨祥银的《婴儿死亡率与近代香港的婴儿健康服务(1903-1914)》(64)、赵婧的《1927-1936年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65)是代表性成果。赵婧一文从政府颁行相关法规训令、设立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妇幼卫生调查和宣传妇幼卫生常识等方面,考察了10年间上海市政府在妇幼卫生上采取的行政管理举措。杨祥银一文考察了香港殖民政府在近代香港婴儿健康服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种族因素对婴儿健康政策的形塑方式,建构了一种从宏观背景出发微观考量近代香港公共卫生事业的分析框架。
上述以外,关于民国时期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市政府在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上的策划管理,学界也有少量探讨(66)。
三 疫病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疫病是人类最可怕的公共卫生问题。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流动频繁,空间狭窄,加上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城市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城市便成为疫病滋生并且蔓延恣肆的温床。因此,在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阵痛中,疫病的频发无疑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疫病的频发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不良存在相当大的因果关系,疫病的肆虐又促使近代城市积极构建现代化的卫生防疫体系,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可以说,疫病的威胁是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起步、发展的重要推力。故而,从疫病流行和防治的视角去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机制的建构和发展,便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
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关于近代上海传染病流行和防治的研究上。胡勇的《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67)考察了1910-1949年间和平时期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及其对近代上海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指出传染病给近代上海社会造成消极后果的同时,这种灾变动力机制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如促进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等。稍遗憾的是,该文在内在逻辑性上有所欠缺,而且对疫病推动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探讨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刘雪芹的《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1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68)考察了1926-1937期间上海华界的疫情及国家和社会在疫情应对上的互动合作,并进一步探讨了瘟疫的爆发和流行给上海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带来的进一步完善,指出疫情应对促进了传统卫生习俗和卫生意识的近代化,推动了华界卫生防疫机制的近代化。刘岸冰的《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69)从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入手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包括传染病防治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传染病防治法规和防治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等。然而,此文对由传染病防治带来的除防疫体系的构建之外其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则涉及很少。李娴婷的《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70),从1910年11月“上海公共租界鼠疫风潮”切入,溯源式地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在1908-1910鼠疫风潮发生前这段时间,在鼠疫防治工作方面进行的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
除以上博硕士论文之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也围绕近代上海防疫与公共卫生建设进行了探讨。饭岛涉的《霍乱流行与东亚的防疫体制——香港、上海、横滨,1919年》(71),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上海、横滨三地的防疫体制,认为上海租界地区与香港和横滨一样此时已经确定了初步的公共卫生制度,各地受霍乱侵害的程度明显降低。福士由纪的《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以霍乱预防运动为例》(72),对抗战时期上海由于难民迁入过多、卫生状况较差而导致的霍乱流行,及日本人和日伪政权为维持统治稳定、防止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大量防治措施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时上海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强烈干涉和介入个人身体的倾向进行了揭示。她的《国际联盟保健机关与上海的卫生——1930年代霍乱的预防》(73),则同样以霍乱预防运动为背景,考察了国际联盟保健机关对30年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在《战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振——以防疫设施的接收管理问题为例》(74)一文中,福士由纪又以防疫设施的接收管理为例,对抗战胜利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构进行了探讨。曹树基的《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75),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对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生态关系和公共卫生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由此,文章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把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该文视角新颖、叙事方式独特、立意深远,是将人群生命史、生态环境史等新社会史研究理念熔于一炉的典范之作。殳俏的《回眸近代上海霍乱大流行》(73),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直接领导的几种反霍乱运动,意在反映近代上海租界工部局建构并实施的公共卫生应对机制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郑泽青的《昨天的抗争:近代上海防疫掠影》(77),生动呈现了近代上海社会在疫病的威胁下,在租界当局采取的冷漠而又科学的防疫措施的冲击下,逐步接受新理念,建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历史片段。宋忠民的《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78),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关于狂犬病例的统计、狂犬病预防措施和治疗狂犬病的制度化方案,认为租界工部局进行的狂犬病防治工作“促进了上海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由此构成了公共租界乃至上海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79)。
以上论文虽各自有所侧重,但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立论,那就是疫病给近代上海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上海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和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学者以某种传染病的长期流毒为据,揭示了上海华洋各界在此公共卫生问题上的不作为倾向。安克强先生在《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80)一文中,就透过性病在民国时期上海乃至中国各省市包括边缘省市流播蔓延的视角,批判了华界当局对性病防治的漠视和租界公共卫生政策的局限性。
四 社会力量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作为近代概念的公共卫生,其立足点在于国家卫生行政,即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有研究者就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81)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绝离不开都市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中,反映社会力量参与疫病应对和公共卫生建设的有不少,但是专门性的探讨并不多,其研究基本是围绕近代上海政府和社会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互动而展开的。
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中专门设置一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强调民间组织与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上是一种合作与互补的关系,认为近代上海社会力量主要是以两种方式参与公共卫生建设:一是社团公共卫生宣传,二是民间时疫救治,指出民间社团进行的公共卫生宣传“基本上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上,有时更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民间时疫救治也在客观上“弥补政府时疫救治的不足”(82)。在《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与政府组织的时疫救治相比较,民间组织的时疫救治体现出较强的自愿性,服务态度积极,受到了社会的好评”。由此,他高度评价了社团公共卫生宣传和民间时疫救治的积极作用,认为它们“不仅促进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彰显了近代上海公共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增长,促进了近代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83)
彭善民对上海都市社会与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互动合作虽然着墨甚多,考察也颇成体系,但他着重于探讨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公共卫生活动本身,而对于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力量何以如此踊跃地参加公共卫生建设,民间社会力量的公共卫生活动对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又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并无太多集中的论述。马长林、刘岸冰的《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则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以传染病防治为切入点,首先阐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力量对传染病防治活动的积极参与,在这里作者除了提到“众多社会团体开展防疫宣传”之外,还对媒体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加以凸显,即媒体展开有针对性地督促和批评以及民众踊跃配合;其次,文章集中探讨了民间社会的积极反应对公共卫生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具体影响,包括“促进了卫生防疫机构及其职能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得以出台”、“影响民众接受和确立公共卫生观念,使传染病防治措施得以推行”和“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公共卫生知识”(84);最后,文章还对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力量所以积极参与传染病防治活动,以及上海何以会形成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进行了一定的剖析。这篇文章虽只是从传染病防治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力量在公共卫生建设上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但是代表了一种研究理路,因此它和彭善民的考察实际是互补长短,相得益彰。
另外,前述胡勇在《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中,特别以中华麻风救济会在近代上海麻风救济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为典型,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秦韶华在《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中也认可了上海社会力量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李娴婷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中,对华人精英在租界卫生防疫体系建构和措施开展中所起的协调和助推作用也给予了真实的定位。侯宣杰还选择民间商人团体这一民间社会力量的重要元素,从参与市容整顿、卫生管理、防治疫病(85)几个角度,对他们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钩沉。
五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
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来看,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起中国传统的卫生管理模式,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效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当这种发源于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中国近代城市之时,它固然推动了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中国都市文明的发展。然而,这种伴随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制度,从在租界实行起也毫无疑问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因此,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不可能不涉及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问题。
在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问题的探讨上,现有研究主要谈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的表现;二是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化的局限性。
关于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的表现,20世纪30年代阮笃成先生就指出,“租界内的一切医疗设施主要为洋人服务,华人虽蛰居数十万人而为其服务的医院寥寥无几。”(86)何小莲也指出,“租界所承办之卫生事务,无一不是以保护界内侨民,特别是欧美侨民为前提。”(87)彭善民也认为,“租界公共卫生设置和管理主要是围绕自身公共健康的需要”(88)。安克强更是尖锐地指出,“公共租界当局除了外国侨民的卫生以外什么也不关心”(89)。研究者们认为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还表现在,租界执行公共卫生管理时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和自我优越感。胡成指出,“在外人市政当局看来,香港、上海等地与外人毗邻而居的华人社会……均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当疫病爆发之后,将某种特定传染病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之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其中隐含的种族偏见,自不待言。”(90)彭善民认为,“早期工部局卫生处,对于西人和华人食用猪肉的检验区别对待,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91)赵宝爱也认为,租界当局在对待租界内被视为公共卫生威胁物的义冢、丙舍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近乎野蛮的行为,固然因‘不了解华人思想’所致,其实也是强势文化的反映。”(92)陈蔚琳把工部局在租界内强制实行妓女体检措施时排除外国妓女、只针对西人常去妓院的华人妓女的现象归结为“侨民潜意识里在公共卫生上的自我优越感及对华人的偏见在作怪”(93)。崔文龙则指出,德国在胶澳租界地(青岛)建设规划中一系列卫生条文的颁布“基于殖民统治当局这样一种假设,即华人不讲卫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而处理的唯一办法便是强制性的迁移住所和严密的社会监控。这就使得种族主义在卫生措施的旗帜下,以胶澳总督府的强权统治为后盾,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得以实施。”(94)
另外,研究者们也把攫取经济利益、扩张领土以及维持军事强势置于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表现的视阈之中。彭善民指出,“在粪秽的承包处理上,租界当局部分官员常与华界少数人勾结牟利,造成垄断之势,严重损及普通人的利益。”(95)崔文龙也认为,胶澳总督府在胶澳租界地建设规划中“强调卫生措施的背后,隐藏着殖民者攫取现实利益的企图”,他还认为由于“在军队中,对于疾病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负”,所以德国强调卫生措施也“是和殖民当局的军事性分不开的”(86)。顾德曼则指出“公共健康为外国市政当局在中国土地上的扩张提供了重要途径”(97),李娴婷也指出“从1909年开始,工部局就试图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借口来扩展租界的边界。”(98)
关于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化的局限性,彭善民认为,“租界卫生管理的殖民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科学管理制度的实施”(99)。《天津城市史》则针对天津的情况,反映了八国租界从各自利益出发进行殖民化公共卫生管理的结果——排水工程混乱、租界与华界公共卫生对比悬殊,指出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乃至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呈现一种畸形成长的状态(100)。
在备受列强凌辱的近代中国,租界公共卫生的成效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性的暴露,必然会激发城市社会中华人的民族自觉,进而推动华界乃至整个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因此,近代中国(开埠)城市公共卫生有着鲜明的殖民色彩,更彰显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特性。
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民族性问题上,Ruth Rogaski颇有研究。她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一书中,以近代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阐释了“卫生”概念在近代中国所隐含的多重意义,认为它不只是指个人养生和获得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方法,也不只是指与医疗、公众健康有关的行政制度,它还是体现“现代性要求”和“民族性”的话语,它代表了中国国家、社会与民众从落后、病态、传统提升到先进、健全、现代,以实现民族自立、国家富强的迫切需要。她还在《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一文中,把天津知识阶层和行政官员在公共卫生上的民族意识归结为两点,即“通过实施卫生近代化,天津将能够加入到世界城市的行列……卫生近代化的实施,也能减少外国列强借口控制疾病要求扩展领土的风险,以及城市一步步被多国租界瓜分的威胁”(101),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双重动机——保卫中国主权和赞成卫生近代化是近代文明的核心——为20世纪天津的中国人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赋予了活力”(102)。另外,台湾学者梁其姿也以麻风隔离政策的近代变迁为透视点,认为西化防疫措施的采用“充分显示了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选择”(103)。
大陆研究者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民族主义特性也多有揭示。何小莲认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兴市之计划,既有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之国际视野,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104)赵婧认为,“一种语境始终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之推展”,那就是“富国强种”(105)。杨祥银认为,1928-1937期间上海卫生局举办的卫生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倒不如说是为了进行一场倡导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社会总动员。”(106)彭善民指出,“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殖民性又“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107)。胡成也总结,“在那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年代,关于华人‘不卫生’的讲述体现外人的强烈文化优越感,同时也激发华人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外人市政当局借公共卫生之名,乘机攫取华界市政管理权,华人社会为捍卫主权而注重公共卫生事业的推展。”(108)
关于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殖民性与民族性问题的探讨,包括上述在内的诸多论著均有涉及,但是专门性的探讨尚不多见(109),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特别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民族性内涵的解读上,除了诠释其捍卫主权、振兴民族的政治意蕴,笔者以为还可以挖掘一下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发展所具有的民族形态和民族内质。
六 公共卫生与近代城市政权扩展
公共卫生既然以国家卫生行政为立足点,那么,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公共卫生事务行政化、制度化加深的过程,进一步而言,也是政权扩展和政府职能泛化的过程。有研究者就指出,“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确立,扩大了政府的职能,部分变化了政府的理念,是中国政府由传统上的‘小政府’向近代以来的‘大政府’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一个具体体现。”(110)梁其姿也认为,“无论哪一国的公卫制度,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已成为政体重要的构成部分。”(111)曹树基更是明确指出,“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和与完善的过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直至民众完全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112)因此,在现有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中,也存在一种探讨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权扩展相关性的研究视角。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近年来着力于从医疗史角度观察和理解现代政治的杨念群先生开展的。其代表性成果有《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113),三文以民国初年北京传统社区内控制生和死并具有文化与仪式协调功能的接生婆和阴阳生职业的没落为叙事背景,考察了兰安生模式、卫生示范区,即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以现代预防医学为指导的公共卫生医疗网络,在北京逐步确立的过程。认为这种来源于西方的制度监控形式(指现代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甚至比另一种形式(指警察系统)更为有效地打破了城区人民原有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实现了“自然社区”和“医疗社区”的全面叠合,把北京人的出生和死亡纳入到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档案化网络之中。文章实际上指出公共卫生网络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对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塑造、规训、调控和惩戒的过程(114)。显然,他把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推进与城市政权的扩展视为孪生物了。赵婧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10年间上海妇幼卫生事业时,也把妇幼卫生行政的实施看作是“政府企图在现代化的框架下,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控制城市社会生活。”(115)另外,Ruth Rogaski在对近代天津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中,也倾向于“把公共卫生的历史论述为社会控制的缓慢增长和政府权力不知不觉的扩展”(116)。
结语
根据以上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现状的梳理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就对象而言,都是近代约开较早的口岸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上海为焦点;就主题而言,集中在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公共卫生管理特别是环境卫生管理、卫生防疫这几个方面;就方法而言,主要是个案实证和微观论述。由此,笔者管见以为,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首先,扩大研究对象。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固然是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先行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他规模较小或约开较晚的口岸城市,甚或非口岸城市在近代就没有公共卫生可言。正如余新忠所言,“若不能立足于中国社会内部,从内外双重视角来观察中国近代卫生观念与行为的变迁,也就很难真正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变迁的种种复杂图景,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与近代的接榫问题。”(117)换句话说,一些西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城市,随着自身内部因子的嬗变、民族主义诉求的增强、城市近代化的推进以及国家范围卫生现代性的追求,到了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其公共卫生事业都会得到或多或少地兴办和发展。然而,有关这些城市公共卫生的系统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其次,丰富研究课题。除深化目前集中探讨的城市环境卫生、卫生防疫等课题以外,要增强对近代城市食品卫生、营养卫生、妇幼卫生、学校卫生、工厂卫生、劳动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专题的考察和挖掘。
再次,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方面,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个案研究中,尽可能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加以分析考量;另一方面,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尽可能开展华界与租界或者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甚或某个城市自身的纵向比较研究,也力求把微观研究纳入宏观审视的框架,把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整合起来进行探讨。
苏智良先生说,“公共卫生史的发掘与研究,尚是近数年的事情,它的兴起,是中国史学变革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入的一个标志。同样,人们对公共卫生史的情有独钟,也正是注意到了加速城市化和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118)诚然,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民国后期就始发于公共卫生学界和医史学界,但历史学界因应史学变革和现实关怀的需要,以社会、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使之成为以开展多学科对话交流为特征的新史学、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使之生机勃发,确实是近数年的事。因此,近代公共卫生特别是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处于成长时期,祈望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注释:
①1987年台湾学者梁其姿首先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分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53页;“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Vol.8 No.1,pp.134-166.
②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
③疾病史研究与公共卫生史研究在关注点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两者在研究内容、研究旨趣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本文在探讨中可能会涉及疾疫史的研究,但都是为考察公共卫生研究现状而服务的。
④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⑤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⑥褚鸣皋:《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护士之重要》,《中央日报》1934年8月5日,第3张第2版。
⑦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65-270页、第366页。
⑧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⑨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3页。
⑩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年版。
(16)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7)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18)Kerrie 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9)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0)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第234页。
(22)朱德明:《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1期。
(23)李达嘉:《公共卫生与城市变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个观察》,中国史学会编《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研究报告集:中国の历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展》,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71-108页。
(2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九十一年度学术研究成果,2003年4月7日,http://www.sinica.edu.tw/info/research-results/91/imh1.pdf,2008年11月20日。
(25)Chieko Nakajima,Health,Medicine and Nation in Shanghai,ca.1900-1945,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4.
(26)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7)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290页。
(28)Ruth Rogaski,From Protecting Life to Defending the Nation:the Emergence of Public Health in Tianjin,1859-1953,Ph.D Dissertation of Yale Univ.,1996; 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9)周瑞坤:《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s)》,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
(30)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第66页。
(31)周启明:《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32)林靖:《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以卫生检疫、粪污处理及自来水事业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
(33)陈媛:《从基督教福音到公共卫生——近代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概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医科大学,2006年。
(34)杜丽红:《近代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博士后报告,中山大学,2007年。
(35)孙善根:《南京政府十年期间公共卫生事业述评——以浙江宁波为中心的考察》,辛亥革命与民初社会暨第三届民国浙江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杭州,2008年7月,第96-104页。
(36)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
(37)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38)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述评》,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3年。
(39)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18页。
(40)杜丽红:《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
(41)杨韵菲:《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初探》,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医科大学,2007年。
(42)刘岸冰:《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史林》2006年第2期。
(43)朱德明:《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环境卫生治理概况》,《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4期。
(44)苏智良 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史林》2006年第3期。
(45)彭善民:《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6)刘岸冰:《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史林》2006年第2期。
(47)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初探—对北平环境卫生管理的实证研究》,《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9)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9)Xu Yamin,"Policing Civility on the Streets:Encounters with Litterbugs,'Night Soil Lords',and Street Corner Urinators in Republican Beijing",Twenties-Century China,Vol.30,No.2.
(50)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
(51)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第163页。
(52)赵文青:《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年。
(53)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
(54)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
(55)朱颖慧:《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56)朱颖慧:《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93页。
(57)朱德明:《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6期。
(58)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
(59)褚晓琦:《近代上海菜场研究》,《史林》2005年第5期。
(60)Lillian M.Li and Alison J.Dray-Novey,"Guarding Beijing's Food Security in the Qing Dynasty:State,Market,and Polic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8,No.4.
(61)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8页。
(62)朱德明:《30年代上海部分学校卫生状况考述》,《中国学校卫生》1997年第6期。
(63)秦韶华:《上海市华界中小学学校卫生研究(1929-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64)杨祥银:《婴儿死亡率与近代香港的婴儿健康服务(1903-1941)》,《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
(65)赵婧:《1927-1936年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2期。
(66)相关研究可见杜丽红:《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公共卫生教育概况》,《北京档案史学》2004年第3期;
Chieko Nakajima,Health and Hygiene in Mass Mobilization:Hygiene Campaigns in Shanghai,1920-1945,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4,No.1.
(67)胡勇:《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
(68)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1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
(69)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硕士学位论文,东华大学,2006年。
(70)李娴婷:《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71)饭岛涉:《霍乱流行与东亚的防疫体制——香港、上海、横滨,1919年》,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2)福士由纪:《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以霍乱预防运动为例》,《现代中国》第77号,2003年10月。
(73)福士由纪:《国际联盟保健机关与上海的卫生——1930年代霍乱的预防》,《社会经济史学》第70-2期,2004年5月。
(74)福士由纪:《战后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振——以防疫设施的接收管理问题为例》,《一桥研究》第29-4期,2005年1月。
(75)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6)殳俏:《回眸近代上海霍乱大流行》,《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
(77)郑泽青:《昨天的抗争:近代上海防疫掠影》,《上海档案》2003年第4期。
(78)宋忠民:《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5期。
(79)宋忠民:《上海公共租界的狂犬病防治》,《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5期。
(80)安克强:《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徐新华译,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1)余新忠 赵献海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388页。
(82)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175-226页。
(83)彭善民:《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84)马长林、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85)侯宣杰:《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86)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杭州永宁院法云书屋1936年版,第135页。
(87)何小莲:《冲突与合作:1927-1930上海公共卫生》,《史林》2007年第3期。
(88)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83页。
(89)安克强:《公共卫生政策与殖民主义放任政策的对立——上海租界的性病与卖淫》,徐新华译,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90)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91)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84页。
(92)赵宝爱:《近代城市发展与义冢、丙舍问题——以上海为个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93)陈蔚琳:《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36页。
(94)崔文龙:《德国在胶澳租界地建设规划中的卫生措施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
(95)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86页。
(96)崔文龙:《德国在胶澳租界地建设规划中的卫生措施及对中国人的歧视》,《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
(97)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98)李娴婷:《近代上海公共租界防疫工作考察——以1908年-1910年鼠疫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27页。
(99)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87页。
(100)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360-364页。
(101)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02)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第158页。
(103)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04)何小莲:《冲突与合作:1927-1930上海公共卫生》,《史林》2007年第3期。
(105)赵婧:《1927-1936年上海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2期。
(106)杨祥银:《卫生(健康)与近代中国现代性——以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1937年)》,《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
(107)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291-292页。
(108)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
(109)胡成先生的《“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考察》可以视为一篇另类诠释近代城市公共卫生殖民性和民族性的专文,同时,该文深刻指出,“围绕着华人‘不卫生’的讲述,中外双方虽各有不同的考量和投射,并常以冲突和竞争的形式展开,却共同开创和推动上海公共卫生的现代性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
(110)余新忠 赵献海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第305页。
(111)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
(112)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13)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98页。
杨念群:《“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杨念群:《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
(114)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
(115)赵婧:《1927-1936年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以卫生行政为中心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2期。
(116)罗芙芸著《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作舟译,《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第178页。
(117)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页。
(118)苏智良:《鉴往知来和谐发展(代序)》,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第1页。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公共卫生硕士论文; 食品安全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卫生论文; 预防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