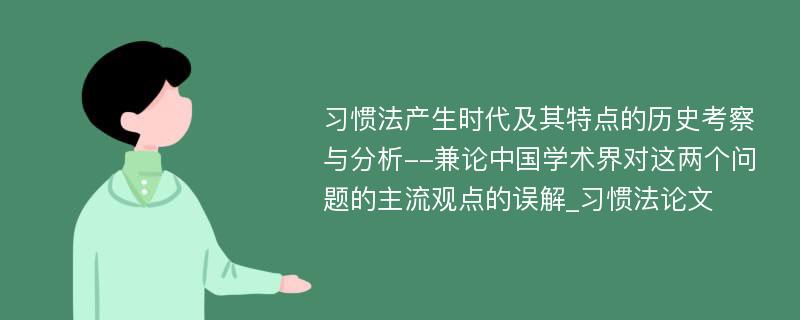
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及其特点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兼论我国学术界在这两大问题上主导观点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在这论文,两大论文,学术界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2-0125-08
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的形成所经历的漫长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类社会早期没有法律,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传统,即习俗;进入阶级社会后,较多体现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国家法才出现。从习俗发展到国家立法,其中间阶段是习惯法,即法律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习俗、习惯法和国家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法制史关于习惯法(Customary Law)产生于什么时代及其特点的问题上,我国权威的辞书和论著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观点,这就是:习惯法产生于国家(即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是统治阶级把有利于本阶级的、不成文的习惯提请国家机关确认而成。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习惯法”条目的释文说:“国家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是法的渊源之一。”[1](第87页)《辞海》条目“习惯法”的释文是“统治阶级对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习惯,通过国家机关加以确认,并赋予法律效力的,叫习惯法。”[2](第96页)薛梅卿等著的《中国法制史稿》一书认为:“从无法律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法律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法律的过渡时期。法律的胚胎或萌芽发展到夏朝则表现为习惯法。”[3](第10页)郭建等所著《中国法制史》认为:“法律从原始氏族习惯到阶级社会的习惯法及早期成文法,到公布成文法运动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4](第1页)类似观点的辞书和论著还有很多,将以上引文中的观点加以归纳,大体可以列出以下几个值得质疑的问题:
1.关于法、法律的产生是经历了两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的问题。按上述权威观点,法律产生的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原始社会没有法,然后从没有法到出现国家法。这里的突出问题是:法、法律这一社会上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社会制度建设成果,为什么从无到有竟没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没有过渡阶段,而只有突变?试问,这种突变论符合历史实际吗?
2.关于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和历史条件问题。按上述权威观点,习惯法的产生时代是阶级社会形成之后,习惯法的产生是统治阶级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习惯,提请国家认可而成的,那么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原始社会末期就没有产生过一些带有一定阶级性的法、法律和类似的规范吗?既然“习惯”是在没有阶级划分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这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习惯”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这种“习惯”究竟是什么?
3.关于习惯法的制订者是什么机构的问题。这种习惯法由“国家认可后生效”,虽然认可后还不成文,但已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认为习惯法的制订者仍然是国家。在国家产生以前,难道父系氏族、部落及其联合体、农村公社或城市公社等已有阶级萌芽或一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形态中,就没有产生过一些带一定阶级性的法、法律和类似的规范吗?
4.关于习惯法内容为谁服务的问题。按照上述观点,习惯法是全面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从世界上一大批习惯法的内容看,许多条款既维护公有财物,又维护财产的私有;既维护社会成员平等,又开始维护一部分人的局部特权、父权和夫权等。那么,这种具有社会转型时期二重性的内容是为谁服务、又是在什么时代中产生的呢?
5.关于习惯法的执法者的问题。上述观点认为习惯法的执法者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机关,而历史实际则是大量习惯法的执法者是部落、农村公社或农村公社下的村寨与村寨联合体以及城市公社等。我们难道可以对后者视而不见或将之归之于国家政权吗?
按照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上述广为流行的主导观点不符合世界上有史实可考的大多数民族的历史实际。我们认为这一习惯法的定义主要是受英美法系习惯法定义的影响。这里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英国法制史中“习惯法”概念使用的发展过程。
公元五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等日耳曼部落从欧洲大陆侵入不列颠,相继建立了十几个王国,当时实行不统一的、分散的地方习惯法。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国后,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加速了英国封建化的进程,为适应中央集权制和统一司法审判权的要求,就对过去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加以利用、改造,并在判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全国普遍通用的普通法(Common law)。正如《牛津英国历史指南》中所说:“到爱德华一世(1272-1307)时,‘普通法’一词就已经存在,它是(原来)全国各地法庭所实行的法律(习惯法),因此而‘普遍通行’于整个王国”。[5](第231页)
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迅速崛起以及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其法律制度也对其殖民地国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直到18世纪末,在英格兰和它的海外殖民地,普通法的这一习惯法主体仍处在演进之中,并经历了现代化的进程”。[6](第492页)英美法(Anglo-American Law)是英美法系的主体,是当今世界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直接在日耳曼习惯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第二,判例法是其法律的主要形式;第三,诉讼法中心主义。[7](第16页)
把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定在国家产生以后的观点,实际上是在简单接受英国法制史有关观点的前提下,进而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把我国法制史、世界法制史发展的进程教条化了。这一套用,脱离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历史实际,对研究法、法制发展的完整过程和规律性造成了根本性的失误和损害。我们认为,这是法制史上一个重大问题,有必要依据社会历史实际,探明法律产生的序列问题,以期达到清源正本、明辨是非的目的。
二、关于习惯法产生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的生产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简单的原始公有制下孕育着私有制的萌芽和雏形,民主平等的社会中初步产生出等级与阶级的差别。习惯法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既有条件地承认原始共产制与公有制和原始民主的平等关系,又有开始以法权形式承认并维护已产生并初步成长的地域关系成份、私人生产与私有制成份、等级与阶级的差别和贵族特权的成份。以下两个典型事例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
事例1:阿兹克特人。摩尔根认为15世纪到16世纪的阿兹克特人“处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略微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洛印第安人”[8](第188页)。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记述,对当时阿兹克特人的社会状况作了一段描述:“财产,个人财产显著增加。个人对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仍是部落共有,但此时已划出一部分作为维护管理机构之用,另一部分则用于宗教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即人民借以谋生的部分,则在各民族之间或住在同一村落的各公社之间分配。没有人对土地或房屋拥有个人所有权。”[9](第387页)这当中“维持管理机构之用”和“用于宗教方面”的土地如何耕种,收入如何分配,都没有讲清,但从其他民族较后阶段的资料可见,这两种土地都由平民和奴隶耕种,其收入一部分作为共同体的支出消费掉,另一方面则成为这些方面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收入。由此可见,氏族首领在与氏族成员的关系上虽然共产制还占主要方面,土地仍属共有,但这其中剥削他人的成份已经显露出来,氏族首领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程度也已较前严重。马克思将这一现象概括为:“由于在同一管理机关之下的人数增多和事务复杂化,社会中的贵族成份以微弱的形式体现在民事和军事酋长中。”[9](第386页)
事例2:云南景颇族。解放前我国云南景颇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地域公社时期,景颇族农村公社首领也称“山官”,山官多由氏族酋长转化而来。因为山官担任公职付出劳动,群众已有意提供报偿。凡村民猎获野兽或杀牲祭祀,都送山官一腿肉,称为“宁贯”;同时又因山官调解纠纷费时较多,陇川县邦瓦寨经村民会议讨论后决定每户每年送山官谷子一驮(2箩,合60市斤),称“石瓦谷”(“石瓦”为“公共”之意)。后来因为有些户头拖欠不交,改为每年春播和秋收时,全村劳力都各为山官劳动一天,称为“石瓦拢”。[10]
“石瓦谷”、“石瓦拢”的性质,主要方面还是山官公职劳动的合理报酬。但由于是群众献出,人多物多,数量自然无法与山官劳动对等,其中已隐藏着山官的多占,从而开始使这种习惯法具有了合理及不合理的两重性、过渡性和短暂性。到了国家出现后,官员的报酬就被捐税代替了。
三、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及其制定者
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逐步出现,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变动、大分化:一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进步都在加快;另一面是人们之间出现了地域关系(与原来的血缘关系并存);财产仍为公有制但也出现了部分私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也出现了个人因分工担任公职而形成了个人权力。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起来,为了调解纠纷,处罚肇事者,维持当时社会秩序等,需要协调这种逐步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习惯法就出现了。习惯法产生、盛行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时代及其晚期与地域公社(农村公社、城市公社)早期并存的时代,习惯法的制定者(或认可者)是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农村公社、城市公社的首领或首领们的联席会议。
以古希伯来人为例。古希伯来人(犹太人)留下的一些古文献,后来基督教称之为《旧约》,与基督教的文献《新约》合称为《新旧约全书》,即基督教的《圣经》。《旧约》中原文虽缺乏具体实践时间的记载,但只要对内容进行分析,其所属的社会阶段还可以弄清。大体说来,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南部迁徙到巴勒斯坦边境,是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从亚伯拉罕直到摩西为首领的数百年间,是原始社会晚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相当于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分期的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还是公有的,父系血缘关系还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但产品在家族内已有私有成份。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希伯来人中产生了习惯法。
《旧约》的许多篇章都涉及到习惯法。它把希伯来人一切行动和一切规章、法律的形成,都归之于上帝耶和华的意志,都是上帝通过他们的首领(从摩西开始,名望高的又称为“先知”)下达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肯定是以其社会实际为基础的,其中《申命记》最为典型。《申命记》所载的内容已有国家法,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国家产生之前的。在《申命记》中,实际是摩西和众长老、民众“立约”或宣布“律例”,但往往由摩西号召民众学习和听从这些“律例”。例如,《申命记》先后记载“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第27章第1节);在摩押,“摩西招了以色列众人来与众人立约”(第29章第2节);摩西吩咐祭司:“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法律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第3章第11-12节)。如此等等,显然这些活动都是确定大事的重要会议。由此可以想见,习惯法正是由这些会议决定和公布的。
再以中国的盘村瑶族为例。中国广西大瑶山盘村瑶族,在中国近代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刀耕火种的阶段。虽有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其本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农村公社形成不久的时代。农村公社村寨的头人为解决日增的社会矛盾,联合制定了习惯法,这是十分明确的。盘村瑶族的石牌制度,是农村公社初期各村寨所实行的习惯法,它是由一个或几个村寨为一个单位所订立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叫“石牌律”。除大多数石刻外,也有少数写在白纸上或木板上。村寨的主要领导者是“石牌头人”,他是村民纠纷和争执的裁决者。石牌头人的产生是由于他处事公道,裁决公平,渐渐得到大家的信赖与拥护,就自然地成为村里的头人。这些人不脱离生产,但在解决纠纷中可以得到少量的报酬。
石牌的成立,首先是通过石牌会议来讨论石牌头人事先制定的规条,认为切实可行后由一人在会议上宣布,大家以默认或欢呼的方式通过。通过的“石牌律”是人们处理山内外关系、解决婚姻、田地、山林纠纷的准则,也是惩办违犯石牌的最高依据。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阐明订立石牌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生产;保障人身安全;防匪盗等”[11](第106-107页)。
再以法兰克人为例。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以克洛维为部落群的首领,正处于军事民主制的时代。克洛维在打败西阿格里乌斯后对教堂进行了抢劫。碰巧有一只很大的广口瓶(是一圣杯)被抢走,教堂的主教派遣使者去见克洛维,向他提出要求,说如果其他圣器不能归还的话,至少让他的教堂收回这只瓶子。结果克洛维说:“跟我们到苏瓦松去,因为我们所有的战利品都要在那里分配,如果我抽签抽中了那只瓶子的话,我一定满足你们主教的愿望。”[12](第81页)对战利品进行“抽签分配”,正体现了习惯法的执行问题。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抽签分配”的分配方式肯定是这时期的军事首长及他们的联席会议制定的,平等、公平观念在分配中还是主流,即使作为军事首长的克洛维也要遵守这一规定。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公元1世纪末的德意志人立法权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决定由人民来做,报怨声表示反对,喝彩、敲打武器表示赞成”[13](第140页);公元前9世纪古斯巴达人在形成国家前夜由莱库古制定的立法;公元前6世纪中叶古罗马人由塞尔维·图里阿制定的立法等;又如,中国达斡尔族的“莫昆会议”(氏族会议),它是习惯法的制定机关,“莫昆达”(氏族长)是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莫昆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莫昆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具有最高的约束力。[14](第271页)由此可见,习惯法的制定者都是原始社会晚期氏族、部落、农村公社、城市公社的首领或首领们的各种会议。而且,在国家与法的起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不认为法律与国家是同时产生的,甚或先有国家后有法律。恩格斯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法,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15](第238页)
四、关于婚姻家庭的习惯法
处于父系氏族晚期时代的婚姻家庭也具有过渡性、二重性的特点。在父系氏族家庭里,妇女在家庭中还占有重要位置,但父权、夫权已开始产生,并逐步强化。即:既维持男女平等,财产共有,同时由于男子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加强,又开始维护一定程度的夫权和父权。在财产继承上既还部分地体现着男女平等,同时又对女性作了一些限制。因而作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习惯法也具有过渡性和二重性的特点。
以英国克尔特族威尔士人的婚姻家庭习惯法为例。威尔士人住在今英国威尔士一带。从英格兰国家征服威尔士以前到11世纪,它还处于父系氏族晚期和农村公社刚出现不久的时代,还存在“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克尔特族威尔士人的习惯法在婚姻方面这样规定:第一,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以后才能不被解除,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第二,婚后,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但除此以外,不允许再处罚她。第三,夫妻分离时如果有三个孩子,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13](第127页)
再以拉丁美洲玛雅人的婚姻家庭习惯法为例。玛雅族印第安人住在墨西哥东南尤卡坦半岛一带。15世纪到16世纪前期,玛雅人已使用铜制工具,会制造金银器,主要经营农业,种植玉米、南瓜、可可等。这个时期虽然玛雅人上层已有国家机关,但社会基层组织处于农村公社刚产生不久、父系氏族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玛雅人的习惯法规定:青年男女订婚后,未婚女婿常常要在岳父家劳动五六年,少的也得四五年。岳父若不满意,可将未婚女婿赶走。结婚从夫居后,丈夫可以遗弃妻子,妻子也可以离开丈夫,重新结婚。不过,一般妻子得不到好评。“离婚后,幼孩留在母亲身边;成年男孩随父,女儿随母。”[16](第7页)同时,妇女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妇女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不许入庙,不许与男人共食,甚至不许在街上正视男人。“妻子不贞要受男人的惩罚,父母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17](第81页)
还可以古希腊人的婚姻家庭习惯法为例。希腊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亦即处于英雄时代(野蛮高级阶段)。古希腊关于婚姻家庭的习惯法也具有这个时代的特色,其财产继承方面的“承宗女”制规定: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有通婚的权利和义务。恩格斯就此指出:“希腊人……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既然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法权的基础。于是,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之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非这样不可。”[13](第95页)这条习惯法保存了氏族财产不得带出氏族的制度,却破坏了氏族内男女不得通婚(即氏族族外婚)的制度。
五、关于处理人身伤害的习惯法
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之间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等血腥的复仇习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要求区别人身伤害的性质,以限制冲突、仇杀和减少伤害。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随着血缘关系的趋于松弛和氏族、部落酋长、军事首长与普通成员的社会分工,这种要求逐步体现在这个时代的习惯法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努埃尔人在原始社会末期血族复仇中形成的“豹皮酋长”,在处理血族复仇方面具有习惯法内容的性质。“豹皮酋长”是努埃尔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权威调停人,这类调停人在一定区域的若干村落中是大家公认的权威。为区别杀人的性质,在发生杀人案件后,凶手逃到“豹皮酋长”的住房,即取得避难权。被杀者的近亲承认“豹皮酋长”的住房是避难所,决不会进入这所住房杀死凶手。此后,“豹皮酋长”即着手了解案件性质并进行处理。其实,“豹皮酋长”只是一名调停人,而不是酋长,“他无权强迫任何一方来谈判,而且一旦对事件作出了裁判,他也无权强制执行。然而争端的双方都属于同一社区并期望能避免一场血族冲突,所以他们通常愿意达成一致意见,而首领正是利用这一事实来进行裁决的”。[18](第48页)
从《旧约》中所列古希伯来人的发展过程来看,大体在他们的首领摩西及其继任者约书亚的时代,古希伯来人的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后期,同时开始形成农村公社和城市公社。《旧约》记载摩西在巴勒斯坦先后设立六个“逃城”,似可认为城市公社其时已经出现;约书亚征服迦南人部分地区后,部落成员用绳子丈量土地,通过拈阄按块分给定居下来的古希伯来人,这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农村公社。在摩西率众先后占领约旦河以东及以西的过程中,为区别杀人案是故意伤害还是误杀,创立了六座“逃城”作缓冲,规定凡杀人者跑进“逃城”,即受到城内长老的保护,被杀者的亲属不得立即杀死杀人者。随后由长老主持查明案情,若是故意杀人,“要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意杀人的杀了”,并规定“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若是误杀,例如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扔石头致人于死等”,会众就要按照典章,在打死人者和报仇者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误杀人者脱离报仇人的手。”但若误杀者在“逃城”以外被报血仇人所杀,“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见《旧约·民数记》第35章、《旧约·申命记》第5章)。我们知道,完全意义上的血亲复仇属于氏族的习俗、习惯,有关规定没有习惯法的意义。上述“逃城”法则属于习惯法,它是“习俗”、“习惯”的一个发展,是因仇杀现象增多而试图分辨案件性质即区别故意杀人与误杀的一个创造。这一创造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从处理血亲复仇的习俗实践中产生了一个飞跃,创立了一个新的法律制度。
六、关于首领职位的习惯法
在父系氏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时期,私有财产和阶级作为社会整体中的次要成分已经出现。在社会管理上,相对于母系氏族而言也必然发生重大变化。首长职位的设置较前固定,这一职位的人选虽然还由选举产生,但又开始由选举向父子世袭过渡。例如德意志人。恩格斯针对德意志人的情况说:“向父权制过渡,象在希腊、罗马一样,使官职逐渐由选举变为世袭,从而促进了各氏族中贵族家庭的产生。”[13](第141页)德意志人在军事民主制时期,人民大会是部落的最高权力机构。塔西佗认为“大事由全部落决议”,首长是“按出身推举产生的,人民大会还有选举和罢免首长的职权”。关于军事首长,塔西佗认为:“有些人因为出身高贵或因祖上有卓越的军功,在尚未成年之前即荣膺酋帅之位”[19](第60页)。再如古希伯来人。从分析《旧约》内容可大体确定从亚伯拉罕直到摩西为首领时,希伯来人的基本社会单位是父系氏族,基本经济单位是父系家族。恩格斯依据“摩西一经”谈到亚伯拉罕是“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酋长”[13](第51页)。这里说“实际上世袭”是因为世袭还没有成为一个严格的制度。这又可说明,既已出现父子世袭,又不完全是父子世袭的。又如我国云南佤族。解放前我国云南佤族仍处于父系氏族后期,其氏族酋长称“窝朗”,从父系氏族向农村公社转变时,窝朗又转为农村公社下村寨的首领。窝朗职位多已世袭,有一个村寨由阿莠姓人当窝朗,口碑已经家传二十四代,但选举仍有作用,必要时仍可改选。如永欧姓人已在马散当了几代窝朗,后来村寨多人生病死人较多,村民认为永欧姓人当窝朗不吉利,即改选阿芝姓人当了窝朗。[20](第33页)
以上历史实际说明这个时期的首领职位虽出现了贵族成分,但原始的民主选举仍然存在,这时选举出的公职人员,一般都是才能出众、办事公平的杰出人物;即使不很突出,也不是那种一贯无所作为、脱离社员群众的人。因为在当时共产制还占主导地位,私有经济还是次要成分,氏族民主制在氏族血缘关系还起重要作用。
七、关于执行习惯法的机构和方式
习惯法一般由部落、部落联合体、村寨联合体或地域公社及其首领制定,实际的执行者也是这些组织和首领。执行的方式以民主制裁为主、个人制裁为辅。除了一部分客观的审判以外,一些短期内无法判明的案件,则往往实行神明裁判或采用决斗等方法来判决。
以德意志人为例。德意志人的制度大体也与野蛮高级阶段相适应。据塔西佗记载,当时氏族首长(Principe)议事会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大的事情要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认为是掌握在祭司们手中。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王”或“部落长”是大会主席,如前所述,决定由人民来做,报怨声表示反对,喝彩、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刑罚的方式取决于罪行的性质。叛逆犯和逃犯则吊死在树上;怯敌者、厌战者和犯极丑恶之秽行者,则用树枝编成的囚笼套住而投入沼泽的泥潭中;轻罪也有各种规定的刑罚:被判定有罪者应出马或牛若干匹作为罚金。罚金的一半归公共所有,另一半则归受害人或其亲属所有。[19](第60页)
以中国独龙族为例。独龙族在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家庭公社阶段,独龙人的土地原是公有的,只是在百余年前才出现私有的情况。独龙族村落之间发生杀伤案件以后,调停人即认真对待。首先,调停人听取双方的陈述,进一步广泛听取双方“克恩”(独龙族的血缘村落)中成年人的意见,如果只是一般案件,经过上述程序,往往能达成和解并宣布处理办法。如果是杀人案件,经过上述程序双方还不一致,即进行公开审理。审理都在室外的空地上进行。为避免诉讼过程中发生冲突,双方人员站立的位置一般都相距百米以上。审理时双方的“卡姗”(村落头人)为双方诉讼和申辩的当然代表,同时邀请其它村落的头人到场作裁判人。因为事关重大,双方“克恩”中的成年男子大都到场,审理的结果必须取得“克恩”中多数成员的认可后才算有效。这一方式的组织工作和运作程序既复杂又井井有条,因此判决和处罚能保证基本合理。[21](第132页)
以中国佤族为例。佤族在解放前尚处于父系氏族晚期,经济上受外界影响很大(进入铁器),但生产技术上仍处于刀耕火种阶段。佤族对偷盗犯处理方式一般是轻者教育,屡教不改而又情节严重者则被处死。对偷盗犯的判决和处理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偶而行窃而偷到的东西不多者,要他赔还所偷东西,并对他进行教育;第二,屡教不改的惯窃往往被处死。有的被父亲兄弟打死,有的在公众拥护下,由头人开会研究处死;第三,若失主没有当场抓着偷者,失主便请魔巴(巫师)杀鸡看鸡卦,以确定偷者。看卦前,失主确定一个被他怀疑的人看鸡卦,若鸡卦果真如此,便认为是此人偷了。若鸡卦不是如此,再怀疑另一个人,再看卦,直到确定了偷者为止。若被怀疑者不承认,就进行第二步“审判”,其方法有三种:失主和被怀疑者互相摩掌、互相打头和双方都用竹签扎手。根据出血情况来确定哪个错了。处罚的方式一般是错方家被拉猪、拉牛或抄家。若出血情况一样,则都不错,也就了结了。[20](第33-35页)
八、习惯法的基本特点及其与国家法的区别
《管子·极言篇》认为“法出于礼,礼出于俗”,说明了习俗与法律之间发展的过渡性。习惯法是在原始社会早期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成为阶级社会法律形成的前驱。通过对以上多个民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过渡阶段的习惯法既有不同于早期的习俗、又有不同于阶级社会国家法的基本特点:
第一,在法的制定者方面,习惯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氏族、部落首长、村寨首领或城市公社的首领及其公众会议,而不是国王、贵族议事会及政府官员;国家法的制定者是王、执政官、皇帝、贵族会议、议会等国家权力机关,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又多有不同。执法者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如国王、官府、警察等,他们严格地维护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第二,在法的内容方面,习惯法的内容具有过渡性、二重性的特点,既维护公共的利益,又开始维护一部分人或私人的利益;既维护公共财产也维护私有财产。在婚姻家庭方面既维护男女的平等地位和婚姻自由,又已开始承认夫权、父权的一些内容;部落和地域公社的首长,既还由选举产生,又已开始出现世袭现象,并与选举并存;这些首长在社会地位上还与公社成员地位平等,又已开始产生职权私有(个人有一定的决定权和职位世袭等)和经济上、政治上一定的特权。而国家法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大多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并且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服务。
第三,在法的发展水平和适用范围等方面,习惯法的特点是多为判例性单项或数项立法,民法和刑法、诉讼程序法和实体法往往混而不分,无综合性大法,抽象性差,适用范围较小;阶级社会国家法的特点大体是:有了综合性的法典,已经分为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多种类型,同时已逐步衍生出多种专项法;法的概括性、抽象性加强;适用范围扩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已产生一些国际法。
综上所述,通过上文对世界多个民族习惯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习惯法作出更为规范的理论阐释:习惯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时期(分前期与后期,后期与地域公社并存)。它是一种不成文法,但一般已用条例的形式公布于众,有的已刻于木石。它由部落、氏族、家族、村寨或其联合体的首长(或一定会议)主持制定。它调整的社会行为规范和内容富有时代特点,即:既有条件的承认血缘关系、原始共产制与公有制和原始民主、平等关系,又开始以法权形式认可并维护已初步产生并正在成长中的地域关系成分、私人生产与私有制成分、阶级与等级的差别、父权、夫权和贵族特权的成分。这些成分以特定的形式交融在习惯法中,具有过渡性、二重性和不稳定性。执行习惯法的是上述制定者或由其主持的会议。执法中既有基本合理的审判,又有神判、卜卦、角斗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草率、简陋、荒蛮的简单性。国家形成以后,还有习惯法,但在整体社会中,已经不居主流地位了。
收稿日期:2003-12-03
标签:习惯法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读书论文; 希伯来人论文; 法律论文; 原始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