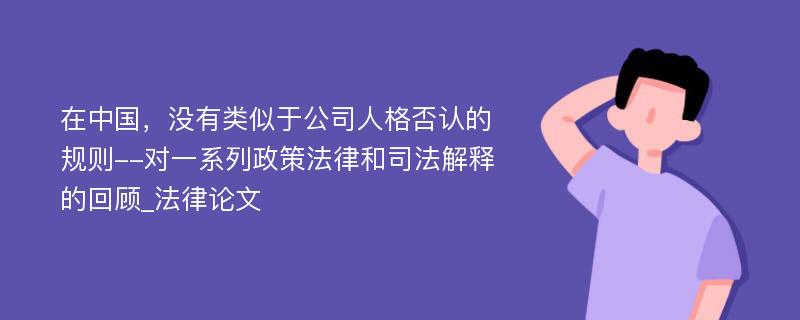
我国不存在类似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则——对系列政策法及司法解释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存在论文,司法解释论文,人格论文,公司法人论文,类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社会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的研究渐呈热潮。论者几乎一致认为应当引进该理论,以弥补有限责任的缺陷、遏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
我国法律关于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定向来严守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立场。尽管《民法通则》第48条在明确有限责任的同时,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产生“另外”的法律规定。因此,至少可以认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法定情形在现有法律中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少学者并不甘心于此。他们将1984~1995年前后的若干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法(注:政策法是指那些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得以实施,成为事实上的法律规范的政策、习惯、行政命令等。这一概念有三层基本含义:第一,政策法不同于政策,它能强制约束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以一定的权利义务责任为内容的行为规则;第二,不同于一般所理解的法律,不来源于立法权,是党政部门职能活动的产物;第三,政策并不是政策法的唯一存在方式。)[2],以及以执行这些政策法为目的出台的系列司法解释视同“中国版本”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3]有的学者甚至称这些规范性文件“已经包含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内容”。从而认为“引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存在观念的障碍”,[4]即使已经觉察出差别的学者,为了说明引进的可行,也硬要坚持说这些做法“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类似”,并称之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相关制度”。[1]这些认识极易误导人们产生移植或改良的冲动。在此实有必要对我国的这些政策法和司法解释进行检讨。
一、我国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系列政策法、司法解释及主要内容
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政策法包括: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各类公司的通知》(198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1986)》;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1990)》。
最高人民法院对应的司法解释包括:《关于行政单位或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务由谁承担的批复(1987)》;《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1994)》等十余件。
其中,规范内容相对集中的是《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清理问题的通知(1990)》(以下简称《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1994)》。(以下简称《批复》)
《通知》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及所属序列的事业单位,凡是向其开办的公司收取资金或实物,用于本机关的财务开支或职工福利、奖励、补贴等开支的,应在收取资金和实物的限度内,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各级机关和单位已向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不得抽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如有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回、转移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
《批复》则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歇业或者依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视同歇业”后,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分三种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第一,“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实际上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以其经营管理或者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但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者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并且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责任。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企业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对这些主要规定,我们应对以下一些问题加以分析并最终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我国有关清理整顿公司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突破了有限责任原则?这些文件是否蕴含法人人格否认规则?它们在特定背景下发挥的作用和局限性如何?
二、系列政策法、司法解释并未突破有限责任原则
绝大多数论者认为国务院的《通知》业已突破股东(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原则,即突破了股东(出资人)不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和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的原则。表现在一方面要求开办者直接清偿公司的债务,另一方面又强调开办者在受益范围内或在侵吞、转移、抽逃、隐匿公司的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公司债务的责任,而不是以出资额为限;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则针对企业法人投资未达到注册资金的情况确认了两个原则:一是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开办者应与企业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开办者承担的连带责任具有补充责任的性质,范围限于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
但是,从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得不出已突破有限责任原则的结论,而且朱著对责任性质的认识也不正确[1]。在民法原理中,有限责任是指“责任人仅以其一定限额的财产作为债务清偿担保的责任。”[5]换言之,是指在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不得请求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为强制执行的民事责任。无论开办者是以受益、侵吞的财产,还是以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作为清偿所开办公司债务的财产范围,都无疑是以一定限额的财产作为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而不是以开办者的全部财产作为清偿公司债务的一般担保。因此,开办者所承担的仍然是有限责任。开办者收取资金、实物没有合法根据;抽逃、转移公司资金则直接违反强制性规范,均构成对公司的侵害。从内容上看,这部分资产本是公司责任财产的组成部分,理应返还公司,开办者以此范围清偿公司债务,可谓毫发未损,当然也不可能扩大债权获偿的范围。至于不投入注册资金或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则属开办者违反设立公司的法定义务,直接责任对象并非债权人。
《批复》与《通知》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判断承担责任的范围有了更“明确”的标准——即是否达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的规定:
其一,如果达到所规定的标准,业主开办的企业应被认定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只是在该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开办企业在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朱慈蕴先生称为“具有补充责任性质的连带责任”[1]。这一概念颇令人费解:一般认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同属共同责任,但在产生根据、内部外部关系等方面各具特点。如为连带责任,两个以上当事人分别对债务均需承担全部清偿的责任,任一责任主体对外清偿全部债务后,对内将产生按份责任,每一责任主体都应在实际上负担一定份额的债务;如为补充责任,当责任人的财产不足给付时,依法律规定应由另一主体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充的民事责任。就补充责任人用以清偿该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来看,由于不存在约定或法定限制,补充责任的性质当属无限责任;再就实际效果来看,当责任人的责任财产充足时,补充责任人就不会实际承担任何债务,也无须与责任人划分内部责任份额,并不会因此招致法律的非难。只有在责任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时,补充责任人以自己的全部责任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可见,补充责任是第二位的责任承担形式,尽管它也具有扩充责任财产的功能,但它不是加重责任。这与连带责任有很大区别。笔者认为,开办者只在所开办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才承担清偿责任,这一点与补充责任的第二位责任特点相似;但由于责任范围仅限于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开办者履行的仍是原本就应承担的出资义务,并没有无限责任的性质,因此决不是补充责任。由于清偿
顺序上的先后有别,且仅于公司财产不足清偿时才追究开办者之责,显然又不是连带责任。再者,开办者责任的承担是在企业被撤销或歇业之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划分内部责任份额问题,何来连带?其实,开办者此时承担的无非是补足注册资金的责任,或者说恢复责任人责任财产的责任。
其二,如果出资未达到《实施细则》的标准,或不具备其他法定条件的,应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此属无效设立情形,开办者以其全部财产清偿债务,并无任何限制,自属无限责任。这类皮包公司、空壳公司此时已不再是民事主体,其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成为开办者责任财产的组成部分。开办者因没有以实际出资履行法定义务,又不能通过补足差额获得对法人人格的承认,故而并不具备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条件,也谈不上对有限责任的突破。
三、系列政策法、司法解释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区别
以《通知》、《批复》为代表的系列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两者间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一)宗旨不同
如论者所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个别正义,作为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其根本出发点不在于消灭法人人格,而在于寻找背后股东直面公司债权人清偿公司债务。在此情形下,法人人格实为债权人获偿债权的障碍,因此必须“刺穿”或“揭开”法人面纱。一旦实现清偿目的,面纱悄然弥合,又还法人本来面目。而我国的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宗旨十分明确:清理不规范公司,消灭其人格,在一定范围内让开办者、主管机关、申报单位等直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
(二)责任承担者不同
我国在清理整顿公司时期确定的责任人不限于股东,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宗旨是遏制几度公司热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当时问题比较集中的是党政部门因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开办公司或随意批准开办公司,因此这些文件的适用对象除实际出资的各级党政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外,还包括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适用的主体是实施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股东。这应归因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要从法律层面对这样的做法进行合理性探讨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三)责任性质与范围不同
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场合,实施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股东应承担无限责任,责任范围是其所有财产。而我国上述规范性文件中并没有规定统一的责任范围:有的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责任;有的在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有的在受益或抽逃、侵吞、隐慝范围内承担责任。无论责任范围如何,都不具备无限责任的性质,已如前述。
(四)后果不同
按照通常理解,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后果,“是就特定法律关系而一时一事否认法人人格的机能,由法人背后的股东直接承担公司债务,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1]因为是于一时一事的否认,所以特定案件处理完毕之后,该法人恢复常态、功能依旧。依《通知》、《批复》的规定,都是在企业法人清算的过程中针对被撤销的企业法人或歇业的企业法人采用的措施,要求开办者、主管机关等对被撤销及歇业的公司、企业的债务直接承担责任,清理债权债务之后均须在注销登记后消灭法人资格。可见,《通知》、《批复》规定的若干措施的适用都将导致法人人格的永久消灭。
由于两者间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别,应可确信,在我国政策法、司法解释中并不存在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相同或相类似的规定。
四、对系列政策法、司法解释作用的评价
(一)确定承担责任的形式与范围标准有一定随意性
例如,达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最低注册资金标准,在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内承担责任;未达到最低标准的则负无限责任。二者的责任范围相差极大,对前者来说开办者完全可以夸大注册资金,只需满足最低标准即可逃避无限责任,达到滥用法人人格的目的。其可能获取的利益远远高于必须付出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难怪江平先生讥之为“鼓励作弊”。[6]
(二)责任追究不彻底
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答复、复函中,强调了直接主管部门如果已被撤销,即使直接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对公司的开办负有一定责任,也不能一直追下去。这反映出当时清理整顿公司的意图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债权人,更大程序上是为了清除累债,以图一劳永逸。其中既有息事宁人的苦心,又暴露出实践中面临的来自党政机关的重重压力。系列文件的规定也有前后冲突之处。总的趋势是力度逐渐平缓,债权人并没有因这些政策法、司法解释减少损失,滥设公司者却从这些不尽规范、科学的规定中找到了空隙。
(三)引发司法实践的混乱
当时的这些政策法、司法解释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但它们对整顿市场秩序,遏制滥设公司发挥过独有的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所公允评价的那样——“在中国立法覆盖面有限,现行法律不够具体明确和规范的条件下,正是司法解释填充了许多社会领域内法律规则的空白与不足,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行为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立法的迫切需要所产生的压力。”[7]其实,无论政策法、司法解释本身是否完全合于法理、前后是否一致,至少它们指明了立法所需注意的实际问题,并宣示了对规则的选择。在立法阙如的困境下,倘若各级法院能忠实地接受、适用,恐怕问题不至于太大,也能较好地解决公司混乱的局面。
不幸的是,实践中的做法偏离了司法解释本就为难的初衷。例如,《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该企业为法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对企业的法人资格
可不予认定。”根据整个《批复》的精神,此规定是为了彻底消灭不具备法定条件的法人的人格,在清算中追究开办者等的民事责任。这一本旨却因部门协作不力、地方保护等因素在实践中走样。据笔者近年在南宁市进行的调查:法院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时,一般并不事先提请工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是径直在审判中认定涉讼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在生效判决做出之后,对不予认定的企业,法院也不通报工商部门吊销其法人营业执照。这在事实上反倒出现类似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所追求的效果——于一 时一事否认其人格!事毕,原本不具备法人资格,理应被撤销的企业照样还是“法人”,完全可能继续从事招摇撞骗损害债权人的“营业活动”。另外,各地法院出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乐意在审判中认定外地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地债权人;或者坚持认定本地企业的法人资格,助其以有限责任为挡箭牌逃债。债权人在不能顺利受偿时,动辄置疑对方的法人资格,向其开办者、主管机关等索偿。因此,涉及“否认”法人人格的案件日益增多。
实践状况堪忧,倘若再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引入中国,势必对尚不成熟的中国法人制度产生剧烈冲击,引发更大的混乱。
标签:法律论文; 法人论文; 公司人格否认论文; 公司法论文; 法人股东论文; 补充责任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债务承担论文; 公司注册资金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有限责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