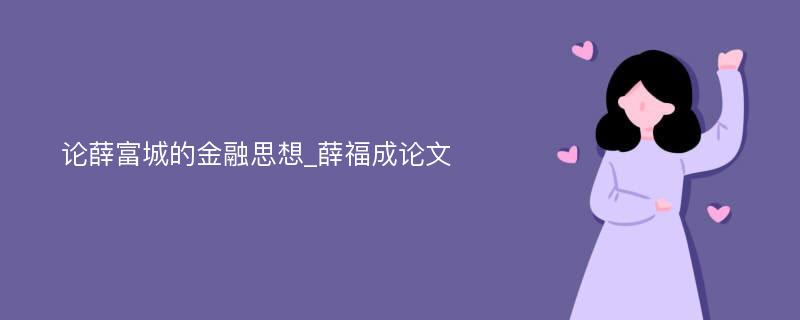
略论薛福成的财政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思想论文,薛福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薛福成是清末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因力主变法图强而名重朝野。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骨干,他又以出使西洋,办理外交,维护国家主权为人称道。从实践来说,薛福成并没有从事财政事务的经历,也没有参与这方面的上层决策。但是,他了解社会实情,忧虑时事国势,勤于思考探索,在他主张匡时济世,强国富民的一系列论述中,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财政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他奉节海外,实地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广泛了解西方的新制度、新办法、新事物,丰富了他按照近代化蓝图实施变法改良的思想认识。本文试对他的财政思想作一概括论述。
一
与同时代其他一些出身官吏,较多从事实际事务的改良派人士一样,薛福成很少有对财政基本原理的论述。他对财政本质,财政功能,财政管理原则,财政体制等问题的认识,需要通过相关问题的论说来加以判断。
薛福成早年对于财政的认识,特别强调节流。他在应两宫太后诏旨,上疏陈言修明之术、变通之道时说:“理财之政,不必开其源也,惟在节其流而已。”“方今不涸之源,则尤赖朝廷崇尚节俭,以风天下,天下尽趋于节俭,而财用无不足之虞”[1]。以后在《筹洋刍议》中又反复申论“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2]。其它涉及军务、工程、外交诸事宜,他也无不强调要“节浮费而济事实”,“裁减有名无实之费”[3]。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薛福成的财政思想偏向于消极保守,有的研究者以此与他晚年主张“浚其生财之源”相对比,认为其思想前后矛盾,其实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清朝末年,财政困窘日益加重,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外乎开源、节流两途,朝中关于财政政策也相应形成两派意见。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名义赋税相对较轻的朝代,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才不断加重税收。起义被镇压以后,一些官员从体恤民情出发,主张适当减轻税赋,也即提倡节流而反对开源。薛福成所谓“节流”的立足点正在于“不伤财,不累民”,主导倾向是减轻人民负担。他认为各项正杂税课,再加征收、调运、管理费用,以及胥吏贪污中饱,“往往朝廷取之不重,而民之所供已至数倍”,为此,他强调“取民之制,不得不务从其俭,以恤民艰”[4]。这与他晚年主张“浚财源”的思想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贯通的。因为“浚其生财之源”的目的,是要“导民生财之道”,救治当时中国“民穷财尽”之病症,出发点也在于“养民厚生”[5]。在薛福成的言论中,常常把“张国势,厚民生,阜财用”相连称[6]。事实上,他早年未必不重视开源,对于开矿山,筑铁路,兴工商,以增强财力,这在他文牍奏议中随处可见;而晚年主张开财源,他也并不放弃“节财用”、“除冗费”的见解。节流与开源,两者统一于民,既要“恤民”,又要“养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恰当把握薛福成财政思想的实质。需要指出的是,从70年代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节流,因为客观上开源的办法大多难以很快见效;而甲午战后,清廷财政转向开源为主,以种种办法扩大筹款,因为那时几乎已无流可节[7]。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财政思想,似乎不能忽略这一历史背景。
正是基于“理财为民”的认识,薛福成着重论述了“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他说:“取诸民以制国用,即量所入以治民事,此古今不易之通义也”,但当今“西国通例,量出为入”[8]。在《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中,他进一步指出:“古者中国制用之经,每量入以为出;今之外国,则按年豫计国用之大者,而量出以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这几处论述都颇为简略,但包含了如下一些内容:一是强调财政的重点,在于“出”,也即以用财为归宿,要以支出来限定和制约收入,特别是防止超出支出需要而盲目加征,造成财富“壅之而勿流”。二是强调支出的主要内容应是“自养本国之民”,其中包括“养老济贫之费”,“贫民子弟入学堂之费”等等,所谓“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也”。这里强调了收入与支出的一致性,不仅是数量上的一致,而且在财政管理原则上对取之于民而用之于他,表示了否定。三是提出了建立财政预算的思想,即“按年豫计国用之大者”,一岁中国家的用度和额外开支,都要事先衡定数额,相应组织收入,调度使用。四是在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上,主张要有收有支,能聚能散,反对但知聚剑敛并死藏于府库[9]。以收入保证支出,以支出促进收入,“旋出旋入”使财富周流不息,由此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人民富裕和国家财政的良性循环。显然,薛福成关于“量出为入”的认识,具有变革中国传统制用之法的意义,也是一个较早提出的借鉴西方经验,建设近代财政的重要构想。
薛福成在理财上强调支出,在用财上强调节流,并不是忽视通过发展经济以充盈财政。恰恰相反,在社会经济与国家财政的关系问题上,他从来都把振兴民族工商业看作是裕活财政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生财大端,在振兴商务”[10]。他举关税而论,说:“余尝考财用盈虚之故矣,大凡土脉膏沃,物产充羡,壤博民殷,商货所趋如水归壑,则税可赢,又或众力勤劬,工艺精良,流貤日广,为遐方日用所必需,则税可赢,又或地虽硗瘠、专产一物,如丝如茶,居民恃为恒业,远人闻而欣羡,则税可赢,又或绾毂通衢,因利乘便,官山府海,发天地自然之藏,都泉布输写之会,则税可赢。”他列举矿藏、物产、交通、工艺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视为“殖财之源”,但认为关键还在于商物流转的通畅,“此数者,贵审其地形,开其风气,……以定群商之辐辏与否”[11]。尽管在振兴工商和增加税收的关系上,薛福成的持论常有偏重,有时为了强调商务的重要而以可增加税收作为论据,有时在论述促进商业时又倡议“优免税厘”。他认为“倘征税太高,财匮力竭,是自塞利源矣”[12]。而从总体上说,他关于振兴经济才能长久地增加财政收入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基于此,他建议当朝者仿效西欧各国,以工商为“立国命脉”,“有鼓舞之权,有推行之本,有整顿之方”,以成“利用厚生之政,探本握要之图”,倘若“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13],特别是对于自筹资本创办公司,经营工商业者,他主张,“经始之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率,则于国课必有所裨”[14]。毫无疑问,薛福成的这些认识是超出其同时代人的。至于他正面论述采用机器,振兴百工,以“殖财养民”,炼铁开煤,以“利用厚生”,修筑铁路,“复收铁路之利以供国用”等等[15],历来研究者颇多评述,此不一一赘论。可以说,把国家财政建立在经济繁盛,人民富庶的基础之上,是贯串薛福成财政思想的基本观点。
二
正因为薛福成的财政思想是以“富民强国”,“为民理财”为出发点,因而他对与财政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大多比较真切实在,又因为他注意吸收国外的新事物,对比分析中国和西方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形,他的一些见解又具有独到的创新之处。
在国家与商民的关系上,诚如上文所述,薛福成认为,既然国家财政取之于民,就必须养民护民。“谋国之精神,必爱民若子”,才能“汲之若水”。如果一味征敛,不知“养护贫民”,则“民必不堪命”。一旦“民穷财尽”,国家财政也就无所寄托。他指出,“大抵古今谋国之经,强由于富,富生于庶”[16]。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才有条件谋求国家财力的充裕和国力强盛。为此,他提倡藏富于民,不止一次论及要“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17]。在比较中国和西方各国国势、国力时,他说,国外“致治之要约有五大端”,其中之一“曰阜民财”亦即“藏富于民”,“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18]。由此出发,在议论当时有关经济举措时,薛福成常常以“为民兴利”与“有裨税课”相对举,作为两个重要标准,而且总是把“养民殖财”作为筹措国家财政的前提,又把“导民生财”,作为国家财政的目标之一,强调“为斯民利用厚生”。显然,薛福成的议论没有停留于一般地反对苛征暴敛上,他把安民、养民、富民作为谋国立国之纲要,并借鉴西方各国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建议和主张。例如,“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行钞票以济钱法”,“开银行以生利息”,“定关税以平货价”等等,强调养民之道的关键在于“求新法以致富强”[19]。这些都在国家与商民的关系上注入了新的内容,不能笼统地把它归之于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薛福成没有多少直接的议论,但从他关于筹措饷糈,整顿税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倾向于以省为单位形成地方一级财政,并把地方财力的扩充作为国家财政稳定的根基。他在评说各省督抚政务、军事、经济的建树时说:“夫天下事远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财力。若财力不裕,则财力虽宏,无所用之”。他对地方官僚善谋经营,奋树规模极为激赏,认为这不仅是封疆大吏建立政绩的基础,也是国家“从容发舒”,“夷艰济变”,“协济邻饷”,“筹奠边疆”的重要条件[20]。具体而言,他认为一部分重要的税收(如关税),理所当然“由户部提拨,非大吏所能主持”,但对一些地方性的税课捐费,如直隶的旗租,江苏的盐课,福建的茶税,广东的沙田、烟膏之捐等,应有“供地方留支之费”。另外,承平之时财政大权“固在户部”,而遇战乱之难,“疆臣竭蹶经营于艰难之中,则部臣亦不能以承平时文法掣之。”特别是对于边疆要冲,中央对地方要“假以事权”,允许“宽筹其饷”,“实力经营”,“定盐课,兴矿利,流通百货,以榷厘税”,这是整个国家自立自强的“经久之道”[21]。清朝前中期的财政是比较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全国财政由户部统理,各省布政使司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职能也只是代户部掌管当地钱粮的征收缴调,征收的项目和数额,解缴(京饷),调拨(协饷)的数量、时限,均服从户部指令。地方留支一律报户部核销,地方藩库也只是代部存储,地方官员不得随意支用。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清廷允许督抚自筹军饷,坐支上解的钱粮,甚至自开科目,征募摊派,中央大一统的财政体制趋于瓦解,各省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一级财政[22]。薛福成的一些见解,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情势,历史地看,地方分权格局比较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客观上有利于发挥地方官、绅、商的经济主动性,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和导向近代市场经济,但也带来财权财力的分散,为各省军阀拥兵自重造就条件。当然,从国家统一和加强控制出发,薛福成也主张中央应严格对地方在财政上的考核和监督。具体办法是“核州县之交盘”,明确条例制度,对官员卸职调任“拖延不交”或“交代未清”的,严格给予处分,“参革毋贷”以此制止坐支、挪移、侵亏,保持对地方的必要约束,达到“功令严而亏挪少,亏项绝而库藏充”的目的[23]。但从他论及的范围看,这主要是就州县官吏而言,而考核督察之职权,主要还得由各省督抚来履行。
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薛福成主张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学说、办法,同时,对于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始终抱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他看到,“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不努力自筹振兴之道,“夺外利以润吾民”。他特别注意到“近年日本人夺西人利者”,采用机器,讲求工艺,取得显著成绩,值得中国仿效。所谓夺外人之利,既指贩运之利,也包括艺植之利和制造之利,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用机器,制造货物,使中国所造之物“能与西人之物相抗”,从而“与西人争利”,“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人就只能购用洋货,其结果将是“彼能借资于我”而“我不能借资于彼也”,最终必然是“厚殖西人之利”。中国的财政就会“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24]。薛福成所言并非旁观者的危言耸听,正是从严竣的矛盾揭示中,他大声疾呼要发愤图强,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扩大对外贸易,“通官民之隔阂”,“融中外之畛域”[25]。这样,中外“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26]。基于这样的认识,薛福成就关税、外债、外贸和国际收支等中外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这将在下面加以讨论。无论如何,他主张把国家财政建立在抵制外来侵略,夺回和分取外人独占之利的基点上,达到了前人所未能企及的思想高度。
三
薛福成作为清廷的重要使臣,多年从事外交事务,因而他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较多涉及对外关系,较多地从讨论对外约章,对外谈判,以及处理对外事务的角度提出问题,加以阐发。这构成他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列强在财政关系方面的重要交涉之一,就是加税裁厘谈判。这项谈判起始于1869年的中英修约谈判。各国为了扩大对华商品输出,要求裁撤厘金,而清政府鉴于海关实际税收大大低于1858年中英通商善后条约所规定的值百抽五的税率,提出要相应提高关税税率。这一谈判在国内朝野引起强烈反响,一时众说纷纭[27]。在这一问题上,薛福成的观点是前后有所变化的。1869年以前,他主张“裁撤厘金”,在《上曾侯相书》中,他指出“昔之创为此法,不过济变一时而已。若军事稍纾,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气也。”因为各地任意增设卡局,提高抽征比例,诡寄勒掯,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为徒设”。但他认为要逐渐裁撤,“可先减天下厘金十分之六”,以后“渐减渐少”,以至于尽裁。并且建议以兵屯垦的办法来替代厘金减少后的经费支出。屯垦所需经费,先移用一年或两年厘金。这样,“用厘金以兴屯政,数年之后屯田毕理,兵饷大减,而厘金故可尽裁也”[28]。显然,薛福成的主张明确,且较为具体可行,不同一般空谈无实的清议。1869年以后,他的观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对内减轻商本,便利转输出发,他主张“整顿厘金”,“以纾商力”。所谓整顿并非骤撤,而是“或酌减捐数,或归并厘卡,以为异日尽裁之渐”,最终目标还是要“普除厘捐,大慰民望”[29]。另一是从对外交涉出发,薛福成反对盲目接受外人意图而立即裁撤厘金。他认为,“中国整饬厘金之弊,严杜中饱,俾商民乐业”。这是中国内政,不应由外人干预。“俟中国财用充足,徐图裁减”,这当然可以,但“外人挠我自主之权不可也”,“予洋人以垄断之柄不可也”[30]。裁厘加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讨论对外交涉时,薛福成曾针对裁厘后是否加税,洋货能否单独免厘,能否以加重洋药(鸦片)之税以补偿裁厘所失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利弊,一一提出预案。例如,对单裁洋货之厘问题,他指出如果洋货免厘,厘卡“所需经费必尽取盈于土货”,结果必然是“畅销洋货,而使土货独受其累”,也即助长外货输入而抑制国货流转。同时,洋商“必更揽庇华商之货”,土货也必“冒洋货以漏捐”,“则土货厘金亦必大绌”。再者,以往“华商因避厘金之故,竞买税单,洋关税因之稍旺”,一旦减免厘金,“则洋税必多偷漏”,“洋税随厘金而减者,又自然之势也。”为此,他明确反对洋货免厘,并且据此提出三项“钤制之法”,如果外人不接受钤制条件,就以“意见不合终寝斯议”,如果接受条件,则对免厘所带来的弊病“尚可收补救之功”。综上所述,在厘金问题上,薛福成的基本观点是加以整顿,逐步裁撤,但裁撤之权应不受制于洋人,并对外国侵略者趁机攘夺我国利权(态度鲜明地加以抵制,这无论从用意还是立论依据、方法来看,都并不错。以往一些研究者笼统地认为薛福成的思想保守、倒退,对厘金的弊害缺乏认识,或者简单地断言他是从维护清皇朝统治的需要来考虑厘金问题,显然是没有把薛福成的议论,放到清末关于免厘加税对外谈判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也没有能真正把握他思想的精神实质。当然,薛福成对裁厘问题的认识也有其暗昧之处。这主要是他出身于曾、李幕府,不可能完全超越作为北洋僚属的局限。他曾说,“是洋货免厘之害,中于淮军与北洋者尤甚也。淮军与北洋受其病,亦天下大局之病也”[31],明显从维护北洋利益来考虑问题。当时朝中也确有一些官僚,欲借裁厘以削弱北洋势力,薛福成所言是有其隐衷的。不过,这是另一层面需要讨论的问题。
与厘金紧密相联的是关税问题。薛福成在反对洋货免厘的同时,还提议对洋货加税,发挥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他引征国外关税征缴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关税之轻,向为地球各国所未有”。“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因而他主张,如果不得不免去洋货之厘,应争取将关税“增至什二,以昭中外之一体,以补厘税之不足”[32]。他的论据是,“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西洋各国税额,大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衡,又多则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今酌中定论,自洋药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或于厘金所失之数,稍足相偿乎”[33]。薛福成对于利用关税率的差别和变动对商品进出口加以调节,还缺乏认识,但他主张利用关税以“保华民生计”,“保中国利权”,则可谓旗帜鲜明。不过当时中国的关税主权已落于外人之手,正如薛福成所说,“抽厘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为了防止洋人为减免厘金而答应加税,事后“彼乘我之无备,又议减洋税”,他又建议,在与各国订立约章时必须载明,中国进口税“于地球各国税额尚属最轻”,今后,“每逢修约之期,但许中国议加,不准洋商求减”,必要时中国还可“就洋货酌量抽捐”[34]。薛福成之议不免有天真之处,但他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有理有节地抵制列强的欺凌、侵略,维护国家权益,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拿出既立即废除厘金,又一举夺回关税主权的万全之策。事实上,薛福成也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思路,“今定税例,华商洋商一律,凡进口之洋货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凡出口之土货纳税于内地之第一子口,各厘卡量加裁并……用新定税额,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35]。这一设想既维护国家和国民权益,又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但这在当时却是注定无法被采纳并加以实施的。直至清朝终结,裁厘加税之议终无结果,正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与关税有关的,还有对外贸易逆差以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薛福成曾以光绪十八年(1892年)海关进出口商品总额及主要分类、国别,与光绪初年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窃查光绪元二年间,出入口货约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货与入货相比较,中国亏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36]。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37]。前者指的是贸易逆差,后者则是指贸易中洋商的赢利。他惊呼,如不制止这两项财富外流,“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在这一问题上,他驳斥某些“论时务者”声称关税收入和洋商雇用买办的佣金足以抵销洋商获利的谬论,强调制止利权外溢乃“牧民之政”,“保邻之本”,“不能不亟为之计者”[38]。为此,薛福成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从分析出口商品大项着眼,他认为要“随事讲求,随时整理”,扩大丝茶等土货出口。从分析进口商品大项着眼,他主张“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纱、洋线,渐推而至于织布,从而遏止洋货输入。”为了鼓励招股办厂和运货出口,国家可以“酌减税额”,以使“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最终达到国课充裕的目的。按照他的想法,“必能如此,然后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不生,境内之财不流溢于海外,而国家于是乎不贫”[39]。薛福成虽然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对外贸易对本国国民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影响,但他重视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以计量分析的方法把问题尖锐的提到人们面前,从发展生产和扩大贸易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的。在这方面还有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他恰当地指出侨汇在弥补国际收支不平中的作用。他说,“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40]。正因为此,在出使途中和任期内,他注意考察侨民情形,大力呼吁在侨民聚居地设领事以加保护,并促进清廷革除旧禁,允许华侨“往来自便”,鼓励他们归国“治生置业”[41]。可以说,清末海外华侨为祖国建设和国际收支平衡所作出的贡献,包含了薛福成的一番心血。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列强财政关系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外债问题。尽管薛福成在世的时候,中国外债的成债笔数不多,债务也远非甲午战后情形可比,但以外债来弥补财政短缺,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体制发生冲撞,并引起朝野人士的种种议论。在这个问题上,薛福成抱极为审慎的态度。首先,他不倾向于借债纾困。他举土耳其、西班牙、日本等国为例,认为其困匮颠危,“皆为国债所累”,由于大量举债,“罄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内变迭作”。中国为筹西征之饷而借外债,洋人将“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倘若朝廷无力还本付息,“而辗转加借”,必致“积累益巨,利不胜害”。所以他认为借洋款“不可不慎也”[42]。其次,他认为不得已而借外债,其借款应用之于生产建设,而不能用于耗费。他对刘铭传为筑铁路而借洋债给予肯定,“顾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43]。再次,他认为借外债不仅要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经济利益,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偿还能力。他对李鸿章借债兴建铁路不以为然,因为“承办之人未能事事核实,难免侵蚀亏短之虞”,还有人“藉借债之名骗款累累以供私用”,结果是路未获利而债息需偿,“则中国两受牵累,财用必日脧月削”。所以一旦借债,必须“期于本利不致亏短”[44]。此外,他主张借外债时必须预先考虑对洋人有所制约,一方面,通过谈判压低利息,以“不受盘剥于外人”,另一方面,坚持所办事业和国家财政自主,避免主权为外人所侵,导致“利未形而害已随之”。具体到铁路借款谈判,薛福成坚持应拒绝洋人的附加条件:(一)不准洋人附股;(二)不得将铁路作抵押;(三)不得指定以关税作偿还。由此保证“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45]。薛福成的这一系列主张,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严正立场,也反映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缜密细致和财经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他的见解对清朝末年大量举借外债敲响了警钟。而且,对于今天的开放和建设也有其意味深长的认识意义。惜乎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些设想,如加税免厘,控制外债之类,并未被当时的清政府采纳,加以清朝末年是那样一付烂摊子,根本无法有所振作,所以很难对清末的财政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
薛福成早已作古。他谢世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我们重新检视他的论说,不只是出于对他个人品格的崇敬,更重要的是,他的某些思想对照今天的现实,仍不失其特有的光彩。
注释:
[1] 《应诏陈言疏》1875年,《薛福成选集》第75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所注页码均为《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6页。
[3] 《上曾侯相书》1865年,第13页。
[4]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7页。
[5] 《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1891年,第367页。
[6] 《出使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十六日记。
[7] 参看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7~549页。
[9] 《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1892年,第416~417页。
[10] 《代李伯相复徐铸庵部郎书》1880年,第152页。
[11] 《海关征税叙略》1893年,第485页。
[12] 《论删除越南华民身税有益无损》1893年,第474页。
[13] 《论公司不举之病》1893年,第481页。
[14]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2~543页。
[15] 《振兴之说》1893年,第483页;《创开中国铁路议》1878年,第109页;《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1893年,第502~503页。
[16] 《南洋诸岛致富强说》1892年,第425页。
[17]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3页。
[18] 《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十四日记。
[19] 《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壬辰)闰六月初六日记。
[20] 《叙疆臣建树之基》1889年,第291~293页。
[21] 《筹洋刍议》1880年,第531页。
[22] 参看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3] 《应诏陈言疏》1875年,第75~76页。
[24] 《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年,第421页。
[25] 《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1893年,第496页。
[26]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3页。
[27] 参看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载上海历史学会1987年年会论文集。
[28] 《上曾侯相书》,1865年,第21~22页。
[29] 《应诏陈言疏》1875年,第70页。
[30]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8页。
[31] 《洋货加税免厘议》1881年,第154~155页。
[32] 《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1876年,第101页。
[33] 《筹洋刍议》1880年,第552页。
[34] 《洋货加税免厘议》1881年,第155页。
[35] 《筹洋刍议》1880年,第553页。
[36] 《海关出入货类叙略》1893年,第487页。
[37] 《筹洋刍议》1880年,第541页。
[38] 《海关出入货类叙略》1893年,第489页。
[39] 《书周官非人后》1892年,第430页。
[40] 《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1890年,第334页。
[41] 《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1890年,第313页。
[42] 《筹洋刍议》1880年,第535页。
[43] 《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1880年,第139页。
[44] 《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五日记。
[45] 《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1880年,第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