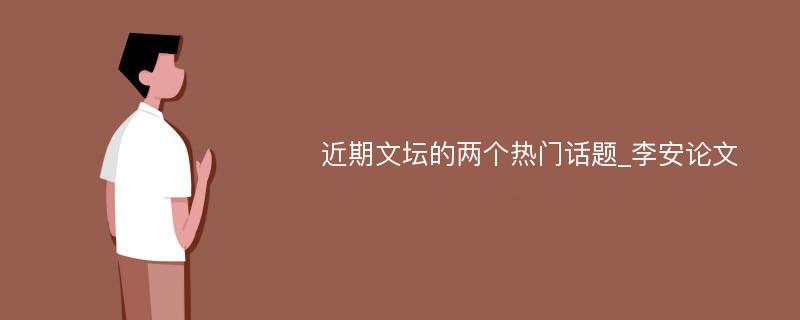
近期文坛热点两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文坛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家长篇竞相描写农民工形象
关注底层民众,直面底层生存,一直是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热点。而在2007年,这样的创作倾向,更为有力地反映在了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之中,其中比较显眼和较为重要的成果,便是三部从不同角度状写农民工形象的小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通过歇马山庄一个名叫吉宽的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际与困惑,描写了当下的农民工实在的生活情景与精神状态。吉宽到城市后,一改在歇马山庄乡下时的懒汉的秉性与旧习,到处打工,自食其力,但始终没有能够走出生存的困境。而因为身份的改变,空间的转换,先前的许多人际关系重又受到了检验、考验,乃至拷问。比如,他早年与许妹娜始与月夜马车的浪漫情爱,是否属于彼此倾心的真爱?他与几个兄嫂之间的亲情总在不断变化,个中是否越来越多地混入了生意与交易的成分?作品经由吉宽这样一个独特人物的独特故事,实际上既实现了“公审”,又实现了“自审”。这“公审”便是就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审问社会,审视现实,审议公理;这“自审”便是在城乡交叉地带构成的尴尬境地,自省自己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自问自己置身何处,又去往何方?作为现代都市森林里的“一片落叶”,吉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时代的垃圾”,这种自审与自省的精神,相当的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吉宽这个农民工人物形象,不仅卓有了个性,而且富有了灵魂。
贾平凹的《高兴》,不是一般的写底层,他写的是底层里的底层——城市里捡拾破烂的。作品在着力描写城市拾荒者刘高兴的进城经历时,一方面极力表现刘高兴的心气高傲的个性与向往,他在心里早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经常以城里人自居,干了诸如清洁城市、制止打架、帮人解困等好事,更是引以为豪;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他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并不爱他”;城里人要不对他视而不见,要不对他视若敝屣。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拾荒者里还有一个五富,这个五富比他更笨,更穷,更没有文化。因而他与五富形影不离,总要帮衬他,提携他。这一方面是他的作为同乡人的责任感之所在,一方面也是他的虚荣心的一个表现。因为,有了这个五富的存在与比照,他感到自己尚有些许优越,或者说虽然是在众人之下,却还在一个人之上。作品在这种心高气傲而地位卑下的强烈反差之中,细致入微地书写了刘高兴的善良为人,贤良助人。而这恰恰构成了人们所忽略的一道社会风景,那就是人们并不看重的城市的拾荒者们,也以他们的朴素又本色的道德情怀,支撑着社会一角,滋润着都市一方。在这个意义上,刘高兴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希图得到愉快,甚至改名“高兴”,但始终不能走出愁苦与悲伤,这种事实上的反差,让人唏嘘,更引人思索。
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也是以某民工建筑队的厨子刘跃进的种种意外遭际,状写农民工走进都市之后难以预料又难以应对的遭际引来的迷失与迷茫。作品在这个刘跃进如何以做饭的手艺来打工糊口上,花费的笔墨并不很多,主要的篇幅都是写他由丢包、捡包引来的不可逆料的命运更变。他不慎丢失的包里,除了几千元钱还有一个六万元的欠条,如果找不回来,他也许会因此赔上终生的劳作;而他无意中捡到的包,钱虽并没有多少,但要命的是里边有一个纪录了一位高官腐败与腐化的证据的U盘,而这个他没怎么当回事的U盘,几路人马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必欲弄到;于是,刘跃进就莫名其妙地陷入了被追逐、追捕的种种凶险之中。这个作品的妙处,是作者由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娓娓道来,写着写着就妙趣横生,意外连连,由极其现实性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不无荒诞的人生意蕴。在这个刘跃进为生存而奔波的过程中又意外地陷入为生死而担忧的故事里,作者写出了人生的或然性,命运的偶然性,更写出了影响与导致这种或然与偶然的复杂社会因素,比如,黑社会现象,官场腐败,官商勾结,等等。这些都让人在好看之余,不免陷入深深的忧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意蕴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真不是一句写农民工就可以简单概括的。
《吉宽的马车》、《高兴》和《我叫刘跃进》面世之后,在文学界广获好评。在北京召开的《吉宽的马车》的研讨会上,与会评论家认为,“《吉宽的马车》好就好在让我们看到了有灵魂的农民工,这是近几年来,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吉宽的马车》值得回味和研究。在西安举行的《高兴》研讨会上,与会的评论家认为,《高兴》超越了众多写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现苦难的局限,开拓和深化了文学对当下农民工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叙述,以乡村精神和共鸣姿态,拓展了新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空间。在于12月27日举行的第四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7)最佳奖”评选中,由白烨、陈晓明、孟繁华、张颐武、阎晶明、雷达和李敬泽七位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委现场记名投票,选出了“年度最佳(专家奖)”《我叫刘跃进》。评论家认为,无论从作品故事的以小见大上,还是艺术表现的风格独具上,《我叫刘跃进》都堪为2007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在认真书写农民工和力求艺术创新上,作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可贵勇气。
《色·戒》从小说到电影众说纷纭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于2007年9月份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夺得金狮奖最佳影片奖,随即影片在香港和台湾公演,两周左右,分别在两地突破3000万港币和2亿台币;10月,该片为了达到大陆电影检查的要求和适应内地观众观赏,影片剪掉七分钟的性爱片段开始公映。短短三个多星期内,其国内票房收入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据知,有些人对无法看到已删除的性爱场面十分不满意,或选择从互联网上下载被删节的片断观看,或在情况允许下,从广东南部直接飞去香港,专程观看未经删节的《色·戒》。
电影《色·戒》改编自小说家张爱玲原名《色·戒》的短篇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占领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卧底的女抗日分子本想暗杀一名亲日的情报官员,但反而陷入了自造的情色诱惑中难以自拔的暧昧故事。但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李安的《色·戒》,不一定非得是张爱玲的《色·戒》。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完全可以将原著推倒重来。其实李安正是这样做的。”
随着《色·戒》的公映与火爆,也在影评界和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网络论坛上,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论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争议的内容从电影的性爱场面到与张爱玲原作的异同,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到中国的电影评级制度,话题相当丰繁,争论极其热烈,不同的看法甚至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论,概要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性爱的内容和政治的取向两大问题而展开的,因为立场的不同、观念的迥异,面对着同一个问题,看法却迥然有异,甚至尖锐对立。从大的倾向上看,大致以三种看法最具代表性。
一种是肯定派,这种看法也有角度上的差异,比如,李欧梵从电影艺术风格的角度着眼,认为:“改编后的《色·戒》比张爱玲的原著更精彩,李安从张爱玲的阴影下走出他自己的一条道路来。”有人从娱乐的角度来解读,认为:“这本来是很娱乐的一部电影,却被某些一本正经的人们解读得不够娱乐了。”有人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上来解读,认为:“《色·戒》是一部表现‘人’被‘绝对国家’所挟持的悲剧。在此悲剧的终局,则又以罪恶者的悔恨暗示最后的救赎。”“《色·戒》是一部秉心纯正、微言大义的杰作。”更有人从影片的暧昧意味入手,指出:从李安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所要诠释的人性和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情感,以及导演在通篇中布下的无处不在的玄机来看,“李安是个伟大的导演,《色·戒》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一种是否定派,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人从情色上予以指斥,认为:“家庭片,同性恋都拍过了,李安要拍一个情色片,翘首以待者何止千万。”“《色·戒》的确大大超过了这些电影史上的情色经典,它将情色表现推向了三级片的程度。”“问题在于,这样‘变态和暴露’对于电影是否是必须的?”比较多的人则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政治蕴涵立足,批评与批判电影作品的政治倾向的模糊与偏离。2007年12月4日的《文艺报》在“观众评说《色·戒》”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陈辽、姜德锋、邵明、李保平的署名文章,在与原作的比较分析中,批评电影《色·戒》“以性易爱”,以“人性”遮蔽“爱国心”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看法中,以阎延文的观点和“乌有之乡”讨论会的意见最有代表性。阎延文先后写了三篇文章,在文章题目中就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如“《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欲望彰显的人性之毒”,“人性之毒与欲望暴力”,她并郑重地提出:“导演李安能否以佛门的‘忏悔业障’,向大众作出负责的道歉,达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设在北大资源楼的“乌有之乡”书社,于2007年11月和12月,分别举办了两次“《色·戒》影评沙龙”活动,讨论的焦点集中于“《色·戒》是不是用肉色混淆了近代以来的大是大非”?与会者的基本看法是:“《色·戒》描写的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色·戒》是一种政治隐喻,反映其实是一种‘皇民史观’。”
还有一种观点可以看作宽容派,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地着眼于作品本身,以及导演本人。如针对有关情色的批评,有人就指出:“情色以及色情的电影类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是客观存在普遍存在的,欧美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用限制级标签的形式保护并支持了该类型电影的发展及其受众群体的利益。李安作为一名国际导演,其所作所为是符合国际视野下该类型电影的题材要求的,并非过分之举。”有人就影片遭人诟病的政治问题指出:“《色·戒》并非要抹去抗战中我地下工作者甚至是我们国家民族悲壮抗击的历史底色。它不过是对于大时代下各色人物的一种比较个人化的记录而已。因为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它所产生的震撼和所引起的不适几乎是同样当量的。”
在这种看法中,长期从事文化批评的戴锦华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她在文中详细介绍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比较了张爱玲的原作与李安的电影的异同,在小说与电影的比较中,她认为“电影比小说好”。“张爱玲以她的练达,以她的精明,以她的灰黑色的人生视野,以她的冷酷,写出了一个决绝的故事。而李安以他的温存,以他的敦厚,以他的敏感,以他的细腻,重写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结局的改写。张爱玲的结局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李安最后给出了一个古老的阐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谈到对于电影《色·戒》的总体评价,她指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国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非干政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在歌颂汉奸,但我也不认为它在谴责汉奸。李安用一个张爱玲故事,极端准确地踩到了一个富于张力的点,他用身体政治,用性别政治,用身体的表述,来找到了一个不是真的突围。”“这个张力状态关系着大政治,关系着小政治,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国族,关系着个人,关系着身份,关系我们岌岌可危的个人的状态,而影片当中提供的所有的丰富的入口、丰富的阐释可能,给我们进入它的可能,也给我们从影片所提请的问题当中逃逸出去的可能。”“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但是艺术始终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标签:李安论文; 我叫刘跃进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高兴论文; 色戒论文; 张爱玲论文; 农民工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