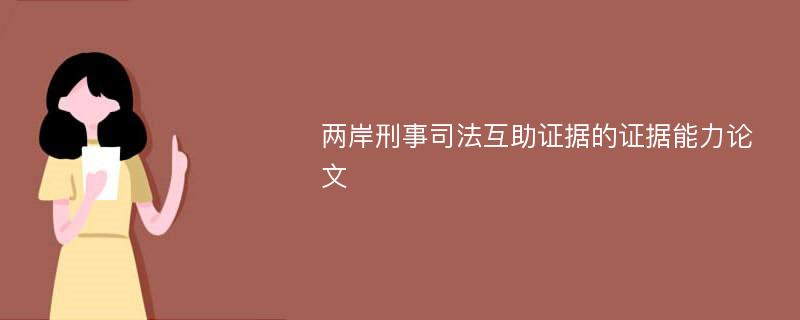
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 *
高 通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350)
【内容摘要】 两岸对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存在直接赋予和经审查后赋予两种模式。经司法互助获取证据能否直接被赋予证据能力,主要与司法互信有关。当前两岸在司法互信的政治基础、刑事实体法互信以及刑事程序法互信方面存在一定欠缺,两岸仍应当确立审查后赋予证据能力的模式。两岸在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上,应当进行鉴真、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要件的审查。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应当以被请求方法律为准据法,并对取证程序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关 键 词】 两岸刑事司法互助 证据能力 关联性 合法性
自2009年两岸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下文简称为《两岸互助协议》)以来,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形式和数量都迅速增加,[1]也将大量两岸司法互助证据带入刑事审判中。证据要想在刑事诉讼中适用,首先应当具备证据能力。传统上证据能力被认为是内国法的事情,由各法域法律自行规定,《两岸互助协议》中对此并未有规定。但这种证据能力完全依据请求方法律来判断的模式,也可能会带来司法互助证据适用的困难。为体现尊重双方原则,《两岸互助协议》确立取证行为应依被请求方法律进行。即取证行为合法性是依据被请求方法律来判断,而证据能力是依据请求方法律进行判断。这也意味着取证行为合法性与证据能力判断依据并不完全一致。而由于两岸法律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可能会出现经司法互助取得的证据在本法域内不具备证据能力的情形。基于相互尊重以及打击犯罪等原因的考虑,过去两岸大都淡化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问题,直接赋予司法互助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但随着两岸司法互助案件数量的增多以及两岸刑事司法制度和两岸司法互助制度的不断发展,两岸对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越来越关注。两岸司法互助实践中也出现否定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案例,如在一起台湾医生涉嫌杀害中国大陆女子的案件中,两岸检察机关通过视频作证的方式获取证人证言,但这些证据最后被台湾地区法院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①而且,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也是一大难题,困扰着各国和地区司法协助实践。国际司法协助为解决这一问题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如互相尊重理论、请求国准据法、“证据自由运动”等。两岸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但这一问题又直接关系到两岸司法互助的成功问题。所以,本文将对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研究,期望通过研究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即两岸应否对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当前两岸司法实践中如何审查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如果需要对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证据证据能力进行审查的话,那么如何审查?本文希望通过回答这些问题,为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研究以及两岸司法互助发展提供有益镜鉴。为行文方便,下文将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证据简称为两岸证据。
由 2.3节可知,提高 Fe2O3/C比可提高合成气H2/CO比,但合成气H2和CO收率较低。而在气化过程中,适当加入水蒸气能促进固体生物质的气化、重整反应,提高合成气H2含量和收率,同时抑制载氧体积碳[18,25]。因此在 Fe2O3/C比为 0.50,TFR为825℃、CaO/C比为1.0条件下,考察了Steam/C比在0 ~ 1.5范围内对合成气制备过程的影响,结果如图5所示。在此条件下,生物质碳完全转化。
一、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必要性分析
当前两岸并未直接赋予经司法互助取得的证据以证据能力,该类证据需经审查后才可被赋予证据能力。这种审查模式与传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模式相同,也存在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问题,故有学者认为特定情形下可直接赋予跨境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2]基于互相尊重原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对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盛行“不审查原则”,请求方默认被请求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并赋予域外证据以本法域内的刑事证据能力。[3]近些年来欧盟学者提出“欧盟区域内证据自由流动”的概念,欲淡化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4]那么,当前两岸司法互助证据是否具备免除证据能力审查的基础呢?
能否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证据能力,主要与司法互信有关。现代国家普遍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证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且经法定程序质证和认定才能作为裁判依据。故证据能力是控制证据使用的第一道关口,也体现了一国的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域外证据来自于另外一个法域,其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与本法域可能存在诸多不同,其证据收集程序也与本法域存在诸多不同。如果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不仅意味着对对方司法主权的尊重,更意味着对对方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的认同。所以,司法互信是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两岸是否存在足够的司法互信呢?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近发展中,相互承认原则一词被用来指代司法互信。相互承认的基本理念在于,一成员国机构签发的判决和其他司法意见在其他成员国将被自动认可,在其他成员国获得相同或相似的效力。[5]依据欧洲议会对相互承认原则的解释,相互承认原则不仅意味着要相信其他国家规则的正当性,还要相信这些规则被正确地实施。[6]P4易言之,司法互信可区分为对对方刑事实体法的互信和刑事程序法的互信。以此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两岸司法互信不足以支撑起两岸取消经司法互助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机制。
第一,两岸缺乏司法互信的政治基础。虽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形式各异,但域外证据审查证据能力的模式在当前却是通例,当前淡化域外证据证据能力审查的努力也只在欧盟区域内出现。欧盟淡化域外证据证据能力的做法并非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着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做支撑。欧盟刑事司法协助自1959年《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引入迄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这期间不仅有大量的司法互助实践做支撑,欧盟更是不断通过规范性文件来完善刑事司法协助。如2000年《欧盟成员国间刑事司法协助公约》、2003年《关于欧盟逮捕令及成员国之间的移送程序》、2008年《为获得刑事司法中使用的物品、文件和数据的欧盟证据令》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完善了欧盟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更积累了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而且,欧盟作为一个“超级国家”也在努力弥合各成员国间的政治差异,逐渐建构“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故而,1999年欧洲理事会坦佩雷会议上,相互承认原则被确认为欧盟民事、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基石。但当前两岸并未建构起足够的政治基础。由于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两岸政治互信的建构之路仍然非常艰难。[7]当前台湾地区抛弃“九二共识”,两岸政治互信自然无从谈起。从两岸司法互助实践来看,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受两岸关系影响非常显著。当两岸关系缓和时,两岸司法互助获得快速发展;但当两岸关系紧张时,两岸司法互助则会减少甚至是停止。虽然两岸司法互助由两岸关系决定,但两岸司法互助亦可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这需要两岸积累起足够的司法互助经验。但两岸司法互助开展时间尚短,未积累起足够的司法互助经验。如两岸司法互助虽然可追溯到1990年《金门协议》,但两岸正式的全面司法互助则开始于2009年《两岸互助协议》,而且2016年后《两岸互助协议》确立的联系机制基本中断。所以,两岸司法互助的政治基础较为脆弱,无法支撑起两岸全面的司法互信。
第二,两岸间刑事实体法互信不足。刑事实体法互信主要体现为双重犯罪、本法域居民不移交等原则的限制适用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确立了双重犯罪、本法域居民不引渡等原则,但这些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基于相互尊重司法管辖权的考虑。因为不同法域的刑事实体法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法域对刑事法律价值及社会价值的不同理解。如果某行为在请求方视为犯罪但在被请求方不是犯罪时,请求方要求被请求方对当事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将会使被请求方陷入违法的困境。双重犯罪原则、本法域居民不移交原则可规避这种冲突,并体现相互尊重的要求。但不可否认,双重犯罪等原则并不利于打击跨境犯罪行为,甚至会影响到法域间的司法互信问题。因为有些犯罪可能会利用不同法域间的法律差异而跨境实施犯罪,也有些跨境犯罪行为可能会因不同法域间的法律差异而被放弃追诉。如近些年持续高发的电信诈骗案件,有不少是都是利用境外相对宽松的法律来实施的。所以,当刑事司法协助数量日益增多时,各法域也逐渐调和其刑事实体法的冲突,并限制双重犯罪等原则的适用。如欧盟建立犯罪和处罚的最低限度规则,促进成员国间更好地理解对方法律,并对32种犯罪取消双重犯罪的要求等。[8]P22-25但从两岸司法互助实践来看,两岸司法互助仍然处于传统刑事司法互助阶段,尚未进入消弭两岸刑事实体法冲突的阶段。两岸在犯罪与刑罚概念方面并未形成共识,如中国大陆曾将部分台湾籍电信诈骗犯遣返回台湾,但被台湾地区法院轻判或释放,在中国大陆引发诸多争议。虽然《两岸互助协议》试图弱化双重犯罪原则、本法域居民不移交等原则,但这一努力也被两岸各自的规范性文件所消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下文简称为《中国大陆调查取证规定》)第16条第3款规定,“台湾地区调查取证请求书所述的犯罪事实,依照大陆法律规定不认为涉嫌犯罪的,人民法院不予协助……”,台湾地区“海峡两岸调查取证作业要点”第9条第1款规定,“‘法务部’接获中国大陆主管机关提出协助之请求时,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协助:……(四)依台湾地区法律认为未涉嫌犯罪……”。所以,当前两岸尚未在刑事实体法方面积累起足够的司法互信。
第三,两岸刑事司法程序互信不足。证据能力审查的核心在于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核心则是对取证程序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审查。但不同法域对取证程序的规范是不同的,在本法域合法的取证程序在另一法域可能会被认定为违法。这与一国或地区对刑事司法人权的保障水平有关。传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基于相互尊重原则奉行被请求地法,只要域外证据取证程序符合被请求方的法律即认为其达到合法性要求。但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逐渐将域外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与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区分开来。域外证据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依据被请求方法律进行判断,取证程序合法的域外证据并不必然具有证据能力,仍需按照本法域法律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所以,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情况也成为域外证据证据能力审查的重要内容,而免除证据能力审查也需要存在刑事司法程序的互信。但刑事程序互信的建构要比刑事实体互信更加困难。以欧盟地区为例,从1950年欧洲签署《欧洲人权公约》至今已近70年,而且《欧洲人权公约》还存在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可督促各成员国不断提升本国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水平。但从实践来看,欧盟地区实现不同法域间的司法程序互信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如2010年欧盟曾就“成员国司法机构是否会滥权侵犯个人权利”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7个成员国的分值分布在从不到10分到80多分的区间里,其中分值越高代表民众对其司法越不信任。[8]P51可见,欧盟内部的刑事司法程序互信尚未形成,这也严重影响了相互承认原则的实现。所以,欧盟不得不致力于建构统一的或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标准,从重视处罚犯人向重视保障被告人人权方向转化。欧盟推广相互承认原则的策略,也从强化司法合作效率向强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转变。[8]P30两岸的司法程序互信是缺失的,且当前尚未有建构两岸司法互信的相关措施。虽然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2012和2018年修订时大幅吸收当事人主义中的诸多内容,但客观来讲中国大陆在人权保障水平方面与台湾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9]加之台湾地区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国大陆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情况存在的偏见,使得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刑事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存在诸多质疑。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中,虽然承认中国大陆法治环境和刑事诉讼制度“有可资信赖之水平”,但同时也指出“虽非完美无瑕,但对诉讼之公正性与人权保障方面已有明显进步”;②台湾地区学界则对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提出诸多质疑。[10]此外,中国大陆也对台湾地区刑事法治存在不少质疑,如前述有关中国大陆将台籍犯罪嫌疑人遣返至台湾后被释放或轻判,以及台湾地区近年来爆发出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等。所以,两岸尚未达到刑事司法程序互信的程度,证据能力审查则可规避因刑事司法程序不互信而引发的证据合法性问题。
二、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实践
两岸自《金门协议》以来逐步开展刑事司法互助,两岸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确立了一些规则。随着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发展,两岸逐渐将两岸证据纳入到域外证据中去,并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获取的证据适用同一套证据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文简称为《刑诉解释》)第405条使用的是“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表述,台湾地区“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第35条也规定,“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刑事司法互助请求,准用本法规定”。总体来看,两岸对域外证据证据能力的认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的直接认定模式,另一种是经审查后认定是否具备刑事证据能力的审查模式。中国大陆过去实践中曾经存在过证据能力的直接认定模式,③但2012年《刑诉解释》废除了实践中的这种直接认定模式,确立域外证据的审查认定模式。所以,当前中国大陆并未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台湾地区实践中存在直接赋予域外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的情形,但这仅适用于对经台湾地区“立法院”审议通过的司法互助协议获取且符合互惠原则的域外证据。④台湾地区对其他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仍然采用审查认定模式,如台湾地区通过与虽签订司法互助协议但协议中不包含证据能力条款的菲律宾进行司法互助获取的证据,台湾地区与德国、英国、瑞士等未签订司法互助条约国家或地区进行司法互助获取的证据,[11]以及两岸司法互助获取的证据等。故当前两岸对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采用审查认定模式。
有一段时间,为了准备学校的朗读比赛,我们每天都要练习。可是,许多同学仅仅是在下面跟着读,因为嗓子已经累得嘶哑了,有些人干脆就只张嘴不出声。班长却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累”字,她坚持在太阳下晒着,双腿因为长时间站立,累得有些哆嗦。尽管嗓子也哑得厉害,她依然大声领读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声音响彻整个校园,我们都被感动了,一个个振作起精神来。看着认真领读的班长,我在心里暗想:“有这样负责的班长,我们一定会获得好成绩的!”果然,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年级第一名。
第一,两岸审查两岸证据证据能力的准据法。《两岸互助协议》中并未规定审查两岸证据证据能力的准据法问题,两岸对域外证据的审查上逐渐采用取证程序合法性与证据能力分别审查的方式,对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依据审判地法律进行审查。如中国大陆2012年《刑诉解释》第405条规定,“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台湾地区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中也明确“依此互助协议之精神,我方既可请求中国大陆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以作为司法上之用途,即有承认大陆公安机关调查所取得之证据,可依台湾地区法律承认其证据能力之意思。”⑤但从规则内容来看,中国大陆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审判地准据法规则。台湾地区对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主要审查其是否属于传闻以及取证程序是否有违台湾法制精神,并非所有不符合台湾地区法律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中国大陆对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是要严格依照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进行,任何违反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证行为都可能导致域外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为《电信诈骗意见》)和《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下文简称为《电信诈骗指引》)确立了证据转化规则。所以,两岸虽然在审查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时均采用审判地法,但对审判地法律的贯彻执行程度是存在显著不同的。
综上所述,复习课是英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思维导图在英语复习课中合理的运用,能够让整个教学过程更加规范有序,在加强学生英语复习能力的同时能够提升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也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为了能够更好地去使用思维导图,作为一名专业的教师,应该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地提升自己,掌握好有关思维导图的技术水平,帮助学生能够在英语学习方面得到最为全面的发展与进步。
第二,两岸审查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时遵循特定性规则。特定性规则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是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域外证据仅能在特定案件中就特定问题来作为证据使用。中国大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立了特定性规则的裁量原则,第18条规定,“外国请求将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取得的证据材料用于请求针对的案件以外的其他目的的,对外联系机关应当转交主管机关,由主管机关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中国大陆《刑诉解释》第405条仅规定如果双方约定有特定性规则,那么违反该规则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但对于双方无约定的则默认域外证据不受特定性规则的约束。台湾地区确立了特定性原则,要求证据必须用于特定用途。如台湾地区“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第16条规定,“法务部”得要求请求方保证,非经台湾地区同意,不得将台湾地区提供的证据或资料,使用于请求书所载目的之外的用途。对于不符合特定性规则的证据,当然也不具有证据能力。虽然两岸在各自立法上存在差异,但《两岸互助协议》确立了特定性规则,第17条规定“双方同意仅依请求书所载目的事项,使用对方协助提供之资料。但双方另有约定者,不在此限。”所以,对于违反特定性规则的两岸证据,也不具备证据能力。
在医生培养方面,上文曾提到医院精细化管理系统构建的病种分析“医师模型”对医生或医生团队治疗管理病种的难度、手术级别、平均住院日、并发症发生率、再入院率等进行评价。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数字分析模型,可以系统地分析患者从门诊、急诊到住院的治疗、检查、用药的过程数据,进而分析医师临床表现。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促进,基于病种视角的医师执业能力评价,通过医师病种管理得分,引导医师发现技术短板,寻找治疗专长。同时,通过同科室、同职称级别医师的得分比较、不同医生同一病种管理得分比较以及医师自身得分纵向比较等,为职称晋升、医师定期考核、医师分级授权等提供数据支撑。
实现被告人诘问权最直接的方式是要求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由被告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进行现场诘问,《两岸互助协议》也确认此种司法互助方式。如《两岸互助协议》第8条规定,双方同意相互协助取得证言及陈述等,第20条规定“为请求方提供协助之证人、鉴定人,因前往、停留、离开请求方所生之费用”由请求方应负担。台湾地区“海峡两岸调查取证作业要点”第9条第3款,也专门规定了中国大陆主管机关请求台湾地区人民至中国大陆作证的情形。如果未来两岸扩大证人赴对方出庭作证渠道,不仅可有效保障被告人诘问权,也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两岸言词类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但考虑到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的成本以及证人的意愿等因素,司法互助中的被告人诘问权并非必然要通过当庭对质来实现,也可通过其他变通方式来实现,如被告人通过音频、视频或书面等形式进行诘问。考虑到被告人诘问的即时性与交互性,通过声音或视频等即时传输设备进行诘问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诘问权。虽然实践中曾发生台湾地区法院否认检察机关通过视频获取中国大陆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但通过视频等变通方式获取域外言词证据的做法已被两岸法律正式确立下来。如中国大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也确认了通过视频、音频作证方式的合法性,台湾地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亦规定台湾地区请求讯问或询问台湾籍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员时,可“依受请求方之法律规定请求以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进行实时传输。当然,被告人诘问权也存在例外情形,特定情形下允许限制被告人的诘问权。如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当满足有关机关已经履行相关告知和拘传义务、证人不到庭系非因可归责于有关机关的事由导致的、被告人应被赋予其他形式的质证权以及该不利证言需要被补强等条件时,可以限制被告人的诘问权。[26]P271
台湾地区的证据能力审查包括消极要件和积极要件两方面审查,消极要件是指不违反证据禁止规则,而积极要件则是指严格证明法则,如符合审理原则的要求、法定证据方法等。[12]P345-346但由于台湾地区法律中规定有直接言词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台湾地区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有所不同。实物类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与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差别,主要涉及到鉴真、合法性审查;但对于言词类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台湾地区则需进行传闻证据规则和合法性审查。如2003年台湾地区增订“传闻证据规则”时曾就“外国法院基于国际互助协议所为之调查讯问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问题进行过讨论,台湾地区“高等法院”认为这些证据属于传闻证据,但“依不同情形,适用同法第159条第1项所指‘法律有规定者外’或第159条之4等传闻法则之例外规定”;如果属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第1项所指“法律有规定者外”之传闻法则之例外规定,那么该证据就具有证据能力。[13]但实践中,台湾地区对域外言词证据的审查主要是依赖传闻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对其他证据能力要求则极少审查。[14]这也招致台湾地区学界的广泛批判。为回应学界的批判,近年来台湾地区也逐步扩张证据能力审查的范围,依据证据禁止规则对域外证据进行证据能力审查。如台湾地区法院在一起危地马拉司法互助案件中,认为“先前陈述所处之环境与附随条件,足保任意性无虞而适当时”,“该外国法院制作之笔录”应依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2关于传闻证据例外的规定赋予其证据能力。⑥
随着两岸交流快速发展,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业务也显著增加。如自2009年《两岸互助协议》签署至2017年底,中国大陆协助台方调查取证案件1105件,请求台方实施调查取证案件1355件;两岸合作侦办案件201起,共逮捕9187人;台方向中国大陆遣返12人,中国大陆向台方遣返476人等。[27]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业务增加会将大量两岸证据带入到刑事审判中,如何对这些两岸证据审查认定逐渐成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一个核心议题。因为如果收集的证据不可采纳,在审判中不能实现任何真正的目的,那么刑事取证将会失去意义。[28]虽然当前两岸对司法互助证据采用了宽松的证据能力审查模式,但随着两岸司法互助实践的开展以及证据裁判原则在中国大陆被确立下来,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获取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逐渐增多。如何化解两岸司法互助证据可能存在的证据能力冲突,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规范对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方式,强化对两案证据合法性特别是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审查,并强化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防止两岸司法互助成为规避程序约束的“法外之地”。当然,具备证据能力并不等同于可作为定案依据[29],两岸司法互助证据还需要通过证明力、真实性等审查后才可作为定案依据。法院也应当强化对司法互助证据证明力的实质性审查,以确保裁判的正确性。
通过上文分析发现,两岸都并未直接赋予两岸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两岸证据均需依审判地法律进行审查后才可被赋予证据能力。但两岸在司法实践中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极少有域外证据会因证据能力不足而排除出刑事诉讼中去。中国大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转化规则,如果域外证据在合法性上存在瑕疵,证据转化规则也可补足该域外证据的合法性。台湾地区虽然认为两岸证据属于传闻证据原则上不具备证据能力,但实践中也通过类推适用或直接适用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等方式肯定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如2008年“台上字”第5388 号判決认为,被告人以外的人在中国大陆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或书面记录,可类推适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2和之3规定来判断其证据能力;2009年“台上字”第1021 号判决认为,中国大陆侦查机关制作的文书属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中的“特信性文书”而属于传闻例外;2013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认为,中国大陆所作书面证据可根据实际情况类推适用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2、之3、之4第3款等规定,作为传闻例外而赋予证据能力。[19]两岸这种放宽证据能力审查的做法,与先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相似。但当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已逐步改变过去不审查或放松审查的做法,确立多种审查方式。而且,两岸学者对这种审查方式也提出诸多批判。所以,两岸未来对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将会日趋严格。
三、两岸证据的鉴真
证据的鉴真,是指“证据提出者必须提出足以支持该证据系证据提出者所主张证据之认定的证据”。[15]P309证据鉴真是证据获取证据能力的前提,两岸刑事司法实践中各自也存在一定的证据鉴真规则。如中国大陆2010年后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通过审查证据来源和证据保管链的形式确立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的鉴真规则;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鉴真规则,但台湾地区实务界也在一些裁判中运用这一规则。[20]证据鉴真主要针对的是实物证据,因言词证据接受交叉询问,故言词证据通常不适用鉴真规则。但在两岸司法互助中,受证人等出庭情况限制,言词证据通常以书面形式呈现,无法通过交叉询问来实现鉴真,故书面类言词证据亦存在鉴真问题。从实践来看,境外取证的情况非常复杂。当被请求方的侦查机关根据请求方要求提供证据并将该证据移交给请求方相关部门时,这个过程涉及到两个法域的多个相关部门。由于证据需要在多个部门间不断转移,而转移过程中极容易出现证据受损或手续缺失等情况。一旦出现受损或手续缺失等情况,将会影响证据的证据能力。中国大陆《刑诉解释》第405条对域外证据确立了严格的鉴真规则,要求“对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等进行审查……材料来源不明或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所以,两岸证据的鉴真是两岸证据获得证据能力的前提。根据两岸证据是否经过正式司法互助途径获取,可将两岸证据分为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的两岸证据和非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的两岸证据两种。下文将对此两类证据的鉴真分别进行分析。
(一)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两岸证据的鉴真
证据鉴真通常通过审查真实来源以及整个证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等来实现,在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国家和地区,证据的鉴真还需要证据收集者、持有人、保管者等出庭作证证明。中国大陆并未完全确立直接言词原则,证据的鉴真可通过侦查人员说明以及书面保管文书等书面材料证明。由于两岸证据取证涉及两个法域,故对于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证据的鉴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证据收集到移交给请求方,鉴真的目的在于确定移交证据与收集证据的同一性;第二个阶段是从请求方接受证据移交至在法庭出示,鉴真的目的在于确定提交至法庭的证据与接受证据是同一的。
常见的灯光形态有点光源、线光源、面光源,通过三种光源的布置营造不同的展示氛围,塑造展示空间形态,绚丽空间色彩。通过不同形态灯光的多手法配置满足参展者的视觉观赏需要。
第一,被请求方收集证据至移交证据给请求方阶段的鉴真。为确保证据鉴真的顺利实现,证据提供者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到两岸证据的鉴真中,通常是控方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两岸证据的同一性。证据的鉴真也存在严格的鉴真规则,如审查证据来源真实性和保管链条的连续性等。如果严格地依照鉴真规则,控方需证明两岸证据在域外保管链条的连续性,但这不仅非常困难也没有太大必要。因为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证据在域外如何取证、保管等应由被请求方依己方法律实施,被请求方无义务向请求方证明证据的收集和保管过程。所以,现代刑事司法协助通常免除被请求方对其所提供证据真实性的证明义务。如《两岸互助协议》第18条规定,“双方同意依本协议请求及协助提供之证据资料、司法文书及其他资料,不要求任何形式之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该种免除仅仅针对刑事司法互助而言的,并不涉及到法院对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的审查。故而,即便是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程序取得的证据,法院仍应对该证据进行鉴真,对两岸证据在域外的保管链条连续性、证据来源真实性进行审查。由于免除了域外取证机关的证明义务,相应举证责任则由请求方的控方来承担。而且,由于前述推定免除了被请求方的证明义务,控方仅承担一般意义上的说明责任。除非有确实证据推翻上述同一性的推论,该域外证据将自动通过第一阶段的鉴真。如《电信诈骗意见》第6条第3项规定,“依照国际条约、刑事司法协助、互助协议或平等互助原则,请求证据材料所在地司法机关收集,或通过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国际刑警组织启动合作取证程序收集的境外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应对其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保管移交的过程等作出说明。”
第二,请求方接收证据至证据提交法庭阶段的鉴真。当域外证据被移交至被请求方时,该证据在被提交至法庭之前仍会经过多个流程,也应当满足鉴真的要求。由于此时该证据已经在被请求方法域内,其保管、转移以及出示等均应当依据本法域法律进行,如独特性的确认和保管链条的证明等。对于不符合此阶段鉴真规则的两岸证据,也不具备证据能力。这一阶段的鉴真还涉及到一类特殊证据的鉴真,即请求方转化证据的鉴真问题。由于两岸证据制度的差异,可能会出现某些两岸司法互助证据不符合各自法域证据种类或证据收集程序的情形,此时请求方侦查机关会通过对该证据重新收集和固定等转化方式,使其在本法域具备合法性。那么,对此类转化证据该如何鉴真呢?从证据来源看,这种转化证据是一类新的证据,独立于原域外证据而存在,而且是属于本法域内的证据。依据鉴真规则,对该证据的鉴真主要是确保其从形成至提交法庭中的同一性,不涉及到转化之前司法互助证据的鉴真问题。但这种鉴真方法可能无法实现对域外证据的鉴真问题。因为证据转化实质上是原域外证据的一种复制或转述,这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证据失真的情形。为防止证据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真、错误等情形,转化证据亦需鉴真,以确保其与原域外证据具有同一性。所以,转化证据除与普通司法互助证据一样都需进行证据收集到移交和接受证据至提交法庭两个阶段的鉴真外,还需特别关注转化过程中的鉴真问题。
(二)非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两岸证据的鉴真
两岸司法互助实践中还存在部分非经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途径获取的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当事人自行提交的,也可能是侦查机关自行赴对方法域收集的,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由于这些证据经查证属实后可作为定案依据,故这些证据也必须经过鉴真。
第一,侦查机关自行赴对方法域自行调取证据的鉴真。无论是两岸司法互助还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都存在侦查机关自行赴对方法域调取证据的情形,如直接通过信件、委托人等方式向居住于另一法域的人员取证。虽然这种自行取证行为更有效率、直接,但却因使本法域法律的效力延伸至域外而违背管辖权原则。因为证据能力、证明力、侦查以及审判等都建立在司法管辖权基础上,而司法管辖权是存在空间效力的。在司法管辖权范围外实施的取证、质证等行为,违背了管辖权的空间效力要求,这些行为自然也就缺乏合法性。为限制刑事诉讼法的域外效力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发展出“限定说”和“域外管辖权限制说”两种观点,认为只有获取被请求方的同意后,请求方侦查机关才可在被请求方进行有效的境外侦查行为。[21]P57-64对于一国侦查人员未经证据所在地国家同意径自到该国取证的行为,则被认为是侵犯了取证地的司法管辖权,据此收集的证据应予以排除。[22]故而从学理上讲,这类证据的确不应被赋予证据能力。
证据材料需具备法定形式且经合法取得才可具备证据能力,合法性审查则涉及到准据法的问题。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合法性审查是以被请求方法律为准据法。但由于不同法域对取证行为的规范不尽相同,绝对的以被请求方法律为准据法也可能带来证据能力的瑕疵,现代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又发展出请求方准据法模式、兼容模式以及分阶段审查模式。请求方准据法模式即被请求方依据请求方的法律进行取证,由此解决域外证据可能会因取证程序达不到请求方正当程序要求而不具备证据能力的问题;兼容模式则融合被请求方准据法和请求方准据法模式,原则上采纳被请求方准据法模式,但被请求方在不违反己方规定的情形下尽可能地依据请求方的要求来取证;分阶段审查模式是将对域外证据的审查判断区分为取证合法性的判断和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取证合法性依据被请求方法律或融合模式进行审查,而证据能力则依据请求方法律进行。[2]如前所述,两岸在合法性审查上将取证程序合法性与证据能力审查区分开来。对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依据的是己方法律;对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则采取融合模式,原则上以被请求方法律为依据进行审查,但如被请求方依据请求方要求取证时则以请求方法律进行审查。对于中国大陆的分阶段审查方法,我们仍可进一步完善。
选择2015年1月—2016年1月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透析的114例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维持血液透析时间>6个月;②定期完成血液净化并完成血液透析治疗;③意识清醒,可配合完成试验;④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系统性疾病病人。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7例。对照组:男31例,女26例;年龄24岁~71岁(48.9岁±10.8岁)。观察组:男33例,女24例;年龄22岁~70岁(51.1岁±11.2岁)。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第二,当事人或其他人员自行提交证据的鉴真。两岸司法互助实践中还存在当事人或其他人员自行提交的证据。与司法互助证据的鉴真一样,当事人等自行提交证据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当事人提取证据至将该证据交由侦查机关或司法机关,第二阶段是从该证据提交侦查机关或司法机关至在法庭出示。其中,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本法域内,该阶段的证据鉴真与域内证据的鉴真并无差别。但对于第一阶段的证据鉴真,两岸法律均对当事人等自行提交证据持审慎的态度。两岸对当事人等自行提交域外证据的鉴真,认为要通过有关机关的认证才可实现,并严格限制未经法定程序认证的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如2008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台上字”第5388号判决中指出“未经验证证明者,其文书之真伪、虚实,难以辨识,不惟程序重大欠缺,更属证据之证明力显然偏低,即难谓符合‘适当性’之要件。”⑧中国大陆《刑诉解释》第405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的,该证据材料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所在国中央外交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机关认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两岸对当事人等自行提交域外证据设计如此严格的审查规则,其目的在于确保域外证据的真实性,通过法定认证程序免除法院查证难的困扰。但这一规则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加剧控辩双方的举证不平等。如控方赴域外取证不需法定程序认证,但却要求当事人等自行提交证据需满足认证要求,这使得控辩双方在举证权的实现上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是可能会使大量域外证据无法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如法定认证程序耗费时间相对较长,且程序繁琐,当事人等可能没有时间或精力完成该认证工作。基于此种考虑,2016年《电信诈骗意见》和《电信诈骗指引》中已经没有关于当事人等自行提交证据需认证的规定,对于当事人等自行提交的这类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的域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当事人等自行提交证据的鉴真,亦需对其材料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等进行审查,以确保提取证据与出示证据的同一性。
四、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是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传闻法则和取证程序合法性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传闻法则审查,主要针对的是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等言词证据。由于中国大陆并未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中国大陆并不对两岸司法互助证据进行传闻审查。传闻法则审查适用于台湾地区对两岸证据的审查,审查两岸证据是否属于传闻法则的例外情形以及属于哪种例外情形,进而依据不同法律条文来认定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如台湾地区曾依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159条之2、159条之3以及159条之4等规定,来分别认定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的证据能力。[19]其次,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取证程序合法性主要是审查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证据禁止规则的范围等。中国大陆《刑诉解释》第405条明确了对域外证据的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如材料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等。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判例中也表明台湾地区法院对两岸司法互助证据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关注,如将法治国刑事程序及公平审判的要求纳入到传闻法则审查中,评价取证地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否达到“不可不信”的状态等。[14]考虑到传闻法则审查并非两岸共同审查规则,而且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越来越被两岸关注,下文仅对两岸司法互助证据的取证合法性进行分析。
(一)两岸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准据法
但在两岸司法互助实践中却普遍认可这类证据的证据能力。⑦既然两岸司法实践中均认可侦查机关自行侦查获取的证据,当这类证据提交至法院时,法院应当对其鉴真。这类证据的鉴真关键在于对域外取证过程的鉴真。侦查人员自行在域外取证的行为并非不受法律约束,其受到取证地和己方法律的双重约束。当然,取证地法律和己方法律对侦查人员取证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取证地法律对侦查人员取证行为发挥禁止性功能,只要其行为不违反取证地法律,取证地就无权对其干涉。因为对于取证地来说,侦查人员在己方的直接取证行为并不能称之为“取证”,也不属于侦查的范畴,而是属于私人行为。对于私人行为的规范,法律奉行法不禁止则为允许原则。所以,取证地法律仅能对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发挥禁止性功能。己方法律对侦查人员取证行为发挥全面规范作用,侦查人员应当遵循己方相关法律的规定。因为对于取证方来说,无论取证地如何看待其自行取证行为,其自行调取的证据未来将会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这也意味着侦查人员的自行取证行为,在己方是被视为侦查行为的,属于公权力的行使。依据职权法定原则,侦查人员行使侦查权当然应当遵循有关法律的规定,否则就属于公权力滥用。所以,对侦查人员自行收集的域外证据也需依据己方法律进行鉴真。而且,考虑到该取证行为发生在境外,侦查人员的境外取证行为是否遵循己方法律并不容易证明。一旦侦查机关滥用职权或取证人虚假陈述,如虚构境外取证程序或虚构境外委托人等,该证据将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极大损害。对于这种非通过司法互助获取的证据必须要进行严格的鉴真,如要求知情证人作证、笔迹鉴定等,确保提交证据与主张证据的同一性。
第一,适当放宽两岸证据证据能力审查的被请求方准据法模式。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适当放宽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标准不同,中国大陆对两岸证据确立严格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对于不符合证据种类和收集程序要求的两岸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这种严格依据被请求方准据法审查的模式虽然可以保证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但可能会使不少两岸证据无法通过审查,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正由于存在这种问题,实践中发展出证据转化方式,对不符合中国大陆合法性要求的两岸证据通过重新收集、补充手续等方式进行转化。但证据转化的正当性也是存在疑问的,如转化过程出现的证据失真、丢失,证据转化可能会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甚至可能会出现通过借用域外较宽松的程序来故意规避本法域法律适用等问题。所以,证据转化并不能完全解决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冲突,其适用也存在一定的限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仍然要从准据法上寻找。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过于严格的请求方准据法模式,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应当适当放松请求方准据法模式,并适当放宽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要求。对两岸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不宜严格依据请求方法律的法律条文进行,应依据请求方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社会安全或公共秩序等进行审查。当然,这种合法性审查的放宽仅仅是针对形式合法性,形式合法性主要是涉及到证据种类、未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取证程序等不违反正当程序要求的内容。如果取证行为违反请求方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安全或公共秩序,或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此获取的两岸证据当然不具备合法性要求。
爸爸果然听见了,吃饭时,说的话就像没熟的杨梅,又甜、又酸、又带刺。他笑眯眯地说:“方舟,你数数外面的香肠有几根。”我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理他。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八十八根。”我才不按他的“剧本”往下演呢,我装傻,“哦”了一声。
第二,请求方应尽可能依据被请求方要求来取证。《两岸互助协议》第8条规定,“双方同意依己方规定相互协助调查取证……受请求方在不违反己方规定前提下,应尽量依请求方要求之形式提供协助。”即两岸对司法互助证据的取证合法性,原则上是依据取证地法律进行审查。但当请求方就取证行为提出具体要求且被请求方依此要求取证时,对该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应当依据请求方的法律。值得注意的是,依据请求方要求进行取证也并非是个强制性要求。即便请求方提出取证要求,且该要求也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但请求方仍无义务必须按照请求方的要求进行取证,只需“尽量依请求方要求之形式提供协助”即可。但从确保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角度来看,这一规定应当成为强制性规定。因为在分阶段审查模式下,取证行为合法性和证据能力有无的审查是区分开来的。取证行为合法性并不必然会带来证据能力,发生在域外的取证行为仍应受到己方法律的审查,以确认其是否属于己方法律所禁止的取证行为。所以,只要请求方所提要求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被请求方就应当依据其要求取证。
调查区橄榄玄武岩化学成分与蒙阴胜利Ⅰ号岩管化学成分进行对比发现,橄榄玄武岩与其他超基性岩相比,其SiO2平均含量42.27%,比胜利Ⅰ号平均含量33.19%[11]偏高;MgO,Cr2O3含量比胜利Ⅰ号岩管稍低,其他元素的含量基本与胜利Ⅰ号岩管一致。
第三,规范对两岸联合侦查获取的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准据法问题。《两岸互助协议》中确立了两岸合作侦查、侦办机制,这也意味着请求方可赴被请求方法域内取证。当然,依据台湾地区“海峡两岸调查取证作业要点”第12条第(三)项规定,联合侦查时中国大陆侦查人员不能直接讯问相关人员,只能通过台湾地区侦查人员代为讯问。如果实践中严格据此实施的话,由于请求方并未有行使侦查权的实质行为,该证据仍然是要通过司法互助程序获取,其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仍应依据被请求方法律进行审查。但有些案件中可能会出现请求方直接进行讯问并记录的情形,形成的证据可能会通过司法互助程序移交,也可能会由现场人员直接带回请求方使用。对于这类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又该如何确定准据法呢?无论哪种情形,这类证据本质上都是请求方自行制作的,属于请求方相关人员的职务行为应受到本法域法律的约束。而且为了防范请求方通过联合侦查故意规避己方法律规定,应当要求请求方相关人员依据己方法律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二)两岸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与标准
第一,两岸证据合法性审查应扩展至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审查。
对取证合法性审查程序中一个较大争论是被告人应否拥有对不利证人的诘问权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司法互助证据大都是以书面形式呈现,而属于传闻证据。传闻证据之所以要被排除,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对其进行质证,这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司法实践中为防止司法互助证据因传闻证据规则而被排除,台湾地区将司法互助证据纳入到传闻例外中。但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趋势来看,诘问权保障情况日益成为影响域外证据证据能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一个国家在刑事审判中对待被告人的态度,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的权利的多寡也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法治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5]故而,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果有罪判决是唯一依据或主要依据某证人之陈述而作成,而被告一方在整个程序内的任何一时点均无法对该证人亲自质问,或是使受质问的情形发生,将违反公约第6条的保障;[13]《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7条规定,“只有在审判或者听审之前,证据提出者就提供该陈述的意图,向对方当事人进行了合理通知,以使该当事人有公平的机会对此进行回应的情况下,该陈述才具有可采性。”[15]P304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虽未确立诘问权规则,但当前也在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证人的出庭。而台湾地区201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为未来确立被告人的诘问权规则预留下空间,第17条规定“请求方请求询问或讯问请求案件之被告、证人、鉴定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时……协助机关得以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将询问或讯问之状况实时传送至请求方。”随着两岸刑事法治的不断发展,诘问权在两岸刑事司法程序中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两岸司法互助中也应当保障被告人的诘问权。
经过对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不少正在使用基于云计算的网络教学平台的老师们进行调查,发现现阶段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和推广存在以下问题。
第二,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中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扩展至取证程序正当性审查时,就涉及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查明案件真相与其他政策性目标之间相互妥协与权衡的结果,[23]并排除“那些法政策上绝对不能容忍、技术上绝对不可信赖的不适格证据”的证据能力[24]。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不同法域对刑事诉讼程序查明真相与实现其他政策性目标的不同权衡结果。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域内的功能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所发挥的功能是受到限制的。如由于司法互助中取证程序发生于本法域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对发生于本法域外的非法取证行为实现程序和实体制约。故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阻吓和维护被取证人合法权益功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可能无法实现,其主要功能可能是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确保司法行为纯洁性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实践中对域外证据是否使用本法域证据排除规则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适用本法域的证据排除规则,如德国的证据禁止规则不适用于司法互助证据,认为“合法依循司法互助途径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考虑取证方式即可使用。”[22]而且,就算确定被请求国于取得证据时违反该国之法律,但当该外国法律规定较德国法律更为严格,而此一取证符合德国法律之要求时,也不会导致证据禁止的结果。[13]另一种是适用本法域的证据排除规则,如日本的实践则是原则上认可其证据能力,但如果该程序对照日本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上之价值标准,有难以采纳之违法性时,则影响其证据能力;[21]欧洲人权法院在2008年Stojkovic案中指出,请求方应对被请求方取证程序进行审查,并将不违反公正审判要求作为使用域外取得证据的前提要件。[14]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对域内证据和域外证据的取证合法性采用不同的审查规则,将会打破本法域内查明案件真相与人权保障的平衡,进而损害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而且,实践中还可能会出现利用双方法律差异来规避本法域严格取证程序的情形。如台湾地区要求讯问时律师必须在场,但中国大陆法律并未规定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如果对其适用不同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两岸司法协助将会成为规避严格取证的工具。故而,取证程序正当性是一法域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维护正当程序的底限要求,不应因域内证据或域外证据而有所不同。但基于相互尊重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请求方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否则被请求方依据司法互助提供的证据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取证程序合法。如果当事人确实证明被请求方取证行为违反其法律规定,请求方可以依据本法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证据禁止规则来进行判断,确认是否将该证据排除。
第三,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未来可逐渐向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正当程序靠拢。
由于两岸法治发展水平不一致,两岸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在两岸各自奉行请求方准据法模式下,实践中可能出现两种极端情形,一种情形是对域内证据与域外证据确立不同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另一种情形是大量的两岸证据无法通过证据能力审查规则。这实际上涉及到取证程序合法性的标准问题,尽可能消除两岸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差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被请求方尽量依据请求方要求来取证,也是要尽量弥合两方取证程序合法性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虽然当前在两岸建构统一的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标准非常困难,但仍存在一定的空间,即利用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正当程序。中国大陆虽然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在不断吸收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正当程序要求。台湾地区并非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约主体,但台湾地区也于2001年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在岛内法律化问题,并对照这两个公约对台湾地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检讨与修改。所以,两岸刑事司法程序都在不断地向这两个国际公约中的规范靠近,这为两岸建构统一的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标准提供可能性。当然,该国际公约中对取证程序规定的是最低标准,两岸可规定正当程序标准更高的取证程序。所以,如果两岸法律中确立的正当程序标准要高于公约的规定,那么应当按照更高标准来进行审查。
(三)两岸证据合法性审查中的被告人权利保障
对法域内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通常包括对证据自身合法性审查和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两方面内容,其中证据自身合法性主要审查是否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是否属于非法证据等,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则包括取证程序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正当性)审查两方面内容。如前所述,两岸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通常更关注证据形式、非法证据以及取证程序的形式合法性等,但对取证程序的正当性审查关注较少。如《两岸互助协议》第18条有关互免证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推定条款,但并未涉及到被请求方取证程序是否正当的问题。两岸实践中对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审查是非常宽松的,基本上都是默认域外取证程序的正当性问题。这种宽松的取证程序正当性审查规则导致形成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的“法外之地”,招致诸多批判。如台湾地区有学者指出,两岸实际上为域内证据和域外证据设置两套证据能力规则,域外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明显宽松于域内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14]现代刑事诉讼在强调程序合法性时越来越关注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亦越来越重视取证程序对被取证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状况。[3]对于严重侵犯被取证人诉讼权利而获取的证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不承认其证据能力。如在2012年Stojkovic诉法国和比利时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虽然比利时(被请求方)依其法律进行讯问,但法国(请求方)应对申诉人是否在符合公平审判要求的情况下讯问进行审查。[13]两岸在司法互助实践中也逐渐关注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审查问题,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中指出,“中国大陆……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视实体法之贯彻与程序法之遵守,虽非完美无瑕,但对诉讼之公正性与人权保障方面已有明显进步,故该地区之法治环境及刑事诉讼制度,已有可资信赖之水平。”⑨此判决中已经出现对中国大陆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进行审查。所以,两岸证据合法性审查应当扩展至取证程序正当性的审查。
第三,两岸审查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国大陆对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审查并未将证据能力审查和证明力审查这两个过程完全区分开来,而是将其糅合到定案依据审查过程中去。审查的核心是真实性审查,真实性审查主要属于证明力审查的范畴,其中的证据能力审查包括同一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同一性审查被称为证据的鉴真,旨在保证主张证据与在法庭出示证据具有同一性;关联性审查是确保证据与待证事实间存在关联性,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证据合法性审查则是确认证据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是证据能力审查的核心。
结 语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似乎不将两岸证据的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审查的内容。这里涉及到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证据能力和关联性的不同理解。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将关联性审查作为证据能力审查的内容,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当然就不具备证据能力。[15]P57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不将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的内容,证据能力通常包括按照取证、质证等程序实施的积极条件和不违反证据禁止规则等的禁止条件。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并非不讲关联性,而是将关联性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如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认为“证据需确与待证事实有重要之关系,而决定其间有无重要关系,则须不违背一般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16]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联性仍然是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这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将关联性作为证据能力审查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当然,证据关联性并非仅与证据能力相关,还与证明力息息相关。所以,证据关联性可分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间存在某种关系,而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则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17]P275-276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旨在确定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的问题,此种关联性审查仅审查有无关联性;证明力意义上的关联性旨在确认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问题,此时需判断关联性大小等问题。本文探讨的是两岸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故仅探讨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审查。考虑到证据能力关联性审查在两岸是事实问题且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法律不应对此做过多干涉,否则将会影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自由心证必须以证据自由和证据评价自由为前提,而证据自由则指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18]基于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两岸证据的鉴真和合法性审查。
注释:
7.2.4天牛①成虫多出现在6~7月,可随同其他田间作业经常检查,发现成虫及时捕杀。②发现幼虫驻干后,先清理虫道,然后塞进浸有敌敌畏的药棉,用铁丝送入虫道深处,然后用胶带或泥球封口。也可填入磷化铝药丸封口。一般都可杀死虫道内的幼虫。③用生石灰乳加入硫磺粉制成涂剂在成虫活动盛期涂干,阻碍成虫产卵或孵化。
① 参见台湾地区“士林地方法院”2011年“重诉字”第2号刑事判决与台湾地区“高等法院”2013年“上诉字”第635号刑事判决。
②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
③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信用证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规定,“根据刑法事诉讼法第17 条的规定,依照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委托境外执法机构询问证人的情况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参见冯俊伟.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J].中国法学,2015,4.)
关于MM患者中Th17细胞比率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研究[15]报道,MM患者骨髓中Th17细胞增多;也有研究[16]发现,MM患者中Th17细胞较正常对照无明显改变,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④ 如“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间之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第9条第5款规定,“依附表A所证明之文件,应准许在请求方所属领土内之法院作为证据使用。”后来台湾地区对此又增加一个条件,除要求签有司法互助协定外,还要求“亦承认台湾地区法官依法之诉讼行为效力”。如台湾地区2009年“台上字”第7049号判决中指出,台湾地区对于依据互惠原则取得的境外证人陈述笔录,认为属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第3款“书证”的范畴,或属于第159条之1第2项中“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的范畴。这些证据除具有显不可信的情形外,都可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⑤ 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
有些人对“碎片化”的批评也有失公允。专业研究要讲全面,系统掌握某一门专业或某方面的知识也不能“碎片化”,但对非专业读者、非专门教育、学术普及来说,又何妨“碎片化”?实际上,面对人类已经积累的浩瀚的知识海洋,每个人能够汲取的无非是一滴一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只能是若干碎片。只要保证这是真正的碎片,而不是垃圾,并且明白这只是一个整体中的极小部分,因而不能代表整体,就能做到开卷有益,闪光的碎片同样能体现整体的精妙。
⑥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第7049号判决。
⑦ 如中国大陆对这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并未做限制,《刑诉解释》将这类证据统称为“其他来自境外的证据材料”。台湾地区亦认可这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如2010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台上字”第1941号裁判认为,板桥地检署检察官在澳门未由澳门官方人员陪同而自行对证人询问所作的询问笔录具有证据能力。(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0年“台上字”第1941号裁判)
⑧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8年“台上字”第5388号判决
⑨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900号判决。
参考文献:
[1] 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涉台司法互助情况并公布相关司法解释[N].人民法院报,2015-07-01(1).
[2] 杨婉莉.浅析经司法互助取得证言之证据能力——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度台上字第7049号案件为例[J].月旦裁判时报,2015,4.
[3] 冯俊伟.刑事司法协助所获证据的可采性审查:原则与方法[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6.
[4] Libor Klimek.Free Movement of Evidence in Criminal Matters in the EU[J], The Lawyer Quarterly,2012,4.
[5] 冯俊伟.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J].证据科学,2016,1.
[6]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utual Recognition of Final Decision in Criminal Matters[[EB/OL]].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0-842_en.htm.2000-07-16/2019/2/10.
[7] 张文生.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J].台湾研究集刊,2010,6.
[8] Pim Albers, Pascal Beauvais, Jean-Francois Bohnert, Martin Bose, Philip Langbroek, Alain Renier and Thomas Wahl. Towards a Common Evaluation Framework to Assess Mutual Trust in the Field of EU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R],2013.
[9] 姚莉.两岸刑事案件调查取证协助中的冲突及解决——以两岸证据制度的比较为视角[J].比较法研究,2014,3.
[10] 李佳玟.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证人供述证据: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近十年来相关判决之评释[J].台大法学论丛,2014,2.
[11] 蔡碧玉.台湾国际刑事司法互助的现状与发展[J].军法专刊,2009,1.
[12] 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3] 杨云骅.境外取得刑事证据之证据能力判断:以违反国际刑事司法互助原则及境外讯问证人为中心[J].台大法学论丛,2014,4.
[14] 林钰雄.司法互助是公平审判的化外之地?以欧洲人权法院的两则标杆裁判为借鉴[J].欧美研究,2015,4.
[15] 王进喜.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年重塑版)条解[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6] 陈祐治.刑事诉讼与证据法系列之二——证据之关联性[J].法令月刊,2008,3.
[17]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
[18] 施鹏鹏.刑事裁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革[J].政法论坛,2018,4.
[19] 许福生.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之证据能力[J].日新司法年刊,2014.
[20] 李荣耕.刑事审判程序中数为证据的证据能力——以传闻法则及验真程序为主[J].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14,3.
[21] 邱鼎文.论经由司法互助取得证据之证据禁止:以传闻法则与排除法则为中心[D].台北:台湾东海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1.
[22] [瑞]Sabine Gless.涉外刑事案件之证据禁止[J].王士帆译.司法周刊,2013,1647.
[23] 孙远.刑事证据能力的法定与裁量[J].中国法学,2005,5.
[24] 万毅.论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简评我国的证据能力规则[J].现代法学,2014,4.
[25] 詹建红.审判中心主义的检察应对[J].甘肃社会科学,2017,2.
[26] 林钰雄.刑事程序与国际人权[M].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
[27] 薛永慧.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成效与挑战[J].台湾研究,2018,3.
[28] 冯俊伟.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J].中国法学,2015,4.
[29] 刘洋.案件事实认定的新思维:从诉讼证据到定案根据[J].甘肃社会科学,2017,3.
Qualific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cross Taiwan Straight
Gao Tong
(Law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odes regulat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cross Taiwan Straight, one of which is given such evidenc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and the other of which is given such evidenc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after examination. Whether such evidence is given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depends on the judicial trust. However, the judicial trust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District can not afford the mode of being given such evidence th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Therefore, the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District should adopt the mode which is given such evidence th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after examination. The rules of examin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should contain the rule of authentication, the rule of relevance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The evidence obtained abroad should be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requested party, and the justice of discovery procedure should be examined.
【Key word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cross Taiwan Straight;th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relevance;legitimacy
【中图分类号】 DF713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刑事陪审员事实认知方式研究:以认知心理学为视角”(17YJC8200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证研究”(631928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高 通(1985-),男,山东淄博人,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文章编号】 1002— 6274( 2019) 03— 096— 13
(责任编辑:黄春燕)
标签: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论文; 证据能力论文; 关联性论文; 合法性论文; 南开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