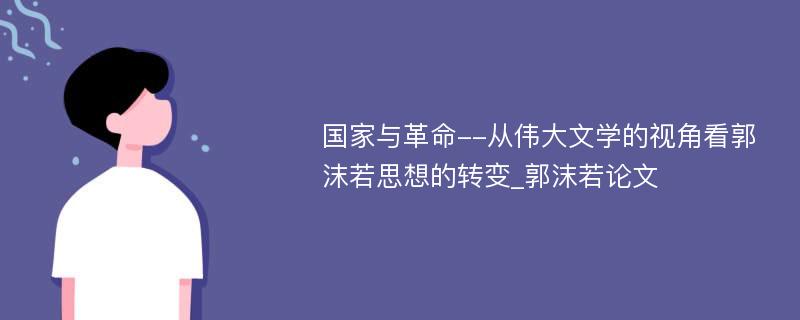
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视野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2-0113-07 五四新文化的主题是个性与自由,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多个时段不断重复的主题却是国家与革命。这样的转折出现在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则是典型代表。曾经激荡着“五四狂飙”的郭沫若自我否定,转向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这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典型事件。至于转折的原因,则一般被解释为郭沫若阅读和翻译国外的思潮与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结果。1924年,郭沫若从翻译日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①。为了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系统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还试图用五年时间翻译《资本论》。自此以降,个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为艺术”的郭沫若开始演变为群体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和功利主义文学追求的郭沫若,“国家”与“革命”的主题成为郭沫若思想与文字的首选。 郭沫若的这一转折并不只是思想和概念的替换,其背后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巨大转换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宏大历史。仅仅透过书籍的阅读和知识的转换显然无法说明这种历史转折的深刻缘由,而且如此重大的转折也绝不会只有某一种单纯的源头,其中渗透的是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状态与复杂的人生选择,需要仔细的辨析。郭沫若思想转变过程本身就从属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文化更新到社会革命的繁复历史进程,同时也来源于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的人际交往与思想互动。换句话说,一般的文字渊源和文学比较并不能真正解释郭沫若转变的奥秘,对郭沫若思想转变的认知有必要置放在“纯文学”之外的历史文化的大框架之中,这种跨出个人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梳理文学现象的方法,一般被称作“大文学视野”。借助大文学视野,郭沫若思想转变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与思维特点有可能浮出水面,而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变化甚至影响了郭沫若的一生,并对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心态不无帮助。 “政治经济学”的认同与歧路 郭沫若的转变以文艺观念的自我否定为明显的标志,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个“文艺事件”。如果说,当年创造社同人汇聚、引领“文学革命第二阶段”体现的是一些理工医科留日学生的“文学理想”②,是中国现代文学面向“纯文学”方向的重要诉求;那么,此时此刻文学观念的转折却可以说是来源于一种“政治经济学认知”,而促成这种转折的则是一群研究政治经济的中国留学生——孤军社同人,也就是说,郭沫若文学思想的转折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问题是这种交往和交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创造社同人范畴,因此辨析起来也需要有特别的耐性与仔细。 孤军派的诸多成员都是东京帝大经济学科的学生,不少直接受教于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受其影响,他们一度就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展开了大讨论。后来的《孤军》杂志从第2卷1期(1923年12月)开始到终刊号(1925年11月)共15期,连续辟专栏“经济政策讨论”。该专栏中关于中国经济模式及发展路向的论争,被日本学者认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到了探索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现状的阶段。③这一思想运动的背景对郭沫若至关重要。郭沫若很早就结识了孤军社健将李闪亭,虽然他那时对这位“中国马克思”的理论还不甚了了。郭沫若的记叙是: 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么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④后来,郭沫若数次旁听过孤军社同人的讨论:“那里的同人大都是同学,而且多是专门研究政治经济的人。特别是那位陈慎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⑤陈慎侯是《孤军》的创办人,而《孤军》又是郭沫若居中引荐到泰东书局出版的,所以他一度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⑥1922年8月8日,就在《孤军》出版前夕,“孤军派”陈慎侯不幸去世,10天后郭沫若作诗剧《月光》,题辞是:“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月光》中的博士先生筹办《孤灯》杂志,“想擎起一把火把在那旷野里驰骋,使狼们见了火光早早退避,使人们见了火光早得安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一直向前”,显然就是喻指陈慎侯。⑦此后,《孤军》由何公敢主持,郭沫若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题写刊名,在上面发表作品。1924年的四五月间,郭沫若在日本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⑧,而此书的原本就是来自孤军社的林灵光。著作译毕,郭沫若还致信给何公敢,自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益见坚固”,“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主义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在此时,孤军同人依然是他愿意分享的思想同道。⑨ 总之,郭沫若以文人之身关注政治,关注中国社会,就是从他与孤军社的接触时开始的,1924年12月,参与孤军社组织的“宜兴之行”更是郭沫若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开端。但是,与孤军派的交流既推动了郭沫若世界观的更新,又在最终的走向上逐渐划开了彼此的距离,各自发现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选择。 1922年9月,在《孤军》创刊号上,郭沫若发表了《孤军行》,号召同胞抨击黑暗、追寻真理: 进!进!进! 同胞们在愁城中, 恶魔们在愁城外: 滔滔的马面牛头 四面攻着愁城在。 进!进!进! 驱除尽那些魔群,把人们救出苦境!诗歌情绪激昂,但究竟这是怎样的“愁城”,有着什么样的“魔群”,如何才能救人于水火,却语焉不详。如此笼统的黑暗抨击犹如同一期的《孤军宣言》,满篇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愤懑,但却未能提出强有力的明确主张。恐怕正是这样,《孤军》创办人何公敢才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态度”。⑩换句话说,在对现实世界的最初的“文学性”的感受中,他们是可以沟通的。 然而,随着各自思想的进一步清晰化,情况就有了不同。到了1923年1月《孤军》第4、5期合刊号上,郭沫若的诗歌《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却在现实批判之中表达了鲜明的“革命”主张: 人们醒!醒!醒! 你们非如北美独立战争一样, 自行独立,抗税抗粮; 你们非如法兰西大革命一样, 男女老幼各取直接行动, 把一大群的路易十四弄到断头台上; 你们非如俄罗斯产业大革命 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 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 人们哟,中华大陆的人们哟! 你们永莫有翻身的希望! 人们哟,醒!醒!醒! 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 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华人权大革命哟!《孤军》第4、5期合刊号为“推倒军阀专号”,虽然郭沫若与《孤军》同人一起致力于“推倒军阀”,但是,在郭沫若这里,“革命”成为了改变现实的重要选择,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获得了肯定与激赏,这就使《孤军》的思想倾向产生了分歧。因为,同一期发表论述的其他《孤军》同人那里,都倾向于通过维护民国法律的体制内措施来“推倒军阀”,寿康称:“我们要想推倒军阀,我们第一非有一种足以推倒军阀的强制力不可!我们有了这种实力,我们方才能够强制军阀去废督裁兵,强制军阀去服法就范,进而言之,我们有了实力,我们方才能够实实在在地推倒军阀。”(11)这“实力”是什么呢?文章未予说明,但从它提示我们“参见”另外一文《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中,我们读到的都是一些体制内的协商主张,所谓“我们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分为促进裁兵,实行裁兵和裁兵善后三层”(12)。姑且不论这里的“裁兵”主张究竟能否保障论者所期盼的“实力”,我们的确可以知道,这样的思路还是以承认现存体制与法律基础为前提的,有别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革命”思维。所以在《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文后,《孤军》编者特地加上了“同人附注”,申明与郭沫若“革命”思维的重要差异: 这篇文稿系旧友郭沫若先生特为《推倒军阀专号》惠寄本社的文字。结构内容真可谓宏伟之至!一读以后令人振奋。同人爱重这篇文字,以为是最近文学上的杰作。文字里面虽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见似乎与《孤军》护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细考察起来,郭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如此郑重其事的说明,显然是为了维护《孤军》思想的同一性。对军阀实施以护法为基础的“推倒”而不是国民革命的“打倒”,这里反映的也是对现有国家制度的根本——法统的维护,《孤军》同人试图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修复法制,重建秩序,而不是根本改变现有体制,再造国家与社会。《孤军》初期,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思想的启发只在对现有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而不是其解决问题的手段——暴力革命,相反,郭沫若则迅捷前行,他不仅服膺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而且最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阶级反抗、暴力革命的主张。 “国家主义”的殊途与同归 当然,民国时期寄“法统”的希望于军阀混战,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自1923年下半年之后,北洋政府的腐朽已经完全践踏了他们的宪政理想,和平的体制维修越来越无望,萨孟武回忆说,《孤军》自第二卷以后,对于政治问题,渐次变其主张,就是由议会主义而转为革命主义。(13)只不过,转向“革命”的“孤军”并不是接受、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是将自己的这一追求概括为“国家主义”: 故吾人当唤醒民众,知国家之如何,使其戮力同心,创设独立统一之国家,如斯主义,即所谓国家主义也。然国家主义,惟以抽象的主义而宣传,对其具体办法毫不一言者,则其不生效果,犹共产主义惟以抽象的主义而宣传,未曾提及其具体办法之生产机关社会化者,相同也。夫中国欲行国家主义,固当振兴产业以抗外国之经济压迫;整顿军备,以拒外国之武力的抑制。然此必国内统一,政治纳入轨道之后,始可实行。故今日中国虽言国家主义,而其步骤,亦从内政始也。(14)萨孟武的这篇论述虽然以“革命”为题——革命理论及革命方略——但不难看出,其关注的出发点还是国家:国家的政治统一、国家的经济生产、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他看来,“抽象的”共产主义理论较少关注这些具体的国家事务因而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共产主义之物质条件,尚未存在,亦未在成立过程之中,故吾人对此问题不能解决者,惟有自己所能解决之政治问题耳。”(15)从早期的“法统”信奉到借助“有道的革命”完成合理的国家设计,《孤军》同人立足国家体制整体设计的思路“变中有不变”。大部分孤军同人最后都走进了国民党,成为“党国”体制的一员,这就与颠覆现行制度、从政治到社会全方位“革命”的郭沫若分道扬镳了。 1925年8月,《孤军》3卷3期在连载郭沫若《到宜兴去》的同时,特地又刊登了“记者”对此文的一段摘录,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提倡》。摘录竭力突出郭沫若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不知这提示般的编排是不是有意识要挽留“旧友”,因为,此时此刻的郭沫若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孤军社的基本立场有了重要的分歧,尤其针对林灵光、郭心嵩等人,陆续写下了多篇争论和驳诘,包括《盲肠炎与资本主义》《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社会革命的时机》《无抵抗主义者》《卖淫妇的饶舌》《文艺家的觉悟》。(16)毫无疑问,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与信奉国家主义的孤军同人的分歧是严重的。然而,这些孤军社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不是就是“极端反动”,与郭沫若毫不相容呢?我觉得远不是这么简单。 从当时的政治立场来看,孤军社质疑和抨击共产主义理想,又最终投入“党国”的怀抱,这固然与郭沫若尖锐对立,但是,如果考虑国家主义——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读解中国问题,通过强化国家整体利益的方式改变现实——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一个更复杂的背景上来仔细清理和描述这些相互纠缠的思想,尽力辨析其中的交叉、共生之处,揭示中国现代思想发生演变的各个细节,否则,也就无法解释郭沫若何以拥有与《孤军》同人相似的知识起点,而且即便是在争论之中,也没有决然断开所有的主张和理念。 我们注意到,虽然郭沫若与《孤军》同人在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及阶级论等问题上分歧明显,但是,在突破个人主义,立足国家立场这一重要取向上却依然有着一致性,只不过,郭沫若为了区别于孤军社的“国家主义”,特意为自己的主张命名为“新国家主义”。 在郭沫若那里,“国家”不再是笼统的一个抽象概念,它被分为了两种:“一种是旧式的国家,一种是新式的国家。”前者是“有产阶级所形成的,它是掠夺榨取的一种机器,它的本身就包含酝酿战争的毒素”。后者却不同于旧式的国家,“它要采取公产制度,它当然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它的目的是在实现永远平和”。从这里出发,“国家主义”自然也就顺势分成了两种:“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这是旧国家主义。反对这种国家主义而欲纠合无产阶级以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不消说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也可以称为新国家主义。”(17)郭沫若又特别指出,所谓“新国家主义”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厉行国家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场。我们假使不想永远做人奴,不能永远做世界的资本国家的附庸,我们中国人只剩着一条路好走——便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劳农俄国的道路。”(18) 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固然有着郭沫若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是作为“新国家主义”的观念,它又的确与当时自由主义者理想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界限明显,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极有代表性的基于“中国国情”与“中国问题”的思路。1925年7月在给漆树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所做的《序》中,郭沫若阐述说:“在中国状况之下,我是极力讴歌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对者。我不相信在我国这种状况之下有资本主义发展之可能。”“要拯救中国,不能不提高实业,要提高实业,不能不积聚资本,要积聚资本,而在我们的现状之下,这积聚资本的条件,通通被他们限制完了,我们这种希望简直没有几分可能性。然而为这根本上的原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缔结了种种不平等的条约。由是他们便能够束缚我们的关税,能够设定无限制的治外法权,能够在我国自由投资,能够自由贸易与航业,于不知不觉间便把我们的市场独占了。由这样看来,我们目前可走的路唯一有一条,就是要把国际资本家从我们的市场赶出。而赶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是以国家之力集中资本。”(19)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解释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为什么来自外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潮最终能够成为“中国问题”的答案,或者说“中国意识”关注的对象?因为,在20世纪,思考如何从国家层面上整体地更有力量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乃是如同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重要选择。同样作为“国家”的信奉者,孤军社认为共产主义的危险在于“消灭国家”,而郭沫若却能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将有利于巩固“国家”,孤军社的“国家”更指向当下和现实,而郭沫若的“国家”则更属于未来,显然,郭沫若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更为准确,也符合后来的实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重视“国家”立场的意义上,郭沫若与孤军社也不无沟通之处。所以,就是在论争中,郭沫若也强调了这些“国家主义者”的“误解”,其中不无包含他个人的某种“同情”: ……但是我们的国家主义者之排斥马克斯学说及其信徒,我想来总不会是因为信奉资本主义,信奉个人主义的原故罢?你看他们也在不满意于国内的特权阶级的暴行,也在不满意于国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他们之中也还有标榜孔子的大同思想的人,虽然他们的经济政策还不见得有甚么鲜明的表现,我想来他们那般爱国的至诚(我诚心诚意地在这里写出这一句话,我深深觉得国家主义者中是有不少的真诚的志士,我们不能徒用感情的话来一概骂倒的)总不会想把我们中国再造成欧西或日本的那种畸形的国家罢?我希望他们对于马克斯主义的排斥要只是出于不了解,或者误解才好,实际上他们实在不免有些误解,就如上面他们引用马克斯的“工人无祖国”的话来说马克斯不承认国家,也就可以证明了。(20) 从旧制度的批判到新国家的皈依 重读郭沫若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尤其是在“国家”与“革命”这样的关键性思想问题上之于现代思想史的复杂纠缠,这就是我所说的“大文学”视野的研究方法。现代中国历史演变与思想动态的复杂性都将我们的文学引入到了一个混杂而丰富的环境中,绝非美丽的“纯文学”所能概括,亦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21)借助“大文学”的广阔视野,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回溯郭沫若思想演化的起点,而且还可以继续追踪,直达他未来人生的终点,进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解如郭沫若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未来的精神状态与思想逻辑。 1917年8月至9月流亡芬兰的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本后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之作,成为俄国革命与俄罗斯民族通往社会主义时代的理论旗帜。作为东方“后发达”民族的相似性,其“国家”与“革命”的命题可以说同样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核心话语。对于不满于现实国家秩序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程度地抨击和批判现实国家的反动性质、揭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势所必然,这就仿佛是列宁的著名论断:国家并不是超阶级的阶级调和的机关,它恰恰“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22)。因此,主张努力修补现有秩序,在现实国家的基础上实现“宪政”的“国家主义”,对郭沫若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国家”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工具,在未来因为“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使得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出现之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23)这样的论述既区别于旧有的国家主义者,但也依然肯定了“国家”立场与“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郭沫若与孤军社的区别与联系都在于此。 通过“革命”完成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改造,这是近代以来包括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只是,单纯的“革命”并不能解决现实秩序重建的问题,也不能在一个资本竞争的时代有效地维护我们的整体利益,于是,“革命”理想与“国家”立场的问题又一次置放在了人们的选择之中。如孤军社这样的国家主义者最终回归到了“党国”的怀抱,试图依赖国家的整体力量解决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与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则继续挑战现存的“国家”秩序。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不同的在于,像郭沫若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一开始就怀有对“国家”整体价值的肯定,并且将对未来“新国家”的皈依当做自己的理想。郭沫若《卖淫妇的饶舌》不仅是与国家主义者的论战,也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回答。 清理这样的“国家”与“革命”理念,有助于我们深切理解郭沫若思想转换前后的心理与文学意义,也可以深刻认知左翼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演进。这两个方面的启示可以如此表述: 第一,我们可以重新解释郭沫若转换的内在逻辑:他为什么如此迅捷地完成了个人—群体、艺术—功利的转折?过去,我们过分突出了“五四”时期郭沫若文学精神中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一面,以致造成对后来“突变”的困惑不解。重读《女神》,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量的抒情都基于整体的立场,如《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炉中煤》《棠棣之花》《浴海》《地球,我的母亲》《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郭沫若的个人抒情往往不是立足于个人遭遇的改善而是对整体的生存境遇的关怀,不是聚焦于艺术独立的目标而是艺术力量的实现,在《棠棣之花》中,聂嫈的理想是“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炉中煤》中的“女郎”被注释为“眷念祖国的情绪”,《浴海》的畅快激发了“新社会改造”的热望,《梅花树下的醉歌》表现的是“全宇宙的本体”,《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解放的呐喊,当诗人发现,这样的“解放”追求可以借助国家民族的整体改造加以实现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及时地调换船舵,顺势前行。在现代中国,如果国家局势的整体改变有助于社会理想的实现,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扬能够赋予艺术以空前的力量,那么,左翼知识分子凭什么不能迅捷接受而要加以拒绝呢? 第二,我们可以重新清理现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和基础,特别是他们从民国时代的激烈批判到共和国时代的由衷认同的思想连接。在过去,我们充分肯定了左翼文化的“民国批判”的这种空前的勇气与正义,但有时却难以说明新中国“极左”年代的万马齐喑,特别是对于郭沫若这样批判—认同前后反差显著的知识分子。近年来,“贬郭”之声不断传响,人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人格”问题上大做文章。然而,历史的繁复终究不是一个飘移不定的“人格说”就能够轻松解释的,对于像郭沫若这样经历近现代血雨腥风考验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思想深层的脉络,简单的性格气质认定是难有充足的说服力量的。如前所述,当我们发现在他那里潜伏着“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思想选择,许多奥秘也许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解释,对“黑暗”民国的拒绝和对“新生”的共和国的充分信任和接受,这本来就是他思想的“一体两面”,具有相当顺畅的逻辑联系。至于如何反省和评价这样的“新国家主义”,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对现存“国家”的强烈不满而生发了“革命”的渴望,又因为“革命”的成功而迎来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保有着对这个崭新“国家”的忠诚,这可以说就是现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与左翼作家的思想状态。这样的左翼不同于古代士人,也有别于国外的思想左翼,它属于现代中国独特语境的产物,如同郭沫若的思想转变一样,其起承转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注释: 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②郭沫若认定:“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到了第二个阶段。”(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③[日]三田刚史:《留日中国学生论马列主义革命——河上肇的中国学生与〈孤军〉杂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④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08页。关于郭沫若与孤军社的关系,潘世圣、何刚、陈莉等学者都有过重要的研究。分别参见潘世圣:《关于郭沫若与“孤军派”关系的概略考察》(《广西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何刚:《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解——以郭沫若与孤军社论战为主的考察》(《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陈莉《郭沫若与国家主义派论战中的人际关系探微》(《郭沫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IGMA学术年会论文汇编》2010年)。 ⑤⑥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44,145、144页。 ⑦首刊于《学艺》月刊第4卷第4号,1922年10月。 ⑧郭沫若:《〈郭沫若选集〉自序》,见《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8页。 ⑨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 ⑩何公敢:《忆〈孤军〉》,《福建文史资料》1986年第13辑。 (11)寿康:《什么是军阀怎样倒军阀》,《孤军》第1卷第4、5期(合刊),1923年1月。 (12)肃清:《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孤军》第1卷第4、5期(合刊),1923年1月。 (13)萨孟武:《孤军已满两岁了》,《孤军》第3卷第1期,1925年6月。 (14)(15)萨孟武:《革命理论及革命方略》,《孤军》1925年第12期。 (16)分别见:《洪水》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洪水》第1卷第4期,1925年11月;《双声叠韵》,《洪水》第1卷第5期,1925年11月;《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1月;《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洪水》第1卷第12期,1926年2月;《洪水》第2卷第14期,1926年4月;《洪水》第2卷第18期,1926年5月。 (17)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 (18)郭沫若:《一个伟大的教训》,《晨报副刊》1925年5月1日。 (19)《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02、304页。 (20)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 (21)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2)(23)[苏]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140页。标签:郭沫若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国家与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郭沫若全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