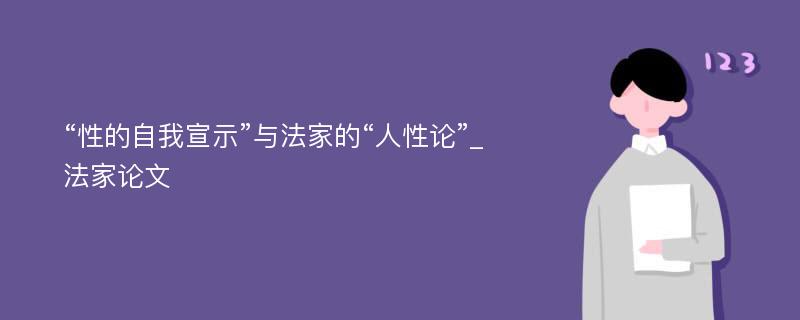
《性自命出》与法家的“人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家论文,人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2)02-0009-06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是今日学界所公认的“言情”篇。它之所以让人如此关注,是因为大家以为,该篇文字的出土,将从根本上扭转世人所谓儒家不重“情”、甚至“非情”的传统看法。从满篇可见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德目看,它似乎应该被划归儒类,所以有人主张,《性自命出》的卓越之处,就在于系统地论述了人的性、情,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性,从主体性的高度,为儒家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人性基础,从而调节、补充和完善了以往孔子对性、情敬而远之的“人学”思想[1]。由于孟子一直被视为孔门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有舆论认为,这些郭店出土的儒家简都应与“思孟”有或多或少的关连,有学者甚至推论说,荀子的“思孟”连称是有道理的,后世学界所谓“思孟学派”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2]。但是,简文中未见孟子“性善”说的言论,且“仁内义外”说与告子同、与孟子反的现象,又让人觉得“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3],甚至有人说,竹简“不属于思孟学派甚明”[4]。显然,在做深入一层的探索时,人们的口气开始变得游移,这种游移集中表现为:若认定孔子思想的核心是重性情,那么这些竹简的价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它们意味着对孔子思想的丰富和重要发展;若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不是重性情,则这批竹简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重要的是,在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之际,孔子并没有去谈情、性;而作为孔子继承者的孟荀花那么大的气力去论证人性善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又一直让人怀疑[5]。
严格说来,《性自命出》中并没有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而且事实上《论语》、《孟子》中亦绝无对“情”的讨论。《荀子》虽言及“人情”,但从《性恶》篇疾呼“人情甚不美”等情形看,在孔、孟、荀三者的范畴体系当中,“人情”本身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就历代儒家或以礼抑情,或以性禁情,甚至以理灭情等不争的事实看,《性自命出》的“人情”论,作为孔、孟、荀思想之鲜明反例,的确也无法被视为经典儒家的舆论。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该篇中最突出的“尚情”思想只是“在庄子学派中得到发扬”了呢(陈鼓应文,见前揭)?情况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恐怕还是出在对“情”和“人情”的解释上。由于解释的不同,特别是由于解释上的歧义迭出,《性自命出》的“人情”真面目,才变得愈加朦胧,愈加难知。由于解释本身直接关乎“人情论”的学派归属,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提出讨论,以就正方家学者。
竹简出土后,对简文“情”字的解释,可称林林总总。大体说来,可理出如下两类。一种观点以为,“情”,指的是“感情”,认为一个治民者,如果与人民有感情上的沟通,虽有过失,人民也不会嫌恶他。他若对人民有情,即使他没有做事,人民也相信他[6]。另一种观点以为,原始儒家所言之“情”是“实”,与“感情”无关。《性自命出》中的“情”,其实是指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美感情怀”,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陈鼓应文,见前揭)。就某个特定的角度或语境而言,上述讲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比方说,按照“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儒家伦理模式和“游心于物之初”的道家唯美主义来理解《性自命出》的“情”,就泰半会得出以上的结论。但是,如果单就字面而言,却会发现,这些解释,其实都带有一定的预设倾向。因为从“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中,并不能读出“感情”或者“美感情怀”的意义来。而在“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一段中,其实也读不出上述两种解释的内涵。倘若去掉先入之见,那么,这两段话的意思就会变得平易许多,也直白许多。前一句话似可理解为:“道开始于人情,而人情则发生于人的本性”。至于后一句,至多也只能作出以下两种解释,即:“大凡人情,多为喜好之事。如果因人情而为之,即使过度一些,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恶的;如果逆人情而为之,即便好事多磨,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贵的”。或者:“大凡人情,多为喜好之事。如果因人情而为之,即使过度一些,也无所嫌恶;如果逆人情而为之,即便好事多磨,也不值得崇尚”。前一种解释法,说的是对人情所做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即人情本身无善恶。这几乎成了《性自命出》中性情说的基调,也是人情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后一种解释法,讲的则是人情论的基本内涵,即以“好”(悦)和“恶”为核心的人的“趋利避害”本能。显然,这两种解释,都没有离开人情论的本旨。而尤为重要的,是《性自命出》所指出的把握人情实相的基本方法,即“以其情”。“以”者,“因”也;“以其情”者,“因人之情”之谓也。当我们了解到《性自命出》的“情”具有不言善恶、只看有无,不言理想、只讲好恶,且提倡“因”道等基本特征后,一个与之极为相近的学术思想——法家的“人情”观,开始浮现,并且愈现愈明。
有关“人情”的界说,在中国古典中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先秦时期,“性”和“情”分得往往不十分清楚。直到荀子,才算有了大致的界定。日本学者荻生徂徕在读解《荀子·儒效》篇“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情(或作“积”)矣”时指出:“‘隆情’‘隆性’,性、情之分始见”。[7](P486)这一点,在《荀子·正名》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又称“人情”。《礼记·礼运》的界说是:“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荀子的“喜怒哀乐”到了《礼运》则变成了“喜怒哀惧”,“好恶”则易为“爱恶”,而且后者还加了一个“欲”字。如果用“死”和“活”的感觉来把握人性与人情,则固定不变的人性是死的,而变动不居的人情才是活的。如将“人情”做进一步细分,则人情表象的“喜怒哀乐”或“喜怒哀惧”,应当被划归“瞬间情感”范围;而决定瞬间情感的“好恶”和“欲”,却往往是不形于色的人情中最根本和最主要的东西,属“恒定情感”范畴。由于它才是人情的本质所在,所以朱伯崐说:“人性中支配人类生活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好恶之情’,即好利恶害之情”。[8](P108)法家的“人情”,便正是这种支配人类生活的人类情感中的本质要素。
《商君书·错法》篇说:“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法家学派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欲”视为人情中恒定不变的因素。如管子——“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管子·禁藏》);如慎到——“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如韩非——“人情者有好恶”(《八经》)、“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等等。法家不相信人没有欲望,至少不相信世上还有悖“趋利避害”之铁律而逆行者:“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制分》)、“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难二》)。在法家看来,人情,就是“人之实情”。人只要来到这个世上,就得学会生存,就要学会如何生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只要这个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存在一天,人“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实情”,就一天也不会改变。显然,这种与人的一般“感情”和“美感情怀”没有本质关联的“人情”,已成为法家诸子对人的一贯观察标准和社会治理原则的终极根据。所以《管子·五行》篇说:“人情已得,万物有极。”它的具体操作原则,便是“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
“因人情”,是法家诸子的一贯舆论。《商君书》即讲:“人情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错法》)管子亦主张要“因人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心术上》)。“因”道之理,似以慎子的说明为最详尽:“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因循》)人情的特征,可谓“昭昭然若揭”,可感、可知、可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情论,几乎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势必要与不可感、不可知、亦不可把握的人性理论关系紧张。事实上,“人情论”的对立项,也正是孟荀所主张的“人性论”。正因为如此,人情论的全部特点,也几乎均体现在与人性论的对立之中,即:“人情论”的依托,是后天原则,而不是先天原则;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这样讲的根据在于,儒家,主要是思孟一系的价值系统,实际上是建立在两端的世界里,即:先天世界(性善·性恶论)和彼岸世界(人性论的理想归宿—圣人论)。由于这两个世界都不具有可证明性,所以,儒家的知行过程便只能依靠来自先天的价值判断原则和通向彼岸的理想主义憧憬。而法家的儒家批判,则刚好展开于夹在这两个虚幻世界中间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人世间的“人情”世界,由于是人世间的“人情”世界,所以,法家也与一味追求“方外世界”的道家、特别是庄子的人情论,划清了界限。
把《性自命出》和法家放在一块考虑,是因为二者在“人情论”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前提的一致。法家的“人情论”,是建立在否定人性“善恶论”基础上的思想体系。《性自命出》强调,“人虽有性,心无奠志”、“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心无奠志”,否定了预设和想定的价值前提。这一前提的否定,就使善与恶的评判标准,不可能再是孟、荀意义上的“人性论”。从篇中“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等主张看,它的善恶标准事实上已落在是否合乎“人情”的根本尺度上,而人情本身就是无善恶可言的。这与法家的价值观可谓空前一致。
2.内容的接近。法家认为,人情总是趋利避害的,故每言“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也”。《性自命出》谓:“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意思是说,好恶是人的本性,物,则是好恶的对象。这里的“性”,显然是韩非所说的“情”。《荀子·正名》篇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之谓情”。《语丛一》在谈到“好恶”时讲:“有生有智而后好恶生”。这里的“智”,与韩非“夫智,性也”(《显学》)的表述也没有什么不同。说明《性自命出》的“性”与韩非所说的“性”,在本质上已与“情”相混一了。难怪陈鼓应说,《性自命出》中的“‘好’‘恶’都是性,这和孟子性善说更加不同”了(同前揭)。而《性自命出》篇“所好所恶,物也”的说明,则与儒门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之类对“物”的鄙薄舆论完全相反,却反而与管子的“人情已得,万物有极”命题密结在一处了。
3.“心学”反对上的相似。法家是反对“心学”的。《性自命出》竟也说:“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求其心之有为也,弗得之矣”。“心”的否定,就使《性自命出》从根本上与孟、荀人性善恶的先验之“根”,斩断了联系。因为研究结果显示,《性自命出》在谈到心、性问题时十分强调后天的“学”与“习”,强调外在教化对内在心性的规约作用和意义。
4.“道”论的趋同。《性自命出》称:“唯人道为可道也”、“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按照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这里的“道”,显然不是非不可道之“道”,故不是老子所讲的“先天地生”之“道”也审矣。这一点,与韩非子非“先天地生”的“道”之间,[9](P28)并无本质差别。
如果说,观点上的相似不足以证明《性自命出》与法家“人情论”之间有何切实的关联,那么,学脉上的考察,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首先,看儒法之间所存在的学术关联。
有学者以为,韩非子“孔、墨之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显学》)的说法多有夸张,人们不必过于认真。但《汉书·艺文志》所录之儒,竟有五十三家开外,而且仅孟子以前的孔门子书就将近十种,即: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说明从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贤人中衍生出八个“新儒家”或更多一些,亦不足为怪。可以推知,“新儒家”覆盖面的如此博大,至少应该与各种主要观点有所交汇和小面积重叠。那么,法家,特别是韩非的“人情论”,究竟与《性自命出》有无干系呢?仅凭现有的资料,这还是一个很难求证的问题。不过,韩非见过《性自命出》篇,却是极有可能的。理由是,韩非在谈到“儒分为八”时,曾提及“孙氏之儒”。一般多将其解作“孙卿(荀卿)之儒”。可是,通《韩非子》全书,“孙卿”字样凡一见,即:“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难三》),而且也从未见过韩非把“孙卿”与儒做过连接。日本近世学者津田凤卿指出:“孙”字前恐脱“公”字。因为《汉书·艺文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注曰:“七十子之弟子”。或曰指孙卿子者,非也。唐敬杲说:《玉海》引《韩子》,“孙”上有“公”字[10]。按照王充的说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论衡·本性》)。《性自命出》通篇论性情,且其人性论亦并非善恶论,故有学者得出结论说:《性自命出》当属《公孙尼子》。而且根据《汉书·艺文志》,《公孙尼子》在《孟子》之前(陈来文,见前揭)。果真如上述推度,则韩非见过《性自命出》,就不再是没有根据的妄测蠡说了。当然,与法家“人情论”将社会治理的方法落诸“法”和“理”不同,《性自命出》的“人情说”最终还是把它落在了仁义礼智这些儒家的德目上。这也是儒法间的重要区别所在。
其次,由告子和管子所透露出的“稷下黄老”学脉,令人瞩目。
很多学者认为,《性自命出》中的“善不善,性也”,与孟子的人性说论敌、稷下黄老学者告子及其“性无善无不善”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指出,《性自命出》中的“礼作于情”(《语丛一》中亦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句),显然也受到了稷下黄老著作《管子·心术》篇之“礼者,应人之情”论的深刻影响。且《性自命出》“理其情”的说法,与仅见于稷下黄老著作《管子》四篇中的情理对举现象的高度一致,并非偶然。《白心》篇说:“言其理则知其情”。[4,6]陈鼓应的例举,目的在于证明黄老学派、尤其是《性自命出》“人情论”的道家属性。问题是,黄老学派的主旨既有道,更有法。且管子是公认的法家人物,托名之作《管子》四篇实不可断然判定就是纯粹的道家作品。唐兰在分析司马谈父子所谓“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其归本于黄老”等断语时讲:“说申韩本黄老,重点是在法家的黄而不在道家的老”。[11]这话是有见地的。这种见地的确凿化,始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
作为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哲学核心是“理”,政治原则是“法”(容另文专论),而社会基础则是“人情”。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黄帝四经》中,法家的这一“理论”,就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展示。
首先,与老子讲“道”而不讲“理”、讲“先天”而不讲“现时”不同,《黄帝四经》不但注重“理”,而且注重“理”的后天性和现时性。
《黄帝四经》之《经法》篇说:“七法(指天之道、天之度、天之期,等)当其名,胃(谓)之物。物各[合于道者]胃(谓)之理。理之所在,胃(谓)之[道]。”该篇主张,要“审察明理”,要“循名究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注:帛书《黄帝四经》引文俱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相关章节,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比起老子形而上的“道”,《黄帝四经》的“理”,讲的是并不“恍惚”的“物”的规律,具有“关心形而下”的鲜明特质。这一点,与韩非《解老》篇中所言,几乎完全相同。日本学者池田知久说:“马王堆帛书《经法》篇把‘物’的各合其道(原文略)状态称为‘理’。这应该说是《韩非子》解老篇‘道理’概念的一个展开。”[12](P315)这一点,反向印证了张岱年先生对韩非“道”论的准确理解。他认为,韩非的“道”,“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而不是老子之“道”的“先天地生”。“韩非所谓道即是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并非超越自然的绝对观念。”[9](P28)韩非之“道”的后天性,决定了“理”的现时性和非彼岸性。韩非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解老》)。这与《黄帝四经》《称》篇的“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毁,非时而荣则不果”和《十大经》篇“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必有成功”的表述,可谓异曲同工。
其次,“理”的社会基础本乎“人情”。
法家的“人情”,在《黄帝四经》中被表述为“人理”。《经法》篇云:“其〈失〉主道,离人理,处狂惑之立(位)处不吾(悟),身必有瘳(戮)”。何谓“人理”?谓“人事之理”也。“[人]事之理也,逆顺是守”,“人事之理也,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这也是《称》篇“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的道理所在。惟此,《十大经》篇提倡“因”道,主张“圣人因而成之”。对人要“因”什么呢?曰“因其所利”:“圣[人]举事也,阖(合)于天地,顺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生(姓)”。表明,治理国家,要根据现世的人情——人之实情。不可忘记“人情好利”的本质而把治国原则建立在不切实际的道德假设上。那样做是冒险的,即便成功,也是侥幸的。帛书的这些舆论,证明“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这一经典法家舆论,其原始命题,已备诸《黄帝四经》;而饶有兴味的是,通《黄帝四经》全书,竟找不到一例引诗书、谈仁义、颂礼乐的文字,所看到的,只是“王者不以幸治国”(《十大经》)这样的务实箴言。这与韩非“圣人治下无幸民”的思想可谓空前一致。惟此,他强烈主张要“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备内》),要“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守道》)。而要做到铲除“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这些“乱之本”(《难二》),就要弃绝“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仁政”。由于“仁政”讲感情不讲原则,讲臆度不讲实际,所以最终将成为乱政的根本:“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八说》)。而理、法、人情,最终在韩非那里实现了完美的“内和谐”,即:“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制分》)。
《性自命出》与黄老学派的深刻关联、《黄帝四经》与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以及韩非与《性自命出》的学脉承继,这些,都在一步步确证《性自命出》中“人情论”的学说沿革和学派属性。在《性自命出》中,儒家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道家的色彩亦不可谓乌有,道法家的感觉也时有所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篇中“人情论”与法家理论的一脉相承,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这些现象而言,把《性自命出》篇归诸“杂家”类,似乎更能贴近一点真实。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见诸儒家的“人情论”,会大量出现在被武断为儒家著作的行文当中,也可以解释何以所谓儒家著作中的人性论竟会与法家的人情论叠韵双声,更可以解释为什么颇似道家的《管子》四篇中会有那么多的法家观点。由于杂家著作具有吸纳百川之特性,所以,在《性自命出》中,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才没有那么紧张,而儒法之间和道法之间,似也可求同存异了。
收稿日期:2001-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