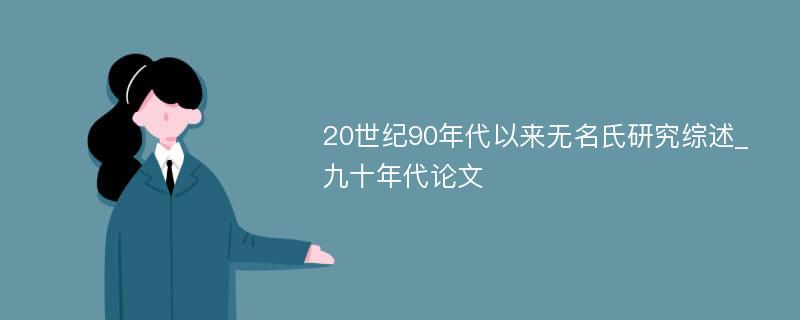
九十年代以来无名氏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名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4-097-07
无名氏原名卜乃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经历曲折、颇有争议的作家。早在20世 纪40年代,无名氏就以小说《北极风情画》(以下简称《北》)和《塔里的女人》(以下 简称《塔》)一举成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无名氏一度沉寂,但他长期坚 持秘密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无名书》(以下简称《无》)的后三部半。到了80年 代,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步放宽和海外学界的大力推介,内地的一些刊物和选本(如 严家炎选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陆续刊登了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重新浮出 海面,有关他的研究开始日益增多。
一、走出沉寂的无名氏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起,无名氏这位曾经声名远扬的作家突然“人间蒸发”,不但在当时 的文学活动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就连他的名字也在文学史著作中完全消失,关于无名氏 的研究更是几乎为零。
20世纪90年代,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无名氏研究开始真正走出沉寂。这种变化突 出表现在:文学史对无名氏成就的肯定,无名氏作品的大量刊印,有关无名氏的专著、 传记的陆续出版,有关无名氏研究论文数量的空前猛增,众多学者对无名氏的关注并形 成一些无名氏研究的“专家”,等等。
在文学史的撰写方面,80年代文学史中对无名氏的论述往往是一笔带过,像杨义、严 家炎这样设专节评述的少之又少。90年代文学史中几乎都会在论述40年代国统区文学创 作时把无名氏作为代表人物之一,肯定他的成就,有的甚至还用专章的大篇幅进行论述 ,以示无名氏的特殊意义。许志英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就辟 出专章——《浪漫传奇的现代包装》将徐訏和无名氏进行较为详细的比较论述。有意 思的是,一些80年代撰写的文学史在90年代出它的修订本的时候,也对先前一些对无名 氏不切实际的评价进行了更改。如黄修己在1997年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2版的 时候,就删除了先前认为无名氏“作品倾向也更坏”的观点。
在无名氏创作的出版推介方面,大陆一直比较滞后。早在80年代初,香港就在无名氏 的哥哥卜少夫的张罗下开始出无名氏的集子,而大陆直到80年代末才由不同的出版社零 星地出了3本集子——《野兽、野兽、野兽》(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塔里的女人》( 上海书店1988)、《北极风情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很不全面也不成系统,极大 地影响了研究者们对无名氏作品的整体把握。这种萧条的情况直到1995年才被打破—— 花城出版社连续推出了《野兽、野兽、野兽》、《塔里·塔外·女人》、《北极风情画 》、《海艳》、《绿色的回声》和《无名书初稿》前两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1995年 将无名氏的一些散文小品选编成了《无名氏集:沉思琐语》。到了世纪之交,无名氏的 另外一些作品又陆续出版——《无名氏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谈情》、《说 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金色的蛇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至此,无名氏 作品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展现,研究者们可以由此获得较为客观的结论,避免了 以往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以偏概全的盲目。
90年代后期,随着无名氏研究的逐渐升温,关于无名氏的传记先后出炉。比较有影响 的是: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传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耿传明的《独行人踪 :无名氏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李伟的《神秘的无名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三者虽同为无名氏传记,却从不同的角度落笔。《神秘的无名氏》勾勒了无名氏的人 生道路和创作概况,材料翔实丰富,更多地从爱情角度表现无名氏传奇的一生,很有可 读性,但对其作品的评论太过简单;《独行人踪:无名氏传》是耿传明的博士论文副产 品,在强调对资料丰富占有的同时,着重分析无名氏特立独行人生选择的动因,寻求其 创作的精神内核;《无名氏传奇》是三者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对《无》的一些评述很 有影响,如作者认为无名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他的作品为中华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塑造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印蒂;他是我国现代派 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与其他传记侧重记述生平大事不同,《无名氏传奇》特别注重一些 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然而实际上对作家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小事”,还从现代主义文 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无名氏的创作一直被忽视、被不堪对待的原因,很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研究无名氏的论文也大幅增多,在2002年无名氏逝世后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 潮,研究也日渐细致深入,很多研究者提出了有创见有新意的观点。这些无名氏研究的 新进展,只要稍稍浏览一下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以《华文文学》为 例,它就在2003年第1期上连续登载了赵江滨、吕周聚、刘志荣的三篇无名氏研究论文 。这些单篇论文的大量出现促成了综述的必要,象吴晖湘的《九十年代徐訏、无名氏 研究综述》[1]就是对无名氏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无名氏研 究中脱颖而出,俨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如陈思和对《无名书》的研究就获得了学界一 致的推崇。
在90年代之前的无名氏研究中,评论者们往往受左倾思想的惯性影响,在评述时更多 地强调无名氏作品的消极影响,强调其小说中“洋场”和“鸳鸯”的腐化气息,钱理群 等学者就把无名氏的小说列入了“洋场小说”,把《北》和《塔》看作“哀艳的鸳鸯言 情体”,并断言“随着政治主张的趋于反动,他的创作生命等于终止了”。只有少数学 者,如严家炎、杨义在指出其缺点的基础上肯定了无名氏的创作,虽有“粗俗”的一面 ,但总体上是一部“长河型的诗与哲理小说”[2](P317)。但由于当时无名氏作品出版 的滞后,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无名氏的两部爱情小说和《无》的前两部,得出的一些结 论还有继续商榷的必要。
到了90年代,研究者们更注重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原则进行新的反思,对于一些 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的评价更为客观。
比如无名氏小说的雅俗归属问题,先前的很多学者都把无名氏的小说与《北》、《塔 》划等号,认为是通俗的言情小说,还埋怨“读者沉醉于无名氏的色情描写和性的挑逗 里”,他们没有看到无名氏爱情小说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贡献,也没有看到无名氏爱 情小说“俗”中有带“雅”的一面,更没有看到《无》作为严肃文学的意义。90年代以 来的研究者们则放开视野,或从“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出发,认为以无名氏、张 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作家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并 涌现出了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3];或从通俗小说的现 代化角度分析,认为无名氏的小说“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现代化的通俗小 说”[4]。研究者们基本认可了无名氏小说雅俗互动的性质,对于先前非议最多的“色 情”问题,也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又比如对无名氏创作与革命文学疏离的问题,80年代对无名氏持贬抑态度的重要依据 之一就是他创作的“与抗战无关论”,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越到后来,这种意识形态对 文学批评的影响越淡化,研究者们更愿意从一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小知识分子在动乱时 期作出个体独立选择的角度来理解无名氏小说与时代主题的游离。耿传明就认为《北》 和《塔》的成功与无名氏以一种“轻逸”姿态跃然于沉重的“时AI写作作”之上,确立其 创作中的审美个人主义原则有很大关系,“超时代的文化价值恰恰是无名氏没有被历史 湮没的原因”。[5]
二、研究热点
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已呈现出 初步繁荣的可喜景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80年代无名氏研究侧重于评点式的平面介 绍、文本解读不同,9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无名氏其人、无名氏小说的 流派归属、《无名书》研究等热点问题的深层发掘上。
(一)无名氏其人研究
无名氏与其他作家比较起来,有其特殊之处:与国民党有着特殊的关系;作品与抗战 无关的倾向;海外关系。结果在以往的政治环境下,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很多学 者要么是回避对他的研究,要么是以“左”的观点非议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无名 氏其人研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其人和其文之间,更注重对其文进行艺术评判;在对 其人评判的时候,也尽量回避社会历史批评,更多地从人性角度分析,强调对他的个性 特质、精神世界的反思。
在推翻了无名氏“反党反人民”的论断之后,评论者们转换思维,首先从文化人格上 肯定了无名氏的独立姿态——那是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等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评论者们一致公认无名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有思想的作家之一:光是长期进行地 下写作就需要超人的毅力和勇气。中国文人在政治势力夹缝中的人生选择是现在很流行 的一个话题,程映虹着眼于此,认为无名氏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一些作家: 无名氏实践了自己“精神独立”的信条,没有象很多“革命文人”那样经历一个从欢呼 雀跃到垂头丧气再到死去活来的过程,他没有“幻灭”,更无需“反思”或“忏悔”, 无名氏在这里窥见的是一个至今在激进政党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信仰和政 纲的矛盾,或者说终结精神目的和现实社会改造以及现实政治手段的矛盾[6]。结论虽 然略显草率,但给了先前“左”的观点以有力回击,从更深广的时空肯定无名氏的意义 。
其次,研究者们开始发掘无名氏其人对其文的作用力,寻找“文如其人”的蛛丝马迹 :何莲芳从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角度出发,认为无名氏青年时曾与白俄姑娘相爱 无果,这使他对青春、美、女性、瞬间与永恒等问题产生了激愤式思考,进而否定一切 现实享乐、现实美、女性美,导致了作品中爱情生命的虚无特征[7]。陈思和从无名氏 的精神特质角度出发,阐释他精神世界里童心似的纯粹和知识分子的浪漫、浮士德似的 不满足、堂吉诃德似的老天真对作品浪漫主义气质的影响。这些都属于对无名氏其人的 更深一层研究,目的已不再是评判,而是为思想之“流”找形成之“源”了。
这种由“其文”引发出来的对“其人”的关注,很自然地带来了无名氏其人研究的第 三个焦点:对无名氏思想源流、人生经历、感情生活等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扩充, 这是一个不断丰盈的长期的过程。在这方面,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传奇》以评传 的方式作了不少的工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流派归属
关于无名氏小说流派的命名历来分歧颇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争鸣的焦点发生了 变异——由80年代“后期浪漫派”和“新鸳鸯蝴蝶派”、“洋场小说”之间的对立分歧 转向90年代以来“后期浪漫派”、“后期海派”、“后期现代派”、“消极浪漫派”、 “新浪漫派”、“后浪漫派”等多种提法之间的争鸣。
早在80年代,严家炎就将无名氏列入“后期浪漫派”的名下,但以曾庆瑞、赵逻秋为 代表的一些学者仍坚持把无名氏划入新鸳鸯蝴蝶派,认为他的小说是典型的“抗战加恋 爱的新式传奇”,以“抗战”吸引进步的读者,又以“恋爱”来迎合落后的口味,以至 于一些读者“沉醉于无名氏的色情描写和性的挑逗里”[8](1130)。
到了90年代,虽然有很多人沿用严家炎“后期浪漫派”的提法,但不同的观点仍然层 出不穷,如孔范今主张“后期现代派”;陈思和主张“消极浪漫派”;吴福辉主张“后 期海派”;朱德发主张“新浪漫派”;许道明主张“海派”,等等。面对这样诸家争鸣 的局面,又有人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把无名氏小说归结为几种流派的混合物:“无名 氏的作品带有一种明显的混交与融合倾向:对新感觉派的感知方式、浪漫主义的手法、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故事编织的综合运用”[9]。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流派命名中,严家炎有关“后期浪漫派”的提法时间较早也比较有 说服力,一些高校教材和专业论文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应该说,每位研究者的观点都有 其依据,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据也很充分,很有生命力。如 李晓宁将无名氏划为“后浪漫派”[10],目的是为了避免“后期浪漫派”让人误解无名 氏的小说与郭沫若、郁达夫代表的浪漫抒情小说有什么渊源,也避免“新浪漫派”在今 天看来已无“新”意可言的不恰当命名,以“后浪漫派”来与之区别,用心可谓良苦。
上述有关流派归属的争论很自然地带来了对无名氏创作方法的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 为无名氏小说属于现代派小说,刘光宇[11]就在一篇论文中着力探讨了无名氏小说在选 择人生哲学命题上所显示的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有研究者在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中间 取值,认为无名氏小说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或过渡,如赵江滨[12]、吕周聚[1 3];还有研究者指出无名氏小说综合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 和艺术方法,韩文革就名之为“五彩斑斓的诗情画意”:“无名氏展示的‘诗情’是抒 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的交融,描绘的‘画意’是写意画、写实画和印象画的合一”[1 4];此外,陈思和从流派的变迁角度,参照欧洲夏多勃利昂的浪漫主义创作流派,认为 无名氏的作品“最有资格被列为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余波”,“从郁 达夫到无名氏,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由盛到衰的过程”。[15]
这些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以《无》为例,主要人物形象 印蒂通身闪烁着浪漫主义色彩,而全书的表现手法又主要是现代主义的,研究者的视点 不同,所划分的流派自然也不可能一致。不过,按基础的文学理论,如果就一个作家的 代表作的主要特色来论他的创作风格,似乎把无名氏的小说认作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 的过渡更合适一些。
(三)《无名书》研究
一般人知道无名氏都是因为他的成名作《北》和《塔》,但研究者们关注最多的却是 无名氏后期的“生命大书”——《无》,说《无》研究是无名氏研究的重中之重丝毫不 为过。在无名氏一生的创作中,《无》是最特殊的文本,其创作历经15年,到出版又是 用去41年,耗费了作家半生的心血,却迟迟不为人所认同。《无》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 大陆出版,研究起步很晚,但先前研究的相对薄弱反而促成了90年代以来《无》研究的 突飞猛进,既有微观的作品分析,又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不 少填补空白之作。
1998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陈思和的论文《试论<无名书>》,这代表了《无》 研究起步期最有影响的成果。陈思和指出《无》的意义:远在一般以启蒙为宗旨的探索 之上,是“文学史上的一座火山”,是一部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河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别具一格的探索。还分析了《无》多年来备受冷落的原因:“西方 浪漫主义只有被改造成抒情传统才能在中国得以传播,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正好成为这种 改造的润滑剂,而《无》从夏多勃利昂式的感伤向浮士德式的探索的过渡,则注定了它 的寂寞与失宠”。陈思和是大陆最早关注无名氏的学者之一,又和无名氏素有私交,加 上深厚的学养,分析自然是处处真知、发人深思。
关于《无》主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形而上特点,研究者们的思路一般都 集中在对人生意义的精神探寻上,只是表述的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刘玉凯[16]、王 冰[17]等人认为无名氏小说的主题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郑春[18]在认同该观点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精神探寻是整个40年代小说创作的突出主题;赵凌河[19]认为生 命意识是无名氏作品的一个共同的主题,而大海又是这一生命的载体和意象;黄永成[2 0]认为,一代知识分子对生命的探索,对信仰的追求及其重建现代文明的理想,是无名 氏小说创作悉心表达的主题……不同阐释表达的意思其实都差不多。显然,在《无》广 阔的主题意蕴上,研究者的思路还没有完全打开。
《无》的文体特征一向都是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早在80年代就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无》缺乏节制的情绪宣泄,造成了文字上的拖沓空泛,影响读者的接受。只是到了90年 代后期,耿传明把它称为“巴洛克”风格,陈思和把它定义为“火山型的语言”——意 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细致地指出了《无》特色文体的表现形式。 汪应果进而分析了造成这种满得要溢出来的文体的原因:现实内容和作家的超现实思考 没有结合得天衣无缝,汪洋恣肆的思想之流往往大于文学形象。
《无》研究是近年来无名氏研究中成果出得最多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无》由于内 容晦涩、意象繁杂、语言欧化、可读性不强,尚未引起世人的足够重视。研究也多数集 中在大而全的宏观层面,微观细化的研究比较薄弱。
三、研究反思
9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在上述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在最大程度上得 益于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一方面,很多研究者转换研究视角、另辟蹊径,提出一些很有新意的观点,对以后的 研究有诱发引导的功用。
陈思和从“潜在写作”角度发掘《无》表现当代文学艺术生命力和知识分子精神追求 的意义,选择《无》作为“对时代共名持独立态度的创作”的一份特殊病例,说明“当 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发出声音的权利的时候,他能否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追 求一份超越现实意义的专业价值”。
刘志荣的观点也比较有开创意义:《无》的精神内核在于对中国现代焦虑的出色把握 ,这种现代焦虑包括个体生命的焦虑、世界性的疯狂混乱与民族精神的危机三个紧密联 系的层面,现代焦虑既是《无名书》铺张放纵的文体背后的怪异的激情的来源,也产生 了《无名书》特有的叙述逻辑,即通过主人公印蒂的经历,揭示中国现代焦虑之深重, 同时也企图从中国思想的核心出发对之进行精神超越。不过,因为产生于这一焦虑的背 景,《无名书》自身也带有现代焦虑的强烈印记。[21]
此外,耿传明[22]独树一帜地分析无名氏小说的“黑夜情调”;何莲芳[7]着眼于小说 的叙事特征,提出无名氏创作叙事模式具有复调特征的观点;李俏梅[23]论述无名氏小 说的美学格调——极端色彩与冲突之美,虽不全面但不乏新意;吴道毅[24]从小说的传 奇性角度,指出“传奇”审美旨趣的现代品格——与现代哲理的遇合、向俗众趣味的倾 斜,并分析了它的成因——浪漫主义的艺术主张、对外国传奇作家创作经验的接受、中 国古代传奇审美精神的熏染;等等。
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者用比较研究、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心理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对 无名氏的创作进行重新解读。
用的最多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无名氏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比较研究 的范围空前广泛。近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在把他与徐訏、张爱玲进行比较,视野空前 拓展:有的把《无名书》和但丁的《神曲》、夏多勃利昂的《阿达拉》、歌德的《浮士 德》进行比较;有的把无名氏的散文和何其芳的散文比较;有的把无名氏出奔北京的心 路历程和丁玲、沈从文相比,既带有对新文化的憧憬,又带有人生冒险的赌博性质……
有研究者将这几年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引入无名氏的研究,汪凌[25]以女性解读 者的身份重新观照无名氏的小说,指出他小说作品中突出存在的“物化”倾向:小说中 随处可见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轻视和玩弄——男性的傲慢、传统士人的风流趣味、个人主 义者的自私,他们对美人可以赞美、欣赏,却始终不过是在“玩赏”的层面上,一旦论 到责任、道义,便退避三舍,这直接导致了男权文化中的女性难以逃脱的悲剧性命运。
心理分析也是文学研究常用的手法之一。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耿传明,他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作家的早年经历对今后文学活动产生的影响,如从“无名氏童年母爱的 缺失”、“对爱的强烈向往”中寻求无名氏“专注于爱情描写”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名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贡献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肯 定,无名氏研究也走出了“左”倾思想的拘囿,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逐 步由狭窄走向开阔,表现出起点较高、发展稳定的良性态势。但无名氏创作是一个相当 复杂的现象,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只能说还刚刚起步,有很多问题上值得我们深思,其丰 富内容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开掘。
第一、无名氏研究在90年代真正走出沉寂,但此时已不单纯是一个学术课题了,它作 为一种带有时代印记的文化现象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意义。
和张爱玲研究一样,大陆学术界对无名氏的关注最初起源于海外学人对无名氏的肯定( 如香港的司马长风和美国的夏志清),加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一批“边缘化” 的作家被发掘出来,无名氏很自然地被列入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成果也很值得关 注。可以说,是时代对文学多元化的要求促成了无名氏的“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很多人的兴趣却由文本解读转向了无名氏传奇的一生。相对于晦 涩难懂的《无》,他曲折的一生似乎更符合大众的趣味。无名氏是一个“谜”:40年代 在沦陷区,他一夕成名、红极一时,接着又神龙见首不见尾地沉寂了半个世纪,以致有 人猜想他是不是在哪儿出了家,到了1982年,他突然出走香港,随后移居台湾,再次造 成轰动;他一生有无数次的罗曼史,从李彦文、闵泳珠、赵无华,到刘菁、西湖女,再 到小他41岁的马福美,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与此相回应,从1998年到2001年的短短三年内,就有三部无名氏传记先后出炉,散见 的关于无名氏生平、爱恋的介绍更是数不胜数。它们学术含量的高低我们暂且不论,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满足了读者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猎奇心理。这其实是一种学术上的媚俗 倾向,对专业领域的进一步挖掘有害无利。
第二、无名氏研究在经历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却走入另一个怪圈:对无名 氏其人其作评价偏高,甚至人为地拔高无名氏的艺术成就,耿传明在《独行人踪:无名 氏传》中就声称“无名氏堪与巴金、沈从文比肩”,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还有很多研 究者在评述无名氏的创作时对作品的缺点忽略不计,似乎生怕一批评就被认为又是“左 ”的思想作祟、走了回头路。可是事实上,无名氏的创作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比如感 情的不加节制、巧合情节的过多使用、艺术形象的选择过于依赖生活原型,等等。对于 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这种潜在的“只说优点 不提缺点”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批评的客观公正,也影响了研究的百花齐放。
第三、作为一个浮出海面不久的作家,有关无名氏的研究不可能做到深入、系统。一 个很自然的现象——研究者们大多只注重对焦点问题的研究,对无名氏的其他小说、散 文(如《崩溃》)、随笔、自传(如《绿色的回声》)、散文诗,杂文(如《谈情》、《说 爱》)研究很少,有的基本没人涉及,忽略了它们相互之间具有的题材、主题承续性, 对无名氏佚文的搜集和打捞工作也很不够,这就使我们很难把握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无名 氏,也很难深度诠释无名氏由前期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说到后期晦涩难解的“生命大书” 其间经历的艺术转化。象邹志仁[26]这样从无名氏早期的三篇朝鲜题材小说出发分析它 们相互之间具有题材、主题承续性的文章还是很欠缺,把无名氏的所有创作理出“一条 思想的红线”的工作还有待以后进一步的加强。
这其实也反映了近十几年来无名氏研究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很多研究者力图通过 剖析单部作品、单个现象挖掘出新的东西,开的口子越来越小,整体性研究严重不足。 例如,无名氏受西方文化和宗教影响很深,宗教在《无》的主题阐释中也有其特殊意义 ,但却少有论述,这其实是“中国现代作家和宗教关系”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有人涉及,如谭桂林的《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7],但对无名氏多 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现在所能见到的这方面的研究只有一两篇发表在师专学报上的简 单分析。甚至在同一部作品、同一个人物形象的研究中,也常常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以《无》为例,印蒂的研究很多,而印蒂的爸爸印修静这一“精神之父”的重要形象被 一再忽略,《海艳》研究的人比较多,而无名氏整部书最满意的《金色的蛇夜》却少有 人涉及。这种研究着力极度不均的状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无名氏研究进一步的突破。
收稿日期:2004-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