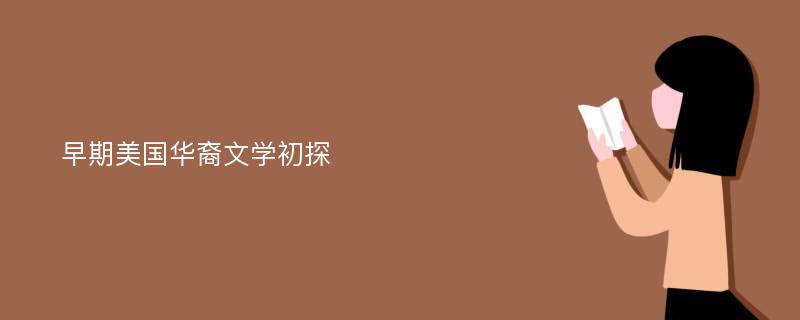
董美含[1]2011年在《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的世界文坛,常常在许多批评家眼中被视为“一场奇幻的文学盛宴”。从90年代初至21世纪前10年,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也迅速增长,从此美国华裔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汤亭亭(《第五和平之书》)、谭恩美(《拯救落水鱼》)的新作,带领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开启更多元化的创作尝试。90年代后登上文坛的美国华裔文学新人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发表作品时年龄在叁十岁上下,且多为女作家。新涌现的作家,如任璧莲等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其他新一代华裔女性作家写作的个性化也趋于鲜明,其主体自我意识更强。不论小说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是关于美国的华裔故事,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注重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根本性的主题是精神家园。换而言之,不论是哪一种叙事策略,都昭示了华裔女性群体对自我存在进行的深刻反思,她们也由此走出了族群的身份限定,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因此本文拟以邝丽莎、张岚,以及大胆突破伦理底线的第叁代美国华裔作家黄锦莲和伍美琴为研究对象,从探寻华裔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出发,挖掘90年代后,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张龙海, 张武[2]2017年在《新世纪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势头更为汹涌,在研究队伍、研究范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诸如"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两支研究队伍各自为政"等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回顾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渊源,然后理性分析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
盖建平[3]2010年在《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文中指出以中美学界早期美华文学研究既存成果的梳理与当代命题的提出为导论,本文的四章正文分别对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的四部代表作品《金山篇》、《逐客篇》、《苦社会》、“木屋诗”展开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阐析与跨学科研究。本文打破美国华人史及排华史研究与中国侨乡文史研究之间原有的学科界线,在相关各类文史资料充分储备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学文本对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特定书写形态,同时阐发文学与既存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文学的场域中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间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经历予以重新观照。贯穿本文正文四章的基本命题,乃是对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文史互证,以及对早期美国华人形象的正面呈现。本文对美国排华主义言论中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几个基本观点[“流民苦力”说(coolie)、“客民”说(sojourner)、“唯利是图”说(gold-digger)、“文盲”说(illiterate)等]予以引入中国学界侨乡文史研究成果的正面解构,由此实现文学研究之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从而阐发以华语写成的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近代时期华人赴美跨国生存经验记录的文学价值。第一章从美华文学开篇之作《金山篇》的艺术风格分析入手,从中“发现”早期美华文学不同于既存美华历史叙事的对近代华人赴美动机的感性呈现,进而导向对中国唐宋以降的出洋传统的认知、对近代华人的美国观的重新认识,并最终解构既存历史叙事中“晚清赴美华人多为贫苦流民”的基本定调。这首长诗创作于美国排华初露端倪的时期,作者张维屏作为中国侨乡的先进知识分子,运用五行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黄金的诸多典故来推想华人在美国的未来。《金山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乐观、期待、向往美国的情绪,体现出“站在侨乡看美国”的特定视角,因而具有广泛而特殊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金山篇》未能指出当时华人在“金山”遭遇的歧视性赋税本质上源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然而,此诗折射出的当年出洋者近乎盲目又自圆其说的乐观态度,应当被视为19世纪中期以来华人不断赴美的一种精神动力。第二章研究美国《排华法案》1882年出台之后的及时之作《逐客篇》,结合作者黄遵宪领先的西学修养、干练外交才华,分析《逐客篇》对美国排华运动来龙去脉的特定表述。本文认为,《逐客篇》贯注着近代中国一位优秀外交官所特具的现实经验与务实眼光。在排华成为美国全民性政治社会运动的特定时代语境下,黄遵宪将早期华人在美国“安居乐业”的“当初”与眼前的现状相对照,其中加入了黄遵宪对《排华法案》的种族主义性质的系统认知。在对《逐客篇》所特具的时代性的解读中,本文植入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欧风美雨的文化变迁背景,主张:正是亲身介入美国排华现实的政治经验,促成了黄遵宪对当时中国进步士人热心西学时所怀的“大同”理想的正面反思。另外,在痛陈华人在美的可悲遭遇时,黄遵宪以美国黑奴作为对照,来突出华人强烈的耻辱之感,这又透露出诗人受到西方种族主义观念沾染的痕迹。由是,晚清近代中国文明转型期“新”“旧”观念驳杂的时代风貌亦得以随之呈现。第叁章从《苦社会》与国内同时期“谴责小说”的比较入手,呈示这部小说跨国书写的别异之处,进而平行参考国内学界对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发掘至20世纪初期为止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丰厚积累,最终得以辨识“美国华人”这一跨国文化身份的最初成形过程。在《苦社会》的文学叙事中,超脱于世俗物欲争斗的伦理诉求与反击排华的现实立场始终隐然并行,这一特定的观念状态与第一、二章所研究的《金山篇》、《逐客篇》对所处时代的观察评说一起,共同构成了早期美国华人跨国生存状态的多个面相。早期美华族群强烈的道德意识与亲情观念,亦在相关的移民观念变迁的框架下得以充分披露。第四章对当代美华学界蔚为显学的“木屋诗”即天使岛诗歌研究予以细化梳理,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内容及形式的文史整合,追溯20世纪前半叶被拘禁于美国旧金山海关候审所“木屋”中的华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从而展现富于感性与个性的早期美国华人形象。本文主张,在衣食不周的囚居困境中,木屋华人除了对自身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出愤怒的抗辨,还依然秉有优美的情感、自尊的气质、开阔的心灵、彼此的关切。如上种种感性力量,皆为早期美华移民群体对抗生存绝境的精神资源。本文将这一特殊创作形态的文学传统追溯到中国唐代的梵志诗,对木屋诗作为古代民间诗歌跨国延伸的文学特质予以比较阐发。最后,参照中国历代《诗经》读法,本文论述了读解《木屋诗》以及对整个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予以深度研究的当代现实社会文化价值。经由正文四章对早期美华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本文将结论落于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主题发展脉络与当代价值的重新描绘。面向美国学界,本文正面讨论了为美国排华话语这一“语言的铁幕”遮蔽的“未名之物”,指出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正面感性形象的要点所在;面向中国学界,则是实践以早期美华文学研究为平台的跨学科文本细读,展现早期美华文学阐释与美华历史重写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而对文学研究、文本读解的既定范式予以突破,并最终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当代中美两国可以共享的文化遗产的丰厚内蕴,以及促进两国文化界反思历史、沟通对话的“桥梁”特质。
徐刚[4]2016年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具有丰富的阐释性,因为文学不仅仅是表意的符号,而且还是一种具有文化、政治和性别诉求等蕴涵的话语。因而作家采用不同写作策略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再现生活﹑反思自身以及表达诉求等功能。然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又使其不同于政治﹑经济等其它话语体系而具有独特之处。因此,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应只关注内容而忽视其形式;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应该坚持从形式到内容逐步深入的路径,而不是抛开作品的文学性而单纯地探究其社会功能。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其丰富的蕴含而沦为没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历史文献式的记录或评说。事实上,作品的文学审美与其社会功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文学话语的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对作品形成既全面且又具有深度的阐释。此外,任何文学创作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因此,文学创作的话语形式和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其兴起与发展都与美国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与变化密切相关。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里,争取话语权对于少数族裔群体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获得言说和表达的机会,其诉求才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在不同社会语境下采取的不同写作策略,实际上都是华裔作家为了表达其特定的话语诉求。基于华裔族群在美国社会历史的生活境况的变化及其应对心态,影响华裔美国文学话语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可分为叁大类,即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女权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主要以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抵抗话语来反击种族主义对华裔族群的压迫及其对华裔历史的扭曲。因此,这一时期华裔作家的作品大都采用具有解构意义的华裔族群“小历史”叙事﹑“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反西方传统小说文类的变异等写作策略来彰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朱路易(Louis Chou)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79)和徐忠雄(Shawn Hsu Wong)的《家园》(Homebase,1991)中,两位华裔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华裔家族变迁的“小叙事”来揭示整个华裔族群的真实历史,以此来解构美国主流社会霸权话语书写下所谓的“大历史”对美国华裔历史和生活现状的遮蔽;而赵健秀在其作品集《“鸡笼中国佬”和“龙年”》(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Dragon,1981)中则通过塑造华裔“愤怒青年”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抗种族歧视,颠覆西方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印象。此外,美国华裔作家劳伦斯·于(Laurence Yep)的《龙翼》(Dragonwings,1975)和赵健秀的《唐老亚》(Donald Duk,1991)一反西方传统成长小说的文类风格,彰显出华裔儿童在充满种族偏见的美国主流社会中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轨迹,从而揭示出种族歧视对儿童成长的危害性,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超越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所持的美好愿望。随着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因而这一时期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权益诉求的特征。受女权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影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双重抵抗的话语特点,即其文学话语同时反抗男权制和种族主义两大枷锁对华裔女性的束缚。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2006)和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通过叙事声音的复调性以及对“中国元素”的运用来展现华裔母女两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解,从而生动地表达出华裔女性群体的心声,展现出她们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文化抉择的困惑与觉醒。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苏珊·兰瑟(Susan Lance)认为,女性作家的独特写作策略不是由女性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规约决定的。所以,女性叙事话语形式的选择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美国政府提出了文化多元的口号,但白人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群体之间享有话语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却仍然在继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少数族裔作家若要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并非易事。有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作出一些妥协或采用一些迂回的写作策略来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学审查机制,因而华裔美国文学中显现出的多样化女性叙事话语策略可以反映出华裔族群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其特定的文化权益诉求。此外,“中国元素”一直是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一点在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通常是以华裔母女之间讲述中国故事的形式而呈现给读者的。这些中国故事往往蕴含隽永,具有反映华裔女性的性别及文化身份诉求的独特话语功能。但与此同时,其话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制约,因而“中国故事”在作品中通常会表现出西方话语政治的无形影响。因此,通过对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中国故事这一独特话语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学术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主旨及其作品背后潜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促使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更为广泛的多元化文化诉求特征,因而华裔美国文学也出现了越界与回归、离散与建构等“多声部”话语共存的现象。如伍慧明(Fae Myenne Ng)在《骨》(Bone,2004)这部小说中的华裔历史与现实创伤书写﹑任碧莲(Gish Jen)的《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2)和《应许之乡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等作品中的身份认同和创伤叙事以及伍邝美(Ng,Mei)在《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中的华裔女性现代创伤叙事;赵健秀(Frank Chin)的《甘加丁之路》(Gung Din Highway,2004)和汤婷婷的《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1998)两部作品后现代话语的狂欢嬉戏对美国霸权话语的挑战;汤婷婷和谭恩美两位作家的新作《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2003)和《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6)中超越族裔性的普世主义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对西方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而进行的审视与剖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叙事”也呈现出不同的蕴含。有些作品出于商业目的,利用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华丽展示以博取西方读者猎奇的眼球,有的则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以夸大扭曲的形式予以呈现,以此来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的手段。当然,其中也不乏对现实中国的真实呈现。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方面,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自我东方主义“中国叙事”书写仍然在继续;另一方面,汲取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彰显华裔族群文化独特性以及超越族裔性的普世主义关怀的文学创作也欣欣向荣。因此,为维护自身族群权益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对超越族裔身份羁绊的美好愿望、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关注以及迎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国叙事”,构成了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多声部”话语,其中蕴含着当代华裔作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政治和文化诉求。华裔美国文学伴随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其话语形式经历了持续的演进过程。从总体来看,其最终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争取言说的机会,并力求在美国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文学作品获得广泛认可的重要标志就是成为文学经典,而华裔美国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要面临来自西方传统文学经典以及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通过分析西方传统文学经典建立的标准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因素,有利于看清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边缘书写”的话语局限性及其健康发展的方向。尼采的美学思想以其酒神精神为核心,并贯穿着他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等主要哲学思想,对当代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因此,尼采美学思想对华裔美国文学反抗所谓的西方正典,建构自身文学审美及其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以“彩虹联盟”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对差异尊重的思想以及建构具有多样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的主张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和阶级等级的价值观,摒弃狭隘的西方文学正典观。在一定程度上,“彩虹联盟”的主张有助于回归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那些在讨论经典时经常被忽视的东西,如文学作品的风格﹑愉悦作用以及启蒙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审美特质。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其表现形态应该是“诗的思想”,即文学话语普世价值观的诗意表达。因此,华裔美国文学要进入经典之列,除了需要摆脱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以外,还需要致力于人类共识普遍价值的诗意体现。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文学经典,但是纵观世界文学的发展,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常常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超越国界”的普世人文关怀,因而成为文学经典评价原则不断演进中的永恒原则。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直接影响着华裔美国文学话语的表达。因此,通过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文学作品在社会、历史和心理层面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出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的特点及其在争取华裔族群话语权和建构全球性的“彩虹文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话语形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更好地阐释华裔作家作品中文学话语的深层内涵,以彰显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于深入了解美国华裔作家独特的写作策略、了解华裔美国文学类型的演化及其文学创作过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建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批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华裔文学话语从边缘迈向经典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华裔美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詹乔[5]2007年在《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文中提出本文以史为线索,以美国主流社会中流传的中国套话为参照,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梳理,进而分析了其产生的政治、历史原因,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区别于美国白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包含了“局内人”眼光的,华裔“自塑形象”和“异国形象”的混合体,有鉴于作家个人经历和写作时代背景的差异大致呈现出四种类型:早期华裔作家在西方文明参照下的“现实中国图景”和“文化乌托邦”,第二代华裔作家刻画的“父权制中国/华人社会”和神话寓言中的“虚幻中国的乌托邦”。从这些富含差异性和流变性的中国形象中折射出来的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也呈多元、流动、开放的形态,从一个侧面反驳了华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本质主义身份观,同时也应和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多元文化身份观和离散身份观。这项研究对于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性的离散文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蒲若茜[6]2005年在《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文中研究表明通观华裔美国小说的主题内容,“唐人街”、“母与女”、“父与子”等典型母题得到了反复的、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这些母题蕴含了华裔美国人特殊的离散、迁徙的族裔经验,是中国和美国文化传统合力作用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而特殊的文化人类学内涵,是我们给华裔美国文学定性的重要依据。本论文在华裔美国历史、文化和族裔心理的观照下,利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文化批评理论,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理论工具,通过对以上叁个典型母题的剖析,对华裔美国文学特有的族裔经验的书写,混合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想像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展示,突破了研究者内部的歧见,从而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本文根据作品的具体形态和历史动态的研究表明,由于作家的个人经历、性别、社会地位的不同,母题表述也不尽相同;而且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随着中美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同一个母题呈现也产生了变异,而这些变异,不仅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内部的殖民话语关系重大,而且对我们在当下“全球化”语境应该采取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连欢[7]2004年在《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初探》文中认为美国华人移民及其后裔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集中体现融合与抵斥并存之矛盾的群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既有文化的合流,又从不缺乏因撞击引起的种种问题与困扰。作为美国多元文化和世界移民现象重要产物的美国华裔文学在当代正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亚裔学者金依莲指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文学意义,整体而言,它还兼顾了社会综述功能,更具有历史文献的重要价值。对于当代评论家来说,拥有详尽、准确的史料是解读文本、进行作品分析的一块基石;而对于当代读者而言,了解作者、文本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激发阅读兴趣,有助于免除不必要的误读和误解。 本篇论文旨在对早期暨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华裔生活和他们的文学作品,及此两者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做一番较为仔细的梳理。以期用翔实可考的资料与分析丰富至此为止关于美国华裔文学早期阶段的研究。本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主要是历史考察和社会背景分析,因为这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出现和存在的前提。第二章在时间跨度上包括了美国排华法案正式实施的60年(1882-1943)。第叁章内容的时间跨度为1943年到60年代中期。全文主要从时间及历史事件的发展上理清脉络,在纵向上整体把握线索的同时做好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细分整理与文学作品分析。
李悦[8]2013年在《走出族裔性创作篱笆: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浓厚的族裔意识和权利诉求,已经成为这—文学的显着特征。肇始至八十年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在创作上呈现出浓厚的文化、政治色彩。族裔的身份和政治性主题几乎是所有这一时期的华裔女性作家的共同诉求。长期以来,在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中,文化民族性和族裔政治性方面的分析占据了研究的主导地位,而该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意识和审美艺术研究则相对薄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新一代的华裔女性作家,更加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其主体自我意识更强,不论小说内容是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是关于美国的华裔故事,关注的重点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注重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根本性的主题是精神家园。不论是哪一种叙事策略,都昭示了华裔女性群体对自我存在进行的深刻反思,她们也由此走出了族群的身份限定,超越了一定的政治思维模式。由此,在近五年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将其研究点落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如张琼、杨春、陆薇等)。他们试图从探寻华裔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出发,这时,他们也往往弱化了为华裔文学本身的族裔属性。其实,既然被称作华裔文学,不论如何冲淡族裔性,族裔仍是一张标签,只不过以往过于放大这种标签的价值为了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而在作者本身创作中或是研究者的分析解读中,把创作的个性化意识和审美艺术功能则相对淡化了。实际上,作为华裔文学,族裔性与个性化、政治性与审美性都不应当成为互相牵绊,此消彼长的存在模式,应当是二元融合、相辅相成的。本论文重点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几部代表作品,对其叙述风格、叙事技巧、象征意义、语言修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析,试图将族裔性与个性化、政治性与审美性相结合,探讨新时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方向,即走出族裔性创作的篱笆,将族裔性意识与个性化的文学审美价值相融合,使二者和谐共存。透过对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种文化、族裔性与个性化、政治性与审美性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所纠结和困惑的问题。显然,新一代的美国华裔小说中仍然有不少“中国故事”,不过,这些“中国故事”和以往已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小说中,中国已经不再是衬托美国之“甜”的“忆苦”对象,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想象创作空间,成为人间故事发生的大舞台。而且,不论是文化上的混血,还是血统上的混血,新一代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身份的复杂性,标志着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属于“双重混血”,和谐发展的艺术创作时代。
项丽丽, 刘增美[9]2009年在《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思考》文中指出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李丽华[10]2011年在《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观华裔美国文学,不仅大批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多视角、深入地透过性别议题揭示美国种族主义歧视下华裔男女的命运,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也几乎发轫于对性别主题的探究。现有国内外研究对华裔美国文学丰富的性别文化叙事展开了不少探索,有力地揭示了华裔在美国遭遇的性别与种族相互纠缠的压迫。但在体现华裔美国文学如何走出二元对立的性别范畴,走出压迫视角,追寻性别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的柔韧性和可变性等方面留下了不少空间。本文以黄哲伦的《蝴蝶君》,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和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为例,围绕性别理论叁个核心概念,在一个与族裔相互交织的系统中考察生物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的相互关系和多元流动特征可能带来的理论提升和社会转化意义,并让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与心理分析,文化,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交叉起来,批判性地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呈现文本中性与性别多彩斑斓的万花筒特征。全文包括七个部分。绪论主要对本研究涉及的问题与方法,概念与定义进行了澄清与阐释,以厘清研究的意义和思路。第一章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材料选取等几个方面对比中美相关研究,以发现本论文的逻辑所在。第二章以华裔美国文学界的赵-汤之争为起点,通过考察各族裔中的类似论战,一方面突显其穿越各族裔的普遍性特征,彰显性别义涵,另一方面,通过突显被推向女作家阵营的男性作家,跳出二元对立的男女之争,将性别复杂化。第叁章回顾了多个与《蝴蝶君》具有互文效应的殖民时期作品及蝴蝶意涵,体现性别文化的非线性特征,尤其是《蝴蝶君》中,不在场的“女性身体实在”也超越了生理性别成为“东方完美女人”,打破了父权规范下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连续性特征。第四章试图较为完整地解读《甘加丁之路》的进步性和多重矛盾性。小说透过六个被铭刻的时间呈现了男主人公的族裔化性别历程,作家还以相当积极的方式展现打破乱伦禁忌对白人律法的挑战。但作家通过突显华裔男性内在的,无比强大的性冲动重建华裔男性形象的努力充满了矛盾和局限。第五章立足于人类生活高度依赖的时间、空间和意义之叁维,诠释作家在《第五和平书》中所呈现的和谐平等性别关系的生成土壤和发生机制——一个以多元和平为总体社会文化动力,外在于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全球化语境的断裂之地。以此,惠特曼超越特定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出离给定的各种男性形象,并践行着别样的政治诉求,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男性气质。结束语体现全球化语境下,此叁部文学文本呈现的差异、多元可塑的性/别在不同层面具有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 董美含. 吉林大学. 2011
[2]. 新世纪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J]. 张龙海, 张武. 社会科学研究. 2017
[3]. 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D]. 盖建平. 复旦大学. 2010
[4].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D]. 徐刚. 吉林大学. 2016
[5]. 论华裔美国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D]. 詹乔. 暨南大学. 2007
[6].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D]. 蒲若茜. 暨南大学. 2005
[7]. 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初探[D]. 连欢.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8]. 走出族裔性创作篱笆: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 李悦.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9].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思考[J]. 项丽丽, 刘增美. 东岳论丛. 2009
[10]. 华裔美国文学的性与性别研究[D]. 李丽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标签:世界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华裔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蝴蝶君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