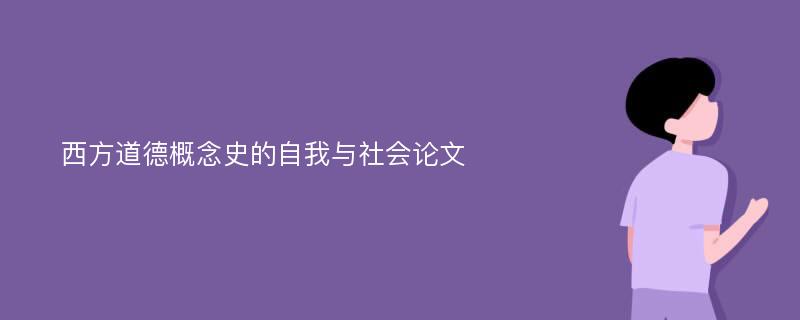
·专题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学术主持人:王志民)
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与社会*
陈 来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4 )
摘要: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公民道德的概念,那么边沁则建立了私人伦理的概念。休谟区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隐含着个人之德与社会之德的区别。康德也讲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只是后者并无涉及公德。密尔建立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两个概念。涂尔干则把每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定义为个体道德,与自身之外的关系的道德分为若干层次;以公德私德来看,个体道德属私德,而公德范围则很广。斯洛特的道德观指出,关乎他人的德性比关乎自己的德性更重要,二者之间并不对称;他认为私德多属于非道德的德性。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风俗改革运动中的条目规定,意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规范。中国古代不能说只重私德轻公德,古代社会公德在礼的体系中,此部分可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公德。
关键词: 西方道德概念;伦理;公德;私德
近代以来,有关公德—私德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伦理的主要论题之一。西方道德概念对自我与社会的分析,构成了近代东亚社会公德和私德讨论的概念基础。梳理西方道德概念史上亚里士多德、边沁、休谟、康德、密尔等思想家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观点,附带考察近代日本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的观念和社会规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伦理中公德—私德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与西方比较可见,中华文化并非重私德轻公德,而是需要发展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精神。
一、亚里士多德论“公民品德”与“善人品德”
古希腊城邦林立,城邦规模一般都不大,故个人与城邦国家的关系可以较为直接,这就是个人作为城邦国家的“公民”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公民的要求。城邦对公民行为的要求可以说即是公民道德。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什么是公民,犹如什么是城邦一样,在当时时常引起争辩,但没有公认的定义。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民的性质如下:“(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6-117页。
城邦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可见,城邦不是血缘共同体,也不是宗教组织,公民和城邦的关系是其作为政治团体的成员与政治团体的关系。在阐明了公民与城邦的定义和关系之后,亚里士多德进入了如下问题的探讨:
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该求之于政制]密切相关的下一问题为:善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但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行说明公民品德的一些概念。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每一良水手所应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他所司的职分而各不相同。但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职品德的各别定义外,显然,还须有适合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倘使政体有几个不同的种类,则公民的品德也得有几个不同的种类,所以好公民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但善人却是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于是,很明显,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3-124页。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概念,即“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他认为二者是不同的。好公民和好人是不同的道德概念,好公民必定是具体的,特定政治体系的成员资格,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好人则是普遍概念,超越不同的政治体系的差异,单纯指向人格与品质的高尚良善。善人或好人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说的君子。
面对困难,小小的蚂蚁尚且能坚韧不拔,努力克服,而我在学习中,只遇到一点点难题,就选择逃避问题而没有迎难而上。和它相比,我真是自愧不如。我要向小蚂蚁学习,在学习生活上,勇敢进取,奋力拼搏!(指导老师:钟华奇)
所谓公民道德,就是超出其个人职业所司所应符合的社会集体的要求,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共同地符合其所属的政治体系的要求。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的城邦,对公民的政治要求不同,故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公民道德要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国家政治体系不同,故公民道德是分殊的,不是普遍的。相比而言,“善人”的道德则是无分于国家体制的,是普遍的,是“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好公民的品德仅仅是被要求符合于他所在的国家,是不会具备善人的品德的,也就是说还达不到善人的品德。可见,善人的品德高于公民的品德,但国家只要求公民具备公民品德,只要求符合好公民的要求。亚里士多德在此提出的正是公民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区别问题。亚里士多德说:
倘使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人组成,而每一公民又各自希望他能好好的克尽职分,要是不同的职分须有不同的善德,那么所有公民的职分和品德既不是完全相同,好公民的品德就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但我们如果不另加规定,要求这个理想城邦中的好公民也必须个个都是善人,则所有的好公民总是不可能而且也无须全都具备善人的品德。(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4页。
针对农商行发展现状和纪检监察部门履职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履职能,营建良好的廉政环境和经营秩序,推动农商行健康、快速发展,建议如下。
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并不全然相同”。然而,他也强调另一点,即统治者和政治家应为善人,统治者的训练应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教育,统治者的品德有别于一般被统治公民的品德,统治者的品德应相同于善人的品德。(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5页。
这里我们再讨论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他在《政治学》中,把他在《伦理学》中的论点概括为“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这里是以定义“幸福”的形式出现的,即幸福是善行和善德的统一。德是内在的德性,故其完全实现即是幸福;善的行为若仅见诸于一两件小事是不够的,须达到极致才是幸福。他还指出,最高的善是“凡由己(出于本然)的善行”,并认为:“一个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绝对的善,当他发扬其内在的善德时,一定能明白昭示其所善具有的绝对的价值(品格)。”(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9-390页。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自由人,统治者要懂得统率、治理自由人,而自由人“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他还说“明智”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则为“信从”,也就是说服从是公民道德的核心。
以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一般结论,但他也指出一个例外,“惟有理想城邦而其所拟政制又属轮番为治的体系,其中公民必须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人人都要具备四善德:在这里好公民便同于善人”(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7页。 。每个公民都要准备参与轮流做统治者,故其教育要以此为目标。“在轮番为治的理想城邦中好公民的道德符合于善人的道德;这里的公民教育也就应该等同于善人的教育,而使之包含众德。”(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2页。 这里指的是卷三四章后部所提及的情形,并没有普遍性。
古代中国文化一向有善人的道德标准,称之为君子之德,并以此为普遍道德标准,而没有出现过公民品德或相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公民道德和善人品德的区分,以及他的观点,对近代以来公德和私德的讨论,对现代社会偏重公民品德、忽视善人品德,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忽略善人品德,只注重公民道德,正是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边沁论“私人伦理”与“自己的完善”
边沁(1748—1832)主张,整个伦理可以定义为一种艺术,指导人的行为,以产生最大的幸福。一方面,艺术即一种技术、方法;另一方面,此艺术即指行为的管理艺术。总之,伦理学是指导人的行为的管理艺术,而其中又有两种基本分别:
那么,在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所指导的是什么行为?它们必定要么是他自己的行为,要么是其他载体的行为。伦理,在它是指导个人自身行动的艺术的限度内,可以称作自理艺术 ,或曰私人伦理 。(8)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8页。
Private ethics 是指导人对自己的行为,是私人伦理,那么指导人对他人的行为则为公共伦理。(9)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9页。 他认为,作为一般伦理的管理艺术分为两类,“这艺术在本身据以表现的措施具备持久性的限度内,一般用立法 这一名称来表示,而在它们是暂时性的、凭当时事态决定的情况下,则用行政 来表示”(10)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9页(文中加点处为原著中标注,下同)。 。他又认为,管理艺术就其指导未成年人行为的范围,可称为教育艺术,其中有两方面,一个是“私人教育艺术”,一个是“公共教育艺术”,这是就履行指导职责的主体而划分的。反推上去,他应该认为有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以对应这两种教育艺术,但他并没有明确加以阐明。
那么,什么是私人伦理、一般伦理?私人和公共的对立在什么地方适用?
治疗后,观察组舒张压、收缩压分别为(80.9±4.6)mm Hg、(121.4±4.9)mm Hg;对照组分别为(95.9±3.9)mm Hg、(1371.4±5.5)mm Hg。两组舒张压与收缩压差异显著(P<0.05)。
说到一般伦理,一个人的幸福将首先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仅他本人与之有利害关系的部分,其次取决于其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幸福的部分。在他的幸福取决于他前一部分行为的限度内,这幸福被说成是取决于他对自己的义务 。于是,伦理就它是指导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行为的艺术而言,可以叫做履行一个人对自己的义务的艺术。……要是他的幸福以及其他任何利益相关者的幸福,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利益的部分,那么在此限度内这幸福可说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义务 。(11)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50页。
企业要想更好的控制和防范风险的发生,必须加大内部控制活动的执行力度。例如:企业应该明确岗位职责、建立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和授权审批制度,对会计系统实施控制、对财产进行保护控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可见,一般伦理既包括私人伦理,也包括公共伦理,这是两种义务。仅与本人有关者为私人伦理,履行此种义务的品质如慎重。可能影响他人者为公共伦理,履行此种义务的品质如慈善。边沁又称公共的伦理为立法的艺术。对自己的义务的艺术就是私人伦理,而对别人的义务的艺术就属于立法艺术。他说:
中国文化中是否有这种对两种道德的分疏?中国古代道德中哪些属于个人道德,哪些属于社会道德?或哪些是兼而有之?个人道德的概念比起边沁的私人伦理观念更切合私德的讨论,因为道德与伦理有别,同时他使用的个人—社会的区分,也比私人—公共的区分要更加合理。因为私字难免带给人一种价值非中立的意味。但社会道德是指公民道德还是公共道德,并不清楚。
立法是公共的,所以强调有利于共同体的幸福,而非个人幸福,此即近于公德之说。私人伦理是私德,立法艺术是公德。因此,公德应当是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德行。
一个人的行为仅与自身有关,是为私人的。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他人,就不属于私人的,但也不见得就直接对共同体有影响。一个人行为影响其他人的幸福,边沁认为有两种:一是消极的方式,即对其邻人或他人的幸福不减不损;一是积极的方式,即谋图增长之。与前者相应的品质是正直,与后者相应的品质是慈善。边沁把这两种都作为“一般伦理”,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某人对自己的义务如慎重属于私人伦理,那么他对他人的义务属于何种伦理?是否属于公共伦理?
总之,边沁试图区别一般伦理和私人伦理,其私人伦理有似于“私德”的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品德”有似于“公德”的概念一样。其一般伦理应包括私人伦理、他人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概念,但他没有真正说清楚公共伦理和对他人的义务的概念区别。其立法艺术有似于公共伦理,但也没有定义得很清楚。他更没有指出私人伦理的具体所指,使这个概念过于抽象和含混而不便实践。
中国古代有没有私人伦理的概念或类似物?中国文化中私人伦理包括哪些内容?这都值得研究。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公民道德的概念,那么可以说边沁建立了私人伦理的概念,这些是近代东亚社会公德和私德讨论的概念基础。而且边沁把“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加以区分,成为西方近代社会文化对公德和私德进行区分的分析基础。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要指出的,这一“对自己—对他人”的框架并不能成为私德、公德区分的合理基础。
三、休谟论个人之德与社会之德
休谟(1711—1776)的《人性论》的第三卷为“道德学”。休谟很重视德行问题,所以此卷的第一章是“德与恶总论”,认为道德的问题,根本上是善和恶的区别,是德性和恶行的区别问题。(13) [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1-512页。
1.2.5 白及无菌苗的生根培养 由于白及生根主要受NAA、赤霉酸(GA3)、番茄汁等因素的影响,为了研究白及无菌苗最佳生根培养条件,实验以1∕2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采用L9(34)正交试验方法探讨NAA、GA3、番茄汁等2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及1种天然复合物对白及无菌苗生根的影响,正交试验各因素及水平见表3。每种处理接种10瓶,每瓶接种2株5 cm左右的无根幼苗。接种后的培养瓶放置到光照培养室培养,培养30 d时记录实验结果。
休谟把道德的善和恶、德性和恶行的区别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德”,即通过自然感情建立的德性,如同情和仁慈;一类是“人为的德”,即通过人为设计建立的德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正义。通过人为设计而建立的德性是针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而言的,与之相反,通过自然情感而确立的德性则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自然的德”是对个人自己有用或令个人自己愉快的品质、性格和才能等。在休谟看来,属于这类德性的有伟大而豪迈的心灵品质、仁慈和仁爱的心理情感。“人为的德”以公共的和社会的有用性为标准,而“自然的德”以个人的和私人的有用性和愉快为标准。休谟对仁慈和正义作了不少比较性的论述,最后指出,仁慈主要是一种人格价值,它更昭示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正义则直接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相联系,着眼于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制度建设。(14) 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
在后来作为《人性论》第三卷改写的《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继续发展了这种分析。但与《人性论》第三卷不同的是,其重点已经从自然和人为的分别转向他人和个人的分别。在他看来,道德可以分为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四种。(15) [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3-120页。 这四种其实是两种,即对他人有用、令他人愉快和对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实际上是把“对他人”和“对自己”作为道德的基本分际。而且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更加强调了《人性论》中“社会之德”(社会性的德性)的概念,认为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中都有社会性的德性、公共的有用性。自然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相对他人而言。
对自己有用的品质,有审慎、进取、勤奋、刻苦、俭省、节约、节制、明辨等,这些可归入个人品质或个人价值。对他人有用的品质,有仁爱、慷慨、和蔼、慈悲、怜悯、宽厚等,这些可归入社会道德。(16) 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关于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的区别,休谟讲得很清楚。而关于个人的德和社会的德的区别,虽然他在概念上没有区别得很清楚,但其思想是明确的。
四、康德论“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思考边沁提出的“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不能不提到比他更早的康德(1724—1804)。康德在1797年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二部《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一书的“德性论导论”中,他区分了“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在此书的“伦理要素论”中,既说明了“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也说明了“对他人的德性义务”。所以,若论到私人道德,则“自己”与“他人”的对分早已是一个普通的分析,思想史很容易出现,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把自己和他人的分别带进道德理论,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
涂尔干认为,“普遍的道德应用规范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被称之为‘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一类是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31)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实际上,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其功能在于把所有道德固定在个体意识之中,广义而言,这是它们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方面,那些能够决定人们对其同胞,也就是对其他人究竟负有何种义务的规范,构成了伦理学的最高点,即顶点。”(32)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在这两种义务之间,还有一种义务,就是家庭义务、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他还强调,职业伦理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伦理,所以侵犯了职业伦理的不等于侵犯了“公共道德”。(33)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页。
那么,哪些是康德所认定的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照他看来,道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如个体与其自身,家庭群体,职业群体,政治群体。政治群体国家的整个规范形成了所谓的公民道德。(29)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6页。 故公民义务即是对国家的义务。(30)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义务,显然就是公民对国家应履行的义务”,照这个说法,“个体与其自身”的道德即是个体的道德,是个体作为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个体作为国民的道德。
对他人的义务,主要是爱和敬重。对他人的爱的义务,包括行善的义务、感激的义务、同情的义务;对他人敬重的义务,包括节制、谦虚、尊严。伤害敬重的恶习是傲慢、毁谤、嘲讽。(19)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3页。 此外,康德区别了“人民相互之间就其状态而言的伦理义务”,主要是友谊,认为爱与敬重在友谊中是最紧密的结合。最后,还涉及“交往的德性”,一些外围、附属的东西,如健谈、礼貌、好客、婉转。康德讲的这两种义务还是比较简单的。他所说的对他人的义务,并没有涉及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见“对他人的义务”这个概念,并不必然指向公德。应该说,康德还是在基本道德的意义上,在此范围之内,来区分对己和对人的分别。
五、密尔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
比起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更为著名的应是密尔(1806—1873)的《论自由》。《论自由》所讨论的是公民自由问题,即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换言之,对统治者施用于人民的权力要予以限制。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20)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页。
在该书的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一开始,作者声明:
在互动交流中,以上5位演讲嘉宾围绕在人工智趋势下,新技术赋能医药物流等话题进行了对话。5位嘉宾认为,未来,将由单一模式向协同、共享、高效等方面发展,医药物流趋于个性化、柔性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定制也应该遵循二八原则。专业团队合作中,链主企业在供应链中起到重要作用,应用场景更为广泛。在轻松、幽默、诙谐的气氛中将本次沙龙推向高潮,众多参会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盛赞沙龙观点犀利,让人意犹未尽。
每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行为,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若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社会所可做的事还不止于此。个人有些行动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犯者便应受到舆论的惩罚,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总之,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21)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9-90页。
体液免疫在MG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B淋巴细胞(B-lymphocytes)是在体液免疫中起着主导作用。MG患者的胸腺中聚集大量B淋巴细胞,形成生发中心。新的研究认识到体液免疫的关键点在于生发中心的调控。
然后,密尔笔锋一转:
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22)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0页。
然后,密尔提出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区分。他认为,他的上述主张是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强制管束,但这决不是反对人应当在自己之外关心他人的善与福。他说:“若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23)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0页, 就是说,他不仅不反对个人道德,而且是重视个人道德的第一名。但他紧接着说,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社会道德。这就建立了两个概念,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两者的关系是,社会道德第一,个人道德第二。他认为,个人道德的教育只应以劝服来进行,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来进行。可惜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两个概念。照其说法,个人道德是个人德性品质的总和。
无论中外的姓名,都是有含义的。不同者,汉语名字用字为普通词语,西语名字为专有名词。普通词语因日用而含义清晰,专有名词因沿袭久远意义往往被遗忘。当然西方人取某个名字往往是为了纪念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或者表示对某一个名人的爱慕或敬重,这样这个名字便有了应用含义,但却未必知道此词的本义。
密尔还强调:“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无论某人个人方面的品质或缺陷怎样,他人对他的观感都不应受到影响。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24)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1页。 如果一个人在品质方面有重大缺陷,他人自然会产生一种厌恶,使他成为被人鄙视的对象。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他人对他加害的正当借口,但人民还有权利以各种不同的办法让我们的观感发生作用。他说:“一个人表现鲁莽、刚愎、自高自大……不能约束自己免于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而牺牲情感上和智慧上的快乐——这样的人只能指望被人看低,只能指望人民对他有较少的良好观感;而他对于这点是没有权利来抱怨的。”(25)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所以,密尔认为,一个人若只在涉及自己的好处、不影响与他发生关系的天然的利益时,他的行为和德性招致天然厌恶,他因此而应当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一些别人不再理睬他的不便。(26)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关于物候期的变化、产量的提高、品质的提升,也与今年葡萄管理和今年的气候条件有关,试验的葡萄园今年无论是施用本然的还是施用化肥的,产量都提高了,同时,检测手段还不先进,所以在研究本然土壤调理剂的作用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涂尔干的讲稿《社会学教程》发表,1950年代英文版的书名改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不过,与书名不同,此书中真正论及公民道德处却不多。
在知识经济兴盛的今天,人们对于知识服务的需要与日俱增,知识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服务理念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有关知识服务的尝试与探讨应运而生。知识服务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浪潮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共同的一种对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和利用的新服务方式。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知识服务,但对知识服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探索阶段,对知识服务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确切统一的认识;对知识服务的定义主要集中在用户问题的解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广义的知识服务与狭义的知识服务等几方面。
那么,哪些是导致这些行为的性情呢?他指出:
性情的残忍、狠毒和乖张——这些是所有各种情绪中最反社会性的和最惹人憎恶的东西——妒忌,作伪和不诚实,无充足原因而易暴怒,不称于刺激的愤慨,好压在他人头上,多占分外便宜的欲望(希腊人叫做“伤廉”),借压低他人来满足的自傲,以“我”及“我”所关的东西为重于一切、并专从对己有利的打算来决定一切可疑问题的唯我主义——所有这一切乃是道德上的邪恶,构成了一个恶劣而令人憎恶的道德性格。这与前节所举只关己身的那些缺点是不一样的。(28)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94页。
他说:“所谓对己的义务,就是说不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除非情况使得它同时也成为对他人的义务。”他的说法似乎是针对边沁的“对自己的义务”作的说明。所谓“对己的义务”,主要是指自重、自慎、自我发展。如果人的缺点只是就对自己的义务而言,只是损害自己,不损害他人,如鲁莽、刚愎、自大、放纵、愚蠢,这些缺点不能算是不道德,故不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在密尔的论述中,“对他人的义务”即是“社会道德”;与此相对,“对自己的义务”即是“个人道德”。这是我们对密尔的分析。明治日本提出的“公德—私德”概念很可能受到密尔这种区分的影响。
密尔的概念很清楚,但用于道德史的分析并不容易。如孔子与儒家的“仁”,究竟是“对自己的义务”还是“对他人的义务”?从克己来说,仁是对自己的义务;但从爱人来说,仁是对他人的义务。如果以对自己和对他人来分别私德和公德,那么只能说,孔子的仁既是私德,又是公德,或既有私德的性质,又有公德的意义。当然,对他人的义务和公共生活的义务并不相同,这是不应被混淆的。全面地说,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还有他人道德,构成私人—他人—公共的序列,那种个人道德—他人道德的两分法,容易把同样是非个人的他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混为一谈。
让我们重述并概括一下被认作一门艺术或科学的私人伦理同包含立法艺术或科学的那个法学分支之间的区别。私人伦理教导的是每一个人如何可以依凭自发的动机,使自己倾向于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幸福的方式行事,而立法艺术(它可被认为是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教导的是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可以依凭立法者提供的动机,被驱使来按照总体上说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12)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0页。
六、涂尔干: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
至于对他人有损害的行动,那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对待了。侵蚀他人的权利,在自己的权利上没有正当理由而横加他人以损失或损害,以虚伪或两面的手段对待他人,不公平地或不厚道地以优势凌人,以致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免于损害——所有这些都是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在严重的情事中也可成为道德报复和道德惩罚的对象。不仅这些行动是如此,就是导向这些行动的性情正当说来也是不道德的,也应当是人们不表赞同或进而表示憎恶的东西。(27)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在涂尔干看来,所谓公民即国家的公民,公民个体作为国家的成员必有其被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的基本特征是,以忠诚和服务的义务为中心,这体现了国家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既不同于家庭的逻辑,也不同于职业伦理(他所讲的职业伦理正如亚里士多德讲的船舶水手一样)。
关于对自己的义务,康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对自己的生理躯体的义务,他称之为“人对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包括不应自杀,不应对性作非自然的使用,不应酗酒和暴食。(17)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6-436页。 另一部分是“人对纯然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包括不应说谎,不应吝啬,不应阿谀奉承;伤害这些义务的恶习是妒忌、忘恩负义、幸灾乐祸。(18)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9-444、470-471页。
放飞想象力,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只有将自己的思维放飞,才能够很快接受童话故事带给自己的快乐,也才能够理解童话故事后的真正含义。发展想象力,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用最本真、最真诚的眼光看世界。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语言的童话性,用儿童视野开展童话教学。
涂尔干也谈到家庭道德:“实际上,家庭生活曾经是,也依然是道德的核心,是忠诚、无私和道德交流的大学校:我们赋予家庭很高的地位,使我们倾向于去寻找那些可以特别归结为家庭的解释,而非其他。”(34)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8页。 他又说:“如果政治社会局限于家庭社会或家庭的范围内,就几乎可以与后者等同起来,成为家庭社会本身。但是,当政治社会由一定数量的家庭社会组成时,由此形成的集合体就不再等同于构成它的每个要素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需要用一个不同的词来描述。”(35) [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8-49页。 罗马的父权制家庭就常常被比作微型的国家。
与其他学者不同,黄慧英很重视“非道德”的领域,所以她重视斯洛特这样的看法:
对于社会生活总体生活的构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从个体本位的权利立论,而涂尔干以及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则从社会结构的系统着眼,把国家看作经济组织的扩大。因此,他把国家的政治作用最终落实到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几乎没有关注个人对自己的义务、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这倒很像百年来中国社会遭遇的境况,只讲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忽视个人道德。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做法开了现代国家的先河。
七、斯洛特的德性伦理:“关于自己的德性”
当代伦理学家麦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其《从道德到德性》(From Morality to Virtue )一书中,将道德分为“关于自己的德性”(self regarding virtue)与“关于他人的德性”(other regarding virtue)。其实,采用这种分析的学者不少,如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也讲“自我关涉”和“他者关涉”的分界。(36) [英]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页。 所谓关于自己的德性是有利于拥有者自己的品质,如深谋远虑、坚忍、谨慎、明智、沉着。所谓关于他人的德性是有利于他人的品质,如仁慈、公正、诚实、慷慨。还有一类,如自制、勇敢,是既关乎自己,又关乎他人的德性。斯洛特认为,在一般的道德观中,关乎他人比关乎自己要更重要,故两种德性之间是不对称的。(37)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4页。 斯洛特认为常识道德观中人我不对称,而德性伦理学则无此困难,故更为可取。黄慧英反对这种观点对儒家适用,她指出,儒家对人际交往的德性,既有关于自我成就,又同时有关于成就他人,所谓关乎自己之德性与关乎他人之德性乃二而一,人我并非对立。(38)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8页。
她误入充气娃娃的世界。她被从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商品们折磨。她的情感世界彻底变得颠倒,一变成二,有变成无,是变成非,恨变成爱。她应该憎恨秦川而不是爱上秦川。她应该逃离豪宅而不是坚守豪宅。尽管,当秦川死去,豪宅便成为她的财产。
而斯洛特所说的关于自己的德性基本上是“非道德德性”,他的问题意识突出非道德德性,并没有意图涉及公德问题。其实,关乎自己与关乎他人的德性都是个人基本德性(道德),而非公共道德,严格意义上的私德只是个人道德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只是小部分。从另一方面来说,私德多属非道德的德性,但非道德的德性可能不止于严格意义的私德,即只关乎自己的道德、德性。
那么,哪些是非道德的德性呢?黄慧英认为,就儒家伦理而言,在儒家伦理系统内的大部分的德性都是有道德含义的,但仍有部分德性属于非道德的范围,前者关注的是道德人格的养成,后者为整全人生所需。她又认为,在儒家伦理,非道德德性有其独立于道德德性的地位,故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狭义的道德系统。(39) 黄慧英编著:《从人道到天道:儒家伦理与当代新儒家》,新北:鹅湖月刊社,2013年,第150-151页。 至于哪些属于非道德的德性,她认为《论语》中所说的文质彬彬,“文”是一种非道德的德性,《论语》中所说的君子所贵于道者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即属于文的德性。另外,“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不惑、不惧,及“知与勇”,也是有助于成为君子人格的非道德德性。孔子所说的九思中“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等也是非道德德性。“柔、明、惠、和”是非道德的。在儒家伦理中,道德德性比非道德德性重要,但只要非道德德性不妨碍道德,是受到鼓励的。(40) 黄慧英编著:《从人道到天道:儒家伦理与当代新儒家》,新北:鹅湖月刊社,2013年,第174-177页。 又如,孟子对古圣人的评论中,圣之和、圣之清、圣之任,和、清、任也是属于非道德价值,但它们都是圣的不同表现形态,是构成美好人生与品格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涂尔干把每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定义为个体道德,而每人与自身之外的关系的道德分为若干层次,即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公共道德、族群伦理,一个比一个应用的范围更广。用公德和私德的语言来看,他确定了个体道德是私德,而其公德的范围很广,划分更细,内部包含不同的逻辑。但他似乎没有在意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区分。
德性伦理学者用来作评价的基本的德行概念,并不专限于道德(moral)(也就是说,并不专指是道德上善,或道德上卓越的),而是“关于一些好的或令人欣羡(admirable)的人格特征,卓越的人格,或者简要地说,一项美德,比较宽广的德行概念”。(41)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48-49页。
这显然是指斯洛特所强调的德行概念,不限于道德的德行,而包括受人肯定的非道德德行。斯洛特还指出,非道德的德性是从自我的福祉出发的,对自我的福祉与他人的福祉有同等的重视。这样的伦理学立场将涵盖大部分常识性思想的以往观点。以往总认为他人的福祉才是道德的,或是重要的。斯洛特提出:
但是依我们共同的认识,无论是利他还是利己的特性和行动都可以是值得欣羡的德性(或其个例)。把这种大多数属于与自己相关的特性,如:审慎、坚忍、不用心、慎重和轻率,作出描述与评价,明显是伦理学的部分事务——虽然也许不是正规的道德观(morality proper)的事。(42)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49页。
黄慧英在其《儒家伦理与德性伦理》一文最后说:
对第①层级案例的资料收集整理可见,乡村民宿建造呈现3种模式:对老民居进行改造(暮云四合院、慢屋·揽清等),偏重参考当地民居进行解构抽象后新建(即下山),又或者偏重结合对场地条件的认知来进行新建(40英尺)。以上可看出乡村民宿的设计现有代码2)包含了当地传统民居的本体与其抽象内涵、场所条件。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人们对传统民居的印象已经形成一种现有意识,是隐含于人们大脑中的惯用语体系,是一种既有信息的来源。此外,地块的现状条件(包括地形、气候、文化等)作为一种长久渗透生活的要素,也是乡村民宿表义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历时性因素。
是否对非道德的价值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从而促使人们去发扬这些价值。如果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得到承认,那么许多相关的原则都可以建立起来,渐渐便会形成一种学问。我们可以给这种学问一个新的名称,或者我们仍然称之为“伦理学”。(43) 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1页。
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新名称,有一个旧名称曾流行甚久,即人生论或人生哲学,它是20世纪前20年广泛使用的概念,具体也许可以恢复它的作用。
八、近代日本的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
在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公德的概念曾流行一时。那么,公德是公共道德还是公民道德?人们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陈弱水认为,社会伦理区别于个人伦理和国家伦理,公共道德近于社会伦理,公民道德近于国家伦理。根据他的研究,公德基本上是要求公民不要破坏公共利益,或不妨害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他人,是人对社会整体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义务。所以,公德应该是指公共道德。(44)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这个主张是妥当的。
汉字“公德”的使用来自近代日本。日本明治时代风俗改革运动中的“违式诖违条例”规定,违者处以罚金或笞刑,其所取缔的条目多达百条,如第四十四条“喧哗、争吵、妨害他人自由、吵闹惊扰他人者”,第五十八条“攀折游园及路旁花木或损害植物者”,第七十五条“夜间十二点后歌舞喧哗妨碍他人睡眠者”。这些都是意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规范。
又如,明治十八年浮田和民的《社会道德论》,共含五十五个条目,而西村茂树明治三十三年的《公德养成意见》中的规条共一百三十项公德,规定个人行为应避免造成对他人或公众的损害,这些事项包括:不守时,聚会无故缺席,攀折公园花木并擅入禁止出入场所,在泥土墙壁与神社佛寺外墙涂鸦,污染政府机关旅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的厕所,在火车、汽船、公共马车内独占利益不顾他人之困扰,拖拽重物破坏道路等。(45)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其实,这类规定条目在中国历史上可列为“礼”之条文,是新时代社会文化应遵循的新礼,可不称为“德”。故此类规定条目不属于德,而属于“新礼”。但是,近代以来无论日本或中国并未就此加以分疏,统以“公德”论之,这就容易把公共生活规范混同于道德规范,在理论上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就实践而言,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风俗开化运动,借用公德观念,推行有力,效果明显。“礼”以禁为特色,公德就其为社会道德而言,以“不”为特色,其核心是“不影响或损害他人”和“不损害公共利益”。此一精神核心的具体化,则为“不害他人性命”“不占他人财产”“不伤他人名誉”“不侵犯他人权利”等等,类似的具体规定可列举无数。但“公德”的概念在百年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如今改为“公礼”亦不可能,也许用“公共礼规”来表达要好一些。这是“礼”的观念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实例。本来,古代有“仪节”一说,以指称各种礼之节目,但现代中文“礼仪”只是仪式,“礼节”只是礼貌,节目成为文艺专用语,度数亦然。所以,我们只得用一个新词“礼规”来表达现代公共生活的行为规定。人在社会上受此种礼规之教化日久,便生起一种“公德心”,或叫作尊礼的德性,这在日本人是很常见的。
因此,很明显,除了教授的历史知识,现代人并不需要学习那么多古礼知识,如古人如何站立起坐、如何行礼作揖、如何穿着冠带等,而是要使礼成为现代人公共生活的节目体系,亦即一个世纪以来公德概念所贯穿的社会精神和行为要求。制订新礼规是当务之急。自然,新礼规也需要奖惩制度的支持。
中国古代不能说只是重私德轻公德,古代社会里,公德即在礼的体系之中,古人非常重视礼的规范和实践,而且古代礼的敬让之道不仅是古代社会公德的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公德精神。只是古礼之文很难完全调适为当代生活的规则。可以说,中国文化缺的不是公德,而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
Ego and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rality
Chen L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f we say Aristotl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civil morality, then Bentham founde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ethics. Hum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virtues” and “artificial virtues”, which impli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virtue and social morality. Kant also talked about obligations to oneself and obligations to others, but the latter did not involve public morality. Mill established the concepts of private morality and social morality, and in his view, the obligation to others is social morality, and the obligation to oneself is private morality. And Durkheim defined everyone’s relationship with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divided the mor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yond oneself into several levels. In terms of public morality and private morality, individual morality is a private morality,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morality is wide in range. Slote in his view of morality pointed out that “self regarding virtue”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regarding virtue”, and they were asymmetrical;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virtues related to one’s own, which was “non-moral virtue”, and believed that private morality was mostly non-moral virtue. In the era of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ustoms Reform Movement were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in public places for daily life. It is not exact to say that in ancient China, they only emphasized the private morality while public morality was ignored; in the ancient society public morality which existed in the system of rites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ity of modern life.
Key words :western concept of morality; ethic; public morality; private morality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9)05-0001-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 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5.001
* 收稿日期: 2019-08-02
作者简介: 陈来(1952— ),男,浙江温州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登德
标签:西方道德概念论文; 伦理论文; 公德论文; 私德论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