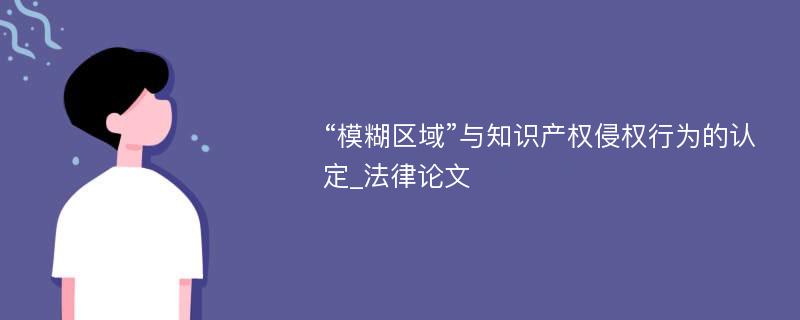
“模糊区”与知识产权的侵权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产权论文,模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当大一部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司法或行政执法机关会面临认定或否定侵权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在“侵权”与“非侵权”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模糊区”。缩小这个“模糊区”,是走向正确判决或决定的关键。本文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这三种不同的知识产权领域,在缩小“模糊区”方面应如何着手做了一些探讨。
一
专利侵权的认定或否定,与商标权、版权相比,客观性及确定性都更强。这主要是因为比商标及版权制度历史更长的专利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了“权利要求书”(Claim)制度, 而这种制度又在较长的发展中,得以不断完善。
17世纪上半叶产生了近代专利制度;一百年后产生了“专利说明书”制度;又是一百多年后,从法院在处理侵权纠纷时的需求开始,才产生出“权利要求书”制度。〔1〕
从理论上讲,“权利要求书”由专利权人(尚且是“申请人”时)把自己要求得到保护的发明范围,清清楚楚地划出来,并在公开后的专利文件中昭示公众:切勿未经许可进入这个圈里来。正如在西方国家驾车驰在公路上,会不时见到大路边的叉路上有牌子写着“Private”, 以示“公路”与属于私人的地产部分的“私路”的界线。当然,稍有不同的是:在“专利要求书”所划的圈子之外,未必均是“公有领域”的技术。属于他人在先已经专有、目前依旧专有着的技术,也会在这个圈子之外。
专利的“权利要求书”所划的这个圈子本来在理论上应当十分清楚,却从两个方面在实践中变得看上去有些模糊了。一方面,专利权人当初在申请专利时,希望专利审查部门把“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解释得越窄越好,以免稍不留意就“宽”到“已有技术”〔2〕之中, 从而否定了所要求保护之内容的专利性。另一方面,已经成为专利权人之人,在侵权诉讼中,又总希望行政主管机关和(或)法院将“权利要求书”的内容解释得越宽越好,以便把凡是权利人认为是“侵权”的行为,均划入圈内,即认定为侵权。
为把这个人为“模糊区”尽可能缩小,有些国家从立法上想了一些办法。如美国的“方法加功能权利要求”。美国的判例法又在1994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这种权利要求的应有解释〔3〕。 有些地区性国际公约,也从理论上给以进一步的阐明。如《欧洲专利公约》,专为解释该公约第69条(有关“权利要求书”条款)而另行缔结了“议定书”。
在实践中,这个人为的“模糊区”可能被缩得更小。这一是由于在许多专利申请中,与“权利要求书”相“配套”,还举出了“实施例”。如果这些“实施例”不曾被专利局的审查员要求修改或删除,则它们就形成“权利要求”这个圈子的实实在在的篱笆墙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很难在自己冒冒失失地撞进这堵墙后却推说并未看见它。二是凡出现专利侵权纠纷、又一时难以认定或否定侵权时,多有专利审批程序或(和)异议程序中曾记录下的事实,提供出客观、准确的依据。例如,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或异议过程中,为使原先申请的内容不致于全部被驳回或被异议掉,而自愿削减掉的那部分要求内容,在侵权诉讼中自然不应被重新纳入“模糊区”之内。所以,有的法庭在专利侵权纠纷案的审理中,花费相当时间清理原专利审批过程。这确是缩小“模糊区”,以最终达到认定或否定侵权的可取途径。
经过上述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处理,从法律意义上看,专利侵权认定与否定的“模糊区”,可以被缩得很小,至少与商标或版权的侵权纠纷相比,其“模糊区”相对可以更小些。反过来讲,就是认定或否定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更强些。
当然,与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相似,在一大部分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指为侵权的一方,往往会反诉对方的专利无效。而在专利的无效诉讼中,较客观、又较容易掌握的,是找对方之专利缺乏“新颖性”的证据。因为,不属于专利可保护的发明创造的范围,在法律中是比较明确的,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会误授专利权。而“技术进步性”标准中,要由行政执法人员或法院先去选择和确认在相关技术领域中一个有中等技术水平的人,还要看看有关技术对他是不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使得这条试图走向“客观性”终点的道路中,已经布满了主观性的荆棘。“实用性”标准中同样的引进了这样一位要由主观去认定的“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至于“实用性”中的其他因素,就似乎比“技术进步性”更缺少确定性了。
而“新颖性”标准,在各国都有分明的界线。以申请日为关键日,在它之前的出版物或行为,均可起到否定作用。这本应是“板上定钉”般地明白无误的。但各国由于对出版物或(和)行为的解释差异,有时也会出现认定或否定专利效力的“模糊区”。
例如,在我国,同一个申请人在先申请(尚未公布)的内容,是否构成对自己新颖性的否定?专利法第22条回答:不构成。对此的法理解释是:如果同一个人的前后两个申请均可以获专利,专利局可以要申请人自己选择一项〔4〕。 但这里的法理解释似乎只考虑到同一个申请人只在中国专利局前后两次申请内容相同的专利的情况。如果我们把眼界扩大,也就会看到问题了。
如果同一个人于中国专利法实施前夕先在美国申请一项美国专利,三年后又在中国就同样内容又申请中国专利。而这三年之中,美国并未公布其申请案,其间又没有“第三者插足”(即没有他人独立自己搞出同样发明在任何国家申请专利的),则该申请人不仅无必要依巴黎公约请求12个月内的优先权,而且实际上反而比公约优先权延长了三倍。如果美国仍旧不公布该申请案,则实际的“优先权”还将继续延长。这只是问题之一。如果该申请人的中、美两申请后来均被批准了,依中国专利法,该两“专利”均应有效,由于地域性原因,这种“重复授权”的有效性,似乎不会出大漏子。但是,如果三年后申请的中国专利,申请人将该申请日作为巴黎公约的“优先权”日,依中国专利法也应是合法的。这时,至少会出现以下问题:
1.该申请人是否可依后一申请的优先权日在国外申请专利?
2.该申请人是否可依中、美两项均有效的独立的“首次申请日”在中、美要求享有两个“优先权”日?
3.如果申请人在“优先权”期内获专利批准,又将中美两专利分别转让不同两方,该两方又均在一个不审查制国家均获得互相独立的专利。日后两家在该国发生专利冲突,法院应认定哪项专利有效?
可能还有一些未例举出的问题。
正因为这些问题在实际中可能发生过,一大批国家(加拿大、芬兰、挪威、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等等)才在法律或审查指南中,认为同一个人自己的在先(未公布)申请,同样可以否定自己在后申请案的新颖性。
如果我国专利法第22条中的“他人”被删去,在认定与否定专利效力方面的“模糊区”,就可能会更缩小一些。当然,从理论上及立法、司法上,我国都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及这一类问题。
二
商标权也与专利权一样,是一种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按理说,申请商标注册时,申请人要明白无误地提交希望获专用权的文字、图形或二者的组合。应当认为,在认定或否定侵权时,有着同专利一样的客观性及确定性。但是国际条约及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法,却偏偏明文划出了一个“模糊区”。正象我国商标法第38条(1)款, 有关的国际条约及各国商标法,都不仅仅把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相同注册标识于同种商品或服务,视为侵权,而且把使用他人的“近似”标识于“类似”商标或服务,也视为侵权。
有人也许说,这种“近似”的“模糊区”,在专利领域也存在。例如,使用了与“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等同”的技术,同样将视为侵权。不过,商标领域的“近似”标识与专利领域的“等同”技术至少有两点明显的实质性差异:
1.注册商标权人虽有权禁止他人使用“近似”标识,但自己却无权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该“近似”标识,否则会违反商标法第30条,从而会因“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被行政主管机关处罚。他的这项专有权的“禁”与“行”两方面,是不一致的。而专利权人在禁止其他人使用“等同”技术的同时,自己却有权使用,也有权许可他人使用。他的这项专有权的“禁”与“行”两方面是一致的。
2.两个标识在市场上的“近似”与否,要看是否会在“公众”中引起混淆。在这里,“公众”的不确定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在多少人当中未引起混淆方可认定在“公众”中未引起混淆;某次是如果在一部分公众中引起了混淆,在另一部分中却没有,则应以哪一部分人的判断为准?在专利领域看两项技术是否“等同”,至少还有“同一领域”中具有中等水平的“技术人员”这两重限定。虽然选择“技术人员”有主观因素,但“两重限定”本身仍旧是客观的。这总比统统甩给“公众”去判断,要有更高的确定性。例如,三个“│”按60度角三向排列,与三个菱形四边形按60度角排,两个图形是否“近似”?我曾在一次课堂上问及学员们。这些“公众”几乎一致说“不近似”。但德国恰恰判定过日本的“三菱”商标与德国的“奔驰”商标近似!
为了在实践中删除“近似”与“类似”这两个“模糊区”,许多国家的商标法为申请人提供了“联合商标”与“防御商标”两种特殊注册。前一种注册指的是:申请人将与其“主商标”近似或可能近似的一切标识,都申请注册。其注册目的(除主商标外)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禁止他人使用。后一种注册指的是:把同一个标识在一切类似或可能类似的商品及服务上统统申请注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在所有这些商标及服务上都用其专有的标识,而是为了禁止他人在这些商品及服务上使用。这样一注册,到侵权纠纷发生时,行政执法机关或法院,就不再有“模糊区”的烦恼了,即无须先去认定“近似”或“类似”与否,而可以直接按注册范围认定侵权了。
不过,如果大家都这样广泛地“注册而不使用”,就又会与我国商标法第30条及大多数国家商标法中均有的“使用要求”相冲突。所以,“联合商标”与“防御商标”一般只允许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标识去注册。
那么,怎样认定“驰名商标”呢?我国法中没有;巴黎公约中基本没有;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指出:要看它在“有关公众”中的被知晓程度。这一下,不仅把我们又推回到“公众”中去,还附加了一个更缺乏确定性的“知晓程度”。况且,“驰名”与否,是个变动着的因素。昨日尚不驰名,一夜而驰名者并不是没有的。曾多年驰名而又消声匿迹者也有之。我们绕出了一个不确定区,却走入了另一个更不确定区。在1995年初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时,仅仅对“有关公众”的地域标准,就争论多日而无结论。“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则在其1995年加拿大年会第127题中,提出更多的有关“公众”的“模糊区”。〔5〕
况且,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已经进一步把“类似”这个“模糊区”扩大到了一切“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6 〕这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更有力了,对消费者也更有益了,当然,对侵权的认定也更加不容易了。
在商标领域,侵权的认定与否定还有一点是与专利领域大相径庭的。这就是:在注册申请人的“权利要求”(即提交的注册标识)范围内,权利人决不会因为自己行使了行政主管机关批给他的专用权而侵犯了他人的商标权(“不当注册”情况除外)。而在专利领域,专利权人如果获得的是一项“从属专利”(即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称为“第二专利”的),则他确有可能因行使了“自己的”专利权而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这样看来,在不超出商标与专利两个领域的“权利要求书”书面范围的情况下,商标权人的“禁”与“行”两种权利这时是一致的,专利权人这两方面的权利有时反倒不一致了。
在我国(以及许多国家)的商标法中,何谓商标权与何谓侵权,是规定在相同的条款中的。〔7〕而专利法, 则把何谓专利权及何谓侵权在前后不同条款中分别作出规定。〔8 〕我国著作权法对版权及侵犯版权的规定也与专利法相同、与商标法不同。〔9〕从法理上分析, 商标法中有关专有权及侵犯专有权的规定是一致的。而专利法与著作权法中,如果后面找得到对某一类侵权的制裁,在前面却找不到这种“权”是什么,就会让人感到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却确实存在着。
在专利法中,这就是第63条前半部分对“假冒”的规定。专利法第11条所规定的专有权包括:使用权、销售权、制造权、进口权。这里的“使用”,似乎不包含商标法意义上的“在广告中使用”。但如果某人在广告中宣称自己的产品是使用某某专利制造的,而该专利事实上属于另一人所有;宣称者又并没有真的使用该专利,不过是骗骗人而已。这很难确认侵犯了该专利权人的“使用权”。专利权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权依专利法第63条诉前者侵权。但如果前者“抬起扛”来问一句:侵犯了你的哪项权利?这就不是一个从法律条文中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了。
在版权领域,民法学家们也常常在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七)款中提出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专利法第63条还是著作权法第46条(七)款,又都是不少国家的已有成例,并非中国立法者的“杜撰”。那么,应当如何回答假冒者(假冒他人专利名称卖自己的产品或假冒名画家之名卖自己的假画)可能提出及民法学者已经提出的问题呢?我想,可以联系商标法中的禁止假冒去解释。
从总的原则上讲,专利法与版权法重在保护权利人的专有权,有时涉及保护公众的利益;商标法从保护权利人的专有权出发,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涉及保护公众利益。但商标权人也有极特殊的时候,其利益受到损害,损害者却未必同时侵害了公众利益。例如,1994年发生在北京的撕去他人不驰名的枫叶商标,将他人产品挂上自己的驰名商标去卖的那场纠纷。受损害厂家在中国商标法中找不到任何起诉依据,却可以从专利法中找到“仿制”,在著作权法中找到“抄袭”。其实,“抄袭”与“仿制”,都是某种类型的“反向假冒”。“假冒”,是拿了别人的牌子去卖自己的东西;“反向假冒”,则是以自己的牌子去卖别人的东西。较发达的商标法中,是可以从反“假冒”条款中解释出反“反向假冒”的,例如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a。〔10〕而在发达的专利法及著作权法中,则同样应从反“仿制”与“抄袭”中,解释出反“反向仿制”及“反向抄袭”,亦即反“假冒”。〔11〕
如果有兴趣的研究者,结合市场经济,把知识产权中这些不同专有权的侵权认定,从法理与实践上加以深入研究,可以看到更多的合理的“权”与“侵权”的表面上的不一致。这正象我国的1982年之前与1979年之后,旧的《商标管理条例》对注册人不产生任何权利;新的可以产生出商标权的商标法又尚未出台,《刑法》则在第127 条明文写上了对侵犯商标权的直接责任者如何惩罚了!这种“依刑法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不仅在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过,而且在近、现代的国外知识产权法中也有成例。〔12〕
三
版权(著作权)是一种“依法自动产生”〔13〕的民事权利。权利人在享有版权之前,既不需要提出“权利要求书”,也不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所以,版权的权利人的覆盖面要比专利权人及商标权人都广得多;在侵权认定上,也比专利侵权与商标侵权的不确定性高得多。
由于权利人在获得权利之前或之后,均未以明确的“要求书”形式向公众昭示其权利范围,所以版权的侵权认定上的“模糊区”可能极大。于是,在侵权纠纷发生时,大多数被指控为侵权之人,往往首先从对方的作品(或对方的作品中被自己使用了的部分)“并不享有版权”出发,来为自己辩护。所以,“版权”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是在版权的侵权认定中必须弄清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最简单明确的,可以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即:“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14〕
当然,这一条最后的“之类”,仍旧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模糊区”。不过它至少向人们表明:专利法所保护的大部分内容,版权法是不保护的。此外,“数学概念”以及“之类”中可能包含的“科学发现”等等,又是专利法及版权法都不保护的。
各国的版权司法实践及大部分国家的版权立法,都明确了只有具备“独创性”(也称“原创性”)的作品,方能受到保护。至于什么是“独创性”,则各国又莫衷一是了。英国法律及司法实践认为,只要作品中体现出了作者的“劳动,就应当认为该作品具有独创性。所以,1995年由“欧州法院”作出最终裁决的BBC 广播时间表不正当竞争纠纷(国际上称为Magill Case), 一开始在英国就被法院确定无疑地判为“时间表”享有版权。〔15〕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同样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美国,最高法院则在Fiest一案中判了“电话号码簿”不享有版权。〔16〕原因是后者认为具备“独创性”的条件是作者的“劳动”加“技巧与判断”。仅仅有“劳动”,就很难把作为创作成果的作品与一般劳务成果产品相区别了。
仅从这两个案例及对“独创性”所下的定义,我们就不难看出不同国家在版权方面的分岐,是远远大于专利的。即使在一国之内,就侵权与否而对同一法律进行解释时,在版权领域出现的分岐,也会远远大于专利领域。
例如,一部分人认为版权只保护“形式”而不保护“内容”;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保护一切“内容”固然有可能弄混版权与专利的不同保护对象,而一概不保护“内容”,则会使许多侵权纠纷无从定论。在先走了几百年的德国,法理界想出一个聪明的解释来协调上述两种意见:第一,版权只保护“形式”,但第二,“形式”中既包含“外在形式”,也包含“内在形式”。〔17〕这样把“内容”披上外在“形式”的衣服再塞回“形式”的队伍中,真不失为一种独创。
再如,早在1989年中国的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立法者们就都已经接受了德国版权主管部门负责人豪依塞尔的建议,删除了“只要不是抄袭他人成果,就符合‘独创性’要求”的错误法条。六年之后,却又有人重新把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18〕临摹、拓印、翻拍等产生的成果,均不一定是抄袭或剽窃,却已明明白白地全部被著作权法认定为不具有“独创性”。“卫星云图”若不经加工,很难说具有“独创性”。它显然并非“抄袭”的成果。而地图中的一大部分,由于体现了测绘人员的取舍(判断),则具有“独创性”。但是,进一步的例子可能又会使人困惑:把五线谱改写为1、2、3…的曲谱, 把速记符号转化为普通人可读的文字,均不属“抄袭”,也可能还体现了改写者的技巧与判断,但又均不体现改写人或转化者的任何“独创性”,故不形成新的受保护作品。而把英文作品译成中文,则体现了译者的“独创性”,形成新的受保护的作品。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司法界在长期版权保护中形成的“唯一表达”原则,似乎在认定或否定侵犯版权时更可取。即:如果对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只有一种(或极其有限的几种)表达方式,则这种“表达”将被认为不具“独创性”,因此不享有版权。这里的典型例子就是科学的公式或其他科学发现。E=MC(2)这个公式是爱因斯坦毕生科研的成果,但如果设想它享有了版权,将会产生怎样荒唐的结果。
与专利侵权认定相同的是:享有版权的整部作品中,也会有一部分处于他人专有领域的内容(如引文),还会有一部分处于公有领域的内容(如校点作品中的原文、专著后附的公约、法条),在认定或否定侵权之前,必须先把这部分内容排除。
于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中出现、并经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法学者肯定的“三步侵权认定法”产生了。〔19〕这种方法告诉司法者:在认定或否定侵犯版权之前,应当先走第一步——“抽象法”,即把属于“唯一表达”方式的部分排除;再走第二步“过滤法”,即把不属于原告版权覆盖范围内的他人、前人的成果“滤”出去;然后才能应用第三步“对比法”,即把原、被告作品进行对比看看有几分相同之处。“三步”中的前两步,正是缩小认定侵权时“模糊区”的有效步骤。
在这几步中,我感到至少“过滤法”是专利司法者应当借鉴的,切勿在“保护专利”的大伞下,包揽进属于公有或他人专有的东西。那样对社会、对他人就会不公了。
当然,同样不能把确实属于特定权利人专有的东西划到其专有领域之外,那样又会失去了知识产权法的作用。
在找这两方面的平衡点方面,重点(或重点之一)在于缩小专有领域边缘上的“模糊区”。这就要看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的才干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才干者,将在认定或否定侵权的过程中,原地踏步,乃至扩大“模糊区”;有才干者,则会缩小乃至删除有关的“模糊区”。后者的智力劳动,虽然是“创作性”劳动,但出色的判决书,却在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依法不能享有版权。这对司法人员似有不公。不过,出色的司法人员如果总结及阐述自己手中出来的出色判例而形成论文、专著之类,则肯定会享有版权。我感到多数国家的版权制度倒象是在推促出色的司法人员,不要在判决书出来后就止步了,而应继续走完一个“学者型”法官该走的路,进而享有自己可享有的版权。
注释:
〔1〕参看W.Cornish: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版权与有关权,S&M出版社1989年版。
〔2〕已有技术(Existing Art), 也可以译为“现有技术”——但在我国专利法中却同时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译法或用法,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这是立法技术上应当避免的。
〔3〕参看《美国专利季刊》第29卷之2第1845页,Donaldson一案。
〔4〕参见汤宗舜《专利法解说》,专利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第99页。
〔5〕参AIPPI,1995年蒙特利尔第36届年会报告。
〔6〕参Trips第16条3款。
〔7〕参见我国商标法第7章。
〔8〕参见我国专利法第11条与第7章。
〔9〕参见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及第45、46条。
〔10〕菲律宾也从其商标法中做出同样的解释。
〔11〕参见德国、英国版权法及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
〔12〕参见英国1958年《表演者保护法》。
〔13〕而不是所谓不依法也能产生的“自然权利”。
〔14〕见Trips第9条2款。
〔15〕参见Case T—69189(1991)ECRⅡ485。
〔16〕参见《美国判例集》1991年第499卷,第340、345页。
〔17〕参见《著作权》杂志1990年第4期《迪茨博士谈著作权》。
〔18〕参见《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87页。
〔19〕参见《欧州知识产权》月刊,1992年10月号Altai—案。
标签:法律论文; 知识产权法院论文; 知识产权侵权论文; 商标保护论文; 模糊理论论文; 商标近似论文; 知识产权服务论文; 著作权法论文; 商标申请论文; 专利法论文; 商标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