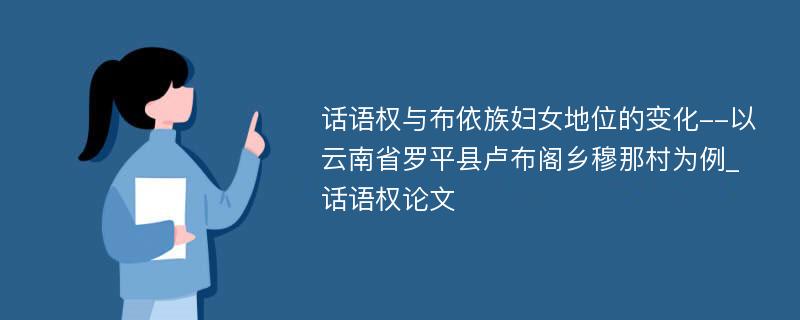
话语权利与布依族妇女地位变迁——以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木纳村妇女问题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平县论文,布依族论文,云南省论文,村妇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6)02—0086—06
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曾说: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利,权利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伊格尔顿(Eagleton)在批评加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时也指出:“阐释学无法承认意识形态问题——无法承认这一事实:人类历史的无穷对话常常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独白;或者,即使它的确是‘对话’,对话双方——例如,男人和女伤——也很少占据同等地位”。[1](P209) 在人类话语权上男性占统治地位,女性语言被称为“无势力语言”,男女在语言使用上反映的性别差异体现了男女在社会上地位的不平等。“自从父权制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形态以来,父权宗法制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造就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意识与男性创造的上帝神话一样无所不在——它通过社会化与教化的途径,直接侵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甚至生理,使之成为每一个人生存的提示、暗示、甚至压抑,造成并最终沉淀为社会每一分子似乎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意识。男性视觉、男性观点、男性声音成为普遍性,而女性视觉、女性观点、女性声音被排斥、被抹去、被忽略、被成为特殊性。”[2](P5) 中国由周礼制定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一直延续了3000年,“从根本上改变了性别间的平等关系和关于性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造就了男性对权势、武功和财富的崇拜,男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增长了‘才干’,那些成功者制造了自己的‘历史’,成为财富与权力、妻妇和奴隶的拥有者,而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男人为自己设就的生活范围和既定角色,将自己的职分降到次要的从属地位,从而形成了妇女无权的隐忍的经历,形成了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偏见,而妇女本身也就成了无史的沉默的群体。”[3](P10)
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拉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鼓吹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是近代以来进步知识分子的声音,尤其女性知识分子努力争取话语权。“在未来时代中国女性的群体记忆中,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我们民族经历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一定是一个百思不厌、回味无穷的瞬间: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中国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的代言人,恰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这已经足以构成我们历史上最为意味深长的一桩事件。”[4](P1) 这些女作家包括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1898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问世,晚清的女性解放即与艰难奋争的女报结伴而行。”“1904年1月17日,一份取名《女子世界》的新杂志在上海出现。”[5](P67) 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解放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等男女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进入社会职业领域的越来越普遍,完全靠个人的劳动获得社会职业身份和地位,不再是依赖于家庭和男人的新的妇女阶层,如女教师、女工程师、女记者、女实业家等。中国妇女在法律保护下享有着发达国家妇女至今还在争取的某些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从此,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女性声音遭到忽视的时代,女性找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多依村公所木纳村布依族妇女有着沉没无语的妇女史,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使村中妇女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无声失语逐渐获得部分话语权,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走上了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道路。
一、布依族妇女话语权与地位变迁
话语权表现在有无参与意见权、决策权、语言使用权上,妇女话语权主要表现在妇女有无说话的机会,发出声音表达的是妇女自己的心声还是男性社会的主流观念。
布依族妇女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在母系氏族社会,布依族先民以采集业为主,狩猎为辅,女性社会地位高于男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采集业发展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阶段,男子在生产中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掌握了经济实权,形成了父系氏族,这是布依族妇女地位的第一次跌落,但仍有很大的自主权、话语权。以婚姻为例,“据《大明一统志》说:‘男女自婚,’指的就是自由择偶。”[6](P63) 木纳村妇女在明代以前较少被束缚,明清时期罗平布依族曾办学教授《三字经》和《四书》、《五经》,汉文化的传播和辐射,使布依族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受到很大程度的汉化,汉族礼教思想的移植,强化了男权地位、男权话语,迫使她们成为他者、“第二性”,伴随而至的是言语权利的丧失。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妇女们的觉醒意识增强,终于又重获部分话语权。
(一)传统布依族妇女话语权
传统文化中东西方都以男权为中心,西方祈祷上帝不要把自己生为女人,因为女人低贱,夏娃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东方中国的《易经·说卦》则这样注释叙述:“乾,健也;坤,顺也。”即男,健也,女,顺也。顺是顺从,顺理,顺男子之意志,顺父权秩序之理。《白虎通》同样规定:“夫者扶也,以道相扶,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儒学宗师孔子曾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男权文化定下了“男尊女卑”的基调,男性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有说话之权与阐释之权。传统布依族妇女同汉族妇女一样终身纠缠于狭小的家务空间,成为没有话语权、没有思想权的“物”,但她们总是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在无声失语和争取话语权这一矛盾统一体中前行。
1.无声失语。有无发言权、参与决策权是话语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人类学意义上考察,男权语境中妇女的“失语”,是在男权至上的宗法农耕文化尤其是在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模式。罗平木纳村布依族解放前属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这种以食为天的农业生活方式使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带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力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及女性在其中的附属和辅助角色。”《诗经·小雅》中记载“乃生男子,在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在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班昭解释,“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下人也;弄之砖瓦,明其勤劳主执勤也。”受汉族“男尊女卑”影响,罗平布依族民歌“送背篼”对女孩歧视也很明显:“针线缝得步步紧,缝得稀的背孙女,缝得密的背孙男。”“黄色镶边的背孙男,花色镶边的背孙女。”做工好的、吉祥高贵的背篼只有孙子能享用。布依族妇女的地位低下也就决定了“丈夫是一家之主,享有决定内外大事的权利,妻子大多只能随丈夫之意。女性成员在许多方面不能享有与男性成员一样的平等待遇。”[7](P181)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对女性言行有种种限制,如家中有客人来, 只能由男性相陪的风俗延续至今。2004年2月,我们调查组一行3人——2女1男在村中一布依族家中做客吃饭,作陪的全是男性,婆婆、儿媳与小孩则另坐一桌,无论我们怎样邀请都不同桌进餐,也不交谈。村中一切公务活动更是与妇女绝缘,村中宗教活动妇女都不得参与,如一年中布依族最重要的“祭老人房”活动只许男性参加,就连妻子怀孕的男子也要回避。大年初一妇女不能到别人家串门,否则主人家会认为晦气、不吉利。布依族没有书面语,妇女使用口语的权利也受到限制,称谓语中妇女常常处于“无名”状态,刚结婚时无面称,以“喂”相称,有孩子后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他妈”,或“某某婶”、“某某奶奶”,成为无符号标志的边缘化附属品。
2.男权文化代言人。说什么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语还是做他者的代言人,是话语权的另一表现形式。东汉班昭在《女戒》中谆谆教导女性在生活中要遵从三从四德,木纳村妇女也在自己演唱的“临嫁训女歌”里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女儿在夫家要做循规蹈矩的好妻子,母亲们不仅自己遵从男性设计的礼规做俯首听命的好女人,还代男子立言去现身说法教育女儿,一方面失语,一方面又充当了男权话语的代言人。“临嫁训女歌”女儿出嫁每从楼上走出一步,母亲都要悉心教诲一番:挪步走出第一梯,父母是自家的天,好吃的东西要留给公婆;挪步下到第二梯,捆担子时要捆紧;挪步跨出第三梯,到夫家不能和小叔子逗玩;挪步跨出第四梯,妯娌对哥哥弟弟要礼貌,不能随意解发辫;挪步跨出第五梯,妯娌之间说话,不能边笑边谈,不能用手蒙着嘴笑;挪步跨出第六梯,你不能同人家丈夫去唱谈;挪步跨出第七梯,晚上你要紧闩门,早上你要紧关门,恐防野蛮的男人进来;挪步跨出第八梯,挑水你要悠悠挑,裤脚不能高卷,免得有时会害羞;挪步跨出第九梯,出门不能过分用力开门;挪步跨出第十梯,和人说话不能小声小气。歌中十条对出嫁女的要求,可概括为“孝”、“贞”、“礼”、“淑”、“顺”,形式是母亲教育女儿的话语,但实质是父权文化对妇女的规范要求,是经过社会性别制度内化了的东西,父系社会对女性的所有规定几乎无不源于家庭秩序的建立、维持、巩固之需要,包括对女性贞操品德、举手投足之做派规定等。男性文化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对两性双重道德和价值标准的制裁和评判,如什么是理想模范的好女人,什么是令人厌恶的坏女人,成为文化塑造妇女的核心,正如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活动家西蒙·德·波伏娃所揭示的那样:“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8](P309) 大多数女性充当男性代言人的初衷是想让其他妇女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谦德忍道在丈夫的家族中站稳脚跟,如班昭,但在男权强势话语的强大攻势下,体现男权意识的传统礼教观念逐渐沉淀为妇女的集体无意识,并内化为妇女对自己的要求,且对女性要求最为严格的往往是女性本身。当然,在男性词语中心社会里,“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则是这一原则所排斥的对立面;只要这一特点固定不变,整个体系就可有效的发挥功能。”人们认识事物的存在是把握对象的真理,也必须使用这一中心社会语言才得以通过,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受压抑的一半,自然而然,不可能不属于男性的观念世界和语言文化。
3.争取话语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木纳村布依族妇女面对男性的压迫并非一直逆来顺受,而是在顺从与反抗中前行,既表现在对话语权的放弃上,又表现在对话语权的争取上,颇具民族特色。
居住形式反映权利的差异,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后,居住形式由女家移至男家,女方称为“嫁”,男方称为“娶”,汉族称女子出嫁为“归”,夫家才是妇女的家。随着女性位置的跌落,布依族妇女们不得不由从妻居改为从夫居,同时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奋力抗争,“不落夫家”婚俗最具女性反抗特点,在最终顺从夫权意志定居夫家的前提下,父权作出妥协让步,女性终于争取到了“不落夫家”的权利。新娘在“不落夫家”期间,在娘家有着特殊身份,既可帮娘家干活,报答娘家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又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田地,得以积攒一些“坐家”后需要的东西和私房钱,做好终生够穿够用的衣物,以补偿定居夫家后失权失语的遗憾。过去布依族青年只有恋爱自由、没有婚姻自由,“包办婚姻”常常使得新郎、新娘彼此陌生不了解,“不落夫家”期间每年农忙、过节的走动接触便于情感磨和,为新娘以后定居夫家作好心理上的准备。
过去布依族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们在没有受到教育的情况下,用口头文学、歌舞、刺绣、织布、服饰等不同话语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记载着自己独特的女性经验和体验。
布依族是一个“无事不歌”的民族,几乎个个都是对歌能手,婚恋对歌、迎客对歌。妇女们在社会家庭生活中受到种种限制,如婚姻的不自由,要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只能到口头民歌中寻找话语权。在“情歌”中,她们大胆倾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意中人互叙衷肠、山盟海誓,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也可尽情发泄。布依族的对歌活动,是由姑娘选小伙子,唱不好情歌的男青年为了获得心上人的爱情,还常常请唱得好的朋友代唱,女性话语权明显高于男性。
刺绣、纺纱织布、缝制衣服是每个布依族妇女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在村中调查时,看到一位母亲正在古老的织布机上耐心地向就读于鲁布革乡中学的女儿传授织布技术,希望这一技能不断延续下去,这也是村中人的普遍心理。有人认为少数民族妇女在手工制作中耗费了她们过多的青春、心血,浪费了过多的宝贵时间,其实只要明白她们被圈于家中、没有话语权的附属生活,就不难理解她们世世代代乐此不疲沉浸于艺术领域的原因了。她们把复杂烦琐的纺纱织布、靛蓝染色、缝制衣裙、镶嵌花边等制作工序当成一件幸福愉快之事,因为只有在服饰艺术天地里才能纵横驰骋,心想事成,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希冀、审美情趣全部倾注在服饰中,在手工制作中享有绝对的自主权、话语权。
(二)当代布依族妇女话语权
福柯“话语”理论认为影响控制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权力。妇女要改变自己的无语状态,就必须获取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可由从“第二性”还原为“第一性”,提高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
解放后,我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木纳村则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由于山川的阻隔,民族文化意识的传统惯性,木纳村在改革开放前基本还延续旧有习俗及伦理道德观念,男女社会地位并无多大变化,但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之风吹进了村寨,为布依族妇女解放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9](P49) 这在历史上已得到印证,“当时妇女经济收入多于男子,社会地位比男子高,形成以妇女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6](P11) 20世纪80年代后多依河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她们冲破封闭、落后的地理环境限制及男权规范要求的伦理道德禁锢,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旅游业带动了餐饮业、手工业、小商业的发展,妇女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她们把平时只能家用的自制布依族服饰、绣品、床单、桌布,以及竹制小水车、五色花饭、凉粉、面条等作为商品拿到集市上出售,很多妇女经商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在家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使她们第一次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村民们普遍认为,男子口笨,只适合做直活路,妇女说话婉转,在生意场上能大显身手。“从家庭经济地位看,布依族妇女有了对家庭经济收入管理支配权,很多人“已不是过去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成为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10](P64) 过去妇女在家中做家务不直接创造产值,没什么经济收入,经济大权牢牢掌握在男性家长手中,是理所当然的一家之长,当然一切都是男人说了算。女性由家庭人变成了社会人,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承认,锻造和增强了女性的社会价值。
社会不仅是谋生的场所,更是接触各种外界文化的重要场地,布依族妇女思想观念的更新导致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当代布依族婚姻注重情感,女青年也敢于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姻说“不”字,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比例达到2/3以上,基本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布依族历来认为离婚是耻辱之事,较少有离婚现象,女性更是不敢言离婚。今天村中妇女讲究婚姻质量,抛弃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陈腐观念,敢于主动提出离婚。大男子主义严重的家庭,丈夫经常大打出手,妻子提出离婚又不同意,只好跑,近年就有三个女青年分别跑到广西、广东,两个做家后跑,一个做家前跑。过去妇女最怕被休妻,现在有的丈夫却怕妻子出走,特别妻子聪明伶俐、各方面出色者,反过来对妻子更好。中国封建礼教要求妇女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木纳村过去一直认为丈夫死了妻子应该守寡,寡妇极少改嫁,但现在村中妇女再嫁者增多,人们也较宽容。
“婚礼者将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婚礼》明确揭示了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家庭是妇女生命的唯一寄托,妇女生存的价值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妇女被沦为生育工具。同汉族一样把多育子嗣当成自己头等大事的木纳村布依族,信奉“多子多福”思想,婚礼上总要由德高望重的老人说些“生儿育女,一本万利”之类的吉利话。确保生育一个儿子是每个村民生育观念的基本目标,没有儿子的家庭面对巨大压力,不得不为生育儿子而不懈努力。过去每个家庭生育数量少则四五个,多则八九个,妇女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耗费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落实,以及妇女自身的觉醒、村民生育观念的改变,一般家庭都只愿生育两个孩子,今天超生现象多发生在没有儿子的双女户家庭。村中李荣春老师一共生育七个孩子,长子与二女儿已养大成人,现有二子三女五个孩子,子女的年龄在30到40之间,他们均只生育两个孩子。生育数量的大大减少,使妇女得以从“生育工具”的命运中解脱出来,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其他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之事,如学习、经商、打工。由单一人类生产主体成为人类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这两种生产的主体,由以人口生产为主转向以物质生产为主。
二、布依族妇女未来话语权展望
当代布依族妇女受传统习惯和现代因素双重影响,在接受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同时,深层积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左右束缚着她们的行为,减缓她们在妇女道路上的前进步伐。
(一)受教育权力平等中的不平等
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地位的提高有赖于女性素质的提高,提高女性素质的关键是女性教育。鲁布革乡中心学校的布依族李校长曾这样总结布依族外出务工情况:“读过书的人才可能出去打工,不识字打不了。”接受教育是布依族妇女迈向平等的第一步,能为她们今后平等地步入社会奠定基础。妇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还能打破男性对文化的垄断,对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产生深远影响。
《宪法》规定,男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木纳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受教育人员历来就少,妇女更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前受教育的绝大多数是男性。调查中了解到,村中40岁以上的妇女几乎全是文盲,30岁以上的中青年妇女也只有少部分受过小学教育。李荣春老师年逾六旬的老伴是文盲,年近40的大儿媳未读过书,比大儿媳小五岁的小儿媳读过小学,大儿子、小儿子分别初、高中毕业,三个女儿所受教育程度都不如儿子,只读过小学。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力度的加强,家长意识的提高,当代木纳村布依族适龄儿童无论男女都有了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都能背着书包高高兴兴走进多依小学读书,但小学毕业到鲁布革乡中学读书的情况则不容乐观,从乡中心学校李校长那儿了解到:女孩小学都能读书,到初中女孩流失40%,男孩流失10%。中途辍学最多的是女孩,男孩情况明显好于女孩,这也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在当代的延续,多数人家对女孩要求不甚严格,关心教育要比男孩少,认为“早晚要出嫁,成为别家人”。
(二)离婚自由中的不自由
木纳村妇女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动提出离婚,离婚逃婚现象呈上升趋势,争取到了离婚自由权,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对封建婚姻习俗强有力的冲击,但她们也有着诸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形式自由实质不自由。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有自由离婚的权力,木纳村妇女即便顺利离婚,日后所面临的困难也是难以克服的。当地民俗习惯是妇女出嫁后夫家不分土地,娘家土地归弟兄种植,离婚女常常夫家不能留,娘家不能回,不仅失去土地等经济来源,连居住也成大问题,忍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另外,布依族生活相对封闭落后,文化上自有其一整套传统习俗,完全或部分排斥国家的政策干预,妇女提出离婚,但传统习惯势力往往阻碍妇女的离婚自由,不得已只好出走,不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离婚问题,就算诉诸法律也难以得到权益保护,因为布依族以办酒请客作为婚姻成立的标志,结婚一般都不领取结婚证。成功出走脱离婚姻关系的妇女,由于终身难以返乡,不得不长期忍受亲情、乡情的煎熬,加之文化程度不高、就业谋生能力较弱,在外生活也难以如意。
(三)有限社会活动中的受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木纳村妇女们基本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方面的意识,村干部中没有一个女性,我们碰到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送电影到村里放映,与村长谈论村上文化工作时,没有一个妇女参与,男性还是村中一切活动的唯一决策者,妇女仍旧无声沉默。村民们说,过去妇女社会地位低,男性占主导地位,现在比较平等,社交活动男女都参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很多妇女至今还不能上桌陪客吃饭、不能参加村子里的宗教等重要活动也不容忽视,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是有条件限制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聪明能干者在家中情况要好些。妇女们虽然由灶间走入市场,但绝大多数仅在村口集市自销一些自产的小商品,家庭覆盖面也有限,多依河风景区旅游景点门口规模大点的商店,都是县城汉族来开设的,外出务工仅限于没有科技含量的劳务性工种。在有限的社会活动中,文化素质又限制了木纳村妇女的活动范围和择业圈子。
“女性真正感觉到与男性相比,除了自然性别不同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平等的。”这是人类理想的女性地位提高、男女平等的最终模式,也是未来布依族妇女社会变迁的目标。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要以综合实力为背景,一是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二是这会社会政治环境,还要依靠群体成员的意识提高,特别男性的理解参与。只要做到三方面的协调发展,罗平布依族妇女就能早日完全获取话语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收稿日期:2006—01—12
项目名称: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罗平布依族社区文化的当代进程”(03Z783E)
[栏目策划]李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