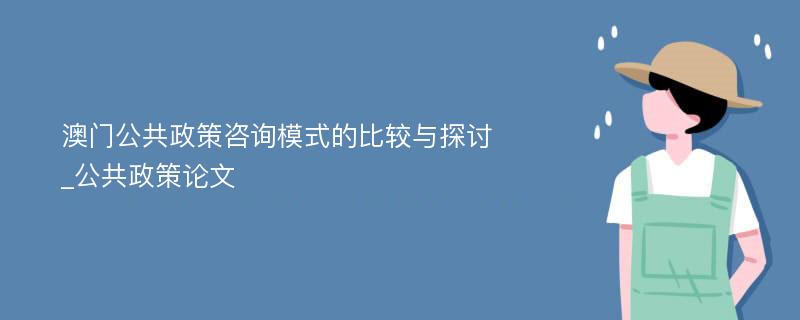
澳门公共政策咨询模式的比较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公共政策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4-0091-07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了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①根据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的定义,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②。这表明公共政策的产出将不仅涉及具体的政府行为,还将影响受政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的资源和价值观。因此,一项合意的公共政策不但应该具有专业性,同时还需拥有合法性。如果决策仅仅关注政策的专业性,而把受政策分配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这样的“专家理性”的决策结果,可能会引起决策合法性的丧失,因为专家拥有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替代公众的主观价值偏好。③可以预见,如果政策失去了公众的参与和赋权,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公众的主观价值偏好容易流于感性,无法满足政策所需的专业性和效率等要求,因而专业知识又是有效的公共决策所必须的要求和门槛。④如何平衡专业性和合法性两者之间的潜在冲突,成为任何公共决策过程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社团是澳门政治系统里最为重要的单位,他们不单是联结普通市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将社会的意见要求反映给政府部门内的决策者,同时协助政府传递具体的政策讯息予市民,使政策得以顺利执行和遵守。这种“社团咨询模式”的有效运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较好地平衡了公共决策过程中专业性和合法性之间的潜在冲突,从而维持了澳门的社会稳定及和谐。随着2002年赌权开放,澳门经济急速发展,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除了使社会问题增多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变得激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即为2006年和2007年两次“五一游行”期间所发生的警民冲突。⑤这些冲突反映出澳门既有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存在着缺陷和局限,未能适应业已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本文将通过“美沙酮事件”和“新城填海公众咨询”两个具体的政策案例,重点关注和探讨三个问题:(1)社团咨询模式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2)这种决策模式的成立条件和局限何在?(3)可能通过怎样的方式改进这种决策模式? 一、社团咨询模式的形成和作用 社团在澳门主要发挥三种不同的功能⑥:(1)NGO功能。如澳门同善堂、澳门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主要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社会服务;(2)“拟政府化”功能。如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属下的坊众学校、柏蕙活动中心、临屋颐康中心等机构,在教育、青少年和老人服务等方面部分承担了一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3)“拟政党化”功能。在政治系统里,普通市民一般是通过政党这样的组织来和政府发生联系,但在澳门,这样的功能则通过社团来完成。除前文述及的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外,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教育会等不同领域的代表社团,均在立法会占有议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利益回馈和政策咨询功能。 上述社团的三种功能,除了NGO功能和其他地区无异外,“拟政府化”和“拟政党化”突出了社团在澳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性。一般而言,NGO通常是针对特定群体提供服务,鲜有像街坊会联会总会这样提供广泛的跨群体的公共服务。其次,政党和NGO同属社会功能性组织中的一种,然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赢取选举和取得政府的领导权而产生,而澳门的选举却恰恰是以非政党化的社团为中心来开展的,参选人往往都具有丰富的社团工作经历,甚至本身就是社团的领袖。这两种特殊的功能,与澳门曾经历过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有着直接关系。澳葡政府是一个外来的政权,潘冠瑾形容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为葡萄牙派驻澳门对当地进行全权管理的总督服务的辅助机构”。它的管治权力来自葡萄牙皇室,而非澳门本土的市民,这使其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⑦因此,如果要对数目上占绝对优势的华人进行管治,单靠暴力压制不单成本高昂,而且不可持久。澳葡政府的做法是通过寻找华人社会代理人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的管治。⑧娄胜华将这种管治方式称为“相互赋权”,即政府通过赋予代表性社团某些“拟政府化”的权力,如某些代表性社团可以为商品签发产地来源证明、代征职业税、代办无证劳工登记及发给临时居留证等。而另一方面,市民赋予社团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政府进行谈判和协商的权力,社团同时为市民转介政府颁布的政策,使政策得以被执行和遵循。⑨ 需要注意的是,“相互赋权”只解决了澳葡政府和普通市民之间如何进行管治的问题,却并未提供不同领域社团之间如何进行利益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这一机制需要另外通过所谓的“蛛网式结构”来进行。表面上看,“蛛网式结构”和“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中一个功能性领域只能有一个代表的“顶级社团”(Peak Association)进行利益表达的情况非常相似。⑩不同的是,核心社团是自发建立的,而非澳葡政府授意其作为某一领域的利益代表。它们和次级功能性社团以及基层社团之间也非“国家法团主义”中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关系。因此,“蛛网式结构”事实上是一种在澳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在共同面对澳葡政府这个外来政权,以及在维护族群利益的前提下,这些社团往往可以通过协调和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内部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形成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11) 二、社团咨询模式的局限:美沙酮事件的反思 然而,“社团咨询模式”的有效运转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首先,这种决策模式形成的首要原因是澳葡政府为了维持管治和社会整合,而和华人族群所形成一种相互妥协和赋权的行为。但当澳门回归祖国后,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市民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外来政权,而是同根同族的华人政府,彼此在文化和语言交流上不再存有障碍(语言曾经是限制澳门市民和澳葡政府进行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大多数市民并不懂得葡语)。市民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讯息公布来了解到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讯息,社团不再是市民和政府之间进行利益表达的唯一管道,而仅仅是其中之一。社团和其成员之间本来存在的“委托—庇护”关系并不必然的存在。(12)若然原来的社团不再能有效的代表和反映自己的利益,社会成员要么另行组织新的社团,又或者选择不参与社团而成为独立于社团外的个人。由此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何澳门社会在回归后会同时存在社团数目快速增长(13),但市民参与社团的比例又偏低的情况(14)。 其次,社团咨询模式的另一个基石是“蛛网式结构”。自发秩序形成的“蛛网式结构”是通过社团间的协商和调解来维持的。这要求社会不同群体问的利益不能过分分化,否则就难以形成利益上的共识。然而澳门的本地生产总值在2004年后一直维持着双位数的增长,收入中位数也由2001年的5000澳门元增加至2013年的12000澳门元。(15)经济发展使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也快速发生分化,最为典型的即为本地劳工和外地雇员之间的矛盾。这使共识的建立变得困难,也更难进行利益调解和协商。另外一点较少为人关注的因素是回归后澳门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使澳门居民的教育程度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据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年龄在3岁以上的人口完成初中和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9%和16.7%,比十年前分别增加了11.1%和9.3%。同时完成小学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占34.2%,比2001年人口普查时减少了20.4%。(16)这对社会利益分化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根据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理论(Post-material Theory),随着市民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他们会更为注重所谓的“主观满足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会促使他们对政府提出更为个性化的政治需求,并可能进行更多的政治参与。(17) 上述社会经济因素的变迁一方面削弱了“社团咨询模式”赖以成功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使其未能有效的响应回归后澳门市民对治理的需求。发生于2010年的“美沙酮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决策模式的不足。“美沙酮事件”的源起是2010年5月澳门社会工作局公布的一则消息,内容是原来位于加思栏后马路的戒毒综合服务中心将被澳门卫生局收回用作兴建传染病大楼,因此社会工作局需要另外寻找新址兴建新的戒毒中心。其中一个美沙酮戒毒中心的选址位于澳门台山的澳门大厦。台山地区是澳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因此戒毒中心的消息马上引起了附近居民的关注和反对,并且迅速通过台山区业主联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和收集区内居民的反对签名。台山的居民认为戒毒中心的使用者将对小区居民的生活造成滋扰,并且中心的设立可能会影响澳门的旅游形象。在台山居民的反对下,戒毒中心计划一度搁置。随后社工局在收集区内居民意见和参考邻近地区经验后,在2010年11月决定把相关服务迁入黑沙环卫生中心。黑沙环卫生中心和台山一样地处澳门半岛的北部,所不同的是卫生中心是教育机构集中的地方,附近有数问中、小学和幼儿园,每日均有大量学生在周边的街道活动。于是中心的选址再次引起了附近居民和家长的反对,三次反对行动均集中在2010年12月。首先是12月4日约有二十名黑沙环区的家长代表向澳门政府总部递信和一千八百名家长的反对签名。他们质疑澳门半岛一共有五个卫生中心,为何要选择教育机构最为密集的黑沙环中心提供戒毒服务。其次,他们认为澳门政府在作出决策前并未充分知会受影响的家长和居民。12月8日,黑沙环多幢大厦居民在区内的宅地集会收集居民签名,后来集会演变成一场几百人的游行,居民通过阻塞交通的方式逼使政府直接对话。随后,澳门卫生局长与社工局代局长于当晚到场,再次指出决策是在参考了邻近地区的经验,以及咨询了相关社团和立法议员意见后作出。其后人群虽然逐渐散去,但据报道他们并不满意官员的解释。(18)部分居民随后再次通过参与12月20日的回归日游行的方式表达对政府决策的不满。虽然最后政府没有更改戒毒中心的地址,但是政府通过加强对美沙酮药物治疗的宣传,举行座谈会以及和学生上下课时段错开来提供服务,加强区内的治安巡逻等方式消除居民的疑虑并确保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至此扰攘时间超过半年的“美沙酮事件”终告一段落。 表面上来看,“美沙酮事件”的选址只是一件因为“邻避问题”而引起的公共纠纷。(19)然而从相关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可以知道居民主要的反对原因更多是因为认为政府在决策前并未进行足够的沟通,而且没有充分咨询他们的意见。(20)换言之,他们不满的是作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却被政府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因此“美沙酮事件”本质上是一场由决策模式而引起的纠纷。而有意思的是由政府官员的表态来看,相关政府部门明确表明认为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咨询。为何两者会有如此不同的认知?最为可能的解释是“社团咨询模式”的惯性使政府相关部门认为只要在决策的过程中咨询了相关的社团、立法议员和专家,就代表了该项决策同时具有了专业性和合法性。而由事件的演变过程来看,显然结果并未如预期般进行。在事件中政府部门一再为决策辩护的理由均基于专业知识,具体表现为相关部门在大量参考了邻近地区的相关经验后,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支持戒毒中心的存在非但不会增加,而且会有效降低犯罪率。过往的数据亦显示美沙酮服务能够有效减低艾滋病在澳门的蔓延。最后,对戒毒中心的地址选择是通过计算了戒毒服务的潜在使用者的数量,对服务使用者的便利和每日使用服务的人流量等技术指标进行的估算来决定的。(21)所有这些理由均合乎科学原则,并且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然而,正如我们在开篇提到的疑问一样,一个政策方案在技术上完全合理、具有效率、合乎科学原则是否就是一项合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答案恐怕并非是不言自明。政策方案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替代市民的价值偏好,而如果一项政策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它将难以得到市民的支持并有效的执行,结果非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更可能如“美沙酮事件”般使纠纷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选址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引起纠纷也反映出“社团咨询模式”的局限性。社团一直以来是联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它使政府可以在不直接接触市民的情况下获取来自社会的意见和声音。由于在“蛛网状结构”下只有有限的核心社团有机会和政府进行协商,协商的效率和可以提供的合法性取决于该核心社团的代表性。可以注意到在“美沙酮事件”中政府事先虽然已经向社团进行过咨询,但仍然引起了大量居民的不满。这使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下的决策模式进行反思。即它是否仍能适用于今天澳门的社会经济环境?社团又是否仍然能够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取态?事实上,在事件中澳门市民在反映自身要求上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表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社团作为他们利益的唯一代言人。正如“后物质理论”预期那样,随着教育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政府更高管治水平的期待也在提高,同时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逐渐展现。这些因素使“社团咨询模式”的有效性降低,政府需要找到新的决策模式来响应社会的这些新变化,从而再次满足公共决策对专业性和合法性的要求。 三、社团咨询模式的可能改进:新城填海公众咨询 2013年末,澳门的土地总面积是31.3平方公里,居民总数为60万人(22),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超过19000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土地资源的稀缺是限制澳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近年澳门经济快速增长,可供发展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因此澳门特区政府早于2006年就向中央政府提出方案,希望增加填海造地以作经济民生之用,最终于2009年11月获得国务院批复同意填海造地350公顷(3.5平方公里)。新填海增加的土地需要响应各个方面的社会需求。首先,是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所作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以及推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其次,完善交通基建设施,使澳门更好地和周边区域融合协调发展。最后,提升澳门居民的综合生活素质,包括响应公屋需求,提供更多的公共绿地,增加文体公共设施等等。(23)可以说,新填海土地不仅关乎澳门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承载了澳门市民的各种期待。因此,新城填海规划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城市规划,其根本问题实质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内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为了最大限度了解社会各方的具体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制订了一项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大型公众咨询计划。第一阶段为发展概念咨询,具体分为公共设施、城市宏观/整体规划、交通基建、环保绿化、旅游文化/多元产业等14个不同的范畴,目的是希望了解澳门市民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发展问题。第二阶段为地块的功能性咨询。新城填海增加的并不是一整块面积3.5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分成了大小不同的五个地段。因此,第二阶段咨询的重点是确定五个地段的具体功能。两阶段的公众咨询已分别于2010年6月至8月和2011年10月至12月完成。第三阶段咨询则会按计划在适当时间进行。 新城填海公众咨询最为值得关注是它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别于“社团咨询模式”,在新城填海咨询中特区政府除了一贯的社团咨询外,还使用了诸如公众咨询,社团、机构和小区咨询,专家座谈会/工作坊/研讨会,电话和电邮查询,电视评论,展览等多种形式的咨询手段。两个阶段的公众咨询一共收到了超过5000条的公众意见。(24)这样的决策模式和“社团咨询模式”相比拥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这种“专家+社团+公众”模式一方面使政策方案拥有了必要的专业性,但又能使政府的相关部门从市民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意见讯息,而且通过公众咨询、电话电邮等多种媒介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市民的意见回馈,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团咨询模式”可能代表性不足的局限性。因此,它在专业性、受众范围和时效三个维度上均要比“社团咨询模式”优胜。第二,通过公众咨询使受政策影响的市民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这事实上改变了“社团咨询模式”原有的政府和市民“相互赋权”给社团的情况。市民通过参与行为直接“赋权”给政府,这使政府的决策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同时更可能使市民满意和接受往后的政策结果。而政府主动把两阶段公众咨询的意见汇编在部门网站上公布,不但有助市民获取相关的政策讯息,同时也是服务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的体现,这又将鼓励市民未来进行更积极的公众参与(第二阶段公众咨询收集到的意见为3185,比第一阶段公众咨询增加近70%可以说明这点)(25),从而达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目的。 当然,新城填海公众咨询并非“十分完美”。首先,是成本问题。因为新城填海土地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一项三阶段时间、跨度超越三年以上的公众咨询项目。然而新城填海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纵使这种决策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但在有限资源(财政预算、时间、其他资源等)的限制下不可能要求政府对每项公共决策均采用类似的决策方式。因此,新城填海公众咨询虽然具有开创性和参考性,但无法在常规公共决策中频繁地使用。其次,是监督问题。即如何能够确保公众咨询收集到的意见最后能够在政策方案中得到反映呢?这不是说政府应该满足所有收集到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无论采取或拒绝接纳市民的意见均应该给出相应的说明和响应,并应该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公布,方便市民查阅和监督。这个体现政府问责性(accountability)和响应性(responsiveness)的程序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文本进行规范。而目前澳门在公众咨询中还没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因此,单就决策过程而言,新城填海公众咨询提供的是一种对传统“社团咨询模式”的改进方案和试验机会,但是如何使这样一种模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常规化和程序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四、政策咨询探讨和建议 “社团咨询模式”是澳门公共决策中常用的范式。这个因为澳门独特历史背景而形成的决策模式曾经在过往的时间里行之有效,不单有效地传达社会的利益要求给予澳葡管治时期的政府,并在市民和澳葡政府的相互赋权和“蛛网状结构”下维护了社会的低度结合及和谐。然而,随着澳门回归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致社会形态变动,“社团咨询模式”赖以成功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美沙酮事件”的案例清楚表明社团已经不再是澳门市民唯一的利益回馈管道,同时市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亦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区政府需要对既有的公共决策模式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城填海公众咨询引入多方面的利益回馈管道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方面政策议案在专家、社团和市民的共同参与下,使得方案的专业性和合法性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平衡。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公共决策模式可以有效刺激市民的公共参与积极性,这不单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也将提高市民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和执行。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新城填海公众咨询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常规决策不可能投入如此多的资源和时间进行决策咨询,因此在参考新城填海公众咨询提供的有益经验后,我们认为澳门特区政府或可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的公共决策模式进行改进: 第一,尽快制订公众咨询的专门性法规,详细规定公众咨询的范围、时间、文本的表现方式,以及相关的监督机制。使政策方案的公众咨询有法可依,避免目前各政府部门因为无法可依而“各自为政”的情况,这样既能增加政府决策过程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同时又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会质疑。 第二,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政策讯息获取的便利性。比如说参考内地地方政府部门开通政务微博的方式,对政府的相关决策情况和消息进行实时的更新,这样不但乎合年轻人口的讯息获取习惯,同时亦能吸引他们更多的关注公共事务。 第三,强化已有政策研究部门的公众咨询功能。澳门特区政府已于2010年12月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作为官方的专门政策研究机构,其职能被定位为“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开展调研、相关工作及研究;在评估、制订及跟进公共政策、发展计划及方案上,向行政长官提供技术及组织性质的支持,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高效决策的目的”(26)。因此特区政府可考虑适当增加政策研究室和社会进行互动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参考南京市“市民论坛”的做法定期举行政策论坛(27),由相关研究人员从科学和专业角度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解释,并接受市民的提问和回馈。这不仅有助于市民了解政府的决策,同时亦能从中获取市民的意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民主”决策。 注释: ①Howlett,M.,Ramesh,M.,Studying Public Policy: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Canad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9. ②[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③王锡锌:《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 ④Robert,N.,Public Deliberation in an Age of Direct Citizen Participation.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4(34),pp.315-353. ⑤《各方反思化解矛盾》,澳门:《澳门日报》,2006年5月3日;《澳门五一游行警民冲突开枪镇压》,香港:《苹果日报》,2007年5月2日。 ⑥⑦(11)潘冠瑾:《澳门社团体制变迁——自治、代表与参政》,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69、56、114页。 ⑧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⑨(12)(13)娄胜华:《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广州:《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⑩Unger,J.,Chan A.,Associations in a Bind: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Corporatism,in Unger,J ed.,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Contested Spaces,Armonk:M.E.Sharpe,2008,pp.48-68. (14)《社会认同感强烈社团参与度低社团生态呈变新兴团体冒起》,澳门:《澳门日报》,2006年12月23日。 (15)(16)《澳门2011年人口普查》,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1年。 (17)Inglehart,R.,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1-18. (18)《反美沙酮站签名会演变非理性抗争,五百居民堵路逼官对话》,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12月28日。 (19)娄胜华、姜姗姗:《“邻避运动”在澳门的兴起及其治理—以美沙酮服务站选址争议为个案》,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4期。 (20)《北区居民反对设美沙酮中心》,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12月21日。 (21)《当局增宣传美沙酮站效用 指黑沙环卫生中心为其一试点》,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12月7日;《指五年前咨询获主流意见认同在卫生中心开设 社局:设美沙酮站尊重病人权利》,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11月26日。 (22)《澳门统计年鉴2011》,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1年。 (23)(24)(25)《新城填海区规划第一阶段公众咨询意见汇编》,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工务运输局,2011年;《新城填海区规划第二阶段公众咨询意见汇编》,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工务运输局,2012年。 (26)《第375/2010号行政长官批示》,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2010年。 (27)梁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