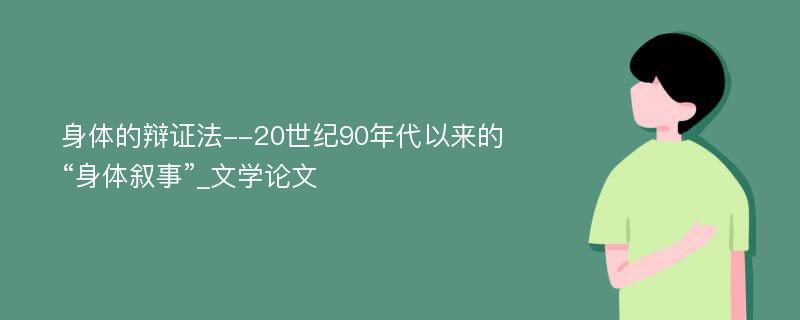
身体的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身体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辩证法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要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话题,恐怕非“身体”莫属了。作为这一现象的延续,21世纪初掀起的“身体写作”热,则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其描写更加暴露,而言词也更加大胆。所谓“身体写作”,其含义也就是叙述完全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身体渴求出发,并充满对自己激昂而骄傲的热恋①。热衷于“身体”,无限制地张扬“性”,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文学叙事中,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更是触手可及。这是个症候性的时代问题。“由于情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单一个体的单一特征,而只有或多或少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特征。每一个体一旦置身于适合的情境之中,都能够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情绪”②。因此,对充斥于“叙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进行分析,无疑是我们把握90年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叙事中的肉体至上现象,我们不是要做出道德、伦理上的界定,而是要分析其变化历程和生成原因,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这些方面有助于我们理清后现代叙事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审视文学危机的切入点,找出后现代叙事的问题所在。进而言之,“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③。这为我们分析中国9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性话语”泛滥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叙事中的身体
对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进行分析的一个有趣的切入口就是语言,从语言可看出看待事物的态度或观点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对“性”及身体的描述方式和言谈方式的变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的微观角度,使我们能够在变化中考察时代语境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赋予身体高度的政治意味。身体的能量被无限放大,身体不仅具有革命的指示功能,而且具有脱性别化的意味。最典型的就是女性自己的身体几乎被剔除,变成了同男性几无差异甚至在体能上超过男性的“铁姑娘”。身体自身的性别光彩被遮蔽了,相应地,情感也处于冬眠状态。80年代初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尤其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抗抗的《北极光》等作品,突出了女性性别意识的朦胧觉醒。这些作品展示出了女性那丰富、美好和充满爱的世界,但身体本身的魅力还并未从“男女平等”的呼声中得到彰显。性爱描写就更加稀缺。这与8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的转型和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有关。对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对人之生存的思考占据了叙事的主要位置。恢复和承认健康的人性,要求懂得爱和尊重,将精神之爱作为叙事的重点所在,这是新时期情爱主题的主要特征。而这些又是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肉体问题被暂时封存起来。新时期文坛上许多女性作家声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它实际上支撑起一种想象/幻觉:我们可以超越阶级、性别、种族,而共同面对“人类”的生存处境。这一想象实际上是当时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一种反映,其结果,便是导致了性别立场在新时期文化语境中一种结构上的匮乏。而反映在叙事语言上,身体也往往是以被遮掩的面目出现的,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描述:
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犷。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而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思考“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这一问题来得重要。发自灵魂的热爱远远超过甚至没有给身体的需要留下一点余地。
相比之下,张贤亮将“身体”从知识、理想、奉献等时代叙事中释放出来,就此而言,他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正是他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打开了“性叙事”的缺口,将肉体从长时间的休克中唤醒,引起了文学叙事中一场不小的地震。“他的小说给习惯于道德主题表述的知识界制造一枚重磅炸弹,也为当时感受到新的思想气息的先驱者提供热带炽烈的阳光”④。然而这里的身体仍未获得自己独立的位置,肉体的满足是为走上政治的红地毯服务的。而走上红毯之时,也正是与肉体迷恋的告别之日。在女性作家中真正体现了性别自觉的当属王安忆。其《小城之恋》充满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爱欲的描写,显现出通过躯体辐射出的女性话语的活力。但其描写依然充满了隐喻的色彩,如“她接触到温热的地板,忽然地软弱了”、“她将头朝后仰着,抬着眼睛望着那腿,腿上有一些粗壮而疏落的汗毛,漆黑地从雪白的皮肤里生出”,使叙述充满了美感并将身体审美化了。
叙事中的身体真正转型是在80年代中后期完成的。这种转型是在爱情主题与性之间进行的。先锋派和“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而“性”变成了叙事的原材料。它们若隐若现于故事的暧昧之处,折射出那些生活的死角。但在具体描写中与前面列举的“曲笔”法仍然保持大体上的一致。性描写,依然是欲说还休。进入90年代,性爱主题几乎变成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到90年代中期,性爱主题显然携带着思想的力度走向文坛的中间地带。这一转变与9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经过思想躁动的80年代,而又为后现代理论所熏染的中国文学,很自然地选取了“身体”作为叙事的突破口。
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们,赋予了性和身体以至高的位置。这不仅体现在对性意识的关注,对性的颠覆力量的重视,而且体现在随处可见的性话语上。不可否认,这种写作方式对长时期的“身体禁锢”是有颠覆作用的,并散射出强烈的反叛意识。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再执著于80年代的“男女平等”的人道主义主题,与男性处于对抗状态的主题已被消解,而代之以纯粹女性经验的叙事。“父”的经验被随时拿出把玩,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严肃性,并在讲述中充满了性的诱惑,如陈染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这样描述她与“母亲”的关系:“在黛二喜欢的词汇中,有很多令她的母亲恼火,其中一些是她的母亲终生也说不出的……比如:婊子。背叛。干。独自。麦浪。低回。妓院。”而男性作家如朱文则在戏谑父辈:“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意,我的性里都有。”(《我爱美元》)
然而这种单独世界的存在,很容易就将个人引向了自恋,而“性”几乎构成了与外部世界的全部联系。赏玩式的、窥视式的视角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中不乏其例。身体渐渐成了被观赏的对象,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描述了这样一副情境:
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然后站在镜子前,把衣服一件一件脱去。她的身体一起一伏,柔软的内衣在椅子上充满动感,就像有看不见的生命藏在其中。她在镜子里看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
类似的描述在90年代文学叙事中渐成常态。而叙述的直露和粗俗在沈浩波、李师江、伊沙等人的作品中更加突出,并成为文学中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有论者指出,“世纪之交,随着诗歌界身体写作、尤其是下半身写作潮流的浮现,身体不但被正名,而且成了膜拜的对象,成为肉体乌托邦的构造内核”⑤。身体在文学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身体的欲求和满足是至高无上的律令。“什么师道尊严,什么伦理禁忌,什么爱的誓言,都在爱欲汹涌的潮水中轰然坍塌,一切都要听从身体欲念当下的指令,都要在这尘世的天国中接受洗礼”。(徐坤《热狗》)
叙事中的身体经历了一个被遮蔽、颠覆反抗再到欲望表达的变化历程,其间的叙事逻辑恰恰就是社会变化的历史逻辑,叙事变化与历史变化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同构性。如果说张贤亮、王安忆、陈染、林白的作品体现出了身体的潜在意义和反抗功能,那么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叙事则将身体埋在了享乐谷,却又不时地把身体作为装饰另类姿态的东西来用。这反映出福柯所说的“性话语实践”中权力无处不在的事实。将性话语的生成机制与权力联系起来,这是对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和宏大叙事解构的结果。这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在这里,性被赋予了“革命”的符号功能,它变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中,人们津津乐道性爱的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快感;一方面,人们借助性来表达对禁忌时代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对性的公开、大胆的描写姿态,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信息社会,媒介就是权力——从而使一部分作家成名,跻身于“新潮”“时尚”的行列。性或由身体展示出的性诱惑,不仅暴露于文字中,而且在形形色色的画面里广为传播,围绕性组织起的话语网络将其原先羞涩的面纱无情地抛却,只剩下公开的隐私和赤裸裸的欲望。结果是,身体从被禁忌的对象变为人们表达“革命”意识和前卫的工具,处于又一轮遮蔽之中。或许,只要有对立,这种遮蔽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为美人塑形
特里·伊格尔顿指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⑥这些事物中身体无疑是其中既经典又感性的个别事物。所以伊格尔顿正确地提示了“一种新身体学的崛起”,他还不无谐谑地写道:“无疑很快在文学批评中的身体将比滑铁卢战场上的还要多。”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补充的是,正是由于文学叙事中身体的出镜数目无限增加,批评中的身体才会难以计数;同时,无论是对身体的赞成还是否定都为身体叙事提供了一种资本。当面对90年代文学叙事这样一个与时代精神结合紧密的文化形态时,其叙事中的身体是如何欲盖弥彰地体现出其商业性和大众性——这一涉及叙事策略的问题是我们分析后现代特征时无可回避的。在后现代语境中,“身体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如在体育运动、各种广告中,身体不再是旧有意义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商品形式”⑧。这已是无须论证触目可及的事实。同样无可辩驳的是,大多数身体注视又都集中于对“美人”的追求上,这使文学叙事中“为美人塑形”的叙事策略成为我们要分析的重点。
其一,在男性视野中“自由”舞蹈。
9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很少有像残雪作品中所刻画的滞重、丑陋和变态,也很少像残雪那样刻画出女性被逼挤、被扭曲了的充满自我挣扎和痛苦焦虑的意识世界。因此也就缺乏残雪作品中那种基于文学话语所带来的摧毁力。有论者指出,“残雪用非常个人化的女性语言,损毁了依附于父权制巨型话语之下的女性叙事。那些怪诞的女性感觉,打破了传统的以‘菲勒斯’(男性阳具)崇拜为中心的女性经验”⑨。
但残雪的作品明显缺少适应90年代文学语境和社会语境的生存能力,而使其成为女性写作中的另类。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女性身体不再被描画得丑陋,而尽可能地以最性感、优美、富有魅惑力的姿态出现。这些作品中的美女形象与大众耳濡目染的媒介宣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女人之美依然脱不了“他者”的塑形。不可否认,男性的眼光依然是评价“美与不美”的主要标准,但与传统文学中“美人”形象不同,后者是男性心目中女性理想的投射,而当代女性小说中的“美人”则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女性自己塑造的自我形象。这就是我在标题中所说“在男性视野中的自由舞蹈”的意思了。这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都离不开男性眼光的评介,但又有着为男性不能驯服的一面,或者说让男人焦躁的一面。这一方面反映出男性中心主义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将男性放在了被阉割的无力位置。如《上海宝贝》中的天天,朱文小说中的小丁,徐坤作品中那些教授和学者们。女性掌握了行动的主控权,使这些女性在拥有美貌和性感的同时更多了份独立、智慧和性格。
这些女性因为有了身体资本,并且有成为“美人”所必不可少的个性,而拥有了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按照女性自己的愿望述说自己的身体感受,终结那种由男人来说“她有一个身体”的被代言的历史。这无疑对传统的女性依附形象有颠覆的作用。正如木子美所言:“我是水,难以定型的水,生来就不甘寂寞地奔腾,一点都不顺利地、跌跌撞撞地奔腾,不知要到哪里去,一点主意都没有,所以我只有两种结局,变成了冰,或者有个很好的容器,让我继续是水,很精致的水。”⑩但这种叙事方式更多了卖弄和自恋的成分。对她们来说,似乎惟一完全真实的部分只是她们自身。
其二,身体环境的虚构与日常生活的脱节。
自恋,几乎是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共有特征。对这种倾向的流布我们需要作辩证分析。一方面,诚如弗洛姆所言,自恋是有积极作用的,并且适合物种发展的趋势,“倘若一个人不把其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放在他人之先,他又如何能得以生存呢?他将缺乏照顾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利己主义的积极品质。换一种说法,物种生存的生物利益要求其成员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恋;反之,个人的道德—宗教目标,却在于将自恋进行最大限度的缩减”(11)。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文学叙述中这种自恋倾向的物的走向。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后现代语境下后现代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缺少分享与互助时,自恋就注定要发展。但自恋发展的一个更为主要的条件,一个仅仅在最近十几年中才被充分估价的条件,是对商品的崇拜。作品中的美人不仅流连于肉体,而且沉迷于人造的高贵华美之中。时尚、前卫的装扮和消费包裹着她们的躯体,并成为其生活的全部。我们很少发现这些美人需要为谋生而发愁。而在对待身体的问题上,自恋者往往将个人的生物需要放在生活首位,这只会使人流于物的层面。
结果是美人形象的生成,大多离不开虚拟的远离生存需要的生存环境,或者多借助边缘生活形态赋予身体一种时尚符号特性,与日常生活则是脱节的。准确的说,与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它不是自由的身体,而在努力地雕饰一种体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尚观念。
女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存环境大都以白领阶层为参照,而这种生活又是商业广告极力吹捧的。二者的一致,透露出文学叙事与大众文化叙事的亲密关联。
其三,活用色情与文学之间的张力。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声言我拥有一个身体即是说:我能被视为一个客体,我努力使自己被视为一个主体;他人可以是我的主人,也可以是我的奴隶,于是羞耻与不羞耻便表达了意识的多元性的辩证法,它们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12)在如何有效运用身体与肉体、色情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上,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是很擅长的。他们很懂得在色情中添加一些文学性的佐料和解构的味道。
所谓的身体写作,除去其宣扬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的意图之外,其实就是修辞上委婉化了的色情文学写作,性或者性感当是身体写作追求的核心。这本来并不新鲜。但是身体写作者通过色情与文学之间的某种张力,从而使自己可以保持其先锋姿态,并像个楔子一样钉入到不断滑移的文学的符号秩序内部,使自己的话语实践得以凝固化,也就是占据文学空间中的一席之地。“身体写作者因此遵循着这样奇怪的悖论:她们尽管诉诸于性感化的身体,但是却以美学的名义拒绝承认自己是色情的,它自相矛盾地要求我们用文学来漂白她们的色情幻象”(13)。这样一来,美学与色情成了奇怪的同谋。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并不能对这种合谋方式背后的交换关系和炒作性有所损毁。他们的意见只是为成为身体写作者增加符号筹码的一份厚礼,通过他们,身体写作的问题性得以凸显,文学炒作的辩证法也以这种悖谬的方式得以生成。先锋与大众的结合透过身体写作呈现于后现代语境中,并成为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突出特征。
其四,坦白与装饰的巧妙搭配。
福柯在考察性史时发现,坦白机制既是人们获得一种稳定身份的方式,也是统治者实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在我们所分析的90年代文学叙事中,以坦白或者告白的方式来结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由此彰显出叙事者隐秘的社会需求。坦白,有时会以偷窥的方式来进行,从而收到揭秘的效果。
坦白,首先诉之于真诚意味。其潜在的意义是所讲必然是真实的。这也不失为一种写作的方式。然而如果自白最终不能被转化为对经验的深度认识和分析,这种表达就流于表面和个人的混乱。而当这些坦白大多借助另类的趣味、情调和作家的身份获得叙事的特权时,就使这些坦白具有了双重意味。即,将暴露与遮掩、放纵与审视、卖弄与反省并于一处。
靠坦白自己的隐私和性生活,来获得读者和市场的兴趣和关注,已经成为谋求快速成名的手段。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满足了人们对隐私的欲望,从而建立起话语交流条件;而当人们的快感被燃起的时候,又以超我的身份规避快感的权力,逃离它,欺骗它或歪曲它。9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诸如“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可以说就是灵活运用这一策略的最好证明。这些作家在获得媒体和市场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了大众的另眼看待,成为时尚潮中不断涌起的浪花朵朵。美人不仅“美”得令人艳羡,而且因为有了作家的身份和“美”而获得了发言的权力。
其五,开发身体的商业价值。
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美人的塑形过程是少不了大众文化的介入的。甚至于大众文化是起决定性力量的。“显而易见,在城市文化中,性欲已不再是压抑的主要对象。由于大众都倾心于成为‘消费者’,性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消费品(事实上是最廉价的一种),只能增加对幸福和满足的幻想”(14)。
商业之手对美人的塑形通常采取了三种策略。其一是使用局部包装方式,使女性的身体写作文本在形象符号的象征意义上被色情化,故意模糊身体写作与色情读物之间的原则界线,借以迎合一种不健康的窥视欲望。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初版时,其封面就被设计成具有春宫画意味的图案——一个无头亦无四肢的裸体女人。她作为一个纯粹的性符号凸现在封面上。其二是将具有暧昧意味的话题无限制放大,并以之充当该文本的广告。这种背景信息意在刺激以至“振荡”读者的购买心理。第三种策略是把“欲望生产”的基本要素,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传达给作家,从而内化为作家的叙事动机和意图,使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欲望生产”的基本要素进行身体写作。这一类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恋物癖、性诱惑、窥视欲、暴力事件、异国情调、跨国性交等等。
博德里亚指出,“美丽的逻辑,同样也是时尚的逻辑。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能量的、动作的、性的)和使用价值,向着惟一的功用性‘交换价值’蜕变。它通过符号的抽象,将完整的身体观念、享乐观念和欲望,转换成功用主义的工业美学”(15)。为美人塑形的过程,将时尚的逻辑演绎得出神入化。
三、双重视阈:先锋性与大众性
为美人塑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力量竞相在女人身体上增加附加值的过程。身体并未回复到尼采高扬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肉体”,或许这些增添的符号只是使身体更加远离自身,沦为为各种利益服务的工具。随着消费文化浪潮日胜一日的高涨,身体的革命性和独立性反倒成了被裹挟并用来装点的浪花。而在90年代的文学叙事中,身体不仅被用来充当女性争夺话语权的基础,而且成为赢得市场和受众的重要尺码。身体在叙事中的处境,由于其脱离了文学环境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更多地用来满足人们某种私密的欲望,而愈发艰难。随之而来的,文学领域被大众文化频繁地入侵,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文化困境和自身的生存危机之中。而这一切,正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生成的文学叙事本身所携有的特征。基于此,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在后现代叙事中的身体之处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这种处境的特征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白身体的指示功能。
我们的分析将从诗人沈浩波对“肉体”的尊崇中展开,“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我们更将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16)。这句话的特点是将“肉体”与“本质”划上了等号,并且有意将肉体作为推动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完全忽视了社会文化对身体的限制。我们无须强调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以及本质一词的形而上性和哲学来源,但就在这种口号下所创作的作品本身的粗俗、浅薄和对日常经验的原封不动的照搬来看,不仅理智和思想稀缺,而且语言的美感和文学的诗性之美被荡涤一空。若论解构的力度,这种写作方式无疑是强的。但其解构只是单纯地停留在物的层面上,而消泯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这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存在价值,从而加深了文学的生存危机。
沈浩波的话无疑是将身体等同于肉体。这已经远离“身体写作”的初衷,尽管二者都有着极具颠覆性的先锋姿态。埃莱娜·西苏以“身体写作”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她说:“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17)。如此才能横扫原有的句法学,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无法被攻破的语言。西苏的“身体写作”充满对男权体制的挑战和对女性存在的压抑的呐喊,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的激情质问。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身体是不可能停留在肉体欲望的满足之上的。沈浩波的一席话,透露出文学叙事中的一种庸俗倾向:将身体简化为肉体,使叙事为本能服务。其先锋性也因此而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只是向世俗表现出了迎合,使“先锋”简化为姿态而已。
但这种先锋姿态无疑为写作者赢得“另类”声名提供了有力支撑。大众文化市场对“新”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暴露身体和谈论身体不仅具有满足人的本能和情欲的功能,而且使“身体”成为一种行使话语权力的工具。很自然地,对“性描写”与“性活动”就具有了双重评价标准。一方面,为“身体”蒙上启蒙、革命、政治或美学色彩,借此隐喻个体“为了(向着诸如智慧、美德和真实性之类的渴望状态)转变自己”(18),将个体结构为精神自足的主体,其核心叙述词为高雅、执著、生命力等。另一方面,则强调身体展示、身体表现的自我表达法和“顾影自怜”的策略,引发消费者的自恋情绪。这些实践常常同引人入胜的社会及消费文化保持一种联合和颂扬的,而不是批判的(或者至少是反省的)关系。
这样的双重评价标准说明存在这样一种欲望:既想暴露自己的隐私,使自己曝光来吸引他人的眼球,又想控制并为这种曝光过程镀上一层美的光晕。用摄像技术看,就是在裸照(未加工的照片)上进行加柔光的处理。这种操纵自我形象的欲望,使得个体处在费瑟斯通所说的“自恋文化”之中,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展示或演示她(或他)自己。
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向人们发布的信息,与其说是一种虚幻的时髦生存方式,不如说是一个真实的情欲套餐,其中有两个基本元素——恋物癖和性诱惑。前者满足了人们对物的占有欲,后者则满足了人们的情欲和窥淫欲望。性的展示价值被大大张扬,而其得以实现的中介则是具有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的身体。在这里,身体被进行了一番商品化的处理,并被穿上了消费文化的内衣。一方面身体被欲望化,而性叙事仅止于赤裸的本能欲求;一方面又被赋予了精神性和抽象性意味,不时牵扯一些道德和审美的影子。但对性的欲望化处理和常常可见的消费文化的痕迹使后者显得画蛇添足。
这样的“身体”依然是在历史的脉络中为宏大叙事服务。男性话语依然处于统治地位,而使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始终处于被奴役和被观看的位置。以“男权制建立起来的性关系,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是强制和剥削性质的;在这一性关系中,性行为意味着对男性意愿的屈服”(19)。而且,“在性的周围,是整个一张多变的、特殊的和强制的话语网络。这是一种由经典时代强迫人们谨言慎行开始的大规模的检查制度吗?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调节有度的话语煽动”(20)。也就是说,一种现象具有它表面应有的意义,但它或许还表示着相反的蕴涵。90年代女性叙事从建立女性自身叙事世界开始,到着重于展示女性身体的美,逐步走向自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变化因素是媚俗和展示意味逐渐占据了叙事的中心。
也许“媚俗”一词,最恰当地表达出身体在叙事中的双重身份,既充当了树立形象的先锋,又同大众与市场暗通款曲。所谓艺术作品中的媚俗,用学者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话来说,“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假造的感觉”。它的本性在于“它的无限不确定性,它的模糊的‘致幻’力量,它的虚无缥缈的梦境,以及它的轻松‘净化’的承诺”,这赋予了它“一种取悦的力量;一种不仅能够满足最简单最广泛的流行审美怀旧感,而且能满足中产阶级模糊的美的理想的力量”(21)。之所以说它是幻象不是从艺术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着眼的,是说它整个的艺术世界就其自身而言有一种十足的虚假意味,是真切的艺术经验的替代品。其实这正是媚俗艺术的特性,它通过虚拟化的表面影像,成了“一种有计划、有意识地逃避日常现实的努力”。
女性开始展现自我独特的性别特征与美丽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这种个性展示的扩张的负面作用和极其媚俗性也不可忽视。与“出售”相连的“美”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因为融入了太多功利性的东西,其美必然会因占有欲的不断繁殖而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论述,对后现代文学叙事中身体的处境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身体不仅是从人的内部出发的一种要求,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许诺,但通过后现代语境运作的方式(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市场化的方式,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以现代媒体的方式,以学术理论的方式,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正日益成为一种后现代机器制造的欲望指令,一种超个人的普遍规范和对一切具体身体的普遍强制。它常常以反叛灵魂奴役和反叛政治奴役的先锋面貌出现,同时让我们获得快感。先锋与大众的结合,使身体在后现代叙事中成了百用不爽的宝贝。“身体的辩证法”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了快感,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
注释:
①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选《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②A.阿德勒:《理解人性》,陈太胜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③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④蒋晖:《当AI写作作中的性别话语》,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⑤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载《钟山》2001年第6期。
⑥⑦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页。
⑧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⑨陈晓明:《勉强的解决: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见《中国女性小说精选·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⑩木子美:《遗情书》,见www.bookhome.net。
(11)埃里希·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申荷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12)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页。
(13)朱国华:《关于身体写作的诘问》,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14)埃里希·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31页。
(15)让·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金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6)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页。
(1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第194页。
(18)玛利亚姆·弗雷泽:《波伏娃与双性气质》,崔树义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页。
(19)凯特·米莉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20)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2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5、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