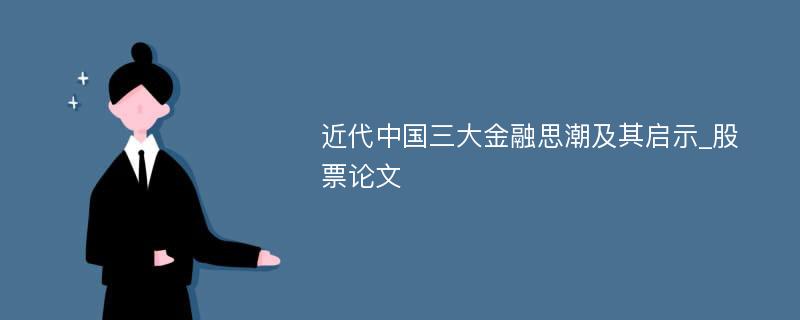
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潮论文,启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不平静的。其间有过多次狂风浊浪、震撼神州的大风潮,常常是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给当时全国的经济造成灾难。至于股市的大起大落则始终是它的基本特征。这类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的活剧似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传代,可以跨越世纪。
本文选取三次金融风潮略加叙述和分析。这三次风潮即1883年金融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和1921年交易所股票风潮。之所以选这三次风潮,不只是因为这三次风潮的规模比较大,对经济有明显的影响,而且还因为这几次风潮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过程中内在的问题所引起的,因而比较典型。
1883年的金融风潮
上海近代的股票市场,是逐渐从无形到有形、从分散到集中发展起来的。上海开埠以后,到上海来的外国银行都是股份制,它们的股票在19世纪60年代就上市了,只是那时的股市是无形的。1869年,外国人成立了一家长利公司,专门办理外国企业股票买卖和居间代理。后来,类似的公司逐渐多了起来。
华商的股份制企业,早先并无有形而固定的股市,股本的筹集往往是由创办人在生意场中“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股票的转让也往往通过私人渠道。
1882年9月,由于大批华商股份制企业诞生,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平准股票公司,代客买卖股票。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1883年的那次金融大风潮。
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中国的绝大多数财主原本是不屑于什么股份不股份的,甚至认为集股就是“劝捐别名”,“莫不视为畏途”。僳们对股份制企业是毫无知识的。但同样是这批人,当他们看到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股价涨至一倍以上时,“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麾之不去,一年之中,聚成公司一二十处”。他们投资于股市,绝不着意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他们之所以“争先恐后,贪得无厌”,唯一的希望就是“得股之后股价聚涨,即得出脱”,带有极大的短期性、投机性。
1883年的金融风潮实际上在1882年冬就已显露迹象,当时上海南北市钱庄和商业行号纷纷倒闭,亏空数万两至数十万两银子不等。其中对市面影响最大的是巨号丝栈金嘉记的倒闭。到1883年9月,北市纯泰、泰来两家大钱庄倒闭,再次冲击市面。1883年12月初红顶商人胡光墉的阜康钱庄倒闭,终于激起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市场再也无法支撑。1883年初,上海共有钱庄78家,到了年底则只剩下10家继续营业,其它都已停业或倒闭。一般商号“亏空闭歇者十居四五”。
1883年风潮不只限于上海,在天津、汉口、苏州、南京、宁波等地也都有发生,只是危机的程度低于上海而已。这是因为上海既是通商枢纽,又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
风潮既起,股市一落千丈,甚至到风潮过后近两年的1885年7月1日,招商局新股原价100两,股市仅58两;开平煤矿原价100两,股市58两;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原价各50两,股市各29.5两;其余各股大多跌落更多,有些股票甚至不能在股市上流通。轮船招商局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怕受战争袭扰,“暂寄”美商旗昌洋行,也就是由旗昌暂时托管,中法战争结束即行收回。主管招商局的当时中国著名商界领袖人物唐廷枢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股市风潮前,尽管中法矛盾已显端倪,招商局股价还有180多两,到中法战争结束以后,也就是股市风潮之后,招商局“生意极旺”,“股价反不及三分之一”。这种现象当然是人们看不懂的。开平煤矿一直经营比较好,股价也照样暴涨暴跌。几年前那些人气极旺的股民们此时又变得诚惶诚恐,避之唯恐不及。牛市时“各怀立地致富之心”,熊市时视若瘟神,千呼万唤不回头,这可以说是中国股民历久不衰的主导心态。
引起1883年金融风潮的原因很多,学术界见仁见智,大致将内部的原因归结为连年灾荒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正常运转,外部的原因归结为中法构兵引起市场银根紧缩等。但是根据笔者的观点,其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却不在这些方面。引起1883年金融风潮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商业资本对工、矿、交通运输等企业作了力不能及的过分投资,抽走了商业流通渠道中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银根,再加上其它一些客观原因,终于激起商品流通渠道的崩溃。据笔者统计,当时新设的股份企业资本总额约为677万两。这些企业成立以后,还需要配套的流动资金。在风潮爆发之前,部分股票大幅度升值,也吸收相当一部分社会资金。1882年夏季股市处于高峰,9月26日轮船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涨到了253两;开平煤矿原价105两的股票涨到216.5两;平泉铜矿原价105两,涨至256两;长乐铜矿原价100两,涨至168两;鹤峰铜矿原价100两,涨至155两;仁和、济和则分别从50两涨至71两和70两。股票发行、升值和股份企业新吸收的流动资金,估计总额在1000万两以上。这些资金的来源之一就是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的。而当时上海市面流通银两的总额只有约260万两。巨额资金转移,引起正常的商品流通环节受阻,金融市场就变得十分脆弱,一有风吹草动,竟会酿成大灾难。
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
时间会淡化人们的记忆。1883年金融风潮造成股市好多年的沉寂,但一旦气候适宜,股市又会重新涌动和疯狂起来,历史的活剧又会重新上演一遍。
1910年的贸易前景似乎特别好,市场繁荣、汽车工业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了橡胶业的发展。世界市场上橡胶由于供不应求,其价格处于频频上涨的趋势之中。由于橡胶的需求和价格持续增长,1903年英商麦边洋行在上海设立橡胶公司。这家公司获得了在华外商银行的支持,它所发行的股票可以在外商银行照票面押借现款。此例一开,后继者源源不断。特别是从1909年冬天开始,在六七个月的时间里,橡皮股票的市场价格涨势旺盛,使投资者盲目跟风抢买橡皮股票,也促使橡胶公司越开越多。到1910年,开设在上海的橡胶公司增加到40家。当时的海关关册有这样的记载:“上海股票公所之名簿上,该[橡胶]公司又加三十五,被撄资本银二千万两。且由上海兑款至伦敦购买股份者,为数亦甚巨。”在橡皮股票热潮中,上海的钱庄是唱主角的。它们不仅以大量短期贷款贷放给投机商人,而且自己也积极收购和持有橡皮股票。许多钱庄向外商银行拆借款项,用以购买橡皮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买进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融约在2600万~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约为1400万两,两方面加起来,投入资金的总额约在400万~4500万两。上海钱庄不仅将自己手中的资金都投入了股票市场,而且还从外商银行处拆借了大量资金投入股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维持市场的流动资金不够了,正常的贸易活动强烈地感到缺乏资金的支持。
1910年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出现持续下跌倾向,上海的橡皮股票价格也随之发生波动,从顶峰一路下泻。1910年3月,上海市场上10股橡皮股票的价格是70两,而到1910年9月至12月间,10股橡皮股票价格跌至7两,跌掉了9/10。当时积存大量橡皮股票的正元、谦余和兆康三钱庄,都被深深套住,资金周转失灵,被迫先后闭歇,亏欠款项达数百万两,牵连到同它们有往来的钱庄数十家,以及若干洋行。在上海的外商银行一见风声吃紧,马上采取一致行动,收回对钱庄的拆款,同时拒收信用动摇的钱庄庄票,这样就把危机推到了顶点。当时外商银行拆借给钱庄的款项大约1000多万两,这笔资金的收回,意味着市面融通资金被抽干了;而且,许多钱庄早已将拆借资金投入股市,此时无法归还,只好宣告破产。大批钱庄倒闭,还牵连大批工厂倒闭和大批工人失业。当是上海市区及近郊已经设有一批稍具规模的工厂,雇用了近30万工人。这些工厂的营运资金一直不足,是靠向钱庄借钱来维持的。钱庄出了问题,也就把这些工厂一起拖下了水。
1921年的信交风潮
所谓“信交风潮”,就是指因滥设交易所及信托公司而引发的金融风潮。
1921年秋冬两季,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了一股交易所(包括信托公司)热,各种各样、稀希百怪的交易所风起云涌,纷纷设立,交易所股票满天飞,成为一时的抢手货。上海成立最多,据报纸记载竟有140多家,额定资本2亿元。这2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25年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中国158家本国银行的实收资本与公积金的总和只有2亿元多一点,这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批五花八门的交易所极不规范,仅从它们注册登记的情况就可看出来。据字林西报报道:这140家交易所中只有10家经农商部正式立案,可称为合法,其它有2家是在驻沪军队系统立案的,有16家在法国领事馆立案,17家在西班牙领事馆立案,1家在意大利领事馆立案,2家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立案,4家在美国政府立案;而大多数则连任何注册登记的手续都没有办过,也未见有像样的规章条例、招股说明书之类的文件刊登在报纸上,就一哄而起,仓促上马了。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功能应该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资本的流动性;物品交易所则是为了保障供求平衡,避免市场出现大起大落。显然,1921年设立的这么多交易所并不能发挥上述功能,舆论说它们是“唱空城计”骗人。一地设立那么多交易所,其正常业务量根本不能保证,只可能专注于投机行为。而且,同上述两次金融风潮前的情况相似,原来在商业流通渠道的短期资金大量流入交易所股市,流入的金额即使不可能到2亿元,也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另一方面,分摊到每一家交易所,实收资本又嫌不够,难以自如地应付风险,所以流入交易所股市的资金是总量过大,而个别又过小。
由于大量资金流入交易所股票市场,上海金融市场的资金短缺就是必然的了。1921年底,银根突紧,人人需要现金周转,股票和公债普遍起了跌风,卖出的多,买进的少,交割时买进的付出现金,卖出的交不出现货,因此酿成了倒账风潮。有的交易所股票跌倒一文不值,投机家破产者不乏其人。上海商界认为交易所风潮不是一件坏事,认为这类“赌博恶疾”的交易所“愈不支”,则上海市面“愈有望”。最后,100多家交易所及信托公司关门大吉,剩下几家有实力有章法的勉强支撑住。从原来只有一两家交易所一下子增加到140家,其间的狂势可想而知;后来又一下子关掉一百多家,其间的悲哀亦可料想。
问题:为什么标金期货市场不起风波?
熟悉中国金融史的人可以知道: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的商业金融中心,是因为其工商业和金融业在国内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远东金融中心,是因为它的标金期货市场。该市场1926年的日成交量高达10万多条标金,年买卖总额达到6232万条,折半计约合150亿日元(当时日元差不多与中国银元同值)。
说起期货市场,人们一定认为其间充满了风险。大家对1995年“327”国债期货风波一定还记忆犹新。但是,国债期货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利率期货,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培育成利率机制和通胀率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利率期货的设计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人们对国债期货品种的预期完全缺乏合理的依据。然而,中国近代的标金期货市场却是市场本身在长期发育过程中找到的一条规避风险的途径。
现在我们的金融理论界有一种言必称西方的倾向,断言金融期货市场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固定汇率体系宣告结束,从而浮动汇率体系开始运转的结果。但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定之前,特别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有的国家采取金本位,又陆续弃金本位,放弃了又恢复,恢复了又放弃,有过几次反复。而中国在1935年币制改革之前,采用的是银本位货币。那时候金本位和非金本位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取消了金本位以后的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金银货币汇率、取消了金本位以后的货币同根本位货币之间的汇率,都是处于市场浮动之中的。特别是金银比价的浮动,在各种汇率的浮动中显得更为突出。市场感受到了金银浮动汇率的风险,并提出了创造新的金融品种和市场机制的规避汇率风险的要求。于是,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上海就出现了当时远东、也是全世界最先进和最发达的标金期货市场。从事国际汇总的中外银行、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外国洋行、通过洋行到国外采购并以外汇结算的中国厂家或商号等,共同需要这个市场、培养这个市场、规范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是当时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一。这个市场的交易量之大,甚至影响到世界市场的金银比价。但这个市场从未闹过大的金融风波。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投机的力量,投机与规避风险从来就是金融期货市场的一对孪生兄弟。但既然几乎整个中外金融业的主导利益是在这个市场的稳定之上,这个市场又是水到渠成地发育起来的,并不存在任何人为因素的强加,因而它就一直是相对稳定的。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是否稳定,并不在于是否有市场风险,而在于这个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否符合当时当地金融业的基本需要,是否适应当时当地金融业的基本状况。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是渐进性的,它不能超越阶段。
启示之一:资本市场要以资金市场为基础
股市不会单独成熟。股市不会率先成熟。
笔者考察了中外金融发展史,认为金融发展基本上是循着三大阶段递进的,即:资金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当然,这三大阶段可以出现交叉,但主要目标不能跳跃。资金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如果基础还比较薄弱的话,那么资本市场的超常发展就会出问题,就会闹出金融风波来。
资金市场的基础体现在规模、工具和机制等方面。
资金市场的规模,其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的M[,2]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接近于M[,2]/GNP,即货币化程度的概念。一国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非市场经济部门卷入市场经济,或者卷入的程度越来越深,在假设通胀率为零或某个固定不变的数值的前提下,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提高了。在中国近代银本位货币的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增长是缓慢的,有限的资金规模尚且不能应付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如果再大量转移到资本领域,那是资金市场所不能承受的。上述三次金融风潮,都是因为大量商业流通环节中的资金转移到股票市场后引起的。
这种资金的转移不仅在于它的绝对量,而且还在于它的结构。从有的风潮来看,资金从商品流通流域大量转移到资本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行为,它们会突然造成信用危机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掀起剧烈的金融风潮。
资金市场包括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等。笔者广义地将短期信贷、短期债券等所有短期资金都归入资金市场范畴;而将长期资金归入资本市场范畴。资金市场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它的规模上,而且体现在它的工具品种和运行机制上。只有短期资金的流动做到了安全、方便、快捷、有效,才能使长期资金的流动(即股市和中长期债市)获得品种和机制上的保障。当时中国的资金市场,除了规模较小之外,其拆借市场虽然比较发达,但带有明显的区域分割性,票据贴现市场则起步迟、交易数量小。短期信贷等都还处于初级阶段。至于企业的短期债券市场则几乎没有。
启示之二:企业发展状况不容忽视
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在企业。只有企业在总体上发展到一定阶段,股市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气候。
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还比较幼稚。首先是规模小。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晚、缺乏原始积累以及中外不平等竞争等原因,国人所办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同外国企业和进口产品不正面冲突。只有个别进口替代的竞争型行业,如棉纺织业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但在当时相对规模最大的纱厂,其资本额也只在100多万元左右,比起国外较成熟的企业来,自然相形见绌。
其次,企业制度还只是处在初步的发育阶段,还缺乏股市所需要的那种规范。中国近代的企业制度可谓五花八门,从企业的控制权的特点来看,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少数是非家族企业,如新式银行;从企业形式来看,既有股份有限公司,又有无限责任公司、合伙制企业、独资企业等。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集团荣氏的茂福申新总公司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因为他们不愿被有限责任制的董事会分散权力和受牵制。无限责任公司当然也就不可能到股票市场上去上市。所以上市的不一定是最大的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
再其次,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种种不利的社会条件,企业频繁出现停产、破产和产权转移,而缺乏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中国最大的行业棉纱织业恰恰同时又是最不稳定的行业。股票市场需要入市企业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企业的保障性非常差,股市也就随之而无保障可言。正如1887年正在筹备漠河金矿的李金镛所说:“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尤甚。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
启示之三:要看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否稳定
股票市场的成熟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制规模是否健全的问题。即使文字法规比较齐全了,它仍然会上下振荡,闹出风潮来。健全的法规当然应该包括文字法,但人为制定的法规往往表现出市场操作性弱和市场定位弱的缺点,因而它还应该让市场作用所形成的不成文的习惯和规范来补充和修正。
股票市场不仅需要上市企业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大环境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中国近代的军阀战争连绵不绝,破坏交通和工商业,造成社会动荡,这对资本市场的培育是很不利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会淹没一切的,它必然会对股市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不是恶性通货膨胀,只要通胀率高过两位数,资本市场也会受到相当大的不利影响。高通胀既会减弱企业的赢利能力,又会令投资者不再抱有长期投资的愿望。
战争和高通胀不利于股市,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有些经济和社会条件则比较隐蔽,如人们的市场心理。上述几次金融大风潮都同人们市场心理的不成熟密切相关。
人们渴望发财的投机心理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变动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开。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虽然也在不断进行,但毕竟比较迟缓,一般可以以“代”来计算,一个自耕农要成为一个大地主,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不健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军阀混战的社会条件下,极少数人可以很块地暴富,例如买办的骤富是令人瞠目的:刘鸿生当上开滦买办,一二年间就赚了80多万两子;郑伯昭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家产多达数千万;徐润做房地产,没几年就赚了几百万两,而比起他同时代上海房地产大王汪某来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而实业家们,无论是做生产的还是开厂的,无论是钱庄主还是银行家,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在短期内成为豪富。另有一类鱼肉百姓的军阀官僚,也很容易赤手致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军阀和官僚是积资最快、最富有的阶层。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别人的渐富,而不大能够承受别人暴富、骤富,因而失去心理平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在别的事情做不成或不会做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股票市场,希望通过炒股票,立地致富。以这样的股民为基础,股市必然是大起大落的。没有理性的股资者,就不会有成熟的股市。而理性投资者的培育是颇费时日的,它往往需要以“代”来计时。
启示之四:哪些人超脱于投机行为?
笔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发现:凡是开创事业的实业家,凡是形成气候的银行家,凡是除了权贵之外的最有实力从事股票投机的那些人,恰恰是最与投机无缘的。
投机可以骤富,而它的另一面就是骤败。这同资本主义的正当经营毫无共同之处,因而为事业有成的人们所不屑。近代华资银行在北洋初期固然是靠经营政府公债滋生和发育起来的,但一般说来,这还不同于投机行为。特别是华资银行的中坚,如中国、交通、“南三行”、“北四行”等,即使在羽翼丰满之后,也从不以投机为取向。尽管这些银行的主持人在事业的开拓上显示了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但涉足股市或证券市场,总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他们从不买空卖空,从不利用自己强大的实力操纵股市。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这样的:第一,他们一般多购信誉较好的外国企业股票和最热门的华资企业股票,特别是银行之间的相互持股;第二,对于所购置的股票,非但不作股市飞涨之想,反而在资产项上折价计算,所打折扣比市价低得多。他们不把证券买卖作为事业的基础,而只是作事业的补充。他们是作为最健康的法人投资者而进入股市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近代中国股市才会时而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而不至于永远处于非理性化的极端状态。
在一般情况下,中国成功的工业企业家们就更不去光顾股市的风光了。成功的企业家一般都是债务大王,荣宗敬、荣德生为了发展他们的纺织业和面粉工业,刘鸿生为了发展他的火柴、水泥工业,都是负债累累,旧欠未清、新债又起,连家产都拿去抵押借债,用于企业的扩展和经营。因而,从资金条件来说,投入企业,就不能投入于股市,两者不可兼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大量买进股票,那就是为了企业的兼并。
银行的相互持股、企业的兼并、银行和工业的相互交融,这体现了股市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近代中国的股市是由两股潮流汇合而成的:一股是投机潮流,一般是合乎经济规律和发展要求的潮流。这两股潮流既相生,又相克。而前者远远超出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可能体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