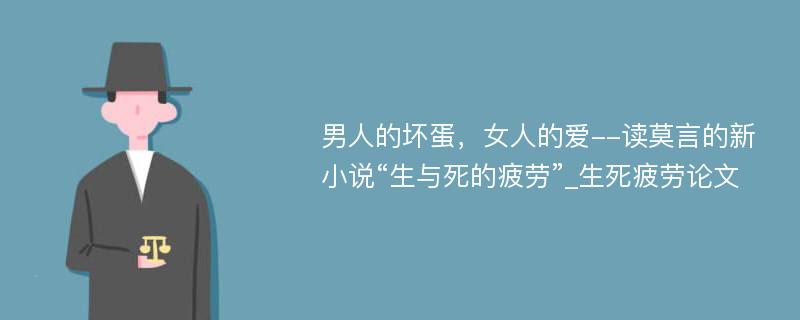
男人之坏,女人之爱——读莫言长篇新作《生死疲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论文,新作论文,之爱论文,疲劳论文,生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莫言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借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重述新中国的土地历史,其中透露了被男权操控的女性不自觉的悲剧命运。西门屯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依次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生活在前世亲人及其后代身边,目睹并参与了半个世纪女性的悲剧。作者莫言缺乏对女性境遇道义上的悲悯情怀和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批判意识,反而热衷于“男人之坏,女人之爱”的男性叙事,宣扬男性寻欢作乐和女性附属观念,表现出作家主体精神的颓废。
白氏、迎春、黄秋香是经历新旧政权制度更替、处于历史和家庭边缘位置的一代女性。她们曾为地主西门闹的妻妾。作为正妻的白氏,贵为大户人家千金,由于不能生育而主动将陪嫁丫头送给丈夫收房。因此,她遭受独守空房的冷遇。尽管如此,她对丈夫仍忠贞不渝,土改时誓死不泄露丈夫藏宝处,在以地主身份参加劳动改造期间还一直怀念被枪毙的西门闹。摘掉地主帽后,白氏不忘老支书洪泰岳多年的照顾,出于感恩表达了与洪泰岳共同生活的意愿。醉酒的洪泰岳一面骂她仍是地主,一面流露深情要占有她。这时,经过驴、牛两世轮回为猪的西门闹咬掉了洪泰岳的睾丸,白氏因此自缢。西门猪为自己的恶毒开脱,认为不能容忍洪泰岳的侮辱,他自己为人时何尝没有在打过三姨太秋香后又与其共赴云雨呢?西门猪所谓动物性的偶然,正是他曾经为人时其占有欲在作祟。他口口声声后悔生前亏待了白氏,当白氏在他死后多年另有所爱时,嫉妒的怒火令他不计后果地实施了报复。
迎春是西门闹的二姨太。西门闹投胎为驴时,他回忆自己被枪毙那天迎春没去送别是由于她怀孕即将临盆。实际上,迎春为他生孩子是他死前一两年的事了,当年他曾因迎春生下一对龙凤胎儿女而感到喜悦万分。传宗接代的任务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以致迎春的生育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这才使他的记忆出了差错。迎春是在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层面上才被偏爱。为了地主后代金龙、宝凤的前途,迎春解放后改嫁给雇农蓝脸,又生了蓝解放。岂料蓝脸违逆全民集体化的潮流,坚持单干;虽然这与后来分田到户的政策偶合,但蓝脸执拗的个性使他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也使迎春失去的幸福无法挽回。一直深为他俩床笫之欢痛苦的托生为动物的西门闹对其分居“略感安慰”,因为迎春是他为人时的“财产”,他关心的不是迎春的幸福,而是她是否被别的男人侵占。
黄秋香作为西门闹的三姨太,被丈夫视为搬弄是非的风骚女人和玩物。秋香在清算大会上说自己为西门闹强占且没为他赴黄泉送行,因此多次遭受在畜生道轮回的西门闹的抽打。秋香所居住的东厢房土改时分给黄瞳后,她明哲保身做了黄瞳的妻子,却又与他人偷情,开酒馆时又甘愿受人轻薄,可见,她并不爱黄瞳。后来她在黄瞳病死的当天夜里吊死,令人觉得莫名其妙。叙事者并不真正关心她的喜怒哀乐。秋香遗言要求把自己安葬在西门闹与白氏合葬的右侧,她认同和回归的是曾经被宠又不受尊重的姨太太的生活和身份。
西门闹的这三个女人无论个性是本分还是风骚,出身是高贵还是寒微,身份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命都无不残缺。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里,共同服侍一个丈夫意味着她们处于弱者地位。而她们却习惯于服从的生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平等。她们彼此之间缺乏同为传统文化牺牲品的体谅,更多的是争风吃醋的不和。作者对此很少反省,反而以轮回的方式为一种“男尊女卑”的制度辩护。
白氏、迎春、黄秋香一生中最爱的都是地主西门闹,原来的家庭结构对她们来说远比重建要幸福得多。尽管她们是以生命的全部回应丈夫不完整的爱,但为其所苦是她们自愿的事。对于西门闹来说,付出的连残缺的爱都谈不上。他完全是为他自己。他需要他的女人们无论肉体上,还是情感上都要忠贞于他。轮回给了他监督、报复的机会。投胎为动物的西门闹阻碍大太太和洪泰岳结合、痛恨二太太和蓝脸之间有性爱、惩罚三太太由于她自我保全而表现出薄情。说白了,西门闹对他的女人们没有爱,有的只是作为财产的占有欲;他不把她们视为有着同等情感、身体需要的女人,而是视为工具或宠物。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乌鸦》中田木根老头临死前不放心自己年轻的妻子,把监督的任务交给一个壮汉,结果弄巧成拙;《生死疲劳》里,叙事者在西门闹死后,赋予他亲临干预的机会。尤凤伟的另一部短篇小说《合欢》与《生死疲劳》题材类似,都是为“反面人物”翻案,都写到了土改对地主家庭的冲击。所不同的是,《合欢》中流淌着温情和希望。地主夏世杰全心全意地爱着小老婆吕月。吕月被重新分配给贫雇农夏发子也带不走夏世杰的牵挂;而大老婆离去,夏世杰落了泪,没有挽留。夏世杰和吕月由于爱情无望,交欢后服毒而死。作品的震撼力来自作者对当时极左革命思潮的大力批判以及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心。作家莫言缺乏的正是这份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关怀。
西门闹被枪毙后,两个姨太太分别重建的家庭通过子女联姻又结成亲家。秋香双胞胎女儿互助与合作分别嫁给迎春的儿子西门金龙与蓝解放,却都只爱西门金龙。后来蓝解放和庞春苗发生婚外恋情,合作不愿离婚又无力干涉,最终原谅了他俩。而互助即便如愿做了金龙的妻子,丈夫却和庞抗美生有私生女庞凤凰。在这些复杂的情爱关系中,我们很难看到新中国的女性在摆脱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束缚的同时所应该获得的家庭权利和精神自主。相反,封建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乃至新的一夫一妻制度不仅不能保障女性的幸福,反而使她们以新的牺牲方式成全了男人们实质性的享用。女性不能找回自身的精神性别,“三妻四妾”时代的很多悲剧仍在重演。
毋庸置疑,作家笔下新时代的女性明显沿袭着传统女性的性格和命运。她们同样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把选择权交给男性。她们的爱往往也就一厢情愿而卑微地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被男人们当回事。宝凤在常天红失意时才有机会。合作明知金龙喜欢姐姐互助,却与他发生性关系。之后叙事者对合作的不幸境遇同情中夹杂着厌恶。其实真正令人厌恶的是金龙,他不娶合作也就罢了,还当着她丈夫的面开她粗俗的玩笑;他和互助结了婚,却去俘获时任高官的庞抗美做他的情妇,为他生孩子、犯错误、自杀。叙事者不仅为金龙开脱,还把金龙和这三个女人先后在杏园的缠绵描写得如诗如画。然而金龙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能是一种伪生命力的表现。
女性近乎自虐的爱和男性近乎炫耀的自得,透露出叙事者对于女性的冷漠。叙事者在美化男性的同时,全不顾惜女人们的牺牲。为了成全蓝解放和春苗的恋情,叙事者让他的妻子合作患病而死;为了圆蓝解放早年喜欢互助的梦,又让比他小二十岁的春苗被车撞死。庞抗美的女儿凤凰早知肚里怀的孩子是乱伦的果实,会带有生理缺陷,还要在车站地下室把他生下来以致自己付出生命代价。这些女性的死,不是故事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叙事者将无法解释的一切归之于神秘的命运,显得局促无力,轮回最终成为作者理念的演绎:被伤害的女人们只配拥有可怜的命运,而伤害人的男人们永远可以得到想要的女人。
学者徐岱在一次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的讲座中说,《女性的发现——论1919-1949年现代女性叙事》这一论题可以“男人之坏,女人之痛”作为结语。不同于现代女性叙事对女性自身痛苦体验的关注,作为新时期的男性叙事,《生死疲劳》表现的则是“男人之坏,女人之爱”。面对男性的侮辱和损害,女性却爱得死心塌地,把自身不幸归结为“命”。苦难对于她们是一种外在强加的东西,也就不在其内心展开。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她们精神上的奴性特征和弱势地位一如既往。叙事者从不关心女性命运,也就不会批判她们浑浑噩噩、不觉醒的麻木状态。
正如书名所提示的,《生死疲劳》只是描述一种生生死死的生存悲剧而无意于批判造成对女性合围的集体无意识;这就使轮回成为重复,轮回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或推进的层次感。我们当然不认为作品中女性的觉醒程度和作家的性别意识成正比,但如果一个作家在新时期仍然津津乐道于坚持男性价值谱系所设计的性别规范,并将由此导致的女性独立的丧失和悲剧境遇归结为轮回和命运,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莫言在创作《红高粱家族》时,对文本中暗含的传统性别秩序尚不自觉;而至《生死疲劳》,则流露出男性视角从骨子里对于女性不尊重,显示了莫言由于不关心女性命运而面临的创作困境。通过自觉的“男人之坏,女人之爱”的叙事,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力趋向萎缩、文本的裂隙不复存在;更要引起警惕的是,这一叙事最终走向的是人性的禁锢而非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