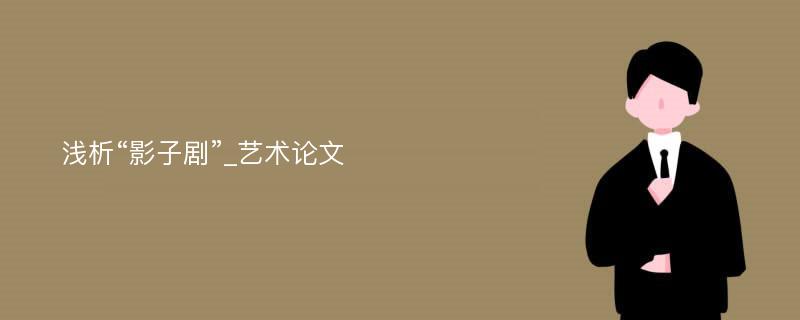
“影戏”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80年代,“影戏”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或美学范畴,一时间成为中国电影美学和历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它努力探寻电影与戏剧携手或联姻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渊源,探讨这种结合在中国电影早期本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阐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电影美学形态和艺术传统的独特内涵,开阔了中国电影史学的理论视野。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研究思路,成为许多中国电影史著述的依据和参照,被反复言说和继续引申。有的研究者由于对历史不甚了解,又不愿做深入研究,或人云亦云,或自说自话;有的夸大其词,说“影戏”是中国电影核心美学和创作主流,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有的则全盘否定,说“影戏”使中国电影自幼拄上戏剧拐棍,造成发育不良。真是成也“影戏”败也“影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究竟什么是“影戏”?应该怎样理解和评价它?早期电影与戏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明白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成长发展道路。现将我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加以重新梳理并作进一步阐释,供对此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批评。
电影传入中国后,名称竟多达二十来种,这在世界电影史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这一舶来品的陌生而又新奇。“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却大同小异,这样同一事物,而有各地不同的称呼,也不过习惯成自然,顺从各便罢了。”“直截了当,自以‘影戏’和‘电影’为是。”①“电影”和“影戏”最为普遍,并彼此通用。被视为“影戏”理论经典著述的侯曜《影戏剧本作法》中,就既曰“影戏”又叫“电影”,不分彼此。所谓“影戏”观念或理论,是由电影名称生发演绎出来的,但事实上名称不能说明实质问题。30年代“电影”取代“影戏”,难道电影观念因此发生根本转变?
“影戏”这一名称,是初期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中给电影寻找对应物的结果。“在中西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时候,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新事物、新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反身于历史传统去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因为‘当自己的历史记忆发掘出了这些资源的时候,无论对不对得上榫,接不接得上头,那种新知带来的文化震撼就会被抚平。’”②舶来品通过被重新命名而接上了中国血脉,顿时由陌生变得亲切起来,迅速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都市中的时尚娱乐和文化消费。
如同名称纷繁一样,电影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探讨最为自由最为活跃,是真正可以称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电影引起了人们广泛兴趣,也激发起他们认真思索。电影是什么?不同人生态度,不同艺术理想,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各种观念和理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人生、为社会的“功能论”。郑正秋提倡“有主义”之影片,以改造人生、批评社会、启迪民众。③侯曜坚持“表现人生”、“批评人生”、“调和人生”、“美化人生”的艺术主张。2.以画面为语言的“本体论”。欧阳予倩强调电影是“光和影的艺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段,是“一种独立的艺术”。④3.戏为本、影为表的“影戏论”。顾肯夫最早提出这个观点,“既名影戏,自当以戏为主体。所谓影戏者,以影传戏也,戏为主而影为宾也”。⑤周剑云认为“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术照下来的戏”。⑥4.美是第一、以美为上的“形式论”,被视为“怪美”的,但杜宇因画美女像闻名于世,其影片以美为特色,开了新派电影风气之先。史东山强调,电影要再现美创造美,“无论‘天然’的美,‘人造’的美,都能在银幕上有调有序的表现出来”。⑦5.制造梦幻和超现实的“造梦说”。郁达夫认为电影能够表达自幻意识,“美应当超现实”。⑧田汉说电影“白昼的梦”,“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⑨6.纯粹把电影当做商品和消遣品的“娱乐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10)是其典型而极端的说法。
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比较重视电影的商品属性和商业价值,关注市场需求和观众反应,从而推动了电影商业化发展,形成第一次中国商业电影的创作高潮。
这些观点是中国电影理论的雏形,在内容论述上比较零碎、感性,缺乏系统,有的混杂不清,甚至自我矛盾,但经过梳理和归纳,其基本理论形态还是清晰可见的。这是多么丰富的理论资源,多么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它们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都起到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和作用,比较而言,“功能论”和“本体论”可能更为重要也更为深远。前者是由于有文以载道、致世经用的文化传统的深厚基因,后者是因为中国电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艺术本性的探讨和研究。
按照江浙一带方言习惯,“戏”并非仅指戏曲戏剧,也有游玩嬉戏的意思。最初人们称电影为“影戏”,是认为它和“把戏”(杂技)、“戏法”(魔术)、“马戏”(马术)一样,都是一种供许多人一起观看的演出,并非意味着一定将之规范为戏剧。早期电影大多是记录生活场景和动作片断的短片,缺少完整的人物故事,不具备戏剧的基本原质。如果要说观念的话,透露出来更可能是一种杂耍观念,与早期西方电影观念并无多大差别。电影放映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和欣赏趣味,“奇妙幻化”、“古今未有”、“乍隐乍显”、“目给不暇”,(11)犹如身临其境,比戏剧演出更刺激更震撼。这种感受,如卡努杜所说:“从电影最内在的本质,即作为演出这个本质去理解电影”,(12)是对电影本质的最初感受和直观认知。
演出需要借助表演,而表演正是连接电影与戏剧的纽带。在表演上,中国电影最初没有借鉴传统戏曲,而是照搬了文明戏的技巧和经验。在日本“新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明戏,是话剧的雏形,其演技是中国现代表演艺术的滥觞。与程式化虚拟化的传统表演相比,它在形式和风格上接近生活,比较写实自由,具有现代气息。如《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所说:“从表演上看,‘甲寅中兴’之初,由于从‘言论派’的化妆演说转向描写情节,刻画人物,加上商业竞争的需要,刺激了一批演员钻研演技,熟悉各阶层市民生活的特点,因此,舞台上从老爷太太、书生才子、小姐丫鬟,直至媒婆、妓女、和尚、流氓、小贩等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演的颇为生动逼真。”(13)同时由于受到舞台条件和剧场环境限制,它也越来越变得夸张造作呆板僵化,很快令人生厌而遭到批评。20年代中期由此引发一场讨论,焦点是舞台表演与银幕表演之异同。郑正秋指出舞台和银幕的空间和视点不同,表演上“影戏和新剧,是截然不同的”,“新剧家要做影戏,有万万不能不牺牲他原来的做作,来另换一种合宜于影戏动作的必要”。(14)照搬文明戏表演与电影格格不入,电影表演必须符合电影特性,适应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段。萌芽期中国电影以文明戏演员为表演主体,他们成功地刻画塑造出第一批银幕人物形象,推动中国电影表演的形成和发展。进入20年代,开始起用非文明戏演员,他们自然质朴的表演,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此,郑君里后来评价说:“不管当时演技的水准怎么样的低落,电影演技的新的本质已经陆续地,一鳞半爪地从当时一些比较接近电影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的出品中流露出来。当时渐渐有一些不假助舞台经验而成功了的新的电影演员(如王汉伦女士等),而且,这种成功在电影的技术观点看来,是跃出了文明戏演技的体系的一种新颖的,比较写实而自然的形式,达到了新剧家的表演习惯所及不到的限度。”(15)经过不断实践提高,他们成为中国电影表演的新生力量,并涌现出像阮玲玉、金焰、胡蝶等等众多堪称世界级的电影明星。
郑君里说:“从初期中国电影用文明戏演技作表演的主体,中间夹着电影演技自身的长成,以至于后来文明戏演技为电影的手法所渗透,变革,进而丰富其原有内容,这是中国电影演技的一条辩证法的发展的路。”(16)文明戏演技为电影表演奠定基础,电影表演对文明戏演技进行革新,在它们共同努力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健康发展。
如果说“戏”所表明的是中国电影最初通过借鉴文明戏的表演而获得外在的演出形式的话,那么随着电影自身进化与发展的需要,其最重要的深层内涵和实质乃在于叙事。顾肯夫说:“影戏之主体在戏,戏即描写也”,“描写剧中一人一事一物之个性”。(17)所谓描写者,乃叙事也。
“在电影机诞生的同时,就产生了将影片首先用于讲述故事的想法。”(18)不再满足于对一个个日常动作的简单复制,而选择一连串有目的动作的视觉叙述,电影需要合适的组织结构和表述方式。然而银幕和胶片没有能够提供现成的这一切,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把它们发明创造出来,借鉴甚至搬用早为人们熟知和喜爱的其他姊妹艺术的叙事经验,是电影成为视觉叙事艺术的必由之路。
电影首先从戏剧中找到灵感,戏剧为电影提供了叙事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技巧。梅里爱把电影与戏剧结合,使电影接近了艺术。向戏剧借鉴叙事方法,是世界电影早期发展的整个走势,中国电影也不例外。郑正秋是位新剧家,掌握编剧诀窍,了解观众欣赏需求。他说:“最好取材要取得戏里面常常有风波,反反复复,高低起伏要来得多。”(19)“戏剧情节,不宜率直,求其曲折,必须多所映衬,旁敲侧击。尤当注重,烘云托月,分外动人,悲痛之至,定当有笑料以调和观众之情感,苦乐对照,愈见精彩,此穿插之所以重也。”(20)追求戏剧的传奇性,情节曲折,有头有尾,起伏跌宕,大喜大悲,出人意外又意料之中。《难夫难妻》(1913)以前一直以为是从媒人撮合到洞房花烛一场包办婚姻种种旧俗陋习的记录而已。但据新发现的史料表明,这只是开头部分,后面还有大段的故事演绎:新郎婚后迷于赌博,输个精光,夫妻大打出手,争相摔砸器物,仆人驰报双方父母,两亲家一路上互相埋怨拉拉扯扯,及至赶到,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小夫妻和好如初。(21)起承转合,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有铺垫有高潮,矛盾解决,圆满结局。其后郑正秋运用多年积累的编制新剧的成功经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影片,针砭时弊,惩恶扬善,开了社会伦理剧情片的先河。侯曜信奉易卜生,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借用西方近代戏剧剧作理论和技法,强调“没有争点就没有戏剧”,提出“危机,冲突,障碍”构成戏剧矛盾三要素和“起头、最高点、结局”三段体结构形式,以激烈的冲突,曲折的情节,复杂多舛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感动人心。(22)他编导的《弃妇》(1924)和编剧的《一串珍珠》(1926),以人物与命运的抗争推动情节的发展,揭示妇女地位低下和思想道德沦丧,“移风易俗,针砭社会”,体现了侯曜“问题剧”电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
然而电影与戏剧是不同的艺术,“戏剧是舞台艺术,是用演员在舞台上演给人看的;电影是一张一张的照片连起来映在银幕上的”。(23)电影突破舞台的限制,享有充分时空自由。从叙事角度讲,电影是用现在时语言讲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具有非现实性,与戏剧的三一律原则相悖,而与小说相近。所以除戏剧外,早期中国电影也从小说、故事等文学作品中学习叙事方法和技巧,直接把传统故事流行小说搬上银幕。1926年8月晨光美术会举办文艺讲演会,田汉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影戏与文学》的讲演,他说:“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格雷菲斯的发明,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24)还借用《红楼梦》中一边黛玉焚稿另一边宝玉成婚为例,来说明格雷菲斯“两面的描写”即平行蒙太奇技巧。他提出电影可以借鉴文学的叙事技法,避免戏剧的有头有尾、平铺直叙,通过暗示、省略和渲染,运用特写镜头、蒙太奇等电影手段,描写心理刻画性格。他的影片《三个摩登女性》(1933),采取了与“一人一事”截然不同的叙述方法和故事结构。夏衍认为电影可以在“连续的空间”展开多个场景,突破时间限制表现不同事件。他说,“在电影的故事叙述(Story telling),也可以像小说一样的驱使那回想的方法,来进行时间的转换”。应改变“亘古以来被认为无可更改的那种以时间为函数(Function)而发展故事的叙述法”,采取“进一步地和小说的叙述法接近的方法”。(25)他对影片《城市之夜》赞赏有加,“全部电影中,没有波澜重叠的曲折,没有拍案惊奇的布局。在银幕上,我们只看见一些人生的片断用对比的方法很有力地表现出来。其中,人和人的纠葛也没有戏剧式的夸张”。导演把一个“非戏剧式的故事”,拍成具有“特别的力量”和“特别的味道”的影片。(26)他创作的影片《狂流》(1932)运用了白描写法,根据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被认为是一部“剧的成分太少”的“纪录电影”。(27)
讲故事的技巧和传统包括戏剧和文学,早期中国电影与文明戏、鸳鸯蝴蝶派等流行小说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结合,既是进行题材的拓展,又是展开叙事的历练。中国人有着酷爱传奇的欣赏习惯和传统,电影作为新兴艺术,必须适应和满足这一观众需求。有了叙事,电影才能成熟起来,有了市场,电影才能生存下去。
麦茨曾经说过:“电影不是由于它是一种语言,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由于它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才成了一种语言。”(28)没有叙事,恐怕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叙事促进了电影的进步,电影的表现潜能在叙事过程中被不断发掘,电影的艺术形式逐渐完善,使它最终摆脱单纯实录而成为一门现代艺术。一部电影艺术史,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就是电影与叙事的结合从幼稚走向成熟、由单一趋于丰富的演进过程。不同艺术形式有不同的叙事模式,文学采用叙述,戏剧采用演示,而电影采用呈现。
综上所说,无论是表演还是叙事,电影从戏剧中都得到宝贵的启发和滋养,若干年后费穆心有感触地说:“一种模仿,需要一些初步的技能。中国电影的最初形态,便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而出现。这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中了文明戏的毒,毋宁说受了文明戏的培植。”(29)同时他又指出:“电影艺术也应该早些离开戏剧的形式,而自成一家数。”(30)电影既要与戏剧结合,又要与它疏离。戏剧这根拐棍,早先帮助了中国电影踉跄学步,后来又成为阻碍它继续前进的绊脚石。麦茨说:“所有的初期影片和而后的许多影片实际上都受到过戏剧的影响,以至于逐渐摆脱这种影响的历史几乎就是早期电影的历史。”(31)中国电影同样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与戏剧结合而又脱离的辩证关系。
1994年我在《关于中国电影理论》一文中曾说过“‘影戏’之谓者,实乃本意在‘影’,而不在‘戏’也。”又说:“‘影’者,‘影子’也,亦即‘活动影子’之谓也。”早期众多电影名称中大多离不开一个“影”字,有人直接提出“影”是“电影的根本”。(32)“电影”很快取代“影戏”,这一命名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戏”反映的是电影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影”体现的则是对电影本体的中国式认知。
在布鲁斯·F·卡温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佐证。他说:“大部分国家是以‘运动’加上‘书写’,类似‘cinema’的意思来指称电影。然而,中国人却有个极有趣的名词‘dianying’(电影),意思是‘电的影子’。这个词强调的不是影像的内容(不论它是动的还是静止的画面),也不是它的纪录过程,而是观众在电影院所看到的东西:当电所产生的光被放映机的景框挡住并被过滤掉,影子便投在银幕上。它所指的,几乎和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第七卷中所述一样。柏拉图将世界比喻为洞穴,观众在其中只能见到真实事物的影子。他认为,如果我们想发现最终的真实,必须完全离开洞穴。不论柏拉图对电影的诠释是否有用,‘dianying’这个名词同样探触到影像的本质,以及它和现实的关系,也把自己落实在剧院经验中。”(33)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与西方不同,人们是从看电影中来感知电影的,“如海市蜃楼,与过影何以异?……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34)通过异乎寻常的观影体验,感悟、了解进而把握电影的本质,从而建构起中国电影观念或理论的独特思维和本土化表述。
“影”即指今天所说的影像,当时是黑白而无声的。电影在摄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摄影为手段,又以摄影为本体,对表现对象进行客观再现。借助摄影的物理性能,它不仅能够具体再现现实中的人物和事物的形象状貌,而且可以把他们的动作和各种运动真实记录下来。影像作为电影的重要元素,不仅赋予电影以外在形式,而且构成它的内在本质。周剑云、程步高说到电影与文学根本区别时说:“在文艺作品中所描写者,只是颗颗文字的变换,而在电影中所描写者,则为幅幅画面移动。”(35)徐卓呆说:“活动影戏,由影片映出来的幻象,是似画似戏的一种特别动作与动态及不完全色彩的总和体。”(36)镜头、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构成单位,电影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画面、镜头展开情节、刻画性格,独特的语言带来了电影与其他艺术不同的叙述方式和结构特点。中国电影人很早就有了比较明确的画面观念和镜头意识。《劳工之爱情》(1922)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影片,片中摄影机位置虽然不动,但有了景别变化,九十个左右镜头,或远或近,层次分明,还用特写突出细节,视点灵活多变。通过前后景的衬托,加大场景纵深。人物由摄影机两侧出入画面,突破“第四堵墙”,加之平行和交叉叙述,创造独特的电影时空。主观镜头、快动作的运用,加强喜剧效果。这部影片完全改变了张石川所说“镜头地位是永远不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37)的拍摄方法,我们从中看到了他电影观念和电影技巧的进步。
电影是再现性的写实艺术,画面影像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幻象,强调视觉冲击和造型表现力。对此,当时人们有着一定认识:“小说与戏剧着眼于文字语言的效能,而影戏则着眼于事象。”(38)洪深说“影戏为美术”,(39)甚至提出“影戏是用眼睛编的”,(40)针对无声电影的特点,强调视觉表现突出造型可以给影片带来无与伦比的真实效果和艺术美感。田汉在剧本《到民间去》(41)中描写道:“一日其昌锄于野,以健康之体魄,挥巨锄于向大地,其风貌有类似米勒的画中人。”犹如一幅风格鲜明的版画,粗犷的线条、明暗的对比、奇特的构图、清晰的轮廓,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力量与美。影片《重返故乡》“如名手作画,远山遥水,孤帆萧寺,但在微墨点染,意到而笔不到,自成隽逸”(42)充满诗情画意,又是另一番风情韵味。
电影的真正魅力在于运动,不仅能够再现各种形式的运动,而且可以创造新的运动。因为运动,才使影像活了起来,使电影真正成为独特的艺术。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认为,电影画面拥有现实的全部外在表现,而首先是运动,“运动正是电影画面最独特和最重要的特征”。(43)中国人一开始就是从发现运动进而认识电影本性的,他们把运动性视为电影的生命,最典型的说法是“影戏,动的美术也”,(44)对电影是一门具有运动美感的造型艺术做出了准确概括。世界电影早期发展中,都有一个拍摄滑稽短片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由单纯记录生活场景和舞台表演,转向夸张强烈的跌扑追逐的拍摄,充分发挥电影的动态特性。滑稽短片是“真正电影化的样式”,(45)它展示动作的力度,突出动作的韵律,促进运动本性的形成,是电影艺术成长与发展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中国早期影片中很少用移动镜头,常常以摇镜头代替横移,展示人物动作的连续过程,表现人物视点变化。这是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所限,并不表明镜头意识淡薄,电影观念比人落后。可见的具象,动态的表现,创造出栩栩欲活奕奕如生的画面影像,电影成为“最是逼真”(46)的艺术。它最贴近人们生活的自然形态和外在表现,观众面对银幕,犹如身在其中,产生一种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真实可信的审美快感。
蒙太奇是电影独特的描写技巧和结构方式,通过镜头与镜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转换与连接,进行明白通畅而又生动感人的银幕叙述。在早期人们使用自己特有的表述语言如“接筍”(47)、“割续”(48)、“穿插”(49)等来说明和阐释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剪接是把分散杂乱的片断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艺术整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重视叙述性剪接,也同样重视表现性剪接,以使影片通俗易懂而又富有意味。陈醉云说,结构影片时必须“注意接剪”,首先要叙述顺畅,首尾如一,“使观众可以明白前因后果”,同时还应力求表现生动,富于变化,例如“将富人的赌博和贫女的劳作接在一起,将豪族的狂喝大嚼和灾民的啼饥号寒接在一起,使它两两对照,那便非常动人,非常有意义了”。(50)利用画面影像的对应关系,形成隐喻、对比、象征等,引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增加艺术感染力。侯曜把“穿插”分为两类:顺序连接法和参错连接法,并指出穿插原无定法,要根据需要去发现去创造。在剧本《弃妇》中芷芳遭劫一场,就利用场景切换,构成两条线索的交替推进,造成“一分钟营救”的紧张气氛和悬疑效果。为了适应当时众多市民观众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讲求条理清楚,道理明白,早期影片大多采用叙述蒙太奇为主、表现蒙太奇为辅的复合蒙太奇语汇和句式。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早期人们对电影本性并非在理论上没有应有的认识、在实践中没有自己的创造,只是我们的研究还不到位。由于现存的早期影片资料太少,而能够看到的更少,不过十来部,且其中还有残缺不全的。再说,这些幸存下来的影片,也未必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我们常常只能根据本事、说明、梗概进行分析研究,只能从里面知道故事,而看不见电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电影研究从何而来呢!
总而言之,把“影戏”作为早期中国电影美学核心和创作主流,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早期电影色彩纷呈,其理论形态和美学特征多种多样,不是可以用一个词汇或概念囊括得了的,何况“影戏”本身也存在着歧义。中国电影的早期成长,离不开戏剧,离不开文学,从这些姊妹艺术中获得了宝贵滋养,但并未成为他们的附庸。更离不开对电影特性的苦心探索和执著追求,强调电影是一门新兴的现代艺术,努力把握电影本体特征,不断开掘电影表现潜能。这是一条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之前许多国家的电影也都走过。
“文革”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人们开始对过去的电影进行反思,纷纷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内容虚假、语言贫乏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在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人们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和“丢掉戏剧拐棍”等激进的观点和主张,以期开创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于是淡化情节、诗意散文、意识流生活流,总之弱化叙事强化造型,盛极一时,对当时及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直接产生于这一思潮的“影戏”研究,把人们的现实诉求引向历史,在传统中寻求支持的依据,推动了中国电影美学和历史的研究,但偏向贬抑、否定的立场和态度不言而喻。
创新运动催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开创了新时期电影的新生面。但过于注重形式追求技巧,也带来某种负面影响甚至留下后遗症。应该反对的是电影舞台化程式化的表演、平面的调度、虚拟的场景、三一律的结构,专属舞台,与电影格格不入。有趣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冲突,鲜明的人物,戏剧需要,电影也不可或缺。可以有诗电影、散文电影,也可以有小说电影、戏剧电影。中外电影史上小说电影戏剧电影成为传世经典的不乏其例。不能因反对电影的舞台化倾向,而连叙事也一起抛掉。
我始终认为电影基本上是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艺术,只要讲故事就是叙事,造型和叙事是这位艺术女神能够自由飞翔的双翼。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不会叙事,再好的造型表现也只能是流于技巧徒有形式。近些年来,银幕上时常出现大搞视觉轰炸奇观展览的现象,究竟说些什么,不是自己没说清,就是人家听不懂,导演沾沾自喜,观众一头雾水。这是偶然发生还是与某种历史有着关联,值得深思。
注释:
①周剑云、汪煦昌《影戏概论》,上海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编印的《电影讲义》之一部分,1924-1925年。
②范志忠,严勤《西洋影戏的本土化改造》,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③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明星特刊》第3期《上海一妇人》号,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7月版。
④欧阳予倩《导演法》,《电影月报》1928年第1—5期。
⑤顾肯夫《描写论》,《银星》1926年第3期。
⑥周剑云《影戏杂志·序言》,第一卷第二期,1926年11月版。
⑦史东山《我们对于社会的两个希望》,《同居之爱》特刊,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1926年4月版。
⑧郁达夫《电影与文艺》,《银星》1927年第12期。
⑨田汉《银色的梦》,《银星》1927年第5—13期。
(10)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现代电影》1933年第1卷第6期。
(11)《观美国影戏记》,《游戏报》1897年9月5日第47号。
(12)[意]卡努杜《电影不是戏剧》,《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3)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14)郑正秋《新剧家不能演影戏吗》,《明星杂志》第4期《冯大少爷》号,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9月版。
(15)(16)郑君里《再论演技》,《联华画报》1935年第5卷第9期—第6卷第5期。
(17)顾肯夫《描写论》,《银星》1926年第3期。
(18)[加]安德烈·戈得罗、[法]弗郎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页。
(19)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明星影片公司1925年6月版。
(20)郑正秋《我之编剧经验谈》,《电影杂志》1925年第13期。
(21)王瘦月《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新剧杂志》1914年第2期,见张伟《前尘影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22)侯曜《影戏剧本作法》,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出版,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1期。
(23)欧阳予倩《导演法》,《明星月报》1928年第1—5期。
(24)李涛《听田汉君演讲后》,《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1926年8月8日。
(25)沈宁《〈权势与荣誉〉的叙述法及其他》,《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1月2日。
(26)黄子布、席乃芳、柯灵、苏凤《〈城市之夜〉评》,《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3月9日。
(27)《〈春蚕〉座谈会》,《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10月8日。
(28)[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语言》,刘森尧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9)费穆《杂写》,《联华画报》1935年第5卷第1期。
(30)费穆《“倒叙法”与“悬想”作用》,《影迷周报》1934年第1卷第5期。
(3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对待电影理论问题》,《世界电影》1983年第5期。
(32)徐碧波《摄影师》,《上海》第4期《盘丝洞》特刊,上海影戏公司1927年版。
(33)[美]布鲁斯·F·卡温《解读电影》,李显立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0页。
(34)《观美国影戏记》,《游戏报》1897年9月5日。
(35)周剑云、程步高《编剧学》,上海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编印的《电影讲义》之一部分,1924-1925年。
(36)徐卓呆《影戏学》,上海华先商业社图书部1924年版,第1页。
(37)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
(38)胡仲持《影戏与艺术》,《探亲家》特刊,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1926年版。
(39)洪深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代拟之《悬金征求影戏剧本启事》,《申报》1922年7月9日。
(40)转引自万籁天《表演之新趋向》,《神州特刊》第3期,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版。
(41)载《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1926年5月14日。
(42)倚虹《评〈重返故乡〉》,转引自张伟《前尘影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43)[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44)转引自任矜苹《导演但杜字》,《晨星》1924年第4期。
(45)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6)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1921年第1卷第1期。
(47)(50)陈醉云《导演学》,上海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编印的《电影讲义》之一部分,1924-1925年。
(48)同(36),第49页。
(49)同(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