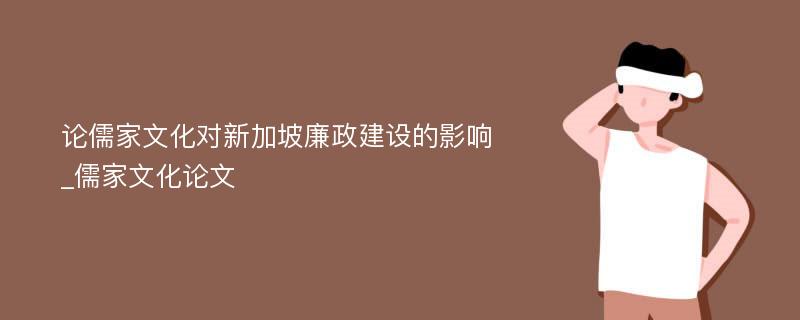
略论儒家文化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廉政建设论文,儒家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77%,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7%,其他少数民族占1%)新加坡人不仅保留了许多儒家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吸取了儒家文化中有用的思想并融于其国家建设中,为新加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廉政建设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特有的经济制度、人事制度、思想制度上。
(一)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影响。
孔子说:“藏富于民。”而孟子更直接地指出要“置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认为让人民钱物富足,生活稳定,民心就易平定,就不会谋求利用不正当的渠道去获取不义之财,这样社会就易安定。新加坡政府正是吸取了这种思想,建立了有其特色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仅是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保证政府人员尽量避免贪污的强有力的一种防范性经济措施。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新加坡每个职工都是中央公积金的会员,每月必须按月薪按一定比例交纳公积金,同时职工的所在单位也按一定比例为职工交纳公积金(目前,职工以每月工资的22%,单位以该职工月工资的18%,共40%,存入以该职工名下的公积金)。这种强制性而支取又有一定限制(一般要达到15万新元才能支取)的长期储蓄,对每个职工而言,数量可观。尤其是地位越高,资格越老的人公积金越多。但是,一旦公务员被发现有违法贪污行为后,除了科以罚款、开除公职外,还要没收全部公积金,其后半生所有的保障都没有了。正如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局长杨温明所言:“一个贪污犯罪的官员除了被罚款外,还要丧失工作,这是为了使干部明了贪污是很不划算的。”这种严厉的经济制裁,加之以严格的法律、严明的执法,对新加坡人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使他们清楚贪污的人要为贪污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君子晓以礼,小人晓以利”。
(二)儒家文化对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相对主动性的以俸养廉工薪制度的影响。
如果说中央公积金制度是经济制度上较为被动的防范性措施,那么,以俸养廉的工薪制度则可以说是相对较为主动的一种手段。
在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开始腾飞之时,国家公务员的俸薪相对于社会企业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而言是过低的。这种过于不平衡的经济收入,一方面不利于留住政府中的精英人才,另一方面对廉政建设也产生负面影响。正如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济”。从现代意义角度上讲,也可理解为政府官员的薪俸不能过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甚至应该较之更高些,否则,过低的收入就极可能使意志薄弱的政府官员“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出于廉政建设和挽留人才的需要,新加坡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逐步提高公务员的薪酬。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5 页)李光耀所说的“以俸养廉”指的是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只是保持在中上水平,与企业的职员相比,差距仍然存在。企业的一些高级职员的薪酬要比公务员高出好几倍。新加坡并不认为自己是高薪养廉,而是给予适度足够的薪酬,使国家公务员能过上较舒适的生活。这正符合孔子所言“富与欲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新加坡一位反贪官员也说过,如果大多数的政府官员生活在贫困中,要制止贪污是很难的。
(三)儒家文化对与廉政建设相配合的“精英主义”人事政策的影响。
以俸养廉说明新加坡并不是单纯地用高薪来制止贪污腐败。它还有一套人事约束机制相配合,即“精英主义”的人事政策。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内圣外王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孔子曾说过“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儒生所向往的学优入仕之道,同时也是为政以德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兼具道德及智性的优点,认为唯其如此,国家治理才能顺达通畅,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富庶。这种带有现代“精英主义”色彩的儒家文化伦理也理所当然地为新加坡政府所借鉴、吸纳。从廉政角度上看,“精英主义”的人事政策也更可能杜绝贪污腐化行为的发生。精英主义从智力上要求人的能力超群,而且从道德上要求具备良好的品质修养。这种良好的道德品质,李光耀认为最基本的就是看其“有没有坚强的性格,有没有无私和牺牲精神”。这种无私精神最基本的就是要求其不为金钱所动,能居高位而清廉。李光耀信奉精英主义,他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只有不断成长、改革、求变,才能使这个岛国屹立不倒。他认定拙劣的领导人会杜绝好人才于门外。因此,他的人才管理一方面要吸收精英分子,使其成为政府一员,另一方面又要杜绝贪污腐化。政府公开指出“贪——是精英的坟墓”。在这种人事管理制度下,新加坡政府的官员都经过种种考察,层层筛选,可谓是新加坡的精英分子。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精英分子舍己为公的无私奉献,使新加坡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同时,也鲜有贪污腐化行为发生。诚如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公共服务署副秘书长陈文发所言“新加坡政府是全世界最诚实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也相信,他们有一个最干净的政府”。
(四)儒家文化对廉政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道德思想建设的影响。
孔子有三达德,“智、仁、勇”,孟子有四端,“仁、义、礼、智”,汉儒又有五常,“仁、义、礼、智、信”。新加坡领导人借鉴了这些观点的积极意义,吸收其精华部分,经过重新阐释形成了所谓“八种美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以促进廉政建设。早在1982年,李光耀在华人农历春节献词中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种美德,同时这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坚持贯彻执行的“治国之纲”。当然,李光耀并非简单地按传统意义上套用这八德,而是赋予其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阐释,使其更符合新加坡国情,更易为其国民所接受履行。
从廉政建设的角度上讲,“八德”所形成的价值观,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防范作用。“八德”中“廉”直接与廉政建设相联系,它要求新加坡政府官员廉洁公正。要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是为官的基本道德规范。新加坡政府认为唯有贯彻这一道德规范,官员才能公正廉洁,政府才会有威信,人民才会信任,否则,必将舞弊成风,贪污腐化,必会失信于民,导致政府的垮台。虽然在这“八德”中只有“廉”直接指的是政府官员的廉洁,但是,其余“七德”对政府官员形成“廉洁”的价值观念,对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八德”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在1990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其中提及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这五大价值观体系深深地刻着儒家文化的烙印。新加坡政府把儒家文化这东方的基本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使之成为新加坡国民的行动指南。他们十分谨慎地借鉴和吸取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有用成分,同时,又使之新加坡化,以此来教育国民,在国民中树立起“敬业乐群”、勤劳进取、讲求效率、廉洁奉公的新加坡精神。
二
现代化的新加坡,在其廉政建设中能够很好地贯彻运用传统的儒家文化,甚至把儒家文化上升为国家意识,这颇耐人寻味。我们该如何看待、解释这一现象呢?
(一)地处交通要冲的自然环境。
从新加坡自然环境来看,新加坡地处柔佛海峡,是太平洋、印度洋交汇的咽喉处。自古以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他们不仅给新加坡带来金钱货物,同时也给新加坡带来各民族、各国家的传统文化思想乃至于现代的东西方文化,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东西方各种文化、价值观在此互相撞击、摩擦,儒学、道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等都在新加坡存在,它们在其各自范围内对新加坡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对新加坡产生各种不尽相同的影响。新加坡领导人经过比较甄别,选定儒家文化作为其国家意识,自有其自然环境因素,也有更深层的社会人文因素。
(二)以华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社会人文环境。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脉脉相承,经久不息,连李光耀本人也坦言,他本人“可被归类为典型的儒释道信徒”。虽然新加坡政府告诫华人不能搞华人沙文主义,但在树立价值观这种关系到民族的心理情结、价值观取向等极易引起社会震荡的关键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到儒家文化在华人社会中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如何使各民族保持种族和谐,各宗教能和平共处,也是新加坡政府长期要解决好的问题。而儒家文化在此方面又有其独到之处。
《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博精神,它告知人们,有道德的人,应胸怀宽大,包容各方面的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种论点从民族意义上讲,可说是一种民族平等、种族和谐的精神。这对于新加坡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而言,极具现实意义。儒家文化还强调政教分离,有着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正是这种对宗教超然乃至冷淡的态度,以及厚德载物的包容胸襟,使中国能使儒学、佛教、道教等长期共存,和平共处。而这种优良的儒家文化对新加坡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具有借鉴意义和学习意义。这也是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儒家文化的重要原因。
(三)新加坡领导人的大力倡导。
儒家文化能在新加坡得到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在廉政建设乃至整个国民建设中发挥作用,这除了与新加坡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关系外,还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吴作栋等人的大力倡导有密切关系。
李光耀身为客家人,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后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学学位,并以双优学位毕业,可以说是同受东西方价值观教育,他因此可以深刻地鉴别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劣。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李光耀意识到一个国家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缺乏一种能使全国凝聚团结的精神力量,那是很危险的。因而李光耀试图寻找一种适宜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哲学。他对历代各大思想家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推崇儒家思想。他说:“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他把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家文化的中心,提倡并把这八字化为新加坡的具体行动准则,一一赋予新的涵义。
作为李光耀的接班人,现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在1988年,他在人民行动党属下青年团的一次讲话时,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在这种整个国家灌输儒家文化的社会大环境下,儒家文化在整个国民建设尤其是在廉政建设中所起的主要影响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