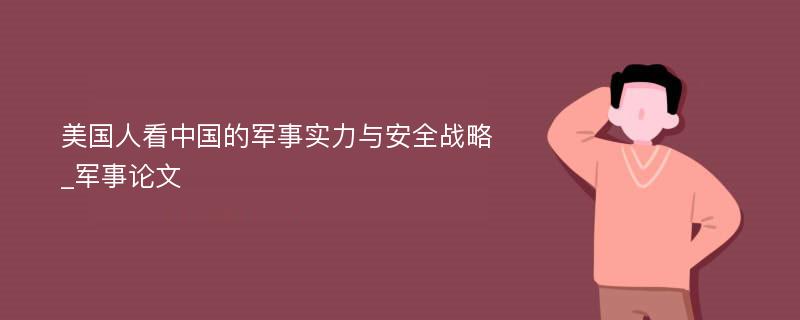
美国人看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人看论文,中国论文,军事力量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结束已有十载,人类步入新世纪之际,惊心动魄的大国对抗似乎已逐渐远去,然而国际间或明或暗、或急或缓的较量似乎从未停止过,战略平衡与失衡依然是牵动人们心弦的国际政治运动状态和引导人们认识和塑造当今世界的思维框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国力增强巧遇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使得中国在地区稳定乃至国际和平中所起的作用颇引人瞩目。当美国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对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实施调整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现状与发展及战略意图表现得格外关注。
以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为标志,中美关系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高潮。然而,时隔不久形势便发生了逆转,两国关系屡遭冲击和考验,刚刚恢复的正常交往一度几乎难以为继。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对峙,两国贸易关系谈判一波三折。由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台海局势再度紧张。台湾选举和新领导人上台进一步给两岸关系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两国军事与安全关系更是风雨交加、险象环生,爆炸性事件交迭出现,相互影响。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案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猜疑,北约袭击中国使馆事件破坏了中美军事交往与安全对话,双方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上的立场分歧更为鲜明。
一、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军事力量与安全战略
以两国总体关系的波动为背景,美国人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其对美国乃至国际安全所造成的影响的议论和探讨尤为活跃,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相互对立。
(一)中国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对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有着不同的估计。一些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表示了忧虑。《时代》周刊报道,1998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加了13%,达到109亿美元,正在对武装部队进行全面重组,用更多的现代武器系统替代现有的落后装备,已从俄罗斯购买了3艘基洛级攻击潜艇、两艘装有SS-N-22反舰导弹的现代级驱逐舰、50架苏27战斗机,建造了约20枚可将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新型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还对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表现出浓厚兴趣。(注:Douglas Waller,"China's Arms Race,"Time,January 25,1999,p.17.)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路加(Richard Lugar)提出要对来自中国的核威胁进行重新评估,认为美国必须认识到“美国现在可能面临着更大的来自中国的弹道导弹攻击的风险”,应密切注意“中国在发展自己的能将多弹头有效载荷投向美国目标的远程导弹方面的所作所为”,必须迅速确定“如何对付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地区和核姿态”。(注:Richard Lug-ar,"It's Time to Reassess the Nuclear Threat From a Militant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1,1999,p.8.)
即使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似乎也不能令美国人释然。耶鲁大学教授布莱肯(Paul Bracken)认为美国也许在军事和其他技术上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但西方对这些技术的独占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快将拥有足够的力量使外部国家在危机时期向那里投送兵力时三思而行。(注:Paul Bracken,"A Disappearing World of Western Military Suprema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5-6,1999,p.6.)一位前驻北京美国空军副参赞1999年出版的新著《中国的战略现代化:对美国的含义》集中探讨了中国的军工企业和中国在导弹、信息战和精准武器方面的投资情况,作者认为中国无需与美国相匹敌的力量便可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国眼前的目标——控制台湾并使美国不敢介入保卫该岛——是完全处于中国掌握之中的较为有限的军事目标。(注: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0,p.162.)
也有一些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不应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落后于美国几十年,远远不具备综合能力与其国界之外的现代敌国交战并将其击败。中国军队基本上只是一支地面力量,武器装备处于30年前的水平;中国飞行员的飞行训练小时数远远少于任何现代空军;海军和空军的现役战舰和战机正面临淘汰;战略核武器数量只有美国的三百分之一(中国有20余枚可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而美国则有约6000件核武器可打到中国),所有武器的爆炸当量仅相当于一艘美国三叉戟潜艇所载有的爆炸力;即使有了东风31型导弹,中国的战略导弹力量也只有美国的十八分之一;中国没有航空母舰(美国有11支航母编队),没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美国有174架);中国的军费只占全球军费总和的4.5%(美国占33.9%),相当于美国的14%;尽管从俄罗斯购买了新型战斗机、潜艇、驱逐舰及一系列新型导弹,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收效甚微;中国进行网络战和发展反卫星武器的计划虽听起来吓人,但距真正实现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因此,中国军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真正的超级大国地位。(注:参见Douglas Waller,"Chi-na's Arms Race,"p.18;Patrick E.Tyler,"Seeing China's Challenge Through a Cold War Len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1999,p.WK3;Frank Gibney Jr.,"Birth of a Superpower,"Time,June 7,1999,p.26;Patrick E.Tyler,"Who's Afraid of China?"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1,1999,p.48;Gerald Segal,"The Myth of Chinese Power,"Newsweek,September 20,1999,p.41;Geral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9,p.29.)2000年6月国防部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尽管中国正在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反击来自技术优势的敌方的威胁,但其武器和训练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将使它“在一段无限期时间内”无法挑战美国。(注:Steven Lee Myers,"Pentagon Study Sees No Early China Th-rea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26,2000,p.6.)
(二)中国的安全战略
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引起了美国人的种种猜测。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意欲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将美国赶出亚洲,从而成为该地区的霸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共和党方面的东亚事务首席顾问布鲁克斯(Peter R.R.Brooks)认为中国寻求发展以多个全球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中国认识到要使其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就必须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注:Peter T.R.Brooks,"Strategic Realism: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9,p.54.)海军上将普吕厄(Joseph Prueher)刚刚离任美国驻太平洋部队司令时表示担心中国正寻求恢复中央王国思想以称霸亚洲,那将与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平衡的态度发生冲突。(注:Richard Halloran,"America and China:Back and Forth to Nowher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2,1999,p.8.)工商管理人员支持国家安全协会(Business Exe-cutives for NationalSecurity)的创始人兼主席维斯(StaleyA.We-iss)撰文称“中国似乎要建立一个其余亚洲人都必须对其俯首贴耳的中央王国的现代版本”,认为中国同西面的巴基斯坦一道对印度形成了包围之势,还在靠近印度北部边界的西藏储存有核武器,在东面,向缅甸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对印度进行间谍活动。此外,文章还说西方专家发现中国为在孟加拉湾、安达曼海、泰国湾和南中国海取得军事立足点正在进行系统的努力,以便控制扼六分之一以上世界石油贸易咽喉的马六甲海峡。(注:Staley A.Weiss,"Washington Panders to Beijing and Patronizes New Delh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2,1999,p.8.)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依然是对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文章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这样一番描述:
中国是一个其重要利益尚未解决的大国,特别是有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国憎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要向有利于它自己的方向改变亚洲力量平衡的强国,那本身就使它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加之这样一个中国在弹道导弹技术上与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记录,安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会尽其所能加强其地位,无论是靠窃取核机密还是靠恐吓台湾。(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56.)
还有人怀疑中国可能会在本地区寻求战略伙们来联合挑战美国的霸权。美国国际事务专家密切注意着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增加合作的迹象以及三国都怀有的、特别是北约轰炸南联盟后不断增强的意识:美国的权力必须受到一定的抑制。尽管分析家们都认为三国还远未组成一个反北约的欧亚轴心,但仍对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心存忧虑,即一个聚集了25亿人口、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大批核武器,并由对抗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联盟。(注:Tyler Marshall,"Russia,China and India:Do Closer Ties Bode U.S.Il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28,1999,p.6.)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无意在军事上与美国一争高低。“13亿中国人民没有兴趣威胁美国的力量,或将美国力量赶出亚洲从而成为称霸该地区的帝国”,因为中国人只需要“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以发展他们的经济”,攻击美国从来就不是中国战略思想的核心。(注:Patrick E.Tyler,"Who's Afraid of China?"p.48.)中国当然有意建设可靠的、能够保卫其海岸附近的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像苏联那样以一个全球军事大国的姿态寻求与美国竞争。(注:Patrick E.Tyler,"Seeing China's Challenge Through a ColdWar Lens,"p.WK3.)2000年6月国防部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层仍然优先重视经济增长问题,甚于军事和国家安全问题。(注:Steven Lee Myers,"Pentagon Study Sees No Early China Threa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ne 26,2000,p.6.)
也有人持观望态度,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还没有最终确定,仍有调整的可能。前中央情报局亚洲问题官员哈灵顿(Kent Harrington)说:“中国人是在建造一门终将指向我们的大炮吗?我认为今天我们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就此事跟他们交谈以确保将来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注:Douglas Waller,"China's Arms Race,"Time,January 25,1999,p.18.)
(三)中国的军事发展趋势及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军事发展走向,有一点美国人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即中国的每一位军事分析家都认为中国的确需要快速武装起来,军事落后的中国正在逐渐地使负责保卫自己后院(包括西藏、台湾和南中国海领土)的那一部分军队实现现代化。(注:Patrick E.Tyler,"Who's Afraid of China?"p.48.)西方专家确信,如果美国实施反导弹防御计划,中国的回应方式将是首次装备强有力的、具有潜在的打破平衡能力的核力量。(注:Joseph Pitchett,"Chinese Nuclear Buildup Predicate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6-7,1999,p.1.)而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同时也是军控问题权威人士则认为无论美国是否继续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都会扩充自己的战略核力量以减弱这种系统对中国的威胁。(注:Jane Perlez,"U.S.Sure China Will Improve Mi-ssil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13-14,2000,p.3.)几位军事问题专家联合在《外交》杂志2000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认为,未来十年,有可能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或任何“无赖”国家)的核武器政策“令美国最为关注”,他们认为中国的核计划尚不确定,但有三种可能性尤为突出:第一是中国通过增加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并加强其穿透防御的能力来保持和恢复对美国的最低威慑;第二是中国更多地专注于印度,维持全球性最低威慑,同时在战区层次上走向更为坚定的有限威慑战略;第三是中国选择发展和部署一支足以在任何情况下让所有敌人吃相当苦头的力量,这样中国便完全奉行了有限威慑战略。(注:Brad Roberts,et al,"China: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0,p.60.)
进一步涉及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国的利害关系,美国人的看法再次出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力量增强的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准备有一天将美国赶出亚洲,然后对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称王称霸”。(注:Patrick E.Tyler,"Seeing China's Challenge Through a Cold War Lens,"p.WK3.)被称为“蓝队”的对华强硬派提出中国军事建设的稳步发展将很快使它处于威胁美国的地位,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威吓台湾”。(注:Robert G.Kaiser and Steven Muffson,"HardL-ine'Blue Team's Influences U.S.Poli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23,2000,p.4.)1999年夏天,美国国防部组织了一批学者、前政府官员和现任国防部官员对亚洲局势进行了预测,写出了题为《2025年的亚洲》的报告。该报告否定了那种认为中美关系会温和而富有成果地发展的观点,结论是无论强大还是相对虚弱,“中国都会成为美国的持久竞争者。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不断挑战东亚现状,而一个不稳定而且相对虚弱的中国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的领导人可能靠对外军事冒险主义来努力支撑他们的权力。”(注:Robert G.Ka-iser,"Imagining an Expansionist 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8-19.2000,p.1.)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克服那种中国一有发展便加紧防范的冷战思维习惯。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指出:“在当前这一时期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也可能永远不会。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同美国发生争执。”(注:Patrick E.Tyler,"Seeing China's Cha-llenge Through a Cold War Lens,"p.WK3.)已从美国国防大学退休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格德文(Paul Godwen)批评某些分析家把“每个传言中的中国收获都当作真有其事”并且“倾向于将每件武器都看作”人民解放军的“杀手锏”。(注:Robert G.Kaiser and Steven Muffson,"HardLine'Blue Team's Influences U.S.Poli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23,2000,p.4.)有人预言“中国目前的和今后十年左右的军事实力,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严重威胁,除非中国领导人选择民族自杀的道路。”(注:见卡里尔沙德在《美国与中国:战略与军事的意义》以及其他文章中的结论。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第68页。)
如果说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对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形成的直接挑战感到忧虑的话,那么中国军力的加强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却令美国人普遍感到不安。有人认为中国发展新式武器、部署一支地区性导弹力量,将改变亚洲的军事力量平衡。(注:Douglas Waller,"China's Arms Race,"p.18;Paul Bracken,"A DisappearingWorld of Western Military Supremacy,"p.6.)《华盛顿邮报》社论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年可能完成的核现代化将对地区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注:"China as a Pickpocke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7,1999,p.12.)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B.Carter)合著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写道:“今天中国正崛起为一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从而与其他太平洋大国,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利害冲突。”(注: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也有更具体的观点认为中国部署新一代具有即时发射能力和洲际射程的核导弹会使日本感到惊恐,对印度形成严重挑战,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危及美国和欧洲领土。(注:Joseph Pitchett,"Chinese Nuclear Buildup Predicate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6-7,1999,p.1.)
二、美国人关于对华战略的主张
上述美国人对中国军事和战略的分析折射出他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格外关注:中国是否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而正在变成美国的潜在战略敌人?无论答案是什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足以引发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深切关注。美国人似乎感到确定一种对华战略乃是处理中美关系首要考虑的问题,(注:一位专栏作家认为中美之间的急迫议事日程不是人权,也不是贸易接触,而是战略敌对。见Jim Hoagland,"America's Reiations With China Are Worsening,"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15,1999,p.8.)因而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对华战略设想。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在谈论对华战略时都对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讳莫如深,而是对所要使用的手段探讨有加。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表明,总体上看,美国人在上述对中国军事与战略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华战略主张大致可分为“温和”和“强硬”两种,分述如下:
(一)战略接触与诱导
“温和”的对华战略侧重于主张通过各种与中国交往的方式引导中国朝着符合美国利益(他们认为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方向演进。《预防性防御》当属这一战略观点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提出的战略方案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应当致力于加深和扩大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以影响中国军官的政治、军事观点;第二,美国应当和中国一道致力于台湾局势的稳定;第三,美国应当寻求与中国的邻国接触,以促使该地区各国之间建立互信;第四,美国应当鼓励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反扩散及其他的全球性安全体系。(注: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21页。)
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应该尽可能地让中国参与新出现的地区安全多边对话”,并指出“东北亚的地区安全不是一场一方收益而另一方必然受损的游戏;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注: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J〕,《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74-75页。)还有人建议美国至少要重新思考其核政策和导弹防御政策以考虑到中国的担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此外,美国还应更进一步,努力与中国就美中关系中的战略稳定所需的条件及如何处理地区性扩散和诸如朝鲜半岛、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军控问题达成某种谅解。(注:Brad Roberts,et al,"China: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0,p.63.)
(二)战略威慑与遏制
“强硬”对华战略侧重于通过施加种种形式的压力迫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近两年这种观点表现尤其活跃,内容也更为丰富,其中布鲁克斯的主张较为全面并有一定代表性。
1、战略对话
布鲁克斯也主张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不过与上述战略接触不同的是,他所主张的对话带有鲜明的警告和威慑色彩,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只有通过传递明确无误的外交信息才能保证两国清楚地认识彼此的地区利益。“战略对话,即使不能取得战略谅解,也能减少错误的观念,限制冒险主义和避免错误判断。”因此,美国要通过这种对话使中国明白美国所看重的利益是什么以及美国有多大的决心来捍卫这些利益。(注:Peter T.R.Brooks,"Strategic Realism: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9,p.55.)
2、战略存在
布鲁克斯认为美国持久的军事存在正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靠性”及对该地区承担的义务的“基础”。不仅如此,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一旦可以投入使用即应在东亚部署以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和部署大型弹道导弹武库并最终使其不敢使用这种武器。(注:Peter T.R.Bro-oks,"Strategic Realism: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9,p.55.)赖斯提出“中国要想成功地控制力量平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因此,她也主张美国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强劲军事存在”。(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56.)
3、战略联盟与合作
近两年来,美国人主张通过在中国周边巩固战略联盟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来牵制和制约中国的呼声逐渐增强。有人提出美国应鼓励日本更积极地发展军事力量以抗衡中国。(注:Robyn Lim,"Now Stand Up to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1,1999,p.8.)布鲁克斯认为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支柱”,这一点不可动摇。美国继续保证致力于扩展威慑“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朋友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因此,美国的双边同盟结构必须得到保持和加强以增加“该地区长治久安的可能性”。(注:Robyn Lim,"Now Stand Up to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1,1999,p.8.)赖斯也认为美国“必须深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56.)
还有人注意到“一个强大而没有侵略性的印度会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而美国似乎也正准备“加紧努力,以两国共有的民主政治传统和对任何一个国家独霸亚洲的真实惧怕为基础,与印度发展新型伙伴关系。”(注:Staley A.Weiss,"Washington Panders to Beijing and Pat-ronizes New Delh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2,1999,p.8.)印度的利用价值同样得到赖斯的注意,她认为美国“应更密切地注意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称印度是“中国的谋划中要考虑的因素”,也应当是美国应考虑的因素。(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56.)《战略评论》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当前正是美国“打印度牌”的时候,认为美国与印度有“共同的强有力的民主传统、共同的语言和在地区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加之印度已成为核国家,因此更应与其进行军事合作。(注:Peter Jensen,"Chinese Sea Power and American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Summer 2000,p.25.)
该文章还进一步建议,美国还应在南中国海重建海军基地,新加坡、苏比克湾和金兰湾都是值得考虑的出色地点。(注:Peter Jensen,"Chinese Sea Power and American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Su-mmer 2000,p.25.)此外,还有人建议美国应重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并以此在南沙对中国形成压力。(注:Robyn Lim,"Now Stand Up to Beij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1,1999,p.8.)国防部长科恩2000年4月访问越南期间还曾建议与越南建立军事关系并鼓励越南与东盟其他国家合力解决与中国有争议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称如果东盟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话,它们的“集体利益将来在和平和合作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时能够产生相当的影响”。(注:Michael Richardson,"U.S.Seeks Hanoi's Aid For Accord In China Se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5,2000,p.1.)
4、出口控制
先进技术的出口形式上是贸易问题,实质上是军事和安全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限制技术出口的对象国之一,先进的军事技术自不待言,有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民用技术也被当作所谓“敏感性技术”或完全禁止转让或禁止转让给军事机构。近两年来,控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更是被当作一项战略措施提了出来。
《纽约时报》一篇社论认为中国虽然不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是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但是却有着自己的军事日程,这一日程时而与美国的军事日程发生冲突,因此“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不应扩展至卫星及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助推器方面”,欧洲或许会向中国出售此类技术,但欧洲技术不及美国技术先进。总之,“这种技术不应让中国的武装部队得到”。(注:"Expertise Not for 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26,1999,p.6.)一些对向中国出口高技术持批评态度的人担心“正在将中国变成一个自动柜员机和移动电话国度的技术同样会帮助人民解放军开始掌握信息战”,担心中国将高技术进口充分用于军事目的从而成为惊人的敌手。(注:Warren P.Strobel and Douglas Pasternak,"By hook or by crook,"U.S.News $ World Report,March 8,1999,p.34.)布鲁克斯提议,为了加紧出口控制,美国应重新起用已失效的《出口管制法》并“确保我们的技术不会改进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他认为帮助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一定要优先于商业利益。”(注:Peter T.R.Brooks,"Strategic Realism: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9,p.56.)非但如此,有人甚至建议美国应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俄罗斯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注:Peter Jensen,"Chinese Sea Power and American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Summer 2000,p.25.)
三、结语:几点思考
美国人对中国军事发展和安全战略的认识和反应是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这里仅对美国人的上述看法作粗浅概括和初步分析,以就教于大方。
首先,太平洋此岸的发展大潮显然重重地拍击和震动着彼岸。尽管在认识上不尽一致,但美国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关注是无庸置疑的。从大的趋势上看,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已呈必然之势,这似乎已是美国人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似乎以其全球老大的地位从心理上逐渐感到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战略挑战。中国已不自觉地成了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战略假想敌,尽管这绝不是中国人希望要看到的现象。同时,美国人似乎一致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战略影响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战略意图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不同评估说明美国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在探讨和形成过程之中,尚未形成共识,还有调整空间。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美国人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何时对美国构成挑战,而不是是否会构成挑战的问题上,即究竟中国的发展是在近几年便会打破亚太地区现有的力量平衡从而危及美国的领导地位,还是在更远的未来构成这样的威胁和挑战。关于对华战略,美国人提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这种辩论本身表明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战略走向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仍存在美国施加影响的余地。从对华战略的分歧上看,主张“怀柔”政策的温和派大体上沿袭了克林顿后期的对华政策,没有新的突破性想法,且在舆论力度上有所式微,而强硬派则表现得较为活跃,所提出政策也更为全面和具体,在舆论上颇成气候,其呼声明显高于温和派。
其次,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国军事和战略的认识表现为上述特点,有一定的必然性。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环境、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近年有学者总结的美国的“寻敌”心态等都是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整体影响的重要因素,自然也会作用于美国人对中国的战略看法。学术界对这些因素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作为从冷战中脱颖而出的惟一超强国家,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世界各地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人称之为领导地位)、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历史长河一再上演大国争霸与沉浮的剧目,也由于汤因比、莫德尔斯基、戈登斯坦等的国际政治周期理论的影响,当今一代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不会不对新兴大国对原有大国形成的挑战具有丰富的认识和高度的敏感。布鲁克斯就有这样一番表白:“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一直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事。人类历史充满了现有大国不能成功地处理一个匹敌的竞争者出现的实例,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新的世界秩序的调整常常导致冲突。”(注:Peter T.R.Bro-oks,"Strategic Realism:The Future of U.S.-Sino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Review,Summer 1999,p.56.)而中国似乎恰逢其时地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和担忧便不足为怪了。头几年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美冲突”论说都是这种意识的兆端。于是,由这种心态衍生出的对中国的防范乃至敌意便促使许多美国人思考和探讨中国的军事发展和战略意图。当然,如此作出的判断是否客观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战略地位和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必然会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安全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缺乏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这种影响的力度和方向也许将是不稳定的。就对华安全战略而言,新政府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现任政府表现得更强硬一些,原因一是近两年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新动向使两国间在安全问题上的互信程度进一步降低,立场对立更形凸显;二是支持现行对华战略的主张没有清晰的构想和确定的目标,显得底气不足,而强硬派的观点却迎合了形势的最新发展,颇有市场。不过,在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国共同利益的框定之下,对华强硬政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以至很快形成两国公开敌对状态。一种可靠的估计是,中美安全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一面,即使发展得好也不会是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的积极因素,搞得不好则会出现严重摩擦和冲撞,对中美关系形成严重制约。
最后,值得中国方面关注的是,美国不仅在政策建议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中国存在有越来越多的戒心。过去几年,美国军方已进行过20余次模拟战争以操练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冲突,超过了针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任何大国所做的同类演习。(注:Jim Mann,"A Wary Eye on Beijing,"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1,1999,p.1.)在外交行动上,美国近期似乎正谋划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构筑一种安全防线,冷战式的战略包围圈隐约可见。对这种活动不可掉以轻心。倘若果真如某些人建议的那样,美国在中国周围巩固联盟体系,加强安全合作,则难免有第二次冷战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