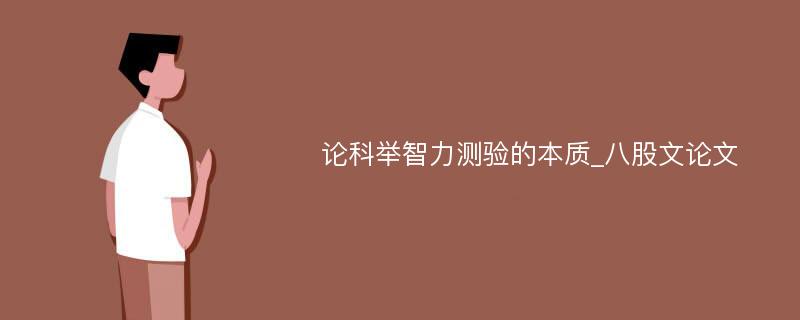
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测验论文,智力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科举并非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只能选拔庸才,而是能够选拔智力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从政人才。由于采用八股文和试帖诗这类标准化考试文体,科举具有智力测验性质。但八股文越是充分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
关键词 科举 八股文 智力测验
对于科举能否选拔人才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在以往批判传统、否定科举的大趋势中,多数学者以为科举选才功能有限,到明清以八股文取士之后,更是只能选拔庸才。按鲁迅的说法,“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1]然而,作为一种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实行之早、历时之久和影响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科举制只能选拔毫无真才实学之辈,它就不可能延续1300年之久。和者认为,科举能够选拔智力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从政人才,具有智力测验性质,而八股文与试帖诗也具有特定的测验功用。
一
科举考试是一种智力测验的说法,是在19世纪以前由西方人首先提出来的。如1871年,一位叫Ewer的西方学者在《三年大比》一文中说到:“没有一个读过一点有关中国书刊的人不知道中国的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这种考试将那些能够成功地回答智力测验的人置于重要职位并给予最好的奖赏。”[2]作者在该文中还一再提到科举考中者有智力。1877年,在中国京师同文馆担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美国教育部发表的《中国教育》一文中也说:“中国的学位(指科名——引者注)代表才智而非知识,它们由国家授予而无院校的介入,并给学位获得者予官阶的特权;它们只授予那些竞争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反之,我们的学位并不带来官员的身份,它们只证明学识而不是能力。”[3]他们从观察中都得出科举考试是考测智能而不是考核学识的结论。尤其是丁韪良,他是一位中国通,对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科举考试和知识分子问题都有相当深入了解,他的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还有科举为智力测验这一说,以往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此有所研究,其中首推心理学家张耀祥。1926年11月,张耀祥在北大作题为《中国人才产生地》的演讲,主要是用直接从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上抄录的25000名左右清代进士的籍贯的地理分布,来说明中国各省人才的分布情况。在演讲稿中,张耀祥认为以进士人物为统计人才的地理分布的资料最为理想、最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学业以外的资格、投考机会、考试地点、经费、考试及阅卷规则、考取额数诸方面考察,科举实在是竞争最自由的取士工具”。他还提出:“科举是一种智力测验,不是学科测验,也不是职业测验。治某学科或从事某种职业,多半属于偶然激发的行为。智力纯是学会各种学科,并创造各种事业的潜势力。……科举人物代表当时国中最高智慧阶级全部。”该演讲稿在1926年11月24日和25日的《晨报副刊》连载。
为了解答个别人的质疑,张耀祥又专门写了《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发表于1926年12月16日的《晨报副刊》上。他声明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发表“科举为智力测验”这个论断,不完全是出于门外汉的武断。他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如做骈文策对、诗词歌赋,用心理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把平素各方面所得的印像(在此处是单字及成语),按测验的要求(即题目的性质)挑选一部分,集合起来,加以新的组织(即连串成文)使之成为一篇有系统有意思的文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智力测验。他认为“说科举是教育测验,无异于说吟诗等于背诗,作文等于抄文”。他还列举西方通行的智力测验也要涉及文字和学习过程加以论证。
科举为智力测验说曾得到一些遗传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同。如潘光旦、费孝通194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卷1期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便说:“我们承认,凡是由科举考试出身的人,一般地说,遗传的智能要好一些,教育的便利要多一些。当代心理学家,对以前考试制度曾作研究的,认为八股文的考试方法多少是一种智力测验,而不止是记忆测验与知识测验。”现代一些优生学家从进士人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一点,也间接地认为科举考试选拔的是智力较高的人才。例如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福州府长乐县先后出了两个状元:马铎和李骐,相传他们是异父同母兄弟。虽然马铎和李骐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但都取得了最高的科名,这有力地说明他们的母亲的智商遗传是相当重要的。
1949年,潘光旦在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优生原理》一书中,指出清代560名巍科人物中,至少有42%是二人之间或多人之间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即属于一个庞大的血缘网,并认为这个血缘网是发现是智力遗传的有力论据。潘光旦还指出:清代江苏昆山徐开法三个儿子都考中鼎甲,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状元,其兄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年)中探花,徐秉义又中康熙十二年(1673年)探花。徐氏昆仲都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乾学比秉义大两岁,秉义比元文大一岁。他们的母亲是顾亭林先生的第五妹。以大学者的舅父,生掇取巍科的外甥,决不是一种碰巧的事。”[4]最近有的学者进一步考证出,徐乾学家五子登科,也全是进士。这样,徐氏父子叔侄兄弟八人都廷试中式,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再明显不过了。而且唐宋明清四个朝代,无论北方或南方,不少进士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形成一种血缘型进士链。血缘型进士链的产生是遗传(智力遗传)与文化、地理环境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遗传因素。[5]
历代进士之间和明清鼎甲人物之间经常存在的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举考试有可能将智商较高者测试选拔出来,因而具有智力测验性质。
二
那么,为什么科举考试能在一定程度上测验和选拔出智力较高者?这与科举采用试帖诗和八股文等考试文体有关。
唐代科举考试的题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几种。有的学者认为,唐代这些考试方法与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有一种巧合。帖经偏重于记忆,属于布卢姆学习分类六大类中第一层次认知阶段;墨义为简答题,属于学习中第二、三层次的理解和运用;策问则考察分析与综合能力;诗赋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与布卢姆学习分类中智能部分最高层次的“评价”具有同等的意义。[6]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墨义,测试的是低层次的技能,后来逐渐为人所轻,宋代科举已将这种考试形式逐渐淘汰。唐代进士科从考策问逐渐发展到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形式,其原因是由于策问内容不外乎政治经济时事等经国大事,范围毕竟有限,猜中策题可能性较大,易于揣摩准备而难以辨别高下,而进士科所代试诗赋取材广泛,非博学多才之士,难成佳作。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中所说:“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知今之人不能作。”诗赋可以言志,而省试诗是命题作诗,只有才情并茂、善于思维并掌握了作格律诗技巧的人,才可能临场作好。
律诗律赋这种考试文体还有一个好处,便是有格律声韵可寻,易于掌握评判标准。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说:“唐进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虽知为文华少实,舍是益汗漫无所守耳。”唐人也说唐代进士科所试诗赋中间或暂时更改,但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7]所以钱穆认为:“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8]诗赋考试为宋、辽、金科举所沿用,元、明科举考经义而不用诗赋,但明代以后八股文实际上糅合了律赋的成分在内,而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为了更好地保证考试的难度和区分度,又增试五言八韵律诗。这说明试帖诗作为测验题型,在科举时代有其存在的价值。
八股文在讲究语言技巧方面又比试帖诗更为复杂。八股文是一种极端形式主义的文体。非常苛求文章的逻辑严密和对仗工整,条条框框很多,作文要紧扣题意,一点也不能出格。如试题为《论语·学而》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节,作文时如文章涉及前面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犯上”,如稍涉及后面的“人不知而不愠”则是“犯下”,都属于不合格之列。有的题目又偏又怪,就更难紧扣题意层层发挥了。八股文不仅要求破题巧妙,通篇文章连贯,而且要求每股之间对仗工整,排比对偶最好能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深一浅,这些对偶句往往又很长,特别是议论重心的中股、后股,一股有时长达数十字或上百字,这么长的对偶还要双声叠韵、平仄抑扬,可以说是极其讲求汉语言的修辞技巧的。八股文的逻辑顺序是层层递进,一环紧扣一环,如起讲处不得势,则以下无话可说,即所谓空不得,实不得,一二句说完不得,层数太少不得,太多又不得。清人丁心斋说:“一篇文字如一身之体段相似,搭配须要匀称,方成一个章法。……八股文恰恰起讲是头脸,入题是咽喉项,提比是两臂双手,点题是心正面是胸腹,后股是两股两足,一处不称则一处不成局。……而其中煞有变化,比如画法有立像有坐像有侧像,有起伏转动趋走跳舞之像,而总不离乎四肢百骸,万不能加臀于项,置股于肩。”[9]在极端严格的形式之下,要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字确实不易,所以有些举业家称八股文是“花团锦簇”,与绣花一样,取其搭配整齐巧妙。讲究形式章法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八股文实际上成了一种高级的汉语文字游戏。
有如田径场上的体育比赛,科举考试是一种智力竞赛,而作八股文就像是有严格规范动作的体操比赛。比如双杠运动,限定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规定动作,越干净利落如行云流水一般连贯优美得分就越高,而自选动作越高、难、险、美越能博得裁判的好评。作八股文就是一种智力体操,在规定的程式内作有限的自由发挥,考官也易于评判优劣高下。本来作文是所有考试题型中最难客观评分的,八股文却定出特别的格式,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可能掌握一致的评价标准。加上阅卷的内帘官本身都是科甲出身,老于此道,一般来说善于评卷。清代《国朝贡举年表》卷二载,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各省乡试选拔评卷官员,“考官以鉴拔为主考,不论曾否入闱,监临试以时艺一篇,文理优长者入内帘,荒疏者另执事”。也就是说,尽管都是科甲出身者,但朝廷担心他们及第从政后多年荒疏八股文,要再检测一下,文理俱优者才能选为考官。
容易评定八股文优劣可以举出两个显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乡试,状元出身的吴鸿为湖南省视学,负责挑选科举生员参加乡试,而主持湖南乡试的是著名学者钱大昕和新科状元王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诸生出闱,以卷呈吴,吴最赏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曰‘此五卷失一不复论文矣。’榜发,第六至末仅陈一人,吴旁皇莫释。五魁报至,四生已各冠其经矣。吴大喜,时传为佳话。”[10]由于八股文是标准化的考试文体,考官可以很快地评阅试卷,一眼就可以看出轻重高下。明代杨士聪说:“余每阅卷,不须由首彻尾,不拘何处,偶觑一二行,果系佳卷,自然与人不同,然后从头看起。场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数百卷,可以顷刻而毕,无能遁者。”[11]左宗棠乡试时便是在搜落卷中被挑上的。
另一个显例是状元王以衔。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正总裁窦光鼐善于衡文,所取第一、二名皆浙江人试卷。揭榜后,第一名会元为王以铻,第二名即其弟王以衔,众议哗然,乾隆皇帝心中也感到奇怪。权臣和珅素与窦不和,欲乘机倾陷窦光鼐,于是在兄弟二人闱墨中找出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一句,指出此即为关节。结果抑置王以铻于榜末,停其殿试资格,降窦光鼐四品休致。可是,殿试拆封以后,王以衔仍高中一甲第一名,乾隆皇帝心意释然,问廷臣说:“此亦岂朕之关节耶?”[12]因为殿试主考官名义上是皇帝本人。王以衔殿试仍中状元,说明他的会试成绩肯定也是可信的,于是再录用王以铻入翰林院,窦光鼐官复原职。这一事例说明才智优秀者答卷往往公认出众,一般来说科举考试糊名誊录试卷加以评定,评卷是较为客观题公允的。
正是因为八股文体式复杂而又明了,易于客观地评定优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确能起到智力测验的作用。八股文中的一些小题,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截搭题、枯窘题,更类似一些文字游戏,要做好实在很难。徐敬轩在《初学玉玲珑》中便说:这种枯窘题,路径很窄,惟其路径很窄,故断不能在本位上说话,而要在题前题后题左题右反面正面去设想。及至上到本位,也要刻画字面,洗去意义,推写情景,逼取神气各方面去用功夫。所以练习纯熟之后,就可以精思壮采,层叠不穷,最足见人才思。台湾学者梁若容《谈八股文》一文也说:八股文“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并不能叫做作文。他的好处是法式明了,规格统一,容易学,容易通,无法跑野马,出奇制胜,篇幅短,看卷子比较容易,定优劣更容易。真是聪明的人,只要熟读几十篇墨卷,就不怕作不出好文章。因为这种迷津似的测验,考的是智力不是学力。王守仁、徐光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能在早年得到极高科第,是显著的例子。八股文的考试,不一定埋没多少天才”。[13]有的学者认为,经常参加考试,以努力进修、悉心钻研之故,可使人脑发达,思想周密。还有西方学者说中国人之聪明智慧有时胜过西方人,谓为系得力于数百年中之作八股文,因为常作八股文可以促进人的聪明才智之上进与知识水准之提高。[14]
三、
对科举考试可以测验和选拔才智之士的说法,人们容易产生疑问,也有的论者指出科举时代许多人一旦中举及第便将八股文视如敲门砖弃之不用,因而毫无价值。不错,八股文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其作用确像敲门砖,用完便可丢弃。但它在敲门之时还是很起作用的,这正像现代考试中的标准化的选择题一样,考过之后谁也不去记它,但它的功能就在测试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八股文以及试帖诗等科举考试文体还是具有测试选拔人才的功用的,科举中式者多为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才。
唐宋以后,多数人才是从科举阶梯登上历史舞台的,[15]而明清以八股试士之后,各种人才也多由八股时文一途进身。中国古代科技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等人也都是进士出身。在文学方面,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绝大多数文学家参加过科举考试,而且大多数文学家是由进士、举人等科第出身的。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有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56.6%。而且这还不包括诸生(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若再考虑到《辞海》所录作家有些是略载其科第内容(如吕祖谦便漏载其进士出身)、女作家从不应科举考试这些因素,科举出身者在作家中的比例还会更高。当然,有些伟大作家并未考中进士,但绝大多数人至少参加过科举考试,从未尝过科场甘苦者只是极少数。
科举考试的目的毕竟不是选拔文学家或科学家,而是选拔从政人才。一般进士和举人入仕后主要精力也是用于行政事务上,在文章学问上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政才、学术,本自异科”[16]。《儒林外史》第49回中迟衡山便说:“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科举选拔了许多后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才,说明其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至于那些不仅在政事上有业绩,在学问上也有较大成就的人,主要还在于他们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从学而优则仕走向仕而优则学,或者说能够做“以学为业,以仕为道”。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隋唐以后多数是由进士出身的,如唐代的张九龄、陈子昂、刘知几、颜真卿、王维、裴度、陆贽、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郭子仪、柳公权、李商隐、杜牧等,宋代的寇准、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蔡襄、苏轼、苏辙、沈括、程颢、黄庭坚、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湛若水、王守仁、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张謇、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等人,多得不胜枚举。这些人在历史上出类拔萃,建立了丰功伟绩。当然,在历史上进士及第者中也有一些无所作为的人,这也不足为奇。我们知道,现代许多研究表明,人才的成长在一定的阶段智力很重要,凡有大成就者多为高智商者。但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不是主要看智力了,起作用的往往是非智力因素。科举考试仅为进士和举人们从政提供一个机会,入仕后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所起作用的大小,关键在自身的综合才能,道德品质、阅历、性格、气质及社会环境和机遇也起重要的作用。
由于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智力测验性质,所以总的说来聪慧者较可能一举成名。倘若一个人的考试生涯可以有50年,那么,在明清时代就有36次以上童试机会,考中秀才后一般有16次的乡试机会。有些人是长期困顿科场,白首仍是童生,而金榜题名者平均年龄进士是35岁,举人是30岁左右,秀才是24岁左右。[17]从朱熹考中进士的一榜,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同年小录》统计,331名进士中,一举成功者有142人,二举为73人,三举39人,四举43人,五举18人,六举11人,七举2人,未详3人。在已知应举次数的328人中,平均应举2.15次,而朱熹及《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中的著名人物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都是一举成名者。明清时期许多著名人物也是善于做八股时文,登第后扔掉此敲门砖,然后在学问和政事上做出成就。
然而,应该指出,科举考试内容为经术与文学,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而八股文的祸害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这种复杂精细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涉,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因其内容空疏,接近于一种文字游戏,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唯其如此,清末才会将废八股作为改革科举的头等大事。而一旦不再用于科举,除了测试功能之外一无所用的八股文便水流云散,迅速成为历史名词。在八股先废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本身也来不及完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转变,于1905年接踵而亡。
注释:
[1]鲁讯:《伪自由书·透底》,《鲁讯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2]F·H·Ewer:"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 The Chinese Reco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3,No.11,April 1871,pp.330~331.
[3]W·A·P·Martin:"Education in China."in" Hanlin Papers,or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the Chinese".London & Shanghai,1880,p.104.
[4]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第1卷1期,1935年。
[5]姚德昌:《历代进士之间的血缘关系举隅》,《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6页。
[6]徐玖平:《考试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页,
[7]《唐会要》卷七十六《进士》太和八年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1页。
[8]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见《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05页。
[9]丁心斋:《科名金针》“炼字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版,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本。
[10]佚名:《国朝贡举年表》卷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十八年申江袖海山房石印本,第45页。
[11]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借阅山房汇钞本,第56页B面。
[12]《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63~3164页。
[13]转引自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18~319页。
[14]侯绍文:《八股制艺源流考》,载台湾《人事行政》第22期,1967年5月。
[15]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16]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四《建置志·建宁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页。
[17]刘海峰:《论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