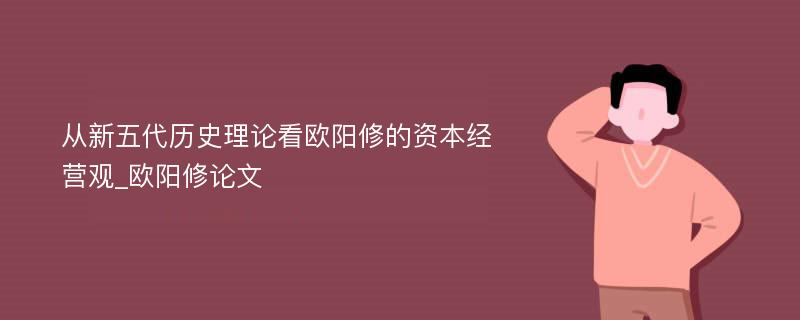
试从《新五代史》史论看欧阳修的资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欧阳修论文,新五代史论文,资治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开一代风气的史学大师。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一生著述很多,在史学方面有《新唐书》(与宋祁合著)、《新五代史》、《集古录》等,其中尤以《新五代史》最著名,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原名《五代史记》,记载了自后粱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宋祖史记,故文章高简。”①《宋史·欧阳修传》也说该书“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可见,文词精炼,褒贬议论,是该书特点之一。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论较多,全书共有58处之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史论并非指包括“历史观、历史哲学和史书撰著方法论,评史原则、史学功能原理等内容的广义上的史论”,②而是专指针对五代史事、人物、制度等所发的正面评论。这些史论从在全书位置的分布来看,或冠于卷首(共16处),或藏于卷中(共17处),或位于卷末(共25处)。其中绝大多数(共48处)都是以“呜呼”开头,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具体分析全书这58处史论,可得知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包括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关系等)、伦礼道德以及天人思想等三方面。从上述三方面在全书总史论的比重来看,政治类的史论占百分之五十,是名符其实的重中之重。这些史论反映了欧阳修一贯的“垂劝戒,示后世”的治史目的,表现出作者极强的现实感和出色的资治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论正是该书核心所在。鉴于此,本文试从下述四个方面具体谈谈欧阳修的资治观,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为时而著,于世有补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说:“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即《新五代史》)为私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欧阳修单单借五代史事大发议论?为什么他要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旧五代史》的情况下,还要私撰另一部五代史呢?这些都是本文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其一,我们应认识到五代是一个“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德,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③的漆黑混乱的时代。在它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政权更替频繁,共有八姓十三君,而每一次政权转移,不是经过赤裸裸的战场厮杀,就是经过刀光剑影的宫庭政变而来。其结果只能是使社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民不聊生。正如欧阳修所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④而北宋王朝正是建立于五代基础之上,建国伊始,可以说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受五代直接或间接影响。北宋统治者出于其自身对乱世的体验,因而便着手定祸乱、整秩序、兴生产,使国势趋强,百姓渐安。然而到了北宋中期,统治江河日下,逐渐转向衰败,具体表现为吏治败腐、国库空虚,在“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⑤等政策的残酷剥削下,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如此,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发动进攻,给北宋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欧阳修敏锐地洞察到“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于五代之时”。⑥
其二,随着北宋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出现,一大批学者从现实出发,“不惑传注”,使当时的学术思想在单纯沿袭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重视历史的“资治”,“求鉴”功效。欧阳修作为这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学者中的突出代表,极力主张历史应为现实服务。欧阳修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王安石称赞他“果敢之言,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二十四岁中进士,自入仕以来,就反对“上因循,”“偷取安逸”的腐朽政治。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指责司谏高若纳庸陋,结果“若纳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⑦该年,欧阳修“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⑧开始着手修撰《新五代史》。实际上是借修史之名,抒自己愤闷之情。历时四年后归京任谏官,知制浩等官。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他又积极参加“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以吕夷简、高若纳等贵族官僚利益,欧阳修等被诬为朋党而赶出朝廷。欧阳修“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⑧他通过仔细考察五代并联系当前现实,认为《旧五代史》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⑨这可能就是他不惜以一人之力,耗十八载时间与心血撰写《新五代》动机所在,也是他借五代史事大发议论的直接原因。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他在给友人梅圣俞的信中说:“此书不可使小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⑩至于其缘由归结到一点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尤其是史论大胆影射时政,使之昭然若揭,表现了作者“垂训将来,警戒世人”这种强烈的资治思想。
二、切中时弊、论古鉴今
如前所述,针对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欧阳修以史家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借唐末五代之变故,大发议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北宋现实,另外对北宋的岳制、民族也有所针贬。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专门写了一篇《唐六臣传》,通过“白马之祸”,从理论和史事上对“朋党”之说的危害进行了阐述。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之”。(11)本篇传意在影射庆历年间上谀皇帝,下诬百官的权臣吕夷简、高若纳,章得象之流。在“庆历新政”期间,正是这伙小人奏“仲淹、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纪,凡所推荐,多挟朋党。”(12)之诬言,使得“帝不悦,遂并黜之,”最终导致新政失败。欧阳修义愤填膺,痛斥他们是“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欲阪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13)的奸诈小人。作者在这里,借古讽今,议有所发,论有所指,指桑骂槐,抨击时政,表达了作者无比愤慨的心情和忧世、忧国之意。
欧阳修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指责皇帝的昏庸无为时,不象斥责小人、奸臣那样直接,那样痛快淋漓,而是间接地、含而不露地旁敲侧击,在方法上更加高明,更加灵活多变。如他在《本纪》中对五代八姓十三君不仅没有具体予以贬斥、丑化,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褒扬了唐明宗、周世宗的仁明有为。他说:“(唐明宗)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是一位“为人纯质、宽仁爱人”(14)的好皇帝。对于周世宗,他是这样评价的,说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夏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及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议论伟然。”(15)他这样写其用意在于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轼相寻”。(16)“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17)的乱世,倘能有象唐明宗、周世宗这样的明君,指责北宋没有或少有贤明君主,进而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报国无门。他进一步说:“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匠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18)写到这里,欧阳修直言为君者的重要性,其言下之意,话外之音是为自己政治遭遇尤其是庆历新政无罪被贬而感叹,指责宋仁宗任用群小,听信谗言,使自己虽有报国之志,兴国之材,而无成己志之君。正是由于欧阳修把矛头指向当朝最高统治集团,因而当宋廷命他进呈《新五代史》时,他以“精加考定,方敢投进”(19)为由婉言谢绝了。实际上他是担心《新五代史》史论所表现出来的不满现实,抨击时政的思想一旦被朝廷察觉,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找了一个还需“精加考定”的理由遮掩过去。这虽然有着时代和欧阳修个人的局限性,但从另一面,欧阳修不敢贸然投进《新五代史》这恰恰表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资治观。
其次,欧阳修联系唐末方镇之旧事,对宋朝军队出现的问题忧心忡忡。他说:“(唐)既其衰也,置军节度,号为方镇。……故其兵骄而逐帅,师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20)在这里,欧阳修之所以重提唐末方镇的专权、叛乱,意在以古鉴今,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性。北宋王朝建立后,“兵变”事件就屡有发生。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兵变”愈演愈烈,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兵变”事件除一部分是属于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反压迫斗争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士兵骄恣横行、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而引起,沿袭了唐王朝安史之乱后的“兵骄则逐帅,师强则叛上”的遗毒。欧阳修以此告诫宋朝统治者要防止武人专横跋扈,重演藩镇割据之悲剧,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担忧和不满。
此外,欧阳修还对北宋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有所针贬。他专门编写了《四夷附录》,介绍了契丹、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渊源、发展等。他以后周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为例,进而指出“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必因其强弱”。(21)又说:“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覊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22)欧阳修借此指责宋朝统治者“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23)的对辽、西夏妥协保守政策,并警告当世统治者应“富兵强国”,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来犯的少数民族政权以保境安民。
三、倡忠义廉耻、志于为治
北宋以后,一场新儒学运动广泛兴起。在这场运动中,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心社会现实,提倡所谓“道德性命”之学,针对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的现实,决定重整伦常道德以安定封建秩序。欧阳修一向主张“道德仁义,所以为治”。(24)他说:“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士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25)进而又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26)从而他得出伦常道德是关系封建国家治乱存亡之根本的结论。
当时北宋吏治腐败不堪,表现之一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吏的贪污受贿。据历史记载,宋真宗时,镇州知州边肃:“私以公饯贸易规利,遣吏强市民买女口自入”。(27)表现之二是官员冗滥,为官“但求无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极少数能为国至忠,图国忘身。针对日益腐败的吏治,欧阳修认为要予以改变就必须“人人要有礼义廉耻,”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8)鉴于此,欧阳修极力表彰那些有节、有义之士,树之为典范、标兵,以此警诫,教育当世官僚。例如他交口称赞“以廉平自励,民甚赖之”的后晋复州刺史郭延鲁,指出“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民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29)他还创立《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等,将那些“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或“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天下者”的事迹搜集起来加以表彰。
与此同时,欧阳修又猛烈谴责寡廉鲜耻之徒。如他在《杂传序》中说:“其(指冯道)可谓无廉耻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冯道这个不倒翁的丑恶面目。又如在《唐六臣传》中,欧阳修描写张文蔚、杨涉等唐朝六大臣趋炎附势、卖国求荣的丑态,斥责他们为“皆庸懦不肖,倾险狡猾,趋利卖国之徒”。(30)另外,欧阳修对那些绝人伦灭天性的人也深恶痛绝。如他将“以子轼父”的友珪“不得列于本纪,”并说明他这样做是为了“伸讨贼者之志”。(31)又如他将后晋问阳行军司李彦珣 “弯弓射其母”一事与晋出帝绝其父相提并论大发议论说:“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32)
虽然欧阳修把儒家伦常道德绝对化、神圣化,过分夸大了礼义制度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他这样做有其较强的现实意义,他通过考察五代礼乐崩坏的情状,予以正反结合,或褒或贬,以此教育世人尤其是统治上层。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努力克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实践着他一贯的资治观。
四、反讳迷信,轻天命重人事
谶讳迷信,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出现。《四库全书总目》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讳者经之交流,衍及旁义”。谶讳神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决定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和发展。这种荒诞的神学在以后很久时期内为人们所尊信。到北宋中期,一方面在“不惑传注”、“疑古辨伪”等思潮的冲击下,旧经学中的谶讳迷信等旧因素被剔除;另一方面一些疑古勇士又以理学的眼光不断总结和补充经学,使经学这只旧瓶装上了理学这新酒。欧阳修所为理学的先驱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谶讳迷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在编修《新五代史》时,一反传统体例,独具匠心地不设《五行志》,而只立《司天考》。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所表现出来反谶讳迷信的强烈思想,更重要的缘由还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公元1004年,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以屈辱条件换得苟且安定。对内为愚弄人民,粉饰太平,便伪造“天书”,大搞谶讳迷信,使“一国君臣如病狂然”。(32)然而一纸“天书”不能改变北宋“兵弱财困”的现实,于是随着宋真宗死去,“天书”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结束了这场自欺欺人的骗局。欧阳修以其独特的时代感和责任感,要求朝廷“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讳之文。”(33)以适应时势发展。
分析《新五代史》涉及此类的史论,不难发现欧阳修反谶讳迷信主要是反天人感应、祥瑞灾异说。他针对五代出现的祥瑞现象说:“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见惑者有以思焉。”(34)欧阳修通过叙述“麟、凤、龟、龙,王者之瑞”皆“出于五代”这个动乱时代这件事,说明所谓“王者之瑞”的出现是“有道之应”的祥瑞说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欧阳修还反对灾异之学,他深感:“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35)因而他对于“吴火出杨林江水中,闽天雨虫之类”嗤之以鼻,说这些“皆非中国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书矣”。(36)欧阳修意在将上述祥瑞灾异现象与北宋伪造“天书”予以对照,揭露北宋统治者倒行逆施,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欧阳修轻天命思想又体现在重人事的作用方面。他对天人关系作了具体阐述,说:“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37)他继承古代“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并阐发为:“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38)进而直之以言:“天,吾不知……若人,则可知者。”(39)欧阳修这种重人事而轻天命的思想,实际上是他联系个人政治遭遇,重在说明人事的好恶直接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欧阳修以后唐庄宗前期励精图治,使得“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后来宠信伶人,骄逸放纵,结果酿成“数十伶人围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40)的悲剧为例,说明:“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41)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42)乃历史古训。他对后唐大理寺卿康澄提出的为国者“五不足惧,六深可畏”的观点深为赞同。即三辰失行,天象变见,小人讹言、山崩川竭、水旱虫蝗这五不惧;而贤士藏匿、四民迂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这六可畏。他说:“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43)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论通过叙述天人关系并予以具体化、比较化,然后绕过这个圈子,使其终极点又回到资治观上来,所论指的仍是北宋现实。欧阳修一面抨击吕夷简、高若纳等奸臣小人倒行逆施、诬害忠良如历史上的伶人、宦者、女色之祸;另一方面又指责当朝皇帝闭目塞听,逸豫无为以致败国害民。欧阳修在这里将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之例予以对照之笔,努力地压抑个人情感,将五代之史鉴最大限度地反馈于社会,反馈于世人。
如上所述,欧阳修从政甚久但仕途坎坷,时而升迁,时而贬降,因而他对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矛盾与问题都有着很深刻的个人体验。尤其是“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被贬在外,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逐渐升级,由反感到厌恶,最后到了仇恨这样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然而他苦于自己一介文人,空有兴国抱负,却得不到统治者的任用与赏识;又不能振臂一呼,扭转乾坤。出于对现实的极端无奈与对统治集团的再度幻想,欧阳修决定另辟蹊径,象以往和当时大多数文人学士一样,潜心撰写史书,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融入其史论,发思古之幽情,抒忧今之哀志,尽可能地将自身的现实感升华。
《新五代史》史论以其精辟的论述和直率的面目,就象一个历史老人站在当世人们面前,娓娓而又伤感地讲述一段五代乱世史事,或褒或贬,讲到最后又常留给人们一个意味深长、耐人回味的结尾,让人们陷入一种持久的沉默与深邃的思考,以此达到作者预想目的。作者之所以能使人们随着他自己的思想变化发展而冷静地考察现实当局,可以说这主要得助于他深具功底的史识和出色的资治观、现实感。
与传统的中国史论一样,《新五代史》以“史论寓政论”的形式使其史论起到“以史论政”的作用,实具有帝王将相政治教科书的性质。(44)欧阳修从北宋“内忧外患”的现实出发,通过仔细分析并不同程度地评价五代人物、史事、制度以及天人思想,将其投影在北宋这个社会的大屏幕上,使之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历史——现实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资治观就好比是中心;其他关于五代政治、伦常道德以及天人思想的史论就象是具有强烈向心倾向的向心力,充分地靠近中心并辅助它更好地运动、协调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新五代史》史论对现实揭露得还不够彻底、有力,这主要归罪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未能提供给人们自我保护的权力,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尤其那些“伴君如伴虎”的大臣,因而我们不能不顾时代去苛求古人。而事实上,欧阳修却在努力地克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尽可能地实践着他一贯治史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五代史》虽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的“资治”之书名,却有“资治”之实。毫无疑问,把欧阳修说成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一代史学大师是不过份的。
本文收稿日期:95-5-24
注解:
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二。P411
②参见白寿彝等主编《文史英华》史论卷
③《新五代史》卷17《家人传》
④《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
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
⑥《居士外集》卷9《本论》
⑦《宋史纪事本末》卷29《庆历新议》
⑧(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
⑨(17)参见《新五代史》出版说明
⑩(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9《与梅圣俞》
(11)(13)(30)《新五代史》卷35《唐六臣传》
(14)(43)《新五代史》卷6《唐本纪》
(15)《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
(16)《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
(18)《新五代史》卷31《周臣传》
(20)《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
(21)《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二》
(22)《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23)《读资治通鉴长编》卷32
(24)《新五代史》卷46《王建立传附子守恩传记》
(25)《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
(26)(28)《新五代史》卷54《杂传》第42
(27)《宋会要辑稿》职官64之22
(29)《新五代史》卷46《新传》第34
(31)《新五代史》卷13《梁家人传》
(32)《宋史·真宗记》
(33)《奏议集》卷16《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札子》
(34)《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
(35)(36)(37)(38)(39)《新五代史》卷59《司天考第二》
(40)《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
(41)(42)《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44)参见张啸虎《欧阳修史论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