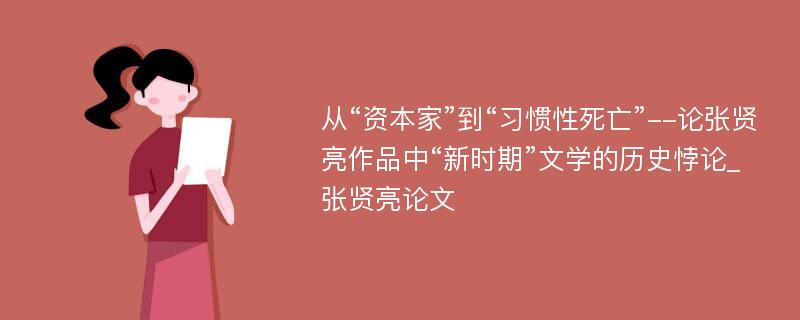
从“大写的人”到“习惯死亡”——由张贤亮作品看“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吊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新时期论文,习惯论文,作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小说”与“小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写道:“小说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小说记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而小说本身的质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因此,“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于是,王德威进一步提出“小说中国”的概念。他说:“但由小说看中国这样的观念,毕竟还嫌保守。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德威的观点,至少表明了两个意思。其一,现代小说始终是和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相联系的;小说的发展脉络,“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表征”。其二,也许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是现代性叙事这种现代中国最大意识形态的表征——或者,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是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它同时也是在通过“想象、叙述”来“规训”我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现代性叙事的认同,通过虚构与想象来推动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和生产。王德威的观点让人不仅想到了赫胥黎的名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创造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实现了对伊格尔顿思想的继承,指出了思想意识生产文学,文学反过来又生产思想意识的循环。李杨因此评价说:“将人们熟悉的‘中国小说’改变成‘小说中国’,表面上看只是简单地改变了概念的顺序,实际上却是改换了研究文学的方式。”(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67、194、19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德威针对现代中国文学提出的“小说中国”概念,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对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上面。实际上,“新时期”文学的叙事是以对“文革苦难”的回忆和对“现代化明天”的展望为肇始的。“新时期”以来,对“文革苦难”的叙述不约而同地成为文革后复出的一代作家与知青作家共同的书写主题。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苦难”历史的叙述不仅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同时也在为我们反过来生产新的思想意识。或者说,“让历史告诉未来”。正如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新时期”文学中对苦难的叙述事实上是借批判“文革”生产现代性话语。(注: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进一步说,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也正是文学叙事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它通过对往日“伤痕”的抚摸,获取今天“康复”的证明与明日“健康”的想象,从而顺利完成对民族浩劫“为了忘却的纪念”,实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和内在凝聚力的重新整合。戴锦华认为,这种整合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和“社会的再度分化与重组”的开始。(注:戴锦华《涉渡之舟》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现在看来,“新时期”文学在“控诉”和“展望”的背后其实充满了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面对现代性的焦虑。其症候有二:首先,是对于“文革”过于简单和“一刀切”的“剔除”与“遗忘”,却忽略了它所蕴涵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面;其次,是对于“现代化”不加反思的渴望与承接。具体地说,“新时期”文学显然将“文革”和“现代化”有意设置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通过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来赋予“现代化”在中国的合法性。或者,更精确地说,否定“文革”和呼吁“现代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体两面。在这里,否定和呼吁主要是通过对“文革”这一“蒙昧”、“混乱”、“反人性”时期的批判——同时自然产生对“启蒙”、“秩序”、“人性”这些现代性叙事的关键词的诉求——来进行的,所以,在今天反思80年代时,“新时期”文学又被更精确地命名为“新启蒙主义”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交,“新启蒙主义”文学在“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基础上,重新发出“文学是人学”的呼唤,并且提出“大写的人”作为自己旗帜鲜明的口号。这种文学思潮在历史层面上试图和“五四”启蒙精神接轨,同时也暗示了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启蒙道路上的“断裂”和“空白”,将它草率地描叙为封建和专制媾和的怪胎。这种“断裂”和“空白”也体现在“新时期”对于文学史的编撰上。在现实层面上,“新启蒙主义”文学则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以文学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来阐释走西方的“现代化”——也就是“全球化”——道路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今天来看,“新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意识显然是成问题的。而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潮不加反思的匆忙承接——同时也是对于民族遗产和传统过于简单的告别。甚至“新时期”自诩的“五四”源头本身也存在这个问题,即将“传统”和“现代”过于僵化地“构造”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忽视了其间的互动和转化。换句话说,“新时期”中国在“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转折期,缺少当年德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时在文化政治上的审慎和自省。进一步说,“新启蒙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认同与承接是建立在只承认一种现代性——也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的,它同时也暗含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一系列“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实践探索的粗暴否定和简单拒绝。这种对现代性的迷信导致“新启蒙主义”急切地向西方镜像进行全面模仿,却全然不知这种模仿最终会导致迷失自己。
当然,迟到的反思尽管“滞后”,却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新启蒙主义”文学走到今天,已经日益失去其对于时代积极的一面,呈现出其负面和消极的色彩来。而相应地对“新启蒙主义”文学的反思,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今天文学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而且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诸多思考。
本文正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试图以张贤亮作品为主要文本,来考察“新启蒙主义”文学的内在逻辑,探询它是如何由“解放人性”走向它的反面。或者说,是如何由“大写的人”这个旗帜性口号,走向“小写的人”,乃至演变成人的“精神死亡”这个最终结果。
二、“身体的意识形态”与“肉体修辞学”:“大写的人”背后的“新启蒙主义”逻辑
李杨曾经通过对《红岩》的文本分析提出了“身体的意识形态”说法。他说:“《红岩》与‘样板戏’最为接近的一个地方,是对‘身体’——准确地说,是对‘肉身’的排斥。这一艺术手法在将50年代的道德艺术化的修辞方式发展到极限的同时,也展示了现代性特有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终极形式,即由‘个人’与‘家庭’的对立发展到‘民族国家—阶级’与‘家庭—个人’的对立,最终发展到更为抽象的人的‘精神’与‘肉身’的对立。”(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67、194、19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身体的意识形态”叙述,在将正义者身体苦难神圣化的同时也净化甚至排斥了其基本的身体欲望,从而将处于二元对立位置的精神最大限度地纯洁化。“在这里,敌我双方的政治对抗被简化为‘精神’与‘肉身’的对抗,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共产党员几乎没有任何肉身的踪迹,因此对共产党员的肉身摧残不但不能伤害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反成为了对共产党人精神纯洁性的考验,而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却无不生活在‘食’、‘色’这些最基本的身体欲望之中,在这种最卑贱的动物性中无力自拔,‘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始终无法了解和进入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注: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67、194、19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实际上,这种对“身体的意识形态”叙述也延续到了“新时期”“复出的一代”的叙述上。而其对身体苦难神圣化的表述,也就是通过磨难衬托出受难者的圣洁品格和崇高理想。可以说,在从维熙的作品里最典型地继承了50—70年代对“苦难”的写作模式。这种叙事主要刻画“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灵魂的“纯净”和道德的“完美”,如《雪落黄河静无声》中,范汉儒被描写成“看不见他身上的一点杂质,透明得就像我们医药上常用的蒸馏水”。这种叙述让我们想到了“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这样的名言,它本身就暗示了某种“非常人性”。
张贤亮也正是带着这种思路写作《灵与肉》的。作品描写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特定条件下,如何通过劳动的磨炼和对身体的考验,“成长”为具有纯洁精神和坚定信念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张贤亮的写作一开始就带有复杂的异质性和含混性。从某种意义上,他笔下的人物比从维熙书写的更具有人的主体特性。张贤亮喜欢描写具有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遭遇,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西方的启蒙主义哲学里,具有人道主义和思想的自由解放这些含义在里面。同样的,在经典文学里,它比无产阶级更具有肉体性和欲望性。而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更让这种对“身体的意识形态”叙述带有复杂性和暧昧性。
在此后的《绿化树》里,这种叙述的异质性和含混性更进一步明晰为对劳动改造的疑问、质询、屈辱和背叛,作品叙述甚至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笔调。在这里,大自然不再像《灵与肉》里的那样充满诗意,是可以用来欣赏和陶冶灵魂,甚至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风景,而是和对更迫切的身体需要联系起来。作品一开始,被饥饿折磨的主人公行进在去农场就业的路上,他看见路边的稻田,心里的念头是“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接着,作者进行了一大段风景的描写:“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但是,在这样美好的自然面前,章永璘却感到“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
实际上,张贤亮在这里清楚地呈现出自己创作思想的演变脉络。这就是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导到“新启蒙主义”文学的创作思想的转变。进一步说,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张贤亮已经有意无意地对经典革命文学里的正面人物形象进行解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新启蒙主义”文学的“人”的理念:即人不仅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是身体上的;即使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也有自己的肉体性和欲望性需要。
因此,张贤亮在宣称自己的作品是“政治小说”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它的人本主义含义:“政治遭遇,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形式。我并不着重去写主人公面对的政治……作家只有面对人本身,也就是面对自己内心,才能在‘人’这个大题目上和整个人类取得共同性。”(注:张贤亮《追求智慧》第22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灵与肉”的冲突让经典革命文学里的“身体的意识形态”叙述逐步转变为“新启蒙主义”文学中的“肉体修辞学”。显然,在张贤亮看来,只有将精神需求和身体需求兼顾起来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同戴厚英相比,张贤亮笔下的人物从另外一个方面发出了“大写的人”的呼吁。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灵肉冲突”与走向对立面的启蒙
“新启蒙主义”文学通过“肉体修辞学”的叙述,将社会主义“新人”由叱咤风云的英雄消解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但是,读者们很快发现,这种对于人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所谓“大写的人”,更没有实现人性和精神的升华,相反,在“新启蒙主义”文学里,到处游走的却是一些极端自我主义的“小写的人”,所谓人性的“解放”蜕变成欲望的露骨释放。这个方面,《绿化树》中的主人公章永璘无疑是个典型。
章永璘先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然后被安排到另外一个农场就业。但是,苦难和劳作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在许灵均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升华,劳改农场也并没有将他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所谓“新人”。相反,在经受着饥饿折磨的主人公内心,“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因此他费尽心机从伙房弄来稗子面煎饼吃,从蒸笼布上刮下馍馍渣吃,甚至不在乎被“营业部主任”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当然,求生到底只是人的原始需要,对章永璘来讲,欲望的野马始终在现实的栅栏里冲突着,时刻向往在栏外那片原野上放蹄驰骋。《绿化树》不仅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章永璘的现实遭遇,更淋漓尽致地给读者呈现了他的“灵肉冲突”。而女性的抚慰和对性爱的渴求无疑成为他迅速长大成“人”的“催化剂”。《绿化树》里,在马缨花满足了章永璘饥饿的需求以后,后者肉体飞快地成熟起来,而这同时导致了精神上的变化:“肚子吃饱了之后,我发觉有一种非常隐秘的东西在撩动我的心弦”。一种崭新的情感——爱情——在章永璘的内心像春天的野草一样悄悄地成长。因为爱情的力量,章永璘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当圣母般的马缨花填饱了他那干瘪的肚子,并指点着他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时,章永璘不无痛苦地发现,在情爱的表达方式和性爱的道德观念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差异。章永璘在拥有了爱情的动力后,开始“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和一度泯灭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苏醒过来。他开始发现自己和马缨花、海喜喜之间根深蒂固的差距——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差距。
正是在这里,“新启蒙主义”文学无意识中暴露了自己的内在逻辑——将因为质朴而显得愚昧的下层民众作为界定自己“文明”和获取优越感的他者和反面。实际上,“新启蒙主义”文学也正是在这里走向启蒙的对立面,因为正是像大地母亲一样善良无私的劳动人民代表着“大写的人”的真正内涵。
在《绿化树》里,无法和劳动民众认同让章永璘发出了对原来认可的“自由”、“理想”的怀疑和迷惑:“过去朦胧的理想,在它还没有成型时就被批判得破灭了。”“我虽然自由了,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落在某一处实地上,相反,更像是悬挂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章永璘的联想和迷惑让人想起了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对“轻”和“重”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也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注:米兰·昆德拉著、安丽娜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页、前言第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这里,昆德拉提出了一个严肃和让人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轻与重”的问题。它实际上在质问人自己:在人漫长的生命旅途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必须坚持和不能背叛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关系人的存在本身的终极问题。昆德拉的提问和章永璘的疑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理解一种存在的可能。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解释说:“全部小说都不过是一个长长的疑问。”(注: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第29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无论有意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注:米兰·昆德拉著、安丽娜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页、前言第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很多学者都将郁达夫式的“欲情净化”作为知识分子灵魂反思的典型,但是,章永璘和郁达夫笔下充满忏悔的知识分子却有很大不同。他并没有在“情智矛盾”、“灵肉冲突”面前止步,反而让新一代中国智识者打上了西方个人主义“恶”的印记。
在这里不妨对二者进行一下具体分析。黄子平曾经对郁达夫式的“欲情净化”发表了有趣的看法。他认为,在郁达夫作品里,作为个人主义“自我”的知识分子面对下层民众流露出来了“人道主义的理性掺杂着自我谴责的复杂情感。”而这样的痛苦,是从‘旧营垒中来’的阶级背叛者的痛苦,是面对着必然的历史进程走向新兴的阶级时的痛苦。这就预示了我们的叙事模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劳动者的形象日渐高大而纯正,知识者对自己身上的‘鬼气’日渐自惭形秽。面对着劳动妇女的正直和善良,‘欲情净化’就不仅是一种生理、心理、道德上的自我超越,而且带有某种历史哲学意味的升华了。”(注: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而在章永璘这里,“自我”与下层民众的相逢是被迫的,他们一方面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另一个面,他们在内心仍然感到自己和下层民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和下层民众产生惺惺相惜的精神共鸣。在章永璘这里,痛苦不是“从‘旧营垒中来’的阶级背叛者的痛苦”,而是想回归到自己原有的身份认同而不得的痛苦。他们虽然为劳动者的朴素无私感动,同时却在内心对劳动者有一种轻蔑感。作为个人主义“自我”的知识分子正是以劳动人民为二元对立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考察张贤亮的作品,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内心仍然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感和自恋感。在这里,不是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仰视,而是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的仰视。因此,才有一个个“书生落难,妇人相救”的“叙事模式”。也因此,章永璘他们一方面因为“劳动者的形象日渐高大而纯正”产生了忏悔的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为自己内心的卑鄙情感寻找合法性。正是在这里,“新启蒙主义”文学的内在逻辑昭然若揭。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张贤亮将这种逻辑推向混乱。肉体的需要让章永璘对文明的作用进行了“价值重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在这种强烈却原始的需求面前,章永璘决定向黄香久求婚。在开口的那一瞬间,他对自己即将行动的爱情成分进行了审视、怀疑和否定:“可是,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显然,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张贤亮对贯穿《灵与肉》和《绿化树》的主题“让苦难改造灵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章永璘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任凭灵魂的堕落,他甚至感到了堕落的快感。
尽管如此,身处苦难之中的章永璘并没有从关怀他的劳动人民身上感到惭愧,相反,他复杂而幽暗的灵魂更加呈现出自私和丑恶的一面。在章永璘的心目中,黄香久仅仅是发泄情欲的工具,吸引他的仅仅是对她“立体感和肉质感”的身体探索,至于她淳朴的内心世界,章永璘则毫无兴趣。黄香久脸上洋溢的“很纯净的天真”和“超凡脱俗的光辉”,显然和《黑骏马》里额吉身上的光芒一致,是大地母亲的象征体和承载者,但是在章永璘看来却显得非常愚蠢。
曾有论者指出张贤亮作品里的“恋母情结”,其实在张贤亮笔下人物的理性世界里,“恋母”倾向只是以辅助性面貌出现的,自我永远是结构核心,自我超越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女性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对于这一目标的催化:要么如马缨花那样鼓励,要么如黄香久那样刺激。她们只是“过程”而难以成为“目的”。这是作品显得“残酷”的又一体现。正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提到的:“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恋于儿女私情的人”,“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持撑自己”。因此,当黄香久利用自己的身体和爱情治愈了章永璘性无能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她的使命。故事的结尾,张贤亮借着她同曹学义的私通情节,让章永璘以投身政治风暴、避免连累对方为由将她离弃了。女人创造了男人,男人却割断了彼此血肉相连的精神脐带,并且以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这样崇高却虚伪的名义,迅速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天地。
可以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展现知识分子在精神成长与蜕变过程中的“心灵史”,同时也是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走向堕落的背叛史。寻求个人主义“自我”的思想实践最终走向它的反面。而这种精神的堕落与背叛,只能导致精神的最终死亡与意义的终结,与之对应的,则是身体哲学的盛行与肉体的狂欢。
四、越堕落越快乐:欲望哲学或意义的终结
在后期作品里,张贤亮更多地将笔触放在对精神“死亡后”的内心状况和个体实践的描述上,试图通过这种描述,反映在理想丧失后人的痛苦、迷惘、超脱或者堕落。这种反映是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完了”的叫喊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完了”象征了章永璘精神的一面:徒然是一具丧失了灵魂的“废人”。而在《习惯死亡》里,这种对精神“死亡”的敏锐意识已经退化为一个令人麻木的“习惯”。在丧失了精神动力后人更多地转向欲望与本能的驱使,因此,在《习惯死亡》里对“完了”的叙述就像音乐剧的主旋律一样贯穿始终。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同的是,“完了”在这里已经不是抗争的呐喊与呼叫,相反,它是人在精神“死亡”后的“一声叹息”,更是在“习惯死亡”后,快乐的欲望呻吟。
这种堕落无疑是和对理想信念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在《绿化树》里,“死亡”成为对一个无神论者在马克思主义信念丧失后“最轻松的解脱”,这里的“死亡”无疑是指精神维度上的,是对丧失理想和信念的一种比喻和修辞。《习惯死亡》的主人公更是以一种变态心理疯狂地渔猎女友,因为他已经不能再过普通人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张贤亮深刻地揭示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悖论。那个在精神上“大写的人”,那个一直到死都在迷恋“意义”的人已经“死了”,苟活的只是本能的载体。因此作家才能在成功地做爱之后产生一种被枪毙的感觉。在《习惯死亡》里,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作家在信念破灭之后开始对所有神圣与崇高性的东西不相信,他转而依赖“跟着感觉走”的身体哲学: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是饥饿挽救了我,使我不至于陷入思考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饥饿,复活了以后我就会想“我是谁?”想什么狗屁的人生悲剧,我的肚子虽然空虚但早就灌满了哲学家关于生与死的名言,那些狗屁肯定会折腾得我再次死去。(注:张贤亮《张贤亮小说自选集》第410页,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
在这里作家发表了一番自以为是看破红尘的高见,其实却是和世俗同流合污的牢骚,是知识分子在精神“死亡”后选择堕落的“告别宣言”。当然,这种从追求崇高到“自由”堕落的转向,对一个曾经迷恋“意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会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它却是“新启蒙主义”的必然逻辑。而这个发展脉络似乎和张贤亮作品的主题演变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性:从对“大写的人”的呼吁到宣告人之精神的“死亡”,从对人性进化的乐观到欲望狂欢的开始。《习惯死亡》于1989年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同时出版,这个时间本身就蕴涵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意味。它意味着一个以对“现代性”的美好想象为肇始的“新时期”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重新认识“自我”和时代的开始。
标签:张贤亮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人性论文; 灵与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习惯死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