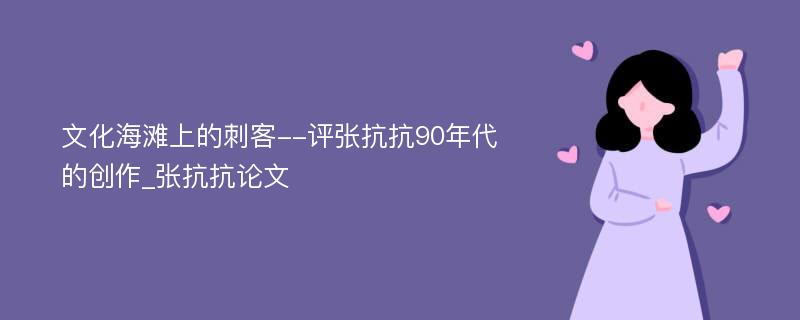
文化沙滩上的拾贝者——张抗抗90年代创作漫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拾贝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张抗抗论文,沙滩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以那些甘愿服务于沙滩的人,那些暂时还不想纵身入海的人,徘徊于岸边沙滩,就只能在海水退潮时分,捡些被海浪冲上岸的贝壳和小鱼小虾了。说不定,还得搭上些时间,去清理人们丢弃在沙滩上的垃圾。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在这样地充满了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文化领域里的喧哗与骚动的90年代里,张抗抗的创作,显然地,似乎是在文学的潮流之外的——
作为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抛洒了青春岁月的知青一代,她没有加入那种最能牵动同代人心灵的怀旧大合唱,没有对于消逝的既往的顽强体认和反复证明;
作为80年代成名的作家,她没有一味地怀恋“过去的好时光”,没有对当下的现实生活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没有将90年代与80年代对立起来,同时,她对于文化沙滩与文化沙漠的界定、区分,在审慎中传达出相当的自信,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态度;
作为同代人中不为多见的思考型女性,她没有参与文坛上火药味十足的激烈论战,没有发表什么愤世嫉俗的宣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写自己的作品,不浮不躁,定力甚强;
她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以独有的姿态,面对现实,追问历史,憧憬理想,切切实实地在这块既热闹非常又冷冷清清的文化沙滩上,作一个拣贝壳的人。进一步而言,在拾贝者中间,有活泼顽皮的孩子,有鉴赏力很高的收藏家,有奇货可居的商贩,张抗抗呢,她拣起一只贝壳,却是以发现者和思想者的目光,去端详贝壳上岁月流逝的痕迹,去倾听历史留下的回响,去辉映阳光下的七彩斑斓,甚至遐想着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的维纳斯……
进入90年代,张抗抗的创作势头,仍然不减当年,她先后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和《情爱画廊》,这两部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她于90年AI写作的一组短篇小说和文化随笔,似乎没有前者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它们对于研究张抗抗的创作道路,对于解读作家的心态,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就是以这些作品为考察对象,对张抗抗的90年代创作,进行一番梳理和剖析。
(二)
时间所创造所赋予的,难道只是一代又一代的牺牲和蒌顿?时间就这样悄然磨灭并销蚀我们少年的锐气,却把它曾经占有过的那个空间中所有的遗留物,为我们制成一双双型号固定的玻璃鞋子,让我们一只脚踏在门外一只脚留在门里,长久地游移徘徊么?
《时间永远不变》
张抗抗1991年的短篇小说《时间永远不变》,让我想到80年代一位著名女诗人颇受称道的一首诗《老去的是时间》。那时,历史的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从浩劫中走过来死而复生的人们,充满了凤凰涅槃的豪情,豪迈地宣布:青春和信念是不会衰老的,老去的只是运动不息的自然时间。如今呢,又是10余年过去了,作家的认识,从正题转向了反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在生命的流逝中,只有时间的尺度是不变的,春秋代谢,周而复始,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从中体味到的,是多少感慨和苍凉!
到了90年代,一股怀旧的情绪在社会上弥漫,关于“老三届”,关于知青一代,一时间成为其中最活跃的因子。张抗抗作为过来人,却没有投入这种带有浓重的自恋色彩的“怀旧潮”,她总是带着怀疑和反省的目光回顾这段历史。在《选择的疑问》一文中,她对用“苦难与风流”来概括“老三届”人的道路,就直言不讳地提出疑问:“苦难是实,风流倒未必。至少,大部分‘老三届’三十岁之前的日子,是没有多少风流可言的。七十年代末期,总算开始有了些许风流的欲望与可能,年龄却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弧度上可见落势,包含‘抢救’的意味,就风流得比较勉强。”她把这一代人的命运曲折归结为无可选择,每个人都失去了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自由,只能听任畸型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任意的拨弄。《时间永远不变》所展示的,就是这种命运扭曲之下的人生哀伤,是80年代初期的雄心勃勃在严峻现实中失落的感叹,更是作品中的“我”对于“老三届”的这种群体心态的冷峻反思和质疑。
如果说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是导致这“老三届”一代人的人生坎坷的社会因素,那么,这一代人能否把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归诸客观环境呢?在许多知青作家那里,他们显然是这样去看的,并且还努力地从这一代人对于心中理想的坚守中,寻找积极的肯定的因素,进而肯定自己。张抗抗自己在同代人中间,可以说是个成功者,她从80年代初期以《夏》和《淡淡的晨雾》为自己赢得文学声誉以来,一直是受到社会关注的重要作家,但是,她却并没有因为现实的既得利益而把昨天也赋予诗意的色彩,没有因为今天的成就而把人生轨迹神圣化,没有把当下的赞扬当作对昨日迷失和尴尬的改写——在同代作家中间,张抗抗的自省意识可以说是最强的,她没美化过去,没有美化从过去走向今天的自己和同代人。从早期的《白罂粟》等作品开始,她就开始了自我的忏悔,写于90年代的《残忍》、《沙暴》等,更集中地体现出她对于同代人灵魂的拷问,而且,这种拷问所面对的,不仅是已经告别的过去,它一直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知和深入的清算,人们只是习惯于清算历史,把个人的不幸都归诸个人无法与之抗争的历史,却很少扪心自问,自己对于历史又做了些什么。因此,不但说,历史往往是一笔糊涂账,更严重的是,历史的荒诞,仍然会在现实中重演。《沙暴》中的辛建生,当年在草原上插队的时候,曾经因为无知,参与了知青们猎杀老鹰的行动,后来,他从事实中得到严酷的教训,对于老鹰的大规模猎杀,破坏了自然的生物链,使得草原生态严重失衡,草场被人为地破坏殆尽,给草原和牧民带来巨大的灾害。为此,他深深地愧疚于心,耿耿难忘。可是,心灵的自责并没有使他真正成熟起来,一旦面对现实利益的诱惑,他就变得动摇起来,最终是跟着他人重返草原,再次举起罪恶的猎枪。他的良知是如此脆弱,简直让人怀疑他曾经有过的忏悔到底有多少真诚。《残忍》则讲了一个以恶制恶的故事。知青牛锛,因为不堪连长傅永杰对全连的盘剥和对女知青的玷污,因为无法对他实行正义的制裁,就密谋策划,与马嵘一道,非常残忍地将其活埋在荒野上,并且一个人承担了谋杀的罪名。一种正义的复仇,却又证明着人性的残忍。如今,牛锛的好朋友马嵘,没有从积极反省的角度回顾他和牛锛当年的行为,而是从实用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从牛锛保护了他,他又摆脱了牛锛的制约以后,在商场上取得的丰厚利润和奢侈享受的角度,对往事进行告别。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像辛建生和马嵘这样地健忘历史,是否正表明这一代人身上的某种劣根性,从历史深处继承而来又在现实中继续下去的民族劣根性呢?
(三)
我要写出历史留在我身上的那个样子,写出我对于那段历史的个人感受和体验。那一段惨痛而凄楚的记忆,早已超越了家世和家族人物命运的意义,成为超越历史的现代寓言。
《走进历史》
或许,除了最初的《夏》、《去远方》等少数几篇作品,张抗抗的创作,大体上是保持了一种低调的,低徊宛转,沉郁感伤。《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80年代初期之作,因为与当时那种虽然历经苦难却依然昂扬奋发的文学步调不一,还遭到过意外的批评。她的知青题材作品,既没有悲壮的英雄主义的赞歌,没有声泪俱下的苦难伤痛,也没有温情脉脉的田园情调,而是始终关注于自我的反省追寻心灵之谜的。这样的作品,自然地,也无法得出令人亢奋的结论。
《赤彤丹朱》是对于历史的袒露,对于命运的拷问。朱小玲和张恺之,在黑暗年代里向往光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和斗争的事业,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萌生了爱情。革命与爱情,是他们的青春洗礼,是他们的生命狂欢。然而,他们在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激情鼓舞下追求和实现的理想,在刚刚向现实转化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浪漫不理想,而是染上了血腥气,开始吞噬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这一曲折,对于作品的主人公来说,长达30年。朱小玲和张恺之,在共同分享革命与爱情的欢乐、共同承担人生的曲折凄凉的同时,又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引发出各自不同的疑问。朱小玲的青年时代的传奇色彩,是与她的天性中喜爱自由、追求浪漫的品质分不开的,她所遭遇到的长期磨难,可以说是青春本性与严酷现实的冲突,为了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努力的自由青年,他们的奋斗所得,却毫无浪漫,也谈不上自由。相比之下,张恺之要成熟得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家,对革命,他比朱小玲更加无保留地投入,他的贡献也更多,但是,无法解释的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多,他遭受的苦难更沉重。
面对着这意想不到的厄运,无法解释的命运(即使是再沉重的苦难,只要能够说得清,它就可以缓解人们心头的压力),难以走出的怪圈,他们两个人超度自我的方式和心态也各不相同。朱小玲似乎一直保持了那种天真的、不谙世事的浪漫气息,以美丽童话和田园情趣,以致把女儿也当作“一个美丽的童话存在”。她始终也没有搞清严峻现实的真谛,因此就无法与现实相融合,而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这使她对于现实缺乏充分理解和认识,却也使她在精神上有所解脱。她还是一个过程论者,面对生活,她产生的是过程性的感受,是心灵和情感的体验,而不去追根究底地去思考“为什么”,然而,她的这种性格,不经意中接近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即过程与目的,方法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悖逆。张恺之呢,从监禁中解脱,又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从事过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他的人格力量,却始终没有被摧折,他像西西弗斯一样,在看不到尽头的苦役中,证明着自己的精神和意志,顽强地证明着他是“不倒的人”。也许,作为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才那样坚决那样奋不顾身,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又难以使他在革命中完全丧失自我泯灭自我,由此导致他的悲剧命运,也把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交到每一个有头脑的读者面前。
失去的最早的,归来的最晚。失落最多的,往往是无法补偿的。历史的残忍的一面,由此表现得铺张狞厉,这又会使我们联想到她的《残忍》——可以说,从历史、现实和人性中表现出来的残忍,是张抗抗近作中一个突出的命题,即使是以唯美情调写出的《情爱画廊》中,都有与全篇不甚和谐的阿秀的死亡,那样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四)
爱和美的探求在她来说还是一个迷梦、一种彷徨、一片沧海、一座高原。她在那森林与荒洲上孤孤寂寂、磕磕碰碰地走。心里的爱和美,同那外界的光怪陆离,那严酷冷峻,永远是一个不协调。
《“生者人试”》
《赤彤丹朱》是一部追问历史和人生谜的作品,然而,这种追问,注定了是没有结果的,是在目前的环境中尚且难以回答的,将来也未必回答得清楚。因为,这牵涉到人类生存发展中最根本的悖论:理想追求与现实可能、变革愿望与牺牲代价、目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等等。为了讨论这样深刻的主题,在写法上,它以极端写实的笔致,撕裂历史的伤口,撕裂人心的伤口,它所引发的“故事以外的故事”,即贾起烈士的弟弟妹妹由这部小说所引起的寻找兄长的故事,足以证明它对历史叙述的充分可信。
然而,对于历史事件的充分可信的描述之中,又经常透露出作家对于宏观历史的一种怀疑态度。怀疑和质询,在张抗抗的文学个性中是非常鲜明的,从在襁褓中就与母亲住在隔离审查的“革大”开始,她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和痛苦,她敬佩自己的父母亲那种九死而不悔的精神追求,但是,时代的和人生阅历的差异,又使她不能完全认同于他们的生活态度。她不能不陷于一种深刻的怀疑和困惑之中。这种对于历史价值的怀疑,又同她对于“老三届”的人生思考所导致的对命运与选择的怀疑相一致。血缘、家族和自己的童年少年,“老三届”一代人和自己的青年中年,交相迭印,构成张抗抗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个人、对于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等深刻命题的追问,就像《赤彤丹朱》中“我”与“父亲”的对话中所表达的那样,“父亲”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厄运中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始终地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并且用这样的自许自慰支撑着度过苦难人生;“我”却从中看到了阿Q的影子, 进而质疑说:“然而我想爸爸却没有说出那最重要的一点: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无论幸运和背运,都同样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支付的。谁能说,一种受尽虐苛的人生,要比自由和欢乐的人生更有价值呢?”
也许,自由和欢乐的人生,其评价的尺度何在,是我们可以向作家提出进一步的追问的。不过,在这里,用以对父亲用30年的苦难经历证明自己的精神优越,张抗抗的怀疑已经足够。
前面说过,在同代作家中,张抗抗的自省意识是最强的,这和她对历史对自我的怀疑与质询,是相辅相承的。与之相应的是,在同代作家中,她的哲学意识,她对于人生选择人生价值和人的本性的执着思索,恐怕也是最强的,这在她的《淡淡的晨雾》《北极光》《隐形伴侣》等作品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带有明显的怀疑论色彩。
对于张抗抗,如果从她现在的立场再迈进一大步,从切身经验出发的对历史与人生的质询,上升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会不会给她的思索和文学创作带来新质,是无法断言的。因为,怀疑论的身边,常常伴随着强大的虚无主义,伴随着对于生命和世界的彻底否定。
张抗抗的怀疑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下得到了缓解,这就是《情爱画廊》,在写作特点上,《赤彤丹朱》是纪实性很强的,《情爱画廊》则具有相当的浪漫和夸饰性,《赤彤丹朱》是对历史与人的刻意追问,是怀疑论的产物,《情爱画廊》则是对于悲观与虚无的强烈否定,是对于爱与美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的高度肯定和炽烈追求。
当代社会生活,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讲求效益和功利。曾经弥漫于80年代的精神追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面前,不能不黯然失色,悄然退隐。对于理想主义的质疑,对于激进思潮的否定,近年来不绝于耳。浪漫和幻想,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同时,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似乎也丧失了地位。《情爱画廊》在此意义上,是对爱与美的热情赞颂,是用爱与美作为理想主义的最后的一道堑壕,向着日益世俗化平庸化的社会作完全的抗争。
在作家笔下,艺术成为当今世界上幻想的最后栖息地,如作品女主人公秦水虹所倾诉的:“那些政治幻想家们,早已让空洞的宣言惩罚得体无完肤。冷战结束以后,幻想已在大部分领域里销声匿迹;艺术本是幻想生存的最后一块领地,如今也被拜金、实利的海水淹得只剩下一些星星点点的孤岛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幻想本能,曾无情地惩罚了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但却无法惩罚艺术家。东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艺术的停滞黑暗时期,究其根源,多半在于当时的专制社会窒息了幻想。失去幻想,艺术便会成为一个无性无情、华丽高贵却无从繁衍生命的单身贵族。”作品中的周由,在秦水虹眼中,正是一个还保留和发挥了可贵的幻想和浪漫情怀的画家,是用精神力量对抗世俗社会的唯美主义者(张抗抗从骨子里来说,是无法把艺术至上作为自己的信条的,在《情爱画廊》中,她也特意让秦水虹和周由表白他们不是唯美主义者,但这样的表白在作品中是有悖于它的整体趋向的,是败笔)。在他们心目中,爱情与艺术,具有相同的品质,它们都是充满浪漫气息和理想精神的,都是充满了创造性和感情色彩的,都是生命的轰轰烈烈的迸发,是灵与肉的谐和与极致,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最高体现,是人的个性价值的淋漓尽致的张扬。而且,它们都是纯而又纯的,容不得半点贪欲和金钱的玷污。
为了加强这种以至上的美和爱对抗物质现实的力量,为了印证秦水虹和周由这种飞蛾扑火不惜自我牺牲的爱情追求,为了显示对于爱与美的追求可能会带来灾难和毁灭的悲剧性,作家还特意刻画了阿霓的形象。她是作为作品基调的烘托出现的,但是,在《情爱画廊》中,是她把爱与美的主题发挥得尽情尽意,甚至超过了作家着意描写的周由和水虹。阿霓这个初次爆发和体验着少女爱情,又差点儿被这无法自控的爱情火焰烧成灰烬的女孩子,她的感情风暴和命运坎坷,她的排除了一切功利目的而又毫无希望的苦恋,比周由和水虹更引人注目,更令人关心。不经意间,她的形象的光彩,使那两位成人也相形见绌。她把爱情浪漫的非现实的一面,把爱与美的追求所导致的悲剧性,演绎得惊心动魄。
(五)
我多么希望读到那样的文章,用女人的火热心肠和真挚坦荡,来谈谈我们四十岁女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谈谈我们这四十年感情经历中所沉淀下来的痛苦的思索…
《请不要问女士年龄》
张抗抗在90年代创作的一个转变,是她的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她对于现代女性的理性思考。
张抗抗和许多女作家一样,每当拿起笔,她优先选择的往往是女性形象。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她对于女性意识,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同她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中写过许多女主人公,如果把她们改换成男性,那么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矛盾冲突在本质上仍然成立。”“因为我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新时期以来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到了90年代,张抗抗不但写了一批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内容的随笔,如《女性话题》、《女人为什么不快乐》、《女人说话》、《两性的极地》等等,其谈论的,既有宏观地讨论男女两性相互选择的历史中体现出的时代价值观的转换,也有具体而微地议论女性如何穿衣服,如何以女性的方式说话等生活常识;而且,在《情爱画廊》中,通过秦水虹的形象,她明确地表达了她理想中的两性关系,表现出她对于女性的形象设计,标志着她对于女性意识思考的新高度。
无论是《夏》和《去远方》中的岑明,还是《淡淡的晨雾》中的梅玫,《北极光》中的芩芩,在这些青年女性身上,作家寄托的,是对于个性解放的热情呐喊,是对于拨乱反正的迫切呼唤,是对于价值观重建的急切期盼。这都是基于多年来极左思潮对于社会和人们心灵的危害有感而发,是历史转折关头全社会需要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与之相比,作品主角的女性色彩,不能不退居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只是一个人物识别的符号而已。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粉碎“四人帮”为时不久,从政治领域,到社会生活方面,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所谓性别意识、女性自觉,还来不及提到文学的日程上来。进入90年代,对于历史的清算,让位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我选择,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选择界域拓宽,中国女性可以说是第一次面对空前开阔的天地,拥有多样选择的机遇;另一方面,商品世界对于女性的诱惑,和女性在商品市场上具有的交换价值,也具有一种爆炸性的趋势。于是,觉醒的女性,不得不同时面对多方面的压力,既要扫除传统文化对于妇女的束缚和压抑,进一步地争取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同时又要抵御商品化社会的诱惑,保持一种东方女性的优雅和纯美;在两性关系上,则是要借助自我的充实和提高,建立一种新型的情爱模式。
前面我们提到,秦水虹在和周由结合以后,轰轰烈烈的爱情追求转换为日常的生活形态,因而失去了扣人心弦的力量。不过,作家敢于冒险犯难,应当是有所考虑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于男女两性的婚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张抗抗得以进行了理想的描述。如果说,在芩芩那里,她面对的3个男性,傅正祥、费渊和曾储,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她对于他们的取舍,与其说是她对于自己的爱情理想的选择,不如说是对于种种人生信念的思索和弃留,爱情抉择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种叙述方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如果说,在肖潇与陈旭的关系中,作家表现出的是肖潇以陈旭为镜子,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两人之间的聚散离合,是为肖潇提供了对于自我的心灵分析的契机;那么,秦水虹对于她与周由的情爱生活的处理,才充分地表现出一个觉醒的现代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其一,有别于先前作品中那种柏拉图式的超越肉体的精神追求,秦水虹与周由的爱情是灵与肉的融合,是从精神到肌体的相互欣赏和相互占有;其二,秦水虹与周由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是通常的那种施动与受动的主从型关系,在精神上,在肉体上,他们互相激活、互相撞击,以同等的质量,激发出生命的光辉;其三,秦水虹和周由在精神气质上,都是既古典又现代的,他们既承继了东方文明的优雅脱俗和内在修养,又经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热情奔放,拥有强大的活力。他们的爱情生活,充满了朝气和创造性,在相互的提高和启发中不断更新。可以说,这是90年代中国版的“新人的故事”,是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对于幸福生活的尽情展望。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当代的女性意识的自觉,是经过漫长的过程的。我们论述过张抗抗从80年代到90年代对于女性意识的变化,换一种角度,在特定意义上来说,从《北极光》《隐形伴侣》到《情爱画廊》,可以排列出女性意识觉悟的历程:芩芩从动乱岁月中走来,是在精神的荒野上寻找新的人生座标;肖潇是在对于往事的反思中,对于道德与邪恶、真实与假相、潜意识与显性行为进行辨析,对自我进行再度认识;确立了新的人生目标,对自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主客观世界都获得了确切的认知,就取得了相对的行动自由,取得了切实可行的人生追求;正是这一切,给秦水虹的思想和行为,奠定了积极的基础,使她能够体现出作家的生活理想。虽然说,在作品中,由于唯美主义色彩的影响,由于对秦水虹和周由的几乎尽善尽美的形象设计,难免会让人感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度闻”,但是,作为张抗抗和她的同一代女作家,将她们觉醒的女性意识和爱情憧憬第一次在作品中进行铺陈扬厉的形象显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