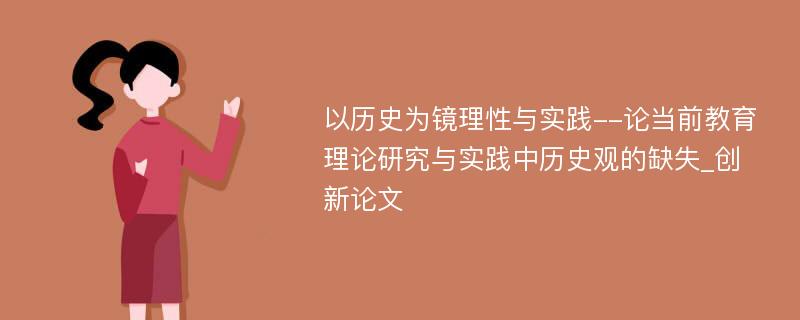
以史为镜裨理行——论当下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历史感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缺失论文,实践中论文,历史论文,镜裨理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2-0066-04
《旧唐书·魏征传》:“魏征薨,太宗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历史的镜鉴作用,可谓尽人皆知。列宁也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知是一回事,而行又是另一回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者于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在当下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新”的理论和观点可谓层出不穷,显得一片“繁荣”,而打着“创新”旗号的教育改革实践更是不胜枚举,似乎学校不改革、不创新就不是在办教育。然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新意和前人不曾有过的创新?有些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能否找到其影子?却是一个经常被忽视和不愿提及的问题,更何况对这些理论和实践作历史性的考察,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则更是一种奢望。认真反思、审视我国当下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所谓的理论和观点轻视历史,忽视历史,甚至有意回避历史的情形时有表现,以致常常显得虚无飘渺、空洞臆断,既不能指导当下的教育实践,也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营养而自善其身;而有些所谓的实践改革更缺少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与扬弃,充其量只能是对历史上有些不成功的教育改革实践的简单重复,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泥潭。这种对教育历史的正确认识和认真反思的缺失,是一种浮躁和轻率的表现,必将无益于我国当下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教育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注重和强化对以往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学习,并感悟其中的道理和启迪,应当成为当下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历史知识的缺失
历史知识的缺失,成为某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缺少历史感的主要原因。2003年5月15日,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在与上海市教科院研究人员就“教育创新”进行的座谈会上曾呼吁: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要学点教育史。他说:“教育这个社会现象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探索教育规律这条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进行过无数次实验,提出过许多教育理念、理论,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创了新理论、新模式呢?”[1]
综观当今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历史知识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不了解历史,对历史史实知之甚少,从而遮蔽了自己的视野和思路
众所周知,人类的教育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同步的。人类千百年来的教育实践和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且不说西方“古希腊”时期的贤哲高论,也不提我国孔孟时代的智慧思想,仅就近世以来国内外关于学校教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探索,其可借鉴性、可学习性,足以裨益于当下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历史知识,我们将不会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理论、思想、经验与教训,进而会失去判别当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参照,最终将无法确定我们是在进行创新还是从事前人曾经的工作。
比如,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发现和人的解放,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把人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不再把皈依神性看作教育的目标,并且发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充分领悟到人的价值和使命,才能使人具备建功立业的素养,才能使人更加完美,才能使人过真正人的生活。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所有的人只有在受到一种真正的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人,这是不受人的出身、地位、性别和智力的高低影响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对人的认识和教育价值观被称为人文主义。它对我们今天更全面、更真实地开展素质教育应当有着较大的启示。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利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年)将其创办的孟都亚学校取名为“快乐之家”,倡导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办学宗旨,既注重学生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的协调发展,又注重学生个人实际能力的培养,把学校变成接近自然和充满欢乐的地方。按照维多利诺的意见,孟都亚学校非常重视体育,经常让学生练习骑马、角力、击剑、射箭、游泳、舞蹈和从事各种游戏活动。维多利诺也注重道德教育,强调实际示范,并经常以乐善好施的行为去影响学生。他与学生生活在一起,关心和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从不因学习上的过失辱骂和体罚学生。学校实行学生自治,为的是有利于他们的自我教育。维多利诺对人的尊重及其人文主义关怀使孟都亚学校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为数不多的人文主义学校的典范,他把通才教育的精神灌输到学校中去,“使受教育者获致德性与智慧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2] (P165)。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也极力主张把儿童培养成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指出:“只使他们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们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绝不能把两者分开。”[3] (P381,396)
再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一些国家相继兴起的旨在改造传统学校和建立新型学校的“新学校”运动,致力于追求7大目标:(1)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和增进儿童内在的精神力量;(2)教育应当尊重儿童的个性,而只有通过解放儿童内在的精神能力,才能发展个性;(3)各种学习和为了生活的训练都应给予儿童的天赋以自由的施展——这些兴趣是在他的内心中自发地唤醒的,是在各种手工的、智力的、审美的、社会的和其他的活动中表现的;(4)每一年龄都有其特殊性质,因此,需要由儿童们自己在教师的协助下组织个人和团体的纪律训练,这种纪律训练应能造成深刻的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感;(5)自由的竞争必须从教育上消失,而代之以合作,用合作来教育儿童为社会献身、服务;(6)要进行共同的教育和教学,让男女儿童合作以产生有益的相互影响;(7)使儿童成为不仅能尊重邻里、本民族和人类,而且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尊严的人。[4] (P169-170)这些目标的提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改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二)不懂得历史,无法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受到启发
不了解历史,是对历史的无知;而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却无法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则是不懂得历史。对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而言,教育的历史知识并不陌生,有的甚至了解得很多,但是,有的人也仅仅是了解历史,并不能从中受到启发。例如,我们都知道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和因材施教等教学思想,但是,一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又有多少人在自觉地、娴熟地运用这些教学思想?有的人是不愿意用,有的人是不会用。如此一来,了解这些历史知识又有什么用呢?
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指出:“教育工作者要读教育史,要知道前人都研究了一点什么,有哪些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又怎么样,有什么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什么基础上去发展它,这才是聪明人。”[5] 他结合自己一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经历,以及自己对克伯屈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实验谈到,“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还有一位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1870-1952年)的教学法,对中国幼教的影响都很大,但最后都没有得到推广”。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课改,课改推出的研究性学习与设计教学法十分相似,我不知道提出研究性课程的同志是否了解过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以及其后为什么会停止执行的原因?”[1]
黄济先生在其《关于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并强调:“教育改革,不但要求创新,同时要求在继承中创新。历史经验是一项宝贵的教育资源,需要有分析地批判继承,也需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发展。盲目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全盘否定过去的经验也可能要走回头路。这种错误的过激的倾向,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今天一定不要重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紧紧地把握住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就能使教育改革与时俱进地健康发展。”[6] 真可谓一语中的,真知灼见。
二、历史意识缺失
历史意识缺失,就是没有了解历史的意识和自觉,根本没想到还有历史这回事,而一味地盲目自大,舍我其谁,对过去的历史不敏感,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疼。历史意识的缺失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对历史的否定和忽视。而否定历史、不正视历史,常常会对现在及未来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这一点已被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然而,在当下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在一些论者看来,教育改革好像越新越好(忽略‘新’与‘正确’、‘适应’应该是一致的),越激进越好(‘大破和大立’),越彻底越好(‘重起炉灶’),好像是在一片空地上进行,可以随意构建玉宇琼楼,在一张白纸上绘画,任我挥毫泼墨。……‘重构’、‘重建’这些词和概念在一些论者的文字中使用的频率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似乎教育上的事情(概念和行动)都需要并可以随意重新做起”[7]。如果任由这种“重起炉灶”、“大破大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行为在教育领域肆意泛滥,那么,世界上几千年以来所积淀起来的优秀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传统必将会失去其应有的历史价值,而以此为指导的教育实践与改革也必将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巨大危险,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风险巨大的赌博。
众所周知,清末我国新式学校之创立,可谓是“另起炉灶”,是对我国几千年封建教育的否定和创新。然而,就是这些新式学校之“炉灶”却依然是建基于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教育历史传统之上,在新式学堂中依然保有一定数量的“经史”教育内容,依然是“中学为体”。因为,即使是西方最完备、最先进的学校模式,毕竟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它也只有从中国的土地上吸收养分,才能维系其生根发芽所必需。这就决定了它无法割断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教育传统而绝对地“另起炉灶”;相反,它只有慢慢地吸收并渐渐地渗透进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之中,才能不断求得发展壮大并最终达到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因此,历史是无法割舍也不可能轻易被割舍掉的,那种忽视历史、淡化历史的历史无意识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招致历史的惩罚。
当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历史的重要性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没有现在,也就无所谓历史;没有现实做基础,历史的价值也将无法体现。现实与历史二者并不相互矛盾、格格不入,历史是相对于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延续的现实。因此,我们在进行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中,不要仅仅着眼于现实,而应当放眼人类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为现实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服务。著名学者许嘉璐在谈到教育时指出:“现在谈到教育,谈到学校系统,着眼于现实的具体需要者多,从人类文化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者少。现实既然是过去与未来的中转站,注重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缺少了历史的眼光,则所谓现在将不是真正的现在,而且可能将损害了未来。”[8] 著名史学教授桑兵先生在谈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时指出:“不了解中国的固有文化,就很难确切把握转型中的种种情形以及转型后的种种面相,也就无从进入近代中国人面对知识与制度转型时的精神世界,难以理解相应的各种行为。”[9]
三、历史情感缺失
历史情感缺失,主要表现为不愿意述及历史,认为历史都是过去的事,都是老皇历,与今天无关;或在内心深处拒斥历史,自以为自己的理论或实践是最好的、最先进的、最完备的,而历史上的东西是不足借鉴和学习的。历史情感缺失其本质是一种对历史价值的否定或歪曲,是对历史的背叛。
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有其一定的意义、影响或作用,这就是历史事件的价值。历史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客体与主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某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意义关系。从静态上分析,历史现象有三种意义关系:一是历史现象在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的意义关系;二是历史现象在后世历史发展长河中改变了存在环境与条件下的意义关系;三是历史现象经过认识主体的升华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意义关系。这样就构成历史价值的三种形态,即原生价值形态、延伸价值形态和抽象价值形态。这三种价值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是历史价值认识的对象。正确认识各种形态的历史价值及不同历史价值形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历史的价值是通过评价来揭示的。评价就是主体关于历史认识对象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判断。历史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人们对于历史价值的认识完全有可能偏离历史本来的价值。这种认识有时可能是真的,即符合价值;有时可能是假的,即不符合价值。
人们对历史价值的认识,不仅取决于历史事件的性质及其原生价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态度与情感。有的人能够正确地对待历史,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以利国利民利己;有的人则拒斥历史,根本不愿意亲近历史,从而陷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还有的人更是别有用心,不是学习历史中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专门从历史中学习一些奸滑之道或糟粕意识,祸害他人,祸害社会。这后两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情感,都可归于历史情感缺失的类型。历史情感的缺失与历史无知或历史无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情感的缺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明知故犯,它暴露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狂妄自大。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研究历史和重视历史向来是其核心和根基,福柯和德里达等现代法国哲学家就很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并直接通过“解构历史”的活动来“诊断现实”本身。福柯在临死前接见评论家罗杰·鲍尔·德洛阿(Roger-Pol Droit)时说:“我对历史学家所作的工作特别感兴趣,但我所要做的,是另一类型的历史研究工作。……我所感兴趣的,是弄清楚被人们称为‘现代性的门槛’的17至19世纪。从这个门槛开始,西方的论述展示了非常令人恐怖的全球化的霸权。……所以,归根结底,我的历史研究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穿透现代性的门槛。”[10] 对任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而言,历史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学术巨擘,还是普通学人,葆有一份对历史的情感,善于亲近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都是极其有益的事情。
其实,任何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创新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和延续性,都不可能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如欧美等先行现代化的国家,其学校发展、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自然演变的结果,其教育中的每次变革往往只是因应社会发展形势作细小的变动,很少大规模地动作。在逐步渐进的过程中,传统逐渐消融于现代之中,教育因之不断地进化和发展。因此,任何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都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率性而为,而必须尊重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以史为鉴,并从中受到启示。为此,对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尽可能多的了解历史,领会历史,培养对历史的敏感性和历史关怀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人,一个具有历史情怀的人,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标签:创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