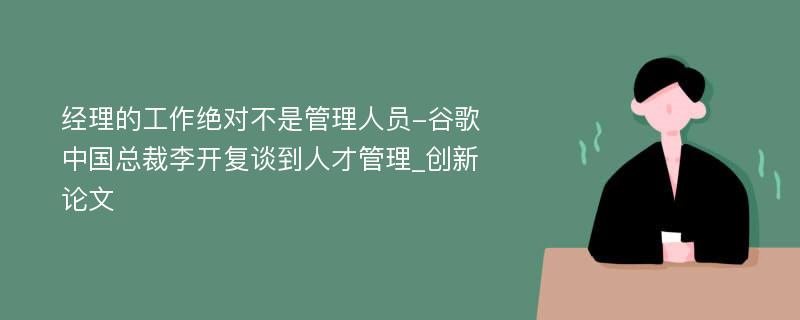
Manager的工作绝对不是管人——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谈人才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李开复论文,总裁论文,人才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7月18日之前,李开复的职务是微软全球副总裁,过了那天,他的头衔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公司名字由微软换成了Google,同时还兼任Google的中国区总裁。这次的跳槽事件,在中国、在亚洲都引起极大的震撼,在美国还闹上了法院。
甚至还有学生、媒体批评他的行为是一种“背叛”。
“如果这么说合适的话,那不是每个人换工作都是一种背叛的行为?”在北京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区,李开复接受记者专访时为自己辩白,“今天已经不是三国时代了,没有一个雇主有权力要求员工永远为他服务。”
李开复来到Google,对于如何找到对的人才,如何管理天才,在访谈中有精彩的论述。他的理念:经理人最重要的真谛就是“不要管人”;应聘人员带着之前工作的商业机密来投靠,他反而绝不录用;破除公司“瑜亮情结”,员工推荐人才一定要比他自己更厉害,否则进不了公司。这套人才管理在中国开启了新的视野。以下是专访的摘要: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您不论在微软或Google都很少谈关于数字的问题,例如公司营收、获利,这与其他CEO的风格有些不同,你似乎对于人文、人才的培养更有兴趣?
李开复答(以下简称答):在高科技的公司,“技术”是公司可以唯一延续的优势,今天不论营业额的高或低,真正可延续的还是技术,而真正可延续技术的则是人才,所以我更多的时间会花在“技术产品”与“人才”上。
美国思维、中国情结,让李开复成为Google中国本土化最合适的领军人物。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种软件、互联网产业,竞争优势很快会失去的,我们可以看到eBay在中国很快被淘宝网逼近甚至是超过,所以我深深地认为技术是很重要的。当然技术是可以被仿造的,如何保持技术有永远的优势呢?就是靠最好的人才,当别人在复制你的技术时,你已经有了更多的新技术。比如我喜欢谈一些数字,我更喜欢谈的是我多少个月可以做一个产品、产品周期是多长,或者一个天才工程师可以比普通工程师多做一百倍或一千倍的工作,这些数字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找到一个天才可以抵十个人管理的最大艺术就是不要管人
问:所谓天才工程师会做几倍的事情,这个观点,在Google起到什么作用?
答:有许多产品跟其他公司竞争,我们得到了很多的优势,很多人会说我们做的某某产品比别人好得多,是因为背后有100个人、很大的队伍。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只有5个人。
团队的大也同时带来一些浪费,因为彼此需要沟通,也会有工作的重复,而且当你在设计任何的工作流程当中,你永远会被慢的那一环所限制,就算你有 100个人,99个人都很能干,但是有一个人他犯了一些错误,或者他没有跟别人衔接得很好,一个人的错误可能造成让产品拖延一倍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人才重要性更加提高。过去工业时代,一家工厂最厉害的工人跟普通工人生产力只差50%。就拿做鞋子为例,我做10双,你最多做15双,不太可能做到1000双。但是现在,一个创新可以代替10个人、一百个人甚至1000个人的合作。我举一个实例,我们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同时运用成千上万台的服务器。一个人同时在一万台机器上,他可以自动去调整,如果死了一台机器,就拿出来丢掉,另外的9999台机器继续运行,非常能够容错并迅速大量地使用运行计算,你如果找1000人,不见得他们会创造出这样的模式。这就是天才与普通工程师的最大差别。
例如我们在北京招了一个工程师,他的前老板在他的推荐信中,只写了一句话:“他一个人可以做十个工程师的工作,你如果不用他,你就是大傻瓜。”然后我们就很快把他找来。
问:就一个管理者来说,您如何定绩效、制指标,对天才来说,会不会比较难制定这些标准?
答:管理天才最大的秘诀就是要放权,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创造一个环境给他资源与支持,在目标上给大方面的指导。我们的工作要靠资料来指点,而不是拍脑袋来决定。
天才型(员工)最大的满足,是在他工作上的成就和对工作的热情,如果你把他全部都框起来,每个星期来衡量他,就意味着我不信任你、我要想办法来管你,这个前提之下,这个天才工程师已经逐渐远离你而去了,这样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在高科技公司。
在Google的管理模式,做一个Manager,我们的工作就是确定大的方向。还有我们是员工为员工支持,帮助他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买计算机、服务器,或者更好的美食环境。我们的厨师广东菜、上海菜都会,每天都准备不一样的菜肴。很多人说,来Google的三大目的就是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要能招聘找到更好的人,让每个人能够发挥他们的热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做最喜欢的工作,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Manager的工作绝对不是管人,我们有很多机制来避免我们的Manager来管人。我们有一个副总裁,向他直接汇报的有120个人,他怎么可能管这么多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方法的真谛,我们不要你管这么多人,我们给你这么多人就是“不要去管他们”。
也有人说你们的评价系统是怎么做的?你管30个人,怎么写他们的评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员工彼此透明的回馈,所以老板看某一个员工,就看他工作周围的五个人,他服务的三个人,也许是他负责部门和他合作的两个人各会给他写一个回馈,然后根据那十人的回馈看他的工作好不好。我可能并没有这么多的详细知识,知道他做了什么,也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详细知识所以也不会去管他,是非常放松的扁平状态。
破除公司内部“瑜亮情结”
推荐的人才一定要比自己更厉害
问:好的人才不容易找,大家都在缺人才,对于Google来说,这些好的人才或天才,他们是自己找上门来,还是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您是如何找到这些人的?
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五年之后,李开复重回中国,再一次与中国年轻人一起工作。
答:有很多方法。Google现在很幸运的是全球知名的公司,确实有很多人是自己找上门的,我们有网站、工作专区,他们自己投上来的,我们相信优秀的人会认识更优秀的人,我们的员工可以推荐他们认识的最厉害的人。
我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希望你只推荐你觉得比你厉害的人,不要推荐跟你关系好的人,或是你欠他一个人情的人。我们希望每个员工的加入,都会造成公司每个素质的提升而不是下降。
问:您希望员工推荐比他能力更强的人,中国人过去说“瑜亮情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老板眼中最优秀的人,但却要他们再去推荐比自己优秀的人才,员工的心态如何去平衡?
答:我想每个人都难免有一点私心,但是做管理就是要以身作则。假设一个人推荐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他不太好我就会找这个人明白告诉他,我觉得这个人不太好,让他有一个回馈,你这么做是不符合公司方式的。
反之,他推荐了一个确实比他优秀的人,我也会告诉他我很感谢他的。当他们知道我们面试的过程是很严厉的,比他们差很多是进不来的,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问:您的管理是“做最好的自己”,您本身也在微软、Google等国际公司工作,等于是用国际的高规格标准在做事情、想事情,对您来说,您的职场已经是蛮高峰的,您已经站上了山顶,但是就中国的现状不管是人才、做事观念其实都还在谷底或山腰,这样对您有没有一些冲突,以及如何克服这之间的差异?
答:这是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中国很多企业可能还在山腰,但是中国的人才很多已经到了山顶,我让这些山顶的人有机会在合适他们的企业工作,让他们工作得更快乐,获得一些工作上的成就。另外一方面让山腰的企业知道,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希望有领头、模范的作用。
问:您跟国际的公司接轨之后,可能会用一些国际的高规格想事情,包括管理模式,怎样才能让员工达到这些要求?
答:我觉得有很多方法。每个人做人要以身作则,如果我希望每个人用诚信方法做事,或是Google要求不做邪恶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要求自己能做到,否则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我们在招聘的过程中,会用各种方法把那些可能在诚信方面有问题的人排除在外。曾经在招聘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学生在电话面试时作弊,在网上用Google查答案,我们一边问问题,他一边查答案,除了查得快,还会利用拖延的方式回答我们各种问题。最后过了关,事后他很得意地把这些面试过程写在网上,可是他可能忽略了我们是 Google,我们很会搜索,后来他就没被录取了。
带着商业机密投靠新公司违反诚信原则绝不任用
问:你们是怎么找的?
答:其实很简单,我们用Google输入一些关键词,“Google”、“面试”、“招聘”等等,我们可以看他自己的描述,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很得意地说,“面试官问了我某某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到网上找到了。”这是一个例子,中国的 BBS很多,很多人做了很得意的事情,就把这些事情登在网上。
我们不会只看他自己提供的履历表,我们会再询问他的老板、同事等等,例如我们在清华招了三个人,招到第四个人时,我们会问他觉得前三个人如何?会把这些所有信息综合起来。
问:您书中还提到一个面试的例子,面试者提供了他在公司做的一个很成功的案子,说可以带到Google来,又说他是用工作之余做的,这个人您也没用他,您为什么不是很认同他?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答: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个确实是他业余做出来的东西;一个是他在公司做的,被我用否认的方式来挑战他,变成他当场撒了一个谎,这两个可能性都有。有这两个可能性我都不要他。
如果是公司做的加上撒谎,他是错上加错,如果前者当时确实是业余做的,他会来推销给我,认为“我知道公司做什么什么技术”,他是利用公司的包装,想要来推销给我,不但我是不诚信的人,你也是不诚信的人,“我偷了公司的东西,我想靠这个作为我进入你公司的工具”,这是错误理解我们公司的价值观。
他的包装也是不诚信的事情,就算当时他是业余做的,因为他曾经把业余做的工作,包装为一个商业机密,想要靠这个商业机密,然后引诱我雇用他,这个过程我不会再给他一点机会。
问:您在书中也提到,不管微软、惠普、Google都把“诚信”奉为圭臬,能否解释这样的价值观,实际上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价值是非常重要而且永远不变的?
答:在今天这个企业里面,我想你的用户与合作伙伴对你的长期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任何公司理解这个重要性之后,很自然地会把“诚信”放在公司很高的准则里。
Google从创立到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希望把更多的信息坦诚放在每个人的面前,让每个人都能平等获得想要的信息,这是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我们也深深地相信,只要做一件事情违背了这样的价值观,就会失去很多的用户跟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观念,我们不只在做技术时,把我们技术平等地给用户使用,我们是个很特殊的公司,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时,都在想能不能帮助用户,平等地将信息传递出去。
灌输员工不做邪恶的事用户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问:以Google来说,在对客户做平等的事情时,用户都知道诚信、平等的原则吗?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些价值观?
答:我想在我们不同的公司介绍、网站都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最重视的价值观,我们的每个产品都可以看到,任何人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他们收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搜索的结果都是客观的,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哪一个公司给了我们钱,我们就把他们的信息放在前面,过去在美国、现在在中国都一样。许多公司还是因为商业的考虑,把搜索结果与广告结合,我们认为这是不够客观的。
问:这样听来,好像您到Google没有运营的压力?
答:压力肯定会有,但不是来自于运营压力,能不能雇到最好的人,创造最好的技术,用户喜不喜欢……这些都是压力。
问:您谈过微软让你觉得“很了不起”,Google让您觉得很“震撼”,很了不起与震撼这两点如何诠释?
答:微软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比尔·盖茨是很伟大的企业家,而且是天才技术员,有幸在微软服务,我学到很多东西,过去我在微软、SGI、苹果工作,都有这样的感觉:了不起的公司、优秀的人、了不起的创业者和CEO。
Google其实在很多程度上是一样,但是它和其他高科技公司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像上面提到的几点,它对它的价值观的执著,不做邪恶的事情,真正地把它当作操作的准则。就像是我们不告诉分析师我们下个季度会不会赚钱,我们不会经过每个季度来调整我们的营运结果,让我们的股票涨上去,这一切都靠自然来决定。
我们希望公司对用户做有意义的决定,我们也深深地理解,有时候对用户有益对股东就有害,我们如果把自己所有的成败都操控在分析师的手中,我们就慢慢的不会有这样的自由。
买我们公司股票的人,我们也希望他赚钱,但是我们也要他理解,作为我们的股东,你们的利益是永远排在我们的用户之后,是这样真正对理想的追逐,这就是我的震撼。
如果你问一个成功的公司,谁比较重要,用户?股东?还是员工?他们都很难回答,答案是“一样重要”。但是在 Google,非常清晰,用户最重要。
另外一个震撼就是,我发现我过去认识的很多人,一些老科学家,白发苍苍非常憔悴,即将要退休了,居然最后还是要加入Google,然后在里面精神焕发,热爱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加入了Google,都觉得他们很热爱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创新实践者的天堂,我们要求员工能够“创新”,又能“实践”,又是研究员又是工程师,这一批人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他们可以从硬件到操作系统、到软件、到服务全都自己来做。
第三个震撼,就是“管理”与“研发转移”的模式,就是把管理的机制与成本压缩到最低。
研发的转换可以说是在我过去的研发生涯中碰到的很大的挫折。就是说当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发明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我拿给工程师跟他们说,“你帮我做成产品。”通常他们会说,“这是什么?谁要这东西?”再过两三年,他可能对你说,前几年你给我看的东西现在我要了,为什么现在又要了呢?“因为对手把东西做出来了。”
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对一个研究员来说多么的懊恼,我两年前就帮你想到的 knowledge,可是predicate,两年以后经过了wireless,经过了新的cpu、internet,我帮你算好了你都不要。两年以后我已经不做了,受了你的挫折,但是你现在又跟我来要,还要我三个月做出来,这是一个研究员的烦恼。
在很多其他公司都会有这种“衔接”的问题,怎么管都不对,你要研究员来负责,他又不懂市场、不懂产品;要产品部门来负责,他又不会创新,又不知道技术的前景,这两部门的彼此衔接、沟通又造成很多的浪费。
在Google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每一个研究员就是工程师,你想到什么点子,你要做成产品,就你负责把它做成产品。你如果你觉得是象牙塔上的研究员,你不愿意编程,或者你只是想做齿轮,那不会是属于我们的研究员。
我们的每个人都是既能“创新”又能“实践”,然后把一个ideaI,从他想法的开始到用户的满意度去执行,是这样特殊的过程。这个震撼就是我过去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理想化的公司可以实际的操作,也没想到研究的转移可以这样不需要转移来发生。这些都是过去我没有看过的。
跳槽不能和没有诚信画上等号?
“雇主没有权力要员工永远为他工作”
问:您一直强调诚信的重要,您也解释了诚信的意义,书中有提到诚信不见得要永远依附一个雇主,您从微软到 Google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就您来看,您不觉得自己这样违反诚信原则,您如何去拿捏这之间的分寸?
答:去年有几种不同的误解,一种是比较基本的误解,好像说诚信就是要永远忠诚一个雇主,今天已经不是三国时代了,没有一个雇主有权力要求员工永远为他服务。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与微软签的合约。这边所谓的竞争条款,认为说你不能加入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这不是美国的法律,华盛顿的法律跟我签的合约是我不能在另外一个公司从事同样的工作。
问:有些人把这样的行为认为是背叛,您觉得这是很严厉的指责吗?
答:如果这么说合适的话,那不是每个人换工作都是一种背叛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适的描述。
问:来之前或是事件之后您有再跟比尔·盖茨谈过吗?
答:走的时候应该就讲清楚了。
问:学生对你有一个“校园教父”的称号,这对你想要办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吗?校园教父不见得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可能是说您对校园的学于影响很大,或给他们生命的方向,可以通过您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对这样的称号您听到过吗?
答:听到过,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也不是我特别认可及喜欢的称号,因为我希望做的事情不是希望用告知来跟别人说怎么做,这有其正面与负面的意义。
正面就是说,在天主教,帮你诠释圣经的意义,负面就是我们看到意大利黑社会的人管下面的人,被称为教父。
不管是正面或负面都好像是说:“我是老大”,我跟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跟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背道而驰的,我的文章是说我希望帮助你找到你生命的方向,看看能帮助你什么?而不是我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做、要听我的话。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会不停吸纳西方知识,有一拨中国人、外国人会帮助对方互相理解,所以我相信未来隔阂愈来愈小……
站在高峰上帮中国人才找出路
进入Google的门槛很高,李开复说,从他到了Google以后,通过个人简历审一遍、笔试、电话面试,一层层过滤,最后一拨才能有真正面试的机会,录取率还不到5%。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人才的信心。对于他处于美国总部、中国业务之间,当一个“空中飞人”,在飞机上来回奔波无法避免,在飞机上,除了处理一些公司业务,很多的时间,他会在“开复学生网”(kaifulee.com)不断地亲自回复问题。除学生问到的出国留学如何选校、毕业后如何找工作、谈人品、谈人性外,甚至还有学生问到类似如何背英文单词这样基础的问题,他也都一一回答,不让这些学生失望。
出于对教育的兴趣,他甚至一度还着手筹备一个大学,但是最后因为资金的缘故没有成功。“一方面我是觉得自己在这边更有影响力,可以作为融会中西人才的机会,然后有更多的一批人可以受我正面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李开复先后在微软、Google都攀到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他认为未来十年,华人会有很多类似他这样的机会,因为目前很多企业进来中国,会借重于华人帮助理解中国,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会不停吸纳西方知识,有一拔中国人、外国人会帮助对方互相理解,“所以我相信未来隔阂愈来愈小之后,就不会有太强烈的需要了。现在很多外国人也很懂中国,中国人也很懂外国,两边都慢慢在成长了。”中国的人才成长很快,再过不久的时间中国的各种人才都会有国际水准,那时候要作为跨中美桥梁的角色会愈来愈多,甚至没离开中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做得很称职。
至于他从微软转换到Google所引起的争议,李开复认为不会、也不应该造成这些企业不愿意再培养华人高层主管。“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司,会因为一个正常的换工作而迁怒到一个人的身上,是相当不公平的事情。”李开复谈起这件事,脸色随即严肃起来,“如果是关于种族,我觉得这个公司是彻底不可接受、没有道德价值观,歧视种族的公司,我们都不应该为它工作。”(张文婷)
甚至从微软跳槽出来,李开复选择新职位的重点并不是Google,而是中国:“我想回国做点事情,我想离中国蓬勃的脉博更近一些……”
李开复:做最有影响力的事,就是我的选择
访问李开复的过程中,他一直强调Google“自由”的精神,自由也意味着尊重。为了能够配合一些摄影画面上的需要,本刊摄影记者希望请李开复钻进一个在员工办公区的小型帐篷里,李开复马上举起双手说:“No!No!No!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在对办公区的员工提出同样需求之后,两位女性员工看了李开复一眼,他马上对她们说:“你们不用看我,你喜欢钻就钻,不喜欢钻你可以拒绝。重要的是你喜欢。”
对于员工的选择要尊重,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是要他喜欢。去年7月,李开复最后一次走进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办公室,他进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也就是说,心之所往,身形随之,不能勉强,也完全要依照自己的喜乐从事。
甚至从微软跳槽出来,李开复选择新职位重点并不是Google,而是中国。“我想回国做点事情,我想离中国蓬勃的脉搏更近一些。”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有观众提出,回国创业也同样可以为中国做事啊,跳槽到Google难免被人怀疑是受利益诱惑。李开复的回答让人意外:“那意味着我就没有时间帮助中国学生了,所以我不能考虑这样的一个选择。”“他真会作秀。”台下也有观众小声嘀咕。
“回国做事”、“帮助学生”,听起来李开复并不从自己的私利为出发点。但是越冠冕堂皇的理由越难让人相信,这些理由真的是他跳槽的原因吗?
1998年加入微软以来,李开复在大陆做的演讲和报告超过300场,平均每年40多场。八年前,李开复本来计划陪微软CEO鲍尔默去拜见朱镕基总理。当天下午,他听说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要来面试,于是他就告诉鲍尔默:“你自己去见总理吧,我要去见学生。”
即便他去杭州进行招聘。也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演讲会场上和学生相见。“公司其实很支持我,我跟我老板说,我用我20%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可以吗?”李开复说,“我老板说你可以再多花点时间。”答应回到中国接受Google的这份工作,主要是他的“心”告诉他,这一生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我要为中国人做一些事情;第二把更多的创新,让世界使用,Google有一套新的做法;第三我喜欢跟最优秀的人很快乐地工作。”在他的想法里,Google中国这个环境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2005年11月,李开复在浙江大学的免费演讲入场券,已经被求购者们竞拍到了450元一张的高价。随后在安徽大学的演讲,李开复干脆在一个露天体育场进行,7000名听众挤满了会场,上座率绝不低于当红明星的演唱会。
这种巨大影响力正是李开复所追求的。他说:“影响力是我一生的价值,我要更多地帮助中国的青年,做最有影响力的事,这就是我的选择。”(暴剑光)
标签:创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