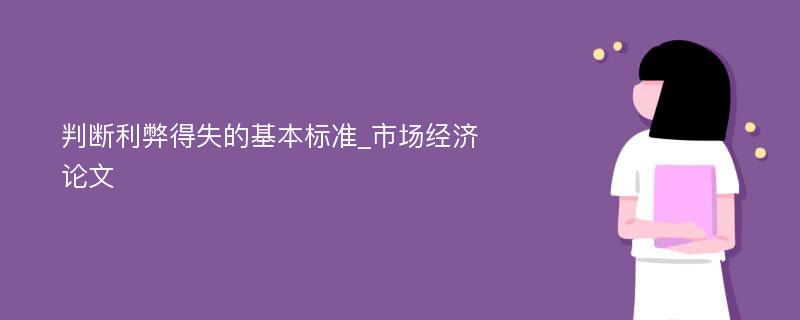
判断利弊得失的根本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弊论文,得失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大解放,带来了社会大发展,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左”的那一套东西根深蒂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提出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判断利弊得失的“三条标准”。“三条标准”的提出,打破了新的思想僵化,把思想解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一次扫清了“左”的思想障碍。
姓“社”姓“资”的质疑和困惑
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左”的错误,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发生的。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提高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这样一个吓人的高度。这方面错误的观点,经过长期的灌输,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移,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时,许多人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发生了一系列困惑,有的站在“左”的立场上不断提出改革开放的措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这是解决“两个凡是”观点后,邓小平同志遇到的又一重大思想障碍。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我们不断遇到姓“社”姓“资”的质疑,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四个回合:
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从农村起步,这种质疑和困惑也从农村改革问题开始。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特大干旱,灾荒威胁着广大农民。当时安徽省委决定,与其让大片受旱的土地抛荒,不如借给农民去种“保命田”,实行谁收谁种。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贯彻执行,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在灾年里取得了丰收,小麦总产比历史最高水平还增产1435万斤。此举获得了省委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带领下“秘密”实行包产到户,鉴于历史的教训,防止日后被人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使队干部受牵连,遭惩处,18户农民的代表在保证书上画押具结,保证万一不测遭惩处时共同照顾队长的家属。结果,这个全县出名的穷队在实行包产到户后,当年的粮食总产量就达到13.2万斤, 相当于这个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量3.52万斤,比50年代合作化以来20多年油料的总和还多。显然,农民的创造给中国落后的农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但是,这种创造却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1979年3月, 某报突然以头条新闻加“编者按”,批评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责任制是“单干”,是搞资本主义。它反映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认识。当时出现这种非议,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在安徽等一些地方出现过,但是当时被作为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否定。60年代初,邓小平、邓子恢等领导同志曾经支持过农民的探索,后来也先后遭到批判。所谓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道路,其中“一包”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于是,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传统观念: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重新开始的这种探索,自然会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这就是说, 包产到户是集体化的组织形式,没有改变发展集体经济的总方向,它不姓“资”而姓“社”;选择包产到户这种形式,是因为它比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更有利于集体化的发展。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议通过的《纪要》中,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指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给予支持。到198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发展到377.7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64.2%。 在实践的推动下,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获得了明确的结论。1981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民兴奋地说:“我们终于给包产到户摘去了‘资本主义’的帽子!”
第二,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
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 华侨众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决定对闽粤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好地对外开放。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划出一定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当时称为“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并公布施行。随即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相继投入施工开发建设,厦门经济特区也参照兴建。
这些经济特区在所得税和投资环境方面给外商以一定的优惠,大量地吸引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广泛的关注。但长期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许多人对于一下子有那么多外商进入中国,在思想和感情上接受不了。特别是当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十年动乱期间对于发展外贸就是所谓“崇洋媚外”的批判在一些人心头仍有阴影。于是,对于经济特区的一些非议出现了。这些非议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
面对着经济特区或褒或贬、或是或非的种种议论,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专程到广东、福建,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视察了开放之初同样争议很大的宝钢。经过实地考察,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回到北京后,他找来中央几位负责同志,鲜明地表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2〕就在这次谈话中, 他提出了不仅要支持和发展这些经济特区,还要再开放大连、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开发海南岛。
1987年6月12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 邓小平同志回顾说:“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一共四个经济特区,广东省占了三个,福建省占了一个。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3〕
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4〕
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1984年、1987年、1992年这三次重要谈话,回答了三个问题:
(1)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
(2)建立经济特区是不是成功的?
(3)经济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
其中,第三个问题是管总的,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之日起就有人提出,到1991年还有人在议论。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践为基础,先后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1984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7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1992年:特区经济姓“社”不姓“资”。
第三,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碰到一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样对待商品、货币?要不要搞商品经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使我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经营管理必须高度重视公平的交换和分配,这种交换和分配只有利用商品和货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才能较好地做到。这样,就纠正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为传播的商品、货币关系是“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的正确观念。但是,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而不只是商品生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有的时候甚至把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的理论观点,作为一种“精神污染”的表现加以批判。一时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成了思想理论上一个无人敢问津的“禁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改革由局部推进进入到全面改革的新阶段。1984年4月, 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并组织了一个文件起草的班子。起草小组在广泛征求中央和地方各经济主管部门和理论界意见的基础上,九易初稿,供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补充,提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会上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作了150 多处修改和补充,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文件起草讨论过程中,人们对于《决定》中是否继续沿用十二大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起草的文件前6稿一直沿用了过去这一提法。在讨论第6稿时,国务院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在1984年9月9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经中央同意,从第7稿以后, 便采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理论上最大突破就是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决定》仍然强调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说是计划经济,但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是说,商品经济不姓“资”,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用。这在当时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到:“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5 〕这就为商品经济是不是姓“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第四,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的时候,我们仍然把“市场经济”区别于“商品经济”,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可见,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和作用,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高尚全、王梦奎、禾村三位同志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事典》,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一问题讨论的过程:
据介绍,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在讨论经济问题时,触及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当时的提法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4月16 日至29日,经济学界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的历时14天、389 人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上,有的专家学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互相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经济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长期刻苦钻研的成果,也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当时经济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概念并未为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际部门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其原因是,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认为市场经济是指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对立的。
但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1979年11月26日,正当经济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的高潮中,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等客人时,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6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谈话,在这次会见外宾后不胫而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党内外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党的文件中长期来采用的是“市场调节”的提法。”十二大的正式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十三大以后,这一问题讨论重新活跃起来。1988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广州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许多人建议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更加完整科学的提法代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明确提出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主张。然而,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这种观点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7〕1个月以后,即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对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再次讲到:“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到了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谈话在党内传达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趋于统一。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针对当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提法,表示“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党的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由此可见,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来之不易。它经历了十多年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反复讨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它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于是,我们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
“三个有利于”标准
面对着一系列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同志不断解疑,不断释惑,推动了改革开放一步又一步地向纵深方向推进。现在需要研究的是,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疑难和困惑的。
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同志突破各种思想障碍的武器是两个:
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
二是“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利弊得失的根本标准。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它联结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可以成为判断认识是否正确的客观尺度。因此,它是对付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邓小平同志就是运用这一锐利的武器,揭穿了“两个凡是”观点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展开,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许多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实践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有的时候还阻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于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认识的正确与否可以靠实践来检验,实践的对错靠什么来判断?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经碰到。当时的难题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实践”,是不是像“四人帮”鼓吹的那样,“就是好”,“就是好”?判断“文化大革命”对错、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曾有一些同志起草过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长文(后来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加以批判)。文中说:“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是什么标准?就是衡量人的认识和实践好坏、对错、利弊、得失的生产力标准。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生产力标准问题,作了大量的深刻的论述。
他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判断各项工作利弊得失的根本标准,必须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9〕1980年5月5日,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0〕1983年1月12日, 他再一次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1〕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讲的是判断认识和实践孰对孰错、有利无利的标准,即哲学界讲的价值标准;它最根本的是要看认识和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还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幸福。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于这么一个实践对错、利弊的根本标准问题,作了一个总括性的回答,他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
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它是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发挥。
有人把它同生产力标准对立起来,认为“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而且包括政治实力、军事威慑力和精神力量等等,因而用综合国力作标准纠了生产力标准的“偏”。这种说法是机械的。的确,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力量的综合指标,但其基础不是别的,还是经济实力。因此不应把“三个有利于”标准同生产力标准对立起来,而应看作是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发挥。
又有人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看作是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这样来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错误的。首先,“三个有利于”标准确实是针对着改革开放中屡屡出现的姓“社”姓“资”的质疑和困惑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就是说,姓“社”姓“资”的质疑束缚了人们的实践,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我们搞改革开放,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搞活社会主义、搞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姓“社”。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要大胆试、大胆闯、大胆改,不能一搞改革开放就说你在搞资本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破除这种思想障碍的最有力的武器。它告诉我们,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的本来没有姓“资”姓“社”问题、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就是对那些确实姓“资,但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合乎“三个有利于”、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如在我国法律下合法经营的外国资本、私人资本),也要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而是判断哪些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政治、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标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规范,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这些标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些具体标准,归根到底,都不能违背“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
由此可见,同实践标准相联系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推动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
注释:
〔1〕〔6〕〔9〕〔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236、 209、314页
〔2〕〔3〕〔4〕〔5〕〔7〕〔8〕〔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52、239、372、91、364、367、23、372页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特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三个有利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深圳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包产到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