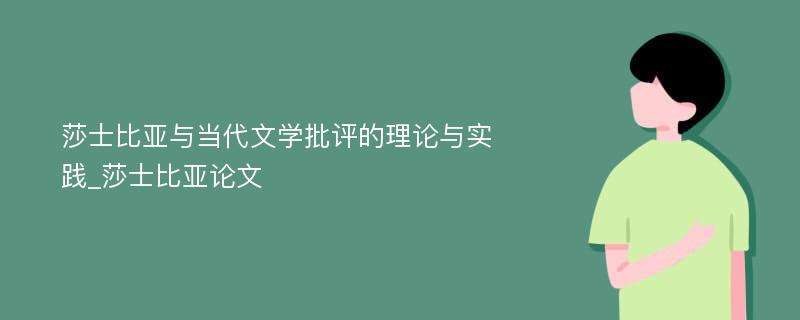
莎士比亚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当代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是文学批评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继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和英美新批评之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和流派,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莎士比亚作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其作品历来都是各种文学理论试图重新发掘和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已经形成一门“工业”的莎士比亚批评和研究作为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各种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本文将讨论莎士比亚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莎士比亚与解构主义批评
在本世纪下半叶继结构主义之后,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勃兴于西方的语言学、文学批评乃至哲学研究领域。它从对语言的微观探索开始,毫不妥协地向西方矗立了二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大厦提出了强有力的、颠覆性的挑战。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其一系列论著和讲演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思想。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首先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反叛。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的根本局限在于它把本文的一切方面、一切因素都纳入某种可以把握的、有确定意义的、先在的、自足自动的“在场”,即本文的总体结构,这种对结构“在场”的本质论的信仰限制了人们对本文的理解,它象传统语言学(甚至包括作为结构主义来源之一的索绪尔的语言学)和传统哲学一样,仍然没有最终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宿命。按照传统语言学的实体语言观,语词的指涉是实在的,符号和符义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种语言观把言语(被说的语言)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言语是同先在的说话者的“在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表达的是真实,是实在;而作为写作媒体的语言是派生的、次要的,它的主体的和情感的色彩总是模糊、甚至歪曲真实。二十世纪语言学大师索绪尔首先对这种传统的实体语言观提出了挑战。索绪尔认为,语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必然的逻辑关系,语词的表义功能并不在自身,而在它与处在同一系统中的其他词语的相互差异中。然而,索绪尔仍然把言语看作中心,而把写作看作言语的补充形式。这种言语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强调声音和存在、声音和存在的意义、声音和意义的理想状态的绝对切近。结构主义从一开始试图摆脱传统语言学和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它对为共时态的永久性“在场”的结构中心的设定,以及围绕这个中心对作品本义的总体有机结构(自足自动的、封闭的共时系统)的建构,表明它实实在在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因此,结构主义首当其冲成为解构主义攻击的首要目标。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作品的本文象语言本身一样不包含任何先在的或终极的“在场”,它绝不是作者一次完成的自足自动的封闭体系,而是由永远处在差异和对立的游戏状态中相互指涉的多种符号体系所组成的不断生成、不断指向其他本文和语言意义的开放的动态体系。因此,本文的意义是潜在的、隐喻性的、不确定的、矛盾的和多元的,对本文的解读是永无止境的。解构主义的目的皆在通过摧毁“言语中心主义”,分解本文结构,突破结构“在场”的限制,发现处在自由游戏状态中的“不在场”或不确定的意义,对本文作出多元化的解读。应该指出,解构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反叛,它实实在在还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事实上,德里达正是通过对传统语言学的批判,进而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和以人、以人的理性为中心的旧人文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和人文主义对世界、人和历史的本体论、本质论、因果论、目的论的解释都是站不脚的,世界和人类历史是由无数个没有起源、没有中心、也没有终结的充满矛盾和差异的、多种因素和力量在其中起作用的符号体系所组成的多元结构。
按照解构主义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衡量,以布拉德雷为集大成者的传统莎评和布拉德雷之后形形色色的现代莎评都应该予以重新检讨和估价。并从根本上作出修正。
在传统莎评中,浪漫派莎评无凝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柯靳律治曾提出“有机形式”的概念。柯靳律治认为,莎士比亚剧作并不象古典主义者所抱怨那样缺乏规则;莎剧的规则也不是古典主义者那种外加的人为的机械规则,而是一种有机形式。他进一步提出:“有机的形式是生来的,它在发展中从内部使它自己定形,它的发展的完成与它外部形式达到完美是统一的,是同一件事”。①这里柯靳律治把莎剧的“形式”看作是某种具有内在中心的、自我生成的、自足自动的有机统一体。这种看法显然与解构主义的无起源、无中心、无定形和异质性、差异性的本文观相抵触。
继以柯靳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莎评之后,对现代莎评影响最大的是布拉德雷。他的论著《莎士比亚悲剧》受黑格尔悲剧理论影响,力图揭示莎士比亚悲剧实质,寻找决定莎士比亚悲剧世界的“最终的力量”。他把这种“最终的力量”描述为抽象的“道德秩序”,认为“它发生作用是出于它自己性质的必然性”②。这种看法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无疑是一种典型逻各斯中心主义。此外,布拉德雷的“性格中心论”,他对莎剧本文和语言可以充分揭示人物性格以及读者通过阅读本文可以接近作者心理“在场”的看法,在解构主义批评家看来,都是值得怀凝的。因为莎剧本文和语言的转义、隐喻、意象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归结为一系列统一的、可把握的、符合作者意图的意义,因而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表现人物性格,也不可能向读者呈现作者心理在场。由此扩展开去,以弗洛依德为代表的运用现代心理分析学说对莎剧所作的一切解释,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也都是缺乏依据的。
在莎士比亚批评史上,以蒂里亚德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曾产生过持久的影响。蒂里亚德力图证明在莎剧中存在一种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统一的、统领一切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伊丽莎白世界图像”,这个世界图像的核心内容是贯穿从上帝到无生物的各个存在层次中的等级、秩序与和谐。这种历史观本质上仍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一元论。事实上,在新旧交替的伊丽莎白时代,各种矛盾着的意识形态是在对立和差异中共存于一起的,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本文中突出地表现为正统的保守主义和各种新的激进的和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等)之间的对立和相互消解。
从上文对莎评史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说的剖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传统的本质论人文主义莎评,还是解构主义之前的种种现代莎评(包括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其共通的根本缺陷在于对莎士比亚本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元论解释。这种解释把莎剧本文看作是围绕一个中心在场的、自足自动的、统一的和封闭的一无意义实体,因而在各自的界定中限制了对莎剧本文的解读,减缩或凝固了莎剧本文的重要意义和意义的不断生成。那么,把解构主义引入莎士比亚批评,对批评家们能产生怎样的启示呢?解构主义的哪些其本原则可以对传统莎评作出激进的修正呢?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的本文观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对传统莎评作出激进的修正。一是本文的多元性的不确定性。莎剧本文并不象传统莎评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有确定意义的、同构同质的一元意义实体,相反,莎剧本文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异质异构的。正是由于本文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它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本文中的多种符号体系在对立和差异中形成了许多空间,这些本文空间是由读者对本文的不断阅读加以充实的,因此,本文永远处于待充实的状态,永远是不确定的;对本文的解读也是多元的和永无止境的。二是本文的互文性(intertex tualitg)。按照解构主义的本文观,本文不是自在、自足、自为和自我指涉的静态的和封闭的意义实体,而是在差异中与其他本文相互指涉、相互交织、相互区别和补充的动态的开放体系;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都留有其他本文的痕迹(trace),任何在场的本文都只有在与其他不在场的本文形成差异时才能产生意义。同时,本文的指涉和源起(source)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因此,本文的互文性进一步规定了本文不可能是同质同构的,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一元意义实体,而是处在差异和矛盾中的异质异构的多元意义动态。
在当代莎评领域,解构主义虽然还没有占居主导地方,但它的理论和方法已开始渗透到许多批评家的评论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奥大利亚学者霍华德·费尔普里恩在题为《“我们的哑巴王后?”:〈冬天的故事〉中的在场解构》一文中,运用解构主义的分解策略对剧中里昂提斯怀凝赫米媪妮的贞洁这一中心事件作了深入剖析,认为里昂提斯的幻想以及阿波罗神谕的真实性都是无法确证的。原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冬天的故事》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所指(reference)的世界最终没有客观的现实性或本体论的稳定性,而是陷入符号和被确认的或权威性的意义之推延(deferral)的无休止的游戏中”。③费尔普里恩最后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艺术的复杂微妙的现实主义理解和接受了语言作为解释人类现实的媒介的堕落和不可救药的本性,突出了在场和所指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所有解释的最终的主观性。④象费尔普里恩一样,耶鲁大学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杰弗里H、哈特曼也是从语言入手对莎剧作解构分析的。他在题为《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诗意人物》一文中对剧中的几个人物及其语言作了深入分析。哈特曼认为,在莎剧中,最炫耀和自我暴露的东西是语言本身的流动,除了语言本身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语言的狂欢(revels)是没有止境的;在语言的压倒性狂欢中,人物似乎是语言的一种职能,而不是相反,“更精确地说,戏剧动作的轨迹似乎是语言对人物所产生的结果。”⑤这样,通过戏剧中人物语言的解构性分析,哈特曼对戏剧中人物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与费尔普里恩和哈曼特对莎剧的解构不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英语讲师伊丽莎白·费里恩德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乔纳森·哥尔德伯格则主要是从本文的互文性入手来分解莎剧的。弗里恩德在题为《“阿里亚十恩的断线”:〈 特洛伊勒斯与克丽西达〉中的引述修辞》一文中,讨论了这部悲喜剧与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荷马和乔叟的作品之间所存在的互文关系,深入剖析了该剧对这些作品的“引述”(cirations)以及这些作品在该剧中留下的“痕迹”(traces)。她认为,在这部剧作中存在一个“引述和对引述的滑稽模仿的迷宫”,剧中的大量悖谬即源出于此;莎剧的互文性、时代错误以及它对大量的文学和修辞遗产的依赖都显示了其本文的派生地位⑥。她明确指出,莎士比亚这部剧作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高度的语言意识”;在当代的文学批评气氛中,批评家们有可能显示莎士比亚的“自我反省的智力突袭”(self-reflexive forays of wit)何以与解构主义者的智力相媲美。她认为,德里达对符号的可引述性或二重性的论述可以被看作是对克丽西达内在二重性的不慎重的注解。最后,弗里恩德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在任何其它剧作中都没有象在这部剧作中如此骇人地对先前强有力的经典文本加以分解、庸俗化、非经典化和重新制作;他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以充满生气的反偶像精神从他所依据的素材以及他自己的文本中剥掉它们“原有的”本质⑦。哥尔德伯格在题为《〈麦克白斯〉与来源的思考》⑧一文中运用德里达的解构方法深入讨论了《麦克白斯》与其素材渊源之间的互文关系。在他看来,德里达的解构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对一切最终皆在维护意识形态强权统治的逻各斯中心和形而上的表现方式提出了质凝,它表明强权统治只是专制主义或集权政治的一种幻想,解构的结果必然导致对这种统治的反叛和颠覆。哥尔德伯格在文中具体分析了《麦克白斯》与霍林喜德的《编年史》、琼生的《女王的假面剧》等作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麦克白斯》的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异质的和分散的,甚至剧作的最终来源一一作者一一也必须在一种异质性分散(a heterogeneous dispersal)中加以考虑;在作品与来源之间所形成的互文空间中,来源分散了,道德差异变得模糊不清,人物的身份多重化,这一切无论是剧中的君王还是剧作的作者都无法控制。因此,在哥尔德亚格看来,象《麦克白斯》这样的剧作既不完全是保守的,也不完全是革命的,因为它自身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不可能服从于任何单一的和确定的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把解构主义引入莎士比亚批评确实在许多方面可以对传统莎评作出激进的修正,从而不断扩大和加深我们对莎剧的理解。然而,从上述几位批评家的批评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批评家有时似乎是在用解构主义的概念和术语硬套莎士比亚。在他们的笔下,莎士比亚似乎是一位深谙后现代主义诗学和语言理论的理代美学家。这种倾向在另一位运用解构主义方法分析莎剧的批评家詹姆斯L、卡尔德伍德的专著《在或不在:〈哈姆雷特〉中否定和元戏剧》(To be or not to be:Negation and Metadrama in Hamlet,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83)一书中表现尤其突出。与结构主义一样,解构主义的主要缺陷还在于它在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主义固疾,这导致它忽略了对莎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舞台演出的研究。
二、莎士比亚与女权主义批评
女权主义是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政治和文化运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与其它女权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是从女权和女性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评价和建构文学史和文学本文。女权主义的戏剧批评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女权主义戏剧批评吸收了人类学、心理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的一些成果,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戏剧美学,对当代观剧的理论和实践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国戏剧评论家苏艾伦·凯斯于1988年制版的论著《女权主义与戏剧》从女权主义戏剧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等方面对女权主义戏剧运动和批评作了总结,并把女权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提出一种“新的诗学”。我们从凯斯的论述和其他一些女权主义莎评家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女权主义戏剧批评,包括女权主义戏剧批评的一般特点。
(一)从女权和女性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对戏剧史和古典戏剧作品(包括戏剧)作出重新解释和评价。凯斯在自己的论著中对伊丽期白时期的戏剧舞台上没有女性演员以及女性主角总是由男童扮演这一史实提出了新的解释。传统的戏剧批判一般是从女性的生理学构成及其所受的教育来说明女性不适于在户外或公众场合表演(如声音弱、缺乏演说训练等)。凯斯对此不以为然。她认为在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首先,在伊丽莎白时代如同在古希腊雅典时代一样,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中,女性总是被等同了性欲,女性的身体被看作是引起性欲的场所。因此,从舞台上驱逐女性是为了避免由性欲引起的社会骚乱,维护现存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其次,这一历史现象还根源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中存在的性对立。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真实的女性不但从舞台上消失,而且舞台上性欲的物理再现也被排斥,代之以在精神领域对性欲的象征性文化再现(例如语言再现)。凯斯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观剧就是发源于这些文化准则和实践之中”。⑨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上,女性角色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性行为是由男童扮演和模仿的,对此一些批评家还从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与此相反,凯斯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把舞台上男性模仿欲加以美学化的男权批评传统所依据的原则,与教会用来排斥女性的原则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在禁欲的实践中,只有男性才是公众表演和艺术生产的适合场所⑩。凯斯进一步指出,男童扮演女性角色是由于男童与妇女一样对成年男子的依赖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她发现莎士比亚喜剧中存在着大量的“性交叉”(Cross-gender)现象。这种现象在她看来清楚地表明,在莎剧中,虚构的“女人”(fictional ‘woman’)是作为男人之间的交换对象面出现的;无论是这些虚构的“女人”,还是十七世纪以后舞台上出现的真实的女性,“都无法逃脱扮演男性交换世界中的商品角色。”(11)
(二)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是在修正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首先肯定莎士比亚和弗洛依德处理的是同一题材,即人类心灵中表达和潜藏的情感,他们都是心理学家(12)。但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与弗洛依德和拉康的男性中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女权主义者来看,弗洛依德和拉康把女性排除于“主体的角色”之外,而把整个艺术创作置于父亲与儿子的男权秩秩中(13)。”在这个男性性欲和阉割的秩序中,女性作为男性的“他体”(other)只是男性欲的对象。与此相对,女权主义者把女性作为两性中的主体,把母性(motherhood)作为心理分析的中心。如女权主义对《麦克白斯》的解读首先是把麦克白斯夫人和三巫女放在突出的地位;《哈姆雷特》里的中心人物不是丹麦王子,而是奥菲利娅,卡罗尔·尼利就明确宣称:“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批评家,我必须‘讲述娥菲利娅的故事”。(14)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在当代莎学界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朱丽叶·杜辛贝尔的《莎士比亚和女人的本性》(Juliet Dusinberre,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women,London:Macmillan,1975),玛丽利恩·弗兰奇的《莎士比亚的经验划分》(Marilyn French,Shakespeare's Division of Experience,London,Cape,1982)以及卡罗琳·梭兹等合编的评论集《妇女的角色:女权主义莎士比亚批评》(The woman's part:Femin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Chicago,1980)等等。
女权主义批评提出的许多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传统莎评的一种进激的修正和补充。然而,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常常把莎剧人物当作真人来处理,把女性的本质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抽去了其中的历史和社会内容。因此,一些受新历史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把女权主义的心理批评看成是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的本质论批评,主张从历史观点出发,把莎剧放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莎剧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关联(historical context)中加以研究,进而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莎剧作出新的解释。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艾莱恩·舒瓦尔特的论文(表现娥菲利娅:妇女、疯狂和女权主义批评的责任》(Representing Ophelia:women,Madnes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by Elaine showalter,收入shakesprae and theQvestion of theory ,ed,by patricia perker and Geoffrey Hartman,1985),凯瑟琳·麦克卢斯基的论文《男权的诗人:女权主义批评和莎士比亚:〈李尔王〉和〈一报还一报〉》(the patriarchaal bard:feminist criticism and Shakespeare:King Lear and Meaoure for Measure,by Kathleen Mcluskie,收入political shakespeare,ed,by Jonathan Dollimnre and AlanSinfiel,d1985)以及丽莎·贾狄恩的论著《满口唠叨向女儿:莎士比亚时代的妇女和戏剧》(still Harping on Daughters:Women and Drama in theAge of Shakespeare,by Lisa Jardine,Brighton:Harvester,1983)等。舒瓦尔特对奥菲利娅的分析在方法是很独特的。她不是象卡罗尔·尼利那样全然依据莎剧的本文“讲述奥菲利娅的故事”而是深入考察奥菲利娅这个人物在绘画、摄影、大众文化、文学、戏剧演出和批评中的历史演变。他认为,对奥菲利娅的不同表现是与不同时代的文化、历史及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的说,是取决于人们对待妇女和疯狂的不同态度的。因此,在她看来,对女权主义批评来说,从古典时代那个有教养的、虔诚的奥菲利娅到后现代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主人公,这中间不存在一个众口归一“真正的”奥菲利娅,也许只有“一个大于其所有部分之总和的、多种视角的立体主义的奥菲利娅”。(15)不难看出,舒瓦尔特的分析在方法上把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从作品全文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批评的视眼。应该说,舒瓦尔特在这方面是受惠了新历史主义的。
三、莎士比亚与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
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英美兴起的两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它是对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有力反击。这两种潮流(在英国主要是文化唯物主义,在美国则是新历史主义)虽然在各自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方法上和总的倾向上是相近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乔纳森·道里莫尔普对“文化唯物主义”的内涵作过具体阐述。他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把历史联系、理论方法、政治信念和本文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历史联系意在挖掉传统上赋予文学本文的那种超验意义的基础,发现本文的历史内容,理论方法可以避免只用本文自身的语汇来再现本文;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信念与传统批评中的保守范畴相对立;文本分析将对传统方法的批评置于它不能被忽视的地方。道里莫尔进一步指出,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的是文学本文在历史中的含义,必须把莎剧置于产生它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而且,四百年来莎剧在不同的历史联系中仍在不断被重新建构、重新评价。因此,“这些剧作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如何产生意义,取决于它们所处的文化领域。”(16)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流派首先是针对旧历史主义而言的。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兴起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达到全盛时期。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1)新历史主义一反旧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对人性的本质论解释,否定历史中存在永恒不变的和普遍的人性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性观;(2)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制约和决定作用。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看来,蒂里亚德所描绘的“伊丽莎白的世界图像”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结构,因为历史和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个包含起主导作用的、残余的、新出现的、从属的、被抑制的和结合而尚未彼此同化的各种文化形式和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吸收、相互修正、相互摧毁、颠覆或代替的矛盾复台体。在新旧交替的伊丽莎白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和矛盾性表现尤其突出;(3)新历史主义强调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考察历史和文化过程,发掘文学本文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互文关系中的政治和意形态含义。实际上,新历史主义对莎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就是通过根本改变传统的美学批评赋予莎剧的意义,重新确定莎剧的历史作用地位。
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莎评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实绩和灼灼逼人的挑战势头,在当今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设计:从莫尔到莎士比亚》(Stephen Greennblatt,Re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Univ of Chicago press,1980)和《莎士比亚的协合》(Shakespearean Negotietions,Berkeley,univ,oi California press,1987)、乔纳森·哥尔德伯格的《詹姆斯一世和文学政治学:琼生、莎士比亚、堂恩和他现的同时代人》(JonathanColdberg,James I and the politcs of Literature:Jonson,shakespeare,Donne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Bal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83)、乔纳森·道里莫尔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o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roaries,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1984)以及乔纳森·道里莫尔和阿兰·辛菲尔德合编的论文集《政治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新论》(political Shakespeare,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rerialism,Cornell univ press,1945)等,这些论著或论文集都集都中体现了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特点。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合》一书中根据文艺复中兴时期的文化史实阐释莎剧,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17)哥尔德伯格在书中研究了詹姆斯时期的权威(主要是詹姆斯一世的权威)及其表现之间的关系,力图揭示詹姆斯一世的自我表现方式及其所采取的施行权力的手段如何形成包括莎士比亚戏剧在内的这个时期的文化产品。在《激进的悲剧》中,道里莫尔从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戏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悲剧实际上比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更加激进,更富有颠覆性。这不仅表现在它对宗教正统性的挑战,而且还表现在由此产生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政治和权力关系的非神秘化以及“人”的非中心化。道里莫尔据此将这些剧作的特征概括为“一种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主义”(18)。这样,道里莫尔就对被普遍接受的以基督教和本质论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戏剧的批评和研究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莎评的优点在于,它强调把莎剧放在其产生和被接受的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结构中,从多种社会的文化因素的相互制约的联系中研究莎剧,从而避免了各种形式主义的纯美学批评所固有的弊病。但是,应该指出,新历史主义由于过分强调对莎剧的历史和文化批评,从而忽略或者没有足够重视对莎剧的美学批评,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一大缺陷。
注释:
①《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p、128
②《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p、48
③Shakespear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ed,by patricia parker and Ceoffrey Hartman,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 1985,P、14
④ibid、P16
⑤ibidP、P43
⑥ibidP、P21
⑦ibid、P、35
⑧Shakespeare Reproduced,Text tec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ed、by Jean EHoward and Marion F、O,Connor,New york and London,Metnuen 1987,PP、242-
⑨sue-Ellen Case,Feminism and Theatre,Macmillan PublishersLTD,1988,p21
⑩ibid、P、24
(11)ibid、P、27
(12)Political Shakespeare,ed、by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Sinfield,Cornell univ、Press,1985,P、89、
(13)Feminism and theatre,P、120
(14)Shakespear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P、78
(15)idid、P、92
(16)Political Shakespeare,PP、Vii-Viii
(17)参见杨正润:《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文艺报》1989、3、11、
(18)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 Religion,Ideology andPower in the Drama of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The univ、ofChicago press,1984,PP、4~5
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女权主义批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