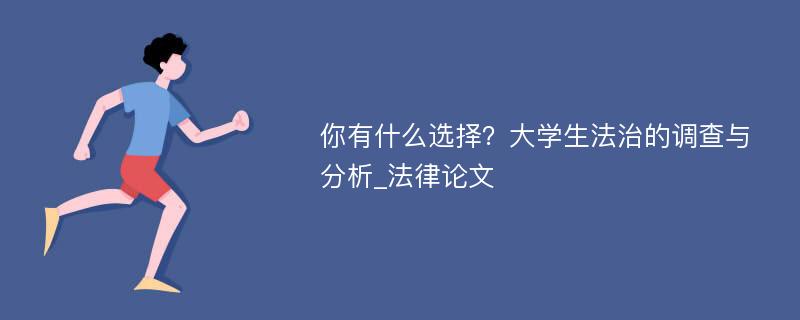
您的选择是什么?——在高校学生中关于法治问题的一些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您的论文,法治论文,高校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千三百多年前,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们不断引述的著名命题:由一个最好的人或最好的法律来统治,何者更为有利?亚氏的结论是法治胜于人治。他的理由是,法律是没有感情的,因而不会偏私;而人却是有感情的。另外,法律是由许多人决定的,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个人好一些。可见,在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里至少包含两重意义:其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其二,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氏的法治论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建立普遍的、良好的法律规则并严格地服从。
无独有偶,差不多一千年以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有大作为的皇帝唐太宗也对他的谏议大夫魏徵谈论过人治与法治(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 那时的法律乃是皇帝手中的一种工具,他本身并不受法律的约束)的问题。唐太宗李世 民说,我看古来的帝王,凡是以仁义治国的,国家都能够长治久安;凡是以法律治国的 ,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但国家很快会垮掉。李世民开创了史称“贞观之 治”的繁荣盛世,颁行了有名的《贞观律》,在中国历史上包括法制史上,也可以算得 上是一位代表人物,而他的结论却是人治胜于法治。他的理由是:治天下要得人心,要 治本,而法律只能治表。李世民是用儒家的人治思想对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略进行简明概括的。儒家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是:其一,力主君主施德行仁,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二,主张在任用官吏上“举贤使能”,即所谓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三,主张对被统治的民众进行德化教育,辅之以刑罚,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时光又流逝了一千多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法学界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中,进行了一场人治和法治孰优孰劣的讨论。当时几乎无人赞成人治,而互相对立的两种观点是: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 法治当然是对的,但是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都要人去执行,怎么能光靠法治呢?“ 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一定要把人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行。主张法治的人则认为,实 行法治不是不要人,而是说法大于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人,而在于法 大于人还是人大于法。
当前在中国法学界,已经没有学者主张“法治与人治相结合”了。因为,经过二十多 年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对法治和人治的概念已经有了形成共识的正确界定。就“人治” 和“法治”的关系而言,这种界定大体是:在治国方略上,“人治”主张依靠执政者个 人的贤明和能力来治理国家,推崇个人的权威,无视或轻视法律的权威。简言之,“人 治”的价值取向是“人大于法”。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 格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强调人民的主权和法律的统治,反对个人的专横独裁或少数人 的恣意妄为。简言之,“法治”的价值取向是“法大于人”。因此,从逻辑关系上说, “人治”和“法治”是不可能结合的。否则,我们在理论上对治国方略就无法选择:到 底是法律服从某个或某些个人?还是所有的个人都要服从法律?
上述界定已经与现代法治理论有了某种契合,不过多少还是在学术界内从理论层面上来阐述的。而我始终坚信,理论应当联系实际。所以,我对“依法治国”的信念在社会生活中实际树立的程度,对法治理论为公众正确理解的程度更感兴趣。因此,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一些跟踪性的调查研究。
这些调查研究还要从1988年初至198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者进行的一项名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的科研课题说起。该课题当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的方式,在上海等十三个大、中、小城市,对两千两百人进行了调查。在该课题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政治人”》一书中,有许多问卷调查的问题及回答很令人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的:
对人治和法治的偏好(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偏好 人数 占总数的%
人 186 9.3
制度42821.4
既要人,也要制度 123661.9
其他111 5.5
未答 34 1.9
显然,第一种选择是偏好人治的,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当时只占极少数。第二种选择是偏好法治的,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当时也占少数。有意思的是做第三种选择的人。在当时,他们的人数不仅占了大多数,而且与十年前法学界争论中主张“法治与人治相结合” 的观点非常相似。《中国“政治人”》的作者分析这种态度说:“可不可以说它又是一 种由过去人治的观念向现代法治观念转变的中间状态。它既希望于制度,同时也寄希望 于人,追求完美与理想但却回避‘万一人不行怎么办’这种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尖锐问题 ,又是一种还很不彻底的法治观念。因此,我们看到,追求法治的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 正在形成。”(注: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 9、40页。)
这些年来,我不时用《中国“政治人”》中设计的关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问卷调查。在这里,我仅举两个与高校学生有关的调查结果并进行分析。
2002年12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设在深圳市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法学硕士学位班上提 出了《中国“政治人”》中的这样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并且规定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的所有选项中,“只能选一项,否则无效”。
问题一:
几个同事在聊到“文化大革命”时发生了争执。假如您在场会赞同谁的意见:
1.老张:要是领导人都像周恩来那样,“文革”就不会发生了。
2.老王:人再好,也不如制度靠得住。有好的制度,出了“四人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3.老李:我看最好是有周恩来那样的领导人,又有可靠的制度。
参加回答问题的共二十九人,赞同老张意见的没有;赞同老王意见的十六人,约占百 分之五十五点一;赞同老李意见的十二人,约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三;持其他意见的一人 ,约占百分之三点四。
问题二:
您觉得,担任党和政府领导人最重要的条件是:
1.廉洁奉公。
2.作风正派。
3.遵守法律。
4.富有才干。
参加回答问题的共二十九人,认为廉洁奉公是最重要条件的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 一;没有人认为作风正派是最重要的条件;认为遵守法律是最重要条件的十六人,占百 分之五十五点一;认为富有才干是最重要条件的六人,占百分之二十点六。
2003年3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级本科生的课堂同样提出了上述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参加回答问题的共五十人,对“问题一”的回答是:
赞同老张意见的没有;赞同老王意见的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二;赞同老李意见的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对“问题二”的回答是:认为廉洁奉公是最重要条件的八人,占百分之十六;认为作 风正派是最重要条件的十四人,占百分之十四;认为遵守法律是最重要条件的二十人, 占百分之四十;认为富有才干是最重要条件的十五人,占百分之三十。
“问题一”和“问题二”与“对人治和法治的偏好”的问题相比,虽然在提问的角度上有些变化,但是实质上是一致的。在“问题一”中,老张的意见显然属于偏好人治,在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有这样的偏好了。与差不多十五年前有百分之九点三的人有人治偏好相比,不仅有了质的变化和进步,而且与今天法学界无人 赞同人治的情况是一致的。在“问题一”中,老王的意见显然属于偏好法治,在我所调 查的人群中,赞同老王意见的均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与十五年前偏好法治的人只占 百分之二十一点四相比,已经有差不多一倍以上的增加,说明法治观念已经大大深入人 心,至少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是如此。在“问题一”中,同样有意思而且令人难以 回答的是老李的意见,它实际上主张的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我同意《中国“政治 人”》的作者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法治观念”。我不认为老李的意见是错 误的,因为他追求的是法治的理想状态。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现实中在“好人”和“好 制度”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持这种意见的人将做何种选择?与十五年前希望“人和制度 兼得”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九相比,上述调查问卷中同意老李意见的人占的比例平均 下降并不多。我认为,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我国法治观念正在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另一 方面也说明了我国从不彻底的法治观念向彻底的法治观念转变还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
在对“问题二”的分析中,我将同意第一、二、四项为担任党和政府领导人最重要的条件的选项归为对人治的偏好,将同意第三项为担任党和政府领导人最重要的条件的选项归为对法治的偏好。两种偏好相比,差不多是各占一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选项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和制度兼得”的中间或理想的状态可选择,所以使 不少人重新偏好了人治。对于这种现象,电影《生死抉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注脚。 《生死抉择》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给人们的印象之一却是:反腐败主要不 是靠法治,而是取决于几个具有高度觉悟的铁面无私的清官,特别是那位从北京回来的 省委书记。我们应当承认的是,《生死抉择》反映的的确是中国的现实,但是它也展示 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迄今仍根深蒂固的“清官”观念。所以,从《生死抉择》所获 得的热烈掌声中,我们也可以体悟到,浸透在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传统观念要向现代法治 观念转换,是多么的任重道远!
从延续几千年的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中,从上述调查问卷中,我们还可以 进行这样一些分析:
首先,“人治”和“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原则和方略:至少历史发展到今天,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作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略,法治是优于人治的。虽然“人治”论和“法治”论都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但前者注重的只是“人存政举”,而后者则看到了如果不严格依法办事,最终只能导致“人亡政息”。所以,江泽民要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其次,在我国实行法治,并不是不要其他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和手段。例如思想的 、道德的等方法和手段,仍然是我们现在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很重 要的方法和手段。他们与法治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在我国实行法治,也并不是要 否定人的作用,因为法治毕竟还是要通过人来立法并加以贯彻和实施。只不过在法与人 的关系上,法治论认为良好的法律比贤明的人具有更大的权威;在治理国家方面,良好 的法律比能干的人更靠得住。惟其如此,我们必须摈弃“人治”的治国方略。
再次,由于“人治”和“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原则和方略,由于我们只能摈 弃“人治”,所以我们就不能“实行法治与人治相结合”。这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要遵 守逻辑同一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治国的原则和方略的根本价值选择问题。
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就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 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 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 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48 页。)同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关于“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 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的问题时也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我 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48页。)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了人治的危害性。1988年 他就指出过:“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 ,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272、311、325页。)到1989年他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一个 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 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311、325页。)同年他又指 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 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注:《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272、311、325页。)邓小平还认为,要解决制度和人治的问题,就必 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也指出,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所提 出和要求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对于保证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保证 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治是不相容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治的问题,而不必实行“法治与人治相结合”。因为,从制度上、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不仅可以保证少出“坏人”,还 可能出现“好人辈出”的情况,何况邓小平还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职业和经费的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域限制,使我的调查从法社会学方面说,存在很大不足。第一,我所调查的人群可以说都是大城市的人士。第二,我所调查的人群都是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第三,我所调查的人群都是学习过或正在学习法律专业的人士。因此,至少与《中国“政治人”》调查所涉及的人口的构成相比,有很多不同。所以,将两者相比较,必然会有不少局限,甚至有不好比和不可比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比较仍然是有一些意义的。此外,由于专业和时间的关系,我一直未能对“问题一”和“问题二”进行修改,没有使它们与今天人们关心的问题更贴近。不过,这两个十多年前的问题,尽管在当下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其内容的核心和实质仍然具有时代性,仍然能够反映“法治”为公众理解的程度。
同样有意思而我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是,正如读者们在本文中所看到的,在人大“深圳班”和“本科班”的回答之间也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差异简单说就是,在“问题一”和“问题二”的法治偏好方面,“深圳班”均高于“本科班”。可能因为调查人数少,这种差异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深圳班”的学生都已经大学毕业并且正在工作,是不是他们对实行法治有更迫切的要求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2003年11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中国法研究生班的课堂上又提出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参加回答问题的共六十五人,对“问题一”的回答是:
赞同老张意见的三人,占百分之四点六;赞同老王意见的二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八;赞同老李意见的四十人,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六。
对“问题二”的回答是:认为廉洁奉公是最重要条件的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认为作风正派是最重要的条件二人,占百分之三点一;认为遵守法律是最重要条件的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认为富有才干是最重要条件的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这样的结果多少令我有些诧异。香港学生在对“人治”的偏好方面,差不多都高于内地学生,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香港人的法治观念应该比内地人更高才是。对其中的原因我只能试猜一二: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里,可能人们对领导人个人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迫切?这也是需要通过继续调查才能得到的结论。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之后,必须彻底摈弃人治观念,已经是不争之说了。然而,只有当全社会不再有人选择“人治”之时,当十几年前和今天仍然选择“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人中的绝大多数转而选择“法治”之时,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不再有任何不彻底的法治观念之时,我们才能说离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远了。因为,毕竟通行的法治理论是将 大众的法治观念高低作为判断是否是法治国家的标准之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