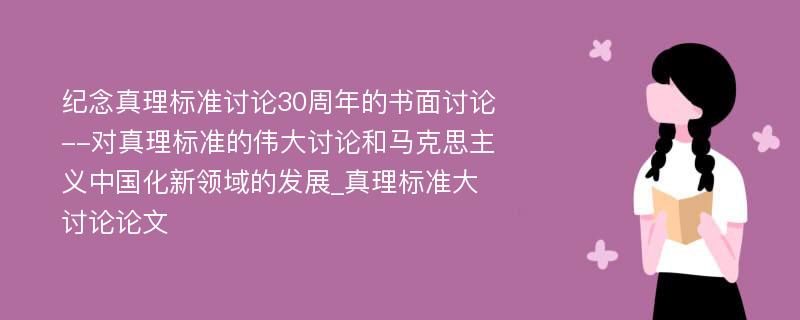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笔谈——真理标准大讨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开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标准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大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反复表明,一个重大事件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往往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真正地感受和领悟。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不例外。从30年后的今天看,这一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决不限于把一切理论推向了实践的审判台,从而恢复了实践的最高权威。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在毛泽东以后,邓小平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革”,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特征。“冷战”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意味着战争与和平、革命与战争的世界总格局正在改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点。这实际上表明,从十月革命以来利用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革命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概括起来就是:需要从满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优越性中回到现实,把立足点从引导世界历史潮流转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认真思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中,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思想上的大解放。
因此,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实质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正是有了思想解放,才有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选择,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就此而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的确是与日俱增的。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现在看来已没有多少分歧。但是,什么是解放思想?怎么继续解放思想?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在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本来,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清晰的表述,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②很明确,解放思想是一个有前提、有党性、高度理论自觉的口号,前提就是实事求是,党性就是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有一个注释:“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同样很明确,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前提是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而不是将它们根本否弃。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了这种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的思想路线。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有人蓄意抽掉这一前提去谈论思想解放,将其作为一个无前提、无党性的口号,甚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而不断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底线,绞尽脑汁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由于去掉了这一前提,在他们看来,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论断就是矛盾的,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要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他们的着眼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而是要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思想禁区”,并最终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认为邓小平本身也是矛盾的:一个是所谓传统的共产主义“解构者”的形象,即努力回归西方文明,淡化革命历史和传统,坚持市场化改革和与国际接轨、极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而奉行实用主义的“非毛化”邓小平;另一个是所谓“刻板的”共产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明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定不移地主张“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毫不含糊地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百年不动摇”,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自豪的“毛派”邓小平。他们认为,这两个邓小平是无法统一的,并企图通过肢解邓小平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实际上,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破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也好,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也罢,其目的是真正走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和现实作用,就在于其在科学解剖资本主义基础上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一种真理的力量,使我们树立了一种科学的信念,有了历史的方向感。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不可能真正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通过自我调整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超越并最终取代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种历史趋势,不是书本教条,而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历史本身的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理想就在我们生活实际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③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决不会在道路问题上动摇,更不会把向资本主义回归视为解放思想。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理想信念出发,不断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化调整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找到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已经主宰了世界的发展,但整个世界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划分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二元分裂”状态。因此,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看到资本主义确实还有扩张和自我调整的空间,但坚信其发展必然有一个“极限”,而一旦到达这一极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全面爆发,所以社会主义的希望只能是“资本主义发达民族的同时行动”,此即“中心引导”式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列宁语)。这时的世界状态也随之从“二元分裂”转变为“二元对立”,即世界已经从外在的“两块”,变成了内在的“两极”,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中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两大民族的基本矛盾,形成了资本主义“核心——外围”两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新格局。于是,出现了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和“焦点”,出现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这个历史新特点,列宁正是据此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成功”的新结论,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几十年,这种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点打开缺口的“外围突破”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
但是,“外围突破”毕竟不能直接引领历史,而只有在其转化为“核心危机”时才能根本扭转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局面。然而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变的新特征,恰恰在于其减少了对于外围地区进行资本输出的依赖,而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上的支配、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国际游戏规则的操纵等获取超额利润,维护资本的活力。这样,通过资本主义外围的政治独立以致随后经济独立的方式,已不可能真正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根本动摇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相反,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上超越发达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领世界潮流,甚至连自身的存在权利也将被剥夺。社会主义必须在回应时代主题方面有所作为,才能获得蓬勃生机和发展空间,于是,改革开放、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定位问题。共产主义对于我们,首先是一种指导实践的历史观和历史方向感,也就是方向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一方向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创新和具体化。因此,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改革开放、探索新路,都是具体路径的开拓,而不是根本方向的改变;搞市场经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都是体制和部分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根本制度的改变,不具有方向和道路意义。
其实,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性,就在于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是一种彻底的理论逻辑,而且其本身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结果,是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发现的生活逻辑。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在其全球化的扩张中,必然不断地制造发达和不发达、中心和边缘两极;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永远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寄希望于搞资本主义,必定是一场灾难一场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不允许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也不能包容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中国。毛泽东对此有过这样经典的描述:“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几乎用同样的话语作了同样的描述:“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⑤
新中国成立即将59年,目前又处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世纪,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变呢?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中国正面对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国际安全领域的斗争、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等依然深刻复杂,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依然存在,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增强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不断壮大总是让一些人感到如坐针毡,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总是让一些国家感到莫大的威胁。它们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事件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对于这种企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否则,将不仅对于中国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世界也是一个难以消化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拓,本身就是对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贡献。
因此,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如列宁指出的:“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经过30年开拓创新树立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历史给我们的启迪,这就是,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不断乘风破浪、乘胜前进。”⑧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36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20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⑦《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⑧转引自刘云山:《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载《求是》2008年第2期。
标签:真理标准大讨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