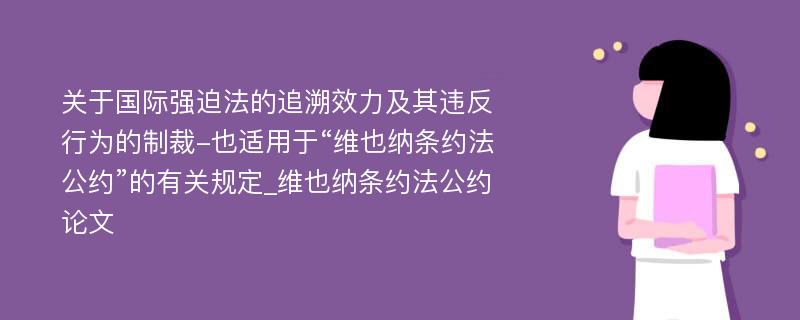
论国际强行法的追溯力及对其违反的制裁——兼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也纳论文,约法论文,对其论文,有关规定论文,公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强行法的研究和应用也就提上了日程。作者对国际强行法下一个定义;并认为国际强行法规则是非追溯性的,但明文规定国际强行法的《条约法公约》第53条则具有追溯力;对于违反国际强行法而订立的条约或实施之行为,应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无效”或“成为无效而终止”的制裁,并应消除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抵触性后果。
在冷战结束的今天,国际社会作为整体,越来越希望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采取某些特别的法律措施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安全。基于这种考虑,对于国际强行法的研究与应用便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
所谓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
1969年的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在国际强行法问题上,率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国际强行法作出若干规定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该公约第53条对国际强行法作出如下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亦即强制规范,下同。——笔者)抵触者无效。就适用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①
《条约法公约》第53条适用于条约因与某项既存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而无效的情形,而该公约第64条则适用于如下情况:即条约缔结后,因与新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使得该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第64条的内容是:“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②
以上两项条款是《条约法公约》就国际强行法有关方面所作的主要规定,这一创举将对当代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秩序中,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作用在于保护整个国际社会及其行为规则不受个别协议或行为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条约法公约》是《国际联盟盟约》、《联合国宪章》以及战后各种多边国际公约所倡导的精神与传统的延续和组成部分。在《条约法公约》中对国际强行法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表明世界各国已逐步认识到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权益和社会目标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正趋向于制度化、法律化,任何一个国际法主体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任意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鉴于国际强行法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国际强行法的某些方面中以若干探讨。
一、国际强行法的追溯力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从国际强行法的作用范围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研究的是国际强行法的时间作用范围。
毫无疑问,时间与某一法律规范的适用结合在一起,是确定该项规范的有效性及其实施的一个因素。一项法律原则或规范必然有其发生作用与效力的时间范围,一般来讲,这个时间范围起始于某项法律原则或规范(此处仅指成文法)经立法机构授权生效之日,终止于该项原则或规范因某种原因而失效之时。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原则或规范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会超出这个时间限制,而对其生效以前的某种情势发生作用,换言之,这些原则或规范可以对某种情势(法律的、亦或事实的)加以追溯适用。
那么,具体到国际强行法,其追溯的效力应该如何?这实际上涉及到两种情形:其一是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具有追溯力,其二是《条约法公约》第53条本身是否具有追溯力。
(一)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具有追溯力。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条约法公约》草案第50条(亦即生效后的《条约法公约》第53条——笔者)的最后评论中,就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追溯力问题作出如下表述:“问题在于,本条款(指草案第50条——笔者)的规则是非追溯性的。该条款必须与第61条(一项强行法新规则之产生)结合起来看。③这一表述说明,在国际法委员会看来,《条约法公约》中所规定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不具有追溯力的,同时,委员会还要求在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追溯力问题上,应与草案第61条(亦即生效后的《条约法公约》第64条——笔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从前面述及的《条约法公约》第64条的规定来看,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某项条约在缔结时是有效的,但由于其条款与后来确立的一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相抵触,因而使得该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所谓“成为无效而终止”这种措词已清楚地表明,一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的产生对某一条约的有效性并不具有追溯力,如果该项条约与新产生的强制规则相抵触,那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仅在于使前者“成为无效而终止”,却不能使得前者自始无效,换言之,从前者订立到后者产生这段时间内,前者应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一但新的国际强行法规则得以确立,则与之相抵触的既存条约就应失去法律效力。因此我们才说,依据公约第64条规定而成为无效的条约不是“自始无效”(void ab initio),而是“自现在起无效”(nullity ex nunc)。
除公约第64条以外,国际强行法规则的非追溯性在《条约法公约》第71条第2款中还得以进一步强调。该条款规定:“遇有条约依第6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之情形,条约之终止:(甲)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义务;(乙)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不相抵触者为限。”④
由于国际强行法规则不具有追溯力,因而有些学者担心,在这些规则产生以前缔结的条约尽管与后来所出现的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相抵触,则此类条约还是会在国际社会中毫无阻碍地继续得以适用。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尽管一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对先于它而缔结并与之相冲突的条约及其后果不能追溯适用,然而一旦国际强行法新规则产生了,根据《条约法公约》第53条、64条和71条2款(乙)项的规定,所有条约,无论是在缔结时与某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相抵触的,还是先于该项国际强行法新规则而缔结、现在与之发生冲突的,均属无效或成为无效而终止。这些条款的各项规定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它表明:国际强行法规则一经确立,是不会允许与之相抵触的任何法律制度与它同时并存的。例如,在早期的国家关系上,曾经存在着许多关于奴隶贸易的条约,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后来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为非法,禁止奴隶买卖的强制性国际法规则因而得以逐步确立,为能与这个新出现的国际强行法规则保持一致,有关奴隶贸易的条约便纷纷成为无效而终止。
将《条约法公约》第53条和第64条的规定结合起来适用,可以使得所有与国际强行法相抵触之条约归于无效。如果只是单独地适用其中的某一条,则有可能形成漏洞,因为第53条只是规定了“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重点号系笔者所加),换言之,该条款只是明确了后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则而订立并与该项规则相抵触之条约的法律效力问题,而对先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则而订立的条约,如果它与该项强制规则相抵触,其法律效力又该当如何?公约第64条的规定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总而言之,将公约第53条和第64条结合起来适用,可以有效地废弃与国际强行法原则或规范相抵触之任何条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条约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损害。
(二)《条约法公约》第53条是否具有追溯力。
关于这个问题,《条约法公约》本身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公约第4条(“本公约不溯既往”)规定:“本公约只适用于各国在对其生效以后所缔结的条约,但本公约中规定的任何规则如在本公约之外,依国际法原应适用于条约,其适用并不受到损害。”⑤从这项规定来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在本公约之外”、“原应适用于条约”?
此外,《条约法公约》第28条(“条约不溯既往”)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⑥由此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即该公约第53条是否包括在这个“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的范畴之内?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认为:“条约法的编纂必须从这一基点出发,即当今存在着国家绝对不得以条约安排来加以损抑之规则。”⑦换言之,在国际法委员会看来,现代国际法上已经有某些强行法规则存在,而《条约法公约》关于强行法的规定只不过是承认了这个事实,是这一事实的逻辑结果。⑧显而易见,《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规定是对早已存在的国际强行法规则的编纂,而不属于“国际法之逐渐发展”,更不是首次将强行法引入到国际法领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依照上述《条约法公约》第4条和第28条,该公约第53条中关于国际强行法的有关规定是“在本公约之外,依国际法原应适用于条约”,或属于“另经确定”的范畴,所以“其适用并不受到损害”。这就是说,《条约法公约》的某些规定可以适用于该公约生效以前所缔结的条约,再进一步明确地讲,可以认为公约第53条能够回溯适用,它具有追溯力。
在追溯力问题上,《条约法公约》第52条(“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施行强迫”)的情况与第53条颇为相似。公约第52条规定:“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含国际法原则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者无效。”⑨如果将公约第52条与第53条的规定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条款的第一句在措词结构上也是相同的,都是“条约……无效”(英文原文为:“A treaty is void……”)。在整个一部《条约法公约》草案里,仅有这两个条款是此种提法。不仅如此,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条款草案第49条和第50条(亦即生效后的《条约法公约》第52条和第53条——笔者)的评论中还认为,这两项条款具有追溯的效力是不成问题的。⑩关于公约草案第49条,国际法委员会还进一步表述道:对条约有效性的追溯力终止于现代法律确立之前。(11)从公约草案第49条的内容来看,这里所谓的“现代法律”显然包括有关禁止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规定。由此可见,条款草案第49条对其生效以前所缔结的条约是有追溯力的,它至少可以回溯适用到《联合国宪章》生效之时。正如国际法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制定某项规则只能从一部条约法公约缔结之日起适用,那将是不合逻辑和不可接受的。”(12)在国际法委员会看来,条款草案第49条的确立,“含蓄地承认了规定在该条款中的规则对于《联合国宪章》生效以来缔结的所有条约,无论如何都是适用的。”(13)
鉴于条款草案第49条和第50条在追溯力问题上的情况是类似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据此得出结论,即草案第50条,也就是现在的《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追溯力,可以溯及适用到该公约生效以前任何与国际强行法规则相抵触之条约。
二、对违反国际强行法的制裁
大家知道,《条约法公约》第53条和第64条都包括在公约第5编“条约之失效、终止及停止施行”这个大的范畴之内,但两者又各有不同的职能。第53条列在第5编第2节,涉及到的是“条约之失效”问题,而第64条则列在第5编第3节,与“条约之终止及停止实行”有关。公约对于强行法条款的这种排列方法表明,将根据违反国际强行法规则的不同情况,对有关条约采取不同的制裁措施。
除此之外,公约中强行法条款在措词上的差异,也反映出制裁方法的不同。第53条规定的制裁措施是使抵触性条约“无效”,而第64条的规定却是使抵触性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这是因为,某些与国际强行法规则相冲突的条约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因而在制裁方法上也就不能要求整齐划一。
前已提及,由于《条约法公约》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国际强行法作出某种规定的普通性国际文件,又是目前我们研究国际强行法的唯一国际法律依据,所以,探讨“对违反国际强行法的制裁”问题,也必须从该公约的有关规定入手。
(一)依据公约第53条的制裁
1.抵触性条约无效。《条约法公约》第53条在句首开宗明义地宣布:“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在对公约有关条文加以仔细研究后,笔者认为,公约所列举的8项致使条约无效的原因中,只有第53条的规定是既清楚而又明确地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说,公约第46条至第52条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缔约方自身的权益,而公约第53条内容的目的则侧重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第53条所确立的无效是自动的、不可挽回的,凡在订立时就与国际强行法原则或规范相冲突的条约,均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依照《条约法公约》第44条第5款的规定,“在第51条、第52条及第53条所称之情形下,条约之规定一概不许分离。”(14)换言之,如果一项条约中的某项或某几项条款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冲突,将导致整个条约因此而无效。这种严格的规定带有惩罚性质,其目的在于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类似的非法条约以及订立抵触性条约的非法行为。
2.抵触性条约无效的后果。既然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相抵触而无效,那么就应该产生相应的后果。《条约法公约》第71条在这方面作出了规定,该条第1款的内容是:“条约依第53条无效者,当事国应:(甲)尽量消除依据与任何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之规定所实施行为之后果;及(乙)使彼此关系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15)
从上述第一款的起始句和(甲)项的规定来看,其中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之任何条约以及实施该约的任何行为后果应予废除,并且这种非法条约的无效具有追溯性,它应该溯及到该约订立之时,并毫无例外地消除其所有后果,以充分恢复该约产生以前的正常情势。
但(甲)项的规定也有两点不明确之处:其一是,“尽量消除”的标准是什么?这种措词伸缩性很大,争端各方可以任意解释,将来具体适用的时候难免产生争议;其二是,根据(甲)项的规定,所要消除的是依据某项条约中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之规定而实施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在同一项条约中,依据未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之规定而实施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就不必去消除?对此,(甲)项的规定不甚明确,易生误解。这实际上又涉及到条约条款是否可以分离的问题。
如前所述,依照《条约法公约》第44条第5款的规定,在第53条所称之情形下,条约的规定是不允许分离的。那么,同样在第53条所称之情形下,依据条约规定所实施行为之后果是否可以分离?关于这一点,公约没能予以确切说明。从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这种后果可以分离恐怕难以解释得通。既然某项条约因个别条款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而致使整个条约全部无效,那么实施这项条约(不论是实施与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的、还是不相抵触的条款)所产生的后果也将是全部无效的。如果说其中某些后果是有效的,那么其效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一项无效的条约?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对公约第71条第1款(甲)项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依据公约第53条而无效的条约,对于按照其中任何性质的规定所实施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完全、彻底地予以消除。
关于公约第71条第1款(乙)项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作出如下评论:“条约因其缔结时与一项实施中的强行法规则相抵触而自始无效,是一种特殊情况的无效,由无效后果而引发的问题,与其说是缔约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对各自立场所进行的某种调整,倒不如说它们有义务使其立场与强行法规则保持一致。”(16)
由此可见,(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确保法律秩序的一致性,而这恰恰是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一项基本要求。从第71条的规定来看,它所关注的是整个国际法律秩序,而不仅仅是有关缔约方的权益。基于这个目的,(乙)项的规定为保护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从而也维护了国际强行法规范的特殊作用。应该说,严格遵守公约第71条第1款的规定,是参加非法条约的缔约方采了善后措施中的最后一个步骤。该条款是《条约法公约》所创立的条约无效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公约第5编中所有其他条款一样,其适用具有强制性,缔约各方对无效条约的处理,不得违背第71条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否则,将构成对《条约法公约》的破坏。
(二)依据公约第64条的制裁
1.抵触性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按照《条约法公约》第64条的规定,当一项新的国际强行法规范产生时,任何与之相抵触的现有条约应“成为无效而终止”。这就是说,尽管某项条约先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产生而订立,但如与后来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那么这项条约也将因此成为无效而终止。
公约第64条规定的目的与第53条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但第64条与第53条在制裁措施上是有差别的,前者是“成为无效而终止”,侧重点在“终止”,后者则强调的是非法条约的自始“无效”。
2.抵触性条约成为无效而终止的后果。依据《条约法公约》第71条第2款,在遇有条约依第6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情况下,条约之终止所产生的后果是:“(甲)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乙)不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范不相抵触者为限。”(17)这就是说,实施公约第64条规定的制裁措施有两项后果:第一,与新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之原有条约不能继续有效;第二,因实施原有条约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如与新产生之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是不能予以继续维持的。从上述规定来看,该条款无疑是维护了国际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以防止出现国际强行法规范与其他法律制度、法律情势或条约义务相互矛盾、同时存在这样一种混乱局面。
(三)对国际法主体所实施之非法行为的制裁
以上本文分别从《条约法公约》第53条和第64条的角度,分析了对违反国际强行法规范所缔结之条约予以制裁的问题,这两个条款所规定的制裁措施尽管都是针对条约而言的,但对国际法主体的各种违法行为同样适用。换言之,当一个行为在实施时,如与一项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则该行为及其后果应属无效;如遇有一项新的国际强行法规范产生时,已经实施之任何行为及其后果如与该项新规范相抵触者,即应成为无效而终止。如因实施此等行为而造成了严重后果或损害,有关当事方应承担国际责任,并向受害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且恢复原状。
如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期,英国官方曾声称,19世纪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关于香港地区的3个不平等条约“按照国际法是有效的”。英国这里所说的“国际法”指的是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传统国际法。在传统国际法上,战争被认为是推行国家政策、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是主权国家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而因战争行为所产生之后果,诸如有关条约的订立等等,也被认为是有效的。
依照现行国际法,19世纪中叶前后,英国政府为进一步推行其殖民政策而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法的,而作为这种非法行为产物的3个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以及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是英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获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不论是英国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是作为这种非法行为后果的3个不平等条约,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都与新产生的国际强行法规范相抵触,因而是非法的,应成为无效而终止。由此可见,英国官方的上述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最终确认了我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对香港地区的主权,这是对国际法上一项新的强制规范产生时,业已实施之任何行为及其后果如与该项新规范相抵触,即应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有力证明。
在当今世界上,国际法主体如果违反国际强行法而从事某些非法行为,就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而且有关的制裁措施不仅具有法律依据,同时也是完全能够予以实现的。
注释:
①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6年6月第2版,第759-760页。
②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6年6月第2版,第763页。
③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vol.1,1966,P.68.
④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
⑤ 《条约法公约》第4条的这段内容系为李浩培教授所译,考虑到该译文要比原译文更易于使人理解,故本文采用了李浩培教授的译文。见李浩培“强行法与国际法”,载于《中国国际法所刊》第55页。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1982年。
⑥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2页。
⑦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el Law Commission
⑧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el Law Commission,PP.24-25.
⑨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9页。
⑩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Vol.2,1966,PP.248-249.
(11) 转引自E.Schwelb,“Son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 as Formu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1,1967, P.971.
(12) 转引自E.Schwelb,“Son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 as Formu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1,1967, P.971.
(13) 转引自E.Schwelb,“Son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 as Formu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载于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1,1967, P.971.
(14)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58页。
(15)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
(16) 转引自Christos L.Rozakis,The Concept of Jus Cogens inthe Law of Treaties,1976 PP.134-135.
(17) 《国际法资料选编》第766页。
标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法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