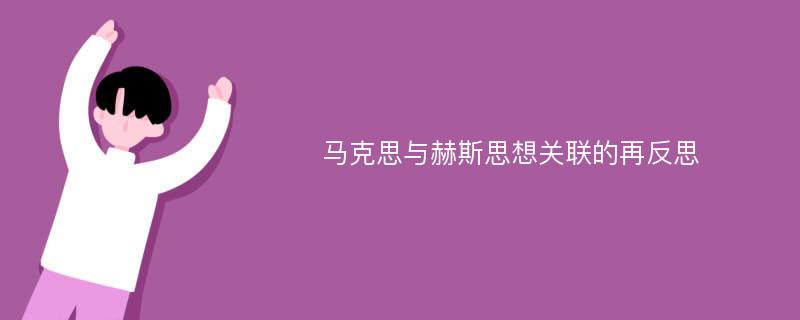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与赫斯的思想关联存在着友好合作、决裂告别、隔空对话三个时期,以往学界只讨论了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决裂告别两个时期,却完全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隔空对话期。在晚年时期,马克思和赫斯分别给予了对方的《物质动力学说》和《资本论》以崇高的礼赞。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决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次性的彻底决裂,而是经历了“友好—决裂—对话”的发展轨迹。二者早期的决裂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发生的,在决裂的同时有没有保持一致性,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不是导致二人在晚年再次相互欣赏的原因,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的讨论。事实上,赫斯曾经一度在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那里停留而忽略了辩证法的革命意义,而马克思却并没有在费尔巴哈那里过多的停留,这是导致二者在1848年发生所谓“决裂”的原因。赫斯在晚年体会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从而挣脱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束缚,与马克思殊途同归,走向了一种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这再次说明,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脱离开历史辩证法去抽象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方法论错误,这一点对于我们反思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赫斯;《资本论》;《物质动力学说》;历史辩证法
中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这桩公案,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在国外学者中,马利宁将赫斯视为批判对象和反面教材,只谈马克思对赫斯的影响,而不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1]卢卡奇对赫斯进行了指责,认为赫斯是“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2],好像赫斯的思想发展在1848年就戛然而止,1848年之后的赫斯完全在卢卡奇的视野之外;广松涉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考察,将赫斯形象高大化,认为赫斯是一位有着“压倒性影响”的大前辈,[3]似乎没有赫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畑孝一承认赫斯与马克思在德国哲学的出发点、私有财产的批判等方面有着相同之处,但二者在对待英国经济学的态度、人类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科尔纽和麦克莱伦的立场相近,均承认赫斯对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转变有着不容否定的影响;[5]等等。在国内学者中,赵仲英肯定了赫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思想交流”;[6]侯才确认是赫斯推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转向;[7]而张一兵则指出,以1844年为界标,此前的赫斯是马克思的先行者和同路人,此后的马克思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赫斯;[8]韩立新承认赫斯的成绩和贡献,但认为“回到赫斯的思想运动”有危险;[9]聂锦芳不主张对马克思和赫斯的关系进行简单化定性和划界,认为赫斯应邀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有关章节的写作,表明了《形态》写作时的马克思与赫斯有思想合作,他们之间不可能是两种异质思想的彻底决裂;[10]等等。中外学者对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然而,究竟是应该将赫斯形象夸大,承认赫斯对马克思有着压倒性的影响,还是应该指认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其思想深度远不及马克思?抑或应该采用其他的立场?拙文尝试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出发,在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分析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三个关键期,即友好合作期、决裂告别期和隔空对话期的具体情况,试图给以上的“赫斯难题”提供一种中肯的回答。
一、友好合作期: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马克思与赫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亟待“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个旧欧洲行将完结、新欧洲还未完全诞生的时代。在这个新旧更迭的时代里,同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和赫斯面临着同样的时代问题——普鲁士专制下的落后国的发展何以可能。有着同样的实践场域,这是他们前期合作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与赫斯真正友好的合作从二人同时为《莱茵报》撰稿开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比《哈雷年鉴》更加激进的《莱茵报》,是马克思与赫斯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马克思与赫斯最初的真正接触便借助了这个平台。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与赫斯有了真正的交往。《莱茵报》创建后,在物色优秀撰稿人时,赫斯结识了当时住在波恩的马克思。赫斯在给其好友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信中,称赞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11]。从赫斯和友人的这封信中可以得知,赫斯和马克思刚刚开始接触时,就被马克思的哲学修养及思想倾向所打动,将马克思视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赫斯坦言,马克思给自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因为马克思高深的哲学造诣,自己会成为马克思“最勤奋的听众”。相比之下,赫斯认为自己只是哲学中的“门外汉”。赫斯对马克思表示出了极大的尊敬和钦佩,将马克思称作自己的朋友和哲学教师。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赫斯会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2]这表明,当时的马克思对赫斯的一些论文是非常认可的,认为这些论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独创性。马克思在写作时不仅参照了魏特林和恩格斯的著作,也参照了赫斯发表在《二十一印张》上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几篇论文。事实上,正如张一兵先生所言:“与青年马克思并步前行的两位重要人物,即赫斯与青年恩格斯。他们是在和青年马克思一同进入一般唯物主义基本构架之后,对他产生更加重要的理论影响的关键性人物。”[13]这一时期的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深度不容忽视,赫斯和青年恩格斯均对马克思有着关键影响。
P.G.Rousseau[8]等调查研究了广泛应用于南非地区的商用热泵热水器,并对提高系统性能和运行经济性进行了分析。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可的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却很少去探讨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先进分子那里接受了什么,受到了何种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并非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简单相加或随意拼接,而是多种思想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这种影响从马克思本人提到的赫斯1843年发表在《二十一印张》上的三篇论文,以及赫斯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这一理论文本中可窥见一二。赫斯于1843年发表的《行动的哲学》是触动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该篇论文使得赫斯成为“第一个在行动哲学中把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人”[14]。赫斯谈到“自由行动”与“奴役劳动”的差别时,指出“自由行动区别于奴役劳动的地方,因为在奴役中,生产束缚生产者本身,而在自由中,精神在其中异化的任何限制都不会变成自然的约束(Naturbestimmtheit),而是得到克服而成为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15]。赫斯所强调的自由行动体现的是人的真正的类本质,这种行动并不是外力压迫或驱使的,而是自由的、内心驱使的自我决定,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谈到的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劳动。从时序上看,赫斯的自由行动的类本质是马克思自由劳动的类本质的逻辑前身。
赫斯发表在《二十一印张》上的匿名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当时的马克思也产生了影响。在该篇论文中,赫斯对造成奴役的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私有制作了批判,对傅立叶的“劳动组织奠定在一切个性最全面自由的运动这个基础上”[16]的思想格外赞同,而这也是后来的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源起处。[17]另外,赫斯文中的破除利己主义私有制、打破奴役牢笼等方面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也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时的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的原生地。赫斯在《二十一印张》上匿名发表的《唯一而完全的自由》,对当时的马克思同样产生了影响。在此文中,当赫斯谈及精神奴役时,指认“宗教,如鸦片伴随着痛苦……奴役地忍受不幸的意识”[18],这一指认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指认不谋而合,反映出马克思与赫斯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共鸣。当我们了解到赫斯在此文中的这些观点之后,才发现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说得如此流畅和娴熟,原来是有赫斯的相关观点在做支撑,马克思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赫斯完成于1844年初的著名论文《论货币的本质》中的经济异化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后的研究视角转向,即从哲学转向经济领域的异化问题。[19]在《论货币的本质》的开篇,赫斯引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麦布女王》,以指认货币是“发光的矿石”,货币周围“聚集着庸俗的大人物、虚荣的富豪、落魄的显贵,以及农民、贵族、教士和王侯等乌合之众”,货币使得“一切都可出售”,“连天上的光明也能用钱来买”, 等等。[20]无独有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片断部分的货币篇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雅典的泰门》,以指认货币是“该死的土块”,货币周围聚集着老人、祭司、仆人、壮汉、奴隶、病人、窃贼、元老们、寡妇等各色人,有了货币,即便是“三春的娇艳”也能得到恢复等。[21]虽然赫斯借用的是雪莱的诗,马克思借用的是莎士比亚的诗,但这种批判逻辑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赫斯与马克思均窥探了货币左右一切,颠倒是非、黑白的“神力”,进而去把握货币的本质,即“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22]。
此外,“交往(Verkehr)”一词成为《论货币的本质》这一文本中的高频词。赫斯在文中指出:“人彼此交换其社会的生命活动的领域——即社会中的交往(Verkehr)——是不可让渡的社会的生命要素。单个人在这里作为有意识的和有意识地行动的个体同其社会生活的交换的领域的关系,正像他们作为无意识的个体,作为身体同其身体的生命活动的交换的领域,同地球的大气的关系一样。……单个的人同整个社会身体的关系,正像单个的肢体和器官同单个的个体的身体的关系一样。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身体的联系。”[23]赫斯在这里提到的社会中的交往、个体、社会身体、现实生活、生产性的生命活动、共同活动、生产与交换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的客观关联,这种关联也正是马克思后来在思考社会生活的本质、思考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时所使用的重要概念。总的来看,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思想影响下,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形成了经济异化观,进而实现了对赫斯异化理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即“马克思再从基于经济学思考中的劳动对象化走向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生产,从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超越了他的前行者——赫斯”[24]。尽管赫斯在有关经济异化、自由共同体等方面的确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但是,拙文认为,不可过分夸大这种影响,而要看到马克思本人特殊的思想构境和话语结构。同时,随着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世界观、新历史观的创立,赫斯的影子便逐渐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的批判和超越。
通过这一时期的一些书信和材料,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与赫斯的确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且二人在思想倾向上没有发生异质性的分歧,这就为1845年秋他们在《形态》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赫斯是1845年9月初到达布鲁塞尔的……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个性对赫斯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因此,赫斯打算同他们进行理论和政论方面的合作,必然被视为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重要原因。”[25]但是,通过《形态》的写作,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以及对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超越,而赫斯仍旧停留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层面。尽管赫斯参与了《形态》部分章节的写作(批判卢格、批判库尔曼),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形态》的写作中,赫斯扮演了双重身份——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事实上,赫斯在《形态》中的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充分表明了此时的赫斯与马克思之间确实有着一种思想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二者之间已经有了潜在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昭示着他们将会走向决裂。
二、决裂告别期:隐藏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从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自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极重要意义。
马克思与赫斯的决裂,实质上也是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歧开始的。马克思与赫斯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方面的差异,具体而言,这种差异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以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为首的一批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称号来讽刺他们。”[26]赫斯和马克思的第一次公开化的分歧,是184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由于赫斯不满马克思在大会上对魏特林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委员会后来对魏特林的处理,而选择以“再见吧,党”字样的信向马克思表达了气愤。尽管在信中赫斯表示此后愿意和马克思保持惬意、频繁的个人交往,但事实是,此后的他和马克思逐渐疏远了。“1847年起,马克思在《驳K.格律恩》,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等文章中继续对‘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予猛烈的抨击,也从侧面表现了他们与赫斯哲学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分歧。”[27] 1847年,在巴黎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讨论会上,赫斯发表了被恩格斯称为“绝妙的教义回答修正稿”的言论。赫斯在会上的这些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反,同时,赫斯《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一文的发表,迫使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请求马克思通过批判立即制止赫斯的“流言”,这使得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分歧不仅进一步扩大,且更加尖锐化。
其实,以上的分歧早在《形态》的写作过程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形态》的写作,使得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这为马克思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形态》中初步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发表了唯物史观,当时盛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为马克思的分析批判提供了现实材料。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武器分析这些思潮,逐步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存在的缺陷,即满足于通过文学词句宣扬抽象的普遍的荒谬的“爱”的呓语,恰恰忽视了现实的阶级斗争,以小资产者为自己的公众,却唯独忘记了真正的公众——无产阶级。为了维护理论的纯洁,防止损害共产主义的声誉以及在工人中间造成的思想混乱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批判。后来,在恩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
《物质动力学说》出版后,赫斯妻子主动将这本著作寄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收到著作后,给赫斯妻子西比拉·赫斯回复了两封信。在写于1877年10月25日的第一封信中,马克思对西比拉·赫斯给他和恩格斯寄来两本《物质动力学说》表达了感谢,并评价道:“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亡友的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并且为我们党增添了光荣。因此,不管我们和多年盟友的私人关系怎样,我们都将把阐明他的这部著作的意义和尽力协助它的传播看作自己的职责。”[36]在写于同年11月29日的第二封信中,马克思说:“这本书里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很遗憾,大概因为赫斯未能做最后加工,其中有不少论点将成为自然科学家严厉批判的材料。”[37]从马克思回复的两封信中可以得知,在马克思看来,赫斯晚年的遗作《物质动力学说》虽有待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有独到见解。尽管马克思对这本著作的评价含有礼貌、客气的成分,但赫斯毕竟是一位很有天赋和能力的哲学家,他的这本自然哲学著作无疑值得了解、重视和深入研究。如果能够将其与马克思的自然观特别是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趣味和意义,更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
如果以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而影射到对赫斯的批判还较为含蓄和委婉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批判就更为辛辣、系统和坚决:“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28]无疑,这里直接表达了对赫斯的批判。赫斯曾在1843年发表了《行动的哲学》,尽管该文曾在有关“金钱和私有制的本质、异化的普遍性”等方面给马克思某些启示,但因其有着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而遭到马克思的批判。[29]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德国的著作家们因为不懂得德国的现实条件,他们所做的工作仍旧是纯粹文献形式的无谓思辨,因而无法看到隐藏在法国生活条件背后的潜在革命因素,更无法让这种革命火种在德国变为现实。当然,革命的实现也是有条件的,这更是德国著作家们无法洞察的方面。
注释:
三、隔空对话期:不该被忽略的方面
学界对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考察大概止于1848年,在今天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赫斯的著作,既要关注与马克思思想形成密切相关的部分,也要关注与马克思思想形成关联不大但被马克思阅览和评论过的著作,如此,对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理解才不至于是片面的。这种隔空对话可以从赫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高度评价、赫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做出贡献的高度肯定、晚年赫斯与晚年恩格斯不约而同地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赫斯妻子主动将赫斯遗著《物质动力学说》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方面谈起。
1867年9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赫斯评价该著作“体现了国民经济学的革命”,认为该著作是“一部重要的、革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但首先是深刻哲学性的著作”[32]。赫斯不仅热情地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向参会代表推荐《资本论》,而且打算将《资本论》法文本的翻译承担起来。赫斯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时指出:“达尔文对于自然经济学发现的东西,马克思在社会经济学方面也发现了。揭示自然和历史中的发展规律并把这一规律追溯到生存斗争,是这两位研究者的伟大功绩。借此,人类的大脑被从溺爱人类心愿和错误判断的铁的必然性规律的宗教和社会空想中解放出来了。”[33]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赫斯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也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许,受《资本论》的启发和影响,赫斯会对自己以往的带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审视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这定会影响赫斯晚年的研究路向。1873年夏,赫斯完成了自己的《物质动力学说》第一卷,而这一年也正是恩格斯开始其自然哲学研究的时间。
作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晚年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在1873年至1882年间,恩格斯写作了《自然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是第一次——探讨了哲学和自然研究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肯定了这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恩格斯认为,为了使工人阶级在世界观上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最要紧的是必须强调进化论和哲学辩证法的一致性”[34]。20世纪自然研究的发展逐渐证明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出的一些论断的正确性,如:量子理论领域的发现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物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观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物质、运动以及时空的正确论述等。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通过对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认识方法。恩格斯在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是有目共睹的。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赫斯晚年也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且赫斯比恩格斯更早开始了自然哲学著作的写作,“宇宙、社会和有机体的规律性的统一重新成为他的研究课题。与达尔文根据有机体为发展学说提供了科学证明相类似,赫斯想根据宇宙和社会为发展学说提供同样的证据”[35]。尽管赫斯与马克思在1848年之后逐渐疏远了,但赫斯并未放弃他的理论研究。在晚年的研究中,他一直努力探寻着社会发展的秘密,而且无意中走了和晚年恩格斯同样的理论研究之路。赫斯晚年的自然哲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物质动力学说》这本著作中,这本著作在赫斯逝世后出版。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精力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严肃的批判,其中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这种批判来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境内已经分裂为许多支派,这些支派肆意发展起来,业已蔚然成风,虽然各派有其独特的个性,但在宣扬抽象的普遍的爱、充满幻想色彩、麻痹德国市民、弱化阶级斗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危害,这些支派主要有最早的威斯特伐里亚社会主义派,扮演“牧夫”角色的泽米希为主要代表的萨克森派,以卡尔·穆尔为主要代表的波希米亚森林派,以及以恩斯特·德朗克为主要代表的柏林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受德国意识形态的羁绊,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揭示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真理也不过是德国意识形态的阐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对现实进行了批判,但其批判仅停留于纯粹的思辨,他们仍旧迷恋“思维着的精神”,仍旧根据纯粹的文献或思辨虚构出了幻想的联系,却让人相信这是一种“科学”。“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现实运动完全割裂,却与德国的哲学任意联系,对法国和英国的现实进行纯粹文献形式甚至是错误的了解,使得社会主义在德国成为了纯粹的社会文学运动,如格律恩先生的美文学。于是,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那里只是作了观念的反映,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中成了变形的理论,沦为了“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看不到现实的基础和现实的关系,看不到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看不到实在的“人”是个人间的关系(只看到抽象的大写的“人”),更无法通过现实的历史基础看到现实运动间的联系。“真正的社会主义”竭力宣扬抽象的普遍的“爱”,实则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丧失的是革命热情,抹杀的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势必使它越来越脱离无产者,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反而代表了僧侣、教员、容克地主等小资产者的利益。
[8]张一兵:《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转引自邓习议编译:《赫斯精粹》,第4-21页。
在此,拙文也呼吁国内熟知德语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和早年马克思有过合作,以及晚年受马克思影响的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赫斯,其著作不应被搁置一边,而应予以必要重视。这不仅可以弥补国内有关这方面文献翻译、引介和研究的不足,更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革。此外,为何马克思没有针对赫斯本人进行具体的批判,相反,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均遭到了马克思的具体批判?或许有人会说因为赫斯的思想分量不够,但拙文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赫斯作为德国的社会主义之父,作为“党的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语),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他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变化中的确在场,并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个性、思想对赫斯一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晚年的赫斯究竟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是否主动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靠拢呢?晚年的赫斯是在怎样的机缘下走向了历史辩证法,重新拥抱在自己青年时期急急忙忙抛弃的黑格尔的呢?或许,对《物质动力学说》的深入研究能解答这些问题。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动态性、开放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它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充分发挥,引导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调研、分析、讨论、辩论、探究和归纳总结等,对所学习过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延伸和拓展,不仅有助于开阔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动手能力,系统地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并将它灵活地应用在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上,而且促进教师不断继续学习理论知识和提高生产实践能力,将教学、理论学习、实践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及时补充和完善自身的不足和短板,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以便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性纺织技术专门人才[1-2]。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中存在着友好合作、决裂告别、隔空对话三个时期。对这三个时期的考察,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后转变,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有助于厘定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域(社会主义部分)。在友好合作期,既有马克思对赫斯的关注,又有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在决裂告别期,因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的显著差异,马克思对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作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看到了赫斯在思想上对费尔巴哈的停留;在隔空对话期,晚年的赫斯受马克思《资本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再次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主动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靠拢的倾向。尤其是其自然哲学遗作《物质动力学说》,力图通过论证宇宙、自然、有机体三者的统一,来寻得社会发展的秘密。由此可见,隔空对话期是研究中不该被忽略的方面。因此,对于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界定,应围绕他们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决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次性”的彻底决裂,而是经历了“非异质性—异质性—异质性和非异质性的交织综合”的发展过程,其中显现着“友好—决裂—对话”的发展轨迹。
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联的再反思,其中的启示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莱茵报》时期到《形态》的写作这一时期来看,马克思和赫斯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马克思与赫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赫斯对马克思研究视角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夸大赫斯的这种影响,“回到赫斯”的思想运动确实是危险的,同时也不能将赫斯淡化为背景,其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不应被遮蔽,而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是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提醒人们,需正确看待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间的关系。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离开了德国哲学的思辨头脑,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科学产物,着眼的是物质生产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热衷于纯粹的思辨,过分拔高了哲学的功能,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则需处理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是对于赫斯晚年遗作《物质动力学说》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晚年赫斯是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者们不应回避的重要方面。四是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并非“一次转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早期、中期、晚期马克思的划分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属于同一个马克思,这也有利于避免长久以来对“马克思”的误读或对其学说的“神话”式理解。五是既然马克思和赫斯的思想都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要厘清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关系,必要的前提是厘清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对这两位大师的原著进行精心细致的研读。
溶蚀作用和红土化作用二者相互促进,紧密集合,并且二者的作用过程与母岩成分、CO2含量、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有关。
此外,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德法年鉴》时期,这种转变已然完成。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30]。反观赫斯,其理论和学说最初虽带有模糊、神秘色彩,但后来竟衍变成枯燥、危险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赫斯虽然偶尔也会使用一些黑格尔的术语,但就其基本倾向来看,赫斯的思想基本上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哲学之中,几乎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神,无法对现实的德国社会形成真正的批判和超越,沦为了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专制统治的帮凶。“到了1848年2月,由于赫斯自身的内在思想逻辑中隐匿的人本学意识形态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内在逻辑发生冲突,这才导致了他最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分道扬镳。”[31]也就是说,随着《共产党宣言》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系统批判的完成,以及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发表,不仅折射出了马克思与赫斯在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的截然不同和必然决裂,同时公开宣告了马克思、恩格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包括赫斯)的彻底分道扬镳。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是否给赫斯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让其认识到自身理论的局限,甚或帮助其进步,使其回到正确的理论轨道?这些尚需日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住宅绿化率对房价也产生明显的提升效应,平均绿化率每上涨1%,房价上涨3275元/m2。从图3(h)可以看出:甘井子区的旅顺北路到滨海公路区域房价影响较大。
[1]马利宁等著:《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曾盛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85-186页。
[2][4]畑孝一:《赫斯与马克思》,转引自邓习议编译:《赫斯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7、275-293页。
[3]广松涉:《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转引自邓习议编译:《赫斯精粹》,第203-204页。
[5]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转引自炎冰:《金钱异化及其罪源——赫斯〈论货币的本质〉之文本解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0页。
[6]赵仲英:《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
本系统集多生命体征采集传感技术、无线传感技术、MCU、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远程Web 监护平台开发、包括生理数据的采集与传输、服务器搭建、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建模与数据分析可视化的效果展示等组成,其中系统组成图如图4 所示。
[7]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
可惜的是,国内有关赫斯本人的论文或著作的翻译出版严重滞后,目前仅翻译出版了一本赫斯的论文集,即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赫斯精粹》(收录了赫斯1837—1845年间的18篇论文)。原本《物质动力学说》应是拙文重点关注的文献,然而,目前国内尚无此著作的中译本,就算英文本或德文本都无法寻得,或许只能前往德国的大学图书馆获得影印本。但是,这并不妨碍拙文在此讨论它,而且提到这本珍贵文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可以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物质动力学说》评论的了解,我们发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物质动力学说》中,赫斯自觉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力图从总体上去揭示自然中所包含的辩证结构,这与恩格斯的做法类似。不仅如此,赫斯似乎是把自然中的辩证的总体结构看作是社会和历史领域的辩证结构的基础,至少是一种印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年赫斯经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之路,这再次说明,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脱离开历史辩证法去抽象地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将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修正”和当代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实证化”处理之中,我们应该对这些思潮保持高度警惕。
[9]韩立新:《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研究史回顾》,《哲学动态》2011年第3期。
[10]聂锦芳:《〈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目前,中国音乐产业虽已经历百年历史,发展过程艰辛且曲折,且处于“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阶段。然而,相对其他领域而言,缺乏全面、系统,且稳定的管理制度。
一直以来,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从哲学内部出发进行研究的趋势,但从1999年张一兵先生出版《回到马克思》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学话语中的哲学思想,这几乎成为二十年来中国马克思哲学不断往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之一。然而,总体来看,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仍然缺少了社会主义的部分,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的方面。事实上,对社会主义语境的凸显不仅能够呈现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理论向度,更有助于厘定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
[11]史清竹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关书信及其研究II》,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02-303页。
爱,是我们教师心中永恒的主题,师爱无异于母爱,爱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语言,教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把全部心灵和才智献给孩子的爱,这种爱是深沉的,它蕴涵在我们为学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使学生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这种爱的真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关注,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学生们就能感受到老师的爱,学习才会有动力,才会在生活中,在学习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地前进。
[12][2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243、245-246页。
[13][17][3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117、111页。
在拙文看来,中国学界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原著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过于借助于后人的评价来定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现在需要转变的是应当直面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文本,在忠实地理解他们文本的基础上,再反过来理解马克思、赫斯、恩格斯等人对他们的评价,从而更为客观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之间的理论关系。经过笔者的清理,我们发现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思想关联真的比我们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些重要的文献我们直到目前都没有办法看到,以往对“赫斯难题”所下的结论可能都有待进一步商榷,或者为时尚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要想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无论是赫斯还是马克思,都是我们还没有穷尽的理论富矿,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全面地解读,这可能是所有重要的思想家的共同魅力所在。
[14]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转引自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114页。
据说人类迟早要被人工智能控制,而电子产品是人工智能派来的先遣小分队。在我看来,如果非得拧巴着不做“低头族”,和这支小分队誓死对抗,不但反人性,还反智性,显然是没有胜算的,不如缴枪算了。
[15][16][18][20][23]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第96、113、129、134-135、138页。
共建,让建设“绿色西江”的力度不断加大。海事部门大力推进西江流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和船舶船型标准化工作。西江沿线各市已经设立21个船舶溢油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初步覆盖沿线水域,大大增强了船舶溢油处置能力;佛山市引导西江9家危险品码头,建立溢油应急联防体和相应工作机制,提升企业联防联控水平。
[19]宋婷婷、刘奕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赫斯因素》,《学术交流》2018年第6期。
[24]张一兵:《赫斯与青年马克思:金钱异化本质的异质基础》,《学海》2012年第3期。
[25]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26][34]海因里希·格姆科夫:《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98、396-397页。
[29][32][33][35]杨金海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与事业研究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7、44、44-45、45页。
木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偶分为杖头木偶和卡通木偶。演员们分别为我们表演了杖头木偶戏《手绢佛珠》和卡通木偶戏《疯狂吉他手》,并进行了互动,若提问的问题回答正确,就可以上台体验卡通木偶,八位学生与四位老师分别进行了互动。后来,那里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走进他们的工作室,向我们展示了木偶造型的制作过程。我真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高超的表演技艺使本无生命的木偶表现得富有生机活力。最后,我们体验了动手彩绘脸谱,感受到了艺术的乐趣。
[27]陈东英:《赫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那时,我们一到暑期就会跟随大人乘坐轿子上庐山,上山后买个大草帽,拿根拐棍四处游玩。小时候,长冲河里的水是可以直接挑回家吃的,那时有一个职业叫挑水工。我们小孩子经常去河里捞鱼摸虾捉小螃蟹,有趣得很。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5页。
[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4、290页。
Rethinking the Ide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Marx and Hess
HUANG Qi-hong, LU Li-juan
(Marxist Theoretical Research Center & Institute of Western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Hess went through three periods: friendly cooperation, breakup and the “trans-time-and-space” dialogue.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ircles only discussed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break-up between Marx and Hess, but completely ignore the “trans-time-and-space” dialogue period. In their later years, Marx and Hess sang high praise of each other’s works - The Theory of Material Dynamics and Capital. This shows that the “breakup” between them was not a one-time complete breakup in the simple sense, but a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friendship-breakup-dialogue”. In what sense did the early breakup of the two happen?Whether there was a consistency in the breakup? In what sense did the consistency show up? Did this consistency make the two appreciate each other again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few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se issues. In fact, Hess once lingered in Feuerbach’s species-philosophy and ignored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dialectics, but Marx did not delve deeply in Feuerbach, leading to the breakup between the two in 1848. In his later years, Hess came to recognize the revolutionary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dialectics, thus breaking free of Feuerbach’s ideological bondage and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Marx to embark on a path similar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again shows that historical dialectics is the key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a serious methodological error to abstractly discus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le being detached from historical dialectics. This has an important warning effect on our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Keywords: Marx, Hess, Capital, The Theory of Material Dynamics, Historical Dialectics
收稿日期:2019-07-23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2014YBZX009);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马克思低阶正义理论研究”(2016YBZX012);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定位及世界意义研究”(SWU1809010);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正义观研究”(SWU1909313)
作者简介:黄其洪,男,四川隆昌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卢丽娟,女,甘肃陇南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9)05-0032-09
[责任编辑:蔡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