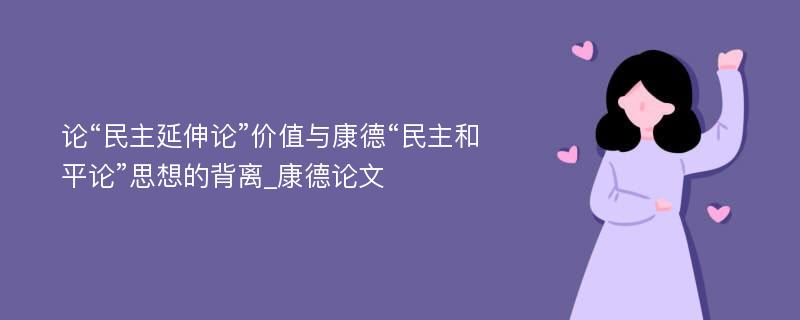
论“民主扩展论”对康德“民主和平论”思想的价值背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民主论文,和平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美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界有两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正受到众多理论家的推崇:一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二是所谓的“民主扩展论”。这两种理论看似互不相干,但却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因为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理论指向.那就是为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奠定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共同构筑支撑所谓“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理论基石。
对于中国的学者们而言,仅仅认识到美国新霸权主义对未来世界和平构成的潜在危害是不够的,从学理上回应其“道义合法性”的挑战应当是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的使命。可喜的是,已有许多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对“霸权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的理论剖析方面,王义桅、唐小松近来发表的《从霸权稳定论到单极稳定论》一文可以说是金石之作。 (注:王义桅、唐小松:《从霸权稳定论到单极稳定论——冷战后新现实主义的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在对“民主扩展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观点的回应方面,国内的学者们也颇有建树:从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阐述,到各个主权国家维护其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保障其国民基本人权的最重要的国家行为取向的学理论证,都极大地丰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应和反击新霸权主义的理论宝库。
然而,国内学术界对“民主扩展论”的论争仍有一个理论瓶颈有待突破。中国的学者们应当看到,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在美国学界和政界积聚非常可观的能量,并对公众舆论带来极大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理论的倡言者在价值判断上利用了人们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理念所抱有的政治图腾式的膜拜心理,并利用这种心理来误导他们,使他们对所谓“民主国家的霸权”产生道义上的认同感。如果我们不能从学理角度来揭示新霸权主义(即国际政治中新的强权政治)与民主和自由价值两者之间在价值本源上的内在冲突以及这种内在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澄清“民主扩展论”在价值内涵方面自我抵牾的本质属性,我们就难以真正摧毁当代新霸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民主扩展论”与“民主和平论”在价值内涵上的差异
“民主扩展论”(DemocraticExpansion)(注:塞缪尔·亨廷顿是最早提出“民主扩展论”系统理论的理论家,尽管他在1981年提出这一理论时使用的仅仅是它的概念,而不是它的称谓。cf.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1981,pp.256,257;Samuel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 Press,1991,pp.29~30.)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家趋之若鹜的理论之一。由于推崇和服膺这种理论的理论家人数众多,使它在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演绎出了多种不同的称谓,而且不同的理论家对这一理论所下的定义、所作的阐述也大相径庭。就其称谓而言,它还有“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Peace)(注:当代“民主和平论”的称谓是由卡尔·多伊奇、迈克尔·多伊尔、布鲁斯·拉西特和约翰·欧文等人提出的。Cf.Karl W.Deutsch 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Michael W.Doyle,"Liberation and World Politics",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80,1986;Bruce Russett,Controlling the Sword: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Principles fora Post-Cold War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M.Owen,"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Fall1994.)和“民主霸权论”(Democratic Hegemony,or Pax Democratica)(注:MarcF.Plattner,"Democratic Moment",in Larry Diamondand Marc Plattner,ed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2 ndedition,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42.)以及“自由化大战略”(Liberal Grand Strategy)(注:Cf.G.John Ikenberry,"Why Exporting Democracy?",Wilson Quarterly,Spring1999,Vol.23,Issue2,pp.57~58.)等等;而就其定义和理论表述而言,由于推崇它的当代理论家们各自见解的差异,致使与它有关的定义和表述并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从当前这些理论家的阐述来看,“民主扩展论”的称谓比其他几种称谓的表述更为准确和贴切,因为它包含了“主动”之意,更切合他们以扩展“民主”、输出“自由”和维护“人权”为由来推行霸权的本意。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前推崇“民主扩展论”的理论家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套用“民主和平论”的称谓来阐释其立论观点。这在学理上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并导致这样一种现象的产生:尽管“民主扩展论”似乎以“民主和平论”为其立论依据或前提,但事实上人们从真正的“民主和平论”所包含的价值内涵中却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民主扩展论”的立意和主张,除非立论者有意识地在推导过程中注入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同时,尽管这两种理论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相同的理论出发点,但其内在涵义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民主扩展论”包含了主张以武力来扩展“民主”和输出“自由”的价值取向(即所谓“民主国家干涉别国内政有理”),而真正的“民主和平论”思想却并未涵盖这种主观倾向性。因此真正能为美国新霸权主义提供“道义合法性”的是所谓“民主扩展论”,而非“民主和平论”。在这一点上,凸显了它们之间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上的鸿沟。
从理论渊源上来追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论”思想最早是由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提出来的。这些思想家认为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因为包括中等阶级和平民在内的民众有热爱和平的自然天性,由他们的意志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才能保障国际和平。在欧洲专制王朝之间常常进行的秘密外交、结盟攻略、王权争夺、领土取让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均势谋略等都被认为是导致国与国之间战争频繁发生的根源。这种思想是“民主和平论”的最早表述。(注:Felix Gilbert,To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Jersey:Princeton,1961,pp.59~66.)在西方近代史上“民主和平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他在写于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详尽阐述了他的“民主和平”思想。今天,无论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论”的赞同者,还是“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实际上都对他们“共同”拥有的这一理论渊源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从中找到了“精神”力量。(注:对于“民主和平论”的这一理论渊源的分析,参见Michael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and Public Affairs,Vol.12,Summer1983.)然而,这一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似乎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出发点,但当代并非所有崇尚“民主和平论”的人都同时认同“民主扩展论”的主张。这是因为,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在这两种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别。这一差别表现在:赞同“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家们所犯的失误,仅仅是他们过分地相信了“民主机制”对于约束依据它而建立起来的政府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的恣意妄为所能起到的作用。譬如,查尔斯·凯格利等人就认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会促使它们的领导人使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冲突,按部就班的程序限制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注:Cf.CharlesW.KegleyandJr.Gregory Raymond,A Multipolar Peace?: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St.Martin'sPress,1994,p.63.)而卡尔·多伊奇则将“民主体制”所能起到的这种作用阐述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和平的;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这些冲突能通过协商、妥协和安抚而不是通过威胁、阻碍和暴力获得解决。在民主国家之间威胁使用暴力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在不求助威胁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关系能够例行解决。(注:Cf.KarlW.Deutschet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Princet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76.)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们所铸成的谬误则是他们在自己的主观倾向性的驱使之下,将“民主和平论”的要义推演成了:(1)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才能掌握民主自由的“真理”;(2)既然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掌握这种“真理”,因此用武力来扩展这种“真理”不仅成了他们的“权利”,甚至还成了他们神圣不可推卸的“使命”。尽管产生这种使命感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早期,但它真正演变成“民主扩展论”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始作俑者塞缪尔·亨廷顿宣言不讳地宣称:“自由在美国的健康发展与自由在其他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自由在世界的未来与美国力量的未来[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注: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Mass.:The Bel knap Press,1981,pp.256~257.)而另一位名叫劳伦斯·怀特黑德的理论家则更是振振有词地声称:“历史表明民主常常是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来建立的。在美国外交史上这一点尤其颠扑不破:它常常卷入通过武力来促进民主的努力。”(注:Laurence Whitehead,"The Imposition of Democracy",in Abraham F.Lowenthal,ed.,Exporting Democracy: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 in America,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356.)倡言“民主扩展论”的理论家们正是通过对“民主和平论”的这种不恰当的引申来使其最终完全背离“民主和平论”的原始定义和内涵的。
奇怪的是,那些对“民主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性”坚信不疑的人通常会对“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方面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完全视而不见。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民主国家”这种两面性的存在,因此更不知道产生这种两面性的根源和实际后果。那就是:那些在国内奉行了某种“民主制度”的国家,同样会由于其国家利益的排他性而在其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方面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他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对立物。由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其民主只是相对于其国内公民而言才有某些实质上的意义)在国家利益的排他性方面与其他任何类型国家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它们在对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犯下种种暴行时几乎从来就不会表现出与“专制国家”和“独裁国家”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像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沃尔特·墨菲(Walter Murphy)这样的学者虽然难能可贵地对“民主国家”过去犯下的种种暴行提出了有节制的批评,(注:有关这两位学者对西方“民主国家”过去犯下的暴行的抨击,可参阅:罗伯特·达尔:《论民主》(On Democracy),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沃尔特·墨菲:《普通法、大陆法与宪政民主》,信春鹰译,裁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但他们最终也只能对涉及这些历史事实的理论问题采取刻意回避的态度,而不去分析造成这些事实的客观背景因素和体制上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进行与此相关的理论分析似乎是给民主制度“抹黑”。这在客观上使得他们不敢真正地去正视那些早期在国内建立起“民主体制”的西方国家过去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因为如果翻开这一部长达几百年的编年史会使得西方“民主国家”过去曾经犯下的种种罪行暴露无疑。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完全漠视或回避对这段历史的感性认识和理论分析,是导致当前“民主扩展论”在美国和西方甚嚣尘上的直接原因。这一点同时也能标注“民主扩展论”的理论基础产生致命谬误的根源——因为其倡言者是试图在一个正义原则阙如的理论平台上构建一个虚拟的“正义”原则。而有了这样一个虚拟的“正义”原则,他们就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对其他国家人民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实施新的暴行。
二“民主扩展论”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价值背离
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平论”者是可以将其理论和思想渊源追溯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之中的。因为这两种理论在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确非常相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今天“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大多也同样将康德“永久和平论”看做是自己的理论渊源,这实际上是对康德思想的严重歪曲。笔者认为,从价值内涵上廓清两者之间存在的质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客观地说来,“民主扩展论”的倡言者们所犯的一个根本性谬误,在于他们在以下这样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上扭曲了康德思想的本意。
在实现“永久和平”的“第一项正式条款”中,康德虽然预设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的门槛(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5页。)(这一点大概是“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们从康德理论中惟一能够有所依凭的),然而,令当今“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们失望的是,康德在这里实际上仅仅表明了他本人对“共和体制”的青睐。在这一点上,康德与其同时代的学者们一样都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学理论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影响。这些古代的学者们大多对“共和政体”备加推崇而对“平民政体”或“民主政体”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民主”一词所包含的概念笼统地界定为“直接民主”所专有。由于古代普遍盛行的“直接民主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使得学者们偏爱“共和”、讳言“民主”的风气一直流行到近代后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定义上的差别,我们才不会对康德之所以认定“民主政体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就必然是一种专制主义”(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08页。)感到奇怪。康德所推崇的“共和体制”与人们现今所理解的“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联系更为密切,而与当前西方片面设定的“民主标准”并无十分密切的关联。因为当前西方的“民主标准”是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反过来追加了诸多“直接民主”因素的标准,而且其中还混杂了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判断。厘清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相对于康德对“永久和平”所预期的载体(共和政体)而言,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不仅仅限于当前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实际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有资格入围“永久和平”体系的国家了。尽管那些试图从康德思想中发掘出“以武力扩展民主有理”的逻辑的理论家们出于为其霸权主义寻找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的目的而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一事实本身都不会有所改变。
与当今“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们的主观立场有着根本不同的一点是,人们从康德这篇传世之作的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以武力扩展民主有理”的逻辑存在,而且也根本感觉不到他抱有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意味。即是说,他的“永久和平论”思想并未为所谓“民主国家”以武力和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提供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依据,恰恰相反,他为实现“永久和平”所预设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国家实施这样的干涉行为无疑都会对“不依附于任何别人的民族的权利”构成“侵犯”,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01页。)康德设定的这一先决条件可以说早已有预见力地否定了当今甚嚣尘上的“民主扩展论”的理论基础。
那些主张推行新霸权主义的理论家们之所以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康德的思想和理论产生误读和误判,并非是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限,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来说,还在于他们在试图奠定“民主扩展论”的动机中注入了太多的利己因素的考量(推行霸权主义的企图从本质上说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利己心理的彰显和宣泄)。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真正的圣人,狭隘的利己心会使得任何人(或任何民族)都变得短视和偏激。这种情形到了那些不可一世、自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掌握真理的人(或民族)那里还会变得更糟: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之间真地误以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既能满足他们的民族自私心理、又符合普遍正义原则的“真理”。他们的“上帝”赋予他们的崇高使命就是去发现并捍卫这种“真理”。这种充满诱惑力的确定感(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觉)会使这种人(或民族)变得不明事理;而且只要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为依托,这种人(或民族)还会由于他们的信念而变得不可理喻,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宗教狂热都与卷入其中的民族(或国家)的某种使命感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构成当今国际政治相对合理的核心成分的,是具备国际民主体制雏形的联合国机制。尽管在目前看来,该体制仍然极其脆弱且极不完善,而且该体制本身还包含了某些有欠公正的因素,但这一体制的创立本身就是人类在国际政治领域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无可否认的是,这一体制对于维系二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作出了它的重要贡献的。然而,这一体制在康德所处的历史时代根本不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为什么康德认定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注:康德对这种状态的表述是“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因此他才感到有必要使“和平状态”“被建立起来”。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04页。)正是这种无序的“战争状态”使得当时的所有国家在遭受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武力威胁和侵略时,其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可以诉诸公理和道义的仲裁机制和保障机制(亚非拉一系列弱国、小国曾经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掠夺和蹂躏便是明证)。尽管今天我们不能说弱国和小国在遭受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威胁和侵略时,一定能够得到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的有效保护(因为这一机制还有某些致命的缺陷和脆弱性),但这一机制至少已使得那些意欲扮演侵略者角色的国家开始感到它们不再能完全不顾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了。道义因素在当今这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影响力的空前高涨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它迫使那些意欲推行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国家也开始感到有必要为它(们)的这类企图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而在以前的历史中,它们甚至连这种借以自慰的“合法性”依据都不需要。尽管除了诡辩性的说词之外它们不可能真正找到这样的依据,但这无疑是过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它标注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可以说,是否理解这种时代的差别也是我们能否真正把握康德“永久和平论”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关键。
三 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看“民主扩展论”的非正义性
康德“永久和平论”思想是奠基于他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国家关系的客观分析之上的。他认为当时各国(尤其是欧洲列强之间)频频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是:
(1)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宁愿无休无止地格斗而不愿屈服于一种他们本身就可以制订出来的法律的强制之下,因而是宁愿疯狂的自由而不愿理性的自由”。“每一个国家”都“要把自己的威严置诸于完全不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强制;而它领袖的光彩就在于他自己不必置身于危险之中又有千千万万的人对他俯首听命,为着和他们本身毫无关系的事情去牺牲自己。”正是这种国家制度上的缺陷在他看来是导致战争“无休无止”爆发的根源,因此战争本身又是“人性的卑劣在各个民族的自由关系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结果。这种“卑劣”的“人性”在他看来是存在于所有的民族国家之中,惟一的区别是“在公民—法治状态[即民主形态——引者注]之下它却由于政权的强制而[表现得]十分隐蔽”,(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0~111页。)但并非不存在。
(2)正是这种“人性的卑劣”使得当时法学家们“撰写的法典”以及他们提出的国际法理论在国际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丝一毫合法的力量”。像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瓦泰尔等法学家撰写的国际法法典(注: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撰《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普芬道夫(FreiherrSamuelvonPufendorf,1632~1694),德国法学家,撰《自然法与国际法》(1672年);瓦泰尔(EmmerichdeVattel,1714~1767),瑞士法学家,撰《国际法》(1785年)。转引自康德《永久和平论》一文之译者注,载康德:前引书,第111页。)不仅未能被用来制止战争,“却往往衷心地被人引征来论证战争侵略的正当”。康德据此认为,“如是的各个国家并不处在一个共同的外部强制力之下”的现实因素(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ll页。)是战争“无休无止”爆发的另一个根源。
上述两个方面的成因可以说是有相互联系的。然而,尽管两者都与“人性的卑劣”有关,但它们在各自指涉的对象方面却完全不同。前者显然涉及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问题,而后者则分明涉及国际社会或国与国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部强制力”的问题。对于康德试图建构的“永久和平”体系而言,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必须予以充分的关注和考量而不可偏废的。
康德对妨碍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状态的原因的分析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而他为消除这两个方面的障碍所作的理论创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针对上述第一个方面的阻碍,即由于“人性的卑劣”而导致的各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方面的阻碍,康德设想可以通过所有国家都实现共和体制(实现“永久和平”的“第一项正式条款”)并利用这种体制在抑制“人性的卑劣”方面的自然理性力量来遏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进而从内部阻止各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冲动。(注:对于这一点的论述和分析,参见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06页。)而针对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阻碍,即由于“各个国家并不处在一个共同的外部强制力之下”而产生的阻碍,康德则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实现“永久和平”的“第二项正式条款”)来加以解决。(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0页。)另外,在康德的思想中还包含了一种依据自然法而必须得到普遍认同的“世界公民权利”观(实现“永久和平”的“第三项正式条款”),但由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讨论。
康德之所以倡导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是由于他认为只有建立这种制度才能有效地保障“国际权利”(即“各个民族彼此之间的权利”)。(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0页。)而他之所以认为这种“权利”观念能够被所有的国家所接受,是因为他看到尽管在争夺国家利益方面人性的“卑劣”是一个事实,但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人类有一种更伟大的……如今还在沉睡着的道德禀赋,它有朝一日会成为自己身上邪恶原则的主宰的”。(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2页。)可以说如果人性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道德禀赋”.那么人类的“永久和平”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这里有两个理论问题是当代“民主扩展论”的理论家们一直未能厘清的:(1)虽然康德认为能够承载他的“永久和平”体系架构的注定是由共和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但他所指的共和体制与当今西方普遍盛行的民主体制并非完全相同。正如笔者在前面已经论及的,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已达到了康德对共和体制衡量标准的要求。(2)康德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寄托其希望的“自由国家的联盟”在类别上绝非是今天由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所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他倡导的这种“联盟”并不具有排他住。而且建立这种“联盟”的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让加入它的国家可以获得一种超越其他国家之上的“国际权利”(某些国家试图谋求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性”便恰恰是这样一种“国际权利”),而是要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强制力”(即得到绝大多数公认的国际法)。因为这是永远杜绝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最根本的、也是惟一可以最后诉诸的手段。国际权利的概念作为进行战争的一种权利,本来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样一种权利不是根据普遍有效的、限制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的外部法律,而只是依据单方面的准则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利是什么。于是它就必须这样加以理解:即,[只有]对于那些存心要使他们自己彼此互相毁灭,因此也就是要在横陈着全部武力行动的恐怖及其发动者的广阔坟场之上寻求永久和平的人们,它才是完全正确的。(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4页。)
正是由于“民主扩展论”的推崇者们谋求的是“依据单方面的准则”来获得他们“通过武力”所能决定的“国际权利”(即使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因此,尽管他们的“单方面的准则”把他们的目的说得十分崇高,但由于潜藏其中的动机是试图摆脱“限制每一个个体自由的外部法律”(即国际法准则)对他们自己的约束,因此“民主扩展论”所能推演出来的内在定义只能是强权政治的逻辑。因为“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无法律状态仅仅蕴含着战争,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再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只有是他们也恰好像个体的人那样放弃自己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并且这样形成一个(确实是不断在增长着的)终将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civitas gentium)”,人类的永久和平才能真正实现。(注: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14页。)
即是说,由于“民主扩展论”是“依据单方面的准则”(即片面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标准)来为自己凌驾于“共同的外部强制力”(即国际法)之上的“国际权利”(即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辩护的,因此,它在本质意义上是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思想相违背的。
概括起来说,康德所指的“自由国家的联盟”实际上只能是一种非排他性的、以共和制体制为基础的“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同时还必须满足的其他几个条件是:在这个联盟之中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得“依据单方面的准则”来试图获得它们“通过武力”所能决定的“国际权利”;而且在这个联盟之中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放弃自己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决不是康德所称的那种“自由国家的联盟”,因为它所谋求的是少数国家依据自己“单方面的准则”对多数国家所能实施的一种“国际权利”。这种“国际权利”使它能够居于国际社会中的霸主地位,对别国内政行使裁判权和武力干涉权,并在它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避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对其他国家发动所谓“惩罚性”的战争。而这种惩罚性的战争常常可能是非正义的。(注:康德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任何惩罚性战争(bellum punitivum)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主宰与隶属的关系”。康德:《永久和平论》,载康德:前引书,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