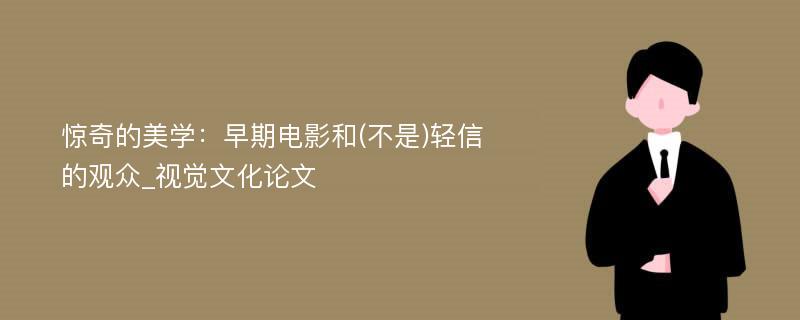
一种惊诧美学:早期电影和(不)轻信的观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惊诧论文,美学论文,观众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道里的惊恐
真实生活的河流发生堰塞的那一刻,就是流动的生活突然停止,那种感觉就像由此产生了逆流:这种逆流的感觉就是惊诧。
瓦尔特·本雅明,《什么是史诗性戏剧》(第一版)
对第一批电影观众的描述总会跳出来这么一个画面:观众对于卢米埃尔放映的《火车到站》所产生的惊恐反应。根据大量历史学家的说法,观众要么坐着往后仰倒,要么尖叫,要么站起来逃离放映会堂(或者三种反应连续不断地发生)。就像追溯许多神话的源头一样,关于早期电影放映描述的这段开头,依然让人猜测揣摩。在我遍查有关巴黎印度沙龙的“大咖啡馆”第一次电影放映的诸多报道中①这一说法还未见成形。在这样一则神话当中,有关电影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有待更多的调查和更精确的证据。观众这种惊慌失措和歇斯底里的表现,为接下来描述电影史的本质和电影影像力量的进一步神话言说提供了基础。
根据这则神话的表述,第一批观众懵懂无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如此激烈和具有威胁性的影像,他们也没有理解这种场面的见识和传统可以参照。活动影像的全新势态导致观众在最初遭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进技术的时候,往往是陷入各种原始未开化的状态。他们在面对新式机器威力的面前,纷纷表现出软弱的尖叫和逃离。首批影像放映的观众完全置身于主动产生难以置信的怀疑,他们瞬间产生的惊恐就像突然的短路,甚至无法婉转地表示一下“我完全了解怎么回事……但是所有的再现都是一样的。”轻信以压倒性的势态覆盖了其他一切细虑和思考,这种身体的反应显示了人们某种视觉上的冲击伤害。由此,人们产生了某种想法,有关这则神话的原初惊恐被界定为电影的力量,即这种史无前例的现实主义,它有能力让观众信服,这种活动影像,事实上是触目可知且危险的,包含了带给观众身体影响的东西。影像已经占据生命,它以无情的力量吞噬着对影像再现——也就是虚拟真实的所有思考。
再进一步,看电影最初的这一幕场景成为了某种当代观众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大咖啡馆被吓坏了的观众依然构成并主导着电影理论家的思考。他们认为面对这种全面主导的机器设备,观众完全被动地任由它魔术师般的力量来施展催眠和震惊的效果,从而让人恍惚和目瞪口呆。当代电影理论家所成就的学术生涯,也是受着此前立论的影响,低估了普通电影观众的基本智力和辨别事实的能力。他们也是以同样的不屑,毫无疑问地继承了先前对待观众的态度和理解。对于这种最初惊恐表现最为精细的解读来自于麦茨。但是麦茨让人敬佩的细读因为更多地从一种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而显得很不完善。麦茨把大咖啡馆观众惊慌失措的反应,依据电影媒介早期神话的阐述,把它看成是当代电影观众轻信本质的表现。麦茨宣称,就像人在孩童期依然相信圣诞老人,也像神话在刚开始的时候总是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一样,这些早期富有传奇色彩的观众的信念使得我们在面对电影的时候也会否定我们自身的信念。过去的观众信服银幕影像的方式同我们现在观众不信服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轻信是建立在电影雏形期的观众学理解的基础上。②
麦茨对于首批观众所起到的神话作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这并没有去掉其中裹缠的神话形态。相反,他从原始观众的神话描述里注入了某种内在的意念,转而把它从历史的分析里迁移出来,主观解释为假想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观众的某种本质属性。1895年法国大咖啡馆的观众不再隶属于历史,这批原初懵懂的看客“仍旧是在下面坐着轻信的那批观众,或者说心里还是坐而不醒的状态。”③这样一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这批内在容易轻信的观众为麦茨对于拜物神的迷信观众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基础。观众会在轻易相信影像以及对影像幻觉的认知所引发的既压抑又焦虑的状态里徘徊摇摆。根据麦茨的说法,发生在大咖啡馆的历史性惊慌失措,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欺骗投射在电影“很久以前”这类说法的神话发源地。
尽管我怀疑大咖啡馆的沙龙放映聚会是否真的出现了惊慌失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某种惊诧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惊恐的反应伴随着许多早期的电影放映。由此我也无意简单地否定电影观众建构的神话基础,而是想历史性地来触碰这一现象和问题。我们不能将原初懵懂看客的意象整个地囫囵吞枣。这些观众对于影像的反应仅仅是简单地相信和惊慌失措。这是需要仔细消化思考和辨别分析的。最初电影放映的影响和不能仅仅通过懵懂天真的观众,在一种短暂的心理状态下,把影像误认为现实这样一种机械的模式来解释。但这又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和背景下来阐释已经很好证明的事实,即最初的放映引发了震惊和惊诧。如果我们排除所谓的孩童般的轻信这种说法,在惊恐的关键点上产生了某种兴奋的情绪?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激动人心的经历如何阐释为新发明带来的吸引力,而不是一种困扰人的因素从而需要被排除的?现实以幻象呈现的时候在这样一种令人惊恐的接受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唯有通过对这些早期影像所处的历史情境和背景进行谨慎细致的思考和分析,才能够还原并理解这些影像作用于观众所产生的这种不可思议且激动人心的力量。历史的情境和背景包括最初的影像放映模式,世纪之交视觉娱乐的传统以及我归纳出的早期电影基本美学,即称之为电影吸引力,把电影视为一系列的视觉震惊体验。如果复原到准确的历史情境和背景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初活动影像的放映正处于视觉娱乐积极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中的一个传统就是极大地推崇现实主义带来的神奇效果。我们需要重新确认一下这个传统,并且回到世纪之交来审视并考察它的作用。
正如我在别的文章中也指出过,许多的早期观众把最初的电影放映看作是在魔术剧院高度发展起来的最高表演娱乐成就,正如法国梅里爱在罗伯特·霍迪恩剧院
以及他的英国导师马斯基林在伦敦的埃及剧场的实践一样。④在二十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这样一个传统已经动用了最新的技术成果(比如聚焦电灯和精心设计的活动舞台机械装置)来制造盛大的魔术奇观。由魔术剧院演绎的看上去超凡卓越的物质世界的定律恰好定义了其中所包含的幻象本质。十九世纪晚期在舞台上的魔术表演包含了把不存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熟练控制呈现的状态,使其与逻辑和经验上的期待不相一致。这样的剧院所针对的观众群基本上也不是那些好糊弄的乡下来的土包子,而是见过世面的城市快乐追逐者,并且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剧院所观看到的舞台表演是最现代的技术和表现方式。如果没有这种广泛存在的对神奇事物的信念和渴望,梅里爱经营的剧院是不可想象的,由此提供了根本上就十分激进的环境和背景。魔术剧院致力于让难以置信的场面出现在眼前。如此视觉上的威力包含了错视画派的所谓障眼法(trompe-l'oeil)的相互迁就,这样一种执迷上瘾的愿望,想要验证一下智力拒绝否定的极限。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看。
错视画派的障眼法作为美学幻觉的一种类型特别强调了完美的幻像在传统的美学接受层面起到了什么样有问题的效果。正如马丁·巴特斯比描述的,错视画派的障眼法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表达再现的精确性,而是要在“观者的想法里激起厌恶的感觉。”这种焦虑和不安源自于“信息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观者的知觉告诉我们看的只是一幅绘画;而另一方面,过去的视觉经验非常充分地让我们确信“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来审视,甚至到了一种想要碰触的感觉”。⑤影像所唤起来的现实主义为的是戏剧性地说明了观众的经验,促使他们在信与不信之间犹疑不定。虽然错视画派的障眼法同影像《火车到站》以及剧院的魔术表演有着一样的共同点,就是在相信和怀疑之间玩弄一种犹疑不定的快乐游戏,但也显示出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通常是小篇幅的错视画派的障眼法的绘画和卢米埃尔火车电影的“宏大的自然场景”⑥,观众在影像前面有一种本能退后的冲动以及观众在魔术剧院观看表演的时候所保持的空间距离,这些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绘画、影像和魔术这三种形式都说明了,这不仅仅是呈现了简单的现实效果,十九世纪的幻觉艺术形式巧妙的利用了它们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本质,对那仅仅只是幻觉的事实保持着清醒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现在翻阅到的早期卢米埃尔放映活动的最为详尽和最为清晰的表述是来自于俄罗斯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他在1896年7月在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的放映现场有过报道),他所强调的是这种奇妙的效果来自于新吸引力对于现实和非现实要素的混合。在高尔基看来,放映机所呈现的世界是一个生动和活力已经逐渐枯竭的世界:“在你面前,某种生命世界激情澎湃,这种生命世界不是通过言语,也略去了那鲜活斑斓的色彩,这是一个黑白无声,荒凉阴沉的生命世界。”高尔基解释说,放映机呈现的不是生命世界本身,而是生命世界的影子,而且他的表述绝无可能让人们错把影像的影子当作是实际的物质。高尔基在描述《火车到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火车逐渐逼近的威胁:“火车正朝你驶来……当心!火车的架势似乎要驶入这片漆黑,而你在当中坐着,它会把你撞得粉碎,血肉和骨架都撕裂得面目全非。”但是,他补充道:“但这也只不过是火车的影子而已。”在信以为真和惊恐的当口还夹杂着一丝对幻觉的清醒认识。甚至,在高尔基复杂微妙的表述感受里,还存在着对非物质世界的幻灭感,对无法捕捉的生命幻影的淡淡哀愁。⑦
人们也许不会接受高尔基这种作为文化知识分子而多少带点蔑视的反应,很明显这和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早期影像的接受不相符合。在那样一个普遍对这种包含新科技的娱乐技艺高声叫好叫妙的欢迎时代,高尔基对电影的负面评价显得非同寻常。但是他注意到了电影影像所包含的既有现实主义的效果,又有着对虚假的清醒意识,则更加和大众的反应高度一致,而不像是传统描述的那样只是一帮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尖叫反应。当代对观众、尤其是没多少见识的观众的反应的描述很难获得,而对卢米埃尔影像放映(以及其他早期电影人的相关活动)的最为真切的呈现方式,其中都包含了破解这种影像现实主义的最初遭遇的东西。这在最早卢米埃尔的放映中不断被人指出,电影的呈现刚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静止不动的影像,投射的只是静止照片的影子,然后为了炫耀一下对视觉表演的熟练掌控,放映员开始转动曲柄,然后影像就开始动起来。或者正如高尔基的描述那样,“突然之间,一阵奇怪的闪动出现在银幕上,接着画面就像被激发并赐予了生命力。”⑧
这样的呈现描述看起来是禁止把影像的理解看成是现实一辆真的物质现实的火车——它所高度强调的是运动瞬间的影响力。观众并没有误把影像当成真实,他们是因为现实通过对投射的运动幻象的转化方式而产生震惊。这绝对不是观众的轻信,而是幻象本身令人不可思议的特质导致观众震惊到目瞪口呆。在观众面前展现的与其说是火车驶近的速度,不如说是电影机械装置的威力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法是,是电影机械装置发出的威力很好地向观众显示了火车驶近的速度。这份莫名的惊诧感不是源于一种对现实不露痕迹的复制,而是来自于这种奇妙转化过程的影响力。乔治·梅里爱,也是制造这种效果的专家,对卢米埃尔的首映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化形式最初的影响力有过如下的描述⑨:
“一张呈现里昂贝勒库尔镇的静止照片被投射在银幕上,稍觉意外,但我还是有时间对我的邻座说:“‘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投影让我们开始惊讶起来?我一直做这样的行当已经不止十年了。’话还没说完,一匹马拉着车子开始走向我们,随后跟着其他的交通工具,接着是行人,总而言之就是街上看到的所有那些活动状态。面对如此奇观,我们张大了嘴坐着,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以至于惊诧到完全无言以对的样子。”
就在剧院,从静止的影像突然变为移动的幻象,这种瞬即的变形转换,让观众万分惊讶,并由此显示了电影的新颖独特和令人沉醉着迷。这样的放映完全不是让人怀疑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从而置身于这些不可思议的景象之外,而是通过影像激发出了某种矛盾的情绪状态,同时揭示出这就像十九世纪其他的视觉娱乐节目一样,观众是怀揣着将信将疑的犹豫不定的情绪状态。活动影像对于错视画派的静物绘画的处理方式和过程恰好相反,并且使场景更复杂化。电影最初只是呈现为一种影像,而不像错视画派在画布上的处理最开始偏爱于追求真实的蝴蝶,明信片或者闪亮贝壳的效果。这种不安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知道同我们看到的之间的差异与分歧。这种对影像的震惊体验来自于瞬间的变形,也就是基本上不是依赖于投射照片的新颖奇观(高尔基甚至特别强调了对这一切“太过熟悉的场景”⑩刚开始的失望),而是令人惊讶的画面忽然动起来的瞬间。与其说观众的震惊体验是来自于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会受到真正火车的威胁,不如说是他们折服惊叹于眼前这种难以置信的视觉转化形式,其不可思议的震惊程度就像是在剧院看到的最伟大的魔术表演一样。
影像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在魔术剧院成功地塑造了幻觉,但是观众还是把它当作幻象来理解。这种变形的转化完全有能力在观众那里引起身体的反应和无从言语表达的窘境,但他们还是会清醒地明白电影仅仅是影子的投射。刚开始静止的画面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随着静止的投影开始活动起来,并且产生了连续的动画效果,正是这不可思议的活动影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静止影像刚开始投射在银幕上的时候,暂时抑制住了动感的幻象,这正是放映机械设备的关键所在,正是它让人对第一次的电影放映产生了怀疑的情绪。观众知道银幕上的运动恰恰是因为放映机所导致产生的(这也正是让梅里爱的情绪无法安定的原因)。通过移动画面的延迟出现,卢米埃尔的放映员不仅突出了机器设备的存在,而且也揭示确立了某种惊诧美学,由此开始的对创造并复制运动的热情远远大于对科学的兴趣。
另外对于早期电影放映的描述则来自于大西洋彼岸。这一次进一步证实了放映机械设备所产生的戏剧性风格,并且清楚地指出了早期观众在惊恐的同时,也清醒地表现出了对这种震惊颤栗体验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阿尔伯特·E·史密斯,他是维他格拉夫公司(Vitagraph Company)的创建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他与合伙人J·斯图亚特·布莱克顿作为流动放映员的早期经历。史密斯和速写画家布莱克顿很早就开始以魔术师的身份,凭着“手上的技巧以及他自己发明的一些不让人看见的机械装置”到处旅行。(11)但就像大多数的舞台魔术表演师一样,他们都改行放映活动影像,这也是视觉娱乐节目技术含量最高的行业。史密斯为爱迪生发明的早期电影放映机做出了机械方面的改进贡献,就是在胶片和灯源之间加上一块水板,以此来吸热降温,从而保证电影影像的时间可以延长,而避免赛璐珞燃烧起火的危险。
史密斯和布莱克顿巡回放映最受欢迎的节目就是《黑钻石特快列车》,这是仅有一卷本的电影,表现一辆火车驶向摄影机镜头。就像大多数早期电影放映的情况一样,布莱克顿在放映的同时配上现场讲解词,好让观众进入看电影的状态,并且制造出戏剧性情境和气氛。史密斯是这样来描述布莱克顿在放映《黑钻石特快列车》的作用的,把他形容为“恐怖主义情绪的制造者。”正如他回忆时提到的,布莱克的解说(就在火车静止不动的时候开始讲)是这样的: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看到的照片是远近闻名的黑钻石特快列车。再过一会儿,一个石破天惊的时刻,我的朋友们,一个我们这个历史时代从未有过的时刻,你们将会看到这辆火车以极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动起来。火车将会向你们飞来,与此同时从它巨大的铁喉里冒出来滚滚浓烟和火焰。”
尽管史密斯对布莱克顿口头讲解的回忆已经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因而不能完全一致地相信。但是这恰好抓住了电影最初放映的时候面对观众可以宣扬兜售的方面,并且让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观众的惊恐反应和体验。布莱克顿直接向观众表白陈述,不断在电影和观众之间做出某种解释,并且强调这是电影放映的一次真正行动。这就像在露天的公共市场,那些杂耍、戏院前叫喊招揽观众的人一样,他引起了观众期待的氛围,一种公开表示出来的好奇夹杂着焦虑和不安,他强调的是这项活动所包含的新颖和令人惊叹之处,并且指出来这正是这样一次电影放映活动所拥有的并且即将被展现出来的吸引力所在。这种期待感,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这样一个瞬间转化过程的密切关注度,并且突出了最初放映时候令人震惊的效果。与其说是一次简单地呈现现实的某种效果,还不如说是从危机瞬间产生的影响力,为观众酝酿,延宕,最终爆发并作用于观众的感受和反应。史密斯的回忆录中说道,对于这样一次不可思议的现实影像化转换方式的呈现,导致女人们惊声尖叫,而男人们惊骇到呆坐着不知所措。(12)
吸引力美学
由电影来满足对动力吸引的新颖迫切需求的这一天来到了。在电影当中,以震惊体验的形式所传达出来的感受力以一种正式的原则建构起来。
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当中的某些图形主题》
当早期电影中扑面驶来的火车以一种过度夸张的方式来呈现电影所具备的震惊体验,但是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也传达了早期电影的核心要素。我曾经把以叙事作为主导建构力量之前的电影(这个时期从电影诞生到1903或者说1904年之间维持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称之为吸引力电影。(13)吸引力直接作用于观众,有时候,就像早期的火车电影,非常夸大这种扑面而来的冲击性体验。与其说吸引力电影结合性运用了叙事行为或者移情注入了人物的精神情感,不如说是通过作用于观者的好奇心而在电影影像的呈现上添加了高度的自觉意识。观众并没有在电影虚构的世界以及戏剧性的情境里迷失,而是保持了一种对看的行动的清醒意识以及好奇的兴奋与满足感。吸引力电影通过各种形式手段,使得影像突如其来,造成一种直接冲向观众的动态画面。这些手段从早期铁路电影所潜在的迎面撞车效果,到这一时期的表演风格,比如演员冲摄影机点头或者做手势(举例说梅里爱在银幕上指示观众注意他所引起的画面形式的转化)或者是一个放映解说员把将要看到的场面提醒给观众,方法是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电影正是通过这样一些表现手段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强调突出这种展示的行动。除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电影也提供并呈现了普遍意义上的某种直白的窥视快感。
快感是在我这里强调的,不管这样的快感有多么特别的复杂。当法国蒙彼利埃的记者在1896的时候把卢米埃尔的电影放映描述成“在惊恐的边界处激发出了某种兴奋”,他在称赞这种新的奇观,并且解释其成功的秘诀。(14)如果第一批观众发出了尖叫声,那是他们意识到了机械装置的威力可以一扫先前牢固确立的现实感。在视觉幻象所爆发的力量前面,我们对世界脆弱的认知突然经历了这么一场绚烂的感受,观众由此产生了焦虑和快感相交织的复杂感受,通常流行艺术的受众把这称之为感动和惊栗,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一种新的吸引力美学。迎面冲撞而来的火车并不仅仅是制造了负面害怕的感受,而是确立了特别现代的震惊娱乐形式,表现在别的地方就是最近出现的对游乐园的倾心与迷醉(比如过山车),这样的游戏交织着加速冲高时候的兴奋刺激,也包含了由现代工业技术所保障的下坠跌落时候的安全。纽约康尼岛游乐园最吸引人的一个项目,叫跳蛙铁路,完全再现了《火车到站》所面临的惊恐。两辆承载着四十位游客的电动机车被设计成以高速冲向对方的撞击游戏。就在相撞的那一刻,一辆机车沿着弯曲设计翘起来的铁轨升举起来,从另一辆机车的顶部滑过。林恩·柯比也曾经撰文指出这种火车机车相撞的游戏安排,无论是在乡村的集会还是在诸如爱迪生1904年放映的电影《火车大碰撞》(15),这在二十世纪初时候是多么受欢迎。
这种扑面而来的生动感,无论就电影自身的形式,还是电影所展现放映的方式,都成为吸引力电影最大的特色。这种展示行动的直接性也突出强调了震惊本身——这恰恰是观众的迅疾本能反应。电影解说员也格外强调这方面的吸引力,特别刺激观众的好奇心。电影影像施展自己展示方面的优势才能,然后再消失。这和融合了心理学逻辑的叙事不同,吸引力电影并不去推进刻意的故事发展;这中间真正可能的就是非常有限的情绪延宕的设置。但是通常这样的影像片段包含了一系列的吸引力,短片电影将所有这些吸引力的设置串联在一起,然后给观众一个交待的时刻。这种持续的惊栗感受只有观众熟悉并感到厌倦时候才会有所收敛。这种惊栗体验的串联也会依据某种主题来结构,并最终导向某个高潮的时刻,这也就构成最吸引人之处(比如史密斯和布莱克顿制作的《黑钻石特快列车》)。恰恰是放映员而不是影片本身赋予这样一个游戏节目以拱起来的曲折结构,解说放映员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强调指出构成吸引力电影最根本的这种呈现展示行动。(16)
爱迪生拍摄于1903年的《电击大象》,这部电影表明了影像展示的这种时间逻辑。大象被带上一个通了电的金属板上,周围都看护起来,一阵烟从它的脚底升起来。过了一会儿,这头大象栽倒在地。这个从技术上来说非常高级的死亡时刻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也没有戏剧化的处理。无独有偶,1904年由比沃格拉夫影业公司出品的虚构电影《给女骗子拍照》,呈现了一个单一镜头表现一位妇女被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架着,并且试图让她别动以便拍摄一张嫌疑犯的面部照片。摄影机通过移动推镜头跟拍这三个人,最后是以一个女人中等的脸部特写框定作为结束。为了破坏这次指认她犯罪的脸部特写镜头的拍摄,这名女嫌疑犯拼命挣扎,并且扭曲着她的脸。通过摄影镜头向拍摄对象迫近的移动,这个女人逐渐放大的脸突出了影像的展示行动,这一展现过程构成了这部电影最基本的特点。这两部电影都显示出同《火车到站》在表现形式上的巨大区别,但是所有这三部电影都表明了通过瞬间的揭示,来说明如何诱发观众的好奇心并且如何实现并满足这种好奇,这正是吸引力电影典型的魅力所在。这是电影的孕育期,而不是一个发展完好的时期。
正如我在别的文章中申明过(17),吸引力电影的拍摄方法是一次展览主义者的呈现,同此后叙事电影发展起来以后所引入的隐藏窥视者的电影完全相反。这种绝无仅有的视线展示非常明显是属于在剪辑成为电影主导之前的某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是由单个镜头组成——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这构成了这一时期电影制作的主体。尽管如此,即使在出现了剪辑和更为复杂的叙事,吸引力美学还可以在定期为观众专门制作的非叙事性奇观的电影作品中呈现(比如音乐歌舞片以及棍棒喜剧都提供了这方面非常明晰的例子)。吸引力电影在此后电影的发展中持续存在,尽管整体上绝少成为故事片电影的主导表现形式。它提供了某种暗流,游走漂浮于叙事逻辑和所表述的现实场景之间,从而制造出深受超现实主义者(18)所喜爱的所谓电影的莫名其诧(cinematicd é paysement)时刻。
这种美学与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普遍流行的艺术审美接受的标准,以分离注视为基本目标完全不同,以至于建立起来一种反美学的态势。迈克尔·弗里德在讨论十八世纪的绘画时,提出了所谓的吸收论(19)。吸引力电影却完全站在这种审美的对立面。在弗里德看来,格勒兹和其他人的一些绘画通过自我完整的密闭隔绝的世界而忽略掉观者的存在,从而创造出同观赏者的新关系。早期电影完全忽略了观者的建构意义。可这些早期电影却十分明显地认识到了观众的存在,影像的表现看上去都是要伸出画面并且做出和人迎面相逢的姿态。视线的吸收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观者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并且通过特别的遭遇,直接的刺激以及一系列的震惊体验来实现并获得满足。
为了打开视觉的好奇心并且激发人们对新颖事物的欲望和兴趣,电影的吸引力正是利用了五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奥古斯丁在他的所谓的“眼睛的欲望”的标签下提出来的好奇心(curiositas)。与视觉愉悦相对照,好奇心回避了美的东西,而是直接探寻的是,“仅仅是因为这种欲望只是为了找出发现并且知道了解。”好奇心驱使观者关注不美的场景,比方说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而且“因为好奇心像一种病态的扩张,致使许多非同寻常的事物和场景被放置并展示在我们的剧院里。”在奥古斯丁看来,好奇心不仅导致了想看的迫切欲望,而且具有一种求知欲的本能冲动,最后就是曲解了魔术和科学之间的差别。(20)如果美在奥古斯丁柏拉图理想主义的目标下也许会形成通往理想的原初起点,好奇心所拥有的力量就是引导人们的迷失。电影的吸引力暗含着分神的危险,相比奥古斯丁所表现的模范基督徒那种凝神和沉淀的生活状态,这种分神算得上是一项极大的罪恶。
吸引力美学以相当清醒的方式,站在传统的对美的关注所产生的视觉愉悦的认定的对立面发展起来。十九世纪在名为伦敦埃及大厅(它是作为激发自然好奇心之家而存在的,里面陈列着自然历史的怪胎和人造物品,随后他变成了马斯基林的魔术剧院)的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表演宣称自己是“丑陋聚结大厅”,并且它的广告宣传词打着的口号是“不会比这更加骇人听闻的了。”(21)这种展示那些让人生厌地东西而引发的吸引力时不时被当作激进的手段,不断推动奥古斯丁对同样无法确定事物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求知欲。就像早期的电影放映,怪异的表演展览和其他对好奇事物的陈列展示都被描述成为开拓新知,启发心智。差不多与此类似,吸引力电影当中的一种广受欢迎并且持久兴盛的类型就包含了这样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比如查尔斯·厄尔本从1903年开始制作的《未见世界》系列影片),它们呈现的是干酪蛆、蜘蛛和水蚤被放大的图像。(22)等到1914年一名电影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反对电影粗俗化,反对展示那些“黏糊糊不美而令人作呕”的东西,他号召给这些心生排斥的观众拍摄可以带来优雅感受的电影。(23)但是电影老板们明确知道,要想制造惊栗的体验,就必须添加一些让人厌恶的东西,或者是有惊无险的东西。路易斯·卢米埃尔明白,他的电影如果要引起观众爆发出身体的反应,就得在日常生活和运动场景的复制过程中,在激发观众对科学的好奇心的同时,要加入一些生死攸关的猛料。
震惊的分心娱乐与模棱两可
电影反映了感受机器的深沉改变,这些改变就私生活的范围来看,是大都市街上行人今天所经历的生活;就历史范围来看,也是任何一个当代国家的市民所要经历的。
瓦尔特·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视觉好奇心的冲动一如奥古斯丁一般古老,可以肯定的是十九世纪强化突出了“眼睛的欲望”这种形式以及对于这种形式的商业化开发与利用。伴随着万花筒接连不断的城市风景的都市化扩张,通过视觉展览所呈现的消费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不断上升的殖民开拓的新种族和疆域的分类与开发,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并激增了人们对影像和吸引力的向往和欲望。城市街景,电影广告以及国外风光,所有这些都毫不奇怪地构成了早期电影的重要类型。异域世界景观普受欢迎(这已经在立视镜与魔灯这些早期电影装置中得以发展和广泛播放),这一点表现出人们希望借助影像来消费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几乎不可遏制的欲望。电影,正如早期电影公司打出的宣传口号一样,是一种将世界置于你的掌握之中的发明。早期电影把可见的世界呈现为一系列不同的吸引力,第一批电影公司出品的名目差不多囊括了百科全书式地对这种新的超视觉领域的调查与呈现,从全景式风景到微观摄影,从国内风景到囚犯的砍头行刑和电死大象。
如果说早期电影的吸引力并不完全表现即将相撞火车的惊恐场面,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电影都会以奇怪和惊讶作为噱头,而且都是针对运动的幻觉来制造震惊体验。即使全景拍摄的风光段落也不会仅仅是流于纯美的注视与欣赏。大家都充分意识到了机器所引发的某种视点的关注,摄影机正立在支撑它的三脚架上。全景式风光片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电影从前后两个角度拍摄火车,这就极大增强了表现效果,调用的不仅仅是活动影像机器,而且还包括把观众从端坐的位置上拉离的火车机车。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在他有关火车旅行所提供的视点转换的描述当中提出了所谓全景式视点,这些火车电影恰恰提供了技术上改变了的媒介呈现视点方式转变的例子。与传统旅行者观看风景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是,火车旅客“不再作为关照的客体而置身于同一空间;旅行者通过承载自己穿越世界的机器来观看目标客体,风光景色等等。”(24)一部从前面拍摄火车的电影,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吞噬着空间”(就像一个旅行者描述火车全景的经历(25)),通过工业机械的装置所发挥的影响力,强化突出了火车旅行的陌生新奇与动感,从而获得倍增的效果。这样的火车电影也许拍摄的是把即将撞车的黑钻石特快列车翻个底朝天,但这依然是通过技术上空间和运动的媒介体验来激发观众的好奇。
从根本上来说,早期电影试图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野心与冲动,把一切现实都转化为影像关照,这让人想起高尔基在电影放映机前面所产生的不安与沮丧。吸引力电影实现了它所激发引起的视觉好奇心,但是视觉好奇心的本质,也就是眼睛的欲望,从来没有完全被满足过。这样一来,早期电影制作和早期影片无法摆脱的本质也显示出电影潜在的无穷无尽的不断展示单独吸引力的能力。但是除了好奇心无限的表现潜能,高尔基的不安来自于这种新式追求惊栗刺激所包含的抽象和异化。
高尔基并且在吸引力的梦想世界之家,即康尼岛(1906年他访问过)发现了一种普遍深入的乏味,他称之为“一种对各式各样厌倦的奴役状态。”在高尔基看来,康尼岛提供的“是一种既不是交通,也不是欢愉的惊愕。”(26)高尔基这样一位来自欧洲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愉悦方式的嫌恶的调子可以清晰无误地感觉出来,而且他还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了这种对惊栗的需求,是源于工业化的、由消费者主导的社会。面对突然活动起来的火车所发出来的特别愉悦的尖叫,表现出不仅是观众愿意把影像当作现实,更多说明的是,观众的日常经历和感受已经失去了过去传统所赋予现实的连贯与直接。这种经验的缺失导致消费者产生渴求惊栗的欲望和需求。
吸引力电影不仅造就了现代审美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也是对现代尤其是都市生活特别之处的回应。本雅明和克拉考尔把它理解为经历和感受的枯竭,取而代之的就是文化的消遣娱乐。本雅明的著述对于视点和经历的现代转变的描述非常具有论辩性(和模棱多义性),(27)克拉考尔的论文《分心娱乐的仪式:论柏林电影宫》(The Cult of Distraction:On Berlin's Picture Palaces)特别关注了电影的功能,特别是奠定了吸引力电影的先决要素——放映。(28)
过去的好几十年我们对电影的分析都是沉醉于文本,导致视野上的迷失,看不到放映实际上是转化并建构了面向观众传达的一种电影方式。早期电影当中凸显这种呈现方式是通过放映的情境以及电影直接对观众进行沟通这样两个方面。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克拉考尔才在他的著述里对电影宫的建筑和电影作为晚间节目的丰富多彩的安排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看电影之所以定义成为持续的吸引力,这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克拉考尔把这描述成为“完美感官印象的片段性场景。”(29)柏林电影院豪华的设计与装饰让人们从古典电影叙事的流畅贯通中游移出来。对此克拉考尔是这么描述的:“电影院的内部装修与设计只起到了一个作用:把观众的注意力固定在外部环境中而避免让他们陷入电影的深渊。感官的刺激以如此快捷的方式循流不断,以至于在这些中间挤不出一点空隙来做哪怕是最微小的思考。”(30)
电影院本身的精美设计(通过特别灯光的操纵来瞬间闪现并凸显)反过来也是推动电影朝着更大规模更为壮观的格局上发展,使其融合进来音乐和现场表演而显得具有反讽意味的大戏。电影在一次体验感受中只是一种元素被克拉考尔描述成为一次“完全的艺术效应”,可以“动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来刺激人们任何一种感官。”(31)在克拉考尔看来,电影节目程式的不连贯和手段形式的丰富多样(把二维的电影与三维的现场表演并置在一起)非常严重地破坏了电影招致幻想的威力。被投射的电影“退回了平面空间,而它的欺骗性就暴露出来。”(32)这和第一批影像放映一样,吸引力的美学恰恰与引起幻觉的吸引投入相颉颃,电影宫节目的变化多端不断地提醒着观众,观看的过程是接受着各种感官方式的刺激。仿佛是为了表示对增加的长度以及故事片电影所构成的窥视性的虚构的不屑,各种吸引力手段所形成的非连续效果依然主导着晚间节目的主要情绪。
尽管这像是丰富多样随意选择的感官惊栗(甚至构成了基本动因)排成了队,但是克拉考尔洞悉出了某种缺失体验,这多少和高尔基感觉的不安是有些关系的(甚至也许就是不同的翻译而已)。这种分心娱乐仪式的聚合元素存在于克拉考尔所谓的纯粹外在性。而且观众热烈追捧这种外在性也折射出他们内在生活的中心缺失,尤其是那些劳工大众:“基本上是一种形式上的紧张填补了他们日常的生活,却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有实现的满足感。这样的缺失需要补偿,但是这种需求只有把这种缺失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是以一种外在表面的方式表达出来。娱乐形式恰如其分地反应出了这样一种状态。”(33)
这种持续的吸引力提供并满足了人们对突然、紧张和一些外在的情绪需求,而这些由克拉考尔确认为揭示出了现代体验的分裂与碎片。这种对惊栗和奇观的口味需求,特别成就了好奇心的现代形式,并且定义了吸引力美学的特征,也就通过充沛完整体验的现代性缺失而形成。接下来的是,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所理解的由铁路旅行带来的现代观感方式的改变也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这中间交织融合了弗洛伊德的超心理学以及西美尔的都市社会学(并且由此延循了本雅明轨迹形成的学术路径),施伊费尔布什描述了一个刺激防护盾,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度遭受刺激的人们可以用来抵挡持续不断的攻击。(34)但是有人也指出这种刺激防护盾让体验感受的边沿有些迟钝,导致人们需要美学上更强烈的能量来穿透破除这种防护盾。正如米莲姆·汉森在阅读本雅明所指出的,现代的震惊体验回应了“人类面对工业化的生产与运输方式的适应与理解,尤其涉及了时空关系非常激进的重新构造。”(35)震惊不仅变成了现代体验的一种方式,而且变成了一种现代惊诧美学的策略。从此以后,对新技术带来的惊栗体验的利用就混同联系着灾难。
吸引力是针对异化体验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克拉考尔(也如本雅明)看来,电影的价值存在于它暴露了连贯与真实之间的根本性缺失。电影致命的诱惑力在于它试图承接传统艺术与文化在美学上的一致性。电影最热切的愿望表现在它一直有意识地强化并使用断续的引发震惊体验的那些手段,或者如克拉考尔所说的:“它的目标一定是热切地朝向某种娱乐形式,从而暴露拆解的力量,而不是遮盖掩饰它。”(36)正如汉森指出的,本雅明对于震惊的分析有着根本性的模棱两可,这肯定是在现代生活的匮乏经历体验里形成,但是也足够承担并发挥“策略性作用——作为一种人造手段推动人类身体进到接受性反应的瞬间。”(37)
人们在银幕影像前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不仅仅是身体上表现出来的反应,它特别类似于日常经历中碰到了城市交通灯,或者说是遭遇了工业化生产时候的状态。在电影的双重属性当中,它把静止的画面转化为移动的幻觉,这就形成并说明了某种状态,那就是惊诧和认知迅速交替缠绕发挥着作用,而在幻觉引起危险的震惊以及纯粹幻觉引起的欣喜之间产生并释放出某种能量,从而导致产生快感。这种摇晃不定的体验感受转变成对震惊的认同。这绝不只是实现了完整对现实复制的梦想,它是完整电影神话的核心——这第一批的电影放映的经历和体验揭示了电影幻觉的空洞中心。把影像转化成运动的震惊感受,这有赖于在放映员的操控下,投射呈现出人为的幻觉。从静止画面到运动影像的运动强化了机械装置令人难以置信和神奇独特的特点。但是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它也消解了人们对影像真实的天真信念。
电影的头批观众不再当作迷惑的看客而用来解释电影神话初建时候的理论话语。历史再延续伸展的同时也揭示了许多缝隙,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先期观众的经历与体验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认知,认为古典时期的观众完全陷入了具有移情迷惑作用的叙事。如果把他们放置到历史的情境和传统来看,第一批观众的体验表明他们并不只是像幼稚孩童般的一味相信,同时也具有毫不掩饰的清醒意识(并且乐在其中)可以分辨电影引发幻觉的能力。我尝试着颠倒过去传统对移动影像冲击力的理解。就像解除神秘的放映员,我把人们在观看奔袭开过来的火车影像而四处逃散的画面定格下来,并且把它当作比喻而不是神话来理解。这样的一次截获会以一种惊诧的方式让我们茅塞顿开,这些表现出来的惊恐和快意兼而有之的尖叫都是为放映员和观众精心准备好的。观众的反应却是与原始本能的解释相反:这是一次与现代性的相逢。从一开始,引起人们惊恐的影像掩盖了一种缺失,并且仅仅寄希望于同鬼魅的拥抱。奔袭而来的火车没有撞上任何人。这正如高尔基说过的,那只是火车的影子,而它裹挟而来的威胁,装载的只是虚空。
(本文译自:《电影理论与批评:引介读本》(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Introductory Readings)第862-876页,Leo Braudy.Marshall Cohen 编选,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版)
注释:
①关于第一次电影放映的描述可以在绝大多数标准的电影历史当中读到。乔治·萨杜尔在《电影通史》第一章《电影的发明》1832-1897(巴黎:denoel出版,1948)第288页,其中描述了观众在《火车到站》前面惊慌失措的情形,但是奇怪的是,他援引的证据却是一场卢米埃尔拍摄的街景,而不是火车电影。其他一些出现过的证据,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下面将讨论的文章,或者如林恩·柯比从《插画》(1896年5月30日)的引用描述了影像自身所包含了的威胁性,但是并没有提及在观众中引发了惊恐(参见)林恩·柯比著《男性歇斯底里与早期电影》,出自《暗箱》17期(1988年5月)第130页。最近的一些历史表述都倾向引用萨杜尔的说法,或者简单地重复这则传奇。然而,查尔斯·马瑟告诉我他对早期旅行放映员莱曼·H·豪的研究发现了好几项证据提到早期放映火车电影的时候都出现过观众的尖叫声,但是,不是最早卢米埃尔的影片。
在这里我得指出柯比的文章以及他对早期电影与火车的研究成果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感觉很少有作者理解并把握住了早期电影震惊的重要性,即使我注意受到了早期观众的这种潜在状态,但与她的看法有不同。另外,我还得提及与纽约大学的研究生理查德·德克鲁瓦的交流,也激发了我写这篇论文的灵感。
②克里斯蒂安·麦茨著《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译者:Celia Britton,Annwyl Williams,Ben Brewster以及Altfred Guzzetti(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第72至73页,本·辛格尔·在他的文章当中指出了麦茨在把弗洛伊德的偶像崇拜概念应用到了电影当中的局限性,这篇文章就是《电影,照相术和偶像崇拜:对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分析》,引自《电影季刊》27/4(1988年夏季号)。然而,我认为麦茨的问题总是从历史的本性出发来展开讨论,这样就导致了对待电影的观众观看学过分轻视和简单化。与此同时,我发现麦茨找到的电影影像中心的缺失是极富洞察力的,完全超越了超精神分析的研究范畴。
查尔斯·马瑟(在他的美国电影历史的系列研究著述里,卷1《电影在美国的兴起》)指出,1671年的《Ars magna lucis et umbrace》第一次完整地对待反射灯泡,魔灯之前的电影设备。Athanasius Kircher宣布破除幻像的神话是一切电影放映设备的核心所在,这样就彻底阻止了把壮丽的景观当作神奇魔术来看待。宗教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动机(Kircher是一位耶稣会士)对破除神话之举是显而易见的。马瑟发表了特有创见的声明,这一刻“预示着电影实践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被投射或者说被反射的影像的看客变成了历史表述的主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观众”(第31页)。换句话说,马瑟把破除神话看作是观众存在的核心关键所在,并且指出了电影观众学的传统要早于卢米埃尔好几个世纪。
③参见前面引用麦茨的书,第72页。
④参看我的文章《原初电影:一种框定,还是对我们的欺骗》,刊载于《电影季刊》29/2(1988-1989冬季号)。有关梅里爱戏剧幻术的描绘可以参阅玛德丽安妮·马尔特特-悔里爱编辑的《梅里爱和电影摄影术的兴起》(巴黎:Klincksieck,1984)特别是53-58页以及皮埃尔·哲恩著《梅里爱,电影家》(巴黎:Albatros,1984)第139-168页。保罗·哈姆蒙德著的《了不起的梅里爱》(伦敦:Gordon Fraser,1974第15-26页)也提及并讨论了梅里爱的舞台工作,而且指出了他所亏欠于马斯基林的。
⑤马丁·巴特斯比著《错视画派:被欺骗的眼睛》(伦敦“学院编辑出版社,1974)第19页。我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我的这篇论文所获得的灵感和动力来自玛·丽安·多恩激动人心的论文《驱动力作用于人的身体的方向改变时:移动影像》,刊载于《广角》7/2-3。我和她的论文化话题上有许多交集的地方,但是在方法和结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⑥相比爱迪生早期电影放映机,卢米埃尔的放映装置更大更重要,这一点在贾奎斯和玛丽·安德烈编著的总集《蒙彼利埃的光明季节》(法国,Perpignan:让维果学院,1987)第64-75页。
⑦高尔基的描述收录在了杰伊·莱达著述的《电影:俄罗斯和苏联电影史》(伦敦:艾伦&安文,1960)第407-409页。译者署名为“勒达·斯旺”。
⑧出处同上,第407页。我必须补充说明,数年前我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安内特·迈克尔森最早向我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关于运动举例所讨论的惊栗是我这篇论文的原动力点。有人也许会举出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卢米埃尔拍摄的《拆毁一堵墙》,影片顺着拍,反着接,以至于造成了一种神奇的效果,被拆毁的墙居然恢复到了原初的模样。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一位记者报道了这部电影“总是从喜欢它的观众那里激起热烈的掌声”(安德烈著《蒙彼利埃的光明季节》,第84页,本人翻译)。
⑨引自乔治·萨杜尔著述第271页,本人翻译。
⑩埃里克·巴诺著《魔术师与电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第75页。这句话引自1899年有关魔术行业的期刊Mahatama里头的一篇文章。
(11)阿尔伯特·E·史密斯与菲尔·A·考里合著《两卷与一柄》(纽约花园城市:Doubleday,1952)第39页。正如查尔斯·马瑟指出的那样,史密斯的书很不准确。虽然绝大多数的错误似乎都是虚假宣称的成就(比如在西班牙和美国人战争时候在古巴拍电影),但是这些并没有削弱他对电影放映所描述的价值。
(12)同上,第39-40页。
(13)参见汤姆·甘宁著《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载于《广角》8/3-4。该术语是由我和安德烈·戈德里奥在提交给1985年在法国Cerisy召开的“电影历史新方法讨论会”的一篇名为《早期电影:半个世纪的电影史》。与亚当·史密斯,一位1984-1985担任哈佛大学视觉与环境研究的卡朋特中心的助教的对话也丰富了这些观点。吸引力这个词往后回溯指的是一种流行传统,往前指的是一种先锋派的颠覆。这个传统就是露天市场杂耍地,嘉年华,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些现代游乐场比如纽约的康尼岛。这个语汇的先锋激进性应用源于谢尔盖·爱森斯坦有关戏剧和电影的理论和拍摄实践。他有关吸引力蒙太奇把一种通俗的能量转化成具有美学的颠覆力量,通过吸引力力量的激进式理论化表述,由此来破除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传统。有关该理论在通俗文化里源起的清晰讨论和理论描述,详见贾奎斯·奥蒙特著《蒙太奇爱森斯坦》,译者:李·希德里斯,康斯坦斯·彭雷以及安德鲁·罗丝(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第41-48页以及爱森斯坦本人的论文《吸引力蒙太奇》以及《电影吸引力蒙太奇》,载于爱森斯坦著《著述集》第一卷1922-1934,翻译与编辑:理查德·泰勒(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
(14)引自贾奎斯和玛丽·安德烈合著《蒙彼利埃的光明季节》第66页。
(15)约翰·F·卡森著《娱乐千百万:世纪之交的康尼岛》(纽约:希尔&王,1987)第77-78页。转引自林恩·柯比,(引自《插画》)第119-120页。
(16)早期美国电影放映员的作用影响力在查尔斯·马瑟的著述里得到了精彩阐释,尤其是他的这篇《镍币电影时代的开始,建构了好莱坞再现模式的框架》(载于《框架》1983年秋季号),以及他接下来有关埃德温·S·波特和莱曼·豪的论述。
(17)甘宁著《吸引力电影》第64页。有关这个问题也在我的书《DW·格里菲斯和美国叙事电影的起源》(Urbana: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91)。
(18)关于超现实主义者喜欢在电影中运用让人迷惑的影像,参见保罗·哈姆蒙德编辑的《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超现实主义者的电影书写》(伦敦:英国电影学会,1978),尤其是布雷顿的论文《仿在林中》第14页。
(19)迈克尔·弗里德著《吸引与戏剧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和旁观者》(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参见比如说第64、第104页,类似对观众的排斥很明显地也在十九世纪自然主义者的戏剧透视法和风格当中出现过,渗透在有关第四面墙的观点里。
(20)圣·奥古斯丁著《承认》,里克斯·华纳翻译(纽约:美国新图书馆,1963)第245-247页。
(21)这样一幅讽刺绘画也在理查德·D·阿尔提克的书《伦敦展示》(牛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第254页再现过。正如米莲姆·汉森向我指出的,迈克尔·弗里德对托马斯·伊肯斯绘画《克罗斯诊所》的讨论,引出了有关吸引力美学以及它与厌恶排斥之间的关系等等相关话题。虽然弗里德把这幅画放在了吸收关注的传统里,但是对克罗斯血迹斑斑的手指和手术刀的聚焦以及病人切开的伤口看上去提供的是别样的经历,其中的体验“纠结混杂了痛苦与欢愉,暴力和奢侈逸乐,厌恶排斥与心醉神迷”(弗里德著《托马斯·伊肯斯的“克罗斯诊所”当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和畸形》,载于《再现》1985年冬季号第9期第71页)。正如弗里德说的,“这首先是那番处境下的矛盾冲突和对立成为关注的中心并且让人感受折磨,并且在最后让人们在这幅画作前面变得麻木”(第73页)。这在我看来,是描述出了吸引力美学的核心体验:但是,弗里德如何看待这同吸收和关注体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却还不是十分清楚。弗里德没有把这种冲突对立和崇高壮观的传统联系起来,后者很明显地构成了吸引力美学可接受的形式(回顾一下伯克把惊诧定义为最高程度上的崇高壮美的效果)。通俗流行娱乐与崇高壮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基本上没有被探讨,而且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超出了本论文讨论的范畴。但是不无必要指出弗里德在参循托马斯·韦斯凯尔的时候,把崇高壮美的效果同弗洛伊德理解的阉割恐惧联系起来。尽管我此刻并不打算深入这个话题,但是从这个方向出发,考察第一批的电影放映所制造的创伤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早期电影当中的物神崇拜,以此来确认麦茨几乎没做什么分隔的这种观影创伤。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关联的思考还是很有意思的,正如本雅明和施伊费尔布什所理解的(我在论文后面将讨论)弗洛伊德概念下的刺激防护盾是一种现代体验的反应,而不是遵循一种生物的原则。
(22)厄尔本的系列电影在拉彻尔·洛和罗杰·曼威尔合著的《英国电影史》第一卷1896-1906(伦敦:艾伦&安文,1948)第60页当中有描述。
(23)哈利·弗里斯著《我们的女士电影》,1914年版的重印(纽约:加兰德出版公司,1978)第41页。
(24)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著《火车旅行》(纽约:Urizen出版社,1079)第66页。
(25)出自《纽约邮报和特快专讯》(1897年9月25日),转引自肯普·R·尼弗《比沃格拉夫电影名录1896-1908》(洛杉矶:罗凯尔研究集团,1971)第27页。记者对比沃格拉夫公司有一部电影从一个火车机车上穿过哈沃斯特洛隧道的拍摄做出评论。
(26)马克西姆·高尔基《乏味》《独立报》(1907年8月8日)311-312。
(27)核心论文当然是《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于《插画》,Hannah Arendt编辑,Harry Zohn翻译,纽约:Schocken Books,1969)以及两篇论述波德莱尔的论文(载于查尔斯·波德莱尔著《高度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Harry Zohn翻译,伦敦:NLB,1973)。我对本雅明著述的理解主要受到米莲姆汉森重量级别的论文《本雅明,电影和体验:技术土壤下的蓝花》,载于《新德国批评40》(1987年冬季号)。这篇论文以及汉森接下来讨论美国默片《巴别塔和巴比伦》的观众,给我的这篇论文提供了关键的背景。她的影像很有说服力。我认为我的观点都是同她的谈话讨论里发展出来的,没有她的启发不可能会有最后这篇文稿。我还得感谢她对论文草稿阶段的评论。(有关本雅明,参见这个版本,第731-751页)。
(28)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分心娱乐的仪式》,载于《新德国批评40》(1987年冬季号)。我得提及Heide Schlpmann对于克拉考尔早期电影理论鞭辟入里的论文《电影现象学: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写作》(司样的话题)对我的帮助以及在涉及魏玛电影理论的专刊上由Thomas Elsaesser,Patrice Petro,和Sabine Hake等人提交的论文所包含的对克拉考尔极具价值的讨论。
(29)克拉考尔,出处同上,第94页。
(30)同上。
(31)同上,第92页。
(32)同上,第96页。
(33)同上,第93页。
(34)施伊费尔布什著《火车旅行》第156-157页。
(35)米莲姆·汉森著《本雅明,电影》第184页。林恩·柯比注意到了被设计的铁路撞击影像的普受欢迎:“基于一种快感叠加惊恐的感受,在技术上安排某种被摧毁的奇观,‘想象出来的灾难’说明了现代观众需要暴力奇观的各种类型以及如何把‘震惊’转化为观众热切期待,并且可以接受的奇观”(柯比,引自《插画》第120页)。
(36)克拉考尔《娱乐的形式》第96页。
(37)米莲姆·汉森著《本雅明,电影》第210-211页。
标签:视觉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神话论文; 火车到站论文; 剧院论文; 电影放映论文; 法国电影论文; 纪录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