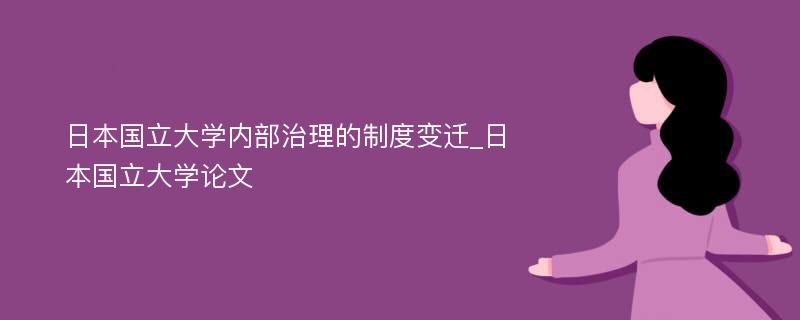
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国立大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10)09-0077-05
大学内部治理是指大学内部的主体在大学内部事务决策中的权力关系,即校长、理事会(日本为评议会)、教授会等内部主体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及其有效的制度安排。
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从1877年创立第一所近代大学以来,已经历了“二战”前、“二战”后及法人化后3个主要发展阶段。本文将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置于历史的范畴,以各历史阶段的大学内部主体为分析主线,从大学法律和惯例两个视角分析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各主体的权力。
一、“二战”前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二战”前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是通过大学初创时期的东京大学时期、帝国大学时期与帝国大学扩大时期等3个阶段形成。“二战”前日本不使用“国立大学”一词,因此,本文分析“二战”前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时,主要以国家设立的综合大学为对象。
(一)东京大学时期的国立大学内部治理(1877~1885)
1877年,日本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创立了东京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具有西方大学制度特征的综合大学。这一时期东京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特点是在医学部和法理文学部各自设置了相当于西方大学校长职务的“综理”一职,两个“综理”各自管理所属学部。根据1878年5月10日文部省颁布的《东京大学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职务编制及事务章程》以及《东京大学医学部职务编制及事务章程》的规定,综理统管大学本部、预备门及植物园的事务及其所属教职员。综理在教职员人事、学科课程、房屋建设和维修、工资等很多大学事务上,具有向文部大臣书面申请权及自主决定权。
1881年,日本改革了东京大学管理制度,颁布了《东京大学职务编制》,设置了统一管理大学的职务——总理。总理在教职员人事上仍然拥有向文部卿书面申请及自我决定的权限。
东京大学初创时期,东京大学内部尚未设置校级和学部的审议机构。直到1881年8月20日颁布《东京大学事务章程的增补》后,东京大学才设置了咨询会。东京大学咨询会分为总会和部会,各自接受总长和学部长的咨询,审议大学及学部的学科课程方面的事情。多数学者认为,东京大学咨询会的总会和部会是日本国立大学评议会及学部教授会的雏形。
(二)帝国大学时期的大学内部治理(1886~1895)
这一时期对大学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文部大臣森有礼和井上毅。1886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在其国家主义教育理念下,颁布了第一部综合性大学法律——《帝国大学令》,将东京大学改称为帝国大学,把学部改称为分科大学。1893年,井上毅担任文部大臣后修改了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至此“二战”前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法律基本形成。
1.校长权力
《帝国大学令》颁布后,总长在帝国大学内部的权力扩大。首先是总长在帝国大学内部的官职等级提高,帝国大学中只有总长一人是勅任官,分科大学长及教头、教授都是奏任官。其次,总长的权力范围扩大。《帝国大学令》规定:“帝国大学总长秉承文部大臣之命,总辖帝国大学”、“保持帝国大学的秩序”,意味着大学院和5个分科大学都由总长来管理。不过,《帝国大学令》颁布后,帝国大学总长失去了教职员人事上的权力。1893年井上毅文部大臣时期,颁布了《帝国大学官制》,重新规定总长在教职员人事上的书面汇报权和自主决定权。
2.评议会权力
《帝国大学令》规定,帝国大学或者文部省可酌情设立评议会,承认了评议会的法律地位。评议会主要审议学科课程、大学院及分科大学等利益事项。总长担任评议会议长,评议官是文部大臣从各分科教授中特定2人。这一时期,评议会的性质是文部大臣及总长的咨询机构,文部大臣选拔和任命评议官,没有总会与部会之分,很难反映教授们的意见。
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评议会的审议事项更加明确和具体化,包括:学科设置及废止、大学规则制定、学位授予、接受文部大臣及总长的咨询等。评议官由校长、分科大学长及各分科大学教授组成。分科大学教授担任评议官时,采用各分科大学内部选举的方式,从而削弱了文部省在评议会中的权力,初步确立评议会合议制机构的性质。
3.分科大学教授会权力
颁布《帝国大学令》后,设置了校级审议机构——评议会,但并未提及学部层次的审议机构。不过,“在井上毅文教政策之前,分科大学已经存在名称为‘教授会’的管理机构,负责召开分科大学管理事项的会议”,“分科大学教授会拥有对评议会提出议案的权利,还可在评议会委任下对某种案件进行审议”。[1]分科大学教授会虽不具有最后的决策权限,但是各分科大学有关的事项都事先通过教授们的讨论再提交到评议会。
《帝国大学令》修改后,分科大学教授会获得了法律地位。教授会的审议事项包括:(1)分科大学学科课程;(2)学生考试;(3)审查学位授予资格;(4)其他文部大臣或帝国大学总长咨询的事项。分科大学教授会权力的确立,为以后的教授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帝国大学扩大时期的大学内部治理
1897年,日本设置了京都帝国大学,并将帝国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建立了帝国大学,“二战”结束之前共有7所帝国大学。这一时期帝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法律规定基本没有变化,而“二战”前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是在帝国大学教授们的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运动中确立的。
1905年,东京大学发生了“户水事件”,确立了总长在教授人事权上的书面申请权。1913年,京都帝国大学发生“泽柳事件”,奥田义人文部大臣与法科大学教授会交换了备忘录,承认“在教官任免之际,总长和教授会协商是正当的,并不妨碍其职权的行使”。[2]泽柳总长辞职后,京都帝国大学在校规规定:教师人事要经过教授会审议;总长由校内选举产生;分科大学长由各分科大学投票选举等。此后,东京、东北、九州等帝国大学也制定了基本相同的校规。
至此,日本近代大学建立37年之后,终于建立了学部教授会的人事权,总长、分科大学长以及教师的任免及惩戒等需要经过教授会的审议。虽然,帝国大学教授会的教师人事权和校长选举权只是大学内部的惯例,没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但是为“二战”后确立学部教授会的“由下至上”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战”后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二战”后,美国、日本政府及国立大学在确立国立大学内部治理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美国主张的“理事会构想”及日本政府提出的《大学法试案要纲》等改革案,都由于大学的强烈反对而失败,日本国立大学最终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但通过《学校教育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法律上承认了学部教授会的权力,形成了以学部教授会为中心的由下至上的内部治理模式。
1.校长权力
学校教育法第92条第三项规定:“校长掌管校务,统领所属职员。”此外,根据《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规定,校长在下列事项上,经过管理机构审议后做出最后决定:(1)部局长选考(评议会);(2)教师选考(教授会);(3)校长选举(协议会);(4)学长、职员及部局长停职或休养、校长及部局长的任期等(协议会);(5)教师退休年龄(评议会)等。而校长独立决定的事项只有部局长(学部长以外)的人事及其勤务成绩评定等。
可见,“二战”后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校长权力大大削弱,主要表现为:(1)在大部分大学事务上,校长要经过评议会等校级管理机构的审议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缺少自主决定权;(2)国立大学未设置校长辅助机构。虽然学部长具有辅助校长工作的职能,不过学部长是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是学部利益的代表,因此,很难从全校的利益出发辅助校长工作。
2.评议会的权力
1953年,文部省发布了《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3]规定了评议会的构成、评议员的选任方式、评议会的权限等具体事项。该规则规定,评议会成员包括校长、各学部负责人、各学部的教授(2名)、各附设研究所的负责人。根据评议会的规定,各学部和教养学部的人数可增加到5人,但是限制各附设研究所负责人的人数。评议员根据校长申请,由文部大臣任命。校长担任议长一职,负责召集评议会。此外,评议会权力范围从“二战”前的教学方面扩展到教学和管理等全校事务、审议和决定教师人事、学部组织的设置及废除、预算、学生等诸多事项的方针,一跃成为国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
同时,评议会依然保持着合议制机构的性质。评议会是各学部讨论大学事务的平台,是各学部交流和协调意见的地方。这表现于评议会与学部教授会之间并非上下级关系,而且评议会对某一事项进行审议及决议时,评议会的各学部代表必须将评议会的讨论结果告知学部教授会,并将各学部教授会的意见反馈到评议会。
3.学部教授会的权力
1949年颁布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教师与学部长的选举必须经过所属教授会的审议,学部教授会获得了教师人事和学部长选举上的法律地位。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第59条规定,“为了审议重要事项,大学必须成立教授会”,而并未具体规定哪些事项属于“重要事项”,为教授会权力的无限扩大提供了法律依据。
除了法律规定的权限以外,各国立大学继承了“二战”前的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通过校规等方式实行校长校内选举制度,由各学部的教授、助教授及讲师等选举校长。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继承了“二战”前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进一步扩大学部教授会的权力。不过大学内部治理中学部教授会权力过大以及对评议会的控制,导致校长的执行权经常受到来自学部教授会及评议会的干预,出现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责任体系不明确、管理效率低下、校长权限架空等问题。
三、法人化以后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2003年,文部科学省颁布了《国立大学法人法》,终于结束学部教授会的统治,完成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转变。
(一)决策机构的权力——校长及理事会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变法人化之前学部教授会以及评议会左右校长执行权力的问题,大幅度扩大大学决策中的校长权力,确立校长作为大学最高责任人的地位。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校长除了特定事情外,可根据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的审议结果,进行最终决策。在人事上,校长可在文部科学省规定的人数内直接任命理事会的理事,并且直接任命经营协议会的委员,以及直接任命教育研究评议会的部分委员。
理事会是国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校长和理事组成。为了理事会能够听取校外人士的意见,因此,理事由校内及校外人士组成。在中期目标、预算及决算、重要组织的设置及废除等特定事项上具有决策权力。
(二)审议机构的权力——经营协议会及教育研究评议会
国立大学法人化前,管理事务与教育研究事务相互交叉是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的问题之一。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后,日本根据大学组织的特点将国立大学的业务分为管理和教育研究两方面。经营协议会审议中期计划、中期目标以及预算等事项中有关大学管理的事项,教育研究评议会审议中期计划、中期目标、教师人事、学生等事项中有关大学教育研究方面的事项,实现了教学研究和管理事项分开的制度构想。
(三)监督机构的权力——监事
《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各国立大学法人必须设置两名监事,监事监督和检查国立大学法人的业务。监事由文部科学大臣任命,根据国立大学法人业务和管理状况提出监查报告,如有必要向校长或文部科学大臣提出改善意见。监事的监督和检查工作包括,定期与校长和主要组织的董事交换情报,或直接出席会议,监督和检查大学业务和管理状况。监督和检查结果作为财务报表和决算报告书的意见记载下来,并公开发表。此外,校长和其他具有代表权的董事利益相反时,监事代表国立大学法人。
(四)学部教授会的权力
除了上述国立大学主体的权力以外,《国立大学法人法》并没有对学部教授会的职权进行规定。随着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实施,《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已经不适用于国立大学,其中所规定的学部教授会的教师人事权和学部长选举权等权限也随之消失。不过,学部教授会对国立大学决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各国立大学仍然用校规及惯例的方式保留了大部分学部教授会的权力。比如:(1)学部教授会具有教师人事及学部长选考的权限;(2)校长选举上学部教授会成员占主导;(3)在教育研究评议会的成员中,学部及研究科的负责人和教授占主体,并且由学部和研究科教授会选举本学部和研究科的评议员。
综上所述,法人化改革改变了“二战”前后的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校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权力大幅度加强。但是,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学部教授会自治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转变。即使确立了“从上至下”的大学治理结构,校长等大学行政机构进行决策时仍需要尊重学部教授会的意见,并协调好各部局之间的关系。
四、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以政策及法律为手段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非政府主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改变现有制度。[4]
对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历程进行梳理后发现,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大学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推动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发展。正如范富格特等学者所指“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由中央提供资金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内,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者,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力,或者至少它不能绝对地行使这个权力”,[5]同理,大学的学术权力也不可能在大学内部治理中成为永远的控制者。可见,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学都不可能在大学制度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扮演主角,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以及教育背景的不同,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日本模式
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提出了日本模式的权力结构,认为“日本的权力结构有类似于欧洲和美国模式的要素”。[6]
日本国立大学从诞生到法人化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移植和模仿了不同国家的制度,其中深受德国和美国模式的影响。然而,经历了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交替影响后,国立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分配模式很难简单划归到教授会控制的德国模式还是理事会及校长掌权的美国模式。
比如,2004年的法人化改革是模仿了美国模式,即建立了理事会制度并扩大校长的行政权力。不过在校长选举、教师人事等问题上,学部教授会仍然具有控制权,德国模式依旧发挥影响。可以说,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经过德国与美国制度移植和本国制度创新的反复调整和磨合后,结合了德国与美国大学的特点,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国立大学法人内部治理。
(三)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学部教授会自治的影响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种制度一旦确立,就会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7]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二战”前确立的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在教授等利益团体的斗争下,“二战”后其权限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法人化改革以后,虽然校长和理事会等校级管理机构的权力扩大,不过,传统的学部教授会自治模式仍以学校规章制度以及惯例的方式保留下来。
从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简单梳理中发现,“二战”前形成的学部教授会自治制度对内部治理改革形成了路径依赖,通过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对以后的制度发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