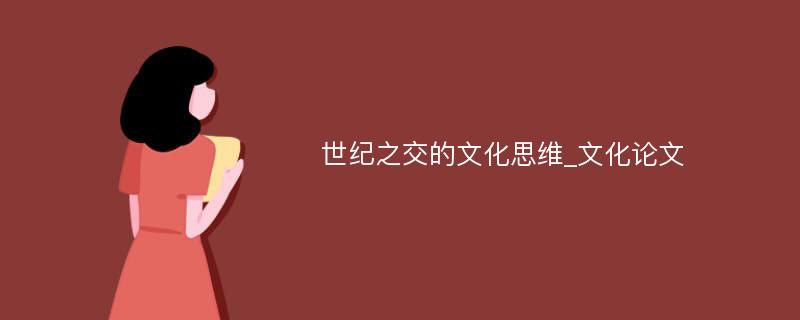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文化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去年5月《中国人可以说不》一书推出不久, “说不”系列很快风靡全国,一时间掀起了一股“说不”热潮,有人认为这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也有人将其视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引人深思的是,这种民族情绪的高涨并非中国独有,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敌对的政治堡垒的瓦解,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渐显剧烈。而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与传播又使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已使世界缩小为一个地球村。在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中,在这个世纪交合的时期,该如何自我调适,既保持民族自尊、把握民族腾飞的机遇,又能在与各民族平等的交流中,共同参与未来人类文明的建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一、摆脱“文化部落主义”的心态
就文化研究而言,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对象首先就有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如完全以西方文化为座标来参照、衡量于东方社会,必然导致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而以为祖宗的东西总是好的,以此来抵制、排斥西方文化,则将陷入一种不合时宜的妄自尊大的夜郎心态之中。
如今“全盘西化”的论调早已为大多数人所摒弃。值得引起警觉的却是近年来打着弘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旗号,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带有封闭排外及简单自保的文化部落主义。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翻版。“这种心态的深层往往是一种观念体系失散、失落后的虚弱和简单保护的抗拒。”〔1〕对于狭隘民族主义所能带来的危害,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早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将泰戈尔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相信无人会提出异议。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爱国主义者清醒地指出:民族主义的概念往往被人利用来推行利己主义,于是“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2〕。而在东方的印度,同样地,“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是多年来印度各种产生麻烦原因中最特殊的情况”。〔3〕
显然,爱国与狭隘民族主义心态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然民族主义的观念总是被人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话语或丑陋或迷人地表现出来。在当今中国的文化界就有这么一些奇怪的现实:要么是怀着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更多的影响;要么是在每一件引进的外来事物上,都要加上一个“我们古已有之”的标签;要么则是当有人使用了几个外来的名词或术语、为几部外国电影叫好时,就另有人痛心地疾呼:我们的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侵略,已被迫充当了宣扬“殖民文化”(或“后殖民文化”)的角色。
这种种对自身文化立场的异常敏感度有其历史及现实的背景。1840年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入侵,我们这个曾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古国,一直饱经内忧外患的种种磨难和艰辛,民族生存的危机感与焦虑情绪笼罩着文化界,国人仇恨外来侵略,产生了强烈地排外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单纯的排外毕竟无力使民族自救自强,忌食并非良策,只会积弱不振。严格说来,“五·四”以前的文化讨论都是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强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本能性反应,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改造行为。〔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哲学成为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导致了人类半个世纪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冷战”的局面。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这种斗争往往还夹杂着民族主义的情感,这使人们很难对其长处和不足做出理性的判断。然而文化与政治,这是两个领域,彼此虽有联系,但更各有其特点和规律。今天,我们更没有必要因政治、经济上曾饱受欺凌而丧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以至怀弓蛇影。
进入80年代,在“寻根”的热潮中,向传统“寻根”是与向西方“求异”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国门顿开,良莠齐进,鱼目混珠,一时难分真伪优劣,对此,有欣喜若狂的,有愤懑不平的,有忧心忡忡的,……而层出不穷的新术语、新理论,又为急于“行动”的学者们提供了文化参预的武器(如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特别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提出,使敏感的东方学者以为:西方以武力征服、经济掠夺开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侵略,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演变,似乎已变成一场文化上的殖民侵略。而由于“后殖民主义”批评所具有的“标语效应”,使人们未能看出“后殖民主义”这一概念事实上是将西方殖民主义提升至历史的正统地位,使之成为历史进程中决定性的标志,而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仅扮演着一种相对于西方的“他者”角色。“换言之,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化样式的标志不是它们实在的独特性,而是它们与线性的欧洲时间的从属性的、回溯性的关系。”〔5 〕这种结论的得出正好与持“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家的初衷相悖。事实上,仅以一个“后”字是很难形成积极的概念去表达一种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的,这姑且不论。我们想强调的不单是以什么样的词语可以准确地替换“后殖民主义”的问题,而是要提倡文化研究的开放度量。须知任何凭借强权政治或经济实力以建立文化中心的做法,都是挟外物以自重,与文化的理念是不相符合的。
二、“和而不同”的启示
观厨师烧菜、乐师演奏,油、盐、酱、醋虽然不同,合在一起才成其为美味佳肴;音乐正因为有清浊、短长、疾徐、哀乐、刚柔之差异,方能相济。于是“不同”成为事物组成、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不同”并非是互不相关,在各种不同因素之间,还必须要有“和”,唯有“和”,才能产生出新事物、才能发展。完全的“同”或相互隔绝的“不同”都是不可能发展的。——这正是《春秋·昭公二十年》中那一则“和而不同”的故事给予我们的文化启示。〔6〕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也成为文化交融、碰撞中的一种准则。这不仅体现在汉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也贯穿于两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之中。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汉民族有过无数次与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以及南方边远部族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记录,如被许多人引以为“国粹”的“京味”文化就有许多满族文化的成分融汇其中。正是有了这种存异而致和的博大胸怀,中华文化才能延续至今,仍充满生机;否则,也早已像有些古老的文明一样成为历史的遗迹了。今天,中华文化虽然不再是单一的汉文化,然而,却无人能否认它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
在此就还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民族文化的问题。从线性的历史发展来看,民族文化可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从文化生成的横切面来看,又可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中,不断有需要抛弃的糟粕,也有已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扎根、与之融为一体的部分;现代文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总之,民族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因为文化毕竟不像汪洋中的一个个孤岛那样相互之间封闭隔离,各民族文化中,既有本民族独特的东西,也有全人类共通的东西;不同文化之间,并非只是敌对与歧视,也能互相取长补短。接受外来影响,是历史的必然,是进步的途径,也是民族气魄的表现。过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被无数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同样,欧洲文化也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各种各样外来文化的因素,1922年,罗素曾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则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尽管如此,欧洲文化不仅未失去其文化传统,而且还大大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涵。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文化交融的现代实例:自从甲壳虫乐队将印度西塔弦琴的音乐和节奏与摇滚乐结合以来,世界流行音乐就逐渐增添了来自西方以外的乐器和风格。目前,一支美国的爵士乐队——杜阿乐队(Doah)正极好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在演奏会上,这个五人乐队经常轮流使用70种以上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乐器。除了传统的爵士乐器,如吉他,钢琴、萨克斯和鼓以外,还有中国的月琴、印度的班西里短笛、玻利维亚的沙兰戈、喀麦隆的摇荡器、西非的巴洛丰等等。其音乐虽是以现代美国爵士乐为基础,却与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南美洲以及东方的旋律融治共鸣。一位评论家称这是一种“肯定生命”的风格。在他们1990年的唱片《世界之舞》(World Dance)中收录了6首歌曲,其中3 首取自《大同世界交响曲》中的乐章。 这张唱片表明这种“世界音乐”经过15年的稳步发展已臻成熟。在谈到灵感的来源时,乐队领队阿姆斯朗(Mr·Armstrong )先生说:“……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与极为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而当我们学会怎样放弃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时,就会发觉被带进了人类所创造的千百种乐器所演奏出的多彩声音的美妙世界里。”〔7〕
考察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这种“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发展规律恰好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原则。
时代的发展,使我们确信:中国已经打开的国门不会再关上。那么在面对异质文化时,除了采取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或对西方价值体系简单认同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立场呢?回答是肯定的。特别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语境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完全地“自力更生”。由于文化研究涉及各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异同及规律,如果研究者的眼界不高,受其乡土感情的支配,带有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情绪,势必不能客观地面对现实,更会影响到其理论的归纳及结论的偏颇。因此在文化研究中,要力图避免单一实体的特殊性被绝对化的倾向和传统的静态实体研究所暗含的排他性,摆脱纠缠于“我们在使用谁的话语来讨论东方问题”的不平,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走出东西方对抗的模式,将亚洲和西方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之中,所研究的对象也不要仅仅局限于某种固有文化的特质,而更多地关注于多种异质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或抵触时所形成的系统。事实上,“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8〕
三、“地球一村、人类一家”
如果说正是对“和而不同”准则的实践,曾使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9〕;然在这个东西方空前接触的时代,这种“和而不同”的原则却因其自身的局限,难以推而广之。其最大的症结在于这一准则中所包含的差别心:“和而不同”历来被视为是一种君子的行为准则,故而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由此这种“和”势必带有在君临他者时所表现出的优越感,而这种“泱泱大国”的“汉唐心态”,今天势必影响到国家间及民族间的交流与往来,面对异质文化时,难以“承认他们的文化也具有与本文化同等的重要意义”〔10〕。
而在世纪之交,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由于交通、通讯等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各民族、各国家彼此贴近;另一方面,民族间频繁的互动,也强化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自尊。而民族文化意识的自我强化,亦会强化彼此间的差异性,由此,世界性的文化冲突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虽是一种夸大的文化冲突论,但也起到了警示人们的作用。因而,达成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与理解,找出一条多元文化共存共繁共同发展的途径就显得越发重要。
因此,作为文化人、作为研究文化的当今中国学者,我们既不能再重复过去的论调、固守“文化部落主义”的保守心态,也“应当超越中国历史上的那种‘汉唐心态’,拥有一种比汉唐时代的人们更为宽广的博大胸怀”〔11〕。面对一个互补互适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真正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来探求共同的文化建构。这种话语应是既非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在新的环境中面对新的共同的问题去共同摆脱困难、共同提出希望。
20世纪是一个剧变、动荡的时代,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多方面突破、物质文明得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核恐怖的巨大威胁及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的精神空虚与贫乏。“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12〕“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13〕在时代的脚步正迈向21世纪的今天,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并非是哪一个政体可以生存下去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是指向人类整体的。我们是否适应生存?我们是否适应在地球上生存?我们是否能团结合力来辖制那因我们自己的愚昧而导致的迫在眉睫的毁灭性狂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确定我们族类——人类——的未来。”〔14〕
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东西方人本是同一的,“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5〕,在根本上彼此应当有相通、相一致的地方。而当今世界也不再允许西方文明的单独发展或东方文明的孤立存在,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东西方文明都必将走向调和。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化从地区化走向世界化,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走向。当然,“世界化”并非意味着平板化、单一化,而是一种“多样性之统一”。未来的世界应是一个多姿多彩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各民族都将分别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对人类共有的价值原则共同负责、共同做出贡献。“多样性之统一”的思想可看做是对过去“和而不同”传统的一个现代阐释与发展。“和”是在对“人类一体”认识上的统一,“不同”则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这种“和”应是超时空、超事物的,它真正超越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政治、经济、民族意识等各种事物,而对人类所面临的那些共同及永恒问题作出一致应对。这种关于“统一”的概念,并不是要求大家千篇一律、一模一样,而是差异性包含在其中。我们欢迎多样化,并深信多样化能够提供新思想、新契机,推动文明的进步。在此可将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喻为同一个花园里千姿百态的花朵。只有当花儿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色彩时,花园才是最美丽的。
“多样性之统一”的思想怀抱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接受多元,另一方面坚持通过磋商来取得共识,它既没有忽视、也没有试图隐瞒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艺术语言、思想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然它呼唤更广泛的忠诚、更博大的抱负——超越于任何曾经激励人类的忠诚和抱负。它既否认过度的集权,又排斥一律化的企图。这是一种对立统一,而非简单的同一,正是其内在的多元性才使得团结一体性有别于同样性或单一性。恰如五味不同,才能组成一桌丰盛的宴席;五音相异,方可构成一篇美妙的乐章。
我们切不可将这种“多样性之统一”的思想仅看做是一种幼稚的激情主义的抒发,或是对一种虔诚希望的模糊表达,甚至也不只是对一种理想的阐述。它意味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它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挑战,它是人类在经过自身存在的无数次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是对人类未来文明图景的总体设想,它将在人类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若以个体生命的成长规律来比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如同一个人必然经过其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而进入成熟期一样。人类社会组织也从最初的血缘家庭,逐步经历了氏族部落、各种形式的城邦直至民族国家的崛起,未来将以地球为单位形成宇宙间的一个基本构成。在这部伟大的演进史中,今日人类正在从它的青春期向其集体成熟期过渡,而人类文明成熟期的标志即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人类本一家,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注释:
〔1〕郝建:《义和团病的呻吟》,载《读书》1996年第3期。
〔2〕(印度)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
〔3〕(印度)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第59页。
〔4〕参见张文建《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融贯说》,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11期。
〔5 〕(美)安·麦克林托夫:《进步之天使:“后殖民主义”的迷误》,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5期。
〔6〕《春秋经传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3页,“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由此引出晏婴关于“和”与“同”的一大篇议论。
〔7〕《引人反省的世界音乐节奏与音乐融合为一》, 载《天下一家》(《One Country》,New York,No 12.1990)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9〕《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10〕(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9页。
〔11〕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断想》,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期。
〔12〕〔1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页,中文版序言,第3页。
〔14〕(美)圣巴布·贝克:《树木人》,(RichardSt.Barbe Baker《Man of the Tree》,California,June,1991,P1)。
〔15〕《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