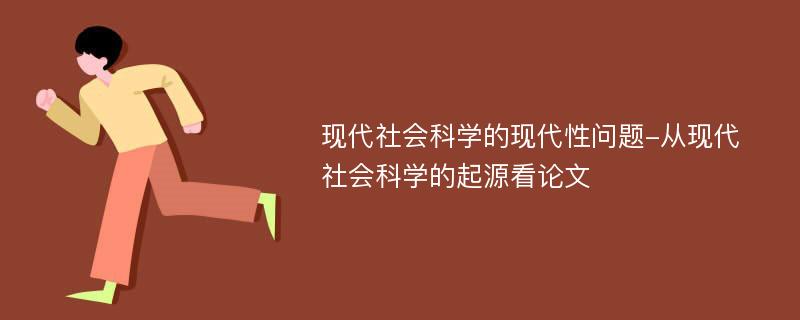
哲学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问题
——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看
崔延强,卫苗苗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自其诞生即裹挟着相应的现代性风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牛顿新物理学的建立将理性主义推到了众人崇拜的地位,现代社会科学中多数学科的建构、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围也都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崇尚理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历时态看现代社会科学的这些特征是在批判传统或古典学术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进步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审视当前,全球化语境下社会科学的现代性症结日渐凸显,成为约束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层力量。今日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超越自身的现代性困境,消解由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等带来的偏狭性,摆脱民族性与国家性的“挟持”,改变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立场。
关键词: 现代社会科学; 理性主义原则; 民族国家; 实证主义; 现代性
从起源来看,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建立,与西方世界的历史、国情以及知识背景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与工具理性、欧洲中心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交融共生。事实上,我们在承认现代社会科学客观价值的同时,也难逃对其“偏狭性”的诘难。社会科学在真理追求上要打破有形或无形的疆界、文化或心理的束缚,建立以“人类知识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体系,消解现代社会科学自身的现代性风险。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出发了解其现代性问题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研究进路,也是探寻中国社会科学超越其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基础。
一、 社会科学概念之起源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有时与“人的科学”“人文科学”等交替使用。在现代社会科学起源初期,“文科”(arts)、“人文科学”(humanities)、“文学或美文学”(belles-ettres)、“哲学”(philosophy)、 “道德科学”“道德与政治科学”“行为科学”“文化”等许多称谓都曾是社会科学的名称和不同叫法。[1]7;[2]《导论》1在20世纪之前的德国,“社会科学”一直被翻译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根据德语直译为“关于精神或心灵问题的知识”,“Geist”可以译为英语的精神(spirit)或思想(mind),“Wissenschaft”一词则是表示系统知识的一般性术语。
(2)地下水的径流。地表水通过岩体风化网状裂隙及节理裂隙缓慢下渗,并逐步汇聚到F1、F2断裂带中,再沿F1、F2断裂带渗流,并以地下水为载体,在长距离的运移过程中吸收周围岩石骨架中的热能及矿物质,形成载热流体赋存于F1、F2断裂带中。F2断裂在深部被F1所阻后,地热水沿F1断裂带上涌,在地势低洼处排泄形成温泉。
而“社会科学”这一概念通常被认为是18世纪90年代由以孔多塞(Condorcet)为主的学术圈创造的,随后传播到英格兰、苏格兰和德语国家。[3]3事实上,“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起源于法语“la science sociale”,最早出现在法国西哀耶斯(Emmanuel AbbeSi-eyes)1789年1月所发表的一本名为《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小册子中。[4]656此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名称不断被更换,直到“大革命”之后的1795年,法国设立了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该学院设立了包括6个组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部”,其中第3组称作“社会科学与立法”,“社会科学”这个术语至此才获得一种保持至今的新的意义,亦即演变为可以预估和干预社会变革的现代社会学科系统。
York R等将Ehrlich P R的IPAT模型和Waggoner P E的ImPACT模型的恒等式转化成一个包含多个自变量的随机回归的非线性STIRPAT模型,用于揭示人口、财富和技术三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14-16]。目前,STIRPAT模型在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应用广泛且较为成熟。王立猛、李琦、姜磊等探索了人口数量、富裕度和技术因素对能源消费总量的驱动作用。[17-19]本文应分析需要,拓展STIRPAT模型自变量,将技术因素(T)分解成能源消费强度T1和产业结构T2,式(2)为扩展后的模型公式:
“社会科学”术语的变化是一种双重过程:一方面社会科学从早期的“自然法”与“道德哲学”等一般性研究框架转向更具体、更“科学”的框架(如经济学、人类学、社会数学等等),体现了一种智识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道德和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科学”等作为新的术语出现并作为那些具体学科的共同名称存在,体现的是制度化的进程。这种双重过程标志着社会科学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的智识场域存在并区别于一般化的社会学知识。一方面,社会科学从普遍性的智识工作开始转向更专业的、制度化的学科构建;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更具共性的学科名称表明了其有别于一般智识场域的学科独立性。[3]3
二、 新权威下的理性主义原则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表示,两组间比较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Dunnett-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这些语汇,阐述了浙南商业文化产生的原因,进而概括了浙南商业文化的特点,最后总结温州人的商业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大量的语汇反映、折射出来的。
(一) 知识世界权威的转移
其次,就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特殊的界域意义而言,它具有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分析依据的必然性。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圈定了空间界限,使民族国家具有了实在的界域。在此之前,地理的边界并不对部族或者以狩猎、农耕为合作的群体造成真正的影响。吉登斯认为,“实际上没有一个前现代社会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有如此明确的界域。农业文明曾经有过‘边界’(frontiers)——这是地理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而在通常情况下,较小的农林社区和狩猎及采集的社会逐渐地渗透和进入周围的其他群体,它们不具有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那种意义上的边界”。[10]12
牛顿力学的出现,打破了知识世界原有的权威结构,对经院哲学以及教会对知识的绝对掌控造成了威胁。起先,中世纪的知识权力掌握在教会手中,知识阶层基本上是教士阶层,知识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由于宗教的特殊影响,直到15世纪,才有学者开始对经院哲学发起批判。对于17世纪的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来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废黜经院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即神学。而此时,牛顿物理学说的出现对传统神学以及教会执掌下的知识世界来说是致命的。“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天上的星球,从而昭示了一种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的存在,整个思想界不禁为之亢奋。人们由此发现,原来整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界,不过是一个按照某种法则运转的巨大的机械装置,而其中并没有上帝的地盘。于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5]528牛顿的物理学理论成功地使理性代替上帝接管了自然世界,新的自然科学取代了传统守旧的、宗教性的知识权威。社会科学因此获得了对生活世界变革的预报与干预的可能性。“他们宣称,自然科学的任何内容,和那些在18世纪将成为‘人的科学’研究的内容,仅能基于直接经验来理解。对这些事情,无论上帝或是神学家们,都没有发言权。”意大利法学家阿尔贝里克·贞体利(Alberico Gentili)甚至说:“神学家,别多管闲事。”[6]32
现代“社会科学”从一个简单术语到一个具有完整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学科系统,经历了艰难的蜕变。特殊的时间、空间以及历史、政治背景使现代社会科学自滥觞伊始就隐含许多现代性问题。“理性主义原则”就是极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也是其现代性其他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罗伯特·沃克勒(Robert Wokler)看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较短的时间跨度内存在一个认识断裂(epistemic break),这个断裂正是形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契机,使新的话语模式最终取代了旧的话语模式。[3]12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与自然知识就已经开始替代旧神,启蒙运动让大自然(the Nature)作为新神登临神坛,科学的合法化也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与神父。原则上,一切事物都可以纳入客观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且这种可知是真实可靠的。真善美,是和应是,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7]69;[8]92
所谓节奏管理,是指在建设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对工程项目中各项事务进行合理、有序的管控,定出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如科学、合理地设计施工流程、各环节操作时间及交竣工期限等问题,使其施工按照统一的节奏进行,利于项目的顺利完成。
(二) 现代社会科学的两种前进路径
当自然科学成为知识权威之后,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便来源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然科学相关,即包含了多少自然科学的特征、概念、定律以及理论。新的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寻求到两种前进路径:一种是牛顿式的物理机制,一种是哈维式的有机机制。人们认为,在牛顿与哈维所倡导的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中一定存在着一种共通的方法可以将社会科学向前推进。
1. 牛顿式的物理机制:新物理学与社会物理学
牛顿的新物理学理论开启了自然科学接管知识权威的开端,是科学性、客观性与权威性的代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开始效仿牛顿物理学,试图在新物理学中寻求科学性的庇护。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有效地预报以及合理地组织。因此,为了得出精确结论,现代社会科学必须具有牢固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宗旨下,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以牛顿物理学为效仿的楷模。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社会学前身的“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为了终结法国自大革命之后陷入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孔德选择重提曾经一度放弃的概念——“社会物理学”,从而在新的权威力量下解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系统性败坏”的局面。直到1955年美国仍在使用这一术语。当时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在不损害自身“科学性”的前提下为社会科学提供发展的必要资助,委婉地以“社会—物理学”(socio-physical sciences)这个中性名称在物理学分支下设置了一个实质为社会科学的小组。[9]15除此之外,经济学家瓦尔拉为了让自己的经济学得到认可,提出了在形式上类似于理论力学的方程,借此表明他的学说是“科学的”“精准的”。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则尝试将微积分引入经济学,暗示它们运用同一种数学原理处理研究问题,他甚至将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与物理学中的“能量”概念等同起来。[9]3-4社会学家凯里(Henry C.Carry)所提出的一般社会引力原则的推论“人必然倾向于受其同胞的吸引”便是同源于牛顿力学定律。贝克莱同样断言人的精神或心灵存在一种吸引力原则,并将社会看作是牛顿物质宇宙的类比物。这一切都是社会科学家在利用自然科学为自己的学科寻求庇护。
首先从理念来讲,由于受人类自身对表象世界认知的有限性的影响,实证主义所期望的“客观性”从根本上难以达成。为了无限接近、达到“客观”,现代社会科学家将“一手的”经验材料视为重要的保障基础。他们热衷于收集未经前人涉及的原始的经验材料,并尽可能地收集最大数量的测量数据与定性材料,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主观性的嫌疑。但是这种客观性是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的,因为“一切数据都是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选择要以某一时代的世界观或理论模式为基础,要受到特定群体所持立场的过滤” 。[1]98正如福柯所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人的实证性所是与存在所是之间的一种延伸,研究者只能在表象空间中开展一种具有有限性分析的科学活动。换句话说,研究者可以以探究客观性为初衷开展研究,却难以摆脱社会科学在人类自身认识下的表象空间的结构有限性。[12]357-369在此意义上,研究对象和数据的选择都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随着人类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的。
很多企业的会计部门已安装了自动化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只需在计算机中输入指令,结果就会自动产生。但职业学校会计专业没有及时掌握外界信息,会计教师没有及时更新教学方式,仍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这就导致学生学而无用,浪费时间。
现代社会科学对生理学以及生物学的模仿是社会有机论的主要来源。如果说对牛顿物理学的模仿来自于对科学理论、理性主义的认同与利用,那么对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模仿就是对直接经验客观性的肯定与崇拜。对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模仿是将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推向实证科学的基础。正如利林菲尔德(Paulvon Lilienfeld)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像自然有机体一样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有把人类社会构想成一个活的、像自然界中的个体生物那样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社会学才具有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基础。[9]91-92在有机论的理论下,人类社会作为自然世界的另一种“物种”存在,才能够符合 “科学性”的基础,才能够适用于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例如哈林顿模仿哈维解剖学所建立了政治解剖学。哈林顿从解剖学与血液循环理论中看到了自然世界秩序的力量,其著作《大洋国》不但表现出对直接经验的认可,而且将政治学与解剖学进行结合与类比,他强调“自己的工作是一种‘政治解剖学’”。[9]175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政治学家也必定如同一个好的解剖学家一般了解政治机构的内部构造并能合理安排这些职能“器官”。他认为,政府就应当像一个完整的人体一般包含有肌肉、神经、动脉以及骨骼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共和国的任何功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9]176在哈林顿看来,阐明一种政治学说就像是一场学术解剖,健康的政治所应该具有的“器官”与“组织”都将通过学术解剖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场学术解剖虽然与生物解剖的对象不同,但二者皆是建立在“自然原理”之上进行的。换句话说,哈林顿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不但有自己的运行原理且这种原理是一种“自然的原理”。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开始选择接近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首先,面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要求,现代社会科学必须确定一个确切的研究范围。早期的现代社会科学将研究对象圈定在生活世界的表象世界,但过于宽泛的世界范围会让它陷入当时饱受诟病的思辨哲学的范畴中。因此,它所面对的生活世界或表象世界亦需要一个圈定范围。新的社会科学“既不注重研究普遍规律,也不一味强调个别性,而是去探寻制约着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系统的种种规则”[1]19。日耳曼地区在这种意义上还建立了“国家学”,主要包括经济史、法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混合知识,强调不同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同时,由于现代国家亟需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需要通过对社会改革进行合理的组织,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良好机会。因此,18世纪晚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可见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并不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盲目崇拜,而是对“理性”与“经验”及其方法的信任。这种模仿本质上来源于理念的相似与融合,是各学科对自然原理的合理寻求。因此,这种模仿仅仅是为了对陈旧权威的否定,不屈于“古人的权威”,但并不能说明自然科学在知识世界中具有绝对地位,只能证明在人们眼中“自然”才是永恒至上的权威与法则。正如哈维所说:“‘自然的行为……不在乎任何意见或任何古代’,‘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然更古老或具有更大的权威性’。”[9]188
(三) “技术统治理性”下的现代社会科学
现代社会科学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模仿并未给社会科学带来期望中的科学性与恒久性,反倒是体现了来源于自然科学的技术统治理性(technocratic rationality)。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展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悖论——社会科学所模仿的自然科学对其发展而言并无过多影响:曾经看起来十分具有科学性、精准性的有机论社会学在今日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仍具有效性与可信性,也不乏荒谬可笑之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因不理解自己所模仿的科学而备受批评,但他们的部分思想还是留存下来并仍然对今天的相关学科产生着影响;同时,今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已经重构了物理学,却对倚靠经典物理学的经济学没有产生颠覆性影响;与此相比较,如今的生物学更好地继承了19世纪的理论,无需重大修正与改动,然而与之相关的部分社会学却没有因此而受益。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被模仿科学的正确性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科学的恒久价值之间似乎并无内在关联。[9]5对科学的盲目模仿本质上都是现代社会科学中技术统治理性的表现。
技术统治理性是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形态,其许多方面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进步是社会斗争的结果,而社会斗争要遵循优胜劣败的规律;因此,干扰社会斗争便是在干扰社会进步。”[1]93所以,任何不适用于“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模式的概念都被取消,任何不具备直接功利性的制度都失去了合法性。[1]93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引入以及对精准性、科学性的强调,更像是技艺的引入和展现,是对源自于外界对其合法性质疑的一种有效回应。但是,从根本上社会科学究竟有没有必要这样做?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回应有关“他将数学热力学的技巧引入经济学是为了夸大经济学的科学有效性”的质疑时,这样说道:“这种数学偏离影响了声誉,而不是提高了声誉”。[9]21由此看来,社会科学学者的如此做法更多地是需要得到学科共同体的认同,即不违反既定的技术标准。
因此,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以及概念类比、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概念转移”。随着某特定概念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新的概念在转移的过程中以“重组”的方式创生。这种过程本质上并不是简单的语词借用而是技术统治理性转移,新的概念借由原有概念的“理性”获得重组的生命。
三、 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欧洲中心主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各国学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问题愈演愈烈并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超越现代性已成燃眉之急。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在非西方世界中“本土化理论”与“本土化研究”逐渐成为其社会科学研究主流方向,但本土化研究进展时常受阻——许多社会科学现有理论与本土研究问题不兼容的情况层出不穷。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学术体系中所产生的弊端。这种弊端是由于现代社会科学起源的特殊性与当今社会快速发展步调的不能耦合性所引发的。众所周知,一种理论之所以受到推崇是由于它适合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19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理论亦是如此。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例,由于19世纪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西方在技术和政治上的优越性,中国为了振兴民族、富强国家,便开始引进“西学”,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标准。但是,简单地借用理论,只能解决早期的、初级的、一般的问题,如今这一理论框架的现代性问题逐日凸显且并不能契合当今复杂多变的研究环境与问题。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问题本身就制约着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建构与发展,这直接导致了现代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知识创造与生产上存在着理论基础的不平衡。因此,与其说如今各国是专注于适合本国的“本土化的理论”,倒不如说这些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为了拮抗现代社会科学中所表现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等问题。但归根结底,本土化研究只是一种针对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的妥协性、被动性解决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为了促使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超越现代性已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一) 建基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科学框架
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和国家性体现于它将民族和国家作为分析的框架依据。在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中,民族国家是各学科研究的背景起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分析的任何问题皆处于这个框架之下,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当然这也与其起源时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国家的性质密切相关。
基于数据驱动深度学习方法的无线信道均衡 ………………………………………… 杨,李扬,周明拓 24-2-25
不止是哈林顿,阿尔伯特·舍夫勒(Albert E. Schaffle)也将人体和社会体进行了广泛类比。例如,把核心家庭比做基本细胞,把警察局比做表皮防护组织。[2]288一些社会学家从菲尔绍(Rudolf 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中获得灵感,将社会理论与细胞学说结合起来。“基于当时的生物学发展(比如细胞学说、劳动分工的生物学概念、正常与病态的医学概念、‘内环境’的生理学等),这些社会学家尤其是利林菲尔德、舍夫勒、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沃尔姆斯(Rene Worms)等,利用这种联系构建了一种社会学。他们甚至还做了一点生物学讲解,以表明他们的观念与当时顶尖的生物学家是一致的。”[9]4
在19世纪初的欧洲,知识世界的权威发生了一次重大转移,它摆脱了传统宗教信仰的桎梏,完成了从教会掌控到自然科学管理的过程。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近乎两个世纪的对抗最终以现代自然科学占据完全优势而终止。至此之后,“科学”一词等同于“自然科学”,“实验”与“理性”成了科学的代名词,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模仿“自然科学”的理性之路。
最后,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国家权力成为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主要力量。现代社会科学家给予人们这样一种认识:只要提供足够的具有确定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就会在不断的改造与改革中获得进步。并且人们相信这个“进步”过程确实需要“颁授权力的”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民族国家是“进步”信念的实际操办者,其强力是推动整个“进步”过程的有力推手。因此,民族国家边界被看成是构成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骨架。[1]88
The authors thank a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育龄期是指15~50岁的妇女,该年龄段女性具有生育能力,育龄期妇女身体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人类繁衍及人口出生质量,对社会及家庭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2]。及时了解育龄期妇女死亡原因,减少育龄期妇女死亡率是目前妇女保健的工作重点。为此,本研究对2015年1月—2017年12月的606例育龄期死亡妇女的年龄、死亡原因等实施了回顾性分析,现进行总结:
(二) 欧洲中心主义原则形成
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论断乃至学科本身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强调所谓“普遍规律研究”的同时,嵌入了实则带有“偏狭性”的论断以及学科理念。这些论断与学科理念以欧洲为中心,强调西方与非西方地区之间的区别。这种带有“偏狭性”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判断绝不是学者由于审视角度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事实上它奠基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科学框架。包括“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早期任务主要是协助欧洲民族国家开展殖民活动。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5个地区。[1]15众多的“研究主题”和“学科”名称也是在此时提出的,其中,人类学、东方学、地理学以及考古学等学科都与近现代欧洲针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殖民活动不可分割。
首先,这些学科最初的主要任务是为殖民的宗主国提供大量的殖民地资料。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民族的征服与殖民。由于许多民族都是以小群体形式存在的,军事力量薄弱,没有书写系统甚至没用共通的语言与宗教,作为殖民者的欧洲国家为了方便了解与统治他们,开始建立人类学(anthrothology),并以肤色定义或以其他偏狭的基因理论划分人种。例如,布丰的《动物博物学》(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提出一种激进的人类学学说。他在赞同人类是单一的基因起源的基础上,强调人类起源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其他种族则是在离开起源地之后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11]392欧洲征服者将殖民地当做了各种研究的场所以及数据来源。[2]410在欧洲探险家以及人类学家相继“发现”新的大陆以及陌生的民族之时,对人体测量的研究、对社会的民族志调查以及对江河湖海、山川、矿脉的了解与测绘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些工作是与确立整治区域、绘制地图以及对殖民地臣民人口进行的研究紧密联系的。[2]410考古学、地理学乃至语言学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为欧洲的殖民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部分学科在宗教文化与殖民政策的传播中担任重要角色。除了初步的人种分类与信息搜集,人类学与东方学还在殖民活动中担任了传播宗教与政策的重要角色。东方学最早发端于教会,初衷是传道福音,在宗教方面对殖民地民族进行精神的征服与统一。在文化输出与政策输出方面,人类学家也适时地扮演了传道士的角色。同时,人类学早期研究对象多以欧洲殖民地的民族为主,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围绕实地调查开展研究工作并且以介入式的观察方法参与到这些民族的生活当中。但是这种方法往往会背离科学要求的中立原则,因为研究者总是不自觉地担当起欧洲征服者与这些民族之间的调解人,这无形中对殖民政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1]23
最后,地理学为国家疆域调查与殖民地扩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地理学虽然试图依其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学科,但仍然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尽管它十分强调环境的影响,但它在某些地方所做的实际上是与人类学家相似的工作。”[1]27地理学不但在提高国家领土价值及其帝国的重要地位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而且也关乎着国境内领土的完整以及对殖民地的划分。因此,“在某些1870年之后的分析中,法国人得出结论说,他们之所以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地理学,而且西班牙人在1989年失去他们的最后一块美洲殖民地之后,也以同样痛苦的评价做出反应。”[2]333正是地理学展现了“空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创造了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空间观念。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也是以国家为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1]28
四、 “客观主义”色彩的实证主义
实证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从19世纪形成并沿袭至今的学术传统。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家开始倡导实证主义,将实证研究与客观性、科学性相联系甚至划等号。他们尝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成分引入社会科学,以经验观察以及数据作为主要证据支持,并尽可能地避免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个人“主观的”见解。但事实上,即使排除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与个人偏见所造成的主观影响,这种实证主义也很难使现代社会科学达到理论上的客观性。
2. 哈维式的有机机制:新生理学与政治解剖学
其次从历史起源来讲,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与实证主义密切相关的“社会调查”与“数据统计”的客观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来源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t)在很大程度上是孔德为了撇清社会学与其前身的渊源关系而提出的。19世纪下半叶,社会学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前,是以社会改革协会的形式存在的。其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通过将社会改革者的工作转移到校园从而让他们放弃针对立法进行的游说活动。但是为了确保社会学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学科就必须割断这种渊源关系。于是,孔德开始培养社会学家的实证主义信仰,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具有普遍、科学的意义的。实证主义的提出正是为了将社会学从普通的社会组织推入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其自身早期仅仅是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的。[1]20
另外,早期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迫使英国的政府机构和专业机构所支持的统计学与社会调查兴盛起来。一时间,社会学家的著作几乎都是由数字组成,统计学的价值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此时,有关社会与人口的数据统计开始成为主流且许多复杂的分析方法也得以创建。布莱恩(Eric Brian)在《18世纪的政府管理者和测量员(1994年)》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国家的测量》对统计学何以兴盛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追溯了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一是概率分析理论、微积分学说的发展,二是有关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数据统计的政治需求的增长。他从中得出结论,过往几十年的政府改革工作与如今社会科学对数据统计的崇尚有很大关系,与社会科学从旧时的“道德政治哲学”至今日的转变也密切相关。只有在法国18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期间智识演变、制度变化以及宏观社会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下才能理解这种发展变化。[3]18
事实上,统计学的建立最初可以追溯到1328年法国的人口普查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受到18世纪晚期统计新方法的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建立以及法国革命后“公开统计数据”的决定的影响发展为现代统计学。在法国的旧制度下,公务员需要参与到实证调查之中,为的是提供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指导有关国家事务的决策。这种实证调查对政府制定有关征兵、税率、关税等事务有着重要的意义。除了将这些数据大量引入政府报告,他们还将特殊问题的数据进行精细的二次分析,并将结果发表在统计或大众期刊上。正如瓦格纳(Peter Wagner)所说:“社会科学因此成为一种经验性的政治哲学,它超越并取代了旧的政治哲学与道德科学,以及早期政治秩序下被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都将其视为‘悲惨的财政科学’的财政行政管理科学。”[3]19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还是有许多社会科学家热衷于使用统计资料,但是这种单纯的定量的实证数据是不被完全接受的。因此,定量社会科学家通常会在进行实证的定量研究的同时兼用传统的理论分析,这种研究模式在德国尤为明显。[13]131
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话语而产生,而现代性本身是具有自由与纪律、偶然与恒定、实然与秩序的二元性的。这就注定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终将绕不开偶然与必然、客观与主观所构成的认知陷阱。现代社会科学早期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原则所带来的研究结果是客观主义的,而非纯粹客观性的。“客观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其意思是:这一社会学把社会活动视为无活动能力的物体,因此,它与人类行为的‘原因’相关,但更与人类行为的‘方式’相关;与改良相关,更与控制相关。”[2]291
五、 超越与创新
现代社会科学自身的现代性问题具有历史必然性,其理性主义、民族国家性、实证主义等现代性问题深刻地影响了自身的结构与演化。现代社会科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今这些因素已慢慢消退,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科学不应再妥协于旧时的学科权威或局限于过往学科共同体的已有认知。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学科系统的发展是在不断肯定与否定、改革与重建的过程中进行的。也正如蒯因(W. V. Quine)所说,任何知识都是人造织物,其外围不停地与经验相互作用。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力场,其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当场的外围与经验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引起内部的再调整。[14]42
(一) “本土化”背后的“超越”尝试
现代社会科学自建立初始就因其研究范围与对象而具有鲜明的国家性与民族性。虽然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社会现象以及社会本身的,但从根本上是关于“国家”——即“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所说的社会其实就是民族国家。[10]11因此,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源来看,其国家性与民族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可以从早期各学科的命名看出。例如国民经济学、财政学(Kameralwissenschaften)、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其字面意义表示国家一级的宏观经济学)、政治学(politics)、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en)以及统计学(Statistik)。其中“财政学”就字面意思可解释为“有关宫廷的学科”。直到19世纪,“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才完全取代“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德国学者约翰·布伦奇利认为“政治学”就是“国家科学”,与此同时“政治学”(politics)的涵义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希腊语“polis”(国家、城邦)。“统计学”(Statistik)一词产生于18世纪的德国,又被称为“政治算术”,用来指国家的描述性科学,其主要任务是对人口和经济进行量化研究。[2]205
一致性检验:λmax=(1.53×0.665)+(7×0.163)+(5×0.172)=3.018,CI3=0.009,则 CR3=0.015 <0.1,表明该判断矩阵的计算结果通过一致性检验。
如何消除现代社会科学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立关系,如何消除双方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如何抹平百年来形成的学术鸿沟,是今日社会科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只要能消解现代社会科学中的现代性,这些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实际上,在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现代性这方面,中国已有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的提倡与复兴。须知,在19世纪近代中国引进“西学”之前,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有别于今日并与当今备受关注的国学研究、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无论是“国学热”还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是一种对抗现代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极具代表性的表现。但这并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话语体系与专业知识领域,而是一种以“传统弘扬”与“文化返潮”为基调的国家内部的民族运动,并不能替代学科内专业性的结构调整与纠错指正。因此,必须以“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包容视野为逻辑起点,将中国文化之精髓以普遍知识的形式有机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
所以,与其寄希望于单纯地强调以国学或传统文化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不如站在“人类知识共同体”的角度,以中国作为非西方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科学加以修正。正如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所启示的,社会科学总是难以幸免于历史的相对性与文化的差异性。由于受知识背景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任何国家的任何学者都很难完全摆脱主观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限制。由此,原则上任何从“人类知识共同体”角度出发,以构建健康平衡的社会科学为初衷的学科结构调整都可以被认为是有利于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接下来的发展道路必然是以“非西方国家”的身份承接“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的任务,构建与发展适应当今全球时代的现代社会科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科学将为部分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出路,不仅可以适时地解决中国当前国情下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可以为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科学将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问题,为其提供长远、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
为了使园林景观更具观赏性,详细研究植物文化内涵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尤为重要。通过探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内涵的表现,阐述植物文化内涵在园林景观中与其他要素的融合,植物文化内涵在建筑中的应用,植物文化内涵在山石中的应用,植物文化内涵在水体中的应用,植物文化内涵在园路中的应用,并分析应用植物配置营造园林景观文化的内涵,植物配置结合观景点,增添诗意,植物配置和环境氛围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意识到植物文化内涵的重要性,从而充分发挥植物文化内涵的作用,以突显园林景观的文化价值。
现代社会科学既不能是强调“欧洲中心主义”的,也不能是强调“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各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由“他者”角色转换为参与构建的“主体”角色,既要尊重各国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主体间性”,又要倡导以“人类知识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健全发展。
(二) 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之路
处在由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所造成的“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学术裂缝”中的中国社会科学,作为“非西方世界”的一员参与构建全球时代的社会科学,不仅是本土研究的需求,也是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种有效途径。
突破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确立全球、多边的研究框架。不再将国家作为分析社会问题时的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必须提倡一种“多元普遍主义”的新的客观性观念。这是确立全球、多边研究框架的基本条件。两百多年间,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极力关注各个学科内部的发展与健康,因此当今时代更应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科学整体所具有的国家性与民族性问题。这就要求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从以国家、地区为框架的“学科共同体”的角度转向以全人类、全球为框架的“人类知识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今日知识世界。而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扬弃以往带有历史色彩的分析框架,加入非西方的研究视野、研究对象乃至研究方法。尽快接纳、吸收多边的、全球性的研究方式,并建立以维护全人类的基本利益与保护并延续人类共同知识宝库为初衷的“研究问题”与“研究主题”。
追溯而言,各企业每月的税金都是足额缴纳,但是在缴纳时间上往往都不太在意。其实,经过几轮调整,国家在每一种税金入库截止时间上基本都定在每月的15日,所以如何保证税金在企业账户内最大限度的保留、生息,实现“纳税最晚”也是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
第二,克服“学科保护主义”,鼓励学科边界作业,推进跨学科、超学科与学科间融合,促进学科间互动。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多根据现有的、具有主导地位的学科划分来限定学科活动范围,然而这种始于19世纪的学科划分主张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相互分割,且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暗含着一些对历史当权者有政治倾斜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这不但有可能造成学科间的不平等发展,也有可能造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学科不平等发展。因此,新时代的社会科学要求重建学科划分标准,鼓励、促进不同学科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协同推进跨学科、超学科以及学科间性融合。打破学科间的藩篱,改变已往陈旧的以“本学科”为主体,“他学科”为客体的学科交往模式,以“自然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间交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共融互动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第三,克服单一数理分析方法,主张多元研究方法共存互补。现代社会科学想要突破现代性带来的局限,更好地建设与发展学科,就必须率先克服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过度崇尚“实证主义”的弊端,向兼容并蓄的方向发展,主张多元研究方法共存互补。在现代社会科学肇始之初,国家政权力量鼓励并引导学科知识以实用为主,并将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引入各学科的理论模型,使“实用性”和“客观性”成为度量知识可靠与否的标尺。但就社会科学而言,由研究者自身力量以完全客观的知识形式再现外在于个体的生活世界是很难达成的事,换句话说,“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可求的,我们还必须理解“客观性”的另一层涵义即“客观性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学习的结果,它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意图,并且证明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 。[1]98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以及“数理分析”至上的学科态度值得商榷,为了避免过度迷信实证主义,现代社会科学不需要刻意强调或主张某种研究方法,摒弃侧重单一方法的研究理念。
第四,实现“中国问题的国际表达”和“国际理论的中国表达”。为避免社会科学的发展由“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以客观的态度平衡本土化与西方中心,寻求一种基于普遍真理同时兼具服务本土的特色化发展之路。泰戈尔曾谈到,即便科学是具有全球性表达的知识,但任何有关人性的东西一旦从产生它的土壤剥离就面临着消亡的结果。[15]21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每个民族国家、地区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下,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肩负着如何建设兼顾全球化与本土问题解决的重任。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即将迎来的不止是一种责任的要求,更是一种果敢的尝试,其初衷绝不是单方面简单地在中国话语体系下研究国际理论。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体系面临着如何将研究问题以国际接受的方式方法合理表达,将中国问题纳入国际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以及话语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国情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如何将国际理论所表达的研究核心依据中国国情转化为适合我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即抽象问题具体化、国际理论本土化,排除遏制本土研究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的根本因素,从而使国内学者快速了解并进入该研究领域,而不是一味地以西方的标准限制我国社会科学的成长与表达。
六、 结 语
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大多源于对理性主义的崇尚,这种崇尚旨在说服——从已经得到公认的科学中寻求权威性与科学性,从而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支持,似乎只要模仿自然科学就可以获得科学性与权威性。然而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并不由被模仿对象所决定,也不能根据模仿的相似性来衡量权威性,而是完全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服务于自己的学科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而社会科学本身的权威性更是取决于学科体系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以及逻辑架构的严密性,而非与他学科的“血缘关系”。因此,“像”科学已经不再是今日社会科学对自身提出的要求和目的。
同时,现代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排除一切欧洲中心主义,去除现代社会科学起源所裹挟的特定制度化形态与各种权力关系。譬如针对权力与身份这样关键的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话语中是具有不同逻辑和定义的。“例如,大乘佛教将‘虚妄’(maya)这一概念用于国家、权势阶层和统治氏族,目的是要证明盛行于一神教话语的权力逻辑并非无所不在。道家提出合法的‘道’的概念,认为合法性是与超越儒家的官僚合法性的混沌现实的一种存在性关联。”[1]60这并不是一种强调非西方世界的特殊主义,而是试图修正现代社会科学原本具有的偏狭性的“普遍主义”。借用华勒斯坦的一句话:“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1]61
[参 考 文 献]
[1]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 西奥多·M.波特,多萝西·罗斯.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M].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3]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BJÖRN WITTROCK.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M].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4] 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M].刘北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安东尼·帕戈登.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M].王丽惠,郑念,杨蕴真,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7]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M].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9.
[8]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9] 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1] 罗伊·波特.剑桥科学史:18世纪科学[M].方在庆,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12]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3] TERRY NICHOLS CLARK.Prophets and Patrons: The French Univers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M].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4]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M].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5] 泰戈尔.民族主义[M].刘涵,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4.
The Issue of Modernity in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Research From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UI Yan- qiang, WEI Miao- miao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Southwest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 Modern social science was carrying corresponding risk of modern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Newton’s new physics, rationalism was pushed to the status of popular admiration. The construc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scope of most disciplines of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are deeply affected by natural science and modernity,an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including extreme worship of rationalism, European centralism and superstitious positivism,are common in these disciplines.Only by transcending its modernity, rectifying radical rationalism and eliminating the insularity of positivism, getting rid of a nationality and state, with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g”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an social sciences lift long-stand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so-called oppositional “west” and “non-western world” position and develop healthily.
Key Words : modern social sciences; rationalism principle; nationality; positivism; 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3-0039-10
收稿日期: 2019-02-25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0531
基金项目: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的现代性危机及其超越”(CYB17052)
作者简介: 崔延强,男,山东青岛人,西南大学副校长,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何菊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