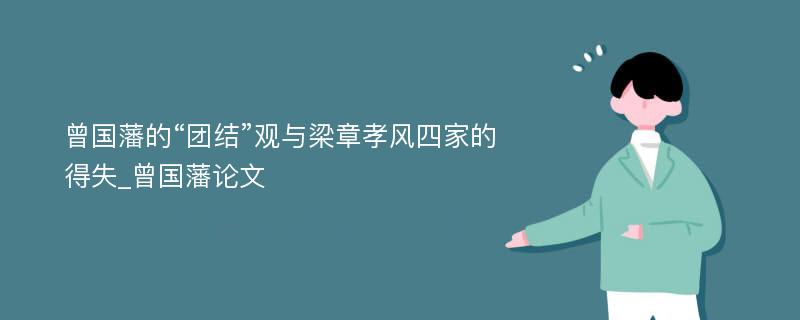
论曾国藩之“道统”观及梁章萧冯四家曾论之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得失论文,四家论文,曾国藩论文,梁章萧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3-0007-07 儒家“道统”之说,始于《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此为尧传舜,舜传禹之统。 孟子接续之。《孟子·公孙丑下》定五百年为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尽心下》并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此为尧舜传汤,汤传文王,文王传孔子,孔子传孟子之统。 西汉扬雄再接续之。《法言·五百》云:“或闻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此为否定孟子“五百年”之期,并非否定孟子所定之统绪。 唐韩愈撰《原道》,以“儒统”而辟“佛统”与“老统”,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这是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后,勉强加上一个荀与扬,之后就是韩愈本人。 南宋朱熹则另行排定统绪:不以韩愈上承孟子,而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承孟子,朱熹本人则上承周、程。 可知朱熹所排“道统”与韩愈所排“道统”,上半截相同,均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差别只在下半截:韩愈以为是孟轲传韩愈;朱熹则以为是孟轲传周、程,周、程传朱熹。韩愈之“道统”偏于以“德”排序,朱熹之“道统”则偏于以“理”排序。 一、“道统”之内涵与性质 曾国藩之“道统”则着力于“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试图超越“德”与“理”,而另行构筑中华文明之“道统”。这个“道统”不仅是儒家的,更是涵盖儒、释、道各家的。 《圣哲画像记》云:“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2]250-251又云:“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2]252 “义理”有义理之统绪,如文、周、孔、孟、周、程、张、朱;“词章”有词章之统绪,如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考据”有考据之统绪,如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曾国藩以为“道统”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最好是分科而言“道统”。这就可纠韩愈“道统”之偏与朱熹“道统”之偏。 《王船山遗书序》云:“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梁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2]277-278仁为体而礼为用,就此体用之统绪而言,是孔子传孟子,孟子传汉儒(如小戴氏),汉儒传宋儒(如张横渠),横渠传王船山,王船山传曾国藩。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曾说明曾氏力挺船山学之理由,谓:“曾国藩所保卫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道学。他是一个道学家,但不是一个空头道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信奉程朱发展到信奉王夫之。……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所要寻找的武器。”[3]76曾氏力挺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代表了曾氏心中高于“政统”的那个“道统”;曾氏尤重《读通鉴论》及《张子正蒙注》,只因为此二书代表了曾氏心中高于“政统”的那个“道统”。“道统”是经,是常,“政统”是权,是暂,“政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有了对于“道统”之信心,曾国藩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 从张横渠到王船山,从王船山到曾国藩的这个“道统”,核心内容就是:“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2]278“育物之仁”、“穷探极论”云云,以今语言之,就是要把一切所为放到“宇宙背景”上去考量,此即所谓“大人视野”。捍卫此“宇宙背景”者,即是“道统”之一环,摒弃此“宇宙背景”者,即不在“道统”之列。张横渠守此最力,故曾氏宗之;王船山守此亦最力,故曾氏亦宗之。 此“宇宙背景”化为“文章之道”,就是所谓“光明俊伟”:“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4]“文章之道”也有一个“道统”,就是由孟子而韩子,由韩子而贾生,由贾生而陆敬舆,由陆敬舆而苏子瞻,由苏子瞻而王阳明,由王阳明而曾国藩。这个“道统”之核心,也是所谓“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 “道统”虽可分科而言,然各科“道统”均得指向一个共同目标,一个共同的“极”,就是所谓“宇宙背景”。旅行之路有千万条,均得依“北辰”而得定位;学问之路有千万条,均得依“宇宙背景”而得定位。这“宇宙背景”就是各科“道统”所共有之“极”。捍卫此“极”,就是捍卫了中华文明之总体框架;放弃此“极”,就是放弃了中华文明之总体框架。洪秀全欲放弃之,故曾国藩誓死捍卫;满人入主中原欲放弃之,故王船山誓死捍卫。 朱东安撰《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曾予曾氏以极高评价,目曾为儒学第三期之代表:“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5]191-205此又构成一个新的“道统”,曾氏三居其一。 然朱文对曾氏所捍卫的那个“道统”之性质的判定,却是有问题的。它以为这个“道统”已经走到绝路,故应以洪秀全之方向为方向:“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几(向)。”[5]191-205洪秀全失败已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也正走在“复兴”之路上,却不是朝着洪秀全的方向走的。要想证明洪秀全“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朱文又以“糟粕”评曾国藩所捍卫的那个“道统”:“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维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5]191-205 就如北京旧城一样,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不拆毁旧城,新城就建立不起来”。既然我们知道北京旧城是“中华文明最高的结晶与最后的精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这旧城的旁边去另建被视为“精华”的西式新城?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先人亿万斯年以来所创造的文化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放到一边,另行去构筑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的西式“思想文化体系”?在胡同里拓汽车道,在四合院里盖摩天大楼,就是“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这种思维模式的产物。 曾国藩所捍卫的那个“道统”,不过就是一个“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而已。这个“道统”即使不是“精华”,也并非时人所谓“糟粕”。西洋三百年“工业文明”,不讲“宇宙背景”,不讲“大人视野”,只讲“自我中心”,只讲“国家中心”,只讲“人类中心”,几乎把天人关系,把人与物之关系,引入绝境。我们从那里还能看得到“未来”与“方向”吗,还能找得到我们心灵的归依吗?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够说,张横渠、王船山、曾国藩等人所捍卫的那个“道统”,那个“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或许正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与“方向”? 二、梁启超章太炎萧一山冯友兰之曾论 (一)梁启超论曾国藩 曾国藩去世后24年,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序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论曾氏云:“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6]122又云:“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以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6]124此处是将曾氏制造局所译西书,放到清末“西学东渐”之全局上来定位,以明其“三居其一”之影响。 曾氏去世后30年,梁撰《新民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论私德”一节,再次论及曾氏,云:“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难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之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7]此处是将曾氏之德才放到清末“救国”之大背景上来定位,以明曾氏“救国之师”之地位。 曾氏去世后44年,梁撰《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民国五年,1916年),予曾氏极高之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8]此处关键,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与“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二句,是将曾氏一生得失放到“天下最大之学问”的大背景上来定位,告诉自卑之国人“尽人皆可学焉而至”之理。 曾氏去世后48年,梁撰《清代学术概论》(民国九年,1920年),在第二十九节再论曾氏制造局译西书及选派留学生之功,云:“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之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9]此处是将曾氏之“西学东渐”界定为明末“西学东渐”之延续。 总起来看,梁启超之曾论偏重于“人生大义”,谓曾氏为后世之楷模。比较而论,章太炎之曾论则偏重于“民族大义”,谓曾氏有“覆满”之力然未能尽其责。 (二)章太炎论曾国藩 章撰《检论·杂志》云:“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豔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徹徼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蚹,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傅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乎!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10]583因其立足于以“汉族罪人”(非“民族罪人”,因满族亦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评曾氏,故所得结论与梁启超刚好相反。梁以曾为胸怀大志之“豪杰”,而章则以之为追求功名利禄之“鼠辈”,以“吾祖民贼”责之。 章又撰《检论·对二宋》,驳宋教仁许曾国藩、左宗棠“无忝于英雄”之论:“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夫风教有变移,而古今无常序。当曾、左时,文化盛在中江以下,湖南处势稍僻,左学艺未兴,魏源、汤鹏、邹汉勋者,覢而一覩,其学术终未就成也。曾国藩虽多识,其部属良将罗泽南辈,财窥朱元晦之小学耳。……是以曾、左用之,为能有功。今湖南文学日盛,乃与江左代兴矣。……夫文学盛,则人自以为高材,莫肯率服;仕宦达,则夸奢中其心,而势利移其志。假令曾、左生于今日,成功大名,终不可就。非其材之绌也,时地异矣。”[10]600总之只以曾氏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之“英雄”,为“湖南文学未盛”时之偶然产物,在他时他地,“成功大名,终不可就”。 章又撰《检论·近思》,益责曾国藩以“汉族大义”,云:“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始知名义。……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獘,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如曾、左、张、刘者,上不敢为伯王,而下犹不欲为馈赠割赂之主,此之易行,而犹几不可覩,则中夏之迹,殆乎熄矣。”[10]625-628“大汉”、“中夏”、“异教”云云,均是以“汉族大义”责曾国藩,认为在这一点上,曾等是“没世不免恶名”,因为他们有“除孱虏”之能力,然却不敢为。 章更撰《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以为曾国藩本就有“乘胜仆清”之志,只是因为情势有变,未及速成。其言曰:“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袄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纲纪不具,又訹于异教之说,士大夫虽欲为之谋,不可得。国藩之屈而之彼,势也。及金陵已下,戏下则有惰归之气,而左、李诸子新起,其精锐乃逾于旧,虽欲乘胜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独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势,清之可覆与否,非所覩也。”文章对王闿运“其性不爱国至是,谓其志覆满洲可乎”一问题的回答是:“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应远西,其闇劣乃如是,此非独国藩一人然也。……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11]此处谓曾氏有“覆满洲”之志,与前面所论稍有出入。可知章氏论曾之观点,前后有变化。 (三)萧一山论曾国藩 史家萧一山所撰《曾国藩传》,对章太炎“志覆满洲”之说,持完全否定之态度。萧云:“章先生即知道他‘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数洪、杨,足征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12]21又谓:“事后论人,自己不免忘掉时代环境了!他们在实际上确把满清的政权转移于汉人,无形中又增加了会党的势力,替民族革命隐隐做下驱除艰难的工作,就在这一点来讲,也算功可补过吧!况且他们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国主义者以方张之势,压迫欺凌我们,汉满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无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出路,计划出一种复兴的方案,守旧维新,安内攘外,虽然没有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毕竟是个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们称赞的啊!”[12]22在曾氏视野中,真正的“异族”不是满人,而是洋人,真正要应对的不是满人之统治,而是洋人之欺凌,故以“汉族大义”责曾氏,乃是降低了曾氏之眼光。萧一山之驳斥章太炎,就是指章降低了曾氏之眼光,曾氏当时已是立足于“全世界”,而不是“汉满的畛域”。 (四)冯友兰论曾国藩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在“曾国藩”一章亦专节驳章太炎之论。谓:“若说曾国藩在主观上本来就有取清廷而代之或排满的思想,那就是臆测了,没有什么迹象可以作为根据。从曾国藩的家庭出身及所受的教育看,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3]371 对于曾氏为何不“乘胜仆清”之问题,冯友兰亦有明确之答案:“……他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思想。打下南京以后,他的想法是要在东南半壁推行洋务,然后以此为基础推行到全国。”[3]373冯以为曾氏与清廷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是“同床异梦,同归殊途”,目的相同,出发点不同,“清廷的出发点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曾国藩的出发点是保卫传统文化”[3]371。冯又以为曾氏刻行《船山遗书》重在其政治意义,“其政治意义是要以此书丰富中国古典哲学的宝库,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从而加强他自己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3]372。冯又以为曾氏虽非“志覆满洲”者,然“客观上”却为“覆满清”准备了人力与物力,“曾国藩虽然没有推翻满清的思想,但是在客观上他确实使汉人的势力在清廷的政治上占了优势”,可名曰“汉人优势派”,曾氏是这一派“第一代领袖”[3]373。 总之冯友兰设专节驳章太炎,乃是以为章不该“壹意”以“汉族大义”责曾氏。“章炳麟的这篇文章以满汉之争为中心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同盟会本以排满为其宗旨之一,但清朝交出政权以后,它就把‘排满’改为‘联满’,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冯以为“时至今日,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之中,满汉之争也成了历史了”[3]373。 三、四家曾论之得失 萧一山与冯友兰之驳章太炎,出于一个共同之目标,就是以“文化大义”之坐标取代章太炎“汉族大义”之坐标,并进而把曾国藩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去定位。 这个新的高度就是“文化”,“文化”之于“政治”,是更高层次的坐标。萧一山视曾氏“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之说,就是立于这个坐标而成立的。他以曾氏为“不世出的哲人”,也是立于这个坐标而成立的。他又引郭斌和氏《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初载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文为自己张目,曰:“我国过去被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12]24-25 萧一山认为,郭氏此一评论“较之梁先生的评论深刻多了”[12]25,就是指“文化大义”之坐标高于“人生大义”之坐标而言。故梁启超虽也曾以“立德、立志、立言三并不朽”评曾国藩,“但梁先生还不晓得曾文正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12]24。萧氏以为梁先生还没有使用“文化大义”之坐标。 萧一山以“文化大义”评曾氏,认为“曾国藩的事业之成就,完全由学问而来,无关乎命运”[12]27。谓:“他生平的事业,完全是从学问修养而来的。”[12]197又以“文化大义”评曾氏之“救国方案”,谓:“他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说,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12]179-180故曾氏之“救国方案”,实际就是一个“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的方案,也就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方案,此种方案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屡试不爽。 萧一山又以“文化大义”之坐标,解释曾国藩为什么“救了满清”。当时“中国文化”面临的威胁,不来自满清,而来自西洋,“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乱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12]178-179。维系一息“文脉”之不坠,被萧一山评为目光远大:“何况舍弃了自己民族的立场,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我们佩服曾文正公,就因为他有这种远大的眼光,就因为,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还离不开这种原则。”[12]180 以“文化大义”为坐标评判曾国藩者,还有哲学史家冯友兰。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曾国藩”章(名曰《所谓“同治中兴”和“同治维新”的中心人物——曾国藩》,国人撰写《中国哲学史》,很少为曾氏设专章,可知冯很看重曾氏),明确论定“文化”乃曾氏之目标[3]355-356。既以“文化大义”评曾氏,则曾氏与洪、杨之争,当然就被判为“文化之争”。对此冯友兰说:“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3]354-355又说:“就是太平天国要毁灭中国传统,推行基督教的‘教义’;曾国藩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他自己的‘教义’。……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用武力推行其‘教义’,他也只得用武力去对付,这就叫‘不得已而用之’。”[3]364 既以“文化大义”评曾氏,则曾氏日以继夜刻行《船山遗书》,当然就被判为“文化之举”。对此冯友兰说:“1852年起,曾国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成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在这场斗争中,曾国藩自觉地以道学的教义与对方的基督教教义相对抗。……这时候更发现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所要寻找的武器。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竟然刊刻《船山遗书》。”[3]356此“教义”之核心内容,就是所谓“气学”:“曾国藩之所以接受并信奉从张载到王夫之的气学,这是由于,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在教义方面,只有气学的‘气’不可能曲解为类似上帝的东西,而理学的‘理’和心学的‘心’都有可能解释为类似上帝的东西,所以只有气学可以与洪秀全的‘上帝’划清界线。曾国藩未必自觉到这一点,但这一点确实能划清两种对立的教义的界线。”[3]359此处“文化”之内容已不再限于“纲常名教”,而是已上升到“气学”之高度。 以“文化大义”为坐标评判曾国藩,也许要优于以“汉族大义”为坐标评判曾氏,也优于以“人生大义”为坐标评判曾氏。然“文化”是可以分层的,“制度层”之文化,不同于“器物层”之文化;“观念层”之文化,又不同于“制度层”之文化。吾人谓曾氏“为文化而战争”,是为“器物层”之文化而战争,为“制度层”之文化而战争,还是为“观念层”之文化而战争?故于“文化大义”之坐标,吾人必得做出具体规定,方能对于曾国藩给出恰当之判定。 萧一山的界定是止于“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当然是属于“制度层”。冯友兰的界定已涉及“气学”,似已上升到“观念层”;但他此层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深究。他讲得更多的,更着意的,是“纲常名教”。除前段所引有关“纲常名教”的话外,他又说:“他的基本思想是保卫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纲常名教,这在他的《讨粤匪檄》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是讨太平天国的檄文,也是他的政治宣言。”[3]369《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曾国藩”章之全章的结论是:“总起来说,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他的功;他的以政带工延迟了中国近代化,这是他的过。他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其主要内容是纲常名教,即所谓‘礼’。但因形势变了,所应付处理的问题不同,所以功过各异。”[3]369“纲常名教”也属于“制度层”。 总之萧一山、冯友兰诸家使用“文化大义”之坐标,基本均以“制度层”之文化为限,而未上升到“观念层”之文化。使用“文化大义”之坐标评曾国藩,是其得;未将“文化”之内涵推展到“观念”之层面,是其失。著者则以为,吾人当特别注意“观念”一层,因为曾氏所捍卫者,主要是“中国式思维”,是以“机体论宇宙观”对抗洪、杨所宣讲之“机械论宇宙观”。冯先生提到的“气学”,就是中国人“机体论宇宙观”的一部分;曾氏捍卫“气学”,就是在捍卫“机体论宇宙观”。这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宇宙背景”,也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大人视野”。换言之,这是中国人所强调的“道统”之共同目标与终极理想。 故“文化大义”之坐标的顶点,是“观念大义”之坐标。吾人评判曾国藩,就当从这个顶点俯视而观。观之结果,就是认定曾氏构筑“道统”、捍卫“道统”、荡平“粤匪”,目标乃是以机体论对抗机械论,以大本论对抗本体论,以理性主义对抗耶教信仰,以连体论对抗个体论,以大化论对抗进化论,以关系主义对抗本质主义,以中式科学对抗西式科学,等等。所谓“近代化”,是以后者化前者;所谓“反近代化”,是以前者化后者。以此观之,曾国藩是个“反近代化者”,而非“近代化者”。曾国藩“延迟了中国近代化”,核心就是延迟了中国“观念层”文化之“被近代化”。这就是他的功绩与贡献。 评判历史人物,坐标总可以是多重的。梁启超等设立“人生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个人”的曾国藩之一面;章太炎等设立“民族(汉族)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族人”的曾国藩之一面;萧一山、冯友兰等设立“文化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文人”的曾国藩之一面;著者设立“观念大义”之坐标,又让我们看到作为“哲人”的曾国藩之一面。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完全是因为坐标的不同,结论其实是可以互补的。一个“千面的”曾国藩,才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反之,一面或几面,总是离“真实”太远。 总之在晚清以降文化史上,曾国藩也许是阻止中华文化在“观念”层面“被近代化”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分科而言“道统”,同时又认定各科“道统”共同指向“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这个最高的“极”,并誓死维系之,捍卫之。他的此种“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的方案,于当今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14-3-20标签:曾国藩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中国哲学史新编论文; 船山遗书论文; 章太炎论文; 冯友兰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