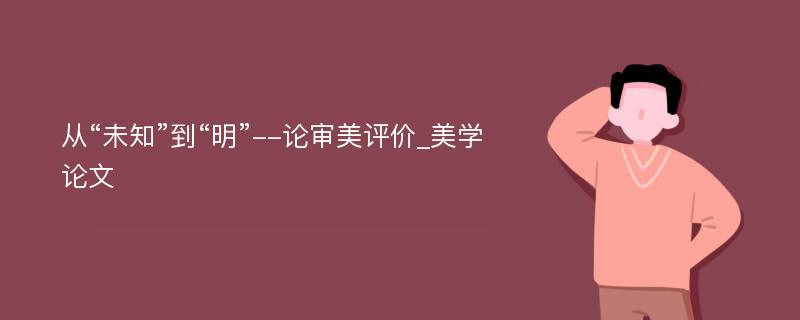
从“无明”到“明”——论审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明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审美评价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它是审美意向与审美指向交融贯通、协调共生后所产生的动态心理要素,属于审美体验中的协调范畴。而且它不像实践活动、认识活动那样侧重于对外在对象的认识,而是侧重对于外在世界的满足自身程度的价值评价。这价值评价,就其内容来说,源出于爱;就其实现来说,则是一种生命的“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1]
审美评价的内容为什么会源出于爱,而不是任何的现实关怀呢?原因在于:审美体验是人之为人的全部可能性的敞开,是人类自由的瞳孔,灵魂的音乐。它永远屹立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因此,审美体验一旦进入评价层面,就只能表现为一种深沉博大的爱。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2],那么我们现在假定进入了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的层面,此时,“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审美评价会如何呢?无疑是只能“用爱来交换爱”了。在这里,爱是超然本然情欲的终极关怀,是超越现实法则和历史规定的生命存在的终极状态。它意味着不论何时都存在着一个自由本性的理想存在,意味着个体与这自由本性的理想存在的相遇。因此,它是在一个感受到世界的冷酷无情的心灵中创造出的温馨的力量、义无返顾的力量、自我牺牲的力量、无条件地惠予的力量、对每一相遇生命无不倾身倾心的力量。它永远不停地涌向每一颗灵魂、第一个被爱者,赋予被爱者以神圣生命,使被爱者进入一个崭新的生命。当然,应该承认,爱是柔弱的、幻想的,爱是一种乌托邦,不过,“天将救之,以慈卫之”[3]。爱又正因为是柔弱的、幻想的,是一种乌托邦,才能够成为现实世界中真正理想性的东西(这世界对我们是何等吝啬!)。爱是一根连接着人类与世界的脐带。没有爱的生命是残缺的生命,没有爱的灵魂是飘泊的游魂。在被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包裹一切的世界大沙漠中,唯有爱才能给人一片水草。因此,学会爱、参与爱、带着爱上路,是审美体验的最后抉择,也是这个世界的最为理想化的抉择。
其次,审美评价的实现为什么成为生命的“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第一,就“方式”本身而言,审美活动基本独立于认识方式。长期以来,美学界把审美活动的方式称作“形象思维”,认为它与理性思维在内容上并无不同,是一种形象的理性思维,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审美活动的“方式”不同于理性思维的“方式”。恩格斯曾经谈到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的人的人格的扭曲,而不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一大堆历史事件、经贸记录、统计数字,并且说这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我看来,这里的“还要多”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也正是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审美活动之所以会在其中看到不同的东西,则是因为它自身“方式”的不同。这不同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内涵不同,以花为例,就理性思维而言,是“这朵花是红的”,在这里主词“花”和宾词“红”都是一个一般概念,具体的花、具体的红都被抽象为分门别类的“花”和“红”了,就审美活动而言,是“这朵花是美的”,在这里主词“花”和宾词“美”都不是一个一般概念,花仍旧是具体的花,美也仍旧是具体的美;角度不同,理性思维强调的是客体的普遍有效性,审美活动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体验性;标准不同,理性思维注重认识标准,审美活动注重价值标准。第二,就“方式”的实现而言,审美评价的实现不同于任何的理性评价、伦理评价、历史评价的实现。后者的实现无法回答生命的意义,一旦以之作为生命意义的回答,就反而会异化为一种占有。结果,不论它们的目光是何等的心平气和,都无异于一种禁锢、一种封闭、一种标签、一种惰性力量。审美评价的实现当然不是如此。它是永恒的缄默、永恒的追求、永恒的身心参与、永恒的生命沉醉、永恒的灵魂定向,因此需要永远重新开始,永远重新进入生命。借此,在审美评价中才有可能消解理性评价、伦理评价或历史评价的对于人类生存本身的揶揄,趋近隐匿的生命幽秘,为生命世界确立福祉、救思、祈求与爱意,使疲惫的灵魂寻觅到一片栖居之地。当然,这并不是说审美体验就与理性、伦理和历史方面的因素毫无关系,审美评价当然也要借助理性、伦理和历史方面的因素,但却毕竟只是以它们为媒介,只是消解中的借用和借用中的消解,所谓“既写出又抹去”(海德格尔),所谓“随说随划”(颜丙),所谓“就我来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苏格拉底)。审美体验与理性、伦理、历史的关系也是这样。似有非有,似无非无,或者说既有既无,既无既有。说它有,是因为它毕竟不得不借助理性、伦理、历史的因素,说它无,又是因为从它的本质看,理性、伦理、历史的因素毕竟只是媒介。并且,归根结蒂,它与理性、伦理、历史的因素既殊出而又不同归。
既然审美评价的实现不同于理性评价、伦理评价或历史评价的实现,那么,它的实现表现为什么呢?我认为,表现为生命从“无明”到“明”的生成。审美活动不同于科学知识、道德修炼或历史进步,它是生命的自我拯救。在理性、伦理和历史活动中,目标集中在作为对象的问题之上,一旦解决了,也仅仅是解决了而已,并不影响自身的生命存在。但在审美体验中,目标却集中在作为自身生命意义的秘密之上,一旦洞彻,无异于生命的再造。试想,人的自身价值原来是人的根据,但由于虚无生命的迷妄,却使之备受阻碍,无从自由展开,所谓“无明”。现在,一旦清除迷妄,单调乏味的生命、空虚无聊的生命摇身一变,成为丰富多彩的生命、自由自在的生命。这不是从“无明”到“明”又是什么?不过,从“无明”到“明”又并非天地之隔,更不存在此岸与彼岸的区别,世界是一个世界,生命是一个生命,“无明”破除就是“无明”破除,从“无明”到“明”也就是从“无明”到“明”,并不是在此之外还能有所得或有所建树。正像佛家讲的:佛虽成佛,“究竟无得”。也正像孟子讲的“予,天民之先觉者也。”苏东坡有诗云:“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就是从“无明”到“明”。神会禅师说:“如暗室中有七宝,人亦不知所,为暗故不见。智者之人,燃大明灯,持往照燎,悉得见之。”[4]这也就是从“无明”到“明”。因此,从“无明”到“明”,就是使生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有所见。当然,这样讲是从日常的功利的角度言之。其实,从“无明”到“明”,还是有所得和有所建树的。这所得和所建树就是:人们缘此而“成就一个是”,缘此而“方成个人,方可柱天踏地,方不负此生”,缘此而“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就是所谓“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
二
进而言之,“大游戏、大慧悟、大解脱”又意味着一种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正如高尔基所说:“当你感受到生活印象在压抑着你的灵魂,就把灵魂提高起来,把它放得稍稍高出于你的经验之上。”[5]审美活动正是一种“把灵魂提高起来”的活动。
对于审美活动与人类理想本性的关系,中国当代美学尚未能予以充分的重视。其具体表现为:忽视了审美活动的理想性,而去片面地追求审美活动的现实性。
我把这样一种对于审美活动的现实性的执著,称之为现实关怀。它是对有限的生命的承领和接受。它从生命的福乐自足、完满无缺出发,是超验之维与经验之维的合一,也是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的合一。一方面,超验之维是经过经验之维的筛选的,并非真实的超验之维,另一方面,经验之维也是经过超验之维的筛选的,并非严格的经验之维,一方面,理想之维就是现实之维,天堂即人间,另一方面,现实之维就是理想之维,人间即天堂。因此,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衡量标准,也就只能屈从于置身蒙蔽状态和刚愎自用的崇信之中的经验的、确定的、一维的生命反诘,屈从于僭越美学理想的过于功利、实用的科学理想、道德理想之中。结果,美学的关怀就不能不沦为一种虚妄的关怀、一种非关怀。
为什么这样说呢?试想,当审美活动把形形色色的现实准则(科学理想、道德理想甚至政治理想、经济理想之类)作为自己的关怀准则,僭越地去审判一切,就必然隐含着一个令人迷惑的失误,即一方面把审美活动混同于现实活动、把美混同于真与善,另一方面把现实活动本身设定为一种绝对的存在,设定为一种不容诘问、不容怀疑、不容审判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个根本的谬误、一种虚无主义的失误。本来,现实世界中,现实活动的非理想、虚无、有限性都是绝对的,但现实关怀却偏偏赋予它以相对的属性。于是,它十分自然地把导致生命的非理想、价值虚无、有限性的原因,推向了外在世界。外在世界的非理想导致现实活动的非理想,外在世界的价值虚无导致现实活动的价值虚无,外在世界的有限性导致现实活动的有限性,改造外在世界的非理想、价值虚无、有限性就不难改变生命的非理想、价值虚无、有限性,审美主义的幻想由是而生,对于生命的现实关怀也沾沾自喜地认定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真实根据。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作为一种价值关怀,现实关怀并未真正涉及“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一本体论的问题,也并未真正解决现实活动的非理想、价值虚无、有限性这一根本问题。
首先,现实关怀的最高价值准则只是同情。同情是现实活动的最高价值选择,但又是一种有限的价值选择,它表明:置身现实活动中的人,在追求物质的占有之外,毕竟还追求某种意义上的价值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是他所能占有的最高价值准则,但另一方面,同情又只是一种有限的价值。因此,尽管同情可以表现为真与善,但在美学的角度,不妨说,同情实在是一种隐蔽的恶。原因在于:同情的基础是“设身处地。”或者说,是“推”,所谓“推己及人”。然而,正像我已经反复强调的,一种美学理想绝对不能从现实的自我出发。否则就只能是虚假的、伪善的,就只能是深刻的不诚和自欺。而在美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幕:当同情作为审美活动的最高价值准则出现的时候,它所深刻蕴含着的正是对自然与人类的蔑视。同情自然就意味着把它看作一个有待进化、提高、人化的“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世界;同情人类就意味着把他看作一个有待赋予某种人类本质力量的弱者,意味着不再尊重伟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伟大的悲剧。
其次,现实关怀导致的只是“兼济天下”的功利化关怀和“独善其身”的伪功利化关怀。就前者而言,现实关怀的经验之维与超验之维的合一和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的合一,使它异常热心于在人间建立美好的天堂。这就产生了以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变人的生命存在的功利的审美目的论。对于功利化的关怀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生命世界的批判,不是对生命终极根据的关注,不是留居在本然的生命世界而瞩望着理想的光芒的莅临,而是瞩目于现实社会的和谐,道德世界的和谐,瞩目人与历史规律、人与社会秩序、人与天道的同一,瞩目一个完美世界——人间天堂的实现。然而,有待反复垂询的是,现实的文明社会的绝对合理性的根据何在?道德世界的绝对合理性的根据何在?人与历史规律、人与社会秩序、人与天道的同一的正当性何在?谁能担保这一切通通是真实的而不是一场骗局?与此相一致,谁又能担保现实理想的实现不会暗含着现实的文明社会、道德世界、历史要求、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和人本身的被奴役化、被工具化和被手段化,以导致任何一次关怀都成为维护现实的文明社会、道德世界、历史规律、社会秩序和天道的关怀?因此,不论这种功利化的关怀是因为天堂尚未降临而去批判现实世界,还是因为天堂已经降临而去歌颂现实世界,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后者而言,现实关怀的经验之维与超验之维的合一和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的合一,使它一旦意识到功利化关怀的失误,便只能遁入伪功利化的关怀。这伪功利化的关怀敏锐地洞彻到文明社会、道德世界、历史要求、社会秩序中的某种虚妄,不屑于效法忧患意识去斤斤计较于现实的得失、荣辱、恩怨,认为这统统是“假乎禽贪者器”,“利仁义者众”,“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6]由是,它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倒行逆施的道路:把自身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舍弃历史、舍弃文化、舍弃价值状态,重返无历史、无文化、无价值状态的自然生命。用庄子的话讲,这便为“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物胜而不伤”、“物物而不物于物”、“有物有宜而莫知其极”,总之是:“与物为春”。应当承认,这确乎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抗,以绝对的虚无主义来控诉现实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状态,谁又能说不是一种反抗?然而,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反抗都是只能无条件地予以首肯的。反抗并非只有积极的、正面的价值。
在我看来,伪功利化关怀的要害是只承认现实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态这一维的此岸世界。这样,此岸世界的否定必然导致信仰世界的否定,价值形态的颠倒必然导致事实形态的颠倒。不难看出,伪功利化关怀的反抗正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重返事实形态,或者说,公开地屈从于事实形态,这就是伪功利化关怀的所谓“反抗”。这“反抗”,起码有两点值得怀疑:其一,当人们对某种价值信念产生绝望、怀疑时,往往会转而走向否定和舍弃价值信念本身。这固然无可非议。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人能挺身而出,抗击世界的残暴、冷酷。或许,只要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不落井下石,只要他能够做到“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责怪他。但对于整个人类,却远不能这样看。我们绝不能由个体的某种选择推导出对于价值信念的否定和舍弃。如此这般的推导,只能导致对世界的片面发展的默许。工业文明对于人类本身的无情挤压,价值颓废、理想隐匿、道德沦丧、欺诈、虚伪、哀伤、眼泪、哭泣、叹息、呼告,面对这一切,怎么能设想有人竟然能够拈花微笑、逍遥自得呢?在此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伪功利化关怀是犯了无罪之罪,是在强化黑暗而不是在驱散黑暗?其二,凭借事实形态去控诉现实世界,这更为令人疑窦丛生。试想,从价值关怀回到价值虚无,回到“吾丧我”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无天怨,无人非”、“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生命本然,又怎么可能指控某种价值关怀的迷误?而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之类的“相忘以生”,又怎么可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根据?因此,不论这种重返事实形态的毅然抉择对现实世界的控诉是何等勇敢、何等执著,对现实人生的可恶、龌龊和鄙俗又保持着一种何等的不困惑、不心悸、不悲观的恬淡超然,对它本身,我们还不妨认定,都实在是一种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丑恶、一种伪审美。
因此,最后,现实关怀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无法关怀。由于现实关怀把自己的关怀稀释分解在一维的世界之中,随着一维世界的急剧变化,这关怀也会急剧地发生变化。今天是以社会为准则,明天又会以历史为准则,今天是以文明为准则,明天又会以自然为准则……每种准则的僭越都首先对前一种准则展开批判,但它本身却又仍旧出于一维世界,并且还丧失了前一种准则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反复循环的结果,是什么也没能关怀,不但没能关怀,而且这种关怀本身也越来越显示出有被加以关怀的必要了。不妨认真地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在一维世界中寻觅着人间天堂,期望借之去化解一维世界的丑恶,并且拯救一维世界,但一维世界究竟得到拯救了吗?而我们一旦从拯救一维世界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干脆沉入“以恶抗恶”的浊流,幻想以认同、参与、同流合污来换取来日的幸福、安宁、完美,我们又真的得到了吗?当我们放弃了虚伪而又过分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却又因此变得无喜无怒、无哀无乐,甚至把痛苦当有趣,把残酷当滑稽,把生命当赌注,我们是否又已经解脱了呢?当我们从令人窒息的禁欲铁幕下脱身出来,反过来在肉体和金钱的泥淖中打滚,我们就健全起来了吗?当我们从“向前看”跌入“向钱看”的人欲横流,我们就可以快乐了吗?当我们一旦弃绝荒谬的信仰而代之以无信仰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了吗?总而言之,一旦发现一维世界的丑恶,就宣布明天便可以建成人间天堂;一旦发现人间天堂的遥远,就把它一把火烧掉;一旦发现理想与事实不符,就把理想顺手推开;一旦发现生命道路上一片漆黑,就连油灯也愤然砸碎,这就是现实关怀的拙劣表演。“翻斤头”,“无持操”,鲁迅当年曾经用这样的评论痛斥那种令人生厌的“美学”态度,现在,我们也不妨用它来批评这种连自己也无法关怀的美学的现实关怀。
三
深入言之,现实关怀的根本失误在于对人的理想活动和现实活动、对人的自由活动与人的对象性世界的关系的割裂与颠倒,在于对于人的现实活动和人的对象性世界的绝对推崇。因此,要彻底弄清现实关怀的虚妄,就要首先弄清上述绝对推崇的虚妄,就要重新回到人的“是”和“什么”二者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来。
既然只有作为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的自身价值才是本真的存在,既然只有不断显示这一自身价值才能荣显人的虚灵昭明的存在,那么就美学而言,对于生命的关怀便只能从生命的本真状态——不确定性、可能性和一无所有出发,只能从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即对于“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的超越追问出发。因此,必然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不可能是一种现实关怀。这终极关怀敞开了人的生命之门,开启了一条从有限企达无限的绝对真实的道路。它通过对于生命的有限的揭露,使生命进入无限和永恒;通过对现实的、占有的生命的拒斥,达到对于理想的超越的生命的肯定;通过清除生命存在中的荒诞不经的经验根据,进而把生命重新奠定在坚实可靠的超验根据之上。试想,假如人们不愿明察自身的有限,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追求完美?假如人们不确知自身的短暂,又怎么可能有力量希冀永恒?假如人们不曾意识到现实生命的虚无,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走向意义的充溢?假如人们不悲剧性地看出自身的困境,又怎么可能有力量走向内在的超越?
在此意义上,不难看出,终极关怀类似于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但不是到了彼岸才进行,所以美学与宗教不同)。它是人类对生命的深切诘问,是超验形态的绝对真实,是无限的否定性,是对于生命的超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乌托邦。然而,又只有立足于此,人们才会看清自己在现实活动中所形成的困窘处境和局限性,看清“在非存在的纯净里,宇宙不过是一块瑕疵”(瓦雷里),看清再“美丽的世界也好像一堆马马虎虎堆积起来的垃圾堆。”(赫拉克利特)为什么在有了改造对象推进文明的普罗米修斯之后,还要有发现自己确定自己的俄耳甫斯和那喀索斯呢?为什么“欲过上一种新生活成为活生生的生命,我们必须再死一次”(铃木大拙)呢?不正是因为有了终极关怀这一绝对尺度吗?“没有救世主,就无所谓堕落”(帕斯卡尔);没有上帝,就无所谓上帝的弃地;没有终极关怀,也就无所谓世界的虚无。只有终极关怀,才超越于科学理想、道德理想和真与善的樊篱,也才是科学理想、道德理想和真与善的世界的理想归宿。
审美活动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否定。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看就是犯罪,审美世界则是赎罪。在这样的时刻,审美活动简直可以说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彻底的离经叛道者,一篇酣畅淋漓的公诉状。它本身有一种破坏性的潜力,无疑就是当代社会的挑战者和揭露者,也正是因此,在当代社会的自我分裂的语义环境中,审美活动往往表现为“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审美活动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审美活动是最趋近现实的,它靠超越现实去趋近现实。审美活动一面超越现实,一面覓就复现了现实。审美活动是生存世界的真实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审美活动有一个债主,这就是人类。
而这就已经涉及到了审美活动的超前性。审美活动的超前性是指人的全部可能性的敞开。它意味着:审美活动是人类自由的瞳孔,它永远屹立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引导着人性回归。它是我们为告别这个世界所描绘的一幅希望的肖像,又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终极关怀。它允诺着某种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东西,把尚未到来的东西、尚属于理想的东西、尚处于现实和历史之外的东西,提前带入历史,展示给沦于苦难之中的感性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活动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根据,或者说,审美活动的世界就成为现实世界的样板,审美活动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真实——理想的真实。
因此,审美活动从来就是人类苦难的拳拳忧心。清醒地守望世界,是审美活动的永恒圣职。在审美活动中,你可以看到生命的绿色、听到人类的欢乐和哭泣,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圣爱,寻找到人类生存之根。审美活动决不会跪倒在“不能哭、也不能笑”的形形色色的必然性面前,更不会在“不能哭、也不能笑”的形形色色的必然性中昏昏睡去。恰恰相反,它裸露着滴血的双足,在冥夜的大地上焦灼地奔走,殷切地呼告人类从虚无主义的揶揄和狭小黑暗的心理囚室中解放出来。它“一面哭泣,一面追求”(帕斯卡尔),引导着人类的感性超越,守望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警醒人类从单向度的物质存在走向全面的价值存在。它在生命超越中体悟着生命,追问着生命意义的灵性的根据。即便是在一个异化的世界,在一个被物质欲望混淆了人性与兽性、正义与罪恶、价值生存与物质生存的界限的世界,审美活动仍然会艰难地寻找着人类的失落了的理想本性,并且凭借这找回的理想本性去找回失落了的世界。
因此,审美活动不是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而是恬然澄明的俄耳甫斯和那喀索斯。审美活动穿越不透明的必然性的屏障,赋予人以超越必然规律划定的现实界线的尊严,使人从奴颜卑膝的束手待毙中傲然站立起来,使人成为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有了审美活动,才有了一线自由的微光,才有了一个圣洁的裁判日。冷漠严酷和同情温柔、铁血讨伐和不忍之心、专横施虐和救赎之爱,或者说,向钱看和向前看才永远不允等价;在蒙难的歧途上孤苦无告的灵魂在渴望什么、追寻什么、呼唤什么?在命运的车轮下承受辗轧的人生在诅咒什么、悲叹什么、哀告什么,才不再成为一件无足轻重或者可以不屑一顾的事情;人们也才不至因为一时的物质贫困而漫不经心地忘却掉回家的路。席勒讲得何其动人:“人性失去了它的尊严,但是艺术拯救了它……在真理把它胜利的光亮投向心灵深处之前,形象创造力截获了它的光线,当湿润的夜色还笼罩着山谷,曙光就在人性的山峰上闪现了”。审美活动,正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守护神,正是“我们的第二造物主”。[7]
不难想象,真正进入审美活动的人,因此也就必然是能够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审视人生的人。卡夫卡指出:审美活动要观照现实,就必须具备“另一副眼光”,这“另一副眼光”要透过或撕开遮蔽在现实之上的“覆盖层”,“在黑暗中的空虚里找到一块从前人们无法知道的、能有效地遮住亮光的地方”。显而易见,卡夫卡所说的“另一副眼光”,实际正是一副终极关怀的眼光。而且,这眼光为每一个进入审美活动的人所必需。例如巴尔扎克,他曾经自称为“书记官”,恩格斯也认为从他的作品中学到的甚至比经济学著作还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是出于一种现实关怀,对此,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有明确的陈述,倒是我们的许多理论家对此有意视而不见。他说,他写作《人间喜剧》的动机“是从比较人类和兽类得来的”,是要“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美,离开了真,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8]。无独有偶,舍斯托夫在论及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也说过类似的警言: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不是社会真相的“揭露者”,而是自己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占卜者[9]。在这里,对“自己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占卜”,无疑正是一种“人类和兽类”之间区别的“占卜”,一种“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美,离开了真,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的“占卜”。而中国古代的廖燕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出精辟的说明:
余笑谓吾辈作人,须高踞三十三天之上,下视渺渺尘寰,然后人品始高;又须游遍十八重地狱,苦尽甘来,然后胆识始定。作文亦然,须从三十三天上发想,得题中第一义,然后下笔,压倒天下才人,又须下极十八重地狱,惨淡经营一番,然后文成,为千秋不朽文章。[10]
这无疑也是对作为终极关怀的审美活动的深刻洞察。
因此,进入审美活动的人虽然并不超脱于现实之外,但却不再仅仅禀赋着一种执著的现实关怀,不再仅仅以科学意义上的真假、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以及历史意义上的进步落后去观照现实,而是从“永恒的法则”或从“三十三天上发想”,去审视“各个社会”,“自己和全人类”以及“十八重地狱”,去固执地追问着生命如何可能,呼唤着应然、可然、必然的理想本性,或者渴望洞彻:人类是在什么样的生命活动中,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僵滞在生命的有限之中,以至丢失了理想的本性,最终使生命成为不可能?!
注释:
[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19回评语。
[2] 马克思:《一九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第108页。
[3] 《老子》。
[4] 《五灯会元》。
[5] 《文学书简》上册,第308页。
[6] 《庄子》。
[7]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本,第63、111页。
[8] 《西方文论述》下卷,第184页。
[9]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译本,第106页。
[10] 《五十一层居士说》,见《二十七松堂集》第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