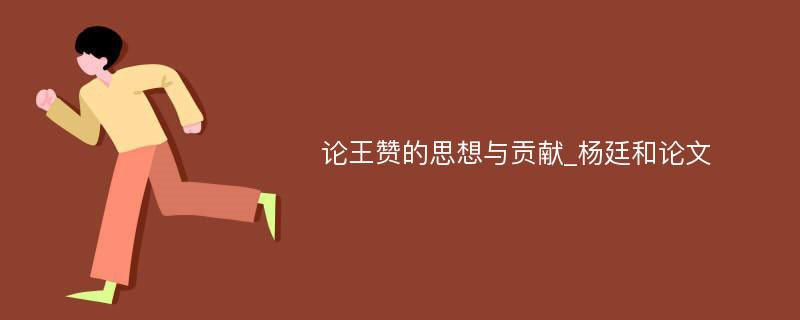
略论王瓒的思想和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瓒(1462-1524)字思献,号瓯滨,温州府永嘉县永嘉场(今温州市瓯海县永强区)人。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榜眼及第,累官礼部左侍郎,追赠礼部尚书,谥文定。《明史》虽未予立传,但他服官三十年,两任祭酒,四典会试,侍讲经筵,纂修国史,是个对时代有一定影响的官员和学者。特别是明代中期“大礼议”斗争开始时,他支持张璁上书反对首辅杨廷和,对当时政治及后期时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王瓒与“大礼议”之争
王瓒于明弘治九年出仕后,初任翰林院编修,参加纂修《大明会典》。十三年父死,丁忧在家,服除,在温州主编《温州府志》。十六年返回北京,参加纂修《通鉴》。正德元年(1506)纂修《泰陵实录》(即《明孝宗实录》),升任侍讲。因经筵讲对时进《举直错枉章》,暗讽太监刘瑾专权乱政,被刘瑾矫旨严责,幸得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的援救,降为国子司业。刘瑾伏诛后,他升任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一度代理部务(《永强五氏宗谱·欧滨公行状》)。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朱厚照病亡,因无子,遗诏由从弟朱厚熜接位,是为世宗。这时发生了历时三年之久的“大礼议”政争。
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欲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皇考,而内阁首席大学士杨廷和却坚持世宗必须以伯父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生父朱祐杭为皇叔。杨廷和根据西汉哀帝尊伯父成帝为皇考,北宋英宗尊仁宗为皇考的成例,认为“程颐濮园之议,最得礼义之正”。并扬言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些大臣如前内阁大臣杨一清等明知杨廷和之议不妥,但“不敢犯众”(同上)。这时新进士张璁上书反对,认为西汉哀帝虽原为定陶王之子,但幼年即入宫为成帝养子,立为皇储,以后接位。北宗英宗原为濮王之子,亦是早入宫中为养子,立为皇储,以后接位的。今世宗不是孝宗养子,亦未立为皇储,而是直接承接从兄武宗之位,与汉、宋情况不同。所以世宗是继承皇位大统,不是继嗣。应该尊崇生父朱祐杭为皇考,才合乎礼法人情。
张璁是个新进士,当时没有政治地位,他之所以敢于上书反对,是王璁支持的结果。王瓒是礼部大臣,礼部又主管议礼之事,王瓒不仅赞同张璁的意见,还将这个意见向同僚宣传,争取支持。这就引起杨廷和的忌恨,假借他事将王瓒贬往南京为礼部侍郎。当时南京因系明太祖建都之地,称为留都,虽有六部之设,实际上都是虚职而无实权。《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记载说:“时,有待对公车举人张璁者(笔者按:根据《瓯滨公行状》,应为新进士),为礼部侍郎王瓒同乡士。诣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帝)、宋英(宗)不类’。瓒然之,宣言于众。廷和谓瓒独持异议,令言官列瓒他失,出为南京礼部侍郎。”
“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世宗尊崇生父兴献之为皇考的问题。实质上,这是我国历史上皇权、相权之争的又一次较量。宋代自南宋中期以后,韩侂胃,史弥远、贾似道等宰相,权倾人主,政由己出,皇帝形同傀儡。明代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杀了宰相胡惟庸,废去宰相,确立皇权。虽然明太祖遗诏后世子孙不得再设宰相,将政事分属六部,权归皇帝。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内阁学士均兼六部尚书之职,品级、权力已有宰相之实。杨廷和在正德二年(1507)以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后,未几年即为首辅。“当廷和柄政,帝(武宗)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明史·杨廷和传》)。这十多年国事实际上都由杨廷和处理,所以这时杨廷和气焰高张,以“定策国老”自居。“大礼议”之争开始时,世宗处于劣势,世宗数次颁诏追尊生父,杨廷和数次退还诏书,一度迫使世宗屈从。迎合杨廷和之意者,即升官重用,如巡抚云南何孟春升为吏部侍郎,已经告老回家的前都御史林俊重新起用为工部尚书。持异议者,如王瓒、张璁都调到南京去(张璁任南京刑部主事)。甚至张璁、桂萼奉召到北京商讨大礼,一些拥护杨廷和的“廷臣欲捶击之,无一人与通。璁、萼称疾不出”,只好匿居武定侯郭勋家中(《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和《明史·张璁等传》)。这些足见杨廷和这时权势之大。可是明代中期之时,皇权已经巩固,经过几次反复斗争,世宗终于得胜。嘉靖三年(1524)二月,杨廷和被免职。同年七月,杨廷和之子杨慎和两个内阁大臣纠合官员二百多人,在京城左顺门举行“哭谏”,自辰至午不散。世宗大怒,逮捕为首者下狱,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杖责,被杖责者有一百多人,受杖创先后死者十六人。“大礼议”之争到此结束。
王瓒是位忠于皇权的大臣,他在武宗离京出游时,曾上《清建储贰疏》和《请回銮罢犒军疏》。要求养育宗室近属子侄于宫内以为皇储,又力请武宗回京主持国事。这些奏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所以当举朝官员纷纷赞同杨廷和“大礼”之议时,他却独持异议,而赞成并宣传张璁的意见,因而受到打击。正德十六年六月王瓒调往南京后,同年十二月被会推为南京礼部尚书,又为杨廷和所压制,不准所请。第二年(1522,即嘉靖元年)五月王瓒老母在家病故,他在心情抑郁之下加上母死悲痛,遂患背痈,带病回家料理丧事,丁忧在家。嘉靖二年四月背痈复发,死于家中。终年六十三岁。
二、王瓒的“实学”思想
“大礼议”之争,是一次权力之争,也是一场学术思想之争。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上反映了程朱与陆王两派价值观的差异。嘉靖三年六月世宗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修撰杨慎率一些同僚上书反对说:“君子小人不并立,正论邪说不并行。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绪也;萼等所言者,冷褒(冷读作“令”)、段犹之余也。学术不同,议论亦异”(《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杨廷和、杨慎等所根据的确是程颐濮园之议,而这时支持张璁、桂萼意见的黄绾、方献夫、黄宗明、席书等,却是王守仁的弟子和追随者(《明史·席书等传》)。杨慎上书所说的冷褒、段犹是西汉时赞成哀帝追尊生父的官员,后世目为势利小人(《汉书·师丹传》)。杨慎是以此诬蔑王学传人,并斥责王阳明学说为邪说。
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即以程朱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程朱理学处于独尊地位。永乐年间,朝廷以程朱思想为标准,将理学家的经传、集注等辑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致使当时学者认为“自程朱后,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章懋语)。这既使其他学说被目为“异端”、“邪说”,逐步消亡;也使程朱理学本身僵化,桎梏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到了明代中期,政治腐败,经济动荡,矛盾百出,道德沦丧,使明王朝濒临统治的危机。于是出现了反省过去,重整学术思想的要求。薛瑄、罗钦顺等继承程朱之学而加以改造,提倡“学贵践履”的“实学”,王守仁亦多次提倡“实学”(见《传习录》),并提倡“知行合一”之说。王守仁这时虽有平朱宸濠的大功,官封南京兵部尚书、新建伯,岁禄一千石,但不为杨廷和所喜,不予铁券,不给岁禄,并被迫回家“探亲”。王学当时亦未被朝廷认可,所以杨慎斥为“邪说”。
王瓒科举出身,历任国子监司业、祭酒多年,精通程朱理学,也崇奉程朱理学。他在《国子监东壁铭》中说:“我思古人,学必有师,传道授业,解释群疑。邹鲁之后,伊闽独盛,万古之准,万物之镜”。又在《国子监西壁铭》中说:“春秋之才,洙泗有造。文章易见,性命难闻。……后贤造兴,是嗣是程;充拓光大,有如考亭。日诵其书,必玩其意,时复译习,其进无疆”(均见《瓯滨文录》)。在当时改造程朱之学的气氛下,王瓒也感到程朱末流,思想庸俗,学术空虚,失去程朱理学中原有之“实学”。他在《鹿城书院集序》中说:“后期所谓学者,役精斵思,锻炼风物,而自为雄长。稽式揣似,铺饰枝蔓而驰循时好。言与心携,心与道贰,河洛、武夷之实学,荒落湮郁,畴克醒寤而还诸旧轨”(同上)。因而他提倡“实学”与“力行”之说。他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常对学生说“凡读一书,必得一书要旨而致之于用。今之业经者,惟作文觅举而已,岂理也哉。”(《行状》)又在《国学六馆箴》中的《力行箴》说:“人能致知,于道无疑。既知勿由,知之奚为?故知必行,而行必力,天理蕲存,人欲蕲息。……去恶为善,表里并实”(《瓯滨文录》)。并在《致知箴》中说:“致知之道,穷理为先。理寓于物,悟则脱然。或验于身,或验于事。浃洽同辙,积久乃至”(同上,六馆箴原有六箴,现残存四箴)。王瓒和薛瑄均皆提倡“实学”,其说相近,但薛瑄是强调程朱之学固有的“实学”思想。如朱熹就本有实学思想,他在《中庸章句》前言中说《中庸》,“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而王瓒则由于生长于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故乡,自少即诵读南宋永嘉诸学者之书,思想上受到永嘉事功学说的薰陶。如他在《止斋陈先生文集序》中说:“瓒幸生公(陈傅良号止斋)之乡,屡尝诵读遗文而私淑之。……公淹贯《六经》,包括百氏,洞彻天人之奥,而于历代经制大法,与夫当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验钩索,委曲该洽,此岂泛然雕饬以鹜于虚言者耶”(《止斋集》卷首)?他又有《游仙岩诗》:“我慕止斋非一日,摄衣更到读书台”(原注:宋陈止斋读书在此。《瓯滨摘稿》38页)。可见他对陈傅良敬仰之深,并自认是私淑弟子。关于陈傅良,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有几句很恰当的评论:“永嘉诸儒本以经制为宗。止斋为薛文宪(薛季宣谥号)弟子,于井地、军赋尤为专门之学。宜其精究治本,非空谈经世者比也”(《温州经籍志》卷三)。陈傅良是位注重“实学”的学者,他说:“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止斋集》卷十四)。陈傅良继承薛季宣的“道在器内”的思想,他教导学生曹叔远等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转引于《朱子语类》卷一二○曹叔远对朱熹所述之言)。而王瓒在上述《致知箴》中也认为“理寓于物”。同时,王瓒在弘治十六年所写《温州府志序》便发挥了陈傅良的“道”与“器”的主张。王瓒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体夫道,道行于其中而纲维之。是形而下者可化,形而上者实在焉。……志所记者,若郡邑、城池、形胜、风俗、山川、土产、赋役、学校、公署、官职、科第、人物,为类不一,皆器也。由器揆道,存乎其人,是故有郡邑,则有治之之道。有城池,则有守之道。……器不能无道而自淑,道不能无器而自行也。”
王瓒依据永嘉事功学说要求实行程朱之实学,“畴克醒寤而还诸旧轨”(见前《鹿城书院集序》)。这和薛瑄所提倡的实学是相近的,也可说是殊途同归。因为永嘉学派与洛学渊源极深。自北宋以永嘉周行己为代表的“元丰九先生”传程颐之学回到温州后,洛学在温州开始传播。周行己两度在永嘉讲学授徒,许景衡在瑞安,陈经邦、陈经正兄弟在平阳传播洛学,使全国“言性理之学者宗永嘉”。到了南宋,郑伯熊私淑周行己,精于经制治法;薛季宣传洛学弟子湖襄学者袁溉事功之学,以经制言事功。陈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宋史·陈傅良传》)。陈傅良之学与洛学自有渊源,王瓒可以说是受陈傅良思想薰陶感到当时程朱末流空虚而提倡实学的。
三、王瓒对乡邦的贡献
今存王瓒较完整著作,就是他所编撰的《温州府志》,而这也是他对乡邦文献所作的贡献。
明代对全国和地方方志的编修是十分重视的。“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篡修天下郡县志书”。(《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到了明代中期,虽然政治腐败,但整个局势尚称稳定,因此出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的局面。明代留传至今的方志几近千种,但佳志极少。王瓒这部《弘治温州府志》却堪称一部佳志,深受后人的好评。而且它是《温州府志》现存的最早一部。
弘治十三年(1500),王瓒丧父丁忧回家守制。十五年服满,应温州府知府邓淮之邀,编篡《温州府志》。他在弘治十六年癸亥所写的《温州府志序》中说:“弘治庚申(十三年),吉水邓侯安济来知郡事,诹察民俗,崇迈文教,锐有志于编篡,方勤抚绥未遑也。越三年(弘治十五年),治洽民和,郡以无事,爰命瓒于南塘(今鹿城区效)日新寺,缘旧志而辑理之。……凡六越月而成编,总为二十二卷,为之叙”。王瓒在此之前,曾参加篡修《大明会典》,有实际的编撰经验,所以他编撰的这部《温州府志》,深得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好评。孙氏在《温州经籍志》卷十赞许说:“王文定公瓒,……《温州府志》修于弘治十六年(笔者按:据永强李浦《王氏宗谱·瓯滨公行状》:“壬戌,郡守请修郡志,志成北上”。是修于弘治十五年),文定官编修时也。《范氏书目》(即宁波天一阁藏书目录)有明刊本,今未之见。《经义考》屡引其书以校,《万历(温州)府志》皆不及其详核。惜传本罕见,不得一补近时诸志之疏略也”。
《弘治温州府志》是海内孤本,唯宁波天一阁藏有明刊本外,以后并未翻刻。温州市图书馆因它是本地府志,特加影抄,笔者有幸得睹,不辞烦琐,现将其凡例和目录抄录于下,以飨读者,并略述其优点。
《弘治温州府志》凡例共有十三条:
一、旧志所载五邑(明代中期温州府辖有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等五县)等事,各自为志。今皆类肄于郡之后,以表其为一志云。
二、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史法也。其缪悠丑诋不可为训者删之。
三、自沿革以下,诸目率依旧志而酌之,惟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殁,乃录,事定也。官职、科目、题名,无间于存亡,可征也。
四、属县悉以去府远近为先后,其境内山川、祠庙、寺观等类,亦以去县远近为次。
五、公署、坛壝,其舍宇数目可省,故止书创修岁月。
六、理学、文艺、忠义、宦业、孝友、行谊、隐逸、科甲、荐辟,惟以人物为总名,其列女、仙释另提出之,遵《大明一统志》例也。
七、物产与他方同者不赘,止存其名,惟特产者详书之。
八、书目系吾乡儒先述作,旧志不载,缺典也。今悉搜访增入,庶不泯其著作之功。
九、寺观必设于洪武前者录之,新增者在所禁,不录。
十、记、序、杂著、奏疏、诗行,惟以词翰为总名,凡泛常私家文字,俱不能载。其叙咏山川名胜之类录之,不厌重复者,以有关于山川郡邑而足以为重者也。
十一、旧志以灾怪,风潮、火灾,各自为类;今俱以灾异为名,但以世代为次。
十二、祠庙在洪武以前立者,仍旧录之。新增者,必其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道开来,以惠及民者耳。
十三、山川、宫室、古迹,旧志题记多条附于下方,今皆剔入诗文目内,以类相从,庶使观览。
在这“凡例”即编篡思想的指导下,全志分为二十二卷。其目录是:
卷一:建置沿革、郡邑名、分野、形胜、疆域、城池、风俗(岁时附)。卷二:官守、公署、学校、书院、坛壝、邮传。卷三:山。卷四:水。卷五:水利(塘埭斗门闸),桥梁、津渡。卷六:邑里、坊门。卷七:土产、农桑、户口、田赋、课程、土贡、差役。卷八:宦职、名宦。卷九:兵卫、武勋。卷十至十三:人物。卷十四:列女、方技、仙释。卷十五:宫室、丘墓、古迹。卷十六:祠庙、寺观。卷十七:祥异、遗事。卷十八:书目。卷十九至二十二:词翰。
温州一郡之有方志,应以南朝刘宋郑缉之《永嘉郡记》为最早。但这书早在唐、宋即散佚不传。以后清末孙诒让从群书中缀辑遗文,仅50余条,予以刊刻成书。宋代有南宋陈谦《永宁编》和曹叔远《永嘉谱》,亦早失佚。明代《温州府志》共有四部,计为:徐兴祖编的洪武十二年《温州府图志》,王瓒编的弘治十五年府志,张璁编的嘉靖十六年府志,王光蕴编的万历三十三年府志。其中《温州府图志》已经失传,现存府志中年代最早的就是这部王瓒编的弘治府志。同时,卷数也最多,有22卷。而嘉靖府志只有8卷,万历府志为18卷。因为弘治府志年代最早,卷数又多,所以深受温州学者的器重,孙诒让就认为它内容丰富。“万历府志皆不及其详核”。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王瓒在“凡例”中提出“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史法也”。将方志视作史体,他的见识高出于当时一般修志的俗士儒生。现在大家只知道“志者史也”,“志乃史体”,“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是清代章学诚的卓绝见解,讵不知早在明代中期的王瓒就已提出。同时,王瓒还在“凡例”中说:“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殁,乃录,事定也。官职、科目、题名,无间于存亡,可征也”。前者就是今天方志“生者不立传”的原则;后者有如今日本地行政负责人一览表和有高级职称的人士一览表等等。很值得我们编方志者的借鉴。
第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瓒对乡邦文献的重视和贡献。他在府志的第十八卷特设《书目》,并认为“书目系吾乡儒先述作,旧志不载,缺典也。今悉搜访增入,庶不泯其著作之功”。在《书目》中录有宋、元至明初的温州学者著作250多部,作者180多人(粗略统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人士,可见当时永嘉学派兴起自有其原因。府志的第十九卷至二十二卷是《词翰》,保存了乡邦的大量文献。这里录有北宋“元丰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的《瑞安县隐居丹室记》,此文不见于《丛书集成》初编之《浮沚集》,当是周氏之佚文。南宋永嘉学者薛叔似,官至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宋史》卷三九七有传,他原有《薛文节集》和《薛恭翼公奏议》,后失佚。《词翰》中录有他的《劾丞相王淮疏》,是淳熙戊申(十五年)任左补阙时的奏疏,王淮因此罢官。这是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南宋平阳学者徐谊,累官宝谟阁待制,建康知府兼江淮制置使,《宋史》卷三九七有传。他是陆九渊的朋友,文集无传,《词翰》中录有他的《重修沙塘斗门记》,是一篇有关平阳县的水利资料。此外还有陈谦、王楠、戴溪等人的诗文,也是其他地方不易看到的。
此外,王瓒在弘治十八年(1505)任经筵讲官兼崇圣堂教书时,利用职务之便“于秘阁录出公(陈傅良)集五十二卷”。(《止斋陈先生文集序》)。并商请同年巡抚浙江的侍御史张伯纯出资刊刻。这就是今天留传的《止斋文集》。因为明代独尊程朱理学后,其他学说被目为“异端”、“邪说”,宋代永嘉学派学者的著作几乎散佚殆尽。如叶适的著作,到明正统年间,处州府(今浙江丽水地区)推官黎淳“尝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叶适集·黎刻水心文集跋》)。陈傅良的《止斋文集》今天得以留传,王瓒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标签:杨廷和论文; 永嘉学派论文; 王瓒论文; 中国温州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论文; 明史纪事本末论文; 历史论文; 陈傅良论文; 永嘉书院论文; 南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