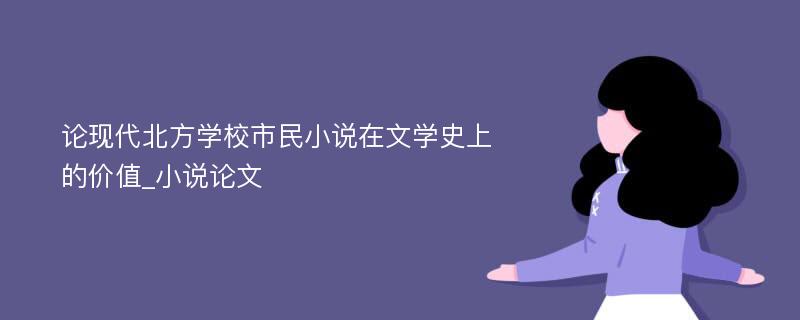
论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文学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市民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代文学(不是从新文学)视角看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是残缺的,特别是将现代市民小说也纳入现代文学视野,既有的现代文学地图失缺的地方就突显。这些年来,经过很多学者的努力,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南派市民小说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以天津为中心的现代北派市民小说却为人们所疏忽。要勾勒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图,现代市民小说就不能少;要勾勒完整的中国现代市民小说,现代北派市民小说就不能少。基于这样思考,本文将从史实、文化价值和史学意义等方面论述现代北派市民小说。
一
现代北派市民小说是相对于现代海派市民小说而以地域为界命名的现代市民小说创作群体。文学史上的概念要非常精确是不可能的,同时也不科学,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概念应该是:1.地域:以天津为中心旁及北京和1931年以后的东北区域;2.作家:既包括生活在北方的作家,也包括由其它地区迁徙到北方来的作家,例如从中部地区来北京的张恨水;3.作品:以发表在北方媒体上的小说为准。
清末民初之际京津地区也有一些市民小说作家作品,但是和苏州、上海地区的市民小说相比京津地区形成不了气候,因为京津地区始终缺少一个作家群。就以北派市民小说创作最活跃的天津为例,清末民初之际也就是赵焕亭、董荫狐等人的小说流行着。这种状况到张恨水小说流行后有很大的改变,一个市民小说作家群在京津地区形成,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市民小说的“北派”。北派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特点展示它的特色。
武侠小说是北派市民小说的强项。1923年南派作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作《江湖奇侠传》拉开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大幕。《江湖奇侠传》等作品虽然令人耳目一新,却也并不比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更能吸引南方读者。30年代以后,武侠小说的创作由北派作家接了过来。武侠小说的创作顿时蔚为大观。现在我们所认定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5大家、4大派,即李寿民(还珠楼主)及其“剑侠派”、王度庐及其“侠情派”、白羽、郑证因及其“帮会派”、朱贞木及其“历史派”,都是北派作家所组成。可以这么说,没有这5大家、4大派,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而言。
北派小说中,与武侠小说同样繁荣的还有社会小说。与南方的社会小说相比,北方的社会小说很少写新旧矛盾的交替和争斗,商业气氛和金钱的欲望也很淡漠,爱国小说和“国难小说”几乎没有。它的特色在于描写政治黑幕、码头文化和小知识分子的卑琐人生。这类小说主要的作家和代表作品有:陈慎言的《故都秘录》等;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耿小的的《滑稽侠客》、《时代英雄》等,刘云若的《小扬州志》、《粉墨筝琶》等。
北派市民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家当然是张恨水,他在北京发表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实际上建立了市民小说的新的模式:言情为经、社会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张恨水在上海发表《啼笑因缘》之后,他的创作中心就开始了南移,就不是单纯地用北派小说家概括他了。张恨水之后,京津地区写社会言情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刘云若和梅娘。与张恨水一样,刘云若也是报人出身。他创作的社会言情小说也和张恨水相同,将社会和言情结合在一起,走的是社会言情小说的路子,因此刘云若也就有了“小张恨水”之称。与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是,他缺少张恨水小说的社会广阔性和政治敏感性。他的小说描写的一般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故事性很强,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描写更为细腻,在“小处”见功夫。梅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女作家。4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创作了很多有关女性婚恋生活的小说,其走红的时间与上海的张爱玲相同,因此也就有了“南张北梅”之称。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起来,无论是小说的社会性、文化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梅娘与张爱玲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写上却胜张爱玲一筹。她特别善于细腻地描写婚恋中的女性的心理,哀哀怨怨、款款曲曲,十足的家庭少妇情调。因此,她的小说可称为“闺怨小说”。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以后东北地区的市民小说。东北沦陷之后,日本推行的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市民小说要表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话秘话史话,真事趣事史事,这些作品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底本,用传奇故事的方式表现之,代表作家作品是古丁的《竹林》、爵青的《长安城的忧郁》等。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中创作通俗小说,其作家作品就有了特别的韵味。
相比较而言,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派市民小说虽然创作量不减,但其势头远不如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时期,特别是缺乏一些新生代的优秀作家。相反曾经沉寂一时的北方市民小说却繁盛起来,甚至还延伸至南方,张恨水就是很好的例子。现象的描述只是说明一些史实,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北派的市民小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繁盛起来了呢?
二
北派市民小说以天津为中心,主要的市民小说作家几乎都聚集在天津。这些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首先要在天津取得影响,然后波及到整个华北、东北地区,再推演到全国。解读这样的文学现象,要从现代天津的文化入手。
天津真正进入现代化城市阶段从1860年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市民人口的急剧增加。据统计,天津在1860年开埠之前,人口只不过19余万,到了1948年,人口达到191万余人,一百年不到,人口增加了10倍之多。 与上海城市崛起以及市民的文化需求相同,这些人口主要是由初识字的产业工人、识字较多的小商业者和为城市功能服务的小职员等三个层面所构成。这些市民主要来自于城市周边的农村,处于由“乡民”转化为“市民”的阶段。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又对城市的现代文明充满了新奇感;他们都从事于第一线工作,为能够饱腹而辛勤地劳作,他们关心影响生计的社会新闻要大于那些国家民族的大事;他们无暇(也无能力)对那些深邃的文学艺术进行思考,却对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和愉悦大众文化艺术充满了兴趣。快速扩张的市民阶层及其文化需求是北派市民小说迅速发展的阅读基础。与上海的南派市民小说创作略有不同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的市民小说创作与出版以书局为中心,例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南派市民小说。天津为中心的北派市民小说则主要以报纸为中心。分析原因,估计有三:一是作为出版集团的书局,一定会建立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处于北京旁边的天津缺少这样的位置;二是政治、文化新闻的采集天津的报纸无法与北京相比,它就会向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上努力;三是天津市民对这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报纸特别感兴趣,市民的文化取向和经济实力支持着这些报纸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状态一方面刺激了天津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报纸快速发展,据统计,天津在1928年以前报纸有14种,到1937年报纸有58种,经过了日本占领军清肃之后,到1946年还有51种,其中著名的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天风报》等,均是以刊登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著称的报纸。这种状态的另一方面使得北派市民小说家与这些报纸有着互为生死的依存关系,例如《大公报》与潘凫公、《益世报》与赵焕亭、《商报》与白羽、《庸报》与王度庐、《天风报》与刘云若、李寿民(还珠楼主),他们是当时天津著名的市民小说作家,也是这些报纸主要编辑,甚至是主编。由于主要依靠报纸连载刊登市民小说,北派的市民小说大多是长篇小说,有些是没完没了的连载,乃至冗长。阅读阶层的庞大而稳定、市民需求的社会世俗化、新闻报纸的愉悦而经济适用,构成了北派市民小说从创作、出版,到阅读的良好的循环体制。
现代天津文化构成了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文化特征,现代北派市民小说同样以现代天津文化显示出价值。地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旁边的天津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就一直扮演着“亚官方”的角色,它是众多下野的政客、官僚、军阀以及前朝官员的落脚地、窥视地、养精蓄锐地。陈慎言在《故都秘录》的第一回中,从衣服的角度写了这样一些人物:“有戴珊瑚顶穿国龙马褂的王公贝勒,有朝珠马褂小辫子的遗老,有挂数珠穿黄马甲红长袍的嘉章佛,有戴顶帽佩荷包的宫门太监,有光头黄衣的广济寺的和尚,有蓄发长颈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有宽袍阔袖拿大皱折扇的名流,有礼服勋章的总次长,有高冠佩剑戎装赳赳的师旅长,有西装革履八字髭的官僚……”这里面有旧有新,有文有武,有老有少,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北派人物”,正是这些人构成天津的上层社会。这些人身在天津,心在北京,往返于京津之间,带回来的是真真假假的政治文化新闻、传说、轶事。这些新闻、传说、轶事成为市民小说最好的素材。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内心肮脏、生活腐败,北派现代市民小说写的就是这些政治黑幕以及这些政治人物的家庭黑幕。对于那些政治上层人物的黑幕,身处市民阶层的市民小说作家还只是风闻而已,对于中下层面的官场,他们却再熟悉没有了。于是他们笔下的小官僚和“小衙门”写得特别生动。耿小的在《行云流水》开头说:“我写小说的意思,以是暴露官场上的一点黑暗,而这点黑暗仅今写了万分之一而已。……这部《行云流水》仍旧是写机关的女职员们,自然故事没有影射,起始仍要写位科长……实际上也许是局长,也许是会长,也许是校长……”科长、局长、会长、校长以及他们周围的各色人等如何地骗人骗钱、投机钻营、虚伪弄巧、不学有术就构成了现代北派小说作家笔下的一个个灰色的人生故事。官场揭黑和官场批判是现代北派市民小说的特征,并以此与南派市民小说善写社会黑幕、家庭黑幕区分了开来。
天津同样是华北地区“亚文化”的中心。上海处于吴方言地区,名士佳人,善于抒情,天津地处燕赵大地,侠气为重。燕赵大地传统的侠气在近代社会被鼓动、被刺激起来。天津开埠之后建立了9国租界。与上海租界相比,天津租界有着更多的政治意义,它建立在中国中央政权的旁边象征着一种威力,当然也激起中国官民的民族自尊感。晚清天津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很深的民族原因。到了民国义和团运动没有了,但是义和团的故事和侠义精神却在天津流传和承继。民国初年霍元甲战胜俄国大力士的事迹无论是真是假,在天津最为人们所接受、所流传,说明天津侠义精神有着很广阔的接受市场。这样的侠义精神如果与古代题材结合起来就是侠义小说,如果与江湖题材结合起来就是武侠小说,如果与天津当地的码头生活结合起来就是帮会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帮会小说成为北派市民小说的特色,有着传统的原因,也有着近代政治文化的逼迫。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官场小说的揭黑、批判的态度不一样,北派市民小说对这类充满着侠气精神小说均以赞扬的态度表现之。例如帮会小说主要写天津“混混”。这些天津“混混”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些地痞流氓的形象,在北派市民小说作家的笔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乡邻排忧解难,热心于公益工作;也有些人讲义气,不怕死,敢出头,平时多吃多沾,关键时候也敢为民办事,他们是地方的黑势力,却也是地方上正义的主持者(可参见李燃犀的《津门艳迹》)。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的曲艺开始繁盛起来,评剧成为了天津此时最受欢迎的大众戏曲,与北京社会盛行的京剧成抗衡之势。一些民间戏曲更是人才鼎盛,如京韵大鼓的刘宝全、梅花大鼓的金万昌、单弦的荣剑昌、莲花落的于瑞凤、河南坠子的乔清秀、乐亭大鼓的王佩臣、辽宁大鼓的朱玺珍、时调的五高姑娘、相声的张寿臣等人均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将天津此时的曲艺、戏曲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的程度。天津曲艺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些曲艺团、戏剧团不再是街头演出,都有了自己的表演场所,于是也衍生出各种戏馆、书场、茶社、饭馆等等。这些曲艺、戏曲的表演主要集中在租界和华界的结合部或者是城乡的结合部(例如“南市”等地),居住在那里大多是中下层的城市贫民,他们成为了这些大众文化的主要的消费者。这些大众曲艺、戏曲都是编故事的好手,它们既有传统的拿手的保留剧目,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于是,它们活动本身一方面为市民小说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另一方面那些曲艺的剧情也不断地给市民小说提供素材。大众的曲艺、戏曲和大众的市民小说互为依存、互为哄抬,给此时的天津大众文化不断地添彩加色,当然也给此时天津的大众文化带来了地韵十足:津味。
北派市民小说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制衡的力量。进入民国之后,日本的力量在东北、华北地区日渐增大,特别是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华北也就成为了日本的扩展地区。日本人利用收买、增派顾问、创刊增发等手法控制华北地区的很多报刊,为了对抗日本的奴化宣传,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利用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进行抗日宣传。由于市民小说基本上不涉及政治,争斗的双方对此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市民小说的繁盛。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逐步成为了新文学的中心,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获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左联”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化批判,市民小说虽不是 “左联”批判的中心,却也受到第二波的集中批判(第一波是20年代初期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阿英等人都写过很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相比较而言,此时北方地区的新文学的力量就弱多了,也就是生活在北京的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这些“京派作家”大多是崇尚个性、名士作风,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冷漠相对,对市民大众的宣传不甚关心,属于大众文化的市民小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是没有风雨地肆无忌惮地茁壮成长。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文化市场,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上海风靡起来,对市场嗅觉特别灵敏的市民小说作家纷纷地将自我的发展中心拓展到电影领域,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成为了此时最为走红的电影编剧,他们直接引领了此时中国商业电影大潮的出现。由于电影等时尚市场的失缺,北派的市民小说作家没有受到电影等时尚文化的诱惑,他们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小说的创作。因此从全国创作的视角看,此时北派市民小说实际上成为了全国市民小说的创作中心。
三
繁荣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北派市民小说在美学内涵上要比繁荣于清末民初之际的南派市民小说丰富多了。南派市民小说主要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改良体,而北派市民小说是以传统小说为主干,融合了业已成熟的新小说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营养的综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派市民小说实际上对中国现代市民小说作了一次很有意义的现代改造。
1934年鲁迅就曾说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此话不错,北派市民小说作家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的教育,都是南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爱好者,不少人年轻时就生活在南方,并以“鸳鸯蝴蝶派”作品为楷模进行试笔,例如张恨水、李寿民。到了他们创作的鼎盛时期,新小说创作已成绩斐然,活跃于这个时期的北派市民小说作家都受其感染,有些人曾有志于成为一个新小说作家,例如王度庐、白羽。他们生活在繁盛的北方大众文化氛围中,对中国传统大众文艺相当熟悉,也相当喜欢。特别的时期构成了他们特有的文化文学结构,也给他们对中国现代市民小说进行改造创造了条件。
他们对现代市民小说进行改造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基本上确立了“现代章回小说”的美学结构。这样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市民小说均为章回小说(或者是改良型的章回小说),作为传统的延续,南派的章回小说在社会现实的表现和白话创作方面为现代章回小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还是以写事为中心。以写事为中心的章回小说故事写得再传奇,也会造成冗长和重复的问题,这恰恰是南派的市民小说的缺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的讲述,人物只是某个故事中的人物,并不贯穿始终。到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新闻色彩更加浓厚,甚至将一些新闻传说直接插入到小说的情节之中,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等小说。北派市民小说的叙事中心逐步地从写事转向了写人。现代市民小说作家中最早做出这样的尝试的是张恨水。1924年张恨水创作了《春明外史》。在这部小说中间,张恨水解决了怎样将章回小说中散乱的材料集中起来的问题。他用一个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头到尾把故事情节贯穿起来。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就叫杨杏园。他这样写给小说带来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小说中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后,这个人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脑,小说中的所有的事情都跟这个人有关系,材料再多,再复杂都不会凌乱。主脑就是小说中的根,从根子上伸展出去的各种枝枝叶叶就是枝枝有来源,叶叶有依据。第二个好处是小说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发展成为了小说主要的情节结构,他的命运完整地描述小说结构自然就能完整地体现。小说中的杨杏园是来自于安徽的一个报人,他来到北京就是小说结构的起端;他到北京来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这是小说结构的延伸;最后他死在北京,这是小说结构的结局,整部小说的结构相当地完整。如果小说中没有一个贯串人物的话,就可以无休止地永远地写下去,小说结构就不可能完整。虽然此时还有一些枝叶散乱冗长叙述的小说(例如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总体上说,张恨水之后的北派市民小说基本上是以人物命运作为中心的小说叙事。
既然确立了人物的中心位置,心理分析就不可少。市民小说创作中将复杂的心理描写引入到曲折的情节描述之中是从北派开始的。中国传统小说受话本小说影响很深。话本小说是说话人讲述故事,以描述的语言讲述曲折的情节,情节生动,表述却比较平面。心理分析是西方小说的叙述特征。心理分析最大的优点就是小说人物描述有了立体感,使得小说故事情节发展有了内驱力。南派的市民小说作家对之却不喜欢,清末民初之际,他们翻译西方小说常常将那些心理描写删去,而强化故事情节。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心理描写最早是由市民小说引进,却是新小说家最早运用。到了北派市民小说家手中,心理描写已广泛使用。张恨水自不用说,《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冷清秋等人物的形象生动正是通过描述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人物个性的差异而造成的心理活动的不同表现出来的。王度庐的“鹤—铁系列”均是在情仇两难、恩怨两难、生死两难中做文章,人物命运的选择总是带来痛苦的心理煎熬,心理煎熬的生动描写使得他的小说人物总给人留下难忘形象,江南鹤、玉娇龙、罗小虎等等都成为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经典人物。此时北派市民小说中甚至还出现了以心理描写为线索的小说,白羽的《联镖记》写小白龙方靖被逼出江湖。方靖有着两副面孔,在其妻面前,他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弱书生,在同伙面前他是一个杀人越货的独脚大盗。在情意和匪气之间,在温文尔雅与面目狰狞之间,复杂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举止。不再是静态的心理描述,而是以心理活动为线索写故事发展,说明心理描写在市民小说作家手上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
中国传统小说一直崇尚“史说同质”说,写小说就是写野史,于是根据事件发展的历程因果循环的叙述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体的基本结构。这样的叙事结构在清末民初南派市民小说中已经有了改变,倒叙体已经广泛运用。但是故事主体还是因果循环地描述。北派市民小说作家对章回小说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改造,他们在章回小说的框架中打破了因果关系的描述,将时空倒转、重叠、停顿或者延长,其手法一点也不输于新小说的结构。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是章回体小说,语言叙述上还有不少评书的色彩,但小说结构却采用倒叙的手法。玉娇龙的新疆生活、罗小虎的家庭惨变、高朗秋和耿六娘的匪盗生涯,这些小说的主要故事都是在倒叙中完成的。倒叙的手法首先就设了一个谜,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回忆的叙述又为前面的谜作了解释,故事情节的推进显得合情合理,小说的结构也显得紧凑。因此王度庐小说虽然故事也是不断地枝蔓,却显得完整和紧凑。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写富家少爷与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故事情节并不出新,小说结构却颇有创意,插叙、倒叙娴熟地运用,使得故事情节十分紧凑,也使得人物形象有了厚重感。自如地运用叙事格局看起来也就是个事件叙述方法,实际上它揭示了市民小说的叙述中心不再顾忌事件是否完整,而是关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或者是人物精神是否完整,因此说,叙事结构的转变是小说叙事的根本性的变革。
北派市民小说美学内涵的现代改造,新小说显然是重要的影响源,不用赘言。我要强调是,除了新小说之外,北派市民小说还接受了民间艺术的营养。民间艺术营养的吸收使得北派市民小说的美学内涵更为丰润。世俗性、民间性本来是市民小说的特点,土里土气、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描述,历史、掌故、轶闻、趣事穿插其中,处处透现出地域的韵味,南北市民小说皆如此。北派市民小说不仅写城市世俗风情,还将很多民间传说进行现代化改造,融汇到小说情节之中,我们都认为张恨水《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生活写得很生动。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他们的爱情故事的情节,就会感觉到“唐伯虎点秋香”、“苏小妹三难新郎”等故事的影子;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故事情节显然是天津的说唱艺术的小说版;白羽的《偷拳》则将历史上的很多民间偷艺故事转化成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情节;郑证因的《鹰爪王》中的拜山、破机关、挑黑道,黑门术语如数家珍,这些都是天津说唱艺术家评说侠义故事的拿手绝活。
四
北派市民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从市民小说的角度上论述,北派市民小说的崛起将中国现代市民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推向高峰,特别是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市民小说创作的新的成就。市民小说从上海地区蔓延到全国,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文学现象。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上论述,北派市民小说的崛起使得市民小说在南方失去了主导地位之后,在北方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的新文学创作很热闹,北方以天津为中心的市民小说创作也很热闹,因此此时的中国文学的地图是“南有新文学、北有市民文学”的双峰并峙的局面。
北派市民小说实际上为中国小说建立了一种新的文体。这个文体有别于新小说,它的核心内容是:说故事、写人物。这种模式的建立对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仅仅是写故事,没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小说的格调就不高,美的东西就不突出。这是一些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毛病。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人物刻画,没有生动的故事,人物形象也不能生动地塑造,小说也不能吸引人,这是有些新小说存在的毛病。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形成好小说。既接受一些新的要素,又坚持中国小说的性质,北派市民小说美学内涵的改造实际上体现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现代小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造。如果我们不是将新小说视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现代化惟一模本的话,我们就能充分体会北派市民小说现代化的意义。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把眼光向后搜寻,就看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也都有一个曲折的人生。如果我们打破雅俗的观念将这条线索隐隐约约地贯穿起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看到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就更加重视北派市民小说的贡献,他们又何止于对市民小说创作的贡献呢?说他们引领着中国小说文体走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又何曾不可。
特别应该提及1931年以后东北文学中的市民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在那个地区、那个时间创作市民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表述,还是一种民族气息的留存。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史材”小说的创作,就是要提醒民众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血脉;他们坚持以服务大众为名进行汉语写作,而不是用那些统治者要求的日语写作,就是要保留我们文学的根。所以说,1931年以后的东北市民小说虽然不如津、京地区那么繁荣,却更应该重视,因为它的价值和意义已不仅仅是文化与文学所能涵盖的了。
注释:
①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2页。
②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10、774页。
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严独鹤要求张恨水为南方的《新闻报》写小说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短。所以《啼笑因缘》只有20多万字,而不同于《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那样100多万字。
④鲁迅:《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⑤张恨水18岁时就学于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开始写“鸳鸯蝴蝶派”式的小说、诗歌向《小说月报》等刊物投稿;李寿民17岁时就读于苏州草桥中学(现苏州第一中学),开始了他的文学阶段。
⑥早年的王度庐是位新文化的批评家,曾用“柳今”为笔名,写下140余篇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杂文;白羽在1921年认识了鲁迅和周作人之后,就曾立志做一个新小说家,为之,他多次写信给周氏兄弟求教写作。
标签:小说论文; 张恨水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市民中心论文; 天津生活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金粉世家论文; 春明外史论文; 王度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