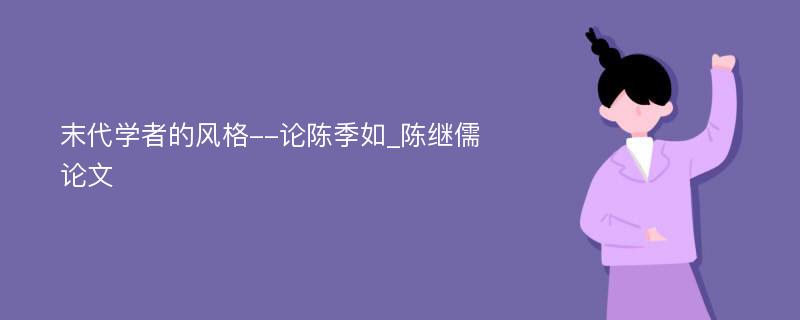
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名士论文,风度论文,陈继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224-04
清人修四库全书,论及晚明小品时总要拉上李贽、屠隆、陈继儒这三个人。在四库馆臣看来,这三个人是儇薄风尚的倡导者。因此我们要谈论陈继儒,最好采取比较的方法,这样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
李贽是晚明思想家,一生倡导真心童心,极力反对伪道学,结果死在监狱里。李贽性行疏狂怪异,袁中道《李温陵传》说他:
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之人,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涕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申,排搨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咮;鸾翮可杀,不驯其龙性。
李贽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与人不同:“读书外,有二嗜:扫地,湔浴也。日数人膺帚、具汤,不给焉。鼻畏客气,客至,但一交手,即令远坐。一日搔发,自嫌蒸蒸作死人气,适见剃者,遂去发,独髭须,秃而方巾。”(刘侗《帝京景物略》“李卓吾墓”条)在李贽眼里,没几个人能当其意。李曾说:“我从来不见有一人果然真正豪杰难得,纵有也不是彻骨地好汉。”(《李温陵外纪》卷二《柞林纪谭》)眼空四海与孤高的个性使他走向愤世嫉俗;当然,他的明察、胆略和锋利的笔舌,却全都向着虚伪卑鄙的世俗,以至于形成了“俗之所爱,因而丑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疏,因而亲之;俗之所亲,因而疏之”(《焦氏笔乘》卷二)。连最敬仰他的袁中道也说他“才太高,气太豪”(《李温陵传》),而他自己也知道,“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续焚书》卷五《石潭即事四绝》其四)。他一生虽不排斥声色酒肉,但对个性独立、自我舒展与自由之心境等精神的追求却孜孜不倦。
再看屠隆。屠隆字长卿,浙江宁波人。他出身贫苦的渔民家庭,35岁中进士,历任知县,继升礼部主事,后被人以淫纵罪告发,落职为民。由官员一下子落职为民,难以为生,只得倚仗他的文名和结交的各级高官来谋生,四处求人。他到处打秋风,并非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却是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他有家庭戏班和女宠娈童,生活放荡。张应文《鸿苞居士传》说他的生活:“坐不可一日无客,客无雅俗,咸礼接,即生平背憎怀隙者诡自前,无间也。颇乐豪华,不问瓶粟,而张声伎娱客,穷日夜。”(《鸿苞》卷首)他总是念念不忘做官的种种好处,以致行为怪异。晚年穷极无聊,被开除十几年了,处分改为冠带闲住,居然仍身穿官服,前往南京一家高级妓院去宴客;最后痛苦地死于梅毒。他思想庞杂,什么都谈,倡导三教合一,其实也没什么突出的见识。屠隆将生命视为虚幻,却又不放弃生命享乐,随缘任运,是晚明士人的一个精神标本。他很有才气,文学上可以说自有一套,自成一家,却时常不能免俗,脚跟不稳,属于风派。他也是当时的怪人之一。
明代士人层级由科举功名决定,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地位很低。如果家境不太好的话,生存会很成问题;若加之较有才气,个性狂放,社会的挤压就会使有些人显得举止怪异,更何况就古代社会而言晚明是个比较充分尊重个性,鼓励追求真性情的时代。但社会的容纳度毕竟是很有限的,所以李贽这样的狂者(异端思想家)被迫害至死,屠隆一类的人物被论列为怪异,经常会受到人们的批评。
然而,在那个产生狂人的时代,有一个人,并无功名,只因曾被举荐,故人称征君;家境并不富裕,早年也曾开塾教书为业;没做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没有怪异之举。没人说他是怪人,却一生得大名,享清福,被称为大名士,大山人。这个人就是陈继儒。
关于陈继儒,清人蒋士铨的一首诗流传较广: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临川梦》见《蒋士铨戏曲集》)
无可否认,陈继儒在晚明文坛上,的确是领袖式的人物:以其山林身份主持文坛,确实是“大架子”;但文学成就并不高,说他是小名家,品评倒也不差。钱谦益曾说:“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极风致,智如炙髁(当作輠),用之无穷。”(《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陈征士继儒”)这等于说他是小名家。至于说他无心走终南捷径,当然也是事实。他弃科举,不求功名是真的,不像有些人内心总是不平,总想碰运气。他曾多次拒绝各级官员的荐举,虽身处江湖,声名却如日中天,倾动寰宇。他的著述虽然不少,结集的就有多种,但影响最大的倒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所编纂的书籍,声气所到,几于无人不知,正所谓“獭祭诗书充著作”;至于说他润色烟霞,妆点山林,也不过分。他曾为王锡爵家伴读,王是当朝首辅,与王世贞交往也很密切。因此,从更深层面上说,了解陈继儒,是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
陈继儒高度自信,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无悔言,既不欣羡高官厚禄,也不自卑,而勿宁说充满了洞达世事的旷达与自信。其文集的第一篇《快赋》就可视为他对自我的设计与安排,充满了自得之情。自古以来咏隐士,其着眼点多在“逸”;而他则着眼在“快”,这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陈继儒身无功名,一举不中,便退隐山林,绝意仕进。《明史·隐逸传》说,明中叶以来,隐逸之士很少,只有陈继儒“抱瑰才,蕴积学,稿形泉石,绝意于当世”。正因为如此,他对科举功名的态度比较平和,不像其他人,屡考不中后虽鄙视科举,却总也放心不下。他与董其昌并游庠序,如宫商相生,水月相赴,时人比为齐晋兄弟之国。但董氏高中,官翰林:而陈氏则枯隐山林。一龙举,一鸿冥,天壤之别。时人或借董以窥陈,引起了陈继儒的强烈不满,因而他在《序董玄宰制义》中称:“大丈夫义不再辱,岂有高卧清凉之荫,而复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他呼吁:“以陈生当陈生,董生归董生!”(《陈眉公集》卷六)在以科举功名衡量人的价值的晚明时代,敢于如此自信地宣称“我不奈我何,卿应自爱卿”的,大概只有陈继儒了。
其实,他虽讲隐士的高洁和孤傲,但实际表现的却是幽冷,是站在外面冷眼观场、嘿然一笑。这不是达观,而是旁观者清,是洞达世事后的智慧与狡猾的结合,正如钱谦益所说,是“妙得阴符之学”。所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世俗的一面。他曾说:“古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钓弋,余禁杀,二不能;多有二顷田,八百桑,余贫瘠,三不能;多酌水带索,余不耐苦饥,四不能。乃能者唯嘿处淡饭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驳先贤,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岩栖幽事》)晚明文人好作自誓之词,此为一例。这里所宣示的“嘿处淡饭,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的生活态度,固然有源于现实的无奈,有一丝隐忧之痛,但毕竟掩盖不了自保的用意。这是末世的名士风度,而不是战士的斗争或失败。陈继儒很讲究交往的艺术,他曾深有所得地说:“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曹臣《舌华录》)别人见他,他都热情接待;有时也发发牢骚,但做起事来却从不含糊。这与李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记载,一位黄山人曾拜访李贽,冲风冒寒,不顾年老体衰,随一位显官同去,见李贽后却说因为去路相同,故同行;又说彼俟我于城中,不能一宿,回来时当聚以三五日。李贽眼明心亮,说其人不过为一食难于割舍,如饿狗思想隔日屎,对别人说要拜访我,对我说要游嵩山少室山,两相欺骗。李贽这样的接物态度,能不得罪于整个社会吗?
陈继儒的风度则受到来自各方的赞扬。董其昌称其“钟鼎之业,乃在山林”(《白石樵真稿》卷首《序》);程嘉燧至以“山中宰相”称之;王思任称其“不以白衣牵带坐,而使之山中宰相以老,弱其雄心,缩其妙手,以写景标韵于水山僧鸟之际”(《晚香堂小品》卷首《晚香堂小品序》)。然而这不但没有使他感到自足,反而增添了忧惧之心,在《与杨学台》中,他说:“天曰忌盈,必罚之以奇祸;人情责备,必中之以奇谗。”(《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三)有谁能想到,他这样一个名动朝野的大名士、大山人在临终遗训中竟说:“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危临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陈眉公先生全集》卷末附)别人称赞他处世平易,他很不满意,说自己生活得如“惊雀拱鼠”。这种忧惧不能说他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但因为他的一生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一切以自我的利益不受损害为中心,而这一切又要靠密切的人际关系、靠结交上上下下各色人物才能达到。要玩得轻松,实在是不易的事,故而他说是“履危临深”;只有以自得的心态,不得罪于人,亦不失自我,才能“鸢飞鱼跃”。他与高官交往密切,在信中也常论及政事;但他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从不得意忘形,不论及具体人事,而只谈具体的地方事务,如某年地方大旱,他出力出钱帮助赈灾,信中所谈非常具体,有事实、也有办法,甚至谈及总赈数量、受赈人数,还统计出未受赈济人数,十分难得。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不能说没有,清代的袁枚也曾以布衣身份得大名,享清福,但与陈继儒相比,总显得有点轻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
陈继儒提出了一种在晚明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态度:“可以经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笔舌,自相尔汝,自相师友,岂必南面皋比塵尾送难哉!”(《岩栖幽事》)经世、出世、警世、垂世、玩世五者在他看来并没区别,只要以“自相尔汝,自相师友”的态度一以贯之,不必南面称师,与人辩难。这与他在《岩栖幽事》中所说的“著述家切弗批驳先贤,但当拈己之是,不必证人之非”是一个意思。他曾自述其志云:“余每欲藏万卷异书,袭以异锦,薰以异香,茅屋芦簾,纸窗土壁,而终身布衣,啸咏其中。客笑曰:果尔,此亦天壤一异人。”(《岩栖幽事》)
尚奇尚异是晚明文艺界最流行的风尚。奇与异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代表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它是晚明士人内在精神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异的产物。陈继儒对“异”的推重,并以之作为人生理想,其实质是对自我身份的确定。“异”是他与其他文士相区别的标志。“解脱”是晚明士人的精神追求,陈继儒也不例外,但他所说的“解脱”却与晚明性命之学不同。他所谓的“解脱”,是对现实的疏离。李贽对生命本质的追求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陈继儒完全抛开,而代之以冷眼旁观,只剩下对个体解脱的关注;与此相关,“自适”之说便成为一个只与个体解脱相关的纯粹自我主义的主张,“自相尔汝,自相师友”,不与现实生活发生大的关联,在个人的小天地中完满自足。
另外,陈继儒在奇与异之间只取异不取奇。他说:“仆非不能奇,顾奇者,畸也,独往独来之谓也。若耦于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耦则二矣,二则能奇乎?”(《白石樵真稿》卷一)他在《与方公旦心》中进一步申说道:“当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然狷之有所不为,尚置之贤知过中,则圣贤豪杰,喜静而不喜动,喜冷而不喜热,可知矣。”(《白石樵真稿》卷二)联系前面所引的文字,可知尚异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意在以此与外在世界隔离开来,是捐者有所不为;而“奇”的最基本指向是“狂”,在他看来,狂者进取与中行乡愿虽为不同行为,但终归救不得世,甚至可能伤生。这是典型的明哲保身哲学,求一己之安足矣。在陈继儒这里,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思想界勇猛精进、豪侠自许的精神彻底消失了,只剩下苟安于世的些微愿望。至此,自适演变为闲适,纯粹以个人高雅脱俗的趣味为中心,以一种自我生命的游戏态度,构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不离不弃、若离若弃的生存空间。
闲适的态度是一种极端的快乐主义,它披着高雅的外衣,表面上看起来淡泊自守,其实是占尽天下便宜;但陈继儒也使人有同道之感,他就生活在现实中,是可学的。他调和狂人恣肆与隐居自适、冷眼看人与热肠报国这样势同两极的人生态度,从而达到了一个建立在洞察世事基础上的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冷眼与热肠互用,不弃世,不厌世。陈继儒真可以说既学到了《老子》的精髓,又成功地辅以老道的为人处世的工夫,柔而不媚,刚而不硬,宽厚与精明结合,智慧与狡猾合一,时刻坚守本分,不做出格的事,完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建构;同时,在思想上,他又以自我为中心完成了思想移植,保留了传统文人的自在与自适,调配上当时代精神解放的内容,在躁动的年代里,拌以清淡平和的精神佐料,造就了一套新旧杂糅的人生模式,因而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
作为一个名士、山人,得大名,享清福,除了独特的人格建构外,还得有文化上的、文学上的特异之处才行。明代很多山人的家境、出身、遭遇与陈继儒相同,但都没能混到他这个份上,不能不承认他有独异于众人之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很多,但一个人要想受别人的尊重,最起码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可现实是,许多穷文人没有。怎么办?很多人投靠公卿,谋一口食,待遇可想而知。但陈继儒一试不中,就弃衣冠,自谋生路,说可以说得很漂亮,具体生活还得靠自己解决。大多数山人选择传统的方式谋生,如入幕、卖文。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文人不能没有影响,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不会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经商,而多以文化产业为主。因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商业的,才多少能让他们心安。所以,不少人失意文人开始从事图书的编纂、出版活动。如张凤翼、梅鼎祚,生活都相当不错。陈继儒的文化经营活动是自觉的选择。当然,他说得很漂亮:“删花洗竹之暇,拾残蕉败叶书古人一二可喜者。”后来,以他的名声和地位,当然就不必亲自动手了。《列朝诗集小传》云:“仲醇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寻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撮成书,流传远迩。”陈氏自己则着力回避,说得非常隐晦。他编了大量的书,很受欢迎,以致出现争相购买的场面,仅《四库全书》就收有八种,如《笔记》、《读书十六观》、《群碎录》、《珍珠船》,《销夏录》、《古今韵史》等,现在市场上印得较多是的《小窗幽记》。这些书往往是“取杂事碎语”或“清胜之事”而成,并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所以蒋士铨说他“附庸风雅”,是“小名家”。虽然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他的收入状况,但从上述情况看,经济收入不会少,不然他不可能过上这样的清雅生活。这在古代文人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文人终于可以既不走科举做官的路,也不必依附于人受邪气,而完全靠自己,靠一枝笔,自得自适。既有经济效益,也有文化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名利双收,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讲的陈继儒。他身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文人,他是时代的产物,是晚明文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形态。
晚明以来,小品盛行。今天我们谈晚明散文,常用“小品”概念,但这个概念更多是受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这里的“小品”概念指的是文类而不是文体。其实,在晚明,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指杂俎笔记,其中的一种类型称“清言”,它与魏晋士人的清谈不同,它没有思辨的色彩,而大多是一些富于哲理趣味的人生感悟和清雅超俗的生活设计,是生活理想的形象化表述。故而小品涉及面很广,举凡人生哲理、人情世态、论文谈艺、山水泉石,花草虫鱼,无所不有。清言在形式上也非常自由:有的是格言、箴言式的,可骈可散;也有的与传统笔记较为接近。陈继儒在这方面的影响极大,如《岩栖幽事》开篇第一句就说:“多读两句书,不说一句话。”这是他为这种清言所代表的清雅生活定下的一个基调,即所谓“一味安稳本色”。第二则的描述就更诗意化了: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鼎彝令人古。
陈继儒所设想的这种生活还包括幽隐生活中所不应涉及的内容,如:
不混酒肉,不竞田宅,不问炎凉,不关曲直,不与征逋,不谈仕籍;如反此者,是饭侩牛店,败马驿也。昔之隐者放言,今之隐者孙(逊)言,然出于口,落于笔,皆言也。慎于口而不慎于笔,谓之孙(逊)言,可乎?
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清赏”,表述的是文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优雅、闲适的情调,把清言小品中的生活理想现实化。读书是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陈继儒很推崇宋代黄庭坚说过的话:“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看什么书呢?当然是清闲消遣之书。陈继儒说:
心闲手懒,则观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闲心懒,则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闲,则写字作诗文,以其可兼济也;心手俱懒,则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诗及杂短故事,以其易于见意,不滞于久也;心闲无事,宜看长篇文字,或经或注,或史传,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风雨之际及寒夜也;心手俱冗,则思早毕其事以宁吾神。
清赏生活具体还包括收藏金石彝器、法书名帖、书画版刻并加以品鉴;品茶也是晚明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陈继儒说:“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他还讲究饮食、园林、室内布置、花瓶、盆景等。总之,举凡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赋与了清雅的意味。
小品的另一类是冷眼相向式的议政小品,但陈继儒很少针对具体人事发论,只有《安得长者言》谈得较多,如:
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此二语其宰相、台谏之药石乎!好义者往往曰义愤,曰义激,曰义烈,曰侠义,得中则为正气,太过则为客气。正气则事成,客气则事败,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义以为实,礼以行之,逊以出之。
联系晚明政治,他的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表现了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晚明士人的言论中并不少见,只是一般士人的思想既无深见特见,也没有深厚的历史感,片言只语,聊以抒愤,政治关怀只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味调料,是一种政治清谈。当然,陈继儒还有很多关于社会道德的论述,多有明显的劝诚意味。
陈继儒的小品传达的是人生体悟。这种人生体悟虽然包含了一些人生哲理,但大多只是情绪化的浅层次的体味,在晚明特定的文化氛围里更是如此。清言、清赏只是想像中的生命安排,因此,禅悟流于浅层次的捏合,议政流于清淡,道德关怀流于劝善,也就一点都不奇怪。陈继儒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晚明士人精神境界的标本。他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一大批士人在政治黑暗的年代里,如何退而自保,如何以虚无的人生观对待现世的肥皂剧。
陈继儒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尚。他矜博识,逞小慧,说尽了便宜话,占尽了天下便宜,又表现得高雅自得。他在文学上并没有太了不起的建树,诗文一如其人,淡雅而舒卷自如;他笔下也经常有些看似平淡实则奇异的话,如“惊雀拱鼠”之喻、“曝鳞点额”之比等,非常形象,可谓绝妙。陈平原说陈继儒哲学上不如李贽,文学上不如袁宏道,才气不如徐渭,绘画不如董其昌,可偏得大名,享清福,其根源就在于他实践了晚明一大批文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
收稿日期:2005-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