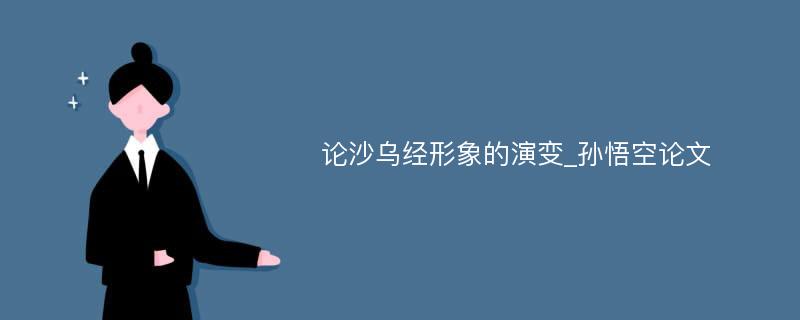
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沙和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游记》中的沙和尚,专家们一般都认为形象苍白,不怎么值得研究。因而,当前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都没有给他一点篇幅,专题论文就更属凤毛麟角了。
实际上,这一形象虽不及孙悟空和猪八戒形象那么鲜活,却是个颇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只要认真作番考察,便知他的那种显得没有任何个性特点,其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个性特点。这在文学作品中是最难刻画的形象,不是大手笔是刻画不好的。所以,也就比较难以研究,而不是不怎么值得研究。
谨从形象演化的角度对沙和尚其人以及有关问题作番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从沙漠恶煞到沙河水怪
沙和尚这一人物形象虽孕育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实萌生于玄奘弟子慧立与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该书卷一“起载诞于缑氏,终西届于高昌”,写玄奘过玉门关外第四烽,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其文云:
从此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今日观之,玄奘“至沙河间,逢诸恶鬼”云云,乃沙漠上的海市蜃楼现象在一个宗教徒心理上的反映,又经其弟子慧立和彦悰着力渲染而已。
然而,旧时的中国是个最严守封建宗法秩序的国家,也是个多神论的国家,认为山有山灵,水有水神。置身于这一社会思潮下而又怀有宗教心理的人,当更易想象出那主宰沙河的神灵定然是个恶煞。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沙河”,乃“长八百余里”的“莫贺延碛”,亦即今戈壁沙漠是也。而这,也就是《取经诗话》中那深沙神形象的由来。
《取经诗话》,据我考证,当是北宋年间的作品。深沙神形象见之于第八则。该则原题缺,正文亦残。其文曰:
深沙(神)云:“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尚曰:“你最无知。此回若不改过,教你一门灭绝!”深沙(神)合掌谢恩,伏蒙慈照。深沙(神)当时哮吼,教和尚莫敬〔惊〕。只见红尘隐隐,白雪纷纷,良久,一时三五道火裂,深沙衮衮〔滚滚〕,雷声喊喊,遥望一道金桥,两边银线,尽是深沙神,身长三丈,将两手托定;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过了。
深沙神合掌相送。法师曰:“谢汝心力。我回东土,奉答前恩。从今去更莫作罪。”两岸骨肉,合掌顶礼,唱喏连声。
这是一段奇文!“金桥”、“两岸”云云,似乎说那“深沙”是条无边无际的弱水,深沙神乃“深沙河”水怪;而“红尘隐隐”、“深沙滚滚”云云,又分明说那“深沙”是片极目千里的沙漠,深沙神乃“深沙河”恶煞。然而说奇也不奇,因为任何奇特的想象都离不开主体的生活经验。这种架桥而过“深沙”的奇想,实反映了作者虽知玄奘昔日所过的“沙河”并非茫茫弱水,而是渺渺沙漠,却由于他未见过沙漠,而只见过河流,所以想象不出那“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的情景,遂方之以江河,让深沙神作法架起金桥以渡唐僧。而这,无意中也就为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将沙河写成弱水、把沙和尚写成水怪着了先鞭。
今见这类作品,当以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为最早。其第三本第十一出“行者除妖”,写:
〔和尚挂骷髅上云〕恒河沙上不通船,独霸篙师八万年;血人为饮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小圣生为水怪,长作河神,不奉玉皇诏旨,不依释老禅规;怒则风生,愁则雨到,喜则驾雾腾云,闲则搬沙弄水;人骨若高山,人血如河水,人命若流沙,人魂若饿鬼。有一僧人,发愿要去西天取经。你怎么能够过得我这沙河去?那厮九世为僧,被我吃他九遭,九个骷髅尚在我的脖项上。我的愿心,只求得道的人;我吃一百个,诸神不能及;恰吃得九个,少我的多哩。看什人来者?〔行者上云〕渡船!渡船!〔沙和尚云〕又是个合死的来者。〔行者云〕你姓什么?〔沙和尚云〕我姓沙。〔行者云〕我认得你,你是回回人河里沙。〔沙和尚云〕你怎么知道?〔行者云〕你嘴脸有些相似。〔沙拿行者咬科〕。
“河里沙”云云,显然是孙悟空的插科打诨,既在说沙和尚像水中的妖怪,又在说沙和尚秃头秃脑像河里的王八,所以沙和尚一醒悟过来,便扑上去咬孙悟空。论者却认为“河里沙”有可能是“阿里沙”之误,而“阿里沙”又有可能是实有其人的回族僧人,沙和尚形象便是以他为原型的,我以为这实在求之过深。
要注意的是,《西游记》杂剧这种将沙和尚写成沙河水怪,当与元人取经故事的说法必不相背。世德堂本《西游记》遂从而继承之,其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写在“流沙河”为妖的沙和尚对观音说:
“菩萨,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
这“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果然是个“异物”,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奉法收悟净”写沙和尚拜见了唐僧,即依木叉的吩咐,“将颈项下挂的骷髅取下,用索子结作九宫,把菩萨葫芦安在当中,请师父下岸。那长老遂登法船,坐于上面,果然稳似轻舟”,飘然渡过渡沙河。
写到这儿,应有的结论是什么呢?主要的结论有四:
《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故事,是由《三藏法师传》中的玄奘过沙河故事演化出来的。那深沙河不是弱水,而是沙漠,深沙神不是弱水水怪,而是沙漠恶煞,便是明证。然而,深沙神以金桥渡唐僧过深沙河一事却为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基因,其凶神亦随之而演化为水怪。此其一。
《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是沙和尚的雏型,尽管他还不是唐僧的弟子。世本《西游记》中流沙河时期的沙和尚,他项下的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是由深沙神项下的两个取经人的骷髅演化出来的,他用以渡唐僧过流沙河的由九个取经人的骷髅结成的法船是从深沙神用以渡唐僧过深沙河的金桥银线演化出来的。随着深沙河由沙漠一变而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弱水沙河,再变而为世本《西游记》中的弱水流沙河,沙漠恶煞深沙神也就随之而演化为弱水水怪沙和尚,其共同特点都是头顶一个“沙”字和曾吃取经人,而这正是种血缘上的和秉性上的文化遗传基因。深沙神两度吃取经人也罢,沙和尚九度吃取经人也罢,这对妖怪来说,是服食采补,它属于道教文化系统。唐僧生前取经曾两度遭难也罢,曾九度遭难也罢,这对和尚来说,是累世修行,它属于佛教文化系统。所以,沙和尚的由曾吃取经人而皈依佛门,实际上也是种“由道入释”;而这种“由道入释”,正是当时社会上的佛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在人物塑造上的深层反映。然而,沙和尚一入释门,便成为品位高于“行者”的“和尚”,显然是由于他在沙河为妖时曾九度吃过取经人。吃了取经人,便获得被吃者的“善缘”,这又是道教的服食采补说在人们头脑中的深层反映。由此可见,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形象,它不只深层地反映了当时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而且还深层地反映了当时释道二教思想的圆融,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此其二。
《取经诗话》中降服深沙神的是唐僧,《西游记》杂剧中降服沙和尚的是孙悟空,世本《西游记》中降服沙和尚的是观音菩萨。凡此,说明取经故事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就是唐僧在取经中的作用日益减弱、孙悟空在取经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观音由一般护法者而日益成为取经队伍的直接组织者和真正领导者的过程。所以,孙悟空和观音也就成为世本《西游记》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没有孙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没有观音菩萨,孙悟空尽不了其器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我以为早晚会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其三。
《取经诗话》之以金桥银线渡唐僧过深沙河,《西游记》杂剧和世本《西游记》则干脆将沙河和流沙河写成弱水。假若再结合作品的形式和语言艺术来考察问题,则知取经故事的起源地和最初盛传地区,当不在缺水多沙的大西北,当在河洛一带及其以南。而我们知道,玄奘取经事迹的神魔化是以推行者的加入取经队伍为标志的。假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早在北宋以前就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成为猴行者的原型,因而孙悟空是个“进口”猴,则此以“取经烦猴行者”为其特点的取经故事,其起源地和最初盛传地区,当不在河洛一带及其以南,当在多沙缺水的大西北。足证我在《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中说孙悟空的形象不是由哈奴曼演化而来的,它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佛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是个标准的“国产”猴,此说并不是没有道理。此其四。
质之方家,以为何如?
从无名天将到卷帘大将
无论深沙神,还是沙和尚,都不是一般的妖魔,都是被玉帝贬入下界的天将。
《取经诗话》写深沙神,一则说他曾两度吃了取经人,宛然是个十足的恶魔,一则说他“一堕深沙五百春,浑家眷属受灾殃。金桥手托从师过,乞荐幽神化却身。”“一堕”云云,则又分明说他是个思凡被谪的天将。正是深沙神的这一实际身份暗中规定了沙和尚的出身是似魔而实神这一本质方面。
然而,深沙神在堕入下界前究竟是哪员天将呢?或说书人在畅而演之时曾作交代亦未可知,但作品中却没有写。《西游记》杂剧呢?它对沙和尚的为妖为神交代得一清二楚:一则说他曾九度吃了一“发愿要去西天取经”的僧人,是个“血人为饮肝人食,不怕神明不怕天”的“水怪”,一则又直白无误地说他“非是妖怪,乃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带酒思凡,罚在此河,推沙受罪。”正因为这位卷帘大将被玉帝贬入下界为妖是由于他的“带酒思凡”,所以在成为唐僧的弟子以后犹“色情未泯”,以至路经“女人国”时还曾偷偷与宫女鸾颠凤倒。凡此,与元人取经故事中的说法当一致的。
那么,世本《西游记》又是怎么交代沙和尚的来历的呢?“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故此这般苦恼。没奈何,饥寒难忍,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九云:“国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唐东岳庙《尊胜经幢》载诸神名,有南门卷帘将军。然则《西游记》衍义,有卷帘大将之名,亦非无本也。”需要予以补说的是:随着深沙神之演化为沙和尚,其前身亦由无名天将演化为卷帘大将,实事有必然。何以见得?还需从《三藏法师传》中的人物配备说起。
《三藏法师传》写玄奘西行,从玉门到伊吾,他是个杖策孤征的苦行僧。从伊吾以西,他是名闻遐迩的访闻学者,再不是孑身一人了,仅高昌王麴文泰就曾为他“度沙弥以充给侍”。
《取经诗话》写唐僧西行,“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云:“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小师应诺。”又云:“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僧行六人”,是始离长安时的人数;“僧行七人”,是猴行者加入取经后的人数。所以,其后各则,皆云“僧行七人”,可谓完全合辙。比如,第三则,云:“良久之间,才始开眼,僧行七人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宫了”。第四则,云:“大小蛇儿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第五则,云:“早起,七人约行十里”。第六则,云:“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第八则,云:“师行七人,便从金桥上过了”。第九则,云:“僧行七人,深谢国王恩念,多感再三”。第十五则,云:“法师七人,焚香望鸡足山祷告,齐声恸哭”。第十六则,云:“僧行七人,密记于心”。最后一则,云:“七人上舡,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我们知道,猴行者的职守主要是充当向导,其次才是降妖伏怪。那么,长安随来的五个“小师”,其主要职守又是什么呢?“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说得明明白白:“买菜做饭”。亦“给侍”僧而已。
这里,“僧行七人”只有一个充当向导的猴行者是神魔,说明玄奘取经历史故事的神魔化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这种神魔化的日益加深,当会演化出一个神魔来充当唐僧的给侍以替代五个“小师”。这个神魔,就是被贬入尘间的卷帘大将沙和尚,而不是天蓬元帅猪八戒。何以知之?
从人物的主要职守来说。卷帘大将既以灵霄殿下侍銮舆为其主要职守,不言而喻,当是玉帝的侍臣。那么,作为取经队伍中的一员,沙和尚的主要职守又是什么呢?《西游记》杂剧没有说,说得一清二楚的是元人取经瓷枕。枕上依次绘着手执生金棍的孙悟空、肩扛九齿钉耙的猪八戒、骑马扬鞭的唐三藏、高擎伞杖的沙和尚,正励志西行。由此可见,孙悟空是开路先锋,猪八戒是唐僧的前卫、孙悟空的主要助手,沙和尚是唐僧的后卫,并照顾唐僧的起居。再看世本《西游记》是怎么写的:孙悟空因一路“炼魔降怪有功”,正果“斗战胜佛”;猪八戒因“口壮身慵”而一路“挑担有功”,正果“净坛使者”;沙和尚因一路“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正果“金身罗汉”。问题很清楚,玉帝的侍臣卷帘大将之成为唐僧的贴身侍卫沙和尚,是有原因的,其契合点是“侍銮舆”和“擎伞牵马”职守上的相若,因而人们于联想中也就将他们挂上了钩。
从形象的实际由来来说。那深沙神的故事在《取经诗话》中虽见于第八则,却前有伏线,后有关照。比如,第二则写猴行者对三藏法师说:“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途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第八则写三藏法师吟诗曰:“两度曾遭汝吃来,更将枯骨问元才。而今赦汝残生去,东土专心次第排。”便是如此。比如,第八则写猴行者吟诗曰:“谢汝回心意不偏,金桥银线步平安。回归东土修功德,荐拨深沙向佛前。”第十七则写三藏法师启奏唐太宗云:“取经历尽魔难,只为东土众生。所有深沙神,蒙佗恩力,且为还恩寺中追拔。”唐太宗允奏曰:“法师委付,可塑于七身佛前护殿。”也是如此。这么一个在全书情节结构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形象自会在后来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三藏法师的给侍又有待于神魔化,于是那曾在流沙河九度吃了取经人、剃度后又成为三藏法师贴身侍卫的沙和尚也就呼之欲出了。假若发现一部宋元取经作品,里面三藏法师的弟子,只有充当向导的猴行者和充当给侍的沙和尚,那我将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这种取经人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正是《取经诗话》中取经人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之合乎逻辑的发展。
要注意的倒是堂堂卷帘大将何以被玉帝贬入下界为妖吃人。《西游记》杂剧说他是由于“带酒思凡”,所以玉帝罚他在沙河“推沙受罪”,他的吃人是出于还“愿心”。世本《西游记》说他是由于“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所以玉帝将他贬至流沙河,又教七日一次用飞剑去穿他胸肋百余下,他的吃人是出于“没奈何,饥寒难忍”。这一变易虽则很微小,但,一个是在歌颂玉帝的圣明,批判卷帘大将的“思凡”,一个是在讥刺玉帝的不仁,同情卷帘大将的遭际,其思想内涵上的差别真是不谤霄壤!
从唐僧二弟子到唐僧三弟子
宋元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本是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已是明代人的作品。这是个历来不为专家学者注意的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圣僧,一个充当向导的猴行者,一个充当给侍的沙和尚,标志着取经队伍的神魔化的完成,形成了取经队伍的基本构架。所以,紧接猴行者加入取经队伍的,当是沙和尚,而绝不会是猪八戒。纵然猪八戒与沙和尚是同时加入取经队伍的,一个是由其他故事演化来的,一个是从取经故事演变出的,也由于中国人的“疏不间亲”而在位分上使沙和尚成为唐僧的二弟子。
这不是我的好推论,是有史料可证的。《朴通事谚解》云:
其后唐太宗敕玄奘法师往西天取经,路经此山,见此石猴压在石缝,去其佛押出之,以为徒弟,赐法名吾空,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雄,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
“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坐次排得多清楚!那么,这会不会是一时的疏忽呢?不会。因为《西游记》杂剧中的唐僧二弟子也是沙和尚。这可以从两方面看问题。一方面,该剧凡六本二十四出,写唐僧收孙悟空为弟子在第十出,写唐僧收沙和尚为弟子是在第十一出,写唐僧收猪八戒为弟子是在第十六出:这已足以说明沙和尚是唐僧的二弟子。另方面,写唐僧取得真经,将返东土时云:“咦!绝怜孙悟空,神通真个有,东土中脱却轮回,西天路翻个筋斗。念沙和尚,有像作无像,喉中三寸元阳,胸中一点灵光。好个猪八戒,神通世间大,已得除新害,既有成必有败,阴阳剥始消除快,有心我你不能安,无念大家得自在。”这又足以说明唐僧的二弟子是沙和尚。既然如此,难道还不能定谳吗?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第十七出“女王逼配”,其中的一处宾白作“诸女做捉翻孙猪沙发科”。第二十二出“参佛取经”,其中也有一处宾白作“孙猪沙弟子三个,乃非人类,不可再回东土,先着三个正果”。该剧虽成书于元末明初,比世本《西游记》早100多年, 却刻印于万历甲寅岁,比世本《西游记》晚12年。刻印时经弥伽弟子“若心雠校”。因而究竟是由于元末明初乃沙和尚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三弟子的转变期而出现了此差异呢,还是弥伽弟子在“若心雠校”时由于蒙受当时的沙和尚已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而出现了此差错?因无足够材料可作旁证,目前还难作出科学的论断,我个人以为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但是,可以肯定,把沙和尚写成唐僧的三弟子,这决不是始于世本《西游记》,早在无名氏《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祐民忠孝二郎宝卷》中就是如此了。该宝卷写的虽是二郎神的故事,却经常说及唐三藏西天取经。特别是“五眼六通品第十三”,其《乐道歌》云:
老唐僧,却取经,丹墀领旨拜主公。谢圣主,出朝门,前行来到一山中。收行者,做先行,逢山开路无人阻,遇水叠桥鬼怪惊。老祖一见心欢喜,高叫徒弟孙悟空。望前走,有妖精,师徒俩,各用心,又收八戒猪悟能。两家山,遇白龙,流沙河里收沙僧。望前走,奔雷音,连人带马五众僧。唐僧随着意马走,心猿就是孙悟空。猪八戒,精气神,沙僧血脉遍身通。师徒们,不消停,竟奔雷音取真经。见活佛,拜世尊,开宝藏,悟心空,三华聚顶五气生……
老唐僧,为譬喻,不离身体。
孙行者,他就是,七孔之心。
猪八戒,精气神,养住不动。
白龙马,意不走,锁住无能。
沙僧譬,血脉转,浑身运动。
人人有,五个人,遍体通行。
这里,辗转相陈,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次第不变。足见,沙和尚已成为唐僧的三弟子。《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祐民忠孝二郎宝卷》刊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比世本《西游记》早三十年。
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沙和尚作为唐僧二弟子的诸多特点,这在世本《西游记》中已成为唐僧三弟子的沙和尚身上依然存在,只是专家学者们谁也没有去注意而已。比如,孙悟空的主要职守是充当开路先锋,沙和尚的主要职守是充当唐身的贴身侍卫,而猪八戒的职守则介乎二者之间,假若必须辞退一个,该是谁呢?当是猪八戒!比如,正如猪八戒自己所说:“三人出外,小的儿苦。”远路没轻担,照理,行李应由唐僧的三弟子去挑,可一路摩肩压担的却是猪八戒,沙和尚只是帮换一肩而已。比如,四人正果西天时,唐僧加封为旃檀功德佛,孙悟空加封为斗战胜佛,猪八戒加封为净坛使者,沙和尚加封为金身罗汉。罗汉乃上座部佛教(小乘)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其义有三,一曰断除贪、瞋、痴等烦恼,二曰应受人天供奉,三曰不受生死轮回。其品位之尊,净坛使者焉能与之并驾!这就难怪他老猪要闹情绪了。
问题是,沙和尚又为什么会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五行观念,决定了人们不只将取经故事中的深沙神演化为沙和尚,而且还将一个黑猪精引入取经故事演化为猪八戒。一个是从其他黑猪精故事引进的,所以形象本来就比较鲜活,一个是从取经故事自身孕育出的,所以形象也就比较苍白。二是,孙悟空作为猴精,猪八戒作为猪精,其形态,其性情,都完全相反,一个瘦小、机敏,一个粗胖、笨拙,用不着怎么驰骋想象,便可将他们处理为天造地设的搭档。《云麓漫钞》云:“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兀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装为山东河北叟以资笑端。”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关系的演化,一旦蒙受这种市民对农民的捉弄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反作弄之结对子形式的影响,那么,岂但作为唐僧给侍的沙和尚,就是唐僧本人也只好俯首低吟“芙蓉开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了。三是,随着取经故事之日益演化为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传奇,猪八戒作孙悟空扫妖灭怪的主要助手,其表演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其在取经人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上升,而沙和尚作为唐僧的给侍,其表演机会也越来越小,其在取经人中的地位则越来越低。由此可见,随着取经故事的演化,沙和尚日益由唐僧的二弟子演化为唐僧的三弟子,这是必然的,不是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世本《西游记》的作者着重从这个取经小家族的人际关系中去描写沙和尚,实在是别开生面;而这一别开生面,在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却开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从日常人际关系中去塑造人物形象的先河,其功是不在禹下的。
请不要以为考察元人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究竟是唐僧的几弟子,是件没有意义的工作。研讨一些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之成书年代,便不可不注意这一问题。比如,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认为杨致和《西游记》“成书于明代前”。可在这部作品中,沙和尚却是唐僧的三弟子,其写唐僧收弟子的经过,也依次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而这,便是它不可能早于《西游记》杂剧,只能是明人作品的硬证。更何况,该书的故事梗概、情节次第及妖精名目,几全同于世本《西游记》,元人决不可能有取经作品如此。
一个品位不高的循吏的典型
世本《西游记》中的沙和尚,昔日玉帝的侍臣,成了唐僧的贴身侍卫。这一职守是心高气傲的孙悟空所不屑干,憨直愚笨的猪八戒所干不了的,只有沙和尚其人堪称材得其用。
首先,他是个唯法是求的苦行僧。
请不要忘记,世本《西游记》写唐僧西行求法,事关“法轮回轮,皇图永固”:象征着一项了不起的事业。
一遇重大困难,猪八戒就想回高老庄,“回炉做女婿”。孙悟空也不是没有回花果山“称王道寡,耍子儿去”的念头,只因头上戴着紧箍,“恐本洞小妖见笑”未走罢了。唐僧虽无半途而废之念,但亦常作乡关之思,且感伤情调日甚。既无散伙之念,又无乡关之思,心不旁鹜,笃而行之,宁静淡泊,矢志西行求法者唯沙僧一人而已。
孙悟空一路炼魔降怪,图名不图利。猪八戒一路所作所为,图利不图名。纵然是圣僧唐三藏,其所以矢志西行,亦“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心无二念,忠于厥职,淡泊宁静,但求正果西天者亦沙僧一人而已。
孙悟空是由于大闹天宫而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的,而一路上只要谈起当年的大闹天宫,便总是那么神采飞扬,骄傲自得不已。猪八戒本堂堂天蓬元帅,只因蟠桃会上酗酒戏了仙娥致被玉帝贬下尘凡托生猪腹,可虽“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圣僧唐三藏呢?“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然而,他的乡关之思和感伤情调,恍若他的矢志西行全然是在为造福生灵、造福社稷而作出努力和自我牺牲似的。凡此,说明他们的西行求法,其行动的本身虽有自我“赎罪”的一面,可思想上的自我赎罪感却微乎其微。沙和尚则不然。“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正是这种赎罪意识(实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使他安闲自若地直面九九八十一难。
其次,他是个唯师是尊的苦行僧。
孙悟空好以锄恶作为行善,所以遇妖怪就打,见草寇也杀,而把唐僧的教诲“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当作耳边风。猪八戒好卖弄威风,显显能耐,所以一见小妖举钯就筑,也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沙和尚却不然,他自秉沙门,从不肯轻易杀生。书中只写他杀死过一个妖魔,那就是花果山变成他模样的猴精,甚至还曾写他为如意真仙求情,望着孙悟空喊道:“饶他罢!饶他罢!”足见,他在思想上虽不反对孙悟空的以锄恶为行善,但在行为上却不敢有忘佛门教义以及唐僧的教诲,因而不到怒火衷烧时决不去一开“杀戒”,“打退群妖”也就算了,尽管他的武艺乃猪八戒之亚匹。
正因为孙悟空好以除恶作为行善,乃至成为他的立身之道,而唐僧却“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所以唐僧曾以“凶恶太甚”为由而两次怒逐孙悟空。沙和尚都一旁站着,缄口不言。论原因,显然有三:一是,认为“尸魔”纵然是妖怪,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孙悟空又心高气傲过甚,说话口气欠当,因而“亦有嫉妒之意”。二是,只知:“兄若不得唐僧去,那个佛祖肯传经与你!”还认识不到:“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取真经只靠美猴精”。三是,深知唐僧不只好刚愎自用,而且“耳根罢软”,正在盛怒之下,猪八戒又在一旁煽风点火,审时度势,说亦无用,也轮不到自己多嘴插舌,不如装愚守拙,明哲保身。因而,甚至唐僧叫他从包袱内取出纸笔写“贬书”,他亦默默地照办不误。凡此,不只反映了他的平凡而“面弱”,也反映了他的明智而沉稳;不只反映了他的思虑虽周而对孙悟空还缺乏真正认识,也反映了他的“唯师是尊”乃他的“唯法是求”之另一种表现形式。
然而,“嫉妒”作为一种意识,是人性的弱点,灵魂的蠹虫,芸芸众生几人能免之?面对孙悟空的天马行空,沙和尚虽则也曾有“嫉妒之意”,却能迅即自我克服,因而不仅始终没有去干扰孙悟空的建功立业,反倒在全力助成,这就使他不失为是个正派的人、高尚的人、有益于取经群体的人。
再次,他是个唯和是贵的人。
取经人中最了解也最能体贴唐僧的,是沙和尚。他知唐僧好刚愎自用,拗是拗他不过的,便来个顺其自然,尊敬不如从命。这一点,第七十二回有集中描写。正值春光明媚,前面是小桥,流水,人家。唐僧道:“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你们没远没近的去化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应,也让我去化一个来。”不言而喻,这是唐僧的豪兴,且情出于一种父辈对子辈的慈爱和慰抚。可孙悟空却不同意,说:“你要吃斋,我自去化。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教师父去化斋之理。”猪八戒也不赞成,说:“古书云:‘有事弟子服其劳。’等我老猪去。”唯沙和尚在旁笑道:“师兄,不必多讲。师父的心情如此,不必违拗。若恼了他,就化将斋来,他也不吃。”一个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一个是“无意种柳柳成荫”。三人跟随唐僧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好我行我素的孙悟空固然常被咒念紧箍,喜卖乖弄巧的猪八戒也常遭厉颜斥责,唯默而侍之的沙和尚却始终未落一詈辞,其深层原因恐怕亦在于此吧!
取经人中最尊重也最爱护孙悟空的,也是沙和尚。他对孙悟空和唐僧之间的矛盾是一清二楚的。尽管他的立身之道不同于孙悟空,并不完全赞成孙悟空的锄恶务尽,但他知道孙悟空的横扫妖魔是为了保护唐僧与取得真经。所以,他不仅没有向唐僧进过半句詀言詀语以博得宠信,相反地,只要知其可为便总是苦谏唐僧不要咒念紧箍。比如,路过号山,红孩儿两次变作红云,想捉唐僧。孙悟空一会将唐僧推下马,说是妖怪来了,一会儿又扶唐僧上马,说是过路妖怪。唐僧大怒,认为孙悟空在捉弄人,“哏哏的,要念《紧箍儿咒》”,就是多亏“沙僧苦劝”方罢。他对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的纠葛,从不介入,只在必要时调解调解。也和孙悟空、猪八戒开点玩笑,但从未伤过和气。不像孙悟空那样动辄使促狭叫“呆子”出洋相,也不像猪八戒那样把“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当作“耍子”,以至弄得彼此“有些不睦”。他对孙悟空的智慧和神勇膺服不已,但对孙悟空的“暴躁”也常施之以柔克刚。比如,“镇海寺心猿知怪”,孙悟空中了地涌夫人的分身计,回来不见了唐僧,竟将一腔怒火发到猪八戒与沙和尚身上:
也不管好歹,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那呆子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却是个灵山大将,见得事多,就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径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那里话!无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
一席话说得孙悟空心悦诚服。这哪里是“情求”,分明是“理喻”!句句说在点子上,而且又是那么有理,有利,有节。好一个柔中有刚、言必中的的沙和尚!
取经人中最理解也最能体量猪八戒的,还是沙和尚。他知道“远路没轻担”,挑担是很辛苦的。因而唐僧教他挑一肩,他固然挑一肩;猪八戒让他挑一肩,他也愉快地接过担子。这就从行动上团结了好耍小心眼的猪八戒。他对猪八戒的动辄闹“散伙”压根儿是不赞成的,却不像孙悟空那样一听就恼火,开口便骂,举棒想打,以至加深兄弟间的不睦。他总是抓住猪八戒愚笨呆直而又自尊心很强这一特点,把自己也摆进去,予以软款温存地劝说。“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钝腮,不要惹大哥热擦。且自换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孙悟空听了固然感到舒服,猪八戒听了也比较容易接受,从而消弭了可能引起的纠葛。
世界上的事最复杂的当莫过于人际关系,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矛盾,所谓“团结就是力量”者,盖亦极言实现团结之难也。要想到达西天取回真经,没有一个取经人的内部团结是不行的。这一团结工作,猪八戒没有去做,孙悟空没有去做,唐僧也没有去做,沙和尚在默默侍候唐僧的同时默默地做了,而且十四年如一日,真是功莫大焉!“一个有福,带挈一屋”,这是沙和尚在朱紫国合药时所说的一句话。真乃甘居人下而胸有全局之人也!
最后,他还是个唯正是尚的苦行僧。
论者都认为世本《西游记》两次写唐僧逐走孙悟空,是在写唐僧,是在写孙悟空,是在写猪八戒,结合后面的情节看问题,是在写没有孙悟空,取经人寸步难行,却没看到这也是在腾出笔来集中写沙和尚与猪八戒的品格。只是一以写猪八戒为主,一以写沙和尚为主而已。何以言之?还是让我们来看事实吧:
“圣僧恨逐美猴王”引出的,是“黑松林三藏逢魔”以及捎书宝象国,是沙和尚降妖被捉以及“猪八戒义激猴王”。黄袍老妖将沙和尚擒入波月洞,咄的一声道:“沙和尚!你两个辄敢擅打上我们门来,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国王教你们来的?”捆在地上的沙和尚,见妖精凶恶之甚,把公主掼倒在地,持刀要杀。心想:“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已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遂编了一套谎,并喝道:“此情是实,何尝有甚书信?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直到孙悟空打到洞口,百花羞来给他解绑时,他还说:“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来家,问你要人,带累你受气。”没想到吧?平素“囊突突”的沙和尚,如此壮怀激烈,真有一种侠义精神!
“道昧放心猿”引出的,是假孙悟空将唐僧打昏在地,抢去两个青毡包袱,是沙和尚去花果山讨行李,打死变成自己模样的猴精,冲出重围去南海告请观音菩萨。“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忽见孙行者站在旁边,等不得说话,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脸便打。这行者更不回手,彻身躲过。沙僧口里乱骂道:‘我把你个犯十恶造反的泼猴!你又来影瞒菩萨哩’!”观音让孙悟空跟沙和尚同去水帘洞辨个真假,二人纵起两道祥光,离了南海,却“原来行者筋斗云快,沙和尚仙云觉迟,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露尾,先去安根。待小弟与你一同走。’大圣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个二人同驾云而去。”想到吗?平素“面弱”和“唯尊是从”的沙和尚,其义愤填膺和铁面无私如此,真有一种大义灭亲精神!
由此可见,以唐僧的固执,孙悟空的好胜,猪八戒的愚拙,其所以皆能听进沙和尚的劝告,当不只由于他说话公道,更由于他立身极正,实在是唐僧的好“副官”。
假若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那么,则不难看出,沙和尚当是个品位不高的循吏的典型。这就难怪作者要将其写成被贬入尘寰而却未经转胎的卷帘大将了,盖亦有以讥刺玉帝即人间最高统治者之常因小过而黜人材也。
实际上,世本《西游记》也是部借神魔以写人间的作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算是清官呢。没有一点苦行僧精神是当不了循吏的,更当不了品位不高的循吏!
简短的结论
写到这儿,该煞住了,我的总结论是:
宋元以来取经故事中的沙和尚,其出身是由沙漠恶煞演化为弱水水怪,其前身是由无名天将演化为卷帘大将,其地位是由唐僧二弟子演化为唐僧三弟子。但不论怎么演化,都依然可以看出他作为唐僧的给侍和二弟子的原型。
世本《西游记》中的沙和尚,其立身也,唯法是求,唯师是尊,唯和是贵,唯正是尚;其为人也,罕言寡语而思虑周密,处事审慎而外圆内方,宁静淡泊而坚韧不拔,无贪无瞋无烦恼而有爱有憎有原则,甘居卑位而胸怀大局。盖因其在书中五行属土,作者便有意以土喻之,不只谓其是个“晦气色脸的和尚”,还将其性情写成像土一样的中和像地气一样的恒温而痴迷于默默中作出奉献,使之不只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全力地卫护着唐僧西行求法,还以自己的一片丹心维系着取经群体的内部团结,成为这一取经群体的另一种精神脊梁而与横扫妖魔的孙悟空相匹。但就其思想性格的总体特点来说,当属品位不高的循吏的典型,故作者不只爱之,亦且敬之,通书未下一谑辞者唯对斯人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