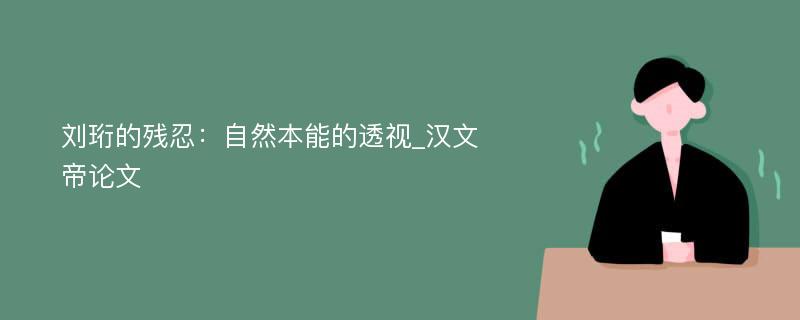
刘恒的残酷:透视自然本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本能论文,残酷论文,自然论文,刘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坛上有那么两位作家,研究者对他们都表达过这种揣测:刘恒(更有余华)受到过什么磨折与伤害,以至于他们把人生的阴暗或是苦难写到这般极致化?孙郁就说:“……刘恒或许受到了什么伤害,他对人的潜意识的描写,有时大胆到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感叹说:“刘恒却看到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困惑,在另一方面,又接近于鲁迅,那种对人生的无情的剖示,和鲁迅的反省一样森冷到让人战粟的程度。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刘恒把笔下的人物,都赶到了那片洪荒的沙漠上。”(注:见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载《当代作家评论》94.3.)
将刘恒的透入骨髓的洞察力和冷静的距离感与鲁迅作比,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自己就最爱读鲁迅。不过鲁迅的爱憎还常溢于字里行间,刘恒则始终与对象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一面是无边的苦海,一面是冰冷的叙述者。正是这种距离感,才使他的作品越发变得冷酷、残忍、惨烈,以至令人窒息。
刘恒的小说大概可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生活两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正是上面提到的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前一类作品侧重于人的外部基本的生存,可以两个字“食色”概括之,其中《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可说是达到了写生存本相的极致;后一类以《白涡》、《虚证》为代表,侧重于人内在的心理真实,借鉴法国自然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于斯曼的说法,是一种“精神的自然主义”(注:参见利里安·R ·福斯特《自然主义》P36.)。弗斯特称它为经典自然主义的“叛离”(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为什么不能看成是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须作些说明。
对于刘恒的前一类写人的食色本能的作品,其自然主义特色不辨即明,也有研究者对它们作过分析。而《白涡》的心理抒写与分析成分较重,有人对它是否自然主义之作心存疑虑。所以我们借用于斯曼“精神的自然主义”这个概念,正象有人称某类意识流小说为“心理现实主义”一样。这样称也不违背自然主义始创者的原意,因为自然主义的核心不过是大胆、真实、客观、准确地摹写自然,自然既指外在的社会现实,也指内在的生理与心理现实。于斯曼既称之为“自然主义”,不过是加了“精神”这一修饰语,而没有改称为别的什么主义(如现实主义),就可见他自己并没想“叛离”自然主义,而意在发展与丰富,所以他说:“人们必然坚持走左拉大胆闯出的路,但也需要在天空中建设一条平行的路,一条伴行道,通向远方的事物,那就是说,创造一种精神上的自然主义。”(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其实,如果全面一些看左拉的文学主张, 把大胆真实的心理描写与分析看作自然主义并不违背他的本意,那种以为左拉要求象做科学实验一样只能如实记录观察(而不是体察)结果的看法实在是对左拉的误会。且不说他本人的文学实践,我们来看他在《论小说》一文中论述“真实感”(这才是自然主义的生命所在)的情形。他认为“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并以此来排斥“想象”(当然这不免偏颇),盛赞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推崇福楼拜和龚吉尔兄弟,认为“他们的才华不在于他们有想象,而在于他们强有力地表现了自然”。他所谓“想象”也不同于我们今天理解的“想象”,而近于“幻想”,所以他举的想象的例子是几位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大仲马、欧仁·苏、乔治·桑。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司汤达的分析力的推崇,在我们看来,司汤达的《红与黑》简直有一半的篇幅在作心理分析(远远大于《白涡》中心理分析的比例),而左拉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分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要比《红与黑》中对于德·瑞拉夫人的爱情分析更为惊人。”(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
我们之起用“精神的自然主义”这一概念,还因为时代在发展,文学也在发展,在现代科学、哲学、心理学日趋发达的今天,在人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文学更加关注内在世界而大量内向转的情形下,有生命力的批评术语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而且,之所以用“精神的自然主义”来看《白涡》这样的小说,也是因为它显然不同于注重内心情感愿望抒发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对内部世界尤其潜意识世界以一种变形夸张表现出来的主义,而是一种原生态的常人精神世界,给人以强烈的似真性,是一种精神的写实。而且这类作品除了这部分内心世界的内容,另外很大的部分也写了人物的俗世活动,并且关注的是前一类作品共同的问题,也即是历来中外自然主义小说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即性。用刘恒自己的话说是“写性本身给人造成的困境”(注:见《中国作家梦》刘恒部分.)。下面先看前一类表现生存本能的作品。
陈思和说:“生存意识与自然主义文学有相似之处,表现为从对人的生理因素而发展为对人的动物性的强调,由性意识进入到对生命繁衍即生殖的歌颂。自然主义作家从不讳避性意识所具含的人类文化心理的一面,他们把生殖看作生命的赞歌。这早有左拉的《生之快乐》和《繁殖》为证。生殖是动物最自然的本性,非人类所专有,但唯有人能从生殖繁衍过程中感悟到生命的升华和永恒,甚至含有社会的意义。”接着他说:“这一特征在当代小说中最集中地表现在刘恒的小说里。”(注:见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一个解释》一文,载《钟山》90,4.)《狗日的粮食》是刘恒也是新时期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一个自然主义小说范本,可以说是一切特征兼备:“一、还原生活本相,在艺术创作中提供一个现实生活的纯态事实;二、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凡俗场景的描写,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入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三、用科学主义的写作态度,也即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注:见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一个解释》一文,载《钟山》90,4.)(注:见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载《当代作家评论》94,3.), 这是陈思和为“新写实”小说特征作的总结,可也恰恰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刘恒不是最早开始自然主义小说的写作,在他之前已有了阿城和莫言的探索(不过他二人还时有浪漫主义情结,如阿城的《遍地风流》和莫言的《红高梁》)更有了王安忆的基本成熟的自然主义小说《好姆妈、谢家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和《小城之恋》。可王安忆女性的审美眼光还不允许她过多停留在污浊、丑陋之上,也不允许她过分藏起她敏感的内心,即使是她通过遗传探索人天性之恶的《好姆妈……》也不乏温馨,《小城之恋》和紧跟着的其他“二恋”甚至后来那篇号称“中国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惊世骇俗的《岗上的世纪》更不乏美好,尤其稍后的这部《岗上的世纪》简直可说是一部奇异作品,它一方面让你充分感到那种自然主义大胆真实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让你感到某种与自然主义格格不入的浪漫质素。而自然主义这个敏锐的家伙眼中从来揉不进沙子,总易从人世间看出丑恶、难堪、凡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恒的〈日的粮食〉虽然不是出现最早却是最成熟的自然主义小说,虽然这样的小说往往真实得让你难受(是极端的真实),你也更愿看王安忆那样真实(并不绝对真实)而又让你难受的作品。
《狗日的粮食》的主人公可说是中国文学史或许还是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形象,一个奇丑无比的瘦袋女人。一个脖子上掉着一块赘肉晃荡的女子无论如何不会引起人的美感,多少有些“令人恶心”(柳鸣九说自然主义被指责为“从生理的角度描写了人因而带来了一些令人恶心的丑恶场面”),读者也多少都在接受一种感官的折磨。这个丑陋的女人甚至也说不上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不象《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那样以其圣洁的爱心最终引得人们深切的同情与感叹(或许这正是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水岭)。生存是她唯一的目的。因为她的丑陋她像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卖了六次,最后一次是天宽用了二百斤谷子不情不愿地换了回来。天宽的终于接受也还是生存的本能使然,要生存就得满足人之大欲,即食色。所以天宽买来了她第一桩事是“做”,而女人也毫无羞耻之心,几近于麻木,不管什么尊严与美丑,一切让位于生存的本能。有人要就行,有得吃能活着就行。除了满足丈夫的“做”,此外她唯一关心的就是一家人的吃。为了吃,丑陋的她还有许多丑陋的行为:将邻家的葫芦据为己有,还能借葫芦骂街骂得邻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有理反被无理欺。不仅东家一颗葫芦、西家一颗南瓜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日日收工回家,都能从身上揪出一样宝: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等等,总之是地里长什么,她往家里拿什么,似乎是天经地义。活着这一目的谁又能说不是天经地义呢?最后为了这“活着”(一家人的吃),她却死去——为了粮证她搭上了自己的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被丈夫“熊”了一顿(以她的泼辣平日丈夫可惹她不起),终于承爱不了如此的打击,死了,最后口中念念不忘絮叨着的还是这维持人生存本能的最为致命的东西——粮食。“粮食——狗日的——粮食,”半是疼半是恨,半是希求半是咀咒。可见再顽强的生命也有摧折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弱女子,她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做为女子的柔美可爱的东西,她已经是比粗糙的生活还粗糙,可说是雄性化了的,生命力不可谓不强。
通篇小说读后,给人一种复杂难言的感觉,可说是五味俱全,然而就是没有美的感觉,可这却是真实,严酷的真实,只有自然主义才能达到的可怕的真实。作家几乎是白描地写下这么一个存活的故事,或说是活与死的故事。的的确确是原生态的生活,没有任何美化与修饰(作者甚至苛吝到舍不得在本已丑得可怕的女人心灵上植下些许善良与美丽,一切水分为外在的生存挤掉榨干);也不带丝毫情感与评价(作者将可能存在的时代内容全部抽空,避免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政治小说,而让全付精力集中于生存本身)。有的是本能,吃的本能与性的本能,即历来指责自然主义的生物性。《狗》与自然主义的契合无间简直让人怀疑刘恒是在刻意实践左拉们的文学主张,甚至比左拉还左拉。左拉还明确写出让人爱或是让人恨的人物,而刘恒笔下的人物则永远叫你爱不得又恨不起。这就是生活与人本身。生活中哪有什么完美无缺?又哪有什么十恶不赦?当然对《狗》这种作品,道德判断是无法进行的。
如果说《狗日的粮食》讲的是食的故事,那么《白涡》说的就是色的困扰,人物活动环境由荒蛮贫困的农村转移到丰衣足食的现代都市,主人公也由粗糙丑陋的村妇村夫变成了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都市精英男女。这里“食”的问题不存在了,而“饱暖思淫欲”,于是“色”的问题现出来了。不看小说,我们很容易想到一种模式,即出现于某个别作家笔下的来自古代饮酒狎妓的名士之风的都市浪子形象。然而刘恒的独特与严肃恰恰是他把这一实验(不知怎么就让人想起左拉爱的这个词)对象放在了一个事业有成、生活严肃的好好男人身上。这个好好男人正当四十岁的壮年,是男人如日中天的年龄。在单位,他是颇有权威与成就的学者(研究员),实乃一谦谦君子,和气待人,检点自爱,人人欢迎。在家中,他对妻子体贴周到、细致温情,是标准的好丈夫;对子女循循善诱、慈爱有加,是合格的好父亲,简直可算得上一个无可挑剔的“完人”。小说有了这么一个并不自然主义或简直就有点浪漫主义的美好的开头。如果不加入其他因素,他会永保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至少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而“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文学最忌讳这个“一样”,一样就无戏,也就没有我们这篇小说。生活也不可能这么单纯,处处是偶然(在沈从文的散文《水云》中,“偶然”恰是一个个女子的代称)处处是陷井,经由“偶然”这个试剂一检,好好男人的全部心理灰暗才呈示出来。面对这个外在包裹层完美厚实的男人,实验者只好给周兆路的研究室“新分来”一个可人的“尤物”,并让这位美丽窕窕的少妇华乃倩主动出击。一张塞进抽屉的小纸条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好好男人的世界开始躁动不宁了,戒备、试探、掩饰、算计……尽管他小心翼翼地全身避祸,在有可能危及自己的高升时适时地抽身而退,然而他毕竟是一步步陷进去,那个正当三十六盛年(这不难让人想到民间那句粗话:如狼似虎)而生活有着某种残缺的女人偏偏又可谓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令他躲不成,逃不掉。家不再如往日的和睦温馨,事业也受到某种威胁。这大约就是刘恒所谓的“性给人造成的困境”之一种吧。性对于这样的一个好好男人都有如此这般的影响力,可见人受其摆布之必然了,人还是难脱其生物性。自小说中我们实在仅能读到这样的判断,至于对男女主人公的道德评判,作品中几乎不作暗示,我们不得而知。孙郁则谓此篇如他的长篇《苍河白日梦》一般,表现了“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和人的无法摆脱”的“精神上的宿命”,具体说来是表现一种“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与人性间的偏离和天然的冲突。”(注:见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载《当代作家评论》94,3.)(注:引自《白涡》.)如此说来,作品应多少对男(女)主人公持同情态度,但是似乎寻不到丝毫蛛丝马迹。刘恒始终远远地审视着他笔下的人物,不肯让人们一窥他深沉的心思。倒是因了作者严格的自然主义笔法,人物内在隐秘世界那些阴暗卑琐的东西得以昭示,给人巨大的震撼。对于理性无法制约的那个情欲世界,刘恒确乎有着入木三分的穿透力。曾与周兆路也算得和谐的妻子遭到丈夫冷落之后反默默的抚慰他,他有些于心不忍。此时作者替他的人物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想补偿一下,但没有情绪。生理受心理支配,这在医学上也是形成某种见解的基础。感觉容易麻痹,熟悉了也就疲乏了。换一种情形,只要出现新鲜的信号,生理就会重新夺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摆脱心理束缚而采取大胆的行动。”“这是一个人平时不大注意的事实。”瞧着,刘恒(其实是周兆路,他可是中医研究员)拿起了医生的解剖刀,大有让文学向医学、生理学靠拢的科学化劲头,即便按照左拉的要求,这段生理与心理的分析也是够“自然”够“惊人”的吧。说穿了,他给人尤其是男人的常见的喜新厌旧倾向找到了一条科学依据。如此也就暗示着某些人性劣的不可逆转性和人类某些灾难的不可逃避。可不是吗?当下的中国每日不知要上演多少大小小这样的悲剧。刘恒总给人以宿命感,总是不肯给人留下一些希望与幻想(或许他也同刘震云一样认为幻想害人?)又如关于人的兽性或谓之生物性,周由他与华偷情时因床过响转移到肮脏的地毯上一事想到“像野兽一样!”(这可是文明人的文明的弊端。当“我爷爷”、“我奶奶”在高梁地野合,杨天青和王菊豆在田间地头做爱时哪有这等文明病?比较起来,岂止“我爷爷”英雄性兼雄性十足,是标准的浪漫主义,连杨天青比之周兆路也要浪漫主义得多,所以才得了“爱情英雄”的封号)接着又有了这样一番“念头”:“他正是一头野兽。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人人都会成为野兽,野兽有野兽的下场。人不会有好下场。吃着、喝着、活着、希望着,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一个冷冰冰的尸首能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刘恒和他的残酷,人、人的豆子运有他笔下确实低调到了“冷冰冰”的程度。既然在适宜的时间地点,人人都会成为野兽,他周兆路也就“野兽”得心安理得,此其一。其二,“人既然那么可悲,就不能不爱自己”。“他的确爱自己爱到得行乐时且“享受她”,不该行乐时就逃离她;因为她不过是“胜利者无足轻重的点缀,是命运给他安排的赏心悦目的小小插曲。”(注:引自《白涡》.)女权主义者可能不会冷静地读这类文字,而这毕竟是事实。是随处可见、百般可信的事实。也许阴暗、也许自私、也许不那么美好,但却是真实。其实,也只有不美好才是真实(一美好无比就变成了浪漫)。这正是自然主义意在真实客观却无意陷进了审丑溢恶的泥沼而难以自拔难以洗刷的真正原因。说来不免让人丧气,真和美原来是不可两全的,真善美集于一身则简直是神话。这也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困境所在:求到了真,却失去文学作为艺术应有的美。
刘恒的《伏羲伏羲》、《虚证》也仍然写的是“性给人造成的困境”(其中《虚证》稍稍有别,但主人公的悲剧的总根源和起点却依然是性的被掠夺和性的尴尬)。无法逃脱的困境最终导致了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死亡。在此不再详加分析。刘恒是个作品数量不大而风格多样化的作家,相比之下,当代作家中他最不喜重复,与贾平的作品数量众多可常有令人生厌的重复恰好成对照。他的数量不多的小说却无法以一个模式去解读。但是,无论是其物质的或外在的自然主义小说,还是其精神的或内在的自然主义小说,都是对人的本能世界(不可否认本能世界又常折射着文化的痕迹)所作的严酷的自然主义写真,读来令人怵目惊心。总的说来,在内容上,刘恒多涉及人的本能,或者说本我世界,同时常常见出本我与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给人制造的困难。其中《伏羲伏羲》还有弑父恋母的影子,自然这里是以叔代父、以婶代母。下一代又宿命般重复了这种弑父的模式,虽无明显的恋母,但若将天白对天青那种阴鸷的、极端的恨完全理解为人伦因素和社会因素,恐怕也不全妥。刘恒似乎并不否认弗氏思想给予自己的启示,他说:“他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是有一点偏激。他把各种事情都与“性”联系起来,显得稍有些牵强,但是他的学说毕竟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认识到从来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此处“他”在马原的问话中是“柏拉图”,疑是“弗洛伊德”之误)(注:见《中国作家梦》刘恒部分.)。 在表现上,刘恒排除了倾向性,一切交由“客观的无限可能性”,不作过多想当然的“虚证”。
标签:汉文帝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狗日的粮食论文; 读书论文; 伏羲伏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