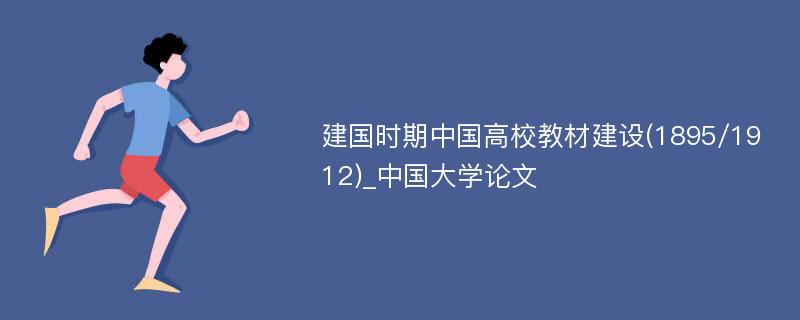
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1895—19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时期论文,教材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现代化始终与教育现代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近代大学发展紧密相连。近代大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上,而且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教材建设。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及大学发展的需求,于是西方大学文、理、工、法、医、农、商“七科之学”被导入中国,由此引发了近代意义上大学教材建设的诉求。中国近代大学教材建设经历了由引进编译到自编自著、由民间主导到官方统一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一时期,除个别教会大学外,中国初创的四所大学包括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它们在教材建设上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可以说,为民国乃至新中国大学教材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一、天津中西学堂的教材建设
天津中西学堂于1895年根据盛宣怀“中体西用”的思想创办,具体的办学权交由美国传教士丁家立(T.C.Daniel)掌控。学堂内设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属工科性质,开设了工程、电力、矿务、机器、律例等高等学科及其课程。《头等学堂章程》虽规定“恐汉文不能尽通,是以汉文教习必须认真访延,不可丝毫徇情”,以及“经史皆当择要讲读”[1](P493),但当时使用的主要教材则是总教习丁家立主编的“北洋丛书”(Tientsin University Series),其中较为知名且流传甚广的有《英文法程》、《亚洲地理》和《世界历史纲要》等。《英文法程》为英文语法教材,分为初集、二集,初集为《英文课程》,二集为《英文语法》。丁家立在《英文课程》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目的是教授和运用最为重要的英语语法原理”[2](Pi),在《英文语法》序言中他又强调,该书“专供中国学生,以及那些选修丁家立英文课的学生使用”[3](Piii)。由于学习对象是中国学生,所以这两部教材的内容相对简单,且均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旨在便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亚洲地理》是一部简明地理教材,对亚洲及其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作了简要的介绍,相对于前两部英文教材而言,它的内容不再以词句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篇章的形式进行编排,除了“专门为说英语的中国学生添加了亚洲地理方面的相关注释,即将每一个地名都同时用英文和中文进行标示”[4](Pi)外,其余部分均未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该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书中含有若干辅助性的地图,以便学生对亚洲的地理形成一种较为直观而形象的认识。《世界通史纲要》是美国学者任纳福(V.A.Renouf)专为“满足新近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东方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而编写的”一部通史类教材。任纳福对东方学生的认识是:“一方面,他通常是一个成熟的年轻人,已经接受过本国语言与文学方面的课程训练,不再需要专供学童使用的教材;另一方面,他在英语方面又几乎是个初学者,复杂的语句与夸张的隐喻,以及引自希腊神话与圣经章节中的典故”,对于他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5](Pvii)基于这样的认识,任纳福在编辑这部教材时,一方面对一些与东方人思维不太一致的历史内容进行了节略处理;另一方面,“在全书简短的篇幅中,对所有那些与东西方均有联系的历史事件尽可能给予最大的关注”[5](Pviii)。他将全书分为古代、中世纪与近代三个部分,对各个主要时期、主要国家的历史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另外,该教材在形式上与《亚洲地理》一样,也附有地图并伴有图解。
由上述内容可知,为使编写的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学习英文,丁家立等人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确实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思考。不过,当时天津中西学堂主要是引进和直接使用了大量外文原版教材,据早年就读于该校的李书田日后回忆:“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伯仲。”[6](P146)一部分学生“因其程度已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相比肩,故可迳行进入美国各著名大学之研究院”[6](P146)。然而,这种注重英文学习、几乎全部使用外国原版教材的做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方面,影响多数学生对本国语言——汉语的学习。例如,南洋公学院监福开森(J.C.Ferguson)在与总理何嗣焜一起参观天津中西学堂后指出:“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多好,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7](P170)何嗣焜也认同这一评价。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使得当时在头等学堂学习的多数学生,在受到良好学术训练的同时,感到沉重的压力。正如毕业于该学堂的孙越崎回忆说:“北洋大学堂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各科老师都是美国人,课本全是英文本子,考起试来没完没了,是个顽固的念书派,星期日是同学们最重要的一天,一周中的课程哪里没搞清听懂,都利用星期日补上,很少有人外出行走。”[6](P46)针对这些弊端,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二、南洋公学的教材建设
继天津中西学堂后,盛宣怀于1897年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先后开办或计划开办外院、师范院、中院、译书院(后附设东文学堂)、上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等。关于创立南洋公学的初衷,盛宣怀在呈清廷的奏折中言明:“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8](P81)“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8](P83)因此,初创时期的南洋公学与天津中西学堂的工科性质不同,它是一所以政法、经济、历史、地理为主的文科大学。盛宣怀在创立南洋公学时,其办学思想与天津中西学堂相比已有所改变,虽然此时他仍然认为,“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四国之为”[8](P85),但鉴于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情形,他也认识到,“西国语言文字,殊非一蹴可几”[8](P85),更将埃及视为前车之鉴,恐一味以外文原版书籍为教材,会导致“比有事曾不得一人之用”[8](P193)的不良后果。于是,在南洋公学的教材建设上,主张尽量翻译外文书籍以应教学之急需。盛宣怀说:“中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将使成名成才者皆得究极知新之学,不数年而大收其用,非如日本之汲汲于译书,其道无由矣!”[8](P85)“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书,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8](P191)南洋公学的中文教习白作霖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谨将中院第三班功课钟刻书籍开呈文》中说:“轻中重西虽时习使然,然中文尚未精通,即西文读成,于彼中学问亦何能?窥见少年无识,甚至见西书则兴起,视中文则若浼,此大惑不解者也。”[9](P16)正是基于此种思想与观点,南洋公学译学院成立不久便开始翻译东西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学、教育、商业、史地等各类书籍,以供南洋公学作为教材使用。盛宣怀在1902年上奏的《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将译书院的功能定位为:“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10](P759)据刊载于1902年的《原富》一书扉页上的译印图书广告介绍:在1899年—1903年间,南洋公学译书院编译书籍共55种①,除军事类译著外②,其余的社会科学类书籍与普通教育教科书,多用作南洋公学教材或参考书。例如,张元济在任南洋公学总办期间就曾教学生读《原富》一书。[11](P64)其中,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的主要有《政群源流考》、《英国枢政志》、《英国文明史》、《计学平议》、《万国通商史》和《西比利亚铁路考》等。
《政群源流考》为美国学者韦尔生(Wilson)所著,由南洋公学师范院英文教习伍光建、李维格合译。该书根据古希腊、罗马政体的沿革来考量欧美政体,虽未必皆适当可信,但正如晚清有的学者在对该书的提要中所说:“较之近日所译西史各书尤具要领”;虽为选译而非全译,但“译者附注各条征引甚备,附列所引书目考尤便钩稽”。[12](P416-417)《英国枢政志》由英国学者图雷尔(Tourel)著,郑鼎元等译出后作为“常课书”使用。伍光建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称其“芟繁撮要,不诩淹博,颇便读者”,“久已风行海内”。[13](序言)该书先以政府及各职能机构为纲目加以分述,再对枢政趋向进行概括,条理清晰,结构工整,作为教材,确能有助于增进学生对英国政体、立法及行政等方面的了解。《英国文明史》为英国史学家勃克鲁(H.T.Buckle,今译巴克尔)所著,为近代英国史研究的力著,也是19世纪西方“文明史学”的代表之作,对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影响甚大,日本史家称此书“如旋风一般,在当时思想界甚为流行”[14]。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读过此书后,曾在其《中国史学通论续编》的“读史总论”中对该书予以很高的评价。《英国文明史》一书涉及领域甚广,有利于全面拓展学生的学识。同时,译者还将该书的理论与方法概括为10条大意置于书前,便于学生把握全书内容之精髓。《计学平议》是继《原富》之后又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著作,由美国学者兰德克略(C.Rand)撰,该书取美国典型的折中主义观点,对新旧两派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均有述评:“其议论虽自简约,而书中要领,包括无遗。若叙述计学之近概,非第详晰而已,尤能将此学为世人轻视之原因,缕悉条举,至斯感悟世人,开辟知识,裨益宏远,更无论矣。”[15](后记)作为教材,不仅便于初学者了解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概况,而且使之对新旧学派的观点与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也能有所知晓。《万国通商史》为英国学者琐米尔士(Sawmills)撰,日本学者古城贞吉重译,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生孟森、郑孝柽合校。该书内容虽有详欧略亚之缺陷,但“叙事简明,了然于古今各国通商之大势”[16](原叙),且附地图两幅。作为教材,不但有益于初学者对近代各国通商大事有概括性了解,而且有助于他们掌握古今地理概况。《西比利亚铁路考》为南洋公学美籍教习勒芬迩(Reuver)所编讲义,由王建极、徐兆熊、朱煌合译。该书虽篇幅简短,对西比利亚铁路的介绍却颇为全面,从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论起,进而述及铁路的规划、营造、费用以及通商与贸易等方面,同时对满洲铁路及中俄国际关系也作了简要评述[17],对于中国学生了解铁路相关知识以及北方邻国的发展状况,很有裨益。
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最早的教材,上述几部译著可谓各有优点,它们便于学生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南洋公学教授西方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课程的需要,并为日后国人自编相关学科及课程的教材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模本;但它们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大多篇幅简短,内容简要,以事实介绍为主。另据当时就学于南洋公学的平海澜、伍特公、张季源、张大椿等人的回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大清会典》、《圣武纪》、《劝学篇》、《盛世危言》等,均曾作为南洋公学文史课教材使用。[11](P63-77)同时,也有中国学者自编讲义作为教材,如唐文治从1906年开始在南洋公学主讲国文,编有《高等学堂国文讲义》(后更名为《高等国文读本》),该讲义由唐文治所选古文辑成,唐氏本人亲加点评,称该书“自成体系,且适用于启发性之教学”[18](P38)。这些传统国学教材的使用,正符合盛宣怀“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的思想。此外,外文原版教材也在南洋公学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南洋公学中院博物、数学、世界史地、物理、化学、法制、经济等学科教学,都曾使用过英文原版教材。[1](P527)
三、山西大学堂的教材建设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因教案而起,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等人发生了联系。1902年4月3日,李提摩太在总教习敦崇礼(M.Duncan)博士和分教习、化学教授新常富(E.T.Nystrom)及6名中国教习的协助下,在太原开办中西大学堂,即后来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早在一年前,李提摩太便在《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中明确提出,要“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19](P1);而后又在《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中再次强调:“开建学堂,考究中西有用之学。”[19](P4)本着这种办学思想,西学专斋的学科分为五门,即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即物理学)、工程学和医学。开办初期,课程全部是新的,上课既无课本,也不编发讲义。为解决教材问题,在李提摩太的倡导下,1902年8月在上海设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其主要任务是为山西大学堂西斋、中斋翻译急需的教材。据有的学者研究,1902年—1908年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先后出版译著23种。[20](P66)笔者据法国学者兰波(A.Rambaud)著《俄国近史》(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刊印)附录的“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新书目录”,并参考《山西大学百年校史:1902—2002》(中华书局,2002年)、《山大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资料,统计所得为25种。③这些教材多用于西学专斋,而中学专斋教材一方面包括《战国策》、《近思录》、《禹贡》、《明史》等传统经史之书;另一方面,中方教习也编有讲义,如学堂监督、教务长傅岳棻编写的《西洋史讲义》(后定名为《西洋史教科书》),以及中斋教习张友桐编写的《中国通史》,均简明扼要,流行一时。[21](P22)在上述25种译著中用作大学教材的主要有7种,分别是《克洛特天演学》、《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无机化学》、《迈尔通史》、《俄国近史》和《世界商业史》,它们大都作为文学与格致二科的教材使用,而法科、尤其是工程学与医学科仍主要使用外文原版教材。
《克洛特天演学》为英国生物学家克洛特(E.Clodd)所著,中译本于1905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1章。上卷5章主要从天文学视角,简要介绍宇宙、太阳系、地球的性质及运行等情况;下卷6章则重点分析生命起源与物种演化。该书结合多个学科的视角论述人类的起源,从正面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对非难该学说的种种观点进行了驳斥。作为教材,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宇宙天体与人类起源问题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书中所附多幅图片,也有利于学生直观了解物种的亲缘关系。《最新天文图志》和《最新地文图志》分别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助理希特(T.Heath)和英国世爵崎冀(Chiechi)所著,由译书院英文译员叶青所译。两部译著具有图文并茂、注释明晰、内容简明扼要的特点。前者分为14章,先述天象观测方法,后对太阳系内诸行星、彗星、恒星的性质、关系及运行等一一进行描述;后者分为地质图、地文图、气候图、水学图、博物图5部分,对各大洲的地质、地文、气候及生物等作了介绍。作为教材,此二书将文字与图表相结合,可加深学生的记忆,并发挥了科普读物的启蒙作用。《无机化学》是西学专斋化学教习新常富所编的讲义,由学生徐宝鸿翻译。该书首先对化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性质、分类、算法及其与物理学的关系等作了简要阐释,然后分别对非金属类与金属类物质进行分析,最后还对“电化学”这一新兴学科有所提及。此部教材印行后,畅销各地,影响深远。张之洞在1904年为《无机化学》所作序文中说:“余虽于化学家言素未究悉,然观兹书以繁赜幽忽之理,而行以平易明简之辞,刊奇诞诡异之说,而详以制作冶炼之事,喜诸生所学之日进也。”[22](序)由此可见,这样一部教材,就当时对西方科学了解甚微的中国学生而言,具有较大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文科方面的教材,《迈尔通史》为美国学者迈尔(P.V.N.Myers)所著,由译书院英文译员黄佐廷、张在新等翻译。据记载,该书曾在我国广为流行,影响甚大。[21](P18)张在新在序中称,是书“议论之纯正,取材之精审,文字之茂美,尤为读者所共赏,其诸简不病略,详不伤烦者欤”,“为近一千九百年新出之书,在彼国高等学堂教科书中,推为善本”。[23](序)从全书内容及其学术性来看,《迈尔通史》确是当时同类教材中的佼佼者,由上古到中古直至近代,对世界各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学术发展与艺术进步、政治经济体制与民风等,皆有所评述,并附有大量的地图与表格,对于学生通晓世界历史颇有价值。《俄国近史》为法国学者兰波所著,译书院法文译员苏本铫翻译。该书“原本风行于欧洲者,既久且著,其文简而事赅”[24](序)。凡16卷,以历代俄皇为纲目,对俄国近代外交、战争、财政、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大事,俱有简明扼要之评述。这样一部教材,对于学生而言,可使其在了解邻国近代史的同时,反观中国历史,激发时代使命感。《世界商业史》为英国学者器宾(H.B.Gibbins)所著,日本学者永田健助原译,译书院法文译员许家庆重译。该书只以一章的篇幅对东洋各国商业的历史发展作了简略介绍,其余各章尽是对欧洲商业史的研究,从上古之希腊、罗马到中古之意大利,再到近代之英、美等国,逐一评述,简明扼要,书后还附有商业史若干问题,作为教材颇具基础性与启发性。
四、京师大学堂的教材建设
京师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后因变法失败,1898年—1900年间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25](P130)。1901年,清廷宣布实施“新政”,将京师大学堂建成近代大学遂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除开设预备科、速成科外,还附设译学馆、译书局和编书处等。关于这些编译机构的职能,张百熙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指出:“非徒翻译一切书籍,又须翻译一切课本……今学堂既须考究西政西艺,自应翻译此类课本,以为肄学西学之需。唯其中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教宗之处,亦应增删润色,损益得中,方为尽善。至中国四书五经,为人人必读之书,自应分年计月,垂为定课。此外,百家之书,浩如烟海,亦宜编为简要课本,按时计日,分授诸生。盖编年纪传,诸子百家之籍,固当以兼收并蓄,使学子随意研求。……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25](P127-128)京师大学堂购置、编译的中西书籍可谓非常丰富。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部分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目录所示,甲乙丙丁戊五柜藏书几千册,既有西学文理方面的著作,也有国学经、史、子、集及《二十四史》等书。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教习从国外购置的,如1905年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从日本一次便采购教育、数学、物理、动物、历史五科图书185部。[26](P17)还有一部分是由各省官书局代购的,如1910年江南官书局一次寄售给京师大学堂的书籍便有325部。[26](P17)此外,按京师大学堂规定,中西学教习“尚须自编讲义,躬自讲述。皆不外以‘明体达用,端正趋向’为宗旨”[27](P942)。
《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由副总教习张鹤龄编撰,全书凡20章。张鹤龄在讲义中言道:“今拟考求伦纪,旧宗六经,参以先贤之讲说,证以史家之事迹,博咨环球立国之道,返求圣人先得之理。理为经焉,法为纬焉,庶几辩其异,统其同,大道既明,辞以息。”④他此处所提出的“理为经”与“法为纬”,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由教习王舟瑶编撰,全书共11章。王舟瑶在《论读经法》一篇中强调:“通经以致用。”他认为,通经之道无他,唯有“求其大义”,“贵乎通今”。[28](P65-66)本着这种观点,他在阐述孔孟学说、尔雅小学之后,总论群经大义,并附《通变》与《自强》两篇。这部讲义的主导思想,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统摄德、智、体三育,主张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为核心的德育为“体”,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智育、体育为“用”。《京师大学堂掌故学讲义》由教习杨道霖编撰。杨道霖认为,掌故应包含所有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因此,这部讲义涵盖面甚广,凡与民生有关者皆有所录。杨道霖最后就“中体西用”所表达的观点,正反映出他如此理解并编撰这部掌故学讲义的思想根源。他说:“大抵中学多主义理,其弊易涉于虚;西学多主实用,自宜急以西学补吾不足,中学如权术,西学如百货,两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推求其是,贵于会通。”⑤他对所有与国计民生相关方面的关注,以及强调用实用之学来弥补虚无之学,在当时虽不乏积极意义,但仍未超出“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史学科讲义包括《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及《京师大学堂万国史讲义》。《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由教习屠寄编撰,全书分太古史与上古史两编,共9章,主要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进行了论述。《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由教习陈黻宸编撰,原讲义已残缺不全,仅存7章,主要论述儒家之学并兼及墨家。王舟瑶所编的《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由于是通史体例,所以内容相对丰富、全面,自三皇五帝直至隋唐盛世。王舟瑶在讲义中提出“读史贵有识”的观点:“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经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⑥他所倡导的“读史贵有识”的观点继承了清代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史学传统,也受到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京师大学堂万国史讲义》、《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和《京师大学堂经济学讲义》均为日本学者编撰的中文讲义。前二者为师范馆教习服部宇之吉所编,《京师大学堂万国史讲义》开篇即对万国史(即世界史)的概念、起源和分期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古代欧亚非各国的历史,从而使学生既可了解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又可对世界史学科本身有所认识。《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是中国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材,它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近代知、情、意三分法的心理学体系之中,以求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表现出明显的进化论取向和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意识,颇与中国当时的“教育救国”思潮相吻合。《京师大学堂经济学讲义》为日本教习杉荣三郎所编,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以“经济学”命名的大学教材,它汇集了欧美各经济学大家的著作成果,对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非常有用,在当时流传甚广。《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和《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志讲义》均由教习邹代钧编撰。前者分为两卷:上卷为《地理学总论》,包括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并以政治地理学为中心,对中国的民生业、社会情态、语言文字、宗教礼仪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下卷则对亚洲的地理概况作了叙述。后者共分35课,同样讲述中国的疆域、地势、海岸、人口等专题。应该说,这两部地理学讲义在“明体”基础之上,均突显了“实用”的价值。
通过对上述四所大学教材建设情况的考察和评析,可将中国大学初创时期教材建设的主要特征初步归纳如下。
其一,从指导思想看,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主要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这与提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清末教育宗旨颇为契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接引进“西用”学科的外文原版教材或编译这些学科的中文教材,成为这一时期教材建设的中心任务。无论盛宣怀、张百熙,还是丁家立、李提摩太,他们在大学教材建设中,均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西用”学科的发展、如何通过这些“西用”学科来培养更多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实用型人才上。
其二,从编译人员来看,中国大学初创时期教材建设的主体是外国传教士、学者和中国的非专业人员。外国传教士、学者的专业程度固然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而中国教材编译人员的非专业性则是明显的。除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以外,其他近代学科教材的建设主要依靠的是近代翻译家群体以及修习过英、日、法等国语言的学生群体,这些编译人员在当时虽已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但较之学科专家还是相差甚远。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反映出中国大学初创时期专业人才稀缺的现状及特点。
其三,从教材类型来看,理、工、法、医等学科的授课,基本上还是依赖于外文原版教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四所大学在外文教材的翻译和中文教材的编撰方面,均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和贡献,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教育、心理等学科的教学,大多使用外文教材的中文译本或自编的中文讲义。同时,传统的经史著作仍作为教材在大学里使用。
其四,从教材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教材大多以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主,总体水平不高,学术性与思想性较弱,基本上处于陈述事实、传播知识的层次,但也不乏一些经典之作,它们对新思想和新学科的引进贡献良多。更为主要的是,上述特征也比较符合对西学了解甚少的中国学生的需求。就当时中国大学里大多数学生的学术和思想水平而言,阅读和理解外文原版教材(如天津中西学堂使用的英文原著)及高水平的中文译著(如严复的《原富》)还是颇具难度的。
综合来看,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完善之处,但为各学科专业课程的开设提供了必要的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中国大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需求;而且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外学者在大学教材建设上所积累的经验和开辟的方向,为后来民国乃至新中国大学教材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原富》([英]亚当·斯密著,严复译)、《步兵操典》(日本陆军省颁行,孟森译)、《步兵斥候论》(日本陆军教导团编,王鸿年译,[日]稻村新六校订)、《野外要务令》(日本陆军省编,卢永铭译述)、《步兵射击教范》(日本陆军省编,[日]山根虎之助译)、《作战粮食给养法》(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编,[日]细田谦藏译述)、《日本宪兵制》(著者不详,孟森译,[日]稻村新六校订)、《日本军政要略》(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编,孟森、杨志洵译述,[日]稻村新六校订)、《日本军队给与法》(日本军部编,[日]细田谦藏摘译)、《美国陆军制》(著者不详,南洋公学译书院译述)、《陆军教育摘要》(日本陆军省编,[日]细田谦藏译述)、《日本陆军学校章程汇编》(日本陆军省编,孟森译,郑孝柽复校)、《步兵教练书》(日本军事教育会编,孟森译)、《步兵斥候答问》(著译者不详)、《军队内务书》(日本陆军省编著,杨志洵译述)、《步兵各个教练书》(日本军事教育会编,[日]稻村新六辑补,孟森译述)、《战术学》(日本士官学校编,[日]细田谦藏译述)、《支那教案论》([英]宓克著,严复译)、《政群源流考》([美]韦尔生著,伍光建、李维格译)、《英国枢政志》([英]图雷尔著,郑鼎元、徐兴范、张景良、杨振铭、杜嗣程、许士熊、沈庆鸿、潘灏芬、章乃炜译)、《计学平议》([美]兰德克略著,陈昌绪译)、《万国通商史》([英]琐米尔士著,[日]经济杂志社译,[日]古城贞吉重译,孟森、郑孝柽校)、《英国文明史》([英]勃克鲁著,汤寿潜署检)、《西比利亚铁路考》([美]勒芬迩著,王建极、徐兆熊、朱煌译)、《法学通论》(著译者不详)、《欧洲商业史》(著译者不详)、《亚东贸易地理》(著译者不详)、《英国财政志》([英]怀尔森著,译者不详)、《商业实务志》([日]佐佐木信夫著,译者不详)、《商业提要》([英]花纳著,译者不详)、《商务博物志》(著译者不详)、《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著者不详,叶浩吾译)、《世界通史》(著译者不详)、《欧洲全史》(著译者不详)、《法规大全》(著译者不详)、《日本矿业条例注释》(著译者不详)、《日本近政史》(著译者不详)、《英国会典考》(著译者不详)、《新撰大地志》(著译者不详)、《五洲地志》(著译者不详)、《社会统计学》(著译者不详)、《科学教育学讲义》([日]谷本富著,译者不详)、《习字范本》(编者不详)、《蒙学课本》(朱树人编)、《蒙学课本》(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编)、《小学图画范本》(黄斌编)、《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张相文编)、《万国地理教科书》(著译者不详)、《格致读本》([法]包尔培、[英]莫尔显著,陆之平译)、《中等格致课本》([英]保罗、[英]伯德台著,陆之平译)、《化学》(著者不详,黄国英译述)、《代数设问》(著者不详,陈诸藻译述)、《心算教授法》([日]金泽长吉著,董瑞椿口述,朱念椿笔述)、《笔算教科书》([日]文学社编纂所著,董瑞椿译)、《物算教科书》([日]文学社编纂所著,董瑞椿口述,朱念椿笔述)、《几何》(著者不详,徐兆熊译述)。
邹振环认为,南洋公学译书院至1904年已译成图书67种,他所举出的《美国宪法史》([日]松平康国著,译者不详)和《万国政治历史》([日]下山宽一郎著,译者不详)两部译著,是对上列55种译著的补充。参见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第770页,学林出版社,2006年。另外,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成的日本军事学书籍还包括《步兵工作教范》(日本陆军省编,樊炳清译)、《步兵部队教练法》(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编,孟森译)、《步兵战斗射击教练法》(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编,[日]山根虎之助译)、《日本陆军学校》(著者不详,孟森译,[日]稻村新六校订)、《骑兵斥侯答问》(日本陆军教导团编,王鸿年译述,[日]稻村新六校订,郑孝柽复校)等。参见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第211-212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②日本军事类译著,或在陆军大尉稻村新六、汉文家细田谦藏的指导下翻译,或由他们亲自翻译,水平相对较高。但据现有资料,南洋公学未曾开设军事方面的相关课程,笔者据此推断,军事类译著旨在配合清末新式陆军建立而译介,并未作为大学教材使用。
③《算术教科书》([日]藤泽利喜郎著,[日]西师意译)、《代数学教科书》([日]渡边光次著,[日]西师意译)、《动物学教科书》([日]丘浅博士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矿物学教科书》([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生理学教科书》([日]丘浅次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物理学教科书》(著者不详,[日]西师意、朱葆琛译述)、《地文学教科书》([日]横山又次郎著,[日]西师意译)、《植物学教科书》([日]大渡忠太郎著,[日]西师意、许家惺译述)、《气象学》([日]马场信伦著,[日]西师意译述)、《十九周新学史》([英]华丽士著,梁澜勋译述,许家惺纂辑)、《应用教授学》([日]神保小虎著,[日]西师意译述)、《最新天文图志》([英]希特著,叶青译,朱葆琛述,夏曾佑、许家惺校阅)、《最新地文图志》([英]崎冀著,叶青译,夏曾佑、许家惺校阅)、《迈尔通史》([美]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夏曾佑校)、《克洛特天演学》([英]克洛特著,黄佐廷口译,范熙泽笔述)、《无机化学》([瑞典]新常富讲述,徐鸿宝纂辑)、《世界商业史》([英]器宾著,[日]永田健助译,许家庆重译,许家惺校)、《俄国近史》([法]兰波著,苏本铫译,夏曾佑、许家惺校阅)、《美国法律学》(著译者不详)、《世界名人传略》([英]张伯尔著,[英]窦乐安、黄佐廷、张在新、郭凤翰译述,许家惺校订)、《中西合历年志》(黄佐廷辑)、《世界故事》([英]辛之著,译者不详)、《万国纪略》(著译者不详)、《插图惊奇世界》([英]华丽士著,译者不详)、《中国编年史表》(著译者不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同文献提供的书名或有出入,例如,《山大往事》中将《世界故事》写作《世界轶事》,将《插图惊奇世界》写作《插图惊奇轶事》,参见行龙著:《山大往事》第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将《世界商业史》写作《欧洲商业史》,参见[英]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86-2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另,根据《十九周新学史》一书的内容,可以判断该书书名中的“十九周”指19世纪。
④张鹤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第2页,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藏本。
⑤杨道霖:《京师大学堂掌故学讲义》第20页,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藏本。
⑥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第2页,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藏本。
标签:中国大学论文; 中国英国论文; 京师大学堂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南洋公学论文; 山西大学论文; 地理论文;
